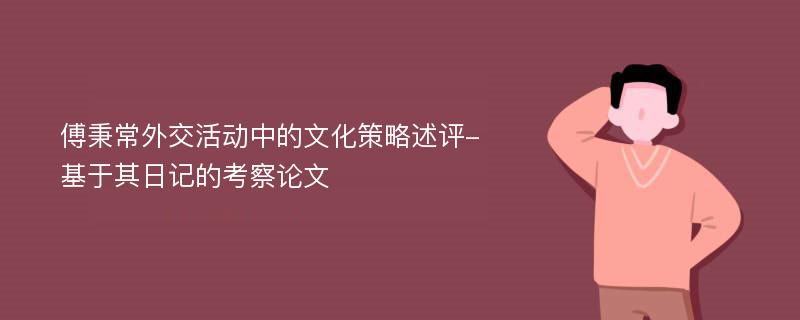
【史海钩沉】
傅秉常外交活动中的文化策略述评 ——基于其日记的考察
刘周颖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傅秉常是民国最后一任驻苏联大使,对中苏关系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傅秉常在使馆建设、馆员责任与礼仪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其本身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艺术修为给外交活动增添了一抹色彩,在被他称为“小投资、大收益”的待客方式中又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使得傅秉常能够在有限的条件下,斡旋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 :傅秉常;外交;文化;艺术
傅秉常1943年至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在此期间,有两个重要议题正在酝酿之中:一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问题,尤其是对日战略;二是国际政治关系对中国的国共权力争夺造成的影响[1]。本文所使用的主要史料是傅秉常1943到1945年的日记。学术界对傅秉常与民国外交已经有过不少研究,这些研究或是涉及傅秉常在四国宣言、雅尔塔问题中的作用,或是从《傅秉常日记》解读中苏关系,进而对傅秉常的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进行述论。本文拟从文化与生活的角度,阐述傅秉常驻苏期间的外交活动与思想,从而揭示一个外交官自身的品格和修养在外交活动中所起的能动作用。
第一步,设置结构利用和处置单元,每单元应符合100m单车道的要求。第二步,需要计算承载力指标BDP,针对双向行车道,通过测试其弯沉值的弯沉盆数据。第三步,必须了解路面破损程度及典型病害并计算其指数。第四步,进行分类判断,当段落的承载力指标小于或等于3.57,若典型病害指数小于或等于60,典型病害指数大于60,但双向路面车辙深度大于或等于18时铣刨整个路面结构。
一、文化与艺术的初步构建
1942年10月末,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在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就运输物资问题交谈后回国述职,同时也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外交难题。此时,正值中日战争处于转折期、国际关系微妙复杂之际,傅秉常被蒋介石任命为驻苏联大使。之所以确定傅秉常担任大使,与傅自身的阅历相关。傅秉常是学工程出身,从事的工作多与海关、立法以及外交相关,尤其是外交工作占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受了伍廷芳的影响[2]。早在1919年,傅秉常曾随伍廷芳出席巴黎和会,这个起点引导傅秉常走向革命,成为有抱负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此外,傅秉常担任过孙中山秘书,又与孙科交好。傅秉常担任孙中山秘书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因此傅秉常也得以与苏联方面打交道,并且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中共党员陈独秀和周恩来建立了个人关系。1938年,傅秉常与孙科从苏联募集到一批抗战急需的物资,赢得蒋介石的肯定。正是这些丰富的外交经历与人际关系使其成为驻苏大使的合适人选[3]。
(一)修缮驻苏联大使馆
1943年初,蒋介石在黄山行宫召见傅秉常,对如何处理中苏关系做了最后一次交代。日记中记载:“十二时,委座在黄山召见。彼已受寒数天,精神尚未复完【元】,因我出国,勉强召见。训示如下:(1)独山子油矿等案,因系在中国境内,故应在中国办理。(2)现在及战后与苏均应交好及合作。此种方案完全不变,因我国与苏方接壤及各种关系均应如此。只要苏方不与我不好,我当然要与之合作。(3)对于新疆问题,主权必须收回。至其他经济利便,我可予他。例如羊毛公司、伊宁铁矿问题等。只在不损失我主权范围内,在经济上可尽量与之合作。至于破坏我法律、有损主权者,则不能有丝毫让步。例如组织合作公司,我方资本应占百分之五十一等,不能变更。希望苏方能与我诚心诚意友好……(6)日苏战事必不能免,苏虽胜德,日亦必攻苏。盖德崩溃,日不能独存,故余应准备一切,以为应付。届时我愿与苏合作,与订军事同盟亦可。(7)对于外蒙领土及主权,我方应收回……”[4]18-19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中苏关系的友好与否对两国都十分重要。对战时的中国来讲,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需要国际上特别是在地理位置上与中日两国都密切相关的苏联的支持。新疆问题又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苏关系总的来讲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在这种平静之下却掩盖着激烈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国共关系与地缘政治都会影响蒋介石的对苏态度[5]。在不破坏我国主权与法律的前提下,“只要苏方不与我不好,我当然要与之合作”显示出蒋介石希望推行积极的中苏关系。提及馆务,蒋介石即“谓以前省俭不对。盖外交上用钱,系国家体面所必须,余应立即改革,场面应与英、美大使馆相同,如须另款,可径行向彼报告领取”[4]19。能够在外交中像美、英使馆那样体现出大国风范,是蒋介石的另一期望。
一个国家的外交风范体现在方方面面。为了体现中国的外交风范,傅秉常着实下了一番功夫。首先是使馆条件的改善,驻苏使馆可以看作是苏联和其他盟国看待中国的一个窗口,使馆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实力和文化礼仪。
古比雪夫的情形已经让傅秉常感到为难,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更是差强人意。所以在同年8月份抵达莫斯科大使馆后,傅秉常“即偕陈参事等到大使馆。一部分馆员仍须暂寓国民饭店”,因为傅秉常已经决定“以后大使馆职员办公地方须集中整洁,眷属一律迁出,另行租屋与之居住。公私事务须划分清楚,不可复如前之杂居一处,公私不分,男女小孩混在一起,殊不成体统也”[4]88。这样就将办公与居住分开,为大使馆留有更大的办公空间和更多的活动场所。这一改变为以后在使馆宴请各位大使、举办舞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傅秉常还对使馆内部进行了装修布置。他把遗弃的板条箱和窗帷利用起来,又请一位知名画家画了孙中山画像和蒋介石画像,并把画像挂在使馆的门厅,来访者都感觉效果很好。积极推进中苏关系,彰显大国风范,这是傅秉常作为一个大使的职责。于细微之处、行为之中,傅秉常本人认真细心的性格特征与小心谨慎的外交思想也体现出来。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傅秉常对使馆工作人员的职责要求中。
浙东“尚古淳风,重节慨”[5],使文人也常带有几分刚硬之气。所谓“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7],以会稽为中心的古越历史上坚实厚重、勇武善战的人物比比皆是,大禹、勾践等是典型例证。鲁迅在其早期著述中曾作过如是描述:“于越古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现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8],从中不掩其对越地民风的激赏之情。
通过滑道来运输粮食并不少见,但周家粮铺院将滑道巧妙隐藏于建筑内部的做法,在风峪沟沿线传统村落中只此一例。建造工匠在碹筑窑洞时,通过把河刨石进行错位拼接组合,预留出孔洞,再用石灰砂浆及黏土封闭石块之间缝隙,避免了粮食在下落时损耗过大,将石块碹筑窑洞的技艺发挥到了极致,规避了用木结构支撑,会因年久、潮湿而糟朽的风险,使得两处滑道历经百年而不坏,至今仍可以使用。工匠的创新精神及巧妙构思,对我们研究农耕文明盛行时传统村落的建筑布局及单体建筑的建造思维有深远的影响。
傅秉常首先到达的目的地是当时苏联的临时首都——古比雪夫,因德军于1941年秋刚对莫斯科进行了轰炸,各国外交使团暂驻这里。1943年8月才返回莫斯科。在古比雪夫宴请英国代办百嘉利(Baggalay)时,因“邵大使在莫斯科家具全未带来,使馆无书画一张,空空如也。不得已,勉强利用中国国画布置一室,以作饭厅”,实际上傅秉常“亦觉颇难为情”,再加上“用人训练亦不佳”,他认为“以后我国派遣外交使节,确须审慎也”[4]59-60。对比而言,“瑞典大使请Cocktail Party,地方设备固佳,食品有自瑞典带来者,女仆训练亦好”,傅秉常“更觉我大使馆之寒酸”。他在日记中写道:“现我经到各使馆与人比较,我大使馆确不及一最小国公使馆,邵先生真使我在此无地自容。现在家具又不能运来,食品又缺,我现束手无策,只自愧恧耳。”[4]64-65
还有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高跟鞋了。可是在我们本街上却不大有人穿,只有我的继母早就开始穿,其余就算是翠姨。并不是一定因为我的母亲有钱,也不是因为高跟鞋一定贵,只是女人们没有那么摩登的行为,或者说她们不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
(二)对使馆工作人员的关心和要求
大使馆规格除了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外,也从侧面反映这个国家对驻馆国家的重视程度。傅秉常改善了驻苏使馆的各方面条件,自然赢得了苏联方面的好感。傅秉常作为大使,还要负责使馆工作人员的各种问题。战时苏联政策使物品购买变得困难,食物的匮乏特别是肉类的缺少使得工作人员的生活和营养问题得不到保障。另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经济情况也不甚乐观,大使馆的经费成为又一难题。再加上日本对运输线路的封锁等,傅秉常和馆员们面临的困难重重。
1943年4月份的一个中午,傅秉常“赴郊外市场,苏制本不许私人贸易,但迩来战时社会之需求,特许此种自由贸易之小市场。古市设有两处,均在郊外,汽车约20分钟始达。所谓市场,系在郊外空地,人之拥挤无以复加,而所售之物品均系贫人自提出来,种类多系日用所需,如鞋、旧衣及零星小物,其残破程度,欧美最贫之区域人民所不要,即中国旧货摊所陈列者,亦较好万倍,其人民之贫苦可见一斑。有一老妇携有面包三块出售,有二少年竟抢其一,老妇追及抢回,旁立众人目之,竟不加干预,绝不责骂少年半句,亦不共帮老妇将少年拿送究办,一则足见其个人主义仍在下等群众心里中,不能免除,二则贫而至抢食,众亦不深责。苏联抗战期间之辛苦,与我亦伯仲也”[4]47。而自6月份起,“食粮分配之定量再行减少”,“每月只能购肉三公斤,面包亦减三分之一。”傅秉常“食量不大,尚可足用,但用人则极苦耳”[4]72。因此,傅秉常不得不经常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物品。1943年6月,“英大使馆转来阶平在英代余所购之公事皮包、药品等,英虽在战事期间,出品仍佳,价格亦不昂。余自抗战以来,数年间未见精品,得此喜极,有如小孩之获玩具,自笑亦自怜也”[4]70。像这样的事情在日记中多有记录,由此可见傅秉常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私人关系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
2.猪传染性胃肠炎(TGE)。各年龄的猪均易感,以2周龄以下的猪多发,且死亡率较高,仔猪吮乳后常出现呕吐,不久出现剧烈腹泻,排水样黄色或灰色粪便,常有未消化的凝乳块,恶臭,日龄越小,病程越短,死亡率越高。
为了做到上述几点,也为了外交的方便和更好地了解苏联,傅秉常不仅自己学习俄语,还让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学习俄语或者一门外语。傅秉常学习俄语极为认真,初学时每星期教员来3次,每次1个小时。自习则每日逾2个小时,2个月后即识字约500个,可阅读报纸上短篇浅近新闻。但俄文变格之多,为世界文字之冠,记忆不易。傅秉常认为如果不稍为彻底改革,实为其进化之大障碍[4]73。3年时间里,傅秉常一直坚持学习俄文,并且从1944年8月份开始将学习俄语的时间改为周一、二、四、五,日记中一般会简单记载:“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一时半,学俄文。”有时因工作需要,也会改成下午。有时仅仅记载一句“学俄文”,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在3年的日记里时常出现,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是如此从未间断。偶有记载更多的地方,也是关于如何改进学习方法以期取得进步。1945年1月3日,傅秉常在日记中写道:“余决意改变方法,遇有不记忆之字,便作为生字,重新练习。”2月1日,“开始用普斯金(Pushkin)之The Queen of Spades 为课本。变更方法,以小读熟习为主”。5月11日,“自本星期其余已变更方法,用Turgenev ’s ‘Acia ’为课本,每日只读十五行,由马教员先读,余随之,后复由彼读,余只听。然后用该十五行之材料,与马教员作为问答,同时温习文法,用Fourman’s ‘Teach Yourself Russian’,并读报纸小许,此法试验后尚佳”[4]398,417,482-483。由此可以看出,在学习俄语两年多后,傅秉常仍然孜孜不倦,以求上进。其中虽不乏因年龄、记忆力下降以及公务繁忙的因素导致学习吃力,但其精神与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保持着一贯的细心与认真。再比如傅秉常对挪威的评价:“虽人口只三百万,但因天气、地理种种关系,养成其善于航海及勇敢耐劳之习惯,确为欧洲之优秀民族也。”[4]47像这样细致入微的观察,对一位外交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国际交往中尤为关键。由于傅秉常的稳健,身经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过程,在外交礼节上从未出过小毛病,很得苏联朝野人士的尊敬。这种专业的素养在傅秉常举办舞会和宴会招待同盟国的各位大使中可见一斑。
二、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
在苏联的生活有时枯燥无味,傅秉常自身对文学和艺术又有一定研究,这些就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傅秉常认识了不少苏联的知识分子和知名艺术家,这些人也成为傅秉常宴会中的常客。
(一)文学与艺术
除了爱好文学,傅秉常对艺术也有研究。傅秉常的母亲麦太夫人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以绘画纸扇闻名。傅秉常显然遗传了母亲的艺术才能,他在就学期间“对于西法的铅笔画和木炭画等,也颇为擅长”。1929年,傅秉常为如夫人宋琼芳所绘的一张炭笔画,仍保留至今。1945年,傅秉常与随员九次游俄画院,观察与研究情感派渐变为现实派作家、印象派作家、近代作家以及雕刻家作品。除了绘画,傅秉常对于摄影也颇爱好。他在20岁出头开始学摄影,这也成为其一生的兴趣。早在1923年,傅秉常与两位友人组织了“景社”,这是华南最早的业余摄影社之一[4]。傅秉常的摄影作品《囿》即刊登在中华摄影杂志上。此外,他的作品还在《良友画报》上登载过。1945年 8月26日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其对绘画和摄影的钟爱之情。是日,傅秉常在奥丹那也之别墅休息及摄影,他认为此“为数年来所仅有之真休养。看屋之老仆白须捶胸,诚为摄影及绘事之良材也”[4]523。
傅秉常到苏联后仍保持着逛旧书店的习惯,并且认为此为其“在此之唯一消遣”[4]286。1945年1月6日上午,傅秉常“偕承庸同出旧书店,获旧书数本,内有一八三三年版Tomas Moore ’s Letters &Journals of Lord Byron ,甚佳,Carlyle全集亦不错”。1月24日,上午又“偕胡、钱两随员同出旧书店及商店,只得旧书数本”。3月19日下午“在旧书店购得一佳本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读之不能释手。此翁为中古时代(死于1123,享有高寿)伊朗名人之一,于天文、算学均及显著,代数即为其所发明其诗更为世所崇奉。彼与首相Nizam al-Mulk友善,那显贵时,彼只要求资助研究学问,彼诗中所言,多为人生哲学,与老子相同”[4]400,415,444。虽然傅秉常很少记载每次去书店购买的是什么书,但是从其日记中可以猜测一二。日记中不时出现“连日读”三个字,后面即介绍了书名、作者以及大体内容,还包括傅秉常的一些见解。例如是年1月14日,日记中记载道“连日读伯聪夫人(郑毓秀)自传My Revolutionary Years 。彼人确有精神,惟未免过于自夸。古人对人主隐恶而扬善,今人则自己为之,似于古礼教不符。余少时本有志将欧西作传之体裁介绍与我国,盖亦以人为鉴,足以自省之意。但观迩来自传多自夸张,大言不惭,觉救国家救人类在彼一举一动,即闺房猥亵,亦目为救世之举。此种人性好夸张之弱点,是否应加以奖励,殊属疑问。是以余究竟将来宜多作传否,现反不敢决也。”1月28日,又写道“连日读Summer Welles ’The Time for Decision 。依照其一九四〇年代表罗斯福赴欧时与Ciano 所谈经过,则Ciano 之见解确较墨氏为高明,与余从前对Ciano之观念不同。是则墨氏实对其婿不住,且误其国,Ciano欲挽救而未能而。彼(Welles)对远东民族解放之主张,对国际安全组织之建议,均甚有见地。至分割德国为三区,则世界学者多所批评,目为全书最可訾议之一节。总之,该书内容异常丰富,以其掌握美国外交数十年所得,自多良好之见解,至其对美于珍珠港以前之外交为之辩护,似未免稍过而耳。”[4]405-406,416傅秉常还曾与阿里克教授畅谈中国文学,阿里克教授是苏联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专家,对中国文学及哲学都有研究,而且翻译了《聊斋志异》《唐诗》及《古文观止》,现又从事翻译《文选》,并拟译《史记》[4]506。与常人不同的是,傅秉常读书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从中探索和发掘更多的信息,及时了解各种动态,整理成情报汇报给国内。
傅秉常平日喜欢读书买书,每日早晚必读书,很少间断。他读的都是政治、经济和法律书籍。有空时,他还喜欢逛旧书店,往往逗留一两个钟头。吴述彭曾每月代傅秉常付上海洋商专售外文书籍的书店购书费约300港币[6]。傅秉常经常阅读英文古典名著,一辈子研究英国文学。南京总统府立法院大楼中还保存着他的一些笔记本,记满了佳句和散文[4]。从本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傅秉常英语流利。1943年1月1日至10日的日记,即是用英语所写。虽然是驻苏大使,但其英语上的优势在外交活动中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傅秉常“见外部代理秘书长Zakin”时,“彼能操英语,人亦和蔼”[4]32,这无疑在交流中提供了方便。
拜访或者回访各国大使是常事,因为在与各国大使的交谈中可以获得较多直观和潜在的信息。同样,各国大使交流时的态度也表现出其对相同事件的不同看法,从中可以窥测出他们及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对未来局势、国际关系的些许预测。据傅秉常日记记载,在3年多的时间里,他正式会见美国大使39次,英国大使27次,这还不包括那些非正式的聚会[1]80。仅1943年一年的时间里,傅秉常拜访、回访各国大使就达几百次。
傅秉常对使馆工作人员的职责与礼仪要求有着自己的见解。1943年3月27日,傅秉常拜访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N.M.Lifanov,“各国大使须拜访外部司长,系苏联创例,尽进不回拜,于国际礼仪未免失态,但此系苏联作风,入境问禁,入乡随俗,不得不已”。但是傅秉常认为,惟此种自高态度令人不快,于国无益,于事无补,其当局似过失策也[4]41。况且在外馆工作与国内本部不同,在部所办日常事务,政府已有一定政策与指导,是以职务虽繁多,责任反而小。在外馆则不然,其职务系观察所驻国之外交、政治、社会情况,作忠实之报告,本国政府才可在此基础上定其应付之政策,观察苟有错误,则影响异常重大。因此,傅秉常对职员有着明确的要求:“(1)增强自己之观察能力,即力求增加其学问,例如世界政治之动态、各国经济情形之异同、社会思想如何,及其文化之优劣比较,均须研究,不独数本国际法及外交礼节及惯例已也。(2)对驻在国作最深切之研究。每一国家均有其历史及环境之关系,故其外交政策亦不能不随之而转移。是以研究一国之外交,不独须研究其本国之政策,即其最重要之对手亦应研究。例如苏联与英、美及东欧各小国关系,苟吾人仅悉苏联情形,而不知英、美情况,或东欧各小国情况,则只听一面之词,亦不得其关系之实况也。其民族之历史、人民之习惯风俗及思想文化,须十分明了。总之,在外馆人员之职务,其重心在于研究,而此种工作不易表现,且须具有耐性及求学之良习,与在部工作人员所须具者不同也。”[4]324-325这里面不仅涉及到职责要求和礼仪要求,更关系到一个外交人员的情报搜集与分析能力。
(二) 宴会和舞会
舞剧是有闲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记里傅秉常有多次观看舞剧或者话剧的记载,在刚到苏联的第一年时间里,傅秉常观看次数就有16次。有的记载一笔带过,有的则详细描述了舞剧表现的内容、演出设备的质量,并且对演员的表演功夫进行了评价。傅秉常在日记里2次记述了《前线》。第一次是1943年3月9日递交国书后,“晚上观其著名之新剧《前线》Front,著者为新文学家A.Korneichuk,描写上级军官之不求新知识及腐败情形。有疑为指Voroshilov者,但在此死战中,将军队此种腐败情形写出,想真有特别用意,谓为向某军官或某部分军官作为警告,亦在情理中也”[4]30-32。同年9月14日,傅秉常有机会接触到《前线》的作者干尼触(Alexander Korneichuk)。据干尼触讲,他对白党作战英雄印象深刻,年少在家乡时曾见军官中有中国人充连长,乘白马做指挥。该连中某华人还赠中文信纸以作留念,只是现在家园被德军占领,纪念品怕是已无存。他还目睹梅兰芳演剧,对于其手及面部表情尤为佩服。在傅秉常与之谈到中苏亲善时,干尼触深表同情[4]97。
举办宴会和舞会可以扩大接触与交流的范围。一方面从客人来看,除了上文提到的文学家与艺术家,重要的客人则是各国大使。一个国家大使的出席与否,以及在宴会上待的时间长短,暗示着两国关系的和缓。另一方面从举办的次数来讲,1943年8月,即从古比雪夫返回莫斯科后的3个月,傅大使举办了4次聚餐会和2次舞会。为纪念双十国庆节举办的那次舞会,使馆共发出400份邀请函。1944年中国大使馆共举办了15次宴会和5次舞会。1945年举办的宴会达19次,舞会11次。中国大使馆的宴会、派对、蒙古热包饭在各国使团中颇有名气。傅大使以这种方式招待他的客人是“小投资、大收益”,在同盟国使团中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宴会创造了一个众人参与互动的空间,很多信息与情报即是在这样的场合中得到的。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艺术修养为傅秉常的外交活动增加了筹码。在外交中,这些因素变成傅秉常个人教养和修为的外在表现。因此,傅秉常结交了苏联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对于中苏关系的影响或许没有政治家与外交家来得那样透明有系统,但很好地补充了政治互动所没有的意识形态的交流[4]。
傅秉常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他和胡随员一行到郊外别墅与诗人、作家以及画家交谈宴会的情境。1945年1月2日,傅秉常与英国记者以及胡随员至郊外汶斯公路旁之别墅,这里“环境极佳,虽在深冬,而积雪盈尺。窗外远望,地天一色,园内松林苍翠,铺以银花,我国内不易得之佳胜。主人款待甚殷,渠夫婿本为名作家,剧本盛行一时,对德抗战,疏散至古比雪夫,因返莫为其夫人取衣裳被炸死,遗下老母及儿女,尚有遗腹之女,现已两岁。渠本美国籍,曾现身舞台,知识甚高,故在此区一带,与名作家异常相得。别墅一甚佳,共有大房十余间,书楼甚好,花园甚大。”附近有小山坡,“成天然之滑雪场,余等以其女孩带来之小雪车,由上滑下,久试始能,虽频翻滚,然亦佳运动。三时返别墅,主人复备午餐,餐毕已五时,天已齐黑,余等遂兴辞而返”。从这段文字可以想象苏联冬季郊外的雪景,以及傅秉常和随员忙中偷闲的愉快心情。1月21日,傅秉常在Afinogenova夫人之别墅宴请苏联诗人巴斯顿诺(Pasternak)、作家伊凡诺夫(Ivanov)夫妇、作家Neeling夫妇,及名导演Tess夫妇,请彼等吃火锅,异常欢洽,极言中苏之文化。傅秉常认为此种文化之接触,于中苏友谊关系异常重要者也。2月11日“上午十一时,偕胡世杰夫妇及胡随员赴阿夫人别墅,苏联作家Lipatov及英使馆Revey均在。与Lipatov作家谈,彼本向在列宁格勒,抗战后往西比利亚各地,业经3年,不久将回列城。彼力言中、苏民族共同处之多,均系自足之国,人民亦恶战争者,是以彼等自然视日本为其可能之敌云云。大约均系实情,现只因环境关系,多未便公开表示耳”。3月25日,上午11时,傅秉常再次偕胡随员赴阿夫人别墅,将李译中国诗50首送巴斯顿诺(Pasternak),并与谈中国诗格及诗之源流。巴斯顿诺为苏联近代最有名之诗人,性情和蔼,对唐诗研究不少,与傅秉常一见如故,傅亦甚乐与交游[4]397-398,411-412,446-447。正是这样非正式场合的社交活动为傅秉常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从日记中可以感觉得出他与苏联各界人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关系。傅秉常50岁生日的当晚在使馆招待同寅和使团,及苏联各界人士稍熟者,名舞星、女雕刻家、画家、作家、导演、诗人、英美记者均到,宾主尽欢,直至翌晨一时半始散[4]425。
作为平衡所涉不同利益的有用工具,在投资条约中列入文化例外或冲突条款,在实践中已有先例。例如,2005年5月28日,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以下简称TPSEP),建立自由贸易区,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TPSEP认识到有必要促进旨在保护有关国家文化遗产的文化政策,该协议中规定了针对文化方面的一般例外的情况,包括有形财产(考古和历史遗址)及其无形财产(创造性艺术),目的在于保护具有历史或考古价值的物品或特定地点。
三、情报搜集中的文化因子
所有的外交活动归根结底还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美、英、苏和中国都有着各自的打算——美国一方面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以减少美国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中国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苏联以对日作战作为筹码确保在中国拥有的特权,同时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国民政府既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又想要确保中国的主权,同时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傅秉常正是在这样扑朔迷离的国际政治、外交背景下上任的[7],情报的搜集工作就变得尤为重要。
在傅秉常招待各国大使的同时,他也受到来自苏联方面及其他盟国不同程度的招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Zotov曾招待傅秉常一行参观古比雪夫工业大学,先由校长介绍该校情况,然后到教室参加听讲,继又参观其化学室。参观完毕,返回校长室,向两教授询问学校情形,大多问题均不敢答,即学生数目、每班学生多少,亦不敢言。有人讲若是问苏联有儿女若干,恐怕也要请示莫斯科,始能答复。参观缝纫机厂时也遇到类似情形。据瑞典使馆秘书告知,参观工业大学前该校已准备一星期,学生如何表现也有所训练[4]62-64。
在这种条件下,与各个国家的大使保持相对良好的交际就显得很重要,特别是与英美大国的大使。傅秉常本人与英国大使卡尔,美国国务卿赫尔、大使哈尔森、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托洛夫等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3年初到古比雪夫,傅秉常“往拜访英卡尔大使,旧友重逢,相见甚欢”。日记中继续写道:彼首句问余:“汝因何来此?”余笑答曰:“我亦不知,大约亦如汝一样耳。”相与大笑[4]32-33。同年6月14日,卡尔大使应傅秉常之请,查佐藤赴莫任务。两日后覆电,“谓佐藤确系因日扣苏船事被召赴莫。缘美国转让与苏之商船共十五艘,中有六艘被日本停止检查,结果扣留两艘,故苏向日提出抗议。此事莫洛托夫已通知美国大使斯坦利云云”[4]70-71。卡尔大使如此帮忙,令傅秉常甚为感激。
情报的来源有很多:一是来自各国的广播、报刊;二是使馆武官的调查工作;三是傅秉常通过自身关系所得,包括与各国大使的交流,举办宴会和舞会,还有就是私人关系获得。上文提及的阅读各类杂志和书籍即是其中一环。傅秉常连日阅读美联社驻东欧主任柏嘉所著《匈都大本营》一书。该书“历叙一九三九——一九四四年巴尔干各国,及波兰、土尔其之政治外交、军事情况,及英、德、俄在各该国活动情形,足参考之资料甚多。彼对德固多将其阴谋[暴]露,而对英政策亦颇多批评,详述各该国腐败情形及领袖无能、人民智识低落、政治佳话尤多,全书尚佳”[4]420。再如傅秉常从苏联《劳工报》上所载拉铁摩尔最近出版之新书得到的信息:(1)美应对苏关于远东事采退让之态度。(2)共产主义在远东应占有其他地位。(3)中共军队不必统一于中央。(4)中国事由英、美、苏三大使共商决定。(5)召集英、美、中、苏四强会议,商决中苏关系。(6)外蒙应为各民族独立之标准。(7)中国在新疆应停止其压迫缠回之政策,而仿苏联对Uzbek等之扶助政策云云。傅秉常认为拉氏之写此书,自系最不道德之举,盖拉氏既充中国政府顾问,为委员长所信任,因此而获悉内幕,而忽而利用此种材料反对中国政府,自无道德可言。美国人大都如此,自不足怪,而苏联登此,自有其用意,自应万分注意,其所选择之数点,更足为吾人之参考者也。总之,吾政府应明白世界大势所趋,急图改革,否则前途实足忧虑者也[4]436-438。分析整理情报并作出相应的判断,而后及时将情报传递给重庆,是大使馆最重要的任务。在传递过程中并不总是顺利的,由于技术和设备的问题,有时一封电报时隔几天才到。在签署四国宣言时,傅秉常就是在签名的最后一刻才获得授权。由于时间紧急,傅秉常本来计划假称已经获得签名授权。类似的情形在雅尔塔协议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署时再次出现。进一步讲,美、英、苏三大国秘密会议的内容一直对中国保密,直至与中国谈判前才告知,这也印证了一点——弱国无外交。
3)在场区地质条件适宜的条件下,采用柔性垂直防渗系统,可以快速、有效地实现污染物的阻隔,结合封场技术,可将垃圾进行三维立体阻隔,形成1个独立的地质单元,确保消除简易填埋场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四、结语
实际上,傅秉常所能够决定的事情是有限的。随着伍氏父子的相继离世以及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反目,傅秉常的政治优势也不再那么明显。再加上由于与孙科交好,傅秉常被视作“太子党”,而孙科在政治上已经处于边缘化。这些政治上的优势,在出使苏联前已然变成了劣势。傅秉常与外交部长宋子文的关系,使得傅在出使苏联前担心宋子文不会与之好好合作[4]3。从国际因素来讲,在傅秉常出使苏联之前,因苏德战争中苏关系开始降温。所以,越是在艰难的境地,越能体现一个外交官的个人能力。在傅秉常身上,原来的优势并没有全然消失。虽然外界的优越条件不在了,但是傅秉常历年来内化于心的素养不会变。以往良好的教育和丰富的经历,使得傅秉常已经熟悉并且清楚如何调适和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应对政治变化。
当然,本文不能否定在国际关系与外交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旨在说明一个优秀的外交官,在临危受命时所能发挥的比较关键的作用。从四国宣言到雅尔塔协定,美、苏、英三大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以中国的权益作为谈判的筹码,再次体现了一点——弱国无外交[7]。傅秉常及其他职员能够在艰难的境地,从大局出发,斡旋周折,忍辱负重,也体现了外交官坚定的爱国精神与突出的外交能力。从《傅秉常日记》还可以看出蒋介石的一些对外政策,政治外交的层面当然是首要的,生活的、文化的层面也不可忽视。从傅秉常的所见所闻,我们可以窥见不同国家外交大使的表现。毕竟政治的世界从来都不只是政治的,它还牵涉到许多个人的、心灵的、实存的、情感的、人生观的层面。本文之所以特别强调外交中的文化与生活这个面相,是因为即使是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也离不开真实的生活[8]。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傅秉常的外交,其实傅秉常在立法中也功不可没[9]。在祖国不断强大的今天,大国外交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希望拙文能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所启示和帮助。
参考文献:
[1]傅铱华.雅尔塔远东问题协议重探——以傅秉常为中心的讨论[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79-82.
[2]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33.
[3]左双文.傅秉常外交活动及外交思想论述[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09-112.
[4]傅锜华,张力.傅秉常日记:1943—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596-597.
[6]吴述彭.我所知道的傅秉常[G]//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76.
[7]叶永坚.傅秉常与美英苏中《普遍安全宣言》[J].档案与建设,2010(12):42-43.
[8]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10.
[9]刘昕杰.法律不离社会:被遗忘的傅秉常[G]//何家弘.法学家茶座:总第39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143-144.
A Review of Fu Bingchang ’s Cultural Strategy in His Diplomac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His Diary
LIU Zhou-ying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China )
Abstract : Fu Bingchang is the last ambassador to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In addition, Fu Bingchang has his own unique insi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bassy, librarian responsibility and etiquette. Its own good literary literacy and artistic cultivation have added a color to diplomacy, and gained a lot of intelligence in the way of being a “small investment, big income” hospitality. These enable him to mediate in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limited conditions and to play his own role.
Key words :Fu Bingchang; diplomacy; culture; art
DOI: 10.15926/ j.cnki.hkdsk.2019.03.004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10(2019)03-0019-07
收稿日期 :2018-11-15
作者简介 : 刘周颖(1993— ),女,山东昌乐人,硕士生,主要从事近现代史研究。
标签:傅秉常论文; 外交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