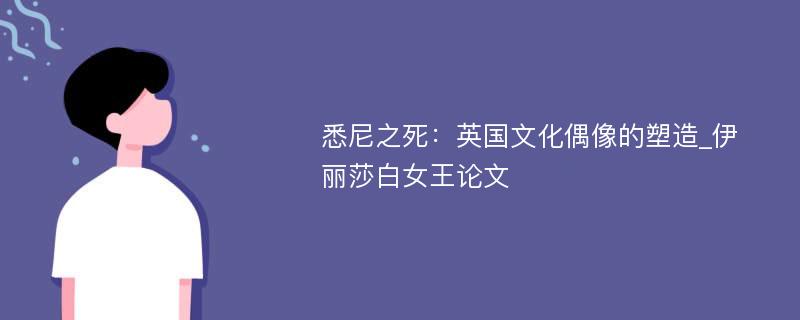
锡德尼之死:一个英国文化偶像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之死论文,偶像论文,文化论文,锡德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的形象在他早逝之后历经多次转变,直至19世纪被塑造成了一个耀眼的英国文化偶像。①理查德·希尔勒在论著《菲利普·锡德尼爵士:文化偶像》中提出,锡德尼生前身后都满足了人们对理想绅士的期望,因此“他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人都更全面地代表一套价值观”②。爱德华·巴瑞的《锡德尼的塑造》则把研究重点放在锡德尼的作品上,提出“锡德尼传说的构建者远不如他本人在作品中对自己的构建有趣和‘真实’”③。虽然约翰·高尔斯的论文《19世纪锡德尼传说的发展》对19世纪前的锡德尼形象的情况未置一词,④但锡德尼为什么会被偶像化,各种权贵或政治势力在这个偶像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其背后的动机又何在,这一系列问题对解释锡德尼形象偶像化的根本原因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锡德尼的偶像形象早在他生前就开始被构建,但直到他逝世之后才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出色才能,锡德尼自幼就被家族及相关欧洲势力⑤寄予厚望。在1568-1578年间,欧洲大陆尼德兰的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十七省和西班牙之间内战频繁,联省多次向英国求助。⑥锡德尼热切渴望参战,希望能建功立业,但伊丽莎白女王不愿向欧洲大陆的胡格诺教派或者荷兰提供实质性援助。⑦1578年,女王再次拒绝施予援手,锡德尼备感受挫,他在给休伯特·朗格的信中写道:“正如您所看到的,我的笔墨显然已经凝滞,我的思想本身即便曾经有过一丝价值,也开始因无聊的嬉戏而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力量。倘若没有机会为了公众利益而运用我们的思想,又有何必要让各种知识激起这些思想呢?”⑧锡德尼抱怨没有机会让他的思想服务于“公众利益”,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的早逝却为各方权贵提供了机会,其中既有女王,也有他声势显赫的家族。可以说,在塑造英国文化偶像的意义上,他对“公众利益”是有所贡献的,而锡德尼本人似乎也早已预言了自己身后名声的形成过程。 在《为诗辩护》中,锡德尼指出,建构历史的过程不失虚妄,历史学家“背负着鼠咬虫蛀的古籍,将自己的权威大多建构在别人的记载上,而那别人的最大权威只是建构在值得注意的传闻的基础之上;他们忙于调和异说,从偏爱中提炼真实”⑨。这番话里的“真实”正如近代早期英国文学研究者阿兰·哈格尔所说,“仿佛是指传闻轶事和著述中他本人历史形象的某些素材来源”⑩。路易斯·蒙特若斯甚至还提出,锡德尼早在去世之前“就被他的家庭、朋友和政治联盟者神话化了”(11)。比如,锡德尼从17岁到20岁在欧洲游学,所到之处无人不被他独具一格的个人魅力和渊博学识所倾倒。锡德尼研究专家约翰·巴克斯顿用一个问题总结了锡德尼人生的这一阶段:“那个1572年春从英伦出发的17岁男孩,在旅居欧洲大陆的三年时光里,为什么能够从意大利到低地国家,从法国到波兰,收获赞誉无数?直至马尔伯勒在欧陆参战的年代,尚无其他英国人可与之媲美,在英国诗人当中唯有拜伦可相提并论。”(12)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更多证据,但其中一个解释或许就是拉斐尔·福尔科所说的:“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中,锡德尼之后的那一代朝臣所继承的锡德尼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他举行的隆重葬礼和15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量挽诗。”(13)锡德尼逝后被尊为“扎特芬英雄”和都铎王朝的典型领导者,几乎所有传记作者都继承了关于他的传说,而构建这个传说的,与其说是他的生,不如说是他的死。 锡德尼之死,是其政治和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各方势力大肆利用锡德尼之死,或有意视而不见,或有选择性地大张旗鼓,以达到各自的宣传目的。事实和虚构合谋构建了一个关于锡德尼的传说,伊丽莎白女王把他塑造成完美的牧羊人骑士,以此对朝臣进行有效控制,同时用盛大隆重的葬礼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审判和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血腥事件中转移,锡德尼不再是生前那个备受多疑的女王排斥和疏远,郁郁寡欢、壮志难酬的朝臣。锡德尼之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则为了唤起众人对其原生家族的记忆,重振家族雄风,以作者、编辑和恩主的身份,把他的形象从最初挽歌中的战士和恩主转变成诗人和为新教事业抛洒热血的殉教者。19世纪以降,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经济取代了以往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活形态,也就在这时出现了对骑士品质和绅士精神的追求,这是锡德尼传说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英王乔治三世对英雄主义的追求也为传说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锡德尼的形象作为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关键性符号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扩张主义时,他最终被塑造成了耀眼的英国文化偶像,即具有骑士风度的完美绅士典范。 伊丽莎白女王出于政治目的主导了锡德尼形象的第一次转变。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事件来了解锡德尼在伊丽莎白女王宫廷里的地位。其一是“网球场事件”:锡德尼一出生就是母系家族中莱斯特伯爵和沃威克伯爵两个爵位的继承人,但是期望中的爵位总是如水中月镜中花一般可望而不可即。游学欧陆时,法王理查九世为他加封了一个荣誉贵族头衔“锡德尼男爵”。锡德尼传记作者迈克·G.布勒南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对于臣民获得国外君主分封头衔之类的事“素来敏感多疑”(14)。因而,当锡德尼跟牛津伯爵因使用网球场而发生争执时,女王便不失时机地警告他,尽管他拥有声名远扬的法国荣誉贵族头衔,但是在她的眼中,“他依然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绅士……他应当谨记伯爵与绅士之间的区别,下级应当对上级表现出尊敬,君主有必要维护他们所有的行为”(15)。虽然女王最终给锡德尼加封了爵士头衔,但那也只是为了让他够格代表缺席的欧洲卡西米尔大公(Prince Casimir)参加在温莎城堡举行的嘉德骑士受封仪式(see Sidneys:88)。 其二是“安茹求婚事件”:1579年,伊丽莎白女王已46岁,这时在她和法国安茹公爵之间似乎还存在联姻的可能性。长期以来,锡德尼的舅舅莱斯特伯爵是女王唯一宠爱并可能下嫁的本国朝臣,特殊的地位让他多少有些不可一世,朝中早已有人因他对女王施加影响而深恶痛绝。安茹求婚一事公布后,派系斗争进一步加剧,莱斯特集团有计划地采取一系列行动,反对女王和安茹公爵联姻。约翰·斯达布什出版恶毒攻击安茹的小册子,称信奉天主教的安茹为撒旦的化身:“这条老奸巨猾的毒蛇化作人形,口含尖刺,绞尽脑汁勾引夏娃,如果她被勾引,我们或许要失去英伦天堂。”(16)三个月之后,在伦敦西斯敏的集市上,斯达布什双手被斩。关于联姻之事,用朗格的话说,锡德尼也“被那些他不得不服从的人命令上书女王”(Correspondence:1013)。在慷慨激昂的《致女王书》中,锡德尼声称自己是女王最忠实的朝臣之一,热切渴望向她进言(see Sidneys:78)。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在联姻问题上,任何违背女王本人意愿的反对之声非但徒劳,而且十分危险。朗格为锡德尼的安危感到忧虑,并相信后者很可能被迫离开祖国(see Correspondence:944)。他的推测合情合理,因为女王一旦与安茹成婚,锡德尼和莱斯特一派在朝中必然处境险恶,远离英伦流亡异乡将是唯一的选择。锡德尼本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站在反对派一边的坚决态度“让自己不仅远离了女王的恩宠,也把仕途置于危险的境地,甚至很有可能自毁前程”(Sidneys:42)。 的确,锡德尼生前很少得到女王的恩宠,正如他在离世前一年给岳父、国务大臣沃尔辛甘姆的信中抱怨的那样:“女王是多么习惯于把任何事情都朝着不利于我的方向解释。”(Correspondence:1214)幸运的是,“在政治上的无能为力,并没有让他失去其他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17)。锡德尼个人政治生涯上的不幸成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幸事。他在去世之前,从未真正有志于做一名诗人,只是在从政愿望一再受挫时,才转向写作,并于1578-1584年之间完成了短暂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为诗辩护》,被称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又因《阿卡迪亚》对后来的英国小说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而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但他本人却在《为诗辩护》中戏谑道:“我不知道由于什么不幸,在我这并不老迈、并不闲散的岁月里,无意中竟盗得诗人的名号,而被激动得要有所陈述,来为我那不是有意挑选的行业有所辩解。”(18)生前被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疏远这一事实,一方面成就了锡德尼的名山事业,另一方面也丝毫不影响女王在他身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他塑造成为一个楷模形象。尽管他为之献身的那场战争既非为了宗教事业,也非因为自由的缘故,但是女王依然在其主要宣传专家亨利·李爵士的帮助下掀起了一股崇拜锡德尼的热潮。 对于伊丽莎白女王而言,维持欧陆各派之间的力量均衡至关重要:“如果法国和西班牙势均力敌,英国就可高枕无忧。倘若平衡遭到破坏,她就必须介入,站在弱势的一边。如果有可能,英国的介入必须通过个人或者国外当局来进行。”(19)在1585年之前,伊丽莎白女王既无意直接援助反抗者,也不认为自己与荷兰的加尔文派之间有何密切关系,更不倡导把荷兰建成信奉加尔文宗的独立国家。1585年,法、西两国平衡深陷危机,女王决定公开支持反叛者,向他们派遣援军,她任命莱斯特伯爵为统帅,锡德尼负责驻守弗拉辛要塞。(20) 因此,英国介入“荷兰反叛”,正如西蒙·戈罗恩维尔德指出的,是“在高度复杂形势下的一个不成功的插曲。‘反叛’不是为了某个单一目标进行的斗争,而是一场有着多重目标的战争,其中不同的组织或个人都有着各自的目的”(“Course”:65),他们仅有的共同点就是“不喜欢菲力二世,或者他的某些政策”(“Course”:61)。例如,莱斯特伯爵向来狂热主张英国向欧陆新教徒施予援手,他“在来到低地国家之前,事先构想的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真正的信仰而战,这是一场必须根据古典骑士规则进行的战斗”(“Course”:63)。锡德尼在女王的宫廷中长期受到压制,一直渴望奔赴欧陆,投身反抗西班牙侵略的军事行动。这种抱负既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又能够满足他的个人愿望,证明自己是尚武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除此之外并无更深层的意义。两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对锡德尼参战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福劳德指出,“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多人丧生,但是在这些如此疯狂地抛掷生命的人当中,就有菲利普·锡德尼”。约翰·理查德·格林虽多少有些夸大这场行动的重要性,但他采用了相同的词汇来表达锡德尼行为的荒谬和虚无感,说锡德尼“是为了在弗兰德斯挽救英国军队而抛掷自己的生命”(see “Nine teenth”:258-259)。 锡德尼身后被塑造成完美的骑士,因为骑士形象对女王加强统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21)为了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女王需要借助理想的骑士形象来“对她的一些急躁莽撞的朝臣加以控制”(“Exemplary”:4)。在整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骑士品质和骑士故事都是宫廷诗歌和娱乐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因为它们对于再现和颂扬皇室贵族的权力有独特的作用。(22)女王继位的合法性曾一再遭到质疑,全国各地多次出现叛乱,反叛者企图推翻统治,因此女王必须千方百计让朝臣、贵族和平民臣服于她,而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宫廷里大力提倡骑士文化,经常在朝臣当中举行骑马持矛的比武活动,鼓励他们把宫廷看成骑士风气盛行的地方。在都铎王朝的宫廷里,这类活动颇为流行,观者中既有本国臣民,也有外交使节。在比武中夺魁无疑代表着令人折服的勇气和技艺,女王的祖先当年都是骑士比武场上出生入死的直接参与者,如亨利二世折戟而亡,亨利八世在一次比武中几近命丧黄泉,但其英武之姿令外国使臣折服。(23)女王不像她的先人,不能参加比武,甚至无力在比武场上奔跑,但是她重新布局,使得比武现场的焦点都集中在她这位最重要的观者而不是比武者身上。(24)在欢闹的骑士氛围中,她成为比武的骑士或朝臣们争先恐后表达忠心的对象。此时的女王仿佛幻化成一个准宗教性质的意象,就像希腊神话中主管正义的阿斯托利亚女神,或是古罗马的维斯太贞女,甚或就是纯洁的圣母玛利亚,正如学者耶迪斯写道:“粗俗的乡下人只需花费几个便士,就可以看到骑士对女王顶礼膜拜的景象。”(25)朝臣对女王的服从,必然对平民有示范作用。女王企图通过骑马比武达到的宣传目的,无论是对诗人、贵族还是平民都产生了影响。 为了达到让平民效仿的目的,女王不得不至少象征性地把她最重要的朝臣降格为自己的崇拜者。孙凤城教授指出,在骑士精神中,“爱情占主要地位,表现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为她们服务,为爱情冒险,以此作为骑士的最高荣誉”(26)。根据骑士传统,贵妇人无需对爱慕她的骑士有相应的表示,骑士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如果朝臣们成为潜在的情人,众星捧月一般地围绕在自己周围,女王是他们爱恋的对象,他们是骑士传统中患相思病的骑士,那么“服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这需要多么盛大的表演!”(27)锡德尼之死正好为女王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把他转化为这场表演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一个具有楷模意义的完美骑士。因此,不无理由相信,这股对锡德尼的崇拜热潮把锡德尼改造为完美的牧羊人骑士,“起到了抑制那些女王难以控制的鲁莽朝臣的作用”(“Exemplary”:7)。 女王把锡德尼塑造成骑士,还有助于她以某种马基雅维利方式利用他的早逝。女王巧妙地拖延锡德尼的葬礼,使之与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的血腥事件“重合”,这样葬礼就如同“烟幕弹”一般,起到了转移公众注意力的作用(see “Exemplary”:8-9)。事实上,锡德尼身后的一切安排,似乎都与审判和处死玛丽女王之间存在某种并置关系。1586年10月16日,审判庭以图谋弑君和叛乱罪,重新开庭审理伶牙俐齿的玛丽女王。10月18日,锡德尼在扎特芬去世,遗体于11月2日从荷兰运抵伦敦,同日开始悼念活动。所有的朝臣都只能身着黑色服装,举国上下沉浸在一片肃穆的哀悼气氛中。1587年2月8日,玛丽女王被处死,八天之后锡德尼盛大的葬礼隆重举行。这两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貌似巧合,实为暗箱操作的结果,正如哈格尔指出,这是“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例子,背后掩藏的是伊丽莎白女王宫廷的欺骗手段”(“Exemplary”:8)。锡德尼的葬礼被不合情理地拖延,其中一个相当确切的原因是费用问题,由于“女王拒绝提供费用”,锡德尼的岳父、国务大臣沃尔辛甘姆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凑足葬礼所需的6,000英镑。然而,女王无疑是这一盛大仪式举行日期的决定者之一。锡德尼传记作者奥斯本指出,这场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上演的葬礼,“是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国葬之前,为皇室等级之下的人举行的最为隆重盛大的葬礼,如此规模以及举国哀悼的情形,对于一个平民而言是绝无仅有的”(28)。当丧礼仪仗队穿行于伦敦街道时,人们的注意力自然从处死玛丽的血腥事件中被转移。 锡德尼之死及其葬礼,不仅被女王出于玩弄权术的目的大肆利用,而且也为莱斯特集团带来张扬其“鹰派”立场的机会。在骑士传统中,不少骑士会为宗教信仰去冒险。官方在对“荷兰反叛”的宣传中重点强调反抗“天主教压迫”等主题,因此锡德尼可以被顺理成章地定性为为新教事业而献身。莱斯特集团成员多半支持军事上的新教干涉主义,希望“在欧洲大陆上对西班牙形成联合新教军事的攻势”(“Exemplary”:3-4)。锡德尼的葬礼是一次公共表演,展示了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决心,它“通过微妙地处理死者,起到鼓舞和增强生者信心的作用”(29)。锡德尼形象的第二次转变也与此相关。 我们可以在锡德尼去世之后的纪念性诗文中发现其形象的第二次转变,这是由锡德尼的妹妹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为了家族利益而主导形成的局面。在锡德尼和莱斯特伯爵于1586年和1588年相继离世之后,锡德尼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联盟就缺乏出类拔萃的男性领导者,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603年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的儿子威廉·赫伯特(即日后的彭布罗克伯爵)长大成人,开始承担起重任。在此之前,伯爵夫人运筹帷幄,力挽家族命运于狂澜。她在走出丧兄的悲伤阴影之后,高调重返社交界,发誓要赋予锡德尼特有的荣誉,以重振家族雄风(see Sidneys:100)。(30)她通过扮演编辑、诗人和恩主等角色发起了一场运动,意在“唤起大家对达德利家族和锡德尼家族的回忆,同时庆祝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为这一支健在的主要成员”(31)。在这场运动中,锡德尼的形象从最初挽诗中多才多艺的恩主和战士,转变为诗人,最后成为新教殉教者。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继承人詹姆斯一世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对锡德尼集多种才艺于一身的评述,贯穿于所有早期的纪念性文集。锡德尼多才多艺的素质,在本质上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所倡导的,也是普适于朝臣的一种文化表达,锡德尼也因此成为了诸神的宠儿,然而,主宰各种才艺的神祇之间却无法达成和解。比如,在约翰·巴尔默的挽诗中,战神马尔斯和众神的信徒墨丘利之间发生激烈辩论,智慧女神帕拉斯接过话题伸张自己的权利,请求主神朱庇特把锡德尼奖励给她。朱庇特允诺,可是心怀嫉妒的战神马尔斯却残酷地结束了锡德尼的生命(see “Instant”:4)。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挽诗因锡德尼的各种才能被荒废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惋惜之情。(32)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在诗中为所有艺术的损失而哀叹: 你强大的马尔斯,英勇士兵的君王, 还有你密涅瓦,引领智慧者, 还有你阿波罗,拥有帕纳塞斯山上 每一种才艺的知识, 连同择彼处而居的所有姐妹 都为他哀伤悲泣。(Sidneys:97) 詹姆斯六世没有提及锡德尼的诗歌,而是盛赞他在荷兰的英雄之举和对各类学术活动的赞助。(33)事实上,绝大多数早期挽诗并没有把他视为诗人。在一首署名为“A.W.”的诗歌中,缪斯女神在悲悼,因为锡德尼再也不能为那些诗人提供赞助了: 除了阴郁的哀叹,没有旋律,没有声音。 可我心知甚明,缪斯痛不欲生悲戚不止, 看墨尔波墨涅羞愧地躲藏在一角。 可听见那细微的叹息,发自她肺腑深处? 卡利俄珀在哭泣,欢乐的塔利亚也时而悲鸣。(“Instant”:7) 墨尔波墨涅传统上是悲剧女神,卡利俄珀是史诗女神,而塔利亚是喜剧女神,锡德尼本人并没有创作过这类诗。因此,正如拉斐尔·福尔科指出的,“与其说缪斯女神的哀叹是因为锡德尼不再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创作,不如说是因为他再也不能为那些创作者提供赞助了”(“Instant”:8)。锡德尼是诗歌创作的对象而不是创作者,是阿喀琉斯而不是荷马。这是他离世之初在各种挽诗中的典型形象,诗人们的第一冲动是“用他作为倒下的骑士和贵族恩主的形象为他建立纪念碑,其次就是作为技巧精湛的纪念碑建造者来吸引其他恩主的注意力”(“Instant”:10)。 锡德尼的上述形象被套路化地呈现在他离世之初的挽诗中,1587年出版的第一部挽诗集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四年之后,锡德尼的形象发生突变,因为从那时开始,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决心鼓励他人按照她的意愿来颂扬兄长,正如1593年出版的新《阿卡迪亚》(Arcadia)中的“致读者”所言:“只要她的决心不被意外事件所动摇,所有这些努力都会继续下去,对出色兄长恒久不变的爱,让她致力于纪念他的事业。”(qtd.in “Moses”:220)伯爵夫人刻意把锡德尼转化为美德的化身,用神圣化的方式来呈现他的作品和生平,极力鼓励传记作者把他视为富有传奇色彩的圣徒,这一过程中她发挥了编者、诗人和恩主的三重作用。 首先,伯爵夫人担任编者角色,整理出版了日后奠定锡德尼文学地位的主要作品。其中《为诗辩护》和《赞美诗》(Psalms)带有强烈的新教色彩,与有关他的圣徒传记相吻合。十四行诗组诗《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il and Stella”)描写对一位已婚女人未能如愿以偿的欲望。(34)伯爵夫人授意家庭医生托马斯·墨菲特在诗歌《高贵》(“Nobilis”)中对锡德尼的这种暧昧之情闪烁其词,反而重点强调他的纯洁:“即使是在刚刚进入青春期,他也抑制住了人生那个阶段升腾而起的狂野冲动……他做到这一点,不是自己的天性如此,因为天性让他精力充沛、血气方刚、活跃敏锐,而是源于他所拥有的美德的力量,尤其是源于上帝的至善。”(35)她没有出版旧版的《阿卡迪亚》,因为书中有些内容表明锡德尼未能控制好自己的冲动,而这些内容很可能会招致对他的攻击。此外,伯爵夫人还亲自创作过多首诗歌来纪念兄长,锡德尼的形象在她的诗歌中明显发生了变化。最初,她根据早期定下的调子把他当做牧羊人来歌颂,后来则把他当做新教殉教者来传扬。这种形象也常出现在献给他的诗歌中,玛格丽特·P.韩耐指出,其中最为典型的描写就是锡德尼“为了维护神圣的教义而抛洒热血”(“Moses”:221)。 不仅如此,伯爵夫人还以恩主的身份大力推动诗人创作诗歌赞美锡德尼。这类作品中最重要的有埃德蒙·斯宾塞的《时间的废墟》(“The Rvines of Time”)、《爱星者》(“Astrophel”)和托马斯·墨菲特的《高贵》。在这些作品中,锡德尼既是诗人也是信仰的捍卫者;他是“道德楷模,行为高贵,远离年轻人常常难以抵挡的诱惑,不屑于为了变得富有而接受不义之财,如天主教徒被没收的财产,他还常常帮助穷苦人”(“Moses”:222)。《时间的废墟》颂扬整个达德利家族和锡德尼家族的联盟,而《爱星者》则是专为纪念锡德尼而作。他不再是早期挽歌中资助各类学术活动的慷慨恩主,转而成为了一名诗人。不同于早期挽歌诗人,斯宾塞把牧羊人爱星者描绘成一名才华横溢、完美无缺的朝臣,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诗歌的价值,或许他认为诗歌毫无用处,于是投笔从戎,最终命丧异邦。斯宾塞对锡德尼的委婉批评隐约流露在字里行间,正如拉斐尔·福尔科指出的,“锡德尼用战场上‘耀眼的成就’来代替对诗歌的追求,这样做的结果是毁灭性的。我们说斯宾塞持这种批评态度是不会错的”(“Instant”:15)。其实,斯宾塞从诗歌方面的损失来哀悼锡德尼,也就是在确立他不可替代的诗人地位。《高贵》是一部关于大学学习的小册子,伯爵夫人希望儿子威廉·赫伯特长大之后能够像“锡德尼家族的花朵”爱星者一样,于是墨菲特在书中把锡德尼塑造成了其侄儿可以仿效的“美德形象”。他把锡德尼的一生划分成不同的阶段,并对每一阶段他是如何实现美德和学识两方面的理想做了详细说明。 锡德尼的上述形象在其终身密友福尔克·格瑞维尔(1554-1628)的书中得以最终确定。在这本题为《献给菲利普·锡德尼爵士》(A Dedication to Sir Philip Sidney)的书中,最著名的一个片段就是描写锡德尼在扎特芬身负重伤时表现出的崇高的利他主义精神: 他因失血过多口干舌燥,想要喝水,水很快被送到他面前。他把水杯举到唇边,忽然看见有人抬着一个可怜的士兵从前面经过。士兵也是在同一场盛宴上最后一次进食,此时正抬起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水杯,这被菲利普爵士察觉到了。他滴水未沾,把水杯从唇边移开,递给那位可怜的士兵,同时说道:“你的需要有甚于我。”(Thy necessity is yet greater than mine)(36) 这句“你的需要有甚于我”此后被当成了锡德尼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而事实上他在受伤三周之后才离世,期间说过的其他话均被有选择性地忽略了。锡德尼一生中最著名的这个场景,日后被称为“格瑞维尔片段”,格瑞维尔是唯一权威的叙述者,却并非亲历者。如果没有他留下的栩栩如生的叙述,锡德尼临终前这个展现崇高精神气概的场景或许就不会进入后人的视野。“此后一代又一代的缺席目击者不仅没有对这个未经证实的场景提出质疑,还不断地增添一些格瑞维尔传记中并不存在的细节。”(37)这也许就像罗杰·豪尔评论的那样,“重伤在身的骑士所展现出的崇高精神,与他的性格以及20世纪所称颂的他的形象之间是如此吻合,以致后人如果直截了当地把它当做虚构的谎言加以拒绝,就会显得轻率鲁莽”(38)。 最后,在锡德尼形象的转变中,我们需要提及伊丽莎白女王的王位继承人、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对于锡德尼身后英名的建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Sidneys:64),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毫无缘由的。早在1575年,锡德尼欧陆游学归来后,因急于想在伊丽莎白的宫廷里崭露头角,就通过詹姆斯的朝臣约翰·萨顿爵士向当时年仅九岁的国王表达了效忠之意。在这之后,一再遭受女王打压的锡德尼家族,以罕见的“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判断詹姆斯六世很有可能在女王驾崩之后继承英格兰的王位(see Sidneys:114),于是精心维护与他的关系。28年后,当后者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时,锡德尼家族收获的季节也就开始了。詹姆斯六世不仅在锡德尼离世之初就写诗悼念他,称失去他是“所有艺术的损失”,还大力推动为他建立不朽的英名——“勇敢的新教殉教者”。 锡德尼的形象经过两次转变后在17世纪上半叶基本定型,之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一形象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流传得更为深远,直至19世纪,一个英国文化偶像终于在此基础上被成功塑造。对锡德尼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的“格瑞维尔片段”在整个17世纪并不广为人知,因为《献给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并不畅销,而两度出版发行的《阿卡迪亚》在作者介绍部分对该片段也未置一词(see “Nineteenth”:253)。不过,进入18世纪之后,情形变得大不相同,不仅《阿卡迪亚》两次再版时都全文引用该片段,更为重要的是,大卫·休谟在《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中也用专章记载了此事: 那个时代的作家把此君描述为造诣非凡的完美绅士,是诗歌或小说凭借无穷想象力所能呈现的楷模。他拥有正直高尚的品行、温文尔雅的谈吐、豪迈的勇气、博雅的学识,所有这些都使得他成为英格兰王宫中华美的装饰和快乐的源泉。女王和莱斯特伯爵把对他的赞赏全部用于鼓励天才和文学事业,因而对他的颂扬得以流芳百世。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卑微,都能够成为他关爱的对象。他在完成英雄之举后,身负重伤倒在疆场。这时有人送上一杯水,以缓解他的干渴。他注意到身旁有一位士兵,情形同样悲惨,于是喃喃地说道:“你的需要有甚于我。”他让人把水递给了他。(qtd.in Nineteenth”:253) 《英国史》在1800年之前再版达9次之多,19世纪再版30次(see “Nineteenth”:260),其影响可谓遍布英伦和欧陆。休谟的叙述虽然在语气和精神上更接近于锡德尼所处的时代,但到了19世纪,他的记载被有选择性地利用,致使锡德尼传说开始朝偶像化方向发展。 19世纪,大英帝国的版图急剧扩张,以贸易和手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经济取代了以往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生活形态。这个时候出现了骑士神话的中世纪化现象,就其本质内容而言,就是通过有选择性的怀旧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价值观。约翰·高尔斯指出,当时骑士风的盛行不只是英国人沉迷于骑士精神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种神话结构,许多英国男女试图用这种结构来使他们的社会有序化,使他们在那个社会中的作用合理化”(“Nineteenth”:249)。 与此相应的是,一套与锡德尼传说相关的价值体系得以形成,如自我克制、谦恭有礼、换位思考、珍视荣誉、拒绝欺诈、在困难面前不屈不挠、积极乐观,等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867年出版的《阿卡迪亚》的前言中看出: 他热情、勇敢,明窗般透亮,优雅得体,无论是在赛场还是战场上都毫不例外。他既是造诣非凡的学者,又是才艺出众的骑士。他热爱语言文字,慷慨大方,勇于牺牲自己的利益,道德高尚,名誉清白。有幸与他相遇的人,无不爱慕和尊崇他。有关他的回忆总是那么纯净、温暖,令人回味无穷。他为国争光,让人自豪。锡德尼的言谈从不愚蠢或平庸,他有过无数慷慨之举,人生最后的行为是其中的登峰造极。在我们看来,一位英国绅士就应当像他这样。(qtd.in “Nineteenth”:252) 上述描写显示,19世纪对锡德尼的认识深受当时流行的绅士概念的影响,编者汉斯·弗里斯威尔几乎把所有优秀品质都集于锡德尼一身,而其中有两个元素特别突出,它们对于19世纪的英国社会尤为重要:其一是爱国主义情绪,其二是英雄主义品质。在这里,锡德尼成为了骑士传统中理想的英国绅士典范,与他早期的骑士、恩主、诗人和新教殉教者的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种典范的形成得益于19世纪骑士神话与爱国情绪的结合,原本就声名远扬的“格瑞维尔片段”在这种结合中被从锡德尼传记中抽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展现出其偶像化的潜质,“偶像一旦得以确立,锡德尼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想象中的人物”(“Nineteenth”:252)。在这个过程中,锡德尼变得越来越远离原来的他,甚至也远离格瑞维尔传记中的他。比如,原书在叙述他最后的英勇行为之前有以下一段描写: 为了阻止西班牙军队从一条狭窄的通道发起攻击,部队很不幸地在扎特芬的前方进行抵抗。无论他多么欣然前往参加战斗,他都没有忘记古代圣贤对正义之战的描写,即最有价值的人总是最严实地武装自己,于是他马上全副武装起来。然而,当他遇见轻装出发的最高指挥官时,难以察觉的竞争心让他想要无可匹敌地展现他的冒险行为。他褪去了护腿甲。就这样在命运女神的秘密操纵之下,上帝似乎决心要击中他的那个部位,他没有任何防护。(39) 从这段描写中可以看到锡德尼性格中的弱点,比如他因急于建功立业而表现得鲁莽大意、缺乏耐心、性情急躁,等等。所有这些性格上的不足都被“从记录中清除”(40),不仅如此,锡德尼还不断地被赋予各种完美的品质。诗人W.H.艾尔兰在民谣《令人悲伤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之死》(Of the Doleful Death of Sir Philip Sidney)的引言中写道: 这位别具一格的贵族青年是他的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特别宠爱的朝臣。他不得不多次抑制自己对荣誉的渴望。他学识渊博、英勇无畏、慷慨大度。他在整个欧陆享有崇高的声誉,被推选参加波兰国王的竞选,但是女王拒绝促成此事,这不是出于忌妒,而是因为她不愿失去她宫廷中的明珠。他于1586年9月22日逝世。(qtd.in “Nineteenth”:254) 到1818年,“格瑞维尔片段”已经家喻户晓,锡德尼这个名字“激起了一种爱戴和崇敬之情,它永远萦绕在同胞的心田”(“Nineteenth”:255)。这种情感不仅存在于锡德尼的本国同胞内心,甚至也为其他国家的人们所分享。比如,一位匿名的纽约女士写了一本题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生平和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Sir Philip Sidney)的书,目的就是要展现他最动人的个人品质。她把此书献给自己的儿子,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是每一种男性美德的同义词,他的榜样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几个世纪之后依然璀璨夺目”(41)。 除了爱国主义情绪融入骑士神话之外,高贵的英雄主义行为也常与中世纪骑士品质联系在一起。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对此分外热衷,这对锡德尼传说的偶像化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早在1779年,乔治三世就让御用历史题材画师本杰明·沃斯特创作了一幅名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之死》(“Death of Sir Philip Sidney”)的油画。画家从锡德尼传记中抽出“格瑞维尔片段”,用以呈现他所代表的高贵品格。更重要的是,锡德尼“最后的行为被赋予了耐心、刚毅和无私等品质”(“Nineteenth”:258),这种表现形式让“格瑞维尔片段”呈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1806年,沃斯特被要求根据《英国史》中记录的事件创作一幅油画,“格瑞维尔片段”再次成为他的创作主题。在这幅名为《身负致命重伤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The Fatal Wounding of Sir Philip Sidney”)的画作中,画家为了达到渲染情感的效果,进一步牺牲了历史真实:画面中央是身负重伤的英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在他的周围是一派让人焦虑不安、杂乱无序的景象。历史上让锡德尼献身的那场小冲突,在画面上被描绘成了一场重大的战役。锡德尼身着镶有花边衣领的洁白服装,戴着护腿甲,面容略显苍白,整个人流露出一丝女性气质。他目光宁静地投向远方,全然没有注意到周围的一片混乱,对为他检查伤口的人也无动于衷,坐姿隐约呈现出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姿态。整个画面激发起观众感伤、虔诚、敬仰的情绪,因为画面上的锡德尼圣洁安详,表情和姿势明显来自宗教题材的传统形象。在这里锡德尼既是圣人,又是具有感伤力的绅士,同时还是拥有自我克制、镇定自若和坚韧不拔等品质的典范(see “Nineteenth”:257)。锡德尼在扎特芬临终前的姿势被刻画得如基督受难一般,当他的形象作为基督教骑士精神的关键性符号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扩张主义时,他终于被塑造成了具有骑士风度的完美绅士典范。C.S.刘易斯有言道,在20世纪中叶,“即便相隔如此遥远的距离”,锡德尼这个偶像“依然耀眼”(42)。 从锡德尼离世之时起,各方权势就开始为了自身的目的操纵他的形象转变。最初,伊丽莎白女王为了宣传的目的大肆利用锡德尼之死,使他的形象在生前身后迥然有别。后来彭布罗克伯爵夫人为了重振家族雄风,又将锡德尼的形象从战士转变成新教殉道者。到了19世纪,锡德尼形象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道德价值,成为完美绅士的典范。锡德尼因为自身的多才多艺,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实现了人们对于绅士的各种完美设想。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或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锡德尼形象的偶像化过程成为某种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其所象征的各类品质又迎合了公众的心理期望。当我们对锡德尼作为一个英国文化偶像进行解构,揭示真实与虚构的勾连,去除表面的神话色彩时,才能够看清这种文化偶像塑造背后的脉络。 ①关于学界对锡德尼及其作品的评价,详见马丁·加勒特编著的《锡德尼:批评遗产》(Martin Garrett,ed.,Sidney: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elge,1996),其中收集了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对锡德尼的各种评判。 ②Richard Hillyer,Sir Philip Sidney,Cultural Ic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xv. ③Edward Berry,The Making of Sir Philip Sidne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8,p.212. ④See John Gouws,"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ment of the Sidney Legend",in M.J.B.Allen,ed,Sir Philip Sidney's Achievements,New York:AMS Press,1990.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锡德尼在欧洲游学逗留巴黎期间,遭遇胡格诺派被屠杀的巴塞罗缪之夜(Massacre of St.Bartholomew),这件事对锡德尼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他强大的家族势力背景,锡德尼被其精神导师、胡格诺派的重要人物体伯特·朗格(Hubert Languet)介绍给胡格诺派领导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新教反叛领袖们。这些人对锡德尼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期待,但本质上是想通过锡德尼的关系,得到其家族甚至伊丽莎白女王的支持。锡德尼日后参战也与这些势力有关,这也是伊丽莎白女王对锡德尼及其家族严加防备的一个重要原因。 ⑥详见约翰·巴特勒《西方社会史》(第二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9-180页。十七省为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1519-1556)继承的十七个地区,包括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1576年,十七省在奥兰威廉王子(William of Orange)的领导下联合起来。 ⑦本文是在16世纪意义上使用“荷兰”这一概念,它不同于现代“荷兰”的国家概念。当时只有十七省的最高统治者及其高级管理者才将此地精英阶层视作“国民”,而普通民众则视与己相关的行会会员或所属城市人民,特别是自己所属的群体为“国民”。有的人从“省”的层面出发,把本省贵族或官僚视作“国民”,任何此地以外的人均被视作“外国人”,包括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任命的摄政。本文所指的“荷兰”是指十七省中北部的七省,它们由荷兰省领导,后来建立了乌得勒支联邦,1581年宣布独立于西班牙的统治,尼德兰联省从中诞生(see Simon Groenveld,"'In the Course of His God and True Religion':Sidney and the Dutch Revolt",in M.J.B.Allen,ed,Sir Philip Sidney's Achievements,p.60;约翰·巴特勒《西方社会史》[第二卷],第18-181页)。 ⑧Philip Sidney,The Correspondence of Sir Philip Sidney,ed Roger Kui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816-81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⑨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⑩Alan Hager,"The Exemplary Mirage:Fabrication of Sir Philip Sidney's Biographical Image and the Sidney Reader",in ELH,vol.48,No.1(Spring,1981),p.1.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Louis Adrian Montrose,"Celebration and Insinuation:Sir Philip Sidney and the Motives of Elizabethan Courtship",in Renaissance Drama,8(1977),p.7. (12)John Buxton,Sir Philip Sidney and English Renaissance,London:Macmillan,1954,p.34. (13)Raphael Falco,"Instant Artifact:Vernacular Elegies for Philip Sidney",in Studies in Philology,vol.89,No.1(Winter,1992),p.3.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4)Michael G.Brennan,The Sidneys of Penhurst and the Monarchy,1500-1700,Wilshire:Antony Rowe Ltd.,2006,p.7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5)Alan Stewart,Philip Sidney:A Double Life,London:Chatto & Windus,2000,p.217. (16)Andrew D.Weiner,Sir Philip Sidney and the Poetics of Protestant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8,p.19. (17)Richard Hillyer,Sir Philip Sidney,Cultural Icon,p.viii. (18)锡德尼《为诗辩护》,第4页。 (19)Simon Groenveld,"'In the Course of His God and True Religion':Sidney and the Dutch Revolt",p.63.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0)法国为增强实力,一直有与英国女王联姻的愿望,但伊丽莎白女王并不想被法国利用,更不想因此得罪西班牙。1585年,法国拒绝担当低地国家对抗西班牙的保护国角色,这意味着法国和西班牙再次结为联盟,因此对女王而言,加强英国与低地国家新教势力的联盟,就显得迫在眉睫。 (21)如果说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宫廷的官方语言习惯是把历史追溯至亚瑟王时代,以证明其统治权的真实性,并伸张英格兰独立于罗马教廷的权利(see Sydney Anglo,Spectacle,Pagentry,and Early Tudor Polic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那么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她所采用的则是更具文学性却带有相同政治色彩的策略,即在宫廷文化中融入骑士传奇故事。 (22)See Monica Santini,"Romance Imagery in Elizebethan Entertainments and Tournaments",in Alessandra Petrina,ed,Queen and Country: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ation,New York:Peter Lang,2012,p.39. (23)See Jane Stevenson,"The Female Monarch and Her Subjects",in Queen and Country: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Peop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glish Nation,p.28.威尼斯大使生动地记录了亨利八世在比武场上的勇猛行为。 (24)See Jane Stevenson,"The Female Monarch and Her Subjects",p.29. (25)Frances A.Yates,Astraea: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London:Routledge and K Paul,1975,p.101. (26)孙凤城《中世纪骑士文学》,收入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4页。 (27)Joseph M.Levine,Great Lives Observed:Elizabeth I,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9,p.5. (28)James M.Osborn,Young Philip Sidney:1572-1577,The Elizabethan Club Series 5,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p.516. (29)Fulke Greville,Lord Brooke,The Prose Works of Fulke Greville,ed John Gouw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p.85. (30)See also Margaret P.Hannay,"'This Moses and This Mirian':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Role in the Legend of Sir Philip Sidney",in M.J.B.Allen,ed.,Sir Philip Sidney's Achievements,p.218.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文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31)Eleanor Rosenberg,Leicester:Patron of Lett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350. (32)See Dominic Baker-Smith,"Preface",in M.J.B.Allen,ed.,Sir Philip Sidneys Achievements,pp.97-98. (33)锡德尼是一位名声远扬的恩主,他及其家族对英国学术的赞助,与美第奇家族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相仿(see John Buxton,Sir Philip Sidney and English Renaissance,pp.133-172)。 (34)See Philip Sidney,Sir Philip Sidney,The Major Wor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317.锡德尼本人临终前似乎对此事甚为痛悔,向牧师忏悔道:“回想起来,我曾心怀虚荣,且沾沾自喜,不能割舍。这就是我的里奇夫人。” (35)Thomas Moffet,Nobilis; or,a View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idney,and Lessus Lugubris,trans.and eds.Virgil B.Heltzel and Hoyt H.Hudson,Berke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0,p.77. (36)Qtd.in Fulke Greville,Lord Brooke,The Prose Works of Fulke Greville,p.77. (37)Richard Hillyer,Sir Philip Sidney,Cultural Icon,p.44. (38)Roger Howell,Sir Philip Sidney:The Shepherd Knight,Boston:Little,Brown,and Co.,1968,p.56. (39)Fulke Greville,Lord Brooke,The Prose Works of Fulke Greville,p.76. (40)Blair Worden,The Sound of Virtue:Philip Sidneys Arcadia and Elizabethan Politic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p.68. (41)Qtd.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vol.88,No.183(April,1859),p.314. (42)C.S.Lewis,English Literatur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Excluding Drama,Oxford:Clarendon Press,1954,p.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