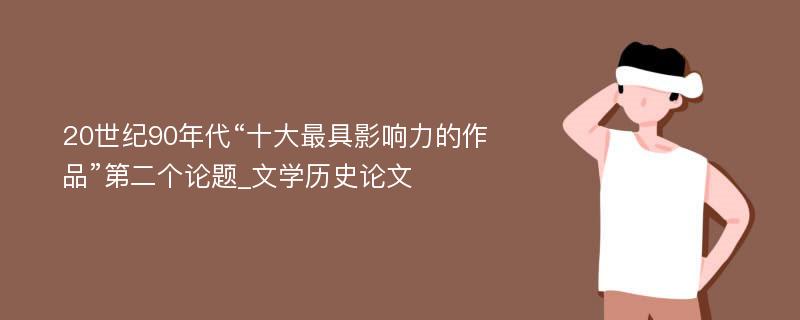
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有影响论文,作品论文,二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发出征集,全国百名批评家推荐的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最有影响的十部作品,在世纪末帷幕即将落下之际面世,它们是: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张炜的《九月寓言》、张承志的《心灵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华的《活着》、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
应该说,它们并不能构成一幅完整的九十年代文学地形图。问题可能就在于,作为限定词的“影响”有些模糊。如果是指文坛内的“影响”,那么有的被批评家们普遍看好的优秀作家作品,如阿来的《尘埃落定》等没有入选,似乎就有些遗憾了;若是指社会“影响”,有的轰动一时、人们争相传阅的作品,即使是边缘作家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也不应被忽视。还有,也许是参与投票的批评家的偏爱,也许是知识共同体中掌握话语权的人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相近,所以入选的作家除个别人之外都是八十年代成名的。尽管正如本文下面将论及的——这里具有一定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合理性,但同时它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九十年代文学基本上沿续着八十年代社会的共同想像。因此,它引起人们的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尽管如此,我想我们还是不能轻易地否认这份作家作品目录。因为,它一方面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并不是指盖棺论定上的,而是说它为今后的文学史写作提供了一种选择的参照。至于其中的感情、偏爱与惯性思维的因素,应由历史的间距去过滤。在文学史写作上,那种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的企图不啻是一种虚妄。另一方面,它是精神同代人的文化指证。这些作家作品至少包含了这个暧昧时代部分文学知识分子精神文化与审美需求上的追求。正是出于上述两种意义,我面对这份作家作品目录,想要追问的是这些作品所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它们的入选意味着什么。
一、同代人的不同追求与相互交叉
从作家研究的角度出发,这份作品目录最引人注目之处,大概就是“知青”一代作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八位入选作家中竟有五人属于“知青”作家:王安忆、韩少功、张炜、张承志和史铁生。(注:我这里使用的“知青”概念,不是指涉文学题材,而主要是指作家的代际身份,这一代作家具有极其特殊的共同历史体验,即他们都曾接受过理想教育,经历了“文革”,下过乡插过队。)
关注九十年代文坛的人都知道,六十年代作家群和七十年代后作家群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颇有创作活力,尤其在私人化话语和女性意识的建构上,他们开拓了当代文学的新空间。与此同时,曾经在新时期文学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归来者”一代在逐渐消隐,而庞大的“知青”作家群体经过时间的淘洗,也只有一部分人继续在文坛守望。把这批精神守望者的代表作品作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是否标示着九十年代文学仅仅在重复八十年代的剩余想象呢?我觉得,在下结论之前还是先检视一下入选的作品吧。
王安忆是一个极富创造潜质的作家。自新时期以来,文学场景急速变换,能够接受这种挑战并不断超越自我的作家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而王安忆则是这为数不多作家中的具有个性的一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她以类似弑父的《叔叔的故事》,拆解了虚假的神圣与崇高。其后的《纪实与虚构》在漂泊孤独的情境中,潜入历史追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长恨歌》则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都市民间社会和私人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地体察。主人公王琦瑶如花的生命偏偏绽放在风雨飘摇的年月,她为了短暂辉煌付出了绵绵无期的卑微生活的代价。在整个社会都被政治高度整合的年代,她仍然自主地生活在社会的边缘,把人生往小处做,为了世俗的情爱默默地承受时代和命运重压。当这个社会在渐渐理解个人的潜在欲望,并试图争取合理满足的权利时,她却美人迟暮死于非命。王琦瑶作为都市民间社会的女性,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飞扬”的人生理想,只有在虚荣与骚动的生存空间中锻炼出来的贴肤可感的物质和情感的需求,而她的生动就在于,为了实现这微末而真实的感性生命欲求,以上海女人的本能,谨慎地抗争与妥协,艰难地冒险与算计。而且,小说把主人公的这种个人性情推向了极致。
王安忆以温情目光打量王琦瑶,一方面纵向地抓住人物的自我与个体本真生命的关联,探寻人性与个体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并没有放弃横向的个体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不过,外在世界在小说中是以淡远的背景出现的,在王琦瑶的眼中,这个外在世界不啻转换成了一种冥冥的命运,她默默地承受又死死地抗争。王安忆在人物自我与命运关系的把握上,显得颇有信心,所以充分地发挥了她所擅长的感性认知与情绪体验的叙述方式,既呈现了一个普通市民的生命韧性,也显示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生困境。
张炜的《九月寓言》与八十年代的《古船》相比,无论在小说形态上还是思想意蕴上都有所不同。《古船》用的是“举隅性”的叙述方法,即潜入历史打捞生活的片断,用残存的记忆重新构想过去的整体生活。作者强调的是他所呈现的历史片断的真实性。《九月寓言》则是“寓言性”的叙述方法,即文本表层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种隐秘的意义。小说以变形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情,既向我们揭示又向我们隐瞒。从内容上看,《九月寓言》描述了小村人的生存形态:首先是对他们最基本也最强烈的生存欲望进行了酣畅淋漓的描绘,比如对“地瓜”和“黑煎饼”的热望,还有“打老婆”、“拔火罐”、在野地里“奔跑”等。其次是对小村人的精神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忆苦思甜”。最后,还讲述了小村内部的情况、小村与矿区的关系。作品并没有回避小村物质与精神的贫乏,也没有忽视权力对人性的戕害,但是它没有沾滞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上,也没有目不转睛地盯在具体的苦难与痛苦上,而是把生存的历史和现状放置在更为辽阔的生生不息的宇宙中,用更为抽象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去理解人类的生活和苦难。这样,过去的苦难融有生命的真义,现实的痛苦也显现生存的本相,而平凡的生活中具有本质的意义。在默默无语又包融一切的大自然中,在所有生命的生死轮回之中,小村人的痛苦和苦难都显得那么淡远和浑融。这倒不是说作者对生活中的痛苦和苦难视而不见,而是说他想沿着人的恩怨仇恨的根须深掘下去,试图抵达永恒之处。作者不但懂得拒绝,也开始尝试忍受。从某种意义上讲,张炜再次沉溺到早期的野地情结,不过这种回溯不是平面上的重复,而是深层次地自我超越。
张承志好像是变化最大的作家,他的《心灵史》宣告了他已经告别俗界而迈向圣界,这位“人民之子”、“草原义子”业已成为“回族长子”。应该承认,这部作品给文坛的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人们不能不敬佩他的勇气和才情——把一个沉默的少数民族中的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宗教教派的悲剧历史,写得如此惊心动魄。但是,书中传达出来的创作主体那种狂热的宗教献身精神和毫无保留的生命情感的投入,那种强烈的鄙视世俗的态度和反智论立场,还有对于苦难和仇恨、暴力和殉道的看法,也是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也许,人除非皈依一种宗教才能知道什么是宗教,这里毕竟有一道由无神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习俗所构成的精神文化的沟壑。然而,从文学思想上看,《心灵史》与作者八十年代的作品有一种贯通性的联系。从《北方的河》主人公崇拜的牛虻、马丁·伊登和保尔·柯察金,到《金草地》中红卫兵模仿长征,人们不难发现,审美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是张承志心中最隐秘的情结。在《心灵史》中,同样可以列出一连串的殉教者和传教者:苏四十三、赛力麦、田五阿訇、张文庆、马化龙等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哲合忍耶教史上,也在成千上万的教徒心中铸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前者是革命英雄,后者是宗教英雄,他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和信仰在内容上不一样,但英雄崇拜的形式是相同的。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功能就是提升和净化读者:人只有当他为某种被抽象的原则效力、并为此献出自己的一切时,他的生命才是最有意义的。这种贯通性的联系也体现了张承志的精神特质,这就是重精神而轻物质、追求理想而鄙夷现实、向往神圣而厌恶世俗,这种特质就决定了他将坚执信仰当作他的人生要义。
相对而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似乎表明他是变化不大的作家。马桥的乡民生活在稳定而停滞的文化空间。他们精神贫困的表征就是蜷缩在语言的屏障下而不自知,自以为是地重复着先人流传下的言语。有时你很难说得清到底是语言显现了他们内心的封闭和观念陈旧,还是这种语言本身具有限定他们精神状态的功能。按理说,语言的重要文化功能之一,是留存记忆和抵御遗忘,可用马桥人的语言表述的历史往事往往模糊不清,完全可以想象,生活在一个缺乏逻辑和意义的历史记忆的空间,历史悲剧的重演只会加重他们的历史轮回的宿命感。马桥人的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很容易让人领悟到这部小说的寓言性:在世界文化环境中,中国有时就是马桥。从作者对文化质料的审察层面上讲,这部小说也可以说是沿着“寻根文学”《爸爸爸》开拓的向度深掘的结果。当然,在西方哲学研究朝着语言方向拓展的文化语境下,作者的文化思考显然没有仅仅停留在既有的启蒙思想的层面上。小说的叙述者作为“词典”的编纂者,明显地介入到马桥人的生活之中。这种介人既有对感知的眷恋,更有理性的自我节制。他自知已经“普通话化了”,所以他在揭示马桥人言说的被动性同时,对自身话语的限定也持有警觉性。这就是说,作者自知不可能完全站在传统之外反传统,从而使小说的意蕴超越了启蒙话语廉价乐观的方面。
上述的四位作家,共同成长的历史情境相同,但是在九十年代小说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却大相径庭。王安忆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以睿智而温情的笔触描述都市民间社会的私人情感,对因被革命时代压抑而处于遗忘中的日常生活和世俗欲望给予了人文关怀。而张承志则站在神圣的立场上,讲述着从血淋淋的历史场景中升华的宗教英雄故事,以一种超凡脱俗的高昂姿态和独特的强悍,抵抗社会的世俗化趋势。面对着同样的乡土中国,张炜与韩少功却生发出不相同的思考。张炜更多地是用质疑现代性的目光去关注自在形态的乡村,而韩少功则沿着启蒙的向度继续前行,从语言这种最基本的思想形式入手,展示传统乡民的精神文化上的贫困。这种创作现象首先表明,九十年代文学知识分子空间的思想同一性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的价值取向日趋个体化,因而无力为社会提供总体性的共同想象关系。而且,对于这种众声喧哗的精神现象,批评界在既有的理论宝库中找不到一种理论来涵盖,只好用“无名”来名状。
其次,思想价值上的分化决不意味着思想价值的崩溃,我们可以在不同的价值意向中找到相互交叉的地方。在“知青”这一代作家中,其交叉之处就是民间理想主义。陈思和先生认为,这种民间理想主义是指那些在创作中提倡人的理想性的作家,在历史的经验教训面前,“改变了五六十年代寻求理想的方式,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确认和寻找人生理想”。(注: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4页。)这种不谋而合的民间理想主义,究其原委,一方面是他们共同的历史体验,在他们的思想底色上不同程度地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理想主义痕印,因此,他们总有一种寻求生活根据和人生理由的意义向心力。另一方面,九十年代赤裸裸的巧取豪夺、物欲横流,以及精神文化的危机,引发了学界“人文精神寻思”的讨论,同时也触动了这一代作家的良知和使命感。既然伪理想主义的大厦已经轰然倒塌,那就重新踏上民间社会的土壤,在质朴的生命中寻找神性的种子,耕耘真正的理想。
最后,在他们的差异中还可以发现共同的盲区,这就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忽视。这种空白,在他们与六十年代作家群及七十年代后作家群的比照中显现出强烈的反差。固然,六十年代作家群和七十年代后作家群对当下现实确实存在着暖昧姿态:前者的创作中,人的精神主动性被幻灭淘空,有时不由自主地沉迷在物与欲的漩涡之中;后者的作品,尤其是被商业文化刻意包装的女性作家,有时紧紧抓住转瞬即逝的生命快感,在自恋性的私人化话语中流连忘返。然而,我们不能断然否认这种欲望化的现实想象关系,它毕竟锲入了日益世俗化的当下现实生活,而且是闯入在喧嚣和欲望的黑浪中翻滚着的城市,感受到功利主义水银泻地一般地渗透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时代气息。与他们相对,“知青”一代作家却与当下的生活现实自动地拉开距离,或进入乡村的历史,或遁入非常态的民族历史事件,即使是写日常生活也是过去时态的,而不是现在进行时态的。这究竟是这一代作家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本质性关联缺乏把握的自信和锲入的力量,还是他们心理中历史的负荷过于沉重,抑或是刻意回避个体生命深处的自我求诉呢?(注: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史铁生是个例外,他的小说《务虚笔记》尤其是散文《我与地坛》,对个体生命和苦难、人生与命运进行了深入地思索。)我不太清楚。但有时我总觉得,任何一种引领当下社会的价值理想,源自历史文化传统和基于人性需求,同时也应该契合现实生活而不宜远离当下的生活情境。
二、历史与苦难
西方自从历史与小说的联姻关系解除之后,除非像“二战”这样无法抹去的心灵巨创之外,历史对小说作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弱。而中国当代文学直至九十年代,历史叙事的创作冲动也没有消解。究其原委,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传统上讲,这是集体无意识的表征;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角度看,个人性的历史叙事是对集体记忆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反叛;在文化语境上,则是社会变革时代人们辨析现实的认知需求——只有了解从何处来,才能确立通往未来的路标。而且,在这些因素上,作者与读者常常互感互动,形成一种戚戚于心的默契。有时,与其说是作者选择了历史,还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作者。基于此,我们对当年《白鹿原》轰动一时、评论如潮的社会反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白鹿原是陈忠实精心地制作的一个宗法社会家族文化的活标本。宗法家族文化决不限于农业社会这一宽泛的概念,因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历农业文明的历史阶段,但并非都有中国历史上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其酿就的家族精神。宗法社会的漫长历史,正是依靠这种以儒学为主体的家族文化得以维系和发展的。进入近代之后,中国社会体制的革命如同一台失去了控制的机器,凭着惯性毫无节制地左冲右突,白鹿原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了漩流中心,宗法家族文化遭受到现代政治文化空前强烈的冲击。族长白嘉轩的失势和黑娃的死表明,血缘家族权威注定得向行政权威转换,而无论这种转换得付出多少代价。但是,由于新政体制缺乏现代经济的支撑和现代文化的提升,除了无休止地征税抓丁和剿杀政敌之外,并不为村落共同体承担任何公益责任,实质上衍变成专制集权在底层社会的统治触须,所以不但没有在农村村落中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反而酿就了人为的社会灾难。小说试图透过白鹿原家族文化的衰亡,从某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奥秘。尽管小说也将家族文化置于理性和生命的天平上加以衡量,标示出它的某些虚伪性和残酷性,但总体上的留恋和袒护是显而易见的。寄托在朱先生身上的完美无缺的人格理想,体现了作者的道德动机:潜入已逝的岁月,企望在失去年华的精神家族中辨析某种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以回应时代的道德焦虑。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则从更为深远的历史中打捞文化意义的碎片。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无形而有力的历史观与缺乏深厚的本体论哲学的文化背景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在表现人的苦难命运时,常常是把生存本体的荒诞放置到历史性的生活世界,转换成人的历史世界的荒唐,并表现人们在这种不可理喻的生活情境中的坚韧。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一改昔日的先锋立场,描写近半个世纪城镇下层社会中日常生活的苦难。《活着》的主人公福贵年青时嫖赌逍遥肆意挥霍,直至家产荡尽,可这种罪孽的活法却使他免遭磨难而获新生。当他浪子回头,由一个纨裤子弟变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一位温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后,却犹如一头套上苦难重轭的黄牛。他真诚地对待人生,而命运却夺走了他身边的一个个亲人,最后孤苦伶仃,活着与不幸同义。
小说中这些残酷的人间苦难是以小说人物自述的方式展开的,也就是说创作主体以不在场的方式抽身而去,以此抑制主观价值情感的介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作主体缺乏价值意向。一方面,如果我们稍略细致地辨析福贵的苦难就不难发现,他的苦难可以——附着在历时性的社会现实上。透过苦难可以瞥见一个以颠倒的形式展开的荒唐丑陋的历史世界,人的命运与人的善恶、真诚和智力毫无关系。所以,站在局外看,福贵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无情的历史强加给他的,是命运的不公和世界的不义。另一方面,福贵顽强地承担着命运的不幸。局中人福贵把人生作为一个过程,并不期待过程之外的其它目的。生活的意义就融汇在他对苦难的承受之中,就像他儿女的死亡关联着新生一样(他儿子为孕妇输血而死,女儿为难产而亡,他们短暂的生命在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命长链上凝聚成意义)。所以,他的内心并没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当他历尽沧桑孑然一身时,不但没有满腔的怨愤和仇恨,反而有一种空灵的淡泊和超然。这种自在形态的“活着”本身,包含了本原性的生存意义,也体现了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坚忍的生命活力。《许三观卖血记》同样是以民间社会的视角审视苦难,可以看作是《活着》的延续,但小说的基调更为乐观和幽默,更贴近下层社会生活的原生态。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以较抽象的方式讲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遇和人生追求。小说不注重生活世界和人物形象的完整,而是让他们的艰难和祈望统统叠现在叙述者的印象上。这种写法让我想到普鲁斯特所说的话,“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就象空间有几何学一样,时间有心理学”。(注:引自莫罗亚:《追忆似水年华·序》,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也许正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体性特征,才更加突现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欲求和危惧苦难的情状,以及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思索与超越的形式:更贴近于他们的生活心理现实。当然也更加体现了“知青”一代作家刻骨铭心的意义焦虑。苦思冥想的创作主体,似乎并不在乎生活记忆的真实,而是想捕捉住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命呼声,并试图穿透生活记忆的表像而逼进人类生存的本相,从人类自身、人与生活世界的关联上追寻蕴含在苦难人生的真义。
二十世纪中国独特的历史形态,使得置身于历史现实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太多的欺骗奴役和血腥杀戮,任何清醒而具有良知的作家都不能无视这种残酷的历史现实,也无法把人生苦难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完全剥离出来。他们在呈现这种历史苦难的同时,苦苦地追寻原由,祈盼自己的民族永远摆脱轮回般的浩劫和宿命般的苦难。也许,这就是九十年代小说历史与苦难仍然紧密相联的原委。
从创作趋势看,作家业已脱离集体记忆的宏大叙事。在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中,先锋性的情感价值中止有所退化,创作主体由冷漠地专注人性残酷转向悲悯而温情地贴近人生。九十年代作家大概洞穿了种种以理想的名义预支未来的虚妄,也深知人的理性限度,因而,他们在思考如何面对与超越苦难时,把民间社会自在状态的艰难人生纳入视野,从质朴的生命中发掘浑融状态的人性力量和道德良知。
这些在九十年代产生一定影响的十部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这要取决它们本身的形式和质地,还要看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回应了未来生活的精神需求,但是我以为,把它们作为部分精神同代人的文化指证并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许三观卖血记论文; 艺术论文; 活着论文; 读书论文; 王安忆论文; 九月寓言论文; 务虚笔记论文; 张承志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