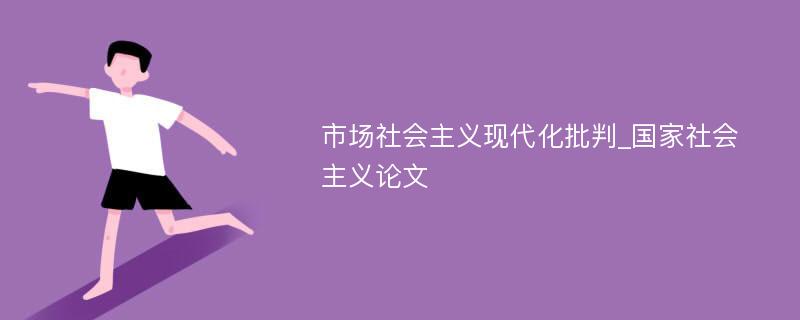
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思潮
“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术语,许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界定,因此可供引用的众多的“现代化”的定义令人眼花缭乱。所幸的是大多数定义的内涵都比较接近,挑选一个基本上可以普遍接受的定义并不太难。就本题而论,笔者比较欣赏美国学者艾恺(Guy S.Alitto)的定义,因为它具有精确和涵盖面广的优点。艾恺认为,“现代化”的定义应建立在两个关键性的概念上:“擅理智”(rationalization )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擅理智”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含义,而“役自然”是指对自然的控制。于是他将“现代化”界定为:“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注: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源于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产生的加速度式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特别是到了19、20世纪,这种影响导致了人类生活及环境的急剧变化。许多变化是正面的,但也有不少变化是负面的。“擅理智”和“役自然”,归根到底属于手段、方法、工具、器物等范畴,有别于各种人文精神价值。现代化强调的是过程而非终结目标,它判断任何事物好坏的惟一的价值标准是理性主义所追求的效率的功利性。贯彻理性主义的效率和功利原则固然会带来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减少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但也会使人类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理性化到一定的程度会走向其反面非理性化,个体或局部的理性化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化。如分工和机器生产提高了效率,却有使工作枯燥乏味和使人异化为物的附属品之虞;科层组织为提高效率所设,却有可能沦为无效率的官僚机构;现代工业提高了商品生产效率,却导致环保和能源利用方面的低效率;现代科技是为人类造福的利器,使用不当也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杀手。现代化在将个人从各种“传统”社会组织和机构的羁绊和“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人付出了“非个人性”、“缺乏恒常的人际纽带”、“没有道德准则或道德的确定性”、“欠缺认同主体”等代价。(注: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1页。 )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必然遭致来自多方面的批判。
在批判现代化的诸多思潮中,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格外引人注目。与强调效率的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一样,强调公平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和对应物。社会主义思潮也可以追溯到被称为现代化的“真正肇端”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时代精神是理性。理性原则在否定了神性高于人性的同时也否定了人性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差异,从而为平等与公平等价值观提供了理论依据。思想家们还从理性原则中引伸出“进步”的信念,即人类理性的应用将不断地改善人类社会和环境。这种信念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认为理性能够设计出一个可行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克服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机制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所有弊端,能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上述价值观和信念构成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共同内核。社会主义者是从左的政治立场来批判现代化的。如果说从右的政治立场批判现代化的保守主义者重点抨击社会规范的衰败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之间的不公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右翼批评家一点也不注意工人的境遇,或左翼批评家一点也不关心社会规范和其他问题。具体来说,依据传统的正统社会主义观念,基于资本主义功利原则的现代社会有诸多弊端: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的异化、失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浪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资本的利益不惜阻挠技术进步、滥用资源、环保和生态问题等。这些弊端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和自由市场机制,即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必然会被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更高一级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
二、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
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与其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有明显的共性,即对“市场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和对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推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公平方面遥遥领先,而且在效率方面优于或至少接近于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应该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弊端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此显而易见,无须在论证社会主义价值观上多费笔墨。
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也有其独特之处。这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20世纪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米塞斯挑战的回应,是在关于高效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的大辩论中逐步充实改进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家不得不正视自由主义论敌在辩论中提出的有价值的论点和论据。另一方面,二战后市场社会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的衰落和失败的影响。自由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和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痛苦经验是塑造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和模式的两大基本要素。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市场具有资本主义属性,正是市场导致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其中包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计划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仅有助于克服剥削和异化等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且能够消除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使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从而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种对计划即理性的过分信赖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的表现,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哲学信念,或更确切地说是理性主义的一个误区。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批判的矛头不仅指向基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现代”社会,而且指向基于“理性的虚妄”的国家社会主义。凯恩斯曾声称:“人类的政治问题是将三件事结合起来: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个人自由。”(注:C.Pierson,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The New Market Socialism,Polity Press 1995,P.85.)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为这个人类的政治难题寻找解决之道。
为了解决将公平、自由和效率结合起来的难题,市场社会主义在市场、国家和所有制问题上的立场均有别于传统的正统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自由市场机制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端负责,然而,作为现代复杂的工业社会配置资源的手段,市场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市场有诸多重要的正面功能。市场社会主义并不否认市场的负面作用,但看重市场的正面功能,强调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正面功能,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市场是一种有缺陷然而非常有用的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同样可以利用,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都是错误的。在《市场社会主义》一书中,英国著名市场社会主义者戴维·米勒分析了左派传统的反市场态度的根源。在他看来,对右派溢美市场的反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左派敌视市场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现代化导致工人贫困化和前工业化社区瓦解的反应:希冀大众分享工业化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同时又浪漫地迷恋已被摧毁的前工业化的社区形式与人际关系准则。在此书中,米勒为市场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他“为市场辩护所诉诸的价值是福利、自由、民主”。首先,米勒根据现代信息经济学理论指出,市场既是一种低成本的信息交换体系,又是一种高效的激励制度,是在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生产最大的物质福利的经济运行机制。市场意味着效率,而国家计划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难以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其次,米勒认为听任新右派“将自由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灾难性”;左派应该把自由视为一种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的自由观应该以个人实质上的有效选择为核心。他力图论证市场社会主义比市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更能保障私人消费选择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后,米勒论证了市场促进民主的观点。他将民主分为工业民主和国家民主两类。米勒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享有自主权,从而使工业民主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国家的作用在市场社会主义之下受到限制,国家民主随之扩大。(注:索尔·埃斯特林、尤里安·勒·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4页。)
通常认为,在组织经济方面, 对市场的敌视与对政治国家(state)的青睐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其实,至少马克思并未明确设想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让国家扮演全民财产总代理人及全能的经济计划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相反,恩格斯提到“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74页。)马克思、 恩格斯的本意是通过经济权力回归社会而非集中于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然而,在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只能是市场或国家计划,没有其他选择。社会主义者既然屏弃了市场,就只能依靠国家。于是,国有制和国家集中计划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和尺度。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国家社会主义视市场为“恶”,崇尚国家的作用,实行国有制和包罗万象的国家计划,导致经济上的低效率和政治上的官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南辕北辙。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标不能通过国家来实现,主张通过市场和公民社会来限制国家的消极作用,保障经济效率和政治民主。但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意崇尚市场、视国家为“恶”的自由主义观念。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始终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市场。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自由市场机制的优势在效率,弱点在公平。因此,为了趋利避害,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只能是有管制的市场,这就给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留下了一席之地。所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不免包括某种国家计划机制。市场社会主义者还主张对市场运行的结果进行适当的干预,以避免两极分化。但市场社会主义的计划是宏观经济计划而非微观经济计划,是指导性的而非指令性的,其实施依靠的是投资、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而非行政命令。 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干预旨在克服市场失灵(
marketfailure)和实行公平,但以不大幅度损害效率为限。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社会主义包括两部分:市场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如前所述,市场是一种高效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其效率之获得不免要以收入、财富的不平等为代价。此外,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为合法,而市场资本主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自由市场机制相结合,会导致剩余价值的产生和对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剥削,势必使业已存在的不平等更趋恶化。这显然与社会主义的平等或公平的价值观相悖。因此,不能完全依靠自由市场机制,更不能搞市场资本主义,需要采取某种措施来纠正市场机制产生的偏差。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部分是为了提高效率,而社会主义部分则是为了实现公平,这两部分应该而且能够结合在一起。一般来说,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这似乎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区别不大。但鉴于历史经验和教训,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不赞同传统的国有化或国有制比例过大,他们主张各种各样非集中的社会所有制,特别是工人合作所有制。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而非经济运行机制,因此中央计划不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往往不得不面对“为什么要搞市场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集中体现在这些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或换句话说在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市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论证中。总的来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论证不尽相同,因此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的具体内容也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19世纪“原始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如蒲鲁东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既反对作为现代化的后果的资本主义剥削,又对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膨胀的国家机构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危险保持警惕。蒲鲁东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案是由独立的小生产者——农民和工匠——组成的社会,这些小生产者拥有自己的个人劳动产品,并进行一系列平等的市场交换。穆勒则设想工人合作制与竞争性市场相结合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注:关于穆勒和蒲鲁东的“原始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参见David Belkin,"Why Market Socialism?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to Positive Political Economy",in Frank Roosevelt and David Belkin,eds,Why Market Socialism?,PP.10-13;David McNally,Against the Market
:Political Economy,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rxist Critiqu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P.140.)20世纪30年代,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者兰格在用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论证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一样高效可行的同时,用福利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论证了“经济学家赞成社会主义的理由”。他辩称,社会主义比生产资料私有的资本主义能产生更大的社会福利,减少浪费,消灭商业循环的波动造成的恶果。兰格强调,更重要的是,资本家制度与经济进步不相容,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显然,兰格保留了大量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并对国有制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计划调节机制持肯定态度,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官僚化”的“真实危险”提出了警告。 (注:Lange,"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in Lippincott,e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PP.98-121 .)二战后,伴随科技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丰裕的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成现实,但基于功利和效率原则的现代化的负面效应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如贫富悬殊、失业、异化和环境污染等。与此同时,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在东方的历史条件下的突出表现是集权化和官僚化。以国有制和中央计划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因无法适应新技术革命而日益陷入深重的危机,逐渐被历史所抛弃。因此,战后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现代化批判越来越带有两面作战的特点——既批判市场资本主义,又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切身体会,又急需在理论上为改革鸣锣开道,所以在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方面贡献突出,如布鲁斯从集权和分权的角度、锡克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科尔内的预算软约束理论都是明显的例证。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中,诺夫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最系统,也最引人注目。对大多数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而言,国家社会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的谬误早已不言而喻,关键在于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论证自己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行性,以摆脱在与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论战中所处的被动局面。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锋芒依旧,但面对自由主义思潮强有力的挑战,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行性问题日益突出,结果是以“淡化”社会主义为代价追求可行性,新模式离传统社会主义概念越来越远。在当前最新一轮关于市场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中,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罗默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设计者不但致力于论证其模式相对于市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且不得不论证自己的模式仍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注:Bardhan and Roemer,eds.,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New York 1993,PP.7-9.)
三、对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批判的评价
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是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的反应。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现代化进程中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市场化追求效率,牺牲了公平;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化强调公平,忽视了效率。市场社会主义者不是笼统地反对市场,而是反对不公平的资本主义市场;他们不是笼统地赞成社会主义,而是赞成有效率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市场所体现的效率和社会主义所体现的公平价值观结合起来的近乎完美的经济制度。对效率的追求和对理性设计的社会制度的信念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现代性。市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批判不是对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简单否定,不是要回到前现代浪漫温情的“旧日良辰”,而是要保留现代化的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批判是对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双重超越。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者对现代化的批判的主观愿望是值得赞赏的,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也是有一定成效的,或多或少地促进了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变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全球市场资本主义似乎凯歌高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之际,在人类正深刻反思现代化的利益和代价准备跨入新世纪之际,市场社会主义的建设性批判的、“非终结论”的声音不啻一副难得的清醒剂。不过,话说回来,现代化既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利益,难免也会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然珍视的某些东西作为代价。希冀只收现代化之利而不付出代价,不免一相情愿。讲求效率至上的现代化的代价之一是对公平原则的严重背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问题,犹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个问题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只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权衡利弊,进行困难的抉择。乍一想来,追求效率与公平近乎完美的结合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似乎颇具魅力,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有的问题难以解决。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尤其复杂,因为效率离不开激励,而激励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某种不平等或不公平。实施公平原则离不开国家等公共机构的作用,如何防止这些机构官僚化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目前设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旨在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但设计者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不是被左派指责为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是被右派斥之为乌托邦或效率低下。即便模式本身无懈可击,也必须解决将该模式付诸实施的社会政治动力的问题。近现代世界史的教训之一是,人为设计的社会模式不是难以实施,就是实施后的效果违背设计者的初衷。这使人们有理由对实施任何设计者自称“高效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持谨慎态度。市场社会主义的价值不在于它向人类提供完善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潜力,而在于它的批判功能。只要人类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类似市场社会主义这样的“提供另一种选择”的批判现代化的思潮就不可能销声匿迹。
标签: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