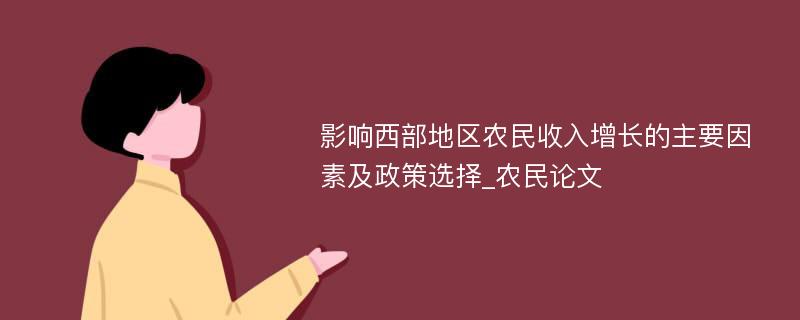
影响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增收论文,西部地区论文,主要因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比较
1.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然而西部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比较优势缺乏,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东、中部地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79∶1.13∶1;1995年上升到1.81∶1.15∶1;2000年进一步扩大到2∶1.09∶1。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596.37元,是最低的贵州省(除西藏自治区外)1374.16的4倍。统计表明,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都低于全国2253.42元的平均水平。(见下表)
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单位:元
地区纯收入地区纯收入地区纯收入
地区纯收入
全国2253.42
山东2659.20
蒙古2038.21 宁夏1724.30
上海5596.37
河北2478.86
吉林2022.50 新疆1618.08
北京4604.55
辽宁2355.58
河南1985.82 青海1490.49
浙江4253.67
湖北2268.59
安徽1934.57 云南1478.60
广东3654.48
湖南2197.16
山西1905.61 陕西1443.86
天津3622.39
海南2182.26
四川1903.60 甘肃1428.68
江苏3595.09
黑龙江 2148.22
重庆1892.44 贵州1374.16
福建3230.49
江西2135.30
广西1864.51 西藏1330.8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不仅如此,在1978—1999年间,西部12个省市区中还有9个省区的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呈下降趋势。1978年四川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比重的87.36%,到1999年下降到83.40%;同期,贵州由80.85%下降到61.66%,云南由92%下降到65.04%,西藏则由1985年的88.77%下降到1999年的59.24%,陕西由99.57%下降为65.86%,甘肃由73.66%下降为61.64%,青海由1980年的106.78%下降到66.35%,宁夏由87.21%下降到79.36%,新疆则由149.11%下降到66.64%。[1]值得注意的是青海、新疆两省区198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6倍和1.49倍,而到1999年下降幅度分别达到40.43个百分点和82.47个百分点,是西部地区下降幅度最大的省区。
2.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与农村家庭收入结构
农村产业结构差异决定农村家庭收入结构差异。从东、中、西部产业构成看,2000年东部农村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7.74%,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92.26%;中部农村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21.60%,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78.40%;西部农村农业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24.30%,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为75.70%。西部农村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比例高东部16.56个百分点,而非农产业却低东部16.56个百分点。这一相反的比重关系,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同年,东部农村居民的收入贡献中,工资报酬收入的贡献率为38%,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为55.73%;中部农村居民的收入贡献中,工资报酬收入的贡献率为17%,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为78.08%;西部农村居民的收入贡献中,工资报酬收入的贡献率为14.69%,家庭经营收入贡献率为77.92%。这说明,中西部地区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使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仍然依赖于传统农业;地区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则源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差异。
3.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水平
家庭收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水平。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为1577.4元,而西部12个省市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都低于这一平均水平,最低的西藏和甘肃两省区,分别为747.1元和880.7元。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有所增加,但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2239元,中部地区为1574元,西部地区为1322元,东部和中部比西部分别高出917元和252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为1.69∶1.19∶1。[2]东、中部地区农民消费水平大大高于西部地区农民消费水平,且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同时,2000年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也反映出来,东部地区为7488亿元,中部为4133亿元,西部为2088亿元,分别占全国的54.6%、30.2%、15.2%。[3]
4.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影响到农村家庭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为52.6%,而西部12个省市区中有10个省市区的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恩格尔系数最高的省份是西藏,达69.2%,与东部地区相比相差甚远。同年,北京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49%,上海为43.15%,江苏为44.70%,浙江为46.07%。从1978—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52.6%,下降幅度为10.1个百分点,但西部多数省份下降幅度极小,贵州仅仅下降了1.8个百分点;西藏从1980—1999年间仅下降了0.8个百分点。[4]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平均为47.8%,四川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高达54.7%。这表明,中国农村虽然经历了20多年改革发展历程,农民生活水平有了逐步改善,尤其是东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东、西部地区差距仍然过大,西部地区农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份额仍然过高。由此判定,西部地区农民的消费水平仍处于满足温饱的初级发展阶段,其小康生活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二、影响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原因分析
影响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有自然、经济、政策、人力资源素质、科技、体制等等,总之,是一系列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1.自然因素:自然灾害频繁,危害极大
自然地理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地区地质地貌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它集中了全国主要的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地域等。西部地区气候受东南季风与西季风的影响强烈,寒、暖、干、湿季节变化很大。受特殊气候影响,西部地区常有灾害发生,西北部水资源匮乏,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旱灾在西部地区的受灾面积中占80%;而西南部常有水灾、泥石流发生。1997年曾因水、旱灾粮食减收476亿公斤,直接经济损失达1975亿元,1998年又因水、旱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72亿元。[5]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与西部农村贫困有直接关联。1989年西部各省区(除西藏外)水、旱灾害的成灾面积达507.4万公顷,平均贫困发生率为15.7%,最高的甘肃达到34.20%,与东部平均贫困发生率2.9%比较,西部要高12.8个百分点。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变化多端的气候,加之人为因素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此是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根源。
2.经济因素:土地有效产出率低,农牧业生产能力低,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
西部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一产业(大农业),农业生产收成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多少。2000年西部谷物单产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6.2%,是东部地区的82.7%;甘肃和青海是粮食单产较低的地区,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7%和57%。西部棉花单产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1.1%,油菜籽是全国的91.8%,甜菜是全国的74%,烤烟是全国的83.3%。西部地区畜产品生产能力也低,2000年猪肉产量占全国30.7%,牛肉占全国25.5%,牛奶占全国38.2%,羊肉占全国47%,绵羊毛占全国62.8%,山羊绒占全国64.6%。[6]西部地区不仅农产品单产能力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同时受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农民收入一直徘徊不前。自1997年开始,全国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逐年下降,1997、1998、1999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分别是上年的95.5%、92.0%和87.8%,2000年农产品收购价格又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粮食类收购价格比上年下降9.8个百分点,2002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体上仍呈下降态势。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产品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需求弹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总量对价格的弹性是:农民得到的平均价格每上涨10%,可以使总量提高2%—5%;而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每下降20%,就会使产量下降4%—15%。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978—1987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弹性系数为0.3,即价格提高10%,产量增长3%,而且价格对出售农产品的刺激作用更大,平均弹性系数为0.67。与此相反,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偏小,价格对农产品消费需求量增长的刺激作用相对较小,反过来影响了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的食品需求收入弹性为0.4435;1997年以后,城镇居民食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出现急速下降趋势,到1999年已降到0.222,近几年来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一直稳定在这一水平上。这表明在农产品尤其是粮食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小于1%。西部4省(四川、贵州、陕西、甘肃)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下降对收入的影响就是有力佐证。2000年与1997年相比,4省区小麦、玉米、水稻、大豆、土豆、红薯价格分别下降了28.6%、20.23%、30.41%、51.56%、25.41%、33.62%,粮食价格的下降对2000年农户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平均为15.39%。[7]在农产品需求弹性偏小的事实面前,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变,需求空间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空间,农民增产并不一定能增收。二是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结构不合理,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从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看,出现了“四多四少”现象,即大路产品多,优质产品少;低档产品多,高档产品少;普通产品多,专用产品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尤其是西部地区,虽然农业资源比较丰富,但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能力低,附加值不高,大量利润流向了加工业发达的东部,这是西部农业经济效益低,农民收入增加难的关键。
3.政策因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扭曲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这对农民收入增加带来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对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作出了很大贡献。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提取了9716.75亿元资金,加上1215.86亿元农业税,共达10932.61亿元资金。但是,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却在不断减弱。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包括支农和农林水气事业费、基建支出、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等)共151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3.5%,随后逐年下降。1995年为575亿元,占8.4%;2000年为1232亿元,比例下降为7.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林牧渔业的比例也在下降,由1978年的3.6%下降到1995年的1.0%,2001年有所上升,也仅为2.9%。扣除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部分,国家对农业的索取与投入之比大约为3∶1。从地域发展看,受东、中、西“梯度发展理论”影响以及区位比较优势的诱使,国家投资向东部倾斜,使东、中、西部农村固定资产投入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东、中、西部农村固定资产额分别为4275亿元、1547亿元和874亿元,占全国的63.8%、23.1%和13.1%,与上年相比,东部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提高0.6个百分点、西部则下降1.1个百分点[8]不仅如此,由于利益驱使,中、西部地区资金大量外流,致使中、西部地区因资金短缺经济发展受阻,加之沉重的税负和“三乱”现象严重,消蚀了农民的部分增收。1997年农民的“三提五统”、“以资代劳”、“社会负担”等费,全国人均180多元,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占现金收入的16%。近几年来,农民向国家交纳的“暗税”平均每年约1000亿元左右,各种农业税平均每年约400多亿,2001年为482亿。[9]有专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而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农业采取保护政策。虽然近年来农民税费负担有所减轻,但是仍未达到理想状态。因此,如果不纠正扭曲的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减轻农民负担,农民收入短期内难以获得较快增长。
4.人力资源素质因素: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长期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中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而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却在不断上升,因此,当今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报酬递增源泉在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的积累和经济制度创新。[10]这说明重视人的培养,提高人的素质,把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经济发展状况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一般来说,教育年限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高教育水平劳动者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低教育水平的收入弹性系数。以2001年不同文化程度劳动力劳均纯收入比较为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年(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劳动收入为2132.56元;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劳均收入为3892.55元;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的劳动力,劳均收入为4919.20元。相比之下,平均受教育年限9年的劳动力,劳均收入高出6年的1.83倍;平均受教育年跟在10年以上的劳动力劳均收入高出6年的2.3倍。2000年东部地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65.7%,高出西部20.1个百分点;而每百名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西部地区达15.9人,是东部地区的3.3倍。[11]东、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不仅反映在文化水平上,更重要的在于市场经济观念和开放意识,而这正是东部农村劳动力收入递增的源泉。
5.科技因素:农业科技应用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程度如何是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西部地区由于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导致产品质量差,缺乏竞争力,市场占有率低,经济发展后劲不足,这是西部地区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有专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0.67亿公顷高产稳产粮田,其中2/3达到高产就能满足将来16亿人口的食物需求。然而,我国对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使得农业技术转化率低,技术落后。据统计,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1%,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5%,而中国仅为0.2%。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1995年仅为0.36%,远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0.57%的水平。如果我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以4%的年增长速度增长,科研投资以5%的年实际增长率(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要到2040年,我国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才能达到0.57%的水平,这与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相差甚远。国家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30%左右,而农业发达国家成果转化率在70%—80%,这意味着我国有2/3的农业科技成果没有转化推广,大量科技成果浪费、失效。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农业科技人员大量流失,部分地区农技推广体系“网破、线断、人散”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一现象在西部农村表现尤为突出。农业科技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
6.体制因素: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保障体系不健全
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缺陷不断暴露。一是农业经营的小型化、分散化,不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目前我国有2.38亿农户,户均耕地7亩左右,西部地区许多农村土地贫瘠且零碎化,这种超小型经营规模所造成的“不经济”和“非经济”情况普遍存在,尤其是农户小规模经营方式的长期凝固,使农业生产规模无法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和扩张。小规模农业生产又形成对先进农业技术的天然排斥,因为分散的小块土地经营不能带来规模效益,农民在土地上投入越多亏损越大,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形成强烈反差。于是,农户在选择生产方式时,偏重于劳动投入型而排斥技术投入型。二是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业部门的利润大量流失,农民很少分享流通中的利润。西部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比东、中部晚,发展势头不足,村级组织名存实亡,产业化合作组织发展缓慢,“龙头”企业少,带动不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和销售各环节仍由分散的农户独立完成为主,一些地区90%以上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销售,深加工产品少,农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三是农业生产保障体系不健全。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区域,尤其是西部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条件和农业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自然风险。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还要冒市场价格涨落的风险。如何帮助农民避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许多发达国家实行了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建立了农业保险制度。而我国对农产品的价格保护范围小、程度低,农业保险的险种少,保险费率高,政府补贴少,保险公司也不愿承接具有高风险、高亏损的业务,这种局面很难保证农民收入有较大幅度提高。
三、西部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选择
1.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发展特色农业
我国西部地区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产品(指比较优势系数大于2.0)有杂豆、马铃薯、糖料、烟叶、生漆、油桐籽、五倍籽、松脂、核桃、紫胶、绵羊毛、羊绒;具有较大比较优势的产品(指比较优势系数1.5—2.0)有花卉、棕片、竹材、羊肉、奶类、山羊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指比较优势系数1.0—1.5)有玉米、高粱、茶叶、水果、乌柏籽、猪肉、兔肉等。[12]西部地区应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按照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培育竞争优势,研制拳头产品,形成产业规模,即“一乡一品”、“几乡一品”甚至“几县一品”,进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产一供一销一条龙产业发展体系,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西部地区农村也要根据自身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进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其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坚持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要加快创建和发展十大农业特色基地,即新疆优质棉花生产基地,广西、云南优质甘蔗和内蒙古、新疆高糖甜菜糖料生产基地,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宁夏、陕西特色瓜果生产基地,云南元谋、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反季节蔬菜、无公害蔬菜、野菜生产加工基地,云南、内蒙古、新疆高档鲜花生产基地,云南、贵州高原优质烟叶生产基地,云南、重庆、宁夏、青海、甘肃名贵中药材种植开发基地,四川、重庆新型优质“双低”品种油菜基地,甘肃、陕西、云南杂粮、杂豆生产基地,陕西杨陵农科城小麦良种繁育和品牌水稻生产基地。[13]
2.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农业就业份额的降低要依托城镇化发展化解。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82—1990年,我国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6510万人,年均转移814万人。90年代后步伐加快,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总量达1.4亿人,年均转移1400万人左右。城镇化发展使非农就业份额从1978年的29.5%上升到2000年的53.9%,与此相应,城镇化率也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0年的36.22%。据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农民收入和城镇化水平的回归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系数为2.04,这说明农民收入增长对城镇化率提高有着很强的依附性。当然,农民收入的区域差异与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密切相关。200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省市有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其城镇化水平分别为88%、78%、72%、55%、49%、42%和4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地区,城镇化水平平均在35%以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关系达0.99。[14]这说明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高,农民收入水平相应较高;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化水平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
3.加大对西部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降低农业的风险损失,增强农户抗风险能力
国家应建立有效的农业支持系统和保障系统,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农业发展支撑体系,即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二是加强西部农村公共设施建设。重点抓好农村道路、通讯、电网、广播、电视、饮水和市场设施建设,以改变西部农村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三是建立国家农产品储备体系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充分利用“绿箱”政策,加大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以保障农业的安全性。四是建立农业科技普及和推广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应用率。五是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保险制度,以增强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减少农民损失。六是支持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15]
4.积极稳妥地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也是近期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应高度重视。作者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关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职责,实行分级负责制。精简机构,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把农民负担控制在合理范围。二是逐步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地方附加税,减少农民分摊集体的公益事业和公共积累以及村级自治管理费用。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从今年起,要逐渐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各级地方政府必须积极贯彻执行。三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费用中央政府应承担大头,省级政府应承担中头,市(县)级政府承担小头。四是中央财政应增加转移支付,加大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公共设施的建设,使西部地区尽快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