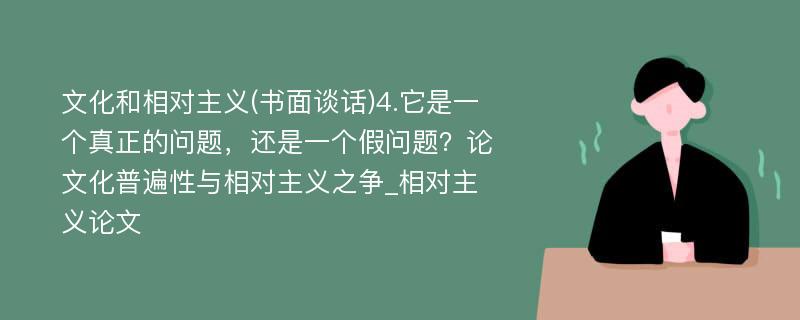
文化与相对主义(笔谈)——4.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关于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笔谈论文,之争论文,文化与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在文化问题上出现过关于文化普世伦理的讨论,这一讨论主要涉及文化的普遍性问题,而此次会议主题则主要探讨文化的相对性问题。事实上,这两个貌似分立的问题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展开的,具体来说,也就是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关系问题。就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我想谈两点看法:(1)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2)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又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个真问题,是个最真、最大的真问题。
关于第一点,我认为,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之所以成立,并且能够成为当前国内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其首要原因在于,将文化的普遍性与相对性的关系问题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内在致思逻辑实质上仍然囿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并由此形成了两种截然相悖的文化态度。这种各执一端的状况,不仅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把当今人类文化困境昭示于众,而且同时在其现实性上,也把整合这两种文化态度而使人类文化得以良性发展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
实际上,现代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普遍性与相对性实则构成了文化的“一体两面”的辩证结构,即普遍性中孕育着相对性,相对性中又存有普遍性。举个例子,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阿佩尔,他们都通过一种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文化交流活动中,本身就实现了一种普遍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简单来说,人类的会话活动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于当中既是一种语义学维度的实现,又是一种语用学维度的实现。如果说语义学代表了语言的普遍性,那么语用学则代表了语言的相对性,语言的语义是与所指的普遍认可相关的,而语用是与具体语境分不开的。因此,人类的日常语言运用本身,就已经为我们彰显出语义学与语用学二者所固有的相互会通的禀性。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语义学与语用学看似相悖实为相通,并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会话活动中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如上所述,关于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争的问题,就其理论层面而言,实际上是个伪问题。
无独有偶,除了西方思想资源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找到消解这种普遍性与相对性之间二律背反的思想资源。在这里,我想粗略谈一下,近年来我从对中国古代的“家哲学”研究中所受到的启发。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家系学”(genealogy)的学说,它的方法既不是整体主义的方法,也不是分析主义的方法,而是一种系谱学的方法。所谓系谱学的方法,就是对家族进行血统、血缘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家系学”的研究,我们也会发现,并不存在文化普遍性与相对性决然对立的关系。
根据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理论方法,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在一个家族里,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家族成员的差异相关关系: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在拥有这种特殊性的时候,又不妨碍整个家族的普遍类似性。王夫之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所谓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趋亦趋哉!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在父与子之间,虽为“异形离质”,却并不意味着父和子没有共同志向。在这种质朴的家庭生活经验中,隐然透露出了对常(普遍性)与变(相对性)的最深刻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家”看做是人类具有“原生态”性质的文化形态,并且透过这种“原生态”结构,可以看到,普遍性与相对性的紧张对立早已在“群己和谐”的家的形式中涣然冰释了。因此,无论是西方哲学思想,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实际上都告诉我们,文化的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是一个十足的哲学上的伪问题。
第二点,我还要说,这两种文化观之间的争论又恰恰构成了一个真问题,一个最真的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由我们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奈格里·哈特在《帝国》一书中所言,是“一个资本主义逻辑全球化”的时代。
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全球化,导致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独白”文化的产生,或者说导致了一种文化话语的霸权主义的产生,而且这种文化话语霸权必然导致其他文化和这种权力话语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文化多元主义或者相对主义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抗衡。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的出现是文化普遍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愈演愈烈的文化中心主义、权威主义思想行为模式的激进反叛。
由此可见,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冲突或文明冲突异常激烈的时代。也正是基于现实性层面来说,文化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争的伪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最为现实的真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无法绕开的一个真实的问题。这个道理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面,子女的独立是相对于父亲的独裁,或者说是相对于父亲的权力话语而言的。今天的文化冲突不仅表现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冲突,而且还表现为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老年文化和青年文化的冲突、科学主义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的冲突等等。这些冲突实际上都在不同层面上凸现了文化的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对立。福柯讲,“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与以文化普遍主义为旗帜的文化霸权主义愈演愈烈之势相伴而生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当今时代的提出。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明一个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解决文化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看到,这一问题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权力话语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根本批判必然超出单纯的文化批判而进入到社会实践领域,也就是说,真正的权力话语批判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实践内容。既然如上所述,这种权力话语是由社会造就的,那么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回到社会中去。因此,我们只能诉诸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批判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无往不克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文化上的权力话语。也就是说,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涉及消除“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消除社会中的“独白”话语(权力话语),涉及一种真正的交往型社会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种致力于在诸种异质性文化中平等的沟通,以形成“和而不同”的文化新格局。从而,才有可能最终消除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紧张对峙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