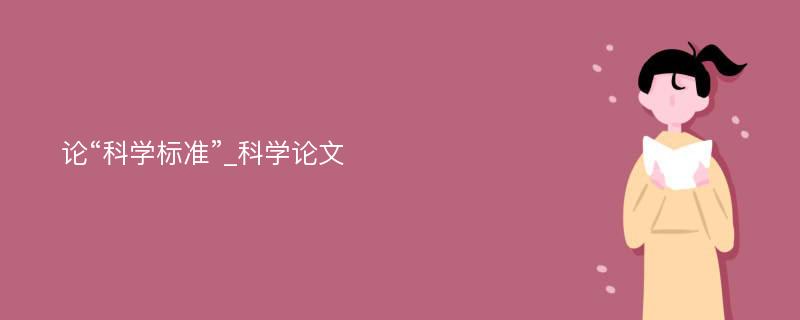
论“科学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辨别事物的优劣、真伪,就需要有判断的根据、区分的标准。同样,科学也有其判断的根据和标准。在古人的蒙昧意识中,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不可能有“科学”与“人文”关系的争论,也不可能有具体标准的划分。柏拉图就曾把物理知识、伦理知识、辩证法统一在他的学说中,亚里士多德则把他的学问分为理论的哲学、创造的哲学、实践的哲学三种,反映了科学的统一。而中国古代也主张,“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一统”。显然,在古代,哲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存在着一个古老的统一联盟。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科学尚无明显的分化,那时虽然出现了一批“巨人”,他们“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都是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1](P6),但他们仍认为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因而也就没有必要讨论科学标准的同一与差异问题。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开始分化,门类多了,自然就有必要讨论其标准。科学分化的主要倾向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因此,探索“科学标准”,也主要应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自然科学标准
自然科学是严密的科学,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真理性认识,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知识体系。尽管对这个体系的价值判断是复杂的,但这个体系中的每门学科都遵守一些所谓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然科学标准。它主要有以下几条:
1.理性标准。自然科学以认识和把握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为宗旨,把理性视为科学研究的最高原则,靠理性来把握世界。在科学家看来,自然科学高度发展之后,在人类社会中,清醒而富有创造力的理性将占主导地位,世界应当是理性的世界,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应当是科学的理性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也都应纳入法制理性范畴。科学在探索客观世界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时,要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尽量排除非理性因素,只承认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不承认信仰。科学把理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宗教则和科学相反,靠信仰来维持。宗教提出的命题、原则、假设,都以信仰为前提,主张“心诚则灵”,“上帝就在你心中”。宗教所崇尚的东西,无须研究和论证,只要求人们诚心诚意地去信仰就可以了。因此,理性还是科学和宗教的分水岭。那么,怎样才能坚持理性原则呢?恩格斯指出:“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1](P112),“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历史中被概括出来的”[1](P75)。事实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全面、最高的理性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最具普遍性的理性原则。相反,信仰主义、宗教、伪科学等,则不符合理性原则。
2.逻辑完备性标准。理论结构的逻辑完备性与否,是判断真伪科学的另一准则。成熟的自然科学,其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是完备自洽的,往往可以用数学推理来证明;其普遍规律,能用数学模型来表达。无论是对动力学规律还是统计规律,也无论是复杂性问题还是混沌问题的探索,在探索和表述时,都要求逻辑的完备。如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一些基本的原理,都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成熟的数学模型;而宗教、迷信、伪科学和一切愚昧说教,因多以信仰为基础,所以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成熟的数学模型;它只要求人们去相信某些假定,而不要求证明,实际上也无法去证明,正如任何数学推导和逻辑演算也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样。事实上,一切神秘主义的东西,因其非理性的本质,也就都是非逻辑主义的。因此,对一种理论性质进行判别时,可以通过研究其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过程、逻辑结论是否完备自洽来进行。当然,在人类全部科学实践中,在认识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历史长河中,会出现一些“科学悖论”、“科学佯谬”、“科学问题”,如“三体问题”、“光度佯谬”等,这些科学认识中的矛盾是科学发展的契机,它和信仰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非逻辑主义完全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
3.科学实验、科学实践的标准。判别科学和宗教的另一标准是实践性。科学要靠反复的实验、实践来证明和发展,科学实验是人类最伟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文明的动力的源泉。一切科学理论都要在实验、实践中经受检验。人们要通过实践发现真理,通过实践发展和证明真理。一个重大的“科学判决性实验”就可以证实、证伪或推翻某种结论。一切宗教、迷信、伪科学、信仰主义都经不住实验、实践的检验,一切信仰的光环都会在科学实践面前黯然失色。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因此,实践性是判别真伪科学的准绳。
4.可重复性标准。可重复性是科学评判的操作方式,真正的科学成果、科学结论是可重复的。例如,一个化学合成实验,在地球环境下,无论谁做,也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只要反应条件一样,结果都是相同的,而且可反复无限地重复。这就叫作科学的“可重复性标准”。一切宗教、迷信、伪科学和信仰主义的东西,都不具备这种可重复性的品质。科学的这种不因时间、地点、主体更换而变化的可重复性,正是事物的客观性、客观规律性的正确反映。而宗教、迷信、伪科学和信仰主义则都属于主观臆造的产物,背离客观规律,当然就不可能具备可重复性。
5.唯物论可知论标准。科学要从实际出发,要通过实验、实践来发现、发展、证实真理,因此,必须遵循求实求真的认识方法,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科学的任务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研究和探索,因此必须也必然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科学的目的是揭示世界的奥秘,把握世界的本质,因此必须也必然是可知论的。如果没有唯物论的可知论前提,也就没有科学了。在人类认识史上,一切宗教、迷信、信仰主义都是以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作为假定和前提,用唯心的先验论演绎出荒谬的迷信和愚昧,反对科学真理,中世纪的黑暗就是神学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对人类心灵无情地戕害。所以,只有辩证唯物论的可知论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前提,才是自然科学生长的理论沃土。
6.科学的简单性标准。简单性质则和形式化是科学理论表述的特色,是从理论表述上判断真伪科学的原则。对科学和迷信、科学和伪科学的判断,从理论形式和表达上,可以其是否符合科学的简单性原则,是否能逐步形式化来划分。科学真理作为事物客观运动规律和存在方式的正确反映,往往是简单明快的,“简则易知,简则易明,简则易行”,马克思主义就是“把辩证法简要地概括成对立统一的规律”。“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2](P234)。真正的科学结论往往是简单明了的,是正常人可以学会、可以把握、可以运用的,其表述决不神秘莫测,尽可能用简易的语言文字、方程、公式,表述完整、准确的信息。而且一旦发展成熟,还可以做到形式化,用计算机处理。相反,宗教、迷信则要故弄玄虚,复杂化、文牍化,搞所谓烦琐哲学。这些引经据典、繁杂混乱的烦琐哲学,不知浪费了人类多少精神力量。现代管理学认为:“简单是一种智慧,简单是一种美,简单就是高效率。”[3](P1)这是颇富启示意义的思想方法。
总之,理性标准、逻辑完备性标准、科学实验和科学实践的标准、可重复性标准、唯物论可知论标准、科学的简单性标准是所有自然科学共有的内在标准,也是科学价值判断的凭据,一切科学的理论都符合这六个标准,而一切主观臆造、脱离实际的经院哲学、封建迷信和伪科学都会背离这六个标准。这主要是对自然科学而言。对人文科学而言,如经济学、定量社会学、法学等也大体符合以上六条标准。但因人文科学研究对象具有更为繁杂的复杂性,所以人文科学的标准就更为复杂一些。
二、人文科学标准
人文科学是指对人类社会和文化艺术进行研究的知识体系。如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学、语言学等等。这些学科研究的时空跨度,远不如自然科学大,但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最难下判断的人的“恨、爱、情”等极为复杂的感情世界,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极为复杂的心理世界的“激情、冲动、灵感”,涉及“人本、人性、人道”等一系列复杂的价值判断,要拟订统一的标准十分困难,但总有一些同一性可以探索。
1.法律道德标准。人文科学肩负着的共同使命是塑造人、武装人,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向上,教化人们走向成熟、遵纪守法,弘扬高尚道德,宣传“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以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来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些表明,人文科学承担着一定的道义和社会责任。
2.先进性和新颖性标准。人文科学的一大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新思想,为人们不断提供精神动力,解决思维方法,促进观念变革,推进理论创新,推进社会发展。人文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体现出先进的“时代精神”,健康进取的先进文化。因此,新颖性、先进性、求实和创新是人文科学发展的原生力之魂。
3.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标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不断增长的,因此,对人文成果、人文产品的品质和数量会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人文科学是满足这种需要和要求的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天职和使命,是人文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所以,人文科学要不断地创造先进的精神财富和精神产品,不断以自身的繁荣推动社会的繁荣。从这个标准看,有利于这种繁荣的思想理论方法就是好的,反之,导致“文化禁锢”,形成“文化沙漠”。因此,只有形成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繁荣发展的人文科学理想生态环境,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4.美学和欣赏性标准。人文科学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包含了人文学家按着美的规律进行的创造,所以,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有一定意义上的美学标准。例如,艺术形式和内容只有符合美学标准,才具有欣赏性,使受众赏心悦目,愉悦人民的精神。因此,对人文科学进行评判或进行价值判断时,应遵循普遍的审美原则。例如,应辩证地考察人文成果的激情与感受、实际与典型、个别形象和一般规律等。尽管在审美方面,个体差异较大,但由于人类共同的物质基础、共同的生理心理规律、共同的主客体关系等决定着人们对和谐、鲜明、匀称等共同美学原则的追求又是一致的,这反映着人类客观主体化中的同一性。在人文科学中,普遍地存在着自然与社会的人化,存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象化、典型化;体现着主体与客体的联系美、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契合美、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美、个别与一般的和谐美、内容与形式的一致美、原因与结果的奇异美等一系列辩证美学关系。因此,评判人文科学时,美学判据是十分必要的。
5.典型性和独创性标准。自然科学研究追求自然界中的普遍规律,人文科学则往往是用个别表达一般、用具体反应普遍、用形象思维表现抽象本质。因为人文科学是通过个别典型事物反映一般的普遍本质,通过个别典型表达对世界本质的情感体悟,经常用典型形象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与发展趋向。因此,典型性是人文科学的判据之一。典型是具体的、个性化的、不可重复的,所以,对典型的塑造往往渗透着人文学家的灵感和激情。他们用个性化的不可重复的形象表达对世界本质的情感体悟,并以此引起受众的共鸣,激发受众情感与冲动,主张社会公正、良知和正义。
6.生产力标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只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才能推动人的发展和人们个性的解放。因此,在判断人文科学价值时,应当看其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是公认的理念,而主要作为精神产品的人文成果,其质量和数量是由精神生产力的强弱来决定的。一般说来,精神生产力生产精神产品,物质生产力生产物质产品,但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又是统一的——精神生产力是灵魂,物质生产力是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动转化。一旦先进的精神生产力与先进的物质生产力相互匹配,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进器”。因此,一般而言,凡是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文化艺术、理论观点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可取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尺,在推动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人文精神中,最有价值的是推动人类的“工具革命”。先进的人文成果,要给人们提供先进的思想工具,从而促进物质生产工具的不断创新与发展。
总之,人文科学的法律道德标准、先进性和新颖性标准、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标准、美学和欣赏性标准、典型性和独创性标准、生产力标准等六条标准是统一的。这些具体标准要求人文科学必须做到“真、善、美”相统一,全面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三、科学标准的同一与差异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属于“同根二枝”,二者在发展中互相促进,同是人类文化的“姊妹双花”,共同形成了人类文化形态。尽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具体标准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共同性,表现出四个共同特点。
一是对象的统一性。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客观世界。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就世界的演化发展而言,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演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第25章)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是科学,科学是客观存在的能动的正确反映,只不过自然科学偏重探索自然界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人文科学偏重探索社会运动的存在方式和运动规律,二者从主客体关系、主体能动反映世界这一大角度来看是统一的、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能动反映的结果。
二是研究目的的统一性。自然科学用理性的完美逻辑反映和表达自然界的规律,人文科学用感悟的激情及典型形象反映和表达社会存在,二者研究的目的都是要反映和把握世界本质,在这一点上,二者是完全统一的,都是力图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世界的本质。
三是成果来源的统一性。自然科学成果的根本源泉来自于科学实验的实践,人文成果的终极根源在于人类社会实践。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成果,都源自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共同进步。在人们对未知的探索中,面临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中介,都是实践的方面,是人们对于世界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把握的不同的但又必须的维度。就科学来源而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四是研究方式的统一性。尽管自然科学是用理性的严密的公式反映由盲目自然规律支配的客观自然界,人文科学用典型的形象个性化的特殊事物体悟和表现受人的激情与目的性影响的复杂的人类社会本质,但二者在研究方式上还是有共同的统一的东西。首先,两种研究者在研究中都遵循着共同的思维规律。不仅自然科学家需要和使用理性的思考,同样,人文学者也需要和使用理性的思考与判断;反之,不仅人文学者需要和使用超越理性的灵感、顿悟、猜想、类比、对称、外推、联想、直觉等创造性思维,同样,自然科学家也需要这种非逻辑的冲动与创造。其次,两种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都不外乎两个方面:理论方法和实验方法。这两种方法是对统一的物质世界进行能动反映的基本方法,也是二者统一的方法。再次,情感思维与理性思维、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都是人类统一的思维的不同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人脑的功能,所以是同一的,这种同一,表现为研究方式的一致性。
五是知识增长方式的统一性。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知识推动着技术和实践大踏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科学知识是科技创新、科技进步的基础,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知识积累可能产生的一种结果,是知识积累的一次升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其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知识的增长。在知识的增长方式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扎实学习、长期积累、逐步提高的过程,都是一个批判地借鉴、吸收、选择的过程。自然科学知识需要通过细致的学习而逐步积累,人文科学知识也同样需要通过细致的学习而逐步积累,任何一种知识的增长都没有捷径可走,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此可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目的、来源、研究方式等,都是统一的。当然,这种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统一反映了世界的统一性,反映了人和自然的和谐与统一。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进步,越来越证明“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念,也就愈来愈成为不可能的东西了”[1](P305)。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标准不仅有统一性,同时又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预言与猜想。自然科学的物理规律,可用动力学方程精确计算,准确预见。社会科学不具备这种预见能力,只能停留在推测、猜想和笼统模糊阶段。
二是重复与独一无二问题。可重复性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疑问的。在自然界中,“就我们的直接观察所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也重复着”[5](P128)。相反,在社会历史中,“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过这样的重复,也绝不是在完全同样的情况下发生的”[5](P128)。所以,人文科学不能也不可能去“重复”。真正的人文成果和艺术成果,是典型的形象,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果说,可重复性是自然科学成果的试金石,那么,独创而不重复、独一无二则是人文瑰宝的灵魂。
三是数学逻辑问题。在自然界中,简单系统的线性因果关系可以用数学逻辑精确描述,社会系统则不能。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应用数学方面,差距较大,前者已发展到比较高的程度,后者则停留在初等数学和一般统计方法的水平上。
四是实验与调查。自然科学可用反复多次的实验进行验证,人文科学则多用调查调研,通过采风和考察了解一些现存的不可重复的事件,用调查结果描述性或统计性地说明事物的本质。一个用反复实验验证自然的普遍本质,一个则用“解剖麻雀”由个别推演一般、用典型示例揭示普遍本质,二者在一条线的两端“相向而行”,两种科学存在着思维路线和思维方向的差别。
总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尽管都是存在的反映,但在预言和猜想、重复与独一无二、数学逻辑、实验与调查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别。所以,两种科学的统一是“有差异的统一”而非“相同”。从本体论上讲,世界的统一性反映为科学文化的统一性,世界的差异性反映为科学文化的多样性。由于人的思维是极为复杂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人的思维中都存在着两对比较普遍的矛盾:其一是理性与感悟的矛盾,二者一个用逻辑推理反映世界,一个用典型形象表达世界;其二是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二者一个用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说明世界,一个用客观世界的虚幻反映说明世界。因而,理性经常处在感悟和信仰的夹击之中。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应当崇尚理性精神。从哲学角度看,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二者终将出现“大统一,小差别”的局面。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将结成更为紧密的联盟,共同为人类文明进步创造日益丰富的文化硕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