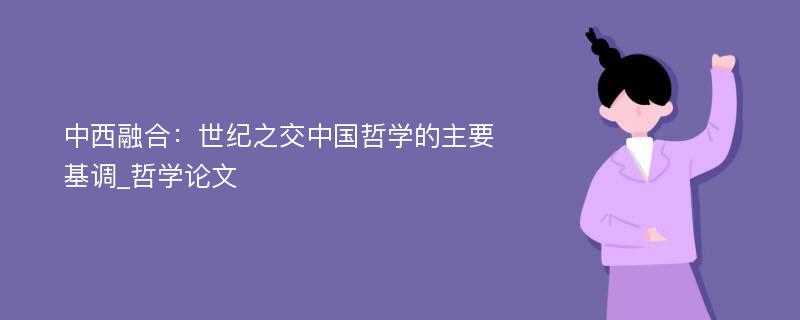
中西融通: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主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调论文,世纪之交论文,中国论文,中西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中西哲学与文化的是本世纪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主调。在中西哲学中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将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契机,而中西哲学的将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一环在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中西的哲学的事例将使中国哲学向更具时代性的实践功能的方向迈进。融合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途径,也是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趋向。在中西哲学的关系上,“求同”不是主要的,明异而求通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中国哲学 融通 超越 明异 求通
哲学发展史上有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现象,即不论其地域的、民族的渊源多么复杂,多么差异迥然,都会在其发展深化的历史过程中相互、吸收,并都会在这种相互融通中得到发展从而既超越自身,也超越对方,这似乎是哲学与文化自身发展的一条规律。注意到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展望世纪之交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前景和未来趋向或许有一定的方法论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先秦至两汉时期中国哲学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的融合主要发生在华夏民族共同体内部产生于不同域的哲学与文化的各系统之间。汉末,源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士,经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开始了中国哲学第一次与异域文化的接触、撞击、归一的结果;明末以后,西学东渐,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开始对中国哲学文化发生影响。鸦片战争后1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因而中文化的是本世纪哲学与文化发展的主调。
由佛教传入所引起的中外哲学与文化的所的直接后果,是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深化但是,中国哲学在理论上虽然有重大超越,而从其基本点说它却未超出传统经学的樊篱。自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并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哲学和宗教以来,中国哲学和文化面临着自佛教传入后的又一次挑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中外哲学的又一镒。自1840年西方用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厦门后,西学大量涌入,此时人们才惊异地发现中国落伍了。从林则徐、魏源、王韬、薛福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之时起,中西之学的融通才有所推进,但此时尚未形成真正融通中西的哲学思想体系。到康有为、严复等人出现后,民政部才有较大改观。可以说,整个中国近代哲学史,是以中西哲学的撞击和为主基调的。相对于佛一儒的冲突与来说。这次文化冲突与无论就范围和内容都较前次广得多。它不仅限于思想观念的层面,而且涉及物质文化、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几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关系蝇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的总是,因而中西之学的所遇到的阻力较之前次要大得多。
中西之学交融之初遇到的阻力首先来自19世纪70年代国派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格。洋务派把西学的引入只限定在如船坚炮利等物质技艺方面的拒绝触动封建社会的根基。真正能冲击并谋略突破这一防线的,是戊戌维新时期涌现出的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他们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哲学与文化典籍,并试图建立融通中西的哲学思想体系。康有为是较早融通中西的人,他以中国传统儒学为基础并借助儒学来宣传西学,采用“托古改”制的方法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他认为西学本一中学西方主张的君主立宪、民主政治是中国古代孔孟儒家“预言之大义”(康有为:《论语注》卷15)。在哲学上,康有为把西方自然科学中的以太、电、磁等要领与中男传统的“仁”、“不忍人之心”等相比附。这种中西学的机械杂揉在谭嗣同的思想城敢有明显表现。谭氏提出的“仁一通”理论亦将“仁”与“心力”、“以太”“电”相比附,说明此时的中西融合还处在外在的浅层。相对地说,昨在中西哲学融通的深度上有较大进展。严复比较系统地译介西方的哲学理论,特别是郝胥黎的进化论和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严复把英国的经验哲学和归纳法等逻辑思维方法介绍进来,强调“即物实测”的经验观察和“内籀”的归纳思维方法,从而使一直与传统心性论和道德修养论难解难分;的认识论向以经验实测为基础的认识论过渡,从传统的、悟性思维向逻辑思维过渡,这是西学输入和中西哲学融合的重大成果。进化论和经验论的输入,是近代西学输入的两大主流,但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还属于西学的译介阶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西文化的冲突了社会的前台,也使中西哲学的融合会通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马中国哲学的讨论放到了国际哲学思潮的大背影下,使之与当时时代的关注的科学与哲学、理性与非理性等起来。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所谓“西化派”自学地介绍西方文化,并用“西学”排斥“中学”,这处态度固然偏颇,但其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还是应该肯定的,这种努力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与哲学的融合。而当时的“东方文化派”虽然极力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但也不能不正视世界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东方文化派”主将梁启超、梁漱溟等人虽固执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却仍能在对中国近代西化道路反省的基础上努力会通中西文化。析儒家正是继承着这一路子而创立了各处的思想体系。
中西文化的融通本世纪30至40年代终天在哲学了有所超越,一些与传统哲学有异的新的哲学体系出现了。较有性的是一国传统文化命运和前任的学者如梁溟、熊十力、冯友兰、钱穆、金岳霖、贺麟等,他们大都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来解释传统哲学特别是会面学,从而对西方文化的做出创造性的。梁漱溟在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的优劣之后虽然仍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主绦引导人类走中国的路、行孔子之道,但他在创建体系时还是吸收了西方哲学的某些思想,其中罚要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并将其与儒家哲学相印证,。“处心探中印两方之学”的熊十力建立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是在新的条件对中国文化中佛教唯识宗、禅宗与儒家陆王心学的熔铸改造,尤其代表了二三十会儒合流的思潮,但也受到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的主义、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他所建立的以“即心显体”、“即用即体”“求自识”的作用关系为的哲学体系,翔实集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之精义亲有所超越。这显然与他博采众学而不为一家之言所囿的包容性的态度与方法有关。相对地说,冯友兰在融合中西建构其“新理学”体系方面更突出些。他自谓其体系是“接着”魏晋字的宋明理学讲的,实际上是把西方哲学中罗素的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通的结果。贺麟在融通中西文化方面表现得更为自学和清醒,他指出“一如鳊文化的输入,在历史曾展开一个新儒家运动一样,西洋文化的输入,无疑亦将大大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新的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儒家思想则生存复活而有发展”。贺麟建立的“新心学”体系,正是把传统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黑格尔主义的产物,其体系虽并不一定正确甚至很偏颇,却已明显使心学具有了新的时代气息。金岳霖建立的“知识论”体系,开始了西方尤其是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并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学派学说如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哲学、英国的经验主义以及康德的认识论等等,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理学的结思想的融通。中西哲学的是他建立“知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
20世纪前期出现的兼综古今、融汇中西而开创的这些哲学体系迂中国哲学扔内容,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哲学跳出经学樊篱、铸成新的哲学品格应该说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所建立的体系虽然并不成功,但毕竟是一次可贵的尝试。20世纪中后期,主义哲学传入中国,这是影响此后中国哲学发展的重大事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它传中国后迅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国哲学与文化的主导方面。但毋庸讳言,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苏俄的消化并以此为中介传入我国大陆的,这就使中国人在对其理解时受到更为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总之,本中西哲学交融的深化,意味着中国哲学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如果说自19世纪中叶西方哲学大量传入以来,自理中西哲学的关系是一代一代中国人关注的重要总是人们不断的自学或不自学地做着事例中西之学的工作,并做出了具有超越贡献,那么,今天时代的需要将促使中国哲学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化而决不会改弦更张。今天的世界更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文化的依赖和密切交往,已使世界日趋一体化。在这种民政部下,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发展日益成为不可能,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体系想封闭起来走自己中国哲学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为背景,来确定中国哲学在跨世纪之后的总趋势。这样,如果试图以某种哲学哲学戏定模式事实上也已不可能,未来哲学的将是中外双向交流、多元互补的。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说,尽管二者的交融已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但由于中西文化传统毕竟差异颇大,价值观念的冲突严峻,加之以儒家文化为分期的东亚文化圈已经形成,所以要在短时期内实现中西文化的合是不现实的。但是深层的融合不仅是可能有,而且是历史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当然今后的中西融通既不同于初期阶段的比附,也不是如同佛教传入时的中国人所进行的“格义”,而是有目的的选择,深层次的内在融通。这种融民非如以前主要为西学输入中学,而将在双向轨道上和广阔的领域内发生,不仅西学要融入中学,中学也要走向世界。就中国哲学的未来趋向说,面对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广泛吸收、接纳西方哲学中有益于现代化的合理成分,使之“嫁接”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砧木”之上,从而形成既富于时代气息,又不失中国本色并具有较强实践功能和持久活力的哲学将是可能的。如刘述先所说:“我们的真正问题既不是抱残守缺,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如何去去芜存菁东西文化的传统,针对时代的问题,加以创造性的综合。”①从当代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中西相兼、融合创新,将是中国哲学未来的基本走向。
现在要勾画出未来哲学的模样还相当困难或者说为时尚早。只能就中国哲学在世纪之交将如何于中西事例得到发展做一点预测。
在中西哲学融通中促进思维方式的变革将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契机,查中西哲学的将是实现这种转化的重要一环。吸收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资弥补中国哲学之所缺的合理思想和思维方式当是首要的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将西方现代哲学中较有影响的分析哲学、解释学、现象学以及学等理论的合理万分与中国哲学相融通是更应该引起注意的方面。中国传统哲学重整体、重直觉的特点虽有其合理性,但不尚分析、疏乎逻辑的弱点也是不可回避的,当然这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有关。中国人一向将天人、主客、道性看成是合一的,把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分的,故不尚分析和不重逻辑而强调整体恶性循环的直接把握是中国人“自觉选择的结果”②。这种思维虽经控的冲击已有有很大变化,但仍不能适应时代。吸收欧美的分析哲学并使之与中国传统思想互补融通,形成既有严密逻辑分析又不失整体性直觉性思维优势的思维方式是很有希望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摈弃传统的整体性思维。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研究对象从实体研究向场的研究的转变从线性研究向非线性研究的转变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意义。相对于西方的哲学思潮来说,这种哲学的转变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意义。相对于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理论等都将会的哲学的一个趋向。同样,有造反地吸收、融通当代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理论等都将会在改善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方面起积极作用。例如:解释学的融入,也许会使中国人的对历史、传统、经典的价值的认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使传统在未来哲学解释者的创造性活动中重新获得再生的能力,从而使传统以新的意义进入现代。
其次,在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中西哲学的融合将 中国哲学向更具时代性的初中功能的方向迈进。中西哲学的融合不能总是仪在文献的事理和诠释上,虽然这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更应立足于现代化的初中初中将是联结古今、中外从而进行综合综合创新的中介和桥梁。
重要的不在于,哲学需要丫在人类未来的高度为解决时代的突出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现代化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至少在跨世纪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只能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当今西方国家面临的所谓“后现代”社会问题的却并不会限定在他们的国界之内,它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道德失范、意义失落、人际关系冷漠、精神生活空虚等,虽然我们对此还感触不深,但化社会的效应已见端倪。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在西方“勘天”思想下,科技的进步使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界没有人类触及到的领域愈来愈少。但是当人类在欢呼对自然界的胜利的暑假,自然界总要报复人类: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的枯竭同眇,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环境的失调共生。这些毋庸置疑的事实,促使世界上的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了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和谐、天人合一等朴素的宇宙系统思想是自《周易》以来一直为哲人们所重视的传统,这一传统所表现出的的令世人瞩目。只是由于中国人有过分强调主客的同一而了与自然抗争的一面,这一点在近代也受到了西方勘天役物思想的冲击。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弊端暴露出来们不能不对天人哲学进行深切反省。为哲人们所中西哲学的交融互补将是未来建立人与自然新型关系的出路据。既积极主动地与自然同时又必须自然因有的规律,在天人的同一中把握对立和在天人的对立中顾及同一,这样,自然界就不仅是被征服的对象,重要的还是被当作人类关切的对象,从而使天人关系达到新的协调。
在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在本世纪的社会变革中挣脱了传统伦理对人的个性、尊严、价值的压抑和亵渎而获得了个性独立和人格尊严,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但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像幽灵一样一直纠缠着人们。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在探讨着这一争论已久的问题。在这些争论中,传统随着来自“批判”和“继承”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一方面,儒家传统中一些在今天还有影响的守法观念、家族本位、人治传统、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等思想观念与当今现代精神相抵牾,甚至是现代化的阻力,所以必然要为所排斥;另一方面,人们面对商品化社会所出现的或已见端倪的“道德失范”、“意义失落”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非人性化的倾向,人们又不能不把目光转向中国的儒家传统,重新儒家的道德理性、心性修养、重义重教等传统的价值。这就使我们在解决儒学相结合,当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正确。在维护儒家传统的文化价值,保护民族文化精神方面,当代新儒家的努力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以及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一直在进行着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事例中西哲学与文化来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谋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努力。他们即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又有对西方社会的体验和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因而能通过中西并在理论上有所超越。当代新儒家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我们谋求建立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时,重视儒家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的功能和道德理性的价值,使之与现代精神事例从而服务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是中国哲学应关注的重要方面。当然,强调提高道德并不是又要压抑个性,而主张把中国传统的群体价值观与西方注重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个体价值观结合起来,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从而形成积极向上、协调健康的新型人际关系。这样,个人的自由发展将与群体的充分发展相辅相成。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是哲学与文化发展的规律。取“和”而去“同”是未来哲学的方向,“和”才有新东西的生成,才有发展。融合是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和途径,也是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趋向,而中西哲学与文化的融通仍将是这一趋向中的主调。在中西哲学的关系上,“求同”并汪是主要的,明异而求通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1995-01-23
注释:
①②刘述先:《哲学与时代》,引自《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8页,第2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