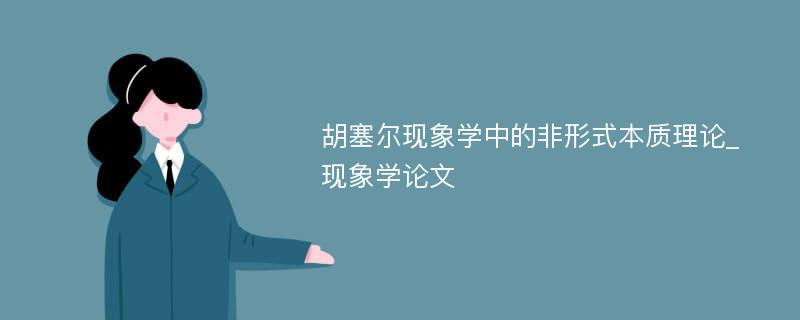
胡塞尔现象学中无形式本质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学中论文,本质论文,形式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塞尔现象学的重点在于意识的意向性理论,即研究在原来的被给予方式上,意向行为在对“对象种类的一般规定性”的原本性朝向过程。就此而言,现象学可视为有关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的关系问题,但是,当涉及“纯粹本质”领域时,本质以及在意向性领域中的本质等问题成为其至关重要的前提。
若把现象学视为本质论,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把本质的属性及其地位确定下来。在现象学中,意识行为的特征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本质”的对象可不附于确定的事实。在意向性领域中,对象的种类和其被给予方式与相应的构造此对象的意向行为的普遍、本质状况和联系,也就是说,对象的规定性与意向行为的本质描述有一种先天的相关性,后者绝对不允许自身完全溶入对象的规定性之中,而使自身成为一种事实的对象。于是,在现象学中,“本质”本身并不是一个对象,同时也不是一种确定的形式(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语言的逻辑形式”),而是一种无形式之形式。
一
正如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有关“本质和本质认识”(这部分由黑尔德编入胡塞尔文集《现象学的方法》中)所阐述的那样,现象学不是以事实,以在个别人那里可经验到的感觉资料为课题,而是一种对本质的关注。它倡导一种对事实特征向作为它们基础的本质规定性的过渡。这种本质还原对任何意识的个别情况都是必然的和普遍有效的。当我们在讨论个别事实时,总能涉及一般本质,但后者决不有象洛克那样被归结为抽象的个别特征。对本质领域考察本身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它向我们表明在思考普遍的东西对应着眼于对意识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而不是对个别化的本质进行心理学重建。
胡塞尔通过本质还原达到了一种完全“观念化”的本质认识。他写道:“‘本质’首先标志着作为个体的何物而处于个体自身固有的存在之中的东西。任何一个这样的何物都可以‘在观念中被设定’。经验的或个体的直观可以转变为本质直观(观念直观)——这是一种可能性,它本身不能被理解为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能理解为本质可能性。”①也就是说,一个这样的何物当它具有物理形态的意义而存在着时,它的事实性的方面的东西是既受限制又可以改变的,因为“任何一种个体的存在都是‘偶然的’”。②虽然,一个这样的何物在可能的经验范围内可以随意改变自身,但是,它事实性的偶然性的意义本身不是随意的,因为每当具有一个偶然性意义本身时,总是涉及到该意义本身的本质,如“红”的本质,某物虽可为“红”或“黑”,但“红”或“黑”本身具有一个本质,它们是与必然性相关的,并具有本质普遍性。于是,个体虽在可能经验的事实性范围内有自身的表现形式,这点作为个体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每一个偶然的表现属性必有一个本质,这点又是必然的和普遍的。“任何偶然的意义都在于具有一个本质并且因此而具有一个可纯粹把握的爱多斯(Eidos),并且这个爱多斯处于不同的普遍性阶段的本质真理中。”③因此,当透过事实性的偶然性的屏障时,我们就进入了普遍性本质的领域,而本质直观是该领域唯一可使用的方法,“被直观之物便是相应的纯粹本质或爱多斯,它们或是最高的范畴,或是最高范畴的一个特殊种类,或是下降为完全的具体性。”④所以,当我们涉及一个这样的何物时,它必定被归入一个由不同层次等级的本质种类之中,换言之,从一个具体个体可以被纯粹地理解到从它作为“自身之中”的所有特征所可直观到的所有因素,而这些必属于那些根本的范畴存在。不过,这里有一个最高的类似本质和一般种类的区别。
本质直观作为个体的何物“在观念中被设定”,它当然以个体的事实性显现为基础,以“一个可见的存在为基础”。⑤但是,本质直观不仅限于此,不然它就等同于感性直观--在经验中关于一个个体对象的意识。“本质直观的被给予之物是一个纯粹的本质。”⑥这里的本质仍是一个对象。不过,这个对象是本质直观在对某物(经验范围上)的意识中所看到的并在本质直观中“自身被给予的”。因此它既赖于对某物的意识,同时又先于一切思维判断,而置于二种“原本给予性的直观”之中。“这种直观在本质的‘真实’自身性中把握本质。”⑦也就是说,对本质的自我显现的一种直观。
本质直观和个体直观的关系,是胡塞尔发展意识的意向性理论的基础,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体事实对象和它的本质形式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是对前者的描述,但同时又超越于此,而发展为一种自由的可能性。对此,胡塞尔写道:“如果没有那种将目光转向一个‘相应’的个体的自由可能性以及构造一个示范性意识的自由可能性,那么任何本质直观都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进行观念直观的自由可能性以及在观念抽象中将目光朝向相应的、示范性地寓于个体可见之物中的本质的自由可能性,那么任何个体直观也是不可能的。”⑧既然纯粹本质以本质直观在经验中被给予,那么,前者可无关乎经验的事实而原本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换言之,本质认识与事实认识无关,前者必不能推演出有关后者的任何真理。这的确沿用了莱布尼兹的有关必然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胡塞尔写道:“对本质的设定和首先对本质的直观把握并不蕴涵着对某个个体此在的设定;纯粹本质真理并不包含着关于事实的断言。”⑨因此,有关对本质的论证不能诉诸于事实认识,只能在本质直观中。
二
若单独实施本质还原,那么就会达到超越的对象。一个本质就会被对象性把握,以致出现对本质的分类和本质的个别化等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本质的个别性的判断必定是绝对的一般性判断,因为本质直观“是以本质的个体个别性的可见为基础,但却不是以对这种本质个体个别性的经验为基础。”⑩个别性的本质在本质直观中被显现和把握。它从来不表现为一个经验的可能性,而是一种本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事实上是一种实事状态,在此状态中我们可以以一种本质可能性的状态达到任何的客观化对象,而这些对象是作为在本质真理中的存在之物。于是,“只要本质的分类和本质的个别化是对一个本质一般的实事状态的分类和个别化,它们便是本质必然性。”(11)因此,这些本质自身的个别性的判断本身,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一定是一般普遍性判断,并一定置于实事状态之中,并保持一种本质的可能性而从来没有形成客观化的层次和分类。纯粹本质判断就是在对个别化本质的判断中,而不是在对其设定中。由此,“本质判断的行为、本质判断或本质命题、本质真理(或本质的真实命题),这些观念是以明显的方式互属的。”(12)纯粹本质性的去(或正在)判断,在这个本质实事状态中,被判断之物的含义就绝对不可能固定化或确定化,而该对象也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
因此,作为对于纯粹本质性的判断,它本身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存在的类(即一个存在对象),而是一个形式的范畴的类。它“只被看作是能够用具体内容加以充实的逻辑的空形式。”(13)于是,形式本体论就是有关对涉及“一般对象”的所有形式范畴的一门学科。它着意发掘一般对象所包含的“形式范畴”,并探索这些形式之间的联系。作为纯粹本质判断,一种本质的可能性本身仍作为一个本质,但它适用于所有可能的本质。因此,形式本体论“它尽管是一个本质,然而却是完全‘空泛’的本质,这个本质以空泛形式的方式适用于所有可能的本质。”(14)鉴于这种“空泛形式的方式”,范畴被标志为形式化和分析性。
“形式本体论在自身中同时包含着所有可能的本体论的形式。”(15)这种形式又以范畴来表述。事实上,作为范畴的概念和作为范畴的对象是有区别的。前者表示一种含义意义上的概念。不过这种含义不是某一个别对象本质的“含义”,而是“含义一般”即作为“含义范畴”体现在命题(判断)的本质中的各种命题、命题成立、命题形式等等基本概念中,并且“还须顾及到本质真理”,(16)以及表述形式本质本身。就此而言,“含义一般”应理解为本质直观的形式表述,它决不能还原为某一个别性对象本质的“含义”,而只能是一种所有本质的可能性。如此,“‘含义一般’便是最高的属。任何确定的命题形式,任何确定的命题成份形式都是一个本质的个别性。”(17)因此,作为范畴的对象即一个本质的个别性,只能通过“含义一般”而得到表述。在本质直观中,“对象一般”即它的对象的被指的东西与“含义一般”所指的东西相区别,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结的,因为“纯粹含义真理可以转变为纯粹对象真理”。(18)所以,胡塞尔有关范畴的概念(作为含义)和范畴的对象(作为本质的个别性)相区别的理论,与弗雷格的意义和对象相区别的理论类似。
就含义的形式学说而言,胡塞尔对它的描述似乎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有关句法形式的理论。“句法对象理解为那些通过‘句法形式’而从其他对象中推导出来的对象‘以及’任何对象,只要它是可以说明的,可以和其他对象发生联系,简言之,可以在逻辑上被规定,那么它便接受了各种句法形式。”(19)与这种句法形式相应的范畴被称为句法范畴。同样,在句法形式中所规定的对象就是“范畴对象”。所有这些对象在句法形式的推演中,总会追溯到一些最后的基础上,“这些对象不再是句法范畴的构成物”。(20)也就是说,这些对象不再是某些范畴对象--被句法范畴所规定的对象,也即由其他对象经句法形式所规定的对象,因为,它们本身“在自身仅仅只包含着句法形式”。(21)它们不是某种形式的被构成物,无需被推导和演绎。
但是,当胡塞尔论述这些最后的基础时,他不是把它们规范为外在的一种确定的形式(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形式),而是描述为由本质的个别性来表现的。这些最后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基础范畴,它“作为所有句法构成核心的最终包含实事的基础”。(22)就此最后基础而言,它有两个相互分离的部分,即“包含实事的最终本质”和“此物”组成。对于前者所谓的最终本质,它本身不是一个本质的属,而是一种本质的个别性,也就是说本质本身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属类,而是寓于本质的个别性之中。由此,“所有形式本体论的范畴称为本质的个别性,这些个别性的最高属在‘形式本体论的范畴一般’的本质之中。”(23)所以,“包含实事的最终本质”本身就是本质的个别性。就基础范畴而言,它是一些自身包含句法形式的无形式的本质的个别性。“任何一个此物都具有其包含实事的本质存在,而这个本质存在具有一种已有的意义上无形式的基础本质的特征。”(24)由此可见,胡塞尔在有关“形式本体论的范畴一般”的无形式本质与本质的个别性表现之间,开创了一条卓有成效的理解之路。
就含义和形式而言,胡塞尔为我们勾勒了先验句法学,它的先验性表现为一种所有可能性的认识,并先于一切个别性。个体性必然在这种形式本体论中被规定,就此而言,所有个别性就已经“先天地”和“综合地“包含着它们自身的东西。于是,类似于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现象学的研究必然会突破纯粹范畴研究的范围,而达到一个意识领域的水平。这就是现象学的先验还原。
三
以本质还原的方法,把事实和本质区别开来并以此确立先验的形式本体论。但是,这种先验形式本体论缺乏意识的基础,没有真正落实到意识领域,并以此揭示意识活动的本质。胡塞尔意识的意向性理论正是对无形式的形式本体论的贯彻和延伸。
现象学的方法是有关我的存在范围以及它与我的本质方式相联系的方法。被体验、被思考的对象是在我的经验、体验、思维的范围内显露出来。作为前者的对象和作为后者的意义的赋予是有区别的。对于后者,胡塞尔称之为意义意向。至于对象,我们的注意力已不是指向对象意义的赋予过程,而直接指向对象本身,这也就是意义充实。就意向的对象有其对象本身和意义相区别而言,其原因就在于意向行为的本质结构,对象始终在我的意识行为中被显现,也就是说始终涉及到对我来说“原本的被给予性上”,这种被给予性胡塞尔称之为“意识活动”(Noesis)。所以,任何一个对象首先必须是“意向对象”(Noema),也就是它必须以原本的给予性的主观情况的方式为前提。因此,“意向对象”即作为“自在之物”在对象的被给予方式中始终与“意向活动”即作为“为我”的原本的被给予性上相关。对象决不能离开“为我”而被超越。
于是,以相关性为契机,以原本的被给予性为突破口,这已成为胡塞尔现象学的关键。在对原本被给予方式本身的考察中,胡塞尔提出了原本的被给予性以其直观基础帮“本质”基础为主要成分。前者是“为我”中由经验、体验、认识的相应的行为多样性构成。但是,它不是混乱的行为集合,所以,对于后者,它“不依赖于偶然出现的经验被给予性,而是依赖于‘本质’,即:对象种类的一般规定性。”(25)于是,胡塞尔的形式本体论学说由此进入了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之中。对象的本质规定性与意向行为的普遍、本质的状况相应,从而在后者“纯粹意识”领域中达到真正的对象“实事本身”。进而,意向性本身表明对“某物”意向既建立在以“此物”为基础的所有意向体验之中,同时又指向该物的本质而处于“一种活的、朝原本性的趋向”中。(26)就此而言,在意向行为中,没有也不可能把“该物”对象的“意义本质”还原为一个对象本身,“该物”被意向的对象与“意义本质”相区别。在胡塞尔现象学术语中,前者称之为意向的质料,它是意向行为中留下理解的“某物”。后者是行为的意向本质能赋予表达以意义,它被称为意义式的本质。因此,意义式的本质就是形式本体论中的无形式本质,它已化入意识的意向活动中,同样“意向对象”作为留下意向的“某物”,它已是本质的个别性而置于意向活动的“朝原本性”趋向中了。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的关系是形式本体论中无形式本质和本质个别性的理解方式的一种贯彻。
当对对象的意义进行剥离,而把其归入“本质”之中时,一切对象所具有确定意义的自然观点将被中止,所有有关的命题和观点被悬搁,这就是现象学的还原。如此,“意义和本质”被归入意识的意向性之中,而此领域是与世界中的对象完全不同的存在种类。所以,胡塞尔现象学“必须走一条思维之路,在这条路上可以看到,对象的被误认的自在存在无非是主观相对的显现而已。”(27)于是,建立在被给予方式上的意向显现,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意义和“内部世界”的主观意义都进行了一种意向性前提的爆破,从而真正消解了二元论。
作为意识的意向显现的前理解领域,意识是一条意向体验的河流,胡塞尔称为“体验流”。这种“体验流”在我的存在方式的所有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体——即在原本的被给予方式上。所以,如胡塞尔所述,我作为“进行的自我”是所有我的体验的相属性的基础。在这种意向性显现中,“我”既可以反思世界中的对象(客观对象),又可以反思正在进行着的自我(主观对象)。以上两者当以一种存在着的方式显现自身时,前理解领域就过渡为对象化的世界,但是,作为对象化的世界的前提,——无论是对象还是作为对象的自我——难以摆脱前理解领域即意向领域,因为“意向体验”所谈的“不是在某个心理学的事件——被称为体验——与另一个实体的存在——称为对象——之间的联系,”同样,“也不是一种在客观现实中某物与他物之间的心理学和其他实体性的联结。这里谈的毋宁说是就其纯粹本质而言的体验或者说,谈是的纯粹的本质,谈的是‘先天地’,绝对必然地包含在本质之中的东西。”(28)于是,在“意向体验”中任何对象的客观化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客观化就是一种存在物。但客观化就不可能达到本质化,后者永远不能还原为一个客观对象,而只能处于一种意识的意向性显现中。所以,有关无形式的本质的观点也必然要求对客观的本质或主观的本质的破除,从而使无形式的本质以“朝向原本性”的意识的意向性来显现。
“我思作为‘行为’”它是一种“非现实性变化”。(29)我作为进行着的自我是“非世间”的方式存在,它在未对象化和未客观化的意向领域中保持着一种连续的体验流:这种非现实性方式中的意识实现“去对象化”,从而进入现实性的客观世界中。因此“一个清醒自我的体验流的本质在于,思维的持续运动着的链始终受到非现实性的介质的包围,这个非现实一直准备过渡到现实性的方式中去。”(30)“我”虽然在进行各种对象化的体验,但“我”本身永远不能对象化,它永远处于对象现实性世界的边缘。“我”既是作为“纯粹的自我”的意向显现的领地,又是作为现实化世界的界限。“我思本身包含着一个内在于它的‘朝向’客体的‘目光’,这个目光另一方面是从永远不可能缺少的‘自我’中发出的。”(31)最终,胡塞尔的全部的现象学归结为作为“先验的自我”的非现实性意向领域对对象客观化的现实性世界的演变和界定。用“先验的自我”的意向性领域来具体表征无形式的本质,是胡塞尔先验的现象学的必然结果。“对象”即个体的个别性已“先天地”包含在“本质”之中了。这种“本质”就是以“纯粹现象”或“纯粹自我”表征的意向性的视域(Horizoh)。由此可见,所谓无形式的本质就是一种先验的整体域本身。
结论
胡塞尔现象学完全信奉哲学是关于本质和形式的学说。他把事实(作为偶然的事件)和本质区别开来,并把本质化的实现置于一种由“先验自我”对“本质”的承担的实施过程之中。这种本质化虽以“某物”的对象化来表现,但它本身永远不能被对象化,即永远不能以外在于它的形式来审视它、重构它。不然,“本质”就独立于一个显现过程,而被对象化——即一种确定的、外在的形式化。这绝对有悖于胡塞尔现象学中有关“本质”的无形式之特征。
所以,当涉及本质化学说时,“先验自我”的确立是必然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先验自我”或“纯粹自我”就是与“纯粹存在”的领域或“事物本身”一致,回到事物本身,即追向事物的本质,就是彻底回到“先验自我”,以此显现事物本质化的过程。不过,把本质化过程归结于“先验自我”的自身显现,并不是把本质归结于自我及其本质。主观的实在在胡塞尔现象中已失去了独立的意义,因为,它已处于“意向性”的先验反思之中,并且表现为先验的整体视域。
于是,就本质和形式的关系而言,“先验自我”作为对本质和形式的承担,对它存在方式的剖析有助于揭示“本质”之无形式的特征。同样,当“先验自我”和“纯粹本质”一致时,本质就是一种在整体视域中自我显现的过程,以此表现无形式本质的先验性。事实上,这种无形式之形式的特征是构成“先验自我”的先验性反思的前提,因为它永远处于一种朝向原来的动态过程中,并且使“本质”不断处于自我显现的过程之中。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第85、84、84、85、87、86、87、87、88、96、91、90、98、98、97、102、99、100、129、126、128、1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3)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E卷第110页商务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