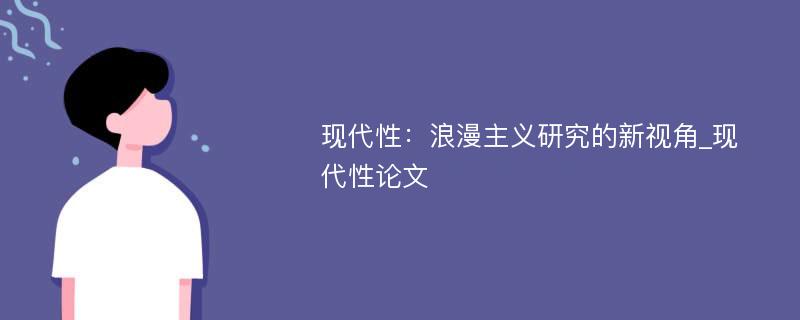
现代性:浪漫主义研究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浪漫主义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浪漫主义研究中的难题和现代性框架的引入
“浪漫主义研究”显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这不仅在于长达150年的浪漫主义研究史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摆脱的“影响的焦虑”, 更在于浪漫主义研究中的这样一个基本难题:在已被离析出来的林林总总的浪漫主义诸特征之间,如“它的个人主义、理想主义、把创造性想象放在首位、对大自然进行主观的感知、重视情感、使用象征意象等等”,似乎只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家族相似性,而难以找到一个最小公分母。(注:Lilian R.Furst,Romantic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6),pp.81,9,80—81,20.)因而E·B·伯格姆宣称:“谁试图给浪漫主义下定义,谁就在做一件冒险的事。”(注:转引自Lilian R.Furst,1页。)格里尔森也认为浪漫主义是一个“别想限定得似乎让自己或别人完全信服”的术语,(注:Herbert J.C.Grierson,The Background ofEnglish Literature (London:Chaffo & Windus,1925),p.256.)而拉夫乔埃则干脆下结论道:“‘浪漫’一词已经发展到用来意指太多的事物,以至于其自身反而变得意义空洞。它已经不能行使一个语言符号的功能了。”(注:Arthur O.Lovejoy,"On the Discrimination ofRomanticisms",in M.H.Abrams,ed.,English Romantic Poet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6.)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那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本质的探索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韦勒克便从其“主导性的规范”标准出发进行文学史的分期研究,从而坚持认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理论、哲学和风格的统一体。”他说: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大陆那些自称为或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就会发现,全欧洲有着共同的关于诗歌、关于创作、关于诗的想象力的性质的认识;关于大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观念。(他们)也有着基本一致的诗风,其对意象、象征和神话的运用,也明显不同于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注:Rene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pp.160—61.)
即是说,韦勒克将想象、自然和象征神话看作是浪漫主义三个最具本质性的、统一的特征。
韦勒克的立论建立在庞博的材料梳理和缜密的文本分析之上,其结论颇具说服力和定论性。阐述这一观点的两篇论文《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和《再论浪漫主义》几成浪漫主义研究史上的经典性文本而一再被人引用,甚至其论敌拉夫乔埃也未能提出强有力的论据予以反驳。
然而,我们发现,韦勒克貌似严密的论述中仍然存在着两点疏漏。
首先,他从其过分的“统一性热情”(P.S.Crane 对韦勒克的批评语)出发,将一场复杂的浪漫主义运动仅仅减约为三个“主导性规范”,从而不得不忽略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注: Lilian R.Furst,Romantic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6),pp.81,9,80—81,20.)例如F·施莱格尔著名的“浪漫主义反讽”( romantic irony)是否应弃之不顾呢? 而柯勒律治的“有机形式论”( theoryoforganic form)也是否属于非主导性原则而应被忽略呢?在浪漫主义诗学理论中有着重要地位的自我扩张、美和艺术的自足性以及生命的诗化等问题能否被排除在外呢?所以,福斯特(L.R.Furst )批评韦勒克犯了“综合法”的错误:“它从实在的某些不会有错的类似点出发,接下去(错误地)推断出欧洲浪漫主义总体一致的结论,它歪曲了欧洲浪漫主义有着不同侧面的真相。 ”(注:Lilian R.Furst ,Romantic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6),pp.81,9,80—81,20.)福斯特认为,在浪漫主义所有作品中,只存在着某种“神秘的家族类似性”,“每一位诗人都属于浪漫派这个家族,但同时又都个性鲜明”;(注:Lilian R.Furst,Romantic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6),pp.81,9,80—81,20.)因此,如果浪漫主义有一个本质的话,那么这一本质就是“它放弃了理性主义的确定性……它是一场引生问题的运动,那些问题往往没有答案。 ”(注:Lilian R.Furst,Romanticism(London:Methuen & Co.Ltd,1976),pp.81,9,80—81,20.)
其次,韦勒克过分执着于“主导性规范”的历史性,从而将浪漫主义历史地推距为一笔可供客观描述的、早已僵化了的文学遗产。他不无肯定地认为:“我们自己是不能接受这种(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了。——确切地讲,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人能接受它了。”(注: Rene Wellek,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Press,1963),pp.107.)事实上, 这也是此前几乎所有浪漫主义研究者所共有的一种姿态,尽管他们在对浪漫主义有无本质以及有何种本质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然而,随着近年来现代性问题讨论的日渐深入,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浪漫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一直致力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E·伯勒(Ernst Behler )就指出:
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争论中所引发的对现代性溯源的兴趣,以及一些早期浪漫派主要著作的整理出版,使我们得以从20世纪末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早期浪漫派的文学理论……以此观之,早期浪漫派文学理论不应被缩减为批评史和文学史的某一章节,它是对诗的根本反思,没有边际和终结……
这(早期浪漫派)是一个难以定位于某一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现象,它有着一种未来的指向性,其中,我们的现代性特征体现得十分明显……人们总试图将浪漫派理论封闭在一个已成陈迹的历史语境里,但这些努力均以浪漫派理论在当代批评潮流中的“现实化”(actualization)而告失败,如新批评、哲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尔诺的理论)、主体哲学批判(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拉古-拉巴特(Lacoue-Labarthe)、南希(Nancy)和保罗·德·曼等的解构主义等。
正是由于其现实性(actuality )和现代性特征(modernisticcharacter), 早期浪漫派成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原教旨批判的、仅次于尼采的主要靶子。在德国,当今的意识形态批判(指哈贝马斯——引者注)将早期浪漫主义视为通往审美现代主义( aestheticmodernism )的第一步,其态度就是摒弃公共理性(communalrationality)、交流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ing )以及共识(consensus)等等。(注:Ernst Behler,German Romantic LiteraryTheory(Cambridge: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x,p.8.)
这样一来,当我们把现代性问题引入了浪漫主义的研究领域,就再也不能像韦勒克那样把浪漫主义减约为几个僵死的历史概念,因为现代现象至今仍是我们最感困惑的生存状态之一。如果浪漫主义是对现代性作出的最早的审美反应(如哈贝马斯所言,“它是导向审美现代主义的第一步”),那它就一定和我们的时代精神状况一脉相通,它在从新批评到解构主义的20世纪各种文学美学流派中的“现实化”翻版正说明了这一问题。据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现代性尤其是审美现代性的引入为我们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拓展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或者从另外一方面讲,从浪漫主义入手来追溯现代性审美精神的起源,也可以为现代性问题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二、浪漫主义和现代性的确立
把浪漫主义和现代性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起源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热潮之中。70年代后,随着对后现代主义讨论的日渐深入,人们突然发现,浪漫主义像一个死而未僵的幽灵一样,又悄悄地复活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旨趣之中。在形形色色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当年浪漫主义曾涉足过的问题乃至思想风格的痕迹,而二者之间这种似曾相似的根源便在于现代性这一至今仍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对此,伯勒在其1990年出版的《反讽和现代性话语》一书中作出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刘小枫对伯勒的主旨进行了这样的概括:
从形式上看,“后现代”与浪漫派的一致之处在于,两者都显得是激越的现代性批判,但实际上两者既不是现代性的克服,也不是一个新的开端,而是在批判现代性中延续或推进了现代性原则;从思想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之终结、人的终结等论点,以及对元知识学的攻击和诗的隐喻、感性的美化和强调,浪漫派已着先声。在这一意义上,浪漫派思想本身就是现代性原则的一种类型,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独特提法,对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结构的转变的独特反应态度。(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2页。亦参见Ernst Behler,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Modernity (Seattle &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0),3—71页。)
这清楚地表明,现代性的问题是浪漫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共同关涉的对象。无论是浪漫主义的“自我”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非我”,其审美批判的锋芒均毫无例外地指向了现代性这一已困扰了西方知识界一百多年的难题。如此看来,作为一场运动的浪漫主义虽已成历史,但其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精神却早已内化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种主义话语中,(注: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就将现代性的五个方面——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和后现代主义均溯源到浪漫主义,可为一证。参见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从而引发人们对浪漫主义本质的永不疲倦的探索努力,以至于有人惊讶地发现“当今的文学史简直可以和浪漫派研究划等号”,因为“浪漫派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注:参见李伯杰:《德国浪漫派批评研究》,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34页。)
那么,浪漫主义是怎样既批判又推动了现代性的原则呢?它“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提法”之独特性何在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现代性的问题性(the problematicity of modernity)。
从语义上讲,所谓“现代”是相对于“古典”而言的一个时间性概念。但是,现代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观念却不仅仅指代一种时间上的历史分期,它意味着和古典社会在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彻底决裂和更新。在形态层面,现代现象体现为“人类有史以来在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一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重排,它体现为一个极富偶在性的历史过程,迄今还不能说这一过程已经停止。”(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序论》,2页。)显然,在这一转型和重构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新的规范的确立,因为只有以新规范取代旧规范,才能从理念上为现代性秩序重排找到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理论基点。
那么,确立现代性之合法性的新规范是什么呢?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解答,他说:
现代性不再从另一个时代的模式里去寻求自己的定位标准,而是从自身中创立规范。
现代性就是毫无例外地返顾自身。(注:Jürgen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pp.7,45.)
这就是说,和古典社会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上帝、神祗等外在的统摄性法则不同,现代性赖以立身的规范就是它自身,也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哈贝马斯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是第一位抓住现代性问题本质的哲学家, 他(黑格尔)首次将现代性的自我确认( self-reassurance)即主体性当作哲学的基本问题予以对待,并认为在现代性之中,宗教生活、国家形态、社会结构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均是主体性原则的转换和表现形式,这终于导致了18世纪末科学、道德、艺术三大领域的分化与独立。这样,以主体性为规范的现代性终于确立起来了,然而这一确立的过程却是漫长的,它经历了科学哲学领域和艺术审美领域两度激烈的“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ts et desModernes)。
“古今之争”发生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后来又扩展到德国。对于亲现代派人士(promoderns)而言,这场论争的目标就是要在哲学、自然科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内彻底否定中世纪经院哲学乃至古希腊、
古罗马传统之不可逾越的权威地位,
以发展、进步(progression)的观点证明今人胜过古人, 并以此确立现代性的自我确认性。圣-埃夫里蒙(Saint-Evremond)断然指出:“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解释不了现代世界,同样,其《诗学》也无法涵盖现代艺术所创造的美。”(注:Charles de Saint-Evremond,"Of Ancient andModern Tragedy",in Scoft Elledge and Donald Schier,eds.,TheContinental Model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0) ,p.123.)正如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一样,美也是无法穷尽的, 它只有一种无限的可臻完美性(infinite perfectibility)。
文艺复兴后,人们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领域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这就要求现代性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进步提供合法性解释,于是现代性的发展进步观念和自我确认性便首先在科学哲学领域内得到了确立。这主要归功于蒙田、笛卡尔、帕斯卡等启蒙哲学家的不懈努力。蒙田的《随笔》(Essays,1580)、培根的《知识的进步》(Advancement ofLearning,1605)和《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 笛卡尔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ethode,1634)等著作均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不仅应将人的理性从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应使其摆脱文艺复兴复古的桎梏。例如培根在《新工具》中就指出,现时不应依赖于传统;传统的权威应被搁置;真理是时间的女儿而非权威的产物。(注:参见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95—97页。)这样,到了18世纪中晚期,启蒙思想家们便逐渐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确立了理性/进步的现代性观念。然而,在文艺美学领域,新古典主义的摹仿论、三一律等“仪轨”(decorum)仍占据着主导地位, 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进步/无限等观念仅适用于直线发展的、以自然和真理为探索对象的科学和哲学,而艺术却始终处于一种盛衰更替的循环运动状态,其中古典艺术已臻于完美的极致,古希腊艺术是永远不可超越的完美范本;无限只存在于哲学与科学领域里,而不属于文学艺术,因为后者所探索的对象是“一成不变的人的心性特征”。(注:1777年出版于日内瓦的《百科全书》这样写道:“趣味的标准是永远一致的,因为它根源于一成不变的人的心性特征。”参见Ernst Behler,Irony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39页。)这样, 在人的情感或心性领域,现代性的原则还难以突破新古典主义的窠臼。这了就表明现代性工程在18世纪中前期的启蒙运动期间还仍是一项未竟工程,因为按照马克斯·舍勒的现代性理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注: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4页。)而现代性在人的心性情感领域以及其外在表达形式——文学艺术领域的突破最终则由勃兴于18世纪末期的浪漫主义运动来完成。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浪漫主义的兴起对于在文学和美学领域里确立主体的自我确认、自我肯定的现代性原则以及最终全面推进这一现代性原则所起到的划时代的作用。伯勒指出:
从浪漫时代的萌芽到18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全面兴起),在人类历史上,诗、文学和艺术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段时间是西方历史的分水岭,因为它将现代主义的意识完全确立起来了。这体现在它(浪漫主义)以一种全新的现代意识彻底否定了古典主义的陈规。它为文学艺术史引入了完美的无限性 (infinite perfectibility)以及创造性观念, 从而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文艺循环发展论和不可超越的完美范本论。这种新的诗歌观的最重要特征是:以创造取代摹仿;强调诗人的天才和想象;以历史的发展变化观打破僵死的文类( genre)等级系统;提倡读者阅读和阐释的无限可能性。至此,在“古今之争”中,现代人(moderns )终于在诗歌领域里也取得了胜利。于是,现代性的时代才真正开始了。( 注:Ernst Behler,Irony and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p.40.)
卡林内斯库也注意到浪漫主义在文学审美领域里确立现代性原则并最终在全面推进这一原则的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在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中(在英国,斯威夫特的《书的战争》体现了这场论争),即使许多赞同“现代”的人们也仍固守古典主义超验的、永恒的美的模式,他们认为,现代人优于古代人仅在于前者能以一种更理性的眼光来理解这一模式。“但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确切地讲,自从以浪漫主义面目出现的审美现代性首次明确界定其反古典主义宗旨的基本立场,并宣称这一立场具有历史的合法性伊始,超时间的、普遍可理解的美的观念才开始造退。”( 注: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pp.3.)
实际上,追溯一下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自己的理论主张,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早已开始探索浪漫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如F ·施莱格尔(F.Schlegel)在其著名论文《论希腊诗歌研究》(On the Study ofGreek Poetry,1795)中就指出:“艺术的完美是无限的,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只存在有条件的、相对的极致,没有绝对的完美。(艺术的完美)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渐进过程(an insurmontable fixedapproximation)。”(注:转引自Ernst Behler,German RomanticLiterary Theory,101页。 )这显然是对古典主义范本摹仿论的断然否定。而其兄A·W·施莱格尔(A.W.Schlegel)更是十分明确地坚持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对立,并始终如一地将“浪漫”等同于“现代”。他说,浪漫主义代表着“现代艺术精神,它与古代或古典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转引自Lilian R.Furst,Romanticism,10页。 )因为“古代艺术和诗歌是一种节奏性的法则,是谐和地颁布一个反映事物永恒理念并经过美妙安排的世界的永久性立法。浪漫诗则表现对一片混乱的一种秘密渴望,它无休止地追求新颖惊异事物的诞生,它隐藏在有条不紊的创造的母胎中……”(注:转引自Rene Wellek,A Historyof Modern Criticism:Romantic Ag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1955),Vol.2,72页。)对浪漫主义现代性意识最清楚的表述体现在司汤达(Stendhal)《拉辛和莎士比亚》一文对浪漫主义的定义中。司达汤对浪漫主义的理解既不是从历史分期入手,也不是从某种特定的风格入手,而是敏锐地抓住了浪漫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即审美旨趣的世俗性和现时性:
浪漫主义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它以当代人的习俗和信仰为旨归,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愉悦。与此相对的是古典主义,其文学愉悦只提供给他们的先祖,……今天谁要想摹仿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而且还假装这些摹仿不会使19世纪的法国人厌烦的话,他就必定是一个古典主义者。 (注:转引自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Modernity,39页。)
在此,司汤达明确揭示了“浪漫”和“现代”的同义性,即美的现时性和世俗性。浪漫艺术的创作原则不再以古典悲剧的“净化论”为准绳,而是将满足现代人的世俗旨趣放在了首位。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浪漫主义的确是现代性在艺术和审美领域里进行自我确认、自我肯定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它对新古典主义僵化教条的否定和超越为身处剧烈变化之中的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打开了情感和想象的闸门。从此,美的评判标准从传统转到了现时,从摹仿转到了表现,从有限转到了无限,从超验转到了此岸,从理性转到了情感,从外在转向了内心——一句话,个我的生命律动成了美和意义的唯一源泉。
而且,浪漫主义勃兴之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在诗歌和美学领域内推进了现代性原则;“古今之争”终于以现代人不仅在科学哲学,而且最终也在文艺美学以及人的情感领域里的全面获胜而结束。这样,主体性自我肯定原则终于全面确立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为浪漫主义的兴起对于现代性的完全确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浪漫主义和现代性的分裂
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原则的确立带来了两大结果:一是世界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解魅化(disenchantment)和社会形态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即对神意安排的目的论(teleology)的拒斥以及以人的理性来重新解释世界;再有就是曾经铁板一块的西方文化(one unitary culture)分化成了三个彼此独立的领域,即科学、 艺术和道德,每一领域都能按各自的内在逻辑和形式理性(formalrationality)取得独立的发展。至此,启蒙工程似乎已大功告成。
然而,如果我们分别从理念和社会形态层面将现代性界定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实现,那么,不难看出,现代性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潜伏着一系列内在的矛盾和紧张。因为主体性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只不过在现代性刚开始赋形的启蒙阶段,反神学、反宗教的首要任务使得启蒙哲学家们不得不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弘扬主体性。但一旦主体性原则被当作现代性的自我规范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及艺术审美领域里完全确立起来之后,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这一启蒙初期的含混矛盾便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于是,一种新的裂变在现代性中悄悄凸现了。关于现代性的分裂,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其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贝尔(Daniel Bell )认为现代性体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冲动和现代文化两个方面,两者在致力于建构现代性工程的初期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这就是自由和解放,因而两者都体现为对主体性的推崇和弘扬。然而,贝尔指出,这两种主体性(或自我)是有所不同的,前者表现为一种“朴实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而后者则表现为一种“放纵无度的自我”(unrestrained self)。因此, “尽管两者在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如出一辙,但它们之间却迅速产生了一种敌对关系……较为符合历史的解答似乎是这样的: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从布莱克、拜伦到波德莱尔,这些现代派文学大师构成了一条不太具体、却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文化冲突线索,有助于证实以上论点。”(注: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of Capitalism (New York:Basic Books,1978),pp.xxiii-xxiv.)贝尔的论述暗含了两种同为主体性的价值观的冲突,即追求财富的实用理性的自我约束和渴望“激动”的审美感性的自我放纵,后者从布莱克、拜伦(均是浪漫主义巨子)以降,形成了反抗前一种现代性的对立文化。如果贝尔对现代性(主体性)的裂变还只是作了暗示性的论述的话,卡林内斯库在其1987年的新书《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便将这种裂变十分明确地揭示出来,并认为这是发生在现代性工程中的一个深刻的历史事件。卡林内斯库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刻,现代性分裂成了两个不可逆转的类型:一是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现代性——它是科技进步、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所带来了的社会经济的迅速变化的产物;另外一种就是作为审美观念的现代性。从那时起,两种现代性就处于不可调合的敌对状态之中。但为了毁灭对方,两种现代性又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相互影响。 (注: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pp.41.)
卡林内斯库认为,两种现代性之对立冲突就在于,第一种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是此前现代观念的继续,它以进步为旨归,相信科学技术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福利和满足;它关注时间(一种可以用金钱加以度量的、像商品一样可以自由买卖的时间);它推崇理性,相信人文主义框架内的自由的理想;它追求实用主义,膜拜行动和成功——这些均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而另一种现代性从其浪漫主义的始源起就坚持其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它对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深恶痛绝;它以反叛精神、无政府主义、天启论(apocalypticism)和贵族式的自我放逐等姿态表达了其憎恶。所以,文化的现代性就是以否定一切的激情拒斥资产阶级的现代性。 ”(注: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Modernity,pp.42.)后一种现代性便是我们一再提及的审美现代性。卡林内斯库认为,审美现代性作为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的反动,其本质根源于一种非计算的、私己的时间意识;它是“个体的、主体化的、想象性的绵延(duree),这是一种自我展开过程中的私己的时间感。 这种关于时间和自我的观念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从这一观点看,审美现代性揭示了其危机感和疏离另一种现代性的原因:宗教死亡后,后者的客观性和理性便失去了令人笃信不疑的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合法性。(注:Matei Calinescu,Five Faces of Modernity,pp.5.)这就是说,产生于宗教解魅化之后的现代性审美意识,敏锐地感觉到了世界始基的缺失和意义本源的匮乏所带来的危机感;其私己的、想象性的内在时间意识使它拒不认同算计的、冷冰冰的工具理性的客观性和合法性地位,它必须要为此岸世界寻求新的立法根基。这就是感性、艺术和审美。基于此,刘小枫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定义了审美现代性。他说:“作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包含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的位置,夺取超越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致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的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审美的态度(用贝尔的说法,即‘及时行乐’的意识)。”(注: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序论》,286页。)
显然,卡林内斯库和刘小枫所界定的审美现代性仍表现为一种作为主体性的现代性原则,只不过这是一种感性主体性而非启蒙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体性。它的出现,既推进了现代性的主体原则,又作为一种异在性因素,开始不断地瓦解现代性的理性化工程。这样,在启蒙运动中尚处于含混状态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便正式裂变为(实用)理性主体和(审美)感性主体两大对立的理念形态。审美现代性从此便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性的一种“对立文化”(adversary culture )开始凸现到历史的前台。现代性的分裂出现了。
那么,这种以感性、艺术和审美为旨归的审美现代性产生于何时呢?或者说,现代性的分裂事件发生在哪一个历史时刻呢?事实上,在前文里我们已经提到,哈贝马斯“已将早期浪漫主义视为通往审美现代主义的第一步”;卡林内斯库也将“现代性的分裂”(split ofmodernity)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一个时刻”, 即西欧浪漫主义的勃兴时期。浪漫主义关于自我的扩张(诗人作为世界的立法者)、艺术的自足以及生活世界(life-world)的诗化和审美化等一系列原则的提出不仅摧垮了新古典主义长期压抑人的感性的陈腐体系,在人的情感、想象等审美领域里完成了主体性的现代性革命,从而导致了现代性(主体性)原则的全面确立,同时,它也以其强烈的反资产阶级工业文明、反工具—实用理性,以情感、想象、灵性、有机的自然和辽远的神话来对抗盘剥的、计算的、冷冰冰的机器世界,在帮助全面确立现代性的同时,又导致了现代性的分裂。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现代性(主体性)的确立之日即是它的分裂之时。这一悖论的根源便在于孕育着现代性审美精神的浪漫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两面性:它一方面是理性、启蒙、文明、进步等现代观念的推进,而一旦这些观念被完全确立起来之后,以至于被当作一种新传统和新神话(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中就将启蒙还原为一种新神话),它又反戈一击,对这些新传统和新神话展开了强烈的批判。卡林内斯库指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转折时期,进步的观念已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至于它自身便翻转成为一种压抑性的(新)传统,甚至成为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残暴的(新)神话。浪漫主义对进步和理性的批判打开了通往审美现代性这一‘对立文化’(再次使用L ·特里林的用语)的道路。”(注:Matei Calinescu,Faces of Modernity (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7),264页。在1987年新版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这段话连同“跋”一齐被删去,特此注明。)哈贝马斯在其《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则将审美现代性起源直接追溯到席勒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审美教育书简》。他说:“席勒的《书简》是对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首部纲领性著作。它导致了图宾根派(谢林、荷尔德林和黑格尔)的法兰克福构想(Frankfurt vision),因为它利用康德哲学的概念,对现代性自身的分裂作出了分析,并且设计出了一个让艺术最终承担社会革命的审美乌托邦。”(注: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Cambridge: PolityPress,1987),pp.7,45.)浪漫主义思想史家马丁·亨克尔更是明确地声称:“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注:马丁·亨克尔:《究竟什么是浪漫》,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6页。 )这些观点充分地证明了一个事实:浪漫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作出的首次具有明确意识的审美反思和审美批判,其美学旨趣和价值取向构成了审美现代性勿庸置疑的最初精神源泉。
四、浪漫主义和审美现代性的精神关联
现在,我们既然已经确认了现代性的审美精神起源于浪漫主义这一事实,我们就不得不回答另外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如果说审美现代性直接发韧于浪漫主义,那么,在审美现代性的诸原则和浪漫主义庞杂的理论体系之间必定存在着某些一脉相承的精神契合之处。问题是,这些契合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卡林内斯库把审美现代性的本质概括为一种自我展开过程中的主体化的、想象性的内在时间意识,它与商品化的可算计的另一种现代性时间意识之根本区别在于,它力图从感性(而非理性)、审美(而非宗教)为世界重新立法,从而恢复人被机器扼杀了的灵性并且将碎片化的世界重新整合在一个审美的乌托邦里。显然,这是一种极端的审美主义,其主旨就是感情、艺术、审美(它具体体现为刘小枫所概括的三项基本诉求,即感性的本体论、艺术代宗教以及游戏或审美的人生态度)。
我们以此来反观浪漫主义便会发现,看似纷繁芜杂、形态各异、因而难以定于一樽的西欧浪漫主义运动(主要指德国早期浪漫派和始于《抒情歌谣集》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实际上都沉思着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这就是如何以内在心性和审美冲动来反抗早期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所建立的“庸俗的散文世界”,以及如何在一个诗意的乌托邦里超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进而为生命找到一个终级的价值根基。不难看出,生活世界的审美化和个体生命的诗意化这一极端的审美主义正是审美现代性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汇通之处,或者说,浪漫主义最早滥觞了至今仍是我们时代状况之一的现代性审美精神。从这一视角入手,我们或许可以尝试着重新梳理浪漫主义诸家貌似庞杂的理论流派,并归纳出一个具有较宽泛涵盖性的浪漫主义美学和诗学体系。这就是审美的本体论(以取代此前中世纪的神性本体论和启蒙时代的理性本体论);创造性想象(而非逻辑推理)的认识论;以及与此种本体论和认识论密切相关的反讽和隐喻(包括象征和神话)的语言论。这三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印证,从而构成了一个既统一、又极富弹性的浪漫主义美学和诗学体系(笔者将有另文详细论述这三个方面在浪漫主义诸家中的体现)。
浪漫主义美学诗学体系的这三个维度:审美(诗)的本体论、创造性想象的认识论以及反讽和隐喻的语言论互为依存、互为证释,共同构成了一种以感性主体为意义中心,以对机器文明的审美批判为旨归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对立文化”。它的出现,既完成了确立主体性原则的现代性工程,同时又反戈一击,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审美批判,从而又造成了现代性的分裂。它对感性自我的弘扬、对艺术和诗的无限拔高、对想象的倚重、对反讽和隐喻的青睐,无不萌芽了审美现代性有关感性、艺术、审美等精神原则,从而名符其实地成为现代性审美精神之源泉。正是由于这一首创性,它所蕴含的现代性审美精神便一再翻版成为自19世纪以降至今各种文学美学思潮的主旨。克罗齐在1929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美学”词条中写道:
我们时代一切需要以美学来克服的问题,都与艺术以及艺术评判的危机有关。这一危机产生于浪漫主义时期……后来,人们以为疾病已经消除,浪漫主义已成为过去之物,但其形式和内容虽死,而其灵魂犹在:它表现在以艺术追求情感和印象的直接传达的趋势中。因而它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名字,并继续生存和作怪。它将自己称为现实主义、真实主义(verism)、象征主义、艺术风格、印象主义、肉欲主义(sensualism)、意象主义、颓废主义等。现在它又以一种更激端的方式称自己为表现主义和未来主义。(注:转引自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p.214.)
显然,克罗齐已敏锐地意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文艺思潮均与浪漫主义有着嫡亲关系(他甚至将现实主义也归入浪漫主义的变种之一!),这就是对艺术、情感等审美因素的一往情深。这已经为我们跳出有关浪漫主义的静态的、僵死的观念,从而以一种客观的、发展的(即审美现代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指明了方向。也只有以这种视角来重新梳理浪漫主义庞杂的体系,我们才能既了解它的历史,又把握住它的发展和现状。
确切地讲,后现代主义仍为浪漫主义的一种变体。只不过当初的审美批判已沦为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放纵。更为严重的是,审美本身已被商品化和大众化了,它已逐渐成为文化领域的主宰甚至已取得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如贝尔所说:“现代主义作为对正统文化的攻击力量,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君临万物之上的正统地位。”(注: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1978),pp.xxiv.)但当个性、审美被正统化、合法化和商品化了之后,这种当初对现代性进行猛烈批判的“反文化”便因其暴力、色情和媚俗的泛滥而彻底堕落了,“与其说这类玩意儿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 (注: Daniel
Bell,The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Basic Books,1978),pp.xxvii.)浪漫主义当初所倡导的审美批判精神发展到后现代主义的审美放纵,不能不说是19世纪初浪漫主义大师们所始料不及的。正是在感性、“酒神精神”淹没一切之时,有识之士开始重提理性和秩序,如贝尔希望恢复自律的清教伦理,以一种新宗教来抵抗无边的审美主义,以拯救现代文化。而哈贝马斯则提出“交流理性”来抵抗无边的审美主义,从而重建现代性工程。这些冷峻的思考或许会使曾同样经历过浪漫主义革命洗礼的现代中国有所警悟。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在中国几成燎原之势,虽然旋即销声匿迹,但郭沫若们所引入的自我和反抗精神却从此深深地嵌入了中国现代文化品格之中,并构成了20世纪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浪漫主义的传入,启蒙了两千年儒家伦理桎梏下的中国青年,这是其积极性一面。但同时,不彻底的启蒙又和封建残余迅速结合起来,孕育出奇特的审美专制主义(罗素等人早就指出了浪漫主义有向专制主义发展的危险,如卢梭就导致了希特勒),并在“文革”发展到高潮,结果反而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了巨大损失。(注: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反思。或许从浪漫主义这条线索入手追索文革的起因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而近几年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喧哗在中国又大有狂燥之势,其中的浪漫主义症候也不难把握。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又一次面临着舶来的“对立文化”的挑战。我们应该怎样来应付这一挑战?也许对浪漫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精神的反思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