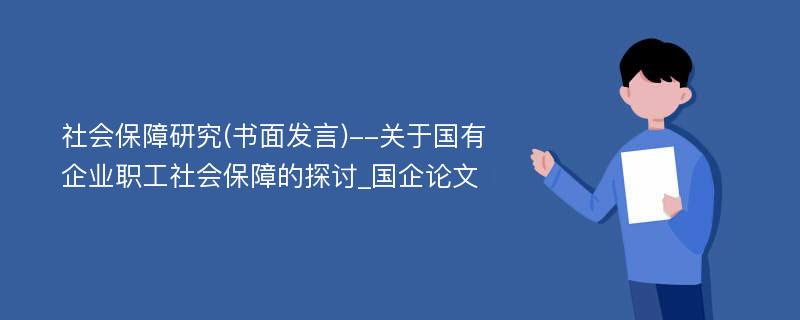
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笔谈)——国有改制企业职工社会保障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障论文,笔谈论文,企业职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国有企业工人获得保障和福利的内容与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
1
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对其员工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所有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中,企业都是社会保险基金积累的最主要供款主体。在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和美国,人们的很多福利是通过职业获得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和轨迹,其中国有企业在为城镇居民尤其是企业工人提供社会保障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直到现在,社会保险在中国也主要表现为一种城市现象,国有企事业单位是落实社会保险的主要组织基础。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国有企业的福利行为取向将直接影响到国企工人获得福利的内容与方式。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由于利益分化程度的不同,企业的福利行为取向也有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政府行政职能的衍生机构,是贯彻政策意图的基本载体,政府与企业之间基本上是控制与依附的关系。企业的生产计划、工资标准、福利待遇、领导人的升迁任免等,都在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企业承担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职能,成为政府行政等级序列中的基层单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呈现出行政化和行为非理性化的特征。由国家投资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除了必须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外,还承担着整合社会的重要职能。每个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养老、医疗、技能培训、住房福利、子女教育甚至就业等社会性事务。后来,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基本劳动保险制度蜕变为单位保险,城镇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是通过单位得到满足的,单位办社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企业追求的目标不是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是福利最大化,职工在获得各种保障资源的同时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企业保险的最终实现由国家财政提供支持。包罗万象的职工福利不仅项目齐全而且分配平均,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要大大高于账面上的工资水平,因此中国也被称为低收入高福利的国家。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朝着人员过密化和福利功能“内卷化”的方向发展,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呈现出单位化特征。
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多方面发生了变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无论是采取渐进的还是激进的方式,都意味着政治权力对企业控制力的减弱,政府对企业控制范围的逐步缩小体现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国有企业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呈现出“去单位化”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双轨制到产权制两个阶段,国有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国企改革初期,企业具有了一定独立的经济利益后,其利益取向是把企业和职工的利益优先于国家利益。在管理层利益和职工利益的共同驱使下,经营状况好的企业提供给职工的福利,随着企业控制资源的增加而增加,职工对企业的福利依赖是增加而不是减弱了。国有企业的改革不但没有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反而使企业走向综合福利最大化的追求。改革后企业的单位化不仅没有削弱,反而由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企业自我分配能力的增强而进一步强化了。
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到产权调整阶段后,政府、企业和职工的利益进一步分化。对于政府而言,从上到下推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迁,既是减轻企业负担、搞活国有企业,又是稳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对企业而言,作为落实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代理人,其利益已经和职工的利益产生了分化,在与非单位制企业的竞争中,由于沉重的社会包袱而处于不对等的竞争位置,在企业经济理性支配下,国有企业并不是被动的行动者,而是采取各种策略行为逃避社会保障责任以减轻社会负担进而增加企业竞争能力。在改制过程中,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诸如瞒报少报工资基数、隐瞒企业利润等非法手段以减轻应该对职工承担的社会保障责任,变相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加,职工的社会保障权利受损。对于职工而言,国企改制既是企业产权关系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国企职工身份的丧失,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意味着原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将由个人承担,生活风险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在产权转让的改制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交易不规范,使得国有资产贱卖和流失的现象普遍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得到好处,普通职工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
虽然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组织基础的地位不断弱化,但在落实社会政策方面,国有企业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组织。国有企业福利动机和福利行为的弱化是一个在企业理性主导下,在既有社会结构制约下逐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是被动的政策执行者,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境采取策略性行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积极行动者。
2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纳把改革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组织的关系描述为父子关系,而这种关系之间体现的是一种父爱主义。改革以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工人与国家之间也存在着父爱主义。工人的自主选择权虽然在各种制度的安排下受到限制,但国家通过单位几乎承担起了工人生活的所有需求。在道义经济学者看来,国家与工人之间通过父爱主义建立了一种“社会契约”[1]143-145。
在计划经济的全民固定用工制度下,固定工享受“铁饭碗”、“大锅饭”需要付出两种代价。一种代价是“低工资”。在以低工资、终生雇佣为特点的用工制度下,职工劳动力的价值没有全部进入工资,而是通过“企业办社会”,以集体福利的形式提供给工人;养老金也没进入工资,而是被企业作为税收上缴,或作为企业利润,或作为生产性资金。另一种代价是劳动者将劳动力所有权让渡给国有企业,意味着与企业或政府签订了“隐性的终生劳动合同”,丧失了劳动者的劳动自主权、流动权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这种父爱主义关系及其制度安排在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制度变革过程中被逐渐改变。通过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的改革,及与之相配套的劳动就业制度、工资和保障制度、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自主权。但与这种自主权获得相对应的是企业所获得的来自国家的父爱主义照顾、关爱的减少甚至消失。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一样,越来越明显地受到硬的预算约束。
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企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国有企业改革后,工人们虽然在很多方面获得了自主权,但国家对他们的全面照顾和关爱也随之减少。工人获得一份稳定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家通过企业向工人提供的几乎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也没有了。从20世纪 90年代初的打破“铁饭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到最近几年进行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劳动与福利制度方面的改革使以往工人们凭借身份就可以获得的特权几近消失。改革以前的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转变为国家—企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国家退出了对劳动的直接控制,也卸下了对工人的无限责任,只是承担起有限的责任,国家力图确立的是一种“工人自立—国家提供有限帮助”的关系[1]147-148。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改革的过程。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工人和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随着社会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加和自由流动空间的扩大,一方面工人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终身雇佣关系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为工人提供福利的动力和能力弱化。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有企业工人面临着就业困难和保障缺失的双重困境。
3
国有企业改制的直接结果,形成了企业的主要管理者和一般职工的利益分比,从而打破了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模式。改制之前,企业管理者和普通职工都不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但在改制过程中,一些企业的主要管理者通过部分或全部购买所在企业的股权,成为企业的所有者,而普通职工成为身份明确的被雇佣者。改制之前,管理者与普通职工的利益并非是对立的,但改制之后,企业的利润与员工的工资福利之间所隐含的对立关系,使得雇主和雇员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日趋显著。
国有企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组织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变迁。本来,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在岗和退休职工是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国有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将大大缩小制度体系内国有经济的比重。原来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职工,在经过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后,企业已经结清了对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样虽然可以解除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屏障,但由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很难再进入到正规就业体系内,而不得不自己缴纳社会保险费,在收入预算的约束下,退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将成为这一群体的无奈选择。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改变社会保障组织基础的同时,必将导致原来体制内受益者的流失,从而降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也使得下岗失业群体的未来生活缺乏基本的制度保障。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切断职工国有身份的同时,也切断了他们获得单位福利和保障的途径。无论离开企业的生存状态如何,他们都经历了一个由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身份转换过程,与此相伴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隔离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之外。社会参与方式和资源获得途径的改变,使这一群体处于利益受损和地位降低的处境,因此,通过就业使他们获得生存保障,并将他们重新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对于维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道义经济学者看来,作为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群体,国有企业工人的生存行动策略应该是与市场对立的。然而事实是,很多工人都对市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从中获益。但这并不能回避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而引起的部分工人的社会保障在当下或者未来缺失而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因此,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保证一切人都处于合适的生存地位,即要发挥家庭、市场、职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作用,建立广泛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