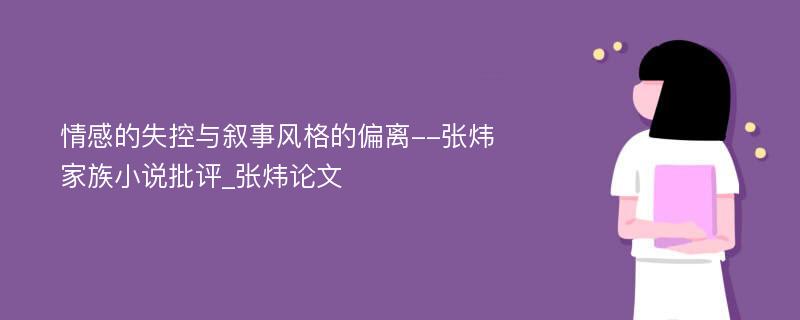
情感把握的失控与叙事文体的偏移——张炜“家族系列长篇小说”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文体论文,批评论文,家族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船》之后,张炜又接连创作、发表了6 部长篇:《我的田园》(1991、1996)、《九月寓言》(1992)、 《如花似玉的原野》(1995)、《柏慧》(1995)、《家族》(1995)、 《怀念与追记》(1996),标明张炜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旺盛期,这种高产在同代作家中也是少见的。如果说80年代是“因言立人”,读者由《声音》、《秋天的愤怒》、《古船》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张炜,那么90年代则是“言因人传”,读者奔着张炜在文坛上业已树起的名望,而追读着他的一部部作品。然而,读过上述几部长篇,却不免让人大失所望。较之《古船》,这些作品多了些空灵的书卷气和创作态度的偏执,减少乃至失却了那种直逼现实、力透纸背的艺术震撼力和感染力。甚至那些能够引发读者思考暇想、造成言人人殊的艺术光点也不多了。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作品一定一部比一部写得更好,也不能要求作家应该写什么和应该怎么样写。但是,就已经发表出版的作品评头论足,探讨其成败得失的原因,对于作家、对于文学创作应该是有益的。
本文重点把视线集中到《家族》、《柏慧》、《我的田园》、《怀念与追记》、《如花似玉的原野》5部长篇上。 张炜曾说过:《家族》“只是个躯干。它还将生长,伸延出枝桠、须络。它是一棵树,要长出侧枝、生出连体。”〔1〕这棵大树目前已延生出《柏慧》等4部长篇,枝繁叶茂,蔚为大观,我们称之为“家族系列长篇”。至于《古船》,那是80年代的作品,对于张炜和新时期小说来说,它都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佳构,一座须仰视才见的高峰,不在我们今天研讨的范围。而《九月寓言》内容也相当特殊,从创作心路上来说,它是那艘“古船”驶向“家族”的一个过渡,也暂不在我们研究之列。
故事或情节是小说的必备因素,我们先从这里入手。《家族》是由宁、曲两姓三代人组成的一个家族的悲剧故事,故事情节是相当生动曲折的。仪表堂堂、正直善良的名医曲予以自己的名望搭救了“八一支队”的负责人殷弓,又为部队购买军火,输送军事情报,却遭暗杀。曲予的女婿宁珂在搭救战友、购买军火、组织武装、指挥战斗、治理城市等方面屡建功绩,却因曾经被捕而屡遭贬斥,送进劳改队罚苦役,刑满后忧愤而死。宁珂之子宁伽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在地质研究所“03所”工作,因坚持实地勘探得来的结论,又遭排挤和刑讯,被逼离开研究所。作家运用历史与现实交错、叙事与抒情穿插的方式,有意使情节断续、跳跃,但无伤大体,因而家族系列小说的故事框架基本定型。《柏慧》是在创作《家族》时一个大的停顿,作家中断了《家族》的写作,一气呵成。宁伽在地质学院与院长女儿柏慧恋爱,因自己生父的政治历史“问题”而又失去了她。辞职后到登州海角、自己出生地的一个葡萄园生活,同时搜集整理有关徐芾传说的古歌。补充了宁伽在大山里流浪的经历,更多的是重复《家族》中的情节。这部小说完全采用与柏慧、老胡师倾诉的形式,“我并不指望那些人会理解我,它——《柏慧》,仅仅是属于我个人的声音。”〔2〕《我的田园》1990年写出草稿,91 年发表后又断断续续改写,96年再次出版。主要写宁伽不顾妻子的劝阻,只身到千里之遥的海滨平原经营荒芜的葡萄园。请来了浪迹天涯的拐子四哥,雇来两个青工,葡萄园复苏了,他又独自远行,来了一次“自我流放”。情节的生动性相对减弱了, 张炜称它是自己的“生活笔记”〔3〕。《怀念与追记》长度仅次于《家族》,更淡化了情节,时而是宁伽儿时的神奇动物阿雅的故事,时而是与柏慧的初恋,时而是“行吟诗人”聚首,时而是和妻子梅深山里寻“义父”。“那些关于一个家庭的过去和今天,关于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生活的复杂感知,或化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或呈现一种情绪和一片斑斓的风景,……这些交替出现的回忆和思绪有时并不连贯,也并非按部就班和头尾照应”〔4〕, 散乱而不连贯,张炜称之为“一个为背叛所伤的诗人在自吟”,又称之为“人生卡片”。《如花似玉的原野》虽然也分为上、下两卷,实际上则是24个短篇的合集。除《一个故事刚刚开始》、《书房》、《一个人的战争》、《四哥的腿》、《消失在民间的人》几篇与家族系列中的某些人和事件相近或相同外,其余均各自成篇并不关联。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说明”中分明写着“为了促进当代长篇小说……”我们怀疑编辑和作者有没有搞错?如果说《怀念与追记》是“人生卡片”的话,《如花似玉的原野》只能是“人生碎片”了。
对于长篇叙事文学来说,情节是锁住众多人物、事件、场景的链条,也是激发读者阅读兴趣而“锁住频道”的重要环节。《家族》有生动诱人的情节,却不时被斩断、续接,其他几部则被逐渐淡化,《如花似玉的原野》则完全消解。同时,“家族”的故事在5 部长篇里多有重复,而重复是艺术的大忌。因此,情节的淡化和重复成为“家族系列小说”的致命缺憾。
人物形象是叙事文学的中心,小说的灵魂。人物形象是否站立得起来,往往是一部作品成败的关键。张炜“家族系列长篇小说”中大约有50余个人物,《家族》中就有30来个人物出现,其他几部由于情节弱化,人物相对减少。这套系列作品中主要人物有三个:曲予、宁珂、宁伽。曲予出身于文明而富有的曲府,他为人善良正直,体恤下人,他背弃了家庭,与侍女闵葵结为夫妻,又到国外学医,学成回乡办起医院,为人们疗救痛苦,成为海滨城市中最有威望的名医。他倾向革命,利用各种合法渠道,为部队购买军火,解救八一支队领导人殷弓出监,在得到敌人血洗黑马镇消息的紧急关头,他冒死骑马给部队送信,不料却被人暗杀于途中。他是一位可敬的开明士绅,又是一位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宁珂出身在没落的大地主家庭,自幼被叔伯爷爷、省府参事宁周义收养,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少年英俊。在解救殷弓、购买军火中,他都是重要的联络人,后被任命为八一支队副政委。被叛徒出卖,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由宁周义保释出狱,却被殷弓怀疑,他经受住了不公正的反复审查。进城后,他还是城管会的三把手,忘我工作。在镇反中再次受审入监,表现十分刚强,被判7年徒刑,到深山做苦役。 出狱后仍不时被押走,身心俱残,性格乖戾,心死如灰,不再对殷弓存有幻想,最后病痛而死。宁珂的两起两落包含了深刻沉重的社会内容。郭小川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中有过类似的形象,但宁珂要比王金更具悲剧色彩。这种潘汉年似的人物形象在张炜小说中出现,表明了作家的魄力和艺术胆识。宁珂、曲予形象是家族系列长篇小说中最有艺术光彩的部分。宁伽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他在父亲遭迫害的苦难中成长。为了使他脱离苦境,父母忍心把他卖给了山里的老孟作义子。他半路逃脱,流浪在山区,采石、讨饭、做工,得遇一位教师,有了学习机会。冷肃的时代刚刚结束,他考上了地质学院。家庭问题不仅使他失去了初恋的柏慧,还险些不能毕业。分配到03所,他坚持与副所长朱亚实地勘探的结论,阻止东部大开发的计划,遭到所长裴济的打击,辞职到一家杂志社任职,但当这家杂志社在金钱利益驱动下一步步走向“恶俗”的时候,宁伽再次辞职,到葡萄园干个体。为使荒芜的园子恢复生机,宁伽吃了不少苦,园子有了收成,他又一次只身远游,做一个行吟诗人。在家族系列长篇小说中,宁伽是一个主角,他又是5部长篇的叙述者。 可惜的是,这一形象没能站立起来。在他身上存在着许多矛盾和悖理之处:他忠实于自己的血缘家族,崇拜外祖父和父亲,却并没继承他们的优长。宁伽既没有父亲那种坚持正义、九死未悔的气概,也没有外祖父治病救人、仁厚宽广的胸怀。 对待邪恶他采取的是逃逸, 而且一逃再逃:03所——杂志社——葡萄园——行吟远游。曲予那样深切地爱着妻子女儿以及家人,宁珂在逆境中不忘给儿子寻找一条生路,宁伽则别妻抛子到千里之外经营葡萄园。对于妻小,宁珂曲予是想顾而不能顾,宁伽则是能顾而不去顾。我们不能不得出言行不一、个人至上的结论,这恐怕与张炜的创作初衷大相径庭了。比起宁珂曲予来,宁伽的形象是那样的苍白虚弱。更重要的是,这一形象还是5部长篇的叙述主人公“我”。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是从“我”的视角、“我”的话语中显现的,因而带有相当的主观色彩。在“我”的眼里,“善与恶是两种血缘”〔5〕,以此为标准,“我”以自己的家族为圆心,以善恶的道德评判为半径,画了一个圆。曲予、宁珂、闵葵、曲綪、山地教师、朱亚、甚至宁周义都在这一个圆内,“叔伯爷爷这样顽固的人物,也活出了一份纯粹”〔6〕。而殷弓、裴济、柏老都在圆外了。 土匪麻脸三婶及其女儿“小河狸”血洗黑马镇,残杀了532人, 而“小河狸”不顾政治军事的对垒只身到我军寻情夫许玉明,为此而被杀。在叙述主人公的话语本文里,也对之倾注了较多爱怜与同情。宁伽形象的暗弱与人物形象的某种错位,又成为张炜家族系列长篇小说的显著瑕疵。
最后再来看看抒情。任何文学创作都是情感活动。孙犁说:“在创作上,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越多,收回的就越大。”〔7 〕但是情感把握却是有一定的艺术规律的。恩格斯主张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应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8〕。孙犁的小说就是典范, 他极少孤立地抒情,却能使小说极富抒情诗味。张炜是一位富有才情的青年作家,他热爱田野钟情于土地,崇尚道德、坚守信仰、忠于纯文学的创作,鄙薄物质主义,反对职业化写作。他这种严格的操守令整个文坛钦敬!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取向,他把对人民、对土地、对苦难和罪恶的爱憎,对人生的感悟,积聚成强烈的抒情文字,倾泻于他的讲话、散文和小说。然而他也许没想到,当他把这种激情释放于小说中时,却得不到与大学生讲话或在报端撰文同样的回报。
在家族系列长篇小说中,张炜感情抒发有三个突破口:一是取第一人称,便于直抒胸臆;二是托寓言故事,象征托物;三是激情倾诉。前二者无可厚非,唯独大段大段的连篇累牍的激情倾诉与叙事文体不合。这种每段约2000字的倾诉在《家族》中出现15次之多。《柏慧》就是以倾诉的方式写就的。《我的田园》、《怀念与追记》边叙边诉,更不计其数了。且抄录《家族》最后一章之最后一节的倾诉部分内容如下:
我相信这是在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里听到的一声问候。这只纤弱的、力拔千斤的手,招回了那飘摇淡远的一丝,让其归来。从此手与心在一起,生生不倦地诉说。那个漫长的夜晚,暖煦的热流覆过周身,从一排茁壮的青杨到防波堤,是深蓝的湖。我们都看到一只鹭鸟无望地吟唱,涕泪交流。它怀想,思念,独自迈出了茂密的小香蒲。
夜色里闪动的颜色,在视网中结为永恒。无数次迷蒙四顾,伸长双臂触探,扶住石壁。午夜的钟声啊,徐徐移动的指针啊,把乳白色的黎明的薄膜划破了。我在这恐慌的时辰里必须依偎,沉入和回避。那铺天盖地的一片淋漓啊,那无遮无拦的奔流啊,溢满了大地与江河。
……
以下还有1000余字。这等作者痴情投入读者却莫名其妙的文字,放在结尾,使作品没有了余味,放在中间,打断了读者阅读兴趣,实在是对读者阅读期待的干挠。然而,就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倾诉”,还居然有人“激赏”,我们怀疑这是否出于真心。情浮于物,就失去了真,在为人物命运担忧、急切追寻下文的心境中突然闯进这种迷离难解的文字,也破坏了美。这种情感把握的失控,又是张炜家族系列长篇小说的遗憾。
故事情节的淡化与重复,人物形象的暗弱与错位,情感把握的失控与浮泛,使张炜90年代的小说创作偏离了叙事文体的规范,表现了作家创作的偏执与某种书卷气,相对削弱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厚度与力度。而这是以牺牲读者为代价的。读者心目中的张炜,是《古船》的作者,也是《家族》的作者,却不是《如花似玉的原野》、《怀念与追记》、《我的田园》这种“长篇小说”的作者。
注释:
〔1〕《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544页。
〔2〕同上,第537页。
〔3〕《我的田园》,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41页。
〔4〕《怀念与追记》,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476页。
〔5〕《柏慧》,1995年第3期《收获》第158页。
〔6〕同上。
〔7〕《怎样把我们的作品提高一步》,《孙犁文集》(四),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56页。
〔8〕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4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