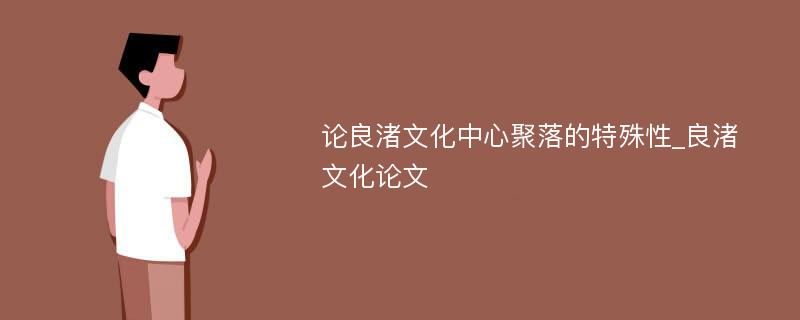
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聚落论文,特殊性论文,文化中心论文,良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龙山时代是华夏文明孕育过程中的黄金时期,在茫茫的中华大地上,各考古学文化竞相崛起,文明的曙光交相辉映,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更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然而良渚文化就象是一颗流星,在划过一道绚烂的文明之光后便随即陨落在茫茫夜空中。与同时期的其它文化相比,良渚文化表现出了独特的文化个性,其中在聚落形态上,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便与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上游的中心聚落有所不同,表现出了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黄河中下游还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进入龙山时代以后,聚落形态都由中心聚落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并且城址的数量较多,构成了这一时期聚落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在良渚文化所处的广阔的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城址的存在,也就是说,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从未发展到城址阶段,这就是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特殊性。
一般而言,史前聚落的产生是与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并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严文明将中国史前聚落的演进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分别代表了史前聚落遗址的发生、扩大和发展阶段,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是聚落遗址的分化阶段,铜石并用时代晚期是早期城址出现的阶段(注: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王震中则进一步结合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注: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5页。)。根据王震中的划分,中国史前聚落发展到初步分层与分化的中心聚落阶段时,典型时期是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屈家岭文化前期、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期等。随着聚落形态的进一步演化,到了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上游的广大地区都进入到严文明所称的早期城址阶段,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普遍出现,而良渚文化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却没有发现一座同时代的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这种聚落形态上的特殊性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在各种考古遗迹中,聚落遗址所能提供的有关考古学文化的信息量是最为丰富的。我们不仅能从聚落的分布、选址、环境等方面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可以从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以及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探讨该文化的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的特殊性在聚落形态上的这种表现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其文化内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视角。
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早期城址,这种聚落形态上的特殊性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首先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进行探讨,看一看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否能够应对建造城垣这样的浩大工程。
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稻作农业。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早在河姆渡文化时期便已初具规模,到良渚文化时,稻作农业已经相当发达。首先从农业生产工具看,良渚文化的石器均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穿孔技术发达,普遍使用管钻法,而且已经出现了石犁和破土器,说明其农业已经告别了刀耕火种以及耜耕的原始农业阶段而进入到先进的犁耕农业阶段,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正如游修龄所言:“良渚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是从河姆渡、罗家角时期的耜耕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并推测良渚文化水稻的产量能够达到播种量的15倍左右(注:游修龄:《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这在史前已经是相当高的产量了。从农作物的品种看,良渚文化不仅广泛种植粳稻与籼稻,在钱山漾与水田畈遗址还发现了象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核、毛桃核、葫芦等植物遗存(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说明其农业经济的多样性。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与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上游地区相比可以说有过之无不及。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之所未能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早期城址,并非良渚文化没有经济实力去修筑,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与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这种特殊性没有本质的关系。
如果说带有城垣建筑的早期城址的出现反映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强大,更反映了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强有力,出现了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的产生又是与阶层与阶级的分化相结合的。如果良渚文化时期尚未出现明显的阶层与阶级的分化以及强制性的公共权力,那么即便其农业经济再发达,也是没有能力去建造那些浩大的城垣建筑的。这样一来,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也就好解释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龙山时代,良渚文化的文明进程绝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任何文化,不仅有明显的阶层与阶级的分化,已形成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而且公共权力机构也是强有力的。
良渚文化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在墓葬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贵族墓与平民墓各居其所,差别非常大。浙江余杭反山、瑶山,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等贵族墓地都建在人工堆筑的高大的土台之上,墓内有木棺或木椁,有的还涂有朱漆彩绘。随葬品异常丰富,尤以玉器最为精绝。如反山墓地已清理出的11座大墓所出玉器以成组成串计即达1100余号,占全部随葬品的90%以上,以单件计数则多达3200余件。其中琮、璧、钺、冠形器、三叉形器等玉礼器种类齐全,制作精美,玉礼器上的神人兽面纹更是雕刻得如鬼斧神工(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与贵族墓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海马桥、松江广富林等地发现的平民墓地,墓葬小且无葬具,随葬品多为一两件陶器或石器,有的一无所有。就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而言,其实还可以细分为几个等级,如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像福泉山这样的贵族墓地,而福泉山又高于像少卿山这样的贵族墓地。同样平民墓葬也可以进一步划分,由此可见,良渚文化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墓葬当中反映得已十分清楚。
再从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机构看,良渚文化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权力机构确实存在,并且是强有力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大量的大型建筑工程上。良渚文化的大型建筑工程很多,有前面已述及的由人工堆筑而成的规模巨大的贵族高台墓地,有人工堆筑或依山修建的祭坛,更有被称为“土筑金字塔”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夯土台基,这在说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上最有代表性。
莫角山遗址为良渚遗址群中的中心遗址,整个遗址规模巨大,呈长方形土台状,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据莫角山发掘工作负责人王明达介绍:“在已经开挖的13个探方中,在红烧土坯以下的看似生土的地层,实际是经过人工搬动的,是人工用自然土筑成的,其最深的一处已达7米。”(注: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如此巨大的土台,竟由人工堆筑而成!此外土台上还有近3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基址,表明这里曾有像宫殿宗庙一样的大型建筑。吴汝祚认为:“良渚遗址的整个礼制建筑,由于规模庞大,估计至少需300万个或更多一点人工,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这决非氏族社会的能力所能达到,需要高于它的社会组织层次,即早期国家的产生。”(注:吴汝祚:《良渚文化——中华文明的曙光》,《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强制性公共权力机构的保障,规模巨大的莫角山“土筑金字塔”便不可能突兀而起。
以上我们仅从最典型的事例说明到了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机构以及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在发达的农业经济的保证下,良渚人完全有能为建造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实际上,莫角山的人工堆筑土台其工程量决不逊色于龙山时代的任何一座城垣建筑。如此看来,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早期城址,既非经济因素,也不在于文化的发达程度,而是另有原因。
良渚文化中心聚落的特殊性要从良渚文化自身的特殊性上去寻找答案。相对于龙山时代的其它文化而言,宗教巫术的盛行以及政教合一是良渚文化最为独特之处,而这正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未能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早期城址的主要原因。
良渚文化的宗教巫术十分盛行,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强烈的宗教氛围之中。赵辉在论及良渚文化的宗教与社会时指出:“良渚文化的宗教性遗物数量之多和品质之精是空前的,此还不算许多和教义有密切关系的反映良渚人的仪仗、祭祀、丧葬习俗方面的遗物遗迹资料。”“良渚文化的宗教性器物集中出土在大型墓地和大型墓葬的倾向,使研究者们相信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个高于基层大众的特殊僧侣阶层,用中国的称呼方式就是巫觋。”(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良渚文化的巫觋已经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特权阶层,并且垄断了宗教大奉权。根据《国语·楚语》一书中关于“绝天地通”的一段记载,在宗教权力被垄断之前,曾经有过“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阶段,因此颛顼才命南正重司天属神,命火正黎司地属民。张光直认为这一段记载是有关古代中国巫觋最重要的材料,为我们认识巫觋文化在古代中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启示(注: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页。)。颛顼“绝天地通”的实质是巫觋对宗教权力的垄断,从而使自己成为凌架于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良渚文化中具有特权的巫觋阶层的出现正是当时宗教巫术盛行的一种反映。
在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其中琮、璧等玉器,尤其是内圆外方的玉琮被认为是巫觋与神勾通的宗教法器。《周礼·大宗伯》中就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有关良渚文化玉琮的功用,各家说法不一,张光直认为,琮内圆像天,外方像地,中间的圆孔表示天地的贯通,也就是说,良渚文化的玉琮是巫觋用来贯通天地的法器,同时也是权力的像征(注: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此外,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也被认为是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徽,在很多玉器上都能见到。如果将良渚文化的大墓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等诸文化的大墓相比就会发现,后者的随葬品更多地表现的是对世俗权力的集中和财富的占有,带有宗教色彩的遗物甚少,而良渚文化大墓中带有宗教色彩的遗物则数量众多,质量精美,突出说明了宗教巫术在良渚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不仅宗教巫术盛行,而且还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即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在一起。在良渚文化的不少大墓中,琮、璧、钺共出。如果说琮、璧是神权的象征,则钺代表的是兵权或王权,亦即世俗权力。琮、璧、钺共出反映了墓主人既拥有宗教权力,同时也拥有世俗权力。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玉钺上刻有神人兽面纹,亦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生动写照。张忠培在论述良渚文化时指出,在良渚文化社会中,军权尚未高于神权,两者在社会的位置基本上处于同等地位。这点亦可从他们同居一墓地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是军权演变为王权,军(王)权愈来愈高于神权,日益凌驾于神权之上。军(王)权与神权并重,当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正因为良渚文化的神权还没有被军(王)权所凌驾,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生活中笼罩着浓厚而神秘的宗教氛围。
在宗教巫术盛行的情况下,良渚文化大量的劳动支出没有用在生产上,也没有用在建造城垣建筑上,而是用在与宗教有关的大型工程上,而这正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的主要原因。
与宗教有关的大型建筑工程首先表现为由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台墓地。与龙山时代的其它文化相比,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最为独特之处,几乎所有的大墓都葬在由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土台上,墓主人当然都是那些握有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贵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余杭反山、青浦福泉山、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吴县张陵山、苏州草鞋山等良渚文化大墓莫不如是。高台墓地规模庞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福泉山墓地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出地面7.5米(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寺墩墓地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面20米(注: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草鞋山墓地东西长120、南北宽100、高出地面10.5米(注:南京博物院:《苏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这些由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庞大,其工程量之大、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是可想而知的。
除高台墓地外,良渚文化的祭坛也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发现良渚文化祭坛的遗址已不在少数,主要有浙江余杭瑶山、汇观山、反山、海宁大坟墩、奉化名山后,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昆山赵陵山等。这些祭坛不仅有堆筑而成的,还有依山修建的。如瑶山祭坛建于海拔35米的小山顶上,平面呈方形,外围边长20米,总面积约400平方米。祭坛由多色土精心营筑成内外三重,中心部分为红土台,其外是灰土围沟,最外层则由黄褐色斑土筑成(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良渚文化祭坛的规模虽不及高台墓地,但无疑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厚葬显然已成为一种习俗,尤其是用大量精美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玉器来随葬。数量众多的玉器从开采、运输到最后的精雕细琢无疑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巫政合一的良渚社会,玉器尤其是带有礼器色彩的玉器,制作得更是不惜成本,一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尽管玉器的制作在人力、物力的消耗上不像大型建筑工程那样一目了然,但良渚人无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良渚文化而言,莫角山遗址也许是唯一一处能体现出一点现实价值的工程。前面所说的高台墓地与祭坛等大型工程不仅是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而且宗教意味浓厚,简言之,是为死人服务的,莫角山遗址好歹是为活人服务的。然而从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看,除了活人居住的宫殿外,必有像后世那样的宗庙,再加上高台上的祭祀遗迹,可以说,宗教的成分在莫角山依然突出。莫角山遗址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吴汝祚估计至少需300万个或更多一点人工,这样的规模在龙山时代是很罕见的。良渚人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营筑起来的不过是突兀而起的一个大土台,这也许只能从宗教的角度才能解释得通。试想良渚人如果将营建高台墓地、祭坛、莫角山超大型高土台基址以及精雕细琢玉器的人力与物力都用来建造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那么在长江下游地区,也必像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城址广布。可惜良渚人为宗教奉献了太多,他们没有这样做,也已无力这样做,这就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的主要原因。
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原因可以称之为外因,而前面所论的可谓内因。内因起主要作用,但外因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外因便是在龙山时代,良渚文化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没有受到大规模战争的威胁。
良渚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根据文献记载,五帝时期爆发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先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然后是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阪泉之战是华夏集团内部的战争,而涿鹿之战则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次对决。除了像这样的大规模战争外,小的冲突更是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下,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了一批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可以说,城址的出现是与战争密切相关的。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的兴废与古史传说中苗蛮集团的崛起以及尧、舜、禹征三苗息息相关,并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至于长江上游地区的史前城址,或许与苗蛮集团战败以后沿江西迁有关,即文献上所说的“迁三苗于三危”。纵观龙山时代古史传说中的几次大规模战争,其发生地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地区,而这些地区恰恰也正是龙山城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良渚文化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在古史传说中并没有大规模战争的记载,从考古发现来看,能反映战争的资料也并不多见。可见在龙山时代,当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中游地区到处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时,长江下游地区并未受到战争的实质性威胁,其中心聚落也一直未筑城垣以加强防御。由于良渚文化的宗教势力异常强大,因此尽管其分布区域很广,但各地出土的玉礼器的类型与形制却基本一致,具有宗教神徽性质的神人兽面纹更是被广泛接受,此外各地高台墓地与祭坛的形制也大同小异,这一切说明在宗教巫术的统治下,各地区尽管有不同的中心,但有着大致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使得良渚文化的凝聚力大大加强,文化认同感大大加强,在没有外来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良渚文化内部之间也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战争冲突。既然没有战争的威胁,那么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城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然理由,这也客观上促使了良渚人能够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都投入到与宗教有关的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上。因此,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当别的地区带有城垣建筑的史前城址纷纷崛起之时,高度发达的良渚文化还深深地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之中,其中心聚落也就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一直没有发展成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但这丝毫不会影响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因为城址仅就是否带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而言,而与中心聚落的性质并无本质的关系。与文明成就息息相关的是城市,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城址未必就能够成为城市,如西亚巴勒斯坦的耶利哥,早在距今10000年到9000年前就由于军事和其它特殊的原因(如保卫宗教上的圣地圣物等)而修筑了带有城垣建筑的城址(注: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页。),这样的城址显然不具备城市的要求。中国早期出现的城址,如大溪文化的湖南澧县彭头山古城(注:蒋迎春:《城头山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古城址》,《中国文物报》1997年8月10日。)以及仰韶文化的郑州西山古城(注: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同样也没有达到城市的要求。就城市而言,也并非一定要带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中国早期的城市体现的主要是政治与宗教上的功能,还不具备贸易中心的性质。正如张光直所言,中国早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注: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尽管没有防御性的城垣建筑,不能够称为城址,但已初步具备了政治中心与宗教中心的功能。张学海从莫角山中心聚落内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墓地与祭坛等一系列要素推论在良渚聚落群中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莫角山中心聚落已具备王都的性质,莫角山古国已经出现(注:张学海:《论莫角山古国》,《良渚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正如张之恒在对良渚聚落群进行综合研究之后所指出的那样,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已经具备了早期城市的性质(注:张之恒:《良渚文化聚落群研究》,《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