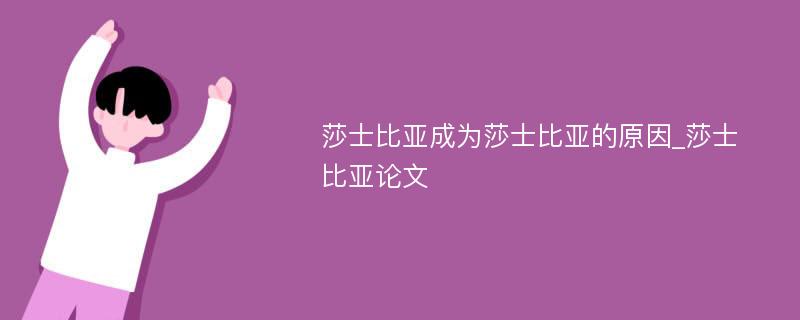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莎士比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世界上,莎士比亚是我们的文化英雄,他的名字几乎成为文学的代名词和人类创造力的象征。《不列颠百科全书》骄傲地宣称:“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他被广泛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像荷马和但丁这样的诗人,托尔斯泰和狄更斯这样的小说家,他们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但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作家的声誉能真正同莎士比亚相比……”然而,莎士比亚作为一种文化崇拜现象,在后理论时代被日益去神秘化。换言之,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各种文化机制作用下的历史过程;正如著名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所指出的,莎士比亚在世时并不是“莎士比亚”,他的经典地位是在十八世纪中期左右确立的(《莎士比亚与书》,30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英国著名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断言:“所谓‘文学经典’,所谓‘民族文学’,毫无疑问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确认为某种建构,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形塑的建构。”(《文学理论导论》)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的历史过程,就是“莎士比亚”被“建构”的过程,无论莎士比亚本人的动机和意图为何。
要讲清楚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援引两个例子。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最有名的台词出自《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朱生豪译文),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哈姆雷特》首次以四开本形式出版时(一六○三),这句话的版本是:“To be,or not to be,I there’s the point.”(“生存还是毁灭,嗯,问题就在这儿。”)而且“I there’s the point”也是明白无误的莎士比亚诗行(出现于《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第二三二行)(26-27页)。大约十年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卡斯顿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班上,我第一次了解了这一点,心中莫名的惊奇。这至少说明三点:首先,我们所知晓的莎士比亚不一定是,甚至很可能不是莎士比亚的本来面目;其次,作为经典作家,莎士比亚的文本其实并不确定;再次,四百年过去了,从本来的莎士比亚到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无论其人其文),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文化建构的过程。在《莎士比亚与书》中,卡斯顿以优雅的大手笔,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这些问题。百多页薄薄的一本,竟然纵横四个世纪,大开大阖,要言不烦,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然开朗,而且引人入胜,极具可读性,不得不令人钦佩。该书二○○一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二○○三年一年美国、英国、加拿大的重要学术期刊就发表了五篇书评,其影响力可见一斑。牛津大学教授多米尼克·奥利弗(Dominic Oliver)所言极是:“戴维·斯科特·卡斯顿在莎士比亚幽灵般文本存在的历史中的旅行必将引导初学者,挑衅专门家,并激发所有人的兴趣。”
卡斯顿教授屡次讲过(不仅在著作中,而且在课堂上),莎士比亚时代的戏剧是通俗的娱乐形式,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无不为之倾倒;其地位恰如今日之电影,作为文学是不入流的。戏剧时代的明星是演员(莎士比亚时代的演员都是男性),而非剧作家,如同电影吸引观众的是男女主角,我们对编剧是谁漠不关心一样。这与我们概念中的作为英国文学核心经典的莎士比亚大相径庭。其实不唯莎士比亚,文学何以成为文学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建构过程。卡斯顿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对于莎士比亚的任何理解,必须以承认莎士比亚与我们的距离为发端(《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经过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理论和主义的洗礼,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呈现出回归历史的倾向;但这里的历史不再是简单的或本质主义的历史,而是建立在各种理论基础之上的有效解释相互竞争的领域。在莎士比亚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研究领域,卡斯顿坚持认为,文学生产的合作性是不可避免的,戏剧尤其如此。在剧院里和印刷厂里,作者意图当然不是决定产品样式的唯一条件,而且往往被漠视、篡改和僭用。比如,剧团为了演出需要,经常调整、删除、添加剧本内容,这些改动可能来自剧作家,也同样可能来自作者以外的其他人,至少莎士比亚一六一二年左右退休后和一六一六年逝世后,是别人修改他的剧本以供演出(15页)。英国第一部现代著作权法一七○九年由安妮女王颁布,一七一○年正式生效,此时莎士比亚已去世近一个世纪。在早期现代英国,政府通过书业公会和审查制度来控制图书行业,版权属于出版商而非作者,“法律规定获取所有权的要件只是出版商不能侵犯别的书商对同一文本的权利,以及他们应该遵循适当的权威渠道来保证权利。只要没有更早的权利要求,出版商尽可以自由地印行原稿,而不顾作者的权利或利益”(23页)。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莎士比亚对其剧本出版抱有兴趣,更不用说介入或监督剧本的出版过程,莎剧的早期版本经常性地存在文本讹误,错漏比比皆是,诚如第一对开本编者、莎士比亚昔日同事赫明和康德尔所称:“各种各样盗窃的、偷印的书”伤害了读者,“暴露它们的有害的骗子们通过欺骗和偷偷摸摸使这些书变得畸形和残缺”(73页)。在印刷媒介中,抄写员、出版商、印刷商、排字工、校对者、装订工、书贩等中介以及后来更多的编者、注释者、改写者、改编者、评论者、译者、读者等,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书和意义的生产和接受,在此复杂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有时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书商的行为主要受利益驱动,迎合市场需要,他们出版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并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保存英吉利民族最伟大作家的作品”(49页)。赫明和康德尔固然要用堂皇的对开本来“永远纪念如此杰出的朋友和同事”(55页),将莎士比亚确立为“作者”(像本·琼森一样的作者),但他们并不像格雷格爵士(Sir W.W.Greg)等新目录学家们假定的那样具备良好的目录学修养(74页),甚至一百年以后的诗人、莎士比亚著作编者亚历山大·蒲柏也并不了解《暴风雨》、《麦克白》、《亨利八世》等剧首次发表于第一对开本,所以登悬赏广告征集这些剧一六二○年以前的早期版本(99页)。莎士比亚剧作的版本、目录、校勘、编辑之学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才逐渐成熟起来,并不断走向深入,其基础无疑是一六二三年出版的第一对开本和其他早期版本,因为莎士比亚流传下来的手稿微乎其微。现代莎士比亚编辑学肇始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大放异彩,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新目录学、文本社会学等颇具影响力的学派,并与新兴的书籍史、媒介研究等学科交织在一起,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可以说,一部莎学史即从一个重要侧面映照了整个西方四百年来的学术史和文化史。
卡斯顿教授正是从这一高度来为他的著作立意的。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卡斯顿远远不是一头扎进故纸堆的老学究(尽管他的考据功夫堪称上乘);恰恰相反,他对过去的关注总是充满着现实关怀。他在一九九九年的专著《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的章首题词中,引用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警语:“关于过去的每一个形象,若非被现在确认为自己的关怀之一,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二○○一年的专著《莎士比亚与书》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数字时代呈示和编辑莎士比亚的种种可能性。十年后,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写道:“我希望本书的翻译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就如何保存和评价我们的历史的问题开展更加广泛的文化讨论,特别是在我们的数字时代,这一讨论变得益发紧迫。”这里的“我们”不仅指美国或西方,也包括中国,包括东方,包括全世界,因为珍惜历史遗产、保存历史遗产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在卡斯顿的原文中,“历史”是复数,这不仅承认了人类文明史的多样性,也暗示了莎学史的多样性。“莎士比亚”同样也是复数的,因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的人从不同视角对莎士比亚的建构非常有可能——如果不是必然的话是多样的。其二,坚持文本社会学或文学唯物主义的卡斯顿却常常从常识和人心的基本角度出发理解历史,体现出博大深切的人文关怀。例如,从钱伯斯(E.K.Chambers)到戴维·贝文顿(David Bevington)的数代著名学者,包括格雷格等,都将书商约翰·丹特(John Danter)视为“声名狼藉”、“恶臭难闻”、“肆无忌惮”,仿佛已成定论。卡斯顿却独具慧眼,为丹特翻了案。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对丹特的作为,而且对新目录学家的阐释都做到了“同情之理解”。卡斯顿指出,“丹特的罪行是印刷了一部有缺陷的莎剧文本”,即《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五九七年“坏四开本”,故此惹得崇拜莎翁的学者们义愤填膺,将丹特的职业行为贬损为“不道德、不称职”。实际上,“我们对莎士比亚文本年代误植的希望和期待干扰了我们的历史判断”:丹特“算不上邪恶的书商,甚至也算不上特别桀骜不驯”;“为了节省十便士,丹特决定逃避剧本的审查和登录,他的目的是为了给家人提供食物,而不是为了出版一部莎士比亚悲剧的残缺版——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看待的话,我们对丹特的印象会好一些”(44—46页)。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卡斯顿的叙述,但他毅然抛开数代学者的道德高地,并非标新立异,故作惊人语,而是以自己博大的心灵之镜和人生阅历照射出一个负责的丈夫和父亲的卑微,一个因为家庭责任而反抗行业权威的小书商。这个故事可能“不那么有趣,但几乎肯定更符合事实”(30页),无疑更深入人心。人本主义的观照使我们对历史的阐释取得了普遍化的意义。在义理、考据、辞章中,三者居其首者乃义理,而卡斯顿教授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就是他的“义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像伟大的塞万提斯、曹雪芹、巴尔扎克、鲁迅一样,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在于他直指人心的效果;正是一代又一代读者成就了“莎士比亚”。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例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燕园初读《李尔王》时,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考狄利娅的死。那种疑惑和揪心的痛,只有在《平凡的世界》中田晓霞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时和类似事件在切身生活中上演时才体会得到。那是年轻的心第一次经历美好的毁灭,为了一探究竟,我特意把《李尔王》选作毕业论文的题目,结论是莎士比亚在向我们艺术化地展示生活的极端可能性,唯其极端,才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现在想来,这个结论还是肤浅了,考狄利娅之死和田晓霞之死哪里是“极端可能性”,这是活生生的每天都在进行中的“日常可能性”啊!然而莎翁太有力量了,以至于我多年以后了解到,十八世纪的著名文人约瑟夫·艾迪生和塞缪尔·约翰逊也都承受不了,他们同样认为《李尔王》的结尾“不可忍受,触犯了一切合乎常情的正义感”,完全违背了“诗性正义”。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作为读者,我的反应不是唯一的,好像一下子为自己找到了撑腰的。
还有更好玩的。一六八一年,正值王朝复辟时期,内厄姆·泰特(Nahum Tate)迎合读者的感受,以“诗性正义”的原则彻底改造了莎士比亚版《李尔王》:考狄利娅不仅活了下去,而且和爱德伽喜结连理,成为神仙眷属,共同主持朝政,李尔王则在欣慰中安度晚年。约翰逊博士对此改编甚为赞赏,一个半世纪中,它代替莎翁版《李尔王》占据了舞台,直至十九世纪中期,莎士比亚的戏剧原本方才回归舞台。更有趣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被重塑为幸福结局,男女主人公得以幸存,两种版本交替上演,一天演悲剧,一天演改写后的悲喜剧(86页)。可见,人们并不总是以近乎神圣崇拜的态度对待莎士比亚,许多时候他无非是一块橡皮泥,任人捏来捏去。自德莱顿以后,改编莎士比亚之风如此强劲,以至于十八世纪致力于恢复莎士比亚真实文本的学者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亦未能免俗,他“吸取其全部精华,去除其糟粕”(91页),按照新古典主义时代的趣味和社会风尚,将历史剧《理查二世》篡改为爱情悲剧。读史至此,我们禁不住一面惊异于后来者的创造性,一面感叹莎士比亚的弹性/韧性/可塑性/灵活性。莎士比亚的弹性和韧性是其丰富可能性的表征,也是其丰富可能性得以实现的条件,二者互为表里。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并不在于有一个真实的、理想的、永恒的莎士比亚。事实上,卡斯顿教授的结论是:无论莎士比亚以何种物质形式呈现出来供我们观看/阅读/聆听/欣赏/批评……他都不是“真实在场”,而是像丹麦王子之父的鬼魂一样,是一个可疑形状,一个“我们称为莎士比亚的幽灵般的存在”(136页),仅此而已,而恰恰在于莎士比亚已化身千百,变幻莫测,伸缩自如,适应性极强。莎士比亚就像那孙悟空的毫毛,说变就变,而各种形式的物质载体——无论表演、朗诵、手稿、印刷,还是电影、电视、录像、电子媒介等则是莎士比亚逃不脱的“紧箍儿咒”。“紧箍儿咒”使莎士比亚痛苦(甚至因此“变得畸形和残缺”,面目全非),但它也成就了莎士比亚,把他培养成为文学界的“斗战胜佛”。试想,如果没有“紧箍儿咒”,没有九九八十一难,孙悟空充其量就是花果山的美猴王和自命不凡的“齐天大圣”,怎么又会成为“斗战胜佛”呢?
诚然,十八世纪追寻或至少标榜追寻莎士比亚“真实文本”或“理想文本”的编辑工作也取得了相当成就。那个时代对莎士比亚持有一种精神分裂般的态度:“一方面自以为是地改编他的剧本以确保剧场演出的成功;另一方面却毅然决然地寻找莎士比亚的原本”(93页)。自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开始,学术性的莎士比亚版本层出不穷,最终在塞缪尔·约翰逊、乔治·斯蒂文斯(George Steevens)和艾萨克·里德(Isaac Reed)的集注版中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数代学者的莎士比亚编辑史恰恰证明了莎士比亚文本的不确定性。卡斯顿正确地指出,“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尽管以其勤奋和才识见称,然而首要的成果却是,人们终于就莎士比亚文本的不确定性和不完美性达成共识”(107页);他并且强调,即便莎士比亚的剧作手稿完全保留了下来,它们“也只是作者文本而已,从来不能等同于戏剧”,因为戏剧的本质是一种具有“极端合作性”的体裁(119页)。更何况,莎士比亚现存的手迹仅限于六七个签名、两个单词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中的一百四十七行,除了舞台演出外,他也不在乎自己剧本的命运。正如约翰逊博士精彩描述的那样:“这位终将不朽的伟大诗人退休生活悠闲富足,年龄还算不上‘跌入了岁月的谷底’,但他如此漫不经心,所以在他疲倦过度,兴味索然,或者体弱乏力之前,并未出版过自己的作品集,也不想挽救那些已经面世的作品,这些作品因为腐坏而晦涩难解,光彩顿失;他同样没有将真实状态下的其余篇什托诸世人,以保证它们更好的命运”(53页)。
尽管在后理论时代的总体氛围下,莎士比亚不再神秘,莎士比亚作品不再那么神圣,但对莎士比亚的“诗人崇拜”远未结束。当然,这种崇拜无可厚非(总比“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拜物教来得好些),但不妥的是,“诗人崇拜”常常蒙蔽了我们的慧眼,导致一种情绪不恰当地支配了我们的认识。仅举一例,国内某学者看到“Master William Shakespeare”的说法即断言,莎士比亚生时就被公认为“大师”了,于是引以为据,喋喋不休。其实呢,查一下字典就知道,早期现代英国的Master A相当于现在的Mister A (mister是master的变体),“Master William Shakespeare”无非就是对有地位、有学问人的尊称“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意思(我在想,他为何不说“莎士比亚师傅”呢?Master也有“师傅”的意思呀,可见还是“诗人崇拜”的心理在作祟)。如果莎士比亚在世时已被称为“大师”,那么当时的“大师”也忒多了些吧。
当然,《莎士比亚与书》也不是没有争议或没有缺憾。有时候,卡斯顿未能做到前后一贯,比如一位书评作者指出,他在上一页称“手稿,而非印刷,是他的媒介”(10页),下一页(事实上,是下一段)却说:“莎士比亚的合法媒介不仅有剧院,还有图书,即便图书不是他的首要媒介”(11页)。这里,有必要区分主动媒介和被动媒介:手稿和剧院是莎士比亚的主动媒介,而印刷和数字化是莎士比亚的被动媒介,正如卡斯顿的评论一样:“虽然他从未追求过伟大,但他逝世七年之后,伟大找上了他”(78页)。然而,正是卡斯顿暗示的主动媒介和被动媒介的区分受到了以卢卡斯·厄恩(Lukas Erne)为代表的学者的质疑和挑战。厄恩旗帜鲜明的论著《作为文学戏剧家的莎士比亚》(二○○三)认为,莎士比亚始终有意识地既为剧院观众创作,也为读者创作,对于其剧作出版也有着“一贯策略”。虽然笔者不一定完全同意厄恩的观点,但确实觉得卡斯顿的看法有值得修正和补充之处。例如,从莎士比亚作品的内证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对印刷媒介的意识和兴趣可能比卡斯顿愿意承认的要多一些。不用说莎翁在十四行诗中提及“我这哑口无声的诗卷”,呼吁他的爱人“请试读无言之爱所发出来的呼声:用眼睛来听该是情人应有的本领”(第二十三首,梁实秋译文),就是在戏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凯普莱特夫人也用“一卷美好的书”来比喻帕里斯的脸,朱丽叶要是嫁给了他,就成了“一帧可以使它相得益彰的封面”(第一幕第三场第81—94行,朱生豪译文)。这一延伸比喻固然可以理解成手稿书,但它同样可以诠释为印刷书,至少原文是模棱两可的。根据马文·施佩瓦克(Marvin Spevack)的《哈佛莎士比亚语词索引》(一九七三),“书”(book/books)在三十六部莎剧中都出现过(仅有《错误的喜剧》、《终成眷属》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例外),总计一百二十八次。卡斯顿的著作专注于物质文化的外部证据,而几乎没有考察内证,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卡斯顿的有些遵从传统的观点,比如他一再强调莎士比亚时代的剧本是“短命印刷品”和“廉价的小册子”,有简单化的嫌疑,值得商榷。这种观点或许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事情正在起变化,戏剧的文学地位正在确立过程中,剧本正在变得不那么“短命”和“廉价”。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论述。不管怎样,这一重要问题显然值得进一步商榷和争鸣。
这里牵扯到方法论的问题。卡斯顿的文本社会学路向或我所谓“文学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聚焦于文本赖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比如印刷书、超文本等,在意义生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自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的经典著作(分别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九六四]和《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九七九])以来,随着媒介研究和书籍史的兴起,这一方法异军突起,近几十年来蔚为风行,其优点是鲜明有效,如果运用得当,尤其是和文学批评的固有方法结合起来,将是潜力巨大、大有可为的。问题就是卡斯顿在《莎士比亚与书》中对此方法的应用稍微有点过了头,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文本阐释等固有的文学批评方法,结果导致鲜明有效有余,而精微全面不足。从文本理论和编辑理论的角度讲,以杰罗姆·麦根(Jerome McGann)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路向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以G.托马斯·坦瑟勒(G.Thomas Tanselle)为代表的、远远更为根深蒂固的柏拉图传统的生命力可能更为久远(参见117—118页)。正如另一位书评作者所指出的,卡斯顿一边排斥追求作者意图的理想主义,一边却倾向于将文本的物质性理想化。这一逻辑矛盾源自作者方法论的根本缺陷。
标签:莎士比亚论文; 文学论文; 英国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李尔王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