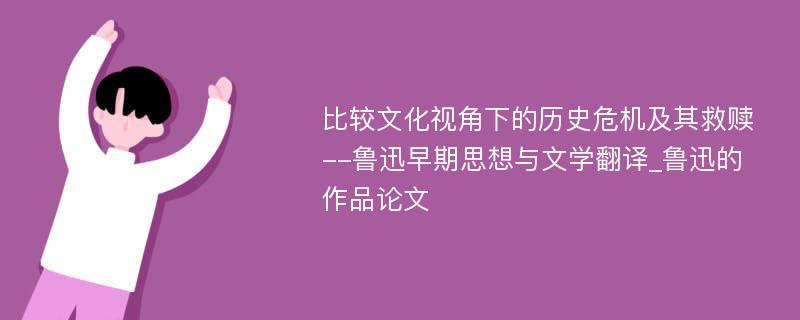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危机及其救赎——鲁迅早期的思想与文学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视野论文,危机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将当时文坛“崇拜创作”的倾向,归入到阻碍天才产生的因素之列,因为“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而且,他认为,即便是中国的作品学习了外国的技术和精神,文笔漂亮,但“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①鲁迅还坚持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必须“开放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②在五四时期,鲁迅一面批判“国粹”,一面主张输入“世界潮流”和“新文化”,甚至将翻译的地位置于创作之上。这种翻译观在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等人那里都可见到。和他们一样,鲁迅自己也身体力行地从事着翻译工作。他一生的译作有两百多部(篇),总计三百余万字。有学者甚至指出,“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是作家”。③
不过,与胡适等人把翻译文学视为新文学的“模范”不同,④在鲁迅那里,翻译的意义超越了文学,而承担着重塑文化、重塑历史的使命。因此,要深入认识鲁迅的翻译,我们必须在其思想发展脉络中展开细致的考察。
一 作为新伦理的科学
受晚清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青年鲁迅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外,还尝试了科幻小说的翻译。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成绩,是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和《地底旅行》(1906)。
《月界旅行》是根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的。该小说讲述的是美国的一群天文爱好者在亚电等人的带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制造飞船并成功登上月球的故事。与同时代人相比,鲁迅对“科学”有不同的理解。
洋务派将中国的被动挨打归因于科技的落后,提倡实业救国。维新派则认为,政治制度的落后才是主要原因,因此需实行君主立宪。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青年鲁迅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路矿学堂学习自然科学技术,后又到日本学医。然而,鲁迅逐渐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的知识,“科学乃是伦理甚至精神问题了”。⑤在翻译《月界旅行》时,鲁迅的初衷并不是要普及科学知识,而是想要倡导一种新伦理、新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他便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部小说。他指出,人类依靠理想、意志和科学技术,正逐步地征服自然,因此,是“有希望之生物也”。而小说作者正是“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鲁迅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证明人的精神力量和认识能力的伟大,使读者“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导中国人群以进行”。⑥
因此,鲁迅特别重视小说的审美效果,而有意排斥其科普功能。他指出,“胪陈科学”,会导致“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的局面。要激发读者的兴趣,必须“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因此,便需要“掇取学理,去庄而谐”,最终“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鲁迅对小说做了一些增删改易。
首先,在文体上,鲁迅采用了章回体。这也是晚清翻译小说的普遍性做法。鲁迅的译本每一回都有回目,在很多回的结尾有回末诗,又有“究竟为着甚事,且听下回分解”这样的套语。
其次,在内容结构上,鲁迅对原文的各章进行了“截长补短”。他删掉的章节主要是原文第五六两章。这两章讲的都是人类对月球的认识,属于一般知识的介绍,没有情节的推进,难免让“常人厌之”。同时,他还对不少章节进行了合并。比如,原文第三章讲巴比堪的报告所引起的反响,第四章讲剑桥天文台的建议,而在鲁迅的译本中,这两章被合并为第三回。这些被鲁迅合并的章节,大体上都属于一个故事单元。为了满足章回体小说在叙事上的紧凑性,鲁迅尽量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浓缩在一章里。在随后翻译的《地底旅行》中,鲁迅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法。
最后,在语言上,鲁迅采用文白混杂的形式,并做了删削。他说:“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⑧这样的处理,显然也是为了便于读者的接受。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译作不多。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幻小说中所蕴涵的探索、进取、求真的伦理精神。他的翻译,只是为了传递这一精神。而对翻译这种行为本身,鲁迅还没有来得及思考。
二“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比较文化视野与翻译的使命
1906年幻灯片事件后,鲁迅开始反省科学救国的理想,并开始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危机。在这一比较文化的视野下,鲁迅的翻译观也发生了飞跃。
沿着早期从伦理、精神的角度来认识科学的思路,鲁迅开始反思科学的局限性。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赞赏了科学的发达给人类带来的进步。但对于中国的“兴业振兵”之说,鲁迅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仅炫于当前之物”,“惟枝叶之求”,只看到了西方科学发达的表面现象,却“无一二士寻其本”,违背了“进步有序,曼衍有源”的发展规律。他提醒人们,片面地追求科学技术,则“所宅不坚”,不能长久,而必须追寻科学得以发达的文化根源。他认为,“教宗学术美艺文章”,“均为人间曼妙要旨”,必须与科学协同发展:
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⑨
鲁迅认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决不能“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仅仅注重科学,就容易造成人“精神渐失”,而最终,失去了文化的沃土,科学也必然“同趣于无有”。
在随后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更深入地阐述了这一思想。他首先再次批评了洋务派“竞言武事”的救亡思路。他的批判,并不是从兵工科技对挽救危亡无效这一角度出发的,而是着眼于社会、文明的进步:“夫以力角盈绌者,于文野亦何关?”他认为洋务派只知道学习西方的兵工技术,却不知道与古人相比,不过是杀戮的机械先进了一些而已,根本无法显示人类的进步:“则曷弗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罟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又何耶?”⑩
然后,他又批判了维新派发展实业的主张。他认为在“国若一日存”的情况下,发展实业,或许能够“广有金资,大能温饱”,但如果“怙恃既失”,就有可能“被虐杀如犹太遗黎”(11),而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这会助长人们自私自利的思想,并不能真正改善人们的生活。
鲁迅认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救国主张的缺憾在于,他们没有找到中国所遭遇的历史危机的真正根源。这一根源,不在科学技术,不在政治制度,而在文化,而且,其所指,不是中国文化,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他认为,对科学技术的偏至让19世纪以来的人类文化遭遇了病变:
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12)
科技的发达,激发了人们对物质和实利的追求,刺激了贪欲,精神上的灵光黯淡了,“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西方列强对中国等弱小国家的侵凌,其根源正在于此。而20世纪的人类文明,则“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将更加偏重于人内部的精神生活:“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13)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还将解决中国的历史危机的出路,局限在科技水平的提升或者政治制度的变革上,那就是沿袭了19世纪文明的逻辑,将无法避免文明的病变。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明哲之士”,应该“洞达世界之大势”,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来摆脱历史危机: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致,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4)
在他看来,要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就必须让国人在精神上“自觉致,个性张”,即明白真正的“人生意义”:“内部生活之强,则人生之意义愈邃。”而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张扬和丰富构成最大威胁的,正是19世纪的物质文明影响下的实利主义倾向,因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15)克服19世纪文化的偏至,“取今复古”,“苏古掇新”,(16)让人类的精神在一种更完整、丰满的文化形态中得到滋养。因此,“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借鉴域外文化,是必须的步骤之一。
这种文化的比较与选择,不但有助于个体精神的发育,而且,就一国国民来说,还有助于其“国民精神”的培育:
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17)
在这里,鲁迅提出的“审己”与“知人”,即包含着文化比较的涵义。“比较既周”,则有真正的自觉,从而培育出“国民精神”。因此,“世界识见”关系着自我与整个民族的新生。
鲁迅将中国的历史危机归因于人类文化的病变,又从文化的层面上提出了解决方案。在这种比较文化的视野中形成的解决方案,自然需要发挥翻译跨语言、跨文化的沟通与整合能力。因此,翻译的意义,不再是为中国的新文学提供“模范”,而在某种意义上承担着疗救人类文化的偏至,解决历史危机的重大使命。这在鲁迅的思想和翻译实践中有进一步的展开。
三 “内曜”与“心里的烦闷”
鲁迅带着一种更明显的译者身份,逐渐成长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从1909年起,他的翻译作品主要有:《域外小说集》(短篇集,1909,与周作人合译)、《一个青年的梦》(剧本,1920)、《工人绥惠略夫》(中篇,1922)、《现代小说译丛》(短篇集,1922,与周作人、周建人合译,其中鲁迅译9篇)、《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内心的挣扎和苦闷的,另一类则是反战文学。鲁迅对这两类作品的翻译热情,也能够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找到归属。
首先,鲁迅热衷于翻译表现内心纠葛的作品,与他对科学的反省,对实利主义的批判,对人的内部精神生活的重视有关。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将他的文化解决方案,又在精神层面上做了更为详细的引申。
这一解决方案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核心要素是“内曜”。鲁迅指出,中国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少数“知者”身上,必须由他们对后觉者进行启蒙:“属望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而这些“知者”率先的觉醒状态,便是所谓“内曜”:“内曜者,破黮暗者也。”这种觉醒是一种真正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它的发生,有时需要一定的“外缘”,但一个人对于内心的忠实,坚持独立的选择,不为外界的毁誉所左右,才是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唱和而不与之言。”(18)
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恰恰是19世纪的文化所缺乏的。鲁迅认为,物质文明的兴盛,导致人们更重视实利,为此常常不敢坚持己见,而外界社会,也会对不合时宜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压制,长此以往,便造成了个体精神的苓落。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批评维新派立宪国会的主张时就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借众以陵寡”的危险,让人丧失自我,“皈依于众志”,(19)而更多的人则是“假是空名,遂其私欲”。(20)因此,他特别赞赏尼采、叔本华等人“仅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确信在是,满足亦在是”。这便是“渐自省其内曜之成果”,从“物质万能之说”中觉醒过来,张扬个体内部精神生活的结果。(21)
这不但是20世纪文明的主流,而且,对当下中国的救亡事业来说,也是急需的:
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傌,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22)
在鲁迅看来,当下急需少数“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能够挺身而出,探索真理,通过“评骘”比较,批判地接受不同的文明,作为启蒙资源,“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启发更多人的觉悟。在这里,鲁迅暗示了这种先觉者可能的遭遇。他们有可能被世人称赞或者诋毁,有可能被追随,有可能被孤立。但在任何情况下,先觉者都不应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鲁迅认为,很多天才(性解)就是这种为真理而不惧抗俗的英雄。他们往往为世所不容,尤其是在传统中国。统治者为了“保位”,百姓为了“安生”,都不允许“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23)《摩罗诗力说》中介绍的拜伦、易卜生等人,都是这样的天才。而在鲁迅后来的翻译和创作中,也有不少表现这类人格的。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鲁迅也在呼唤着这样的天才:
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
他希望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能够让少数“卓特”之士,“不为常俗所囿”,领会其中独特的“心声”和“神思”,由此培养一种天才(“性解”)的精神品格。
这里的“心声”也是鲁迅的文化解决方案在精神和美学上的重要投射。一个人在觉醒之后,不可避免地会通过言语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己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24)这就是所谓的“心声”。它是内心的真实表达:“心声者,离诈伪也。”(25)如果每一个觉醒的个体都能够发出自己的“心声”,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宰,那么,一个独立的个体就真正诞生了。这种“心声”也会感染他人,“发国人之内曜”。而如果人人都能够发现自我,那就会迎来群体的觉醒:“盖惟有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26)因此,少数天才发出“心声”,真实地表达自我,是开展启蒙工程不可避免的步骤。
鲁迅认为,好的文学,即是“心声”的表达:“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27)而那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28)的“摩罗诗力”,则是“心声”最典型的呈现。
“摩罗诗力”是鲁迅“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文化救赎方案在美学上的具体表达。他认为,像柏拉图、老子那样“不撄人心”的“顺世和乐音”,会让人“入于苓落”,“复由渐即于无情”,而一旦“有情已去”,则“一切虚无”,人类就堕落到“虫兽”的位置了。(29)而“摩罗诗力”正是一剂良药:“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30)发挥出生命的全部潜能。因此,他对诗人的定义就是:“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31)其效果就是:“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和平,以之将破。和平之破,人道蒸也。”(32)
鲁迅这样定义诗歌,针对的也是现代人对“实利”的趋向。因为人一旦将眼光局限于“实利”,其后果就是“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由此便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麻木。同时,实利之念还往往让人“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诗人的作用,就是移其性情,打破人内心的平衡,将其推向一种运动状态,“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33)
在这样的观念下,鲁迅非常注重翻译那些表现与外界对立的个体内心的不安、不平与挣扎的作品。鲁迅的这些翻译作品又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一类写源自平凡的生活的焦虑、不安或感伤,如安特莱夫的《谩》《默》等;一类写尼采式的孤绝英雄为拯救世界而产生的苦闷甚至疯狂,如阿尔志跋绥夫的《黯澹的烟霭里》《工人绥惠略夫》;还有一类,则通过描写被压迫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生活的暗淡”,通过渺小的个体与社会的冲突来表现其内心的痛苦,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
《谩》和《默》均收入《域外小说集》中。《谩》的主人公怀疑恋人对自己不忠,不但怀疑她的言语,甚至怀疑整个世界“一切谩耳”,以致最后亲手杀死了恋人。当逮捕他的人责骂他是“狂人”或“可怜人”时,他对这些惊恐之人鄙夷不屑,“视之咥然”。最终,绝望中的主人公发出了“援我”的呼救声。
小说《默》写神父伊革那支的女儿威洛吉伽从圣彼得堡回来后一直将自己幽闭在屋里,不久后突然自杀。神父的妻子悲痛欲绝,随后中风并失去了语言能力。整个家庭从此被沉默笼罩着。神父为女儿的死而内疚自责,一次次在臆想中对她说话,而得到的回应,却只是沉默。小说的结尾写恐惧的神父在不能动弹不能言语的妻子面前,似乎感到了她的宽恕,最终发现她“恕宥怨愤,两复无有”,“而此荒凉萧瑟之家,则幽默主之矣”。这种沉默如无物之阵,让渴望求得真相、安慰、宽恕和交流的神父,处于一种无法反抗、无法突围的压迫中,最终甚至疯狂。
这两篇小说中人物内心的冲突与挣扎,均来自平凡人的现实生活。此外,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鲁迅所译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医生》以及契里科夫的《省会》、《连翘》,对这种心理状态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小说《医生》以1905年俄国的反犹运动为背景,写一位叫柏拉通密哈罗微支的医生被请去为一位在冲突中受伤的警厅长治伤的故事,表现出了主人公内心中“爱与憎”的冲突。一开始,医生一直处于两难中。一方面,犹太人受到惨烈迫害的场景让他对警厅长产生了厌恶;另一方面,出于本能的同情,他又不能抛下受伤的警厅长不管。最终,他对犹太人的同情占了上风,毅然逃离了警厅长的家。在《医生》的译后记中,鲁迅说:“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34)
这种内心的“纠缠”,在契里科夫的《省会》《连翘》中,则化为了一种怀旧性的失落与感伤。《省会》写自己回乡的所见所闻。主人公是一位作家,从圣彼得堡回到家乡省会。因为革命的动荡,家乡已物是人非。曾经的初恋情人和情敌已不知所踪,而自己的大学同学,一个曾具有正义感的年轻人,而今已经做了警察厅的副厅长,还盘问我回乡的动机。这位“为要防止和扑灭那一切无秩序而设的警官,却回想起自己所做的无秩序的事来以为痛快,而且仿佛淹在水里的人想要抓住草梗似的,很宝贵的保存着这记忆”。当主人公走出警察厅时,对此感到万般疑惑,又怀疑自己也许和“白发满头”的他一样,“在人生的长途上,早已是掉了生命之花”。这样,作者把对社会的停滞和黑暗的批判,集中于它对美好的“生命之花”的吞噬上,在乡愁之外,更是传达了对人生和岁月的无奈与哀伤。这种情绪,以及那胆小的旅店掌柜、由一个有理想的年轻大学生堕落为专制的帮凶的警察厅副厅长,都可以在鲁迅同是以还乡为题材的《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中找到影子。
《连翘》则讲述了一个清新美好的小故事。很多年前,主人公和二十岁的恋人外出散步,路过一处围墙时,见里面连翘开得正艳,在恋人的要求下,主人公爬上围墙为其摘了几枝。分别后,主人公从美好的幻想中醒来,“现世的生活已经开始了”。鲁迅说,契里科夫的小说“虽然稍缺深沉的思想,然而率直、生动,清新”,而且善于心理描写,取材源自生活,“颇富于讽刺和诙谐”。(35)鲁迅所翻译的这两篇小说,都渗透着怀旧的失落和感伤气息,只是其情绪波动的程度,相对安特莱夫的小说来说,已变得有些温和。
鲁迅所翻译的另一类小说,则主要表现高傲的尼采式的英雄内心的苦闷以及他们与外在世界的冲突,比如安特莱夫的《黯澹的烟霭里》、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
《黯澹的烟霭里》(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写一位叫尼古拉的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被学校开除,与父亲争吵之后离家出走。七年后,他突然回到家里。家里人热情地接纳了他。全家人都希望他能够与父亲重归于好,留下来一起生活。然而,他厌倦了“这里有钱,三个工场,四所房屋,我们天天结股票”的生活,在圣诞节前夜毅然再次离去,消失在黯澹的烟霭里。主人公是一个不向世俗妥协的人。而他的存在,也让家里充满了不安和恐怖。鲁迅说作者“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36)主人公的阴郁、苦难与固执,与鲁迅所赞赏的那种尼采式的英雄非常相似。
鲁迅还翻译过安特莱夫的另一篇小说《书籍》(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这篇小说写一位身患绝症的作家在弥留之际将生命的价值全部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上,然而,他的书在排版、运送、审查的过程中,却仅被人们当成了一种普通的物件,并未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体现出特别的精神价值并得到尊重。小说由此表现了一颗高傲的心与鄙俗的世人之间的冲突,有“颜色黯淡的铅一般的滑稽”。(37)
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其主人公是一名叫多凯略夫的大学生,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逃脱,化名为绥惠略夫,租住在玛克希摩跋家中,与同住的亚拉借夫,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大学生,发生了思想冲突。绥惠略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认为“人的一切欲望,全不过猛兽本能”。而亚拉借夫却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对世界抱有希望,相信真理与和平。不过,在严酷的现实中,他们最终都走向了反抗。亚拉借夫为了保护革命的友人送来的资料而选择了与警察对抗,被追捕的绥惠略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举枪向无辜的群众疯狂扫射。鲁迅说:“他根据着‘经验’,不得不对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发生反抗,而且对于不幸者们也和对于幸福者一样的宣战了。于是便成就了绥惠略夫对于社会的复仇。……然而绥惠略夫确乎显出了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终身战争,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反抗而且沦灭(Untergehen)。”(38)这种试图拯救庸众并最终走向彻底的绝望和疯狂的人,与鲁迅常常提及的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的主人公,都属于悲哀的先觉者。
除此之外,鲁迅还翻译了一些描写被压迫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生活的暗淡”的小说,比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明那·亢德的《疯姑娘》、亚勒吉阿的《父亲在亚美利加》(均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这类小说虽着重写人物的外在境遇,但却无情地解剖着人的内心的软弱、黑暗,或者呈现其痛苦。
阿尔志跋绥夫的《幸福》,写妓女塞式加烂掉了鼻子,姿容不再,遇到生存危机,无奈之下,只好在一个寒冷的雪夜里,让一个在工厂当仆人的色情狂毒打自己,供其娱乐,以换得五个卢布。小说特别细致地呈现了塞式加内心的挣扎。一开始,她绝望地走在雪夜的街道上时“悟到了伊的没意义的生存的恐怖”,“说不出的感情,在伊只是增高增强起来,而且已经达到了这境界,就是以为人们际此,便要陷入野兽的绝望,用了急迫的声音,狂叫起来。叫彻全原野,叫彻全世界”。这本该是一个觉醒的过程。然而,当她受辱并拿到五卢布后,想到自己马上可以吃饱穿暖时,“伊的全存在已经充满了幸福的感情”,她“向狭路转过弯去,在那里是夜茶馆的明灯,忽然在伊面前辉煌起来了”。鲁迅在后记中特别提到当下很多的批评家对写实主义感到厌倦,其原因在于,“人们每因为偶然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只有庸众才贪恋现实的安稳,“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39)这是人性中阻碍人觉醒的重要因素。
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写一个叫塞林的女人,年轻时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和皇家大公跳过一次舞,成为当地男人追捧的对象。她拒绝了很多人的求爱,幻想着大公有朝一日会来娶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不得不放弃这一希望,便又试图到舞会上去重新赢得男人们的关注。然而,年老色衰的她,受到了羞辱。她退出了名利场。母亲去世后,穷困潦倒的她成了人们眼中的“疯姑娘”,只有靠回忆来打发时光。鲁迅在译后记中,肯定小说写出了“无可补救的绝望”,并引用培因的话说,“夸张与无望的悲观,是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惨而且不快的小说的特色”。这种让人不快的“撄人”之声,却正是鲁迅所期待的:“大抵惨痛热烈的心声,若从纯艺术的眼光看来,往往有这些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Dostojovski)的著作,也常使高兴的读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40)
亚勒吉阿的《父亲在亚美利加》写一个农夫抛妇弃子到美国淘金,逐渐与家人断了音讯,而一家人在穷苦中逐渐绝望,猜测着他的处境,艰难度日。小说特别写到了这一家人遭受债主逼迫和邻人嘲笑的情景。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让读者“自然能理会出悲惨来”。(41)
总的来看,鲁迅在这一时期所翻译的小说,不管是直接描写人物内心的挣扎的,还是从个体与社会对立来展示人物内心的纠葛的,都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是真正的“撄人”之声。这也是鲁迅创作《呐喊》《彷徨》《野草》,以及翻译《苦闷的象征》的精神基调。
四 “反诸己”与世界主义
关注内部的精神生活,让鲁迅对描写“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的作品产生了热情。如果说,这些色彩暗淡、基调悲观的作品,反映了鲁迅思想和精神中黑暗的一面,那么,鲁迅对反战小说的翻译热情,则显示了其光明和积极的一面。从《域外小说集》开始,反战题材的文学作品,便成为鲁迅翻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同样能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找到根源。
鲁迅指出,疗救19世纪以来文化的偏至以及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转向主观的精神生活,促成“内曜”的发生。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精神秩序,个体之间就难免产生冲突,压迫与侵略的现象就不能完全消除。因此,真正的觉醒,不但包括自我意识的发生,还应该包括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合理关系的想象。
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将部分民族主义者表现出的以牙还牙式的“崇侵略”的倾向,归结为“恶声”之一。他认为这是一种“兽性其上”的表现。但他没有简单地否定人类的兽性,而是认为,一方面,人类的兽性不可能得到消灭,它一开始就存在,虽历经进化,但“古性伏中,时伏显露”,另一方面,兽性也不应该被消灭,因为它对于个体的存在是必须的,如果和平日久,则“民性柔和,既如乳羔”,(42)一旦遇上兽性者入侵,则无法自保。因此,他反对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
真正解决侵略问题的出路,需要精神上的“反诸己”:“不尚侵略者何?曰反诸己也。”(43)“反诸己”这一精神活动,“意味着主体进入与他人、与异己者的关系中落实和体会‘人不乐为皂隶之心’”,然后再反过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由单一关系的存在而发展为一种相互关系的平等存在”。(44)因此,它的真正目标,不是让被侵略者取代侵略者的地位,而是让双方在精神上彻底清除“强/弱”、“主/奴”的二元对立模式,将一切他者视为平等的存在。而如果将这种个体间的精神秩序,推及到社会,以至文明、国家关系的层面上,不但中国可以摆脱受侵略的处境,而且整个人类也将彻底根除侵略现象。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鲁迅对反战小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域外小说集》中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翻译的最早的一篇反战小说。该小说以俄土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俄国士兵伊凡诺夫的口吻,写其受伤后被被遗弃荒野四日并最终获救的经历。在荒野中,面对被自己刺死的土耳其人的尸体,伊凡诺夫反问:“斯人浴血死,定命又何必驱而致之乎?且何人哉?彼殆亦——如我——有老母与?每当夕阳西匿,则出坐茅屋之前,翘首朔方,以望其爱子,其心血,其奉养者之来归也!”最后,他领悟到自己与他“皆同也”,对发动不义战争的统治者提出了批判。这种精神上的“反诸己”,与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中对战争的歌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中,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也是一篇反战小说。小说写俄土战争期间,巴尔干半岛的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两个兄弟国家也卷入了战争中。保加利亚的威尔珂立下军功,受到了表彰。然而,“只有一件,这简单的农夫不能懂:人为什么和塞尔比亚人打仗呢?”在后记中,鲁迅明确地批判保加利亚的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45)而这一篇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也将“塞尔比亚人”视为平等的存在,对狭隘的国家观念和战争产生了质疑,因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鲁迅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也是表达反战思想的。这部剧本写的是一位青年(“为了人类的命运不怕十字架的人”)在一位“不识者”的带领下,参加各种反战活动的经历。在第一幕中,“不识者”带青年参加了一场由亡魂们举行的“平和大会”。在战争中死去的各种人物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对“国家”的质疑,原来敌对的双方互相表达了悔意,握手言和,“很愿意做兄弟”。其中,“鬼魂五”说:“我们至少也须尊重别国的文明,像尊重本国的文明一样。……和别国交情好,尊重别国的文明,比那拿别国做成亡国以来,不知道于我们多少利益。”青年也认为,消灭战争的方法就在于:“不用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用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认识到“民族的互助,才能增进幸福的事”。第二幕和第三幕则探讨了消除战争的方法。一个乞丐主张通过“爱”来打破这个“国家主义时代”和“金钱万能时代”,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秩序不可站在金钱的上面,不可站在憎恶的上面,该站在爱的上面,大家的幸福上面。”而一个画家则希望通过“美”来改变世界:“知道我的事业,是将人类和运命打成一气的事。”青年则主张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立场,而不是国家的立场:“只要不从国家的立脚地看事物,却从人类的立脚地看事物,各国的风俗和习惯,在或一程度调和了,各国的厉害,也在或一程度调和了,不要专拿着我执做事的时代一到,战争也便会自己消灭了。”在第四幕中,“不识者”带领青年观看了一出反战剧。该剧以拟人化的方式,再现了“一战”爆发的整个过程。演出结束后,剧作者乞丐出场,再次重申:“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争便许自然消灭了。”
这部剧本以剧中人物的口吻,多次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战争,使“民众成了一气”的世界主义理想。鲁迅在译者序中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46)他认为,“人的真性”,可以穿越国家、民族等一切障碍,成为人们理解和沟通的基础,帮助人们消除隔阂,消除战争。这种破解历史难题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将仇恨洒向对方,而是反问和质疑造成仇恨的机制,力图在普遍的“人性”的基础上实现全人类的平等与和平,正是鲁迅“反诸己”的真义所在,同时也呼应了鲁迅对中国彻底摆脱西方侵略的出路的思考,以及在一战的背景下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在五四时期,鲁迅在翻译上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成绩,就是爱罗先珂的童话。尽管鲁迅的翻译是为了表达对爱罗先珂的声援,(47)但江口涣称“爱罗先珂君是无统治主义者;是世界主义者”,(48)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鲁迅当时的思想是契合的。这些童话中,除《春夜的梦》写的是超越阶级的沟通和理解外,大部分写的是不同的生命超越了物种的同情,比如《狭的笼》《鱼的悲哀》《古怪的猫》《为人类》《世界的火灾》等。
《春夜的梦》写一个公爵的女儿和一个百姓的儿子分别抓走了萤火虫和金鱼,因为误会发生争吵。水底的王告诫他们说:“凡有美的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倘起了一种要归于自己,夺自别人的心情,好好的记着罢,这心情,便不纯粹了。”由此,两个小孩在出于对美的尊重中消除了隔阂,成了好朋友。《狭的笼》写一只热爱自由的老虎想要帮助羊、女人、金丝雀、金鱼获得自由,却最终被人类关进了“狭的笼”,供人参观。他悲哀地意识到“人类被装在一个看不见的,虽有强力的足也不能破坏的狭的笼中”,因此,“人才是下流的奴隶,人才是畜生”。这种超越物种的同情,还表现在《鱼的悲哀》中。这篇童话写一条小鲫鱼盼望“大家个个都相爱,快乐的生活起来”,到一个没有饥寒的“更好更美的国土”里去。然而,当它和其他小动物发现教堂里为万物祈祷祝福的男孩,抓走了很多小动物时,终于意识到“单为人类的哥哥们做食物而被创造的自己的运命”是很多悲哀的。最后作者发表议论说:“对于将一切物,作为人类的食物和玩物而创造的神明,我是不愿意祷告,也不愿意相信的。”在《古怪的猫》中,一只猫以“我”的口吻,写自己的朋友,另一只猫“虎儿”,因为坚持认为“老鼠是我的可爱的可同情的兄弟”,无心再抓老鼠,被视为“古怪猫”,并被捉走处死。最后,“我”也认同了它的观点,并陷入了绝望中。《为人类》写一位解剖学家九岁的儿子非常同情被解剖的小狗。梦中,一条狗告诉他:“狗和人单是衣服两样,内容都是相同的。”《世界的火灾》写一个美国实业家,因为同情白杨和枫树受冻,便为它们生火取暖,结果引发了一场大火,被当做“狂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爱罗先珂以童话的方式,书写人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同情与理解,传达了其世界主义的理想。在1922年版的《爱罗先珂童话集》扉页上有一首题为“Homarano”(意为“人类中的一员”)的诗。其中一行为:“我的名字是人类中的一员。”(49)这正是爱罗先珂童话的基本主题,也是鲁迅的“反诸己”为人类的精神秩序所做的规划。
五 结语
在短暂地尝试了科幻小说翻译之后,鲁迅以反思科学救国思潮为契机,开始从比较文化的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危机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解决方案,又将这一方案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上,并最终落实为一种美学方案。
鲁迅反对科学崇拜所带来的实利主义,认为这是中国遭受西方侵略的文化和心理根源,主张通过文化的比较和综合,来超越19世纪以来的物质文化所引发的心灵的偏枯,滋养出一种健康完整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养成,一方面需要催生个体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也需要这些觉醒的个体具有精神上的平等意识。而这两个方面,也相应地投射在鲁迅的翻译热情中:一方面,他注重表现内心的纠葛的作品,另一方面,他注重主张人类平等的反战文学。在翻译对象的选择上这种鲜明倾向性,表明在鲁迅那里,翻译已经超越了个人趣味或者文学本身,而承担着解决历史危机,重塑历史的重大使命。而鲁迅的创作也受到翻译的极大影响,这使得中国新文学从诞生之初,就处于一种跨文化的语境中,并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现代性做出了承担。这无疑是中国新文学留给我们的宝贵传统。
注释:
①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176页。
②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11页。
③《孙郁谈〈鲁迅译文全集〉》,《北京青年报》2008年10月7日,C2版。
④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期,1918年4月15日。
⑤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⑥⑦⑧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64、164页。
⑨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⑩(11)(12)(13)(14)(15)(19)(20)(2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6、54、56~57、57、47、46、47、55页。
(16)(18)(22)(24)(25)(26)(42)(43)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5、27、25~26、25、26、34、35页。
(17)(23)(27)(28)(29)(30)(31)(32)(33)(39)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70、65、68、69、70、70、70、71、70页。
(34)鲁迅:《医生·译者附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35)鲁迅:《连翘·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0页。
(36)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37)鲁迅:《书籍·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38)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4页。
(40)鲁迅:《疯姑娘·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
(41)鲁迅:《父亲在亚美利加·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44)高远东:《鲁迅的可能性——也从〈破恶声论〉寻找支援》,《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45)鲁迅:《战争中的威尔珂·译者记》,《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46)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2期,1920年1月1日。
(47)鲁迅:《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页。
(48)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49)该诗由张过大卫译成中文,参见《鲁迅先生保存的爱罗先珂的一首世界语诗原文的文学史价值与许广平先生关于此诗的一封信》,《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标签: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