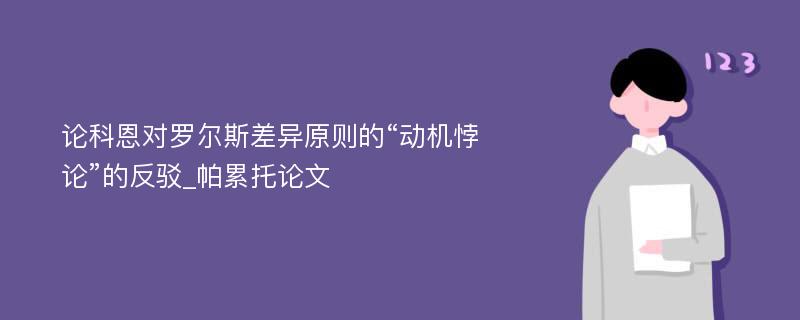
论柯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反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动机论文,差别论文,原则论文,罗尔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本预设
柯恩于2008年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一书试图做两个拯救:一是将均等主义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中拯救出来;二是将正义概念从罗尔斯的建构主义正义观中拯救出来。(cf.Cohen,p.2.下引仅标页码)本文主要关注柯恩的第一个拯救。笔者认为,柯恩在这里从运气均等主义的预设入手,对差别原则做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深入甚至最有力的批判。在柯恩看来,差别原则是罗尔斯对运气均等主义与帕累托标准所做的一种妥协,而他的批判表明差别原则所体现的妥协方式存在着内在的动机困境。不过在笔者看来,柯恩的批判只是对差别原则这种特定方式的妥协有效,对妥协本身则并不有效。而帕累托标准存在的问题才是这种妥协本身的真正困境。柯恩设想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运气均等主义,但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因为运气均等主义自身具有更严重的动机困境。相反,如果从帕累托标准入手解决差别原则的动机困境,效果会更好,因为在去掉效用的人际间不可比性这个假设后,帕累托标准所代表的理由能更好地体现在后果主义之中,而后果主义可以更好地解决这种动机困境。
理解柯恩的批判需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它针对的是接受罗尔斯的基本设想的人;第二,这种批判预设了罗尔斯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三,柯恩的反驳论证是符合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方法的。尽管罗尔斯强调他所用的是社会契约方法,但他的契约达成并不取决于人们的实际心理状态,罗尔斯所要求的实际上是根据原初状态中的预设推出其正义原则。(参见葛四友,2012年b,第50页)正因为如上所述,所以柯恩可以根据罗尔斯的一些基本预设,对其导出差别原则的论证做出批判。
柯恩的批判预设了以下几点:第一,罗尔斯接受运气均等主义的如下观点:除非出于人们的选择或过错,没有人应该比其他人过得差。(cf.p.156)第二,柯恩区分出关于平等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平等只具有工具性价值,平等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过得更好。这种观点不赞成把更好者变差以得到平等。另一种认为平等具有内在价值,这是柯恩所支持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具有一样多的有价值的事物,这本身就是好的。因此,减少一个人的所得从而与另一个人变得一样,这就平等而言是好事,即使综合来看未必是好事。(cf.pp.30-31)柯恩认为,罗尔斯的起点平等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讲的。(cf.p.91)第三,罗尔斯承认帕累托标准具有强大的力度,从而间接承认了人们过得有多好是很重要的。(cf.p.90)第四,罗尔斯所接受的差别原则体现了博爱精神。(cf.p.130)第五,罗尔斯主张的公平正义社会是一个良序社会,里面的人都是因为真正接受公平正义原则而遵守它,也就是人们都有充分的正义感。(cf.p.74)第六,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原则只适用于制度的选择,而不适用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选择。(cf.p.117)
二、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
柯恩早期对差别原则的批判主要是对上述第六点的批判,即差别原则在应用上的限制。柯恩认为,如果人们在政治领域(即制度选择的领域)是均等主义者,而在私人领域(即个人行为选择的领域)却是利益最大化者,这就存在着动机的悖论:个人的动机是不一致的。(cf.p.2)柯恩着重讨论了罗尔斯关于差别原则之应用限制的论证,表明这些论证无法消除上述动机的不一致性。其中对罗尔斯激励论证的反驳是最根本的,奠定了反驳其他论证的基础。
1.现在先来看柯恩对激励论证的反驳。为了简便,可以把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最有利者阶层(即能干者阶层),另一个是最不利者阶层。激励论证的基本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干者得到的报酬不高,那么他们的动力就不够,生产的东西就会少得多。由此,相对于给高报酬而言,最不利者得到的反而更少。因此,我们应该以不平等作为激励,提高能干者的努力程度,从而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12、87、116页)
激励论证的基本精神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在柯恩有关增税的例子中:
(1)如果经济不平等有利于最不利者,它是有证成的。(大的规范性前提)
(2)当税率是40%的时候,(A)能干者生产的比在60%税率下要多,(B)结果最不利者在物质上反而得益更多。(小的事实性前提)
(3)结论是:税率不应该从40%升到60%。(cf.p.34)
这个论证抽象起来看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为了反驳,柯恩提出了一个类似结构的论证:
(1)付钱赎回孩子比不赎回孩子对父母是更好的。
(2)(假设没有别的办法)除非得到钱,否则绑架者不会把孩子还给父母。
(3)因此,父母应该给绑架者钱。(cf.p.39)
尽管结构一样,但这个论证看起来就不那么合理了。为了突出这种不合理性,柯恩提出了一个共同体之中的人际间检验,即论证是由共同体中的人向共同体中的人提出的,无论是谁对谁提出都应该是有道理的。(cf.p.42)然而,当这个论证是由绑匪向人质的父母提出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论证的不合理性了:绑匪是在抢劫。在柯恩看来,如果我们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的话,那么激励论证就与绑匪论证是一样的。因为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能干者也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由此也就赞同偶然性(包括能干者的天赋)所产生的利益与负担应该由共同体内的人所均分,所以当能干者要分得偶然性利益的更大份额时,他的论证与绑匪的论证是一样的,他也是在抢劫。这就是说,只有当能干者不接受运气均等主义时,小前提(2)才为真,由此差别原则才可以证成不平等激励。(cf.pp.48-49)换言之,不平等之所以有利于最不利者,是因为如果不给予激励的话,能干者会罢工。而能干者之所以会罢工,只是因为能干者不具有均等主义的态度。然而,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他就不会因为税率从40%上升到60%而选择罢工。所以,对收入不平等的激励对于最不利者并不是必要的。这表明罗尔斯的激励论证是不成功的。
2.人们还可以从罗尔斯的理论中构造出一种略微不同于激励论证的帕累托论证,它可以证成差别原则的应用。这种论证分两个阶段来看差别原则的证成。罗尔斯在第一阶段认可起点平等状态D1,比如说是(5,5),然后转到由差别原则所认可且更好的不平等状态D2,比如说是(6,9)。相对于D1而言,在D2中不仅能干者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且最不利者也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据此,如果我们不从D1转到D2,则是不理性的。换言之,平等状态D1与帕累托最优是相冲突的,这个论证由此也被命名为帕累托论证。(Barry,p.217)由于柯恩认可帕累托最优所具有的力度,因此,他对这种论证的反驳是致力于表明其平等观与帕累托最优是相容的。
在这一反驳中,柯恩提出了一个新的状态D3。现在假设在D1时人们拿的小时工资都是5,这是起点平等状态(5,5)。在D2(6,9)时他们拿的小时工资分别是不能干者为6,能干者为9,显然9高于6高于5。按照帕累托论证,这里6与5之间的差别证成了9和6之间的差别。然而,柯恩认为,只要能干者不出现激励论证所假定的动机不一致,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到分配状态D3(7,7),那里大家都拿7,7小于9,但大于6。非常明显,D3按帕累托标准优于D1,但与D2是不可比较的。这样,D3的平等与帕累托最优就是共存的。换言之,只有当能干者在私人选择时违背支持初始平等的正义观念的要求,我们才得不到D3。由此,如果我们真正接受支持初始平等状态D1背后的根据,并且不具有动机不一致,那么我们得到的初始分配状态就是D3而不是D1,而由D3转向D2并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由此,帕累托论证是失效的。(cf.pp.101-105)
3.但是,罗尔斯还有一个论证,认为差别原则只适用于制度,它管辖的是人们对制度的选择,而不是人们在制度之下所做的行为选择。(参见罗尔斯,2000年,第298-299页)这就是认为“公平正义”主要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柯恩对此有两个反驳:第一个反驳着重于说明这种限制与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说明有冲突。(cf.pp.130-131)首先,罗尔斯之所以认为差别原则体现了博爱原则,是因为不平等是为了改善最不利者。(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80页)但前面关于激励论证的讨论表明,如果只通过社会的基本结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且允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动机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那么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就需要不平等作为激励,而若人们在日常行为中的动机能体现平等主义精神,则改善最不利者的生活并不需要不平等作为激励。因此,“除非改善他人,否则不想要更多”与“最大化的自利动机”是不相容的。其次,罗尔斯认为,最不利者在他的社会里也能保有尊严,因为他们的处境无法得到改善了。(同上,第139页)然而关于激励论证的讨论表明,最不利者目前占有的地位只是因为能干者强烈反对平等才获得的。因此,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在日常选择中也支持差别原则,那么最不利者的处境能够得到进一步改善。所以这种限制并不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尊严。最后,罗尔斯认为具有正义感的人会出于正义原则去做事,因为他们相信这能表现他们作为自由且平等的人的本性。(同上,第417页)但是,如果我们把正义原则仅限于基本结构,仅限于政治领域,而在私人领域中却允许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则将有悖于上述表现。
柯恩的第二个反驳是认为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划分理据不清楚。罗尔斯本人的看法并不是很确定和清楚,柯恩将其归纳为两种主要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基本结构就是国家的强制制度。(cf.p.132)人们在此可以区分出维持这种结构并将其结构制度化的选择,与发生在这个结构之内的选择。但是,柯恩指出这种划分理据有两个问题。(cf.pp.132-134)第一,罗尔斯强调基本结构是因为其影响极为深远且自始至终,基本结构是正义的首要主题恰恰是因为这种影响。(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6-8页)然而,为什么我们可以对基本结构之中的人们的选择所产生和破坏的机遇等不闻不问呢?此外,有这种影响的肯定不只是强制性结构,宗教、家庭等都具有这种影响,因此按说它们都应该接受正义原则的管辖才对。第二,罗尔斯本人有时候并不支持这种看法,而是有所摇摆,比如对家庭的看法就是如此。(同上,2000年,第11、71、214、273、285页)
罗尔斯的第二种看法强调基本结构是主要的社会制度,更多地依赖习俗、规定、期望而不是法律。(cf.p.134)不过,柯恩指出,一旦基本结构的理解从强制转到约定与习俗,则个人的选择行为是否应该在正义的权限之外就不清楚了。(cf.p.134)因为这种理解有两个麻烦:第一,非强制性结构所能维持的那种约束和压力恰恰存在于行为者的倾向中:当行为者选择一种有约束和压力的方式行动时,他们就实现了这种倾向。第二,就非正式结构而言,结构的选择与个人在这种结构之内的选择这种区分只在概念上是可能的;两者在外延上却是等价的,因为非正式结构无法把形成这种结构的选择与这个结构之内的选择区分开来。因此,适用于非强制机构的正义原则也适用于个人的日常选择行为。(cf.pp.134-138)据此,柯恩认为罗尔斯处于困境之中:一方面,如果罗尔斯认可上述关于“基本结构”的第二种看法,那么正义原则就既适用于基本结构也适用于个人选择;另一方面,如果罗尔斯认可第一种看法,那么他对基本结构的选择就是专断的,没有依据的。(cf.p.138)以上分析表明,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论证也无法消除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
4.柯恩还着重考察了自由主义者支持差别原则的另一个有力论证:平等面临三难困境,即平等、帕累托最优与职业选择自由是无法共存的。柯恩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论证。假设能干者在20000美金年薪下偏爱园丁而不是医生,但若做医生有50000美金年薪,他就偏爱做医生。如果在20000美金年薪下他愿意做医生,那么他会极大地帮助其他人。几种选择的情况如下:
A.50000美金,做医生。此时在工作满足和收入上都比其他人好。
B.20000美金,做园丁。此时在工作满足上比其他人好很多,收入则一样。
C.20000美金,做医生,此时在工作满足上还是比其他人好,但收入则一样。(cf.p.185)
共同体对三者的排序是:C好于A,A好于B。柯恩总结了这个例子的一般意义,即:除非消费者偏好可以决定生产什么,否则就会违背帕累托最优。但只有当人们具有职业选择自由,能对它做出回应时,消费者偏好才能决定生产。如果国家不做劳动安排,则只有通过价格才能让职业选择回应偏好,这就会违背平等。因此,要实现平等,或者需牺牲帕累托最优,或者需牺牲职业选择自由。这也就是说,前面的D3状态只有牺牲职业选择自由才能得到。(ibid)
但是,柯恩认为这种三难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对于自由成分的描述不清晰。他举了另一个简单的例子,即社会上的捐血情况:(1)不买血;(2)有足够的血;(3)有选择献血的自由。如果没有足够的人愿意无偿献血,就会出现(1)、(2)和(3)无法同时实现的类似三难:如果不买血,又给予人们献血上的自由选择,我们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血。因此,要想有足够的血,就需要么买血,要么强制人们献血。(cf.pp.188-189)
柯恩认为对此有一个伦理解决法:如果足够数量的人受感动,出于共同体情感而自愿捐赠,那么三难就消失了。柯恩非常清楚:在现实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有足够的人自愿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认为这恰恰说明:只是在某些条件下下,三难困境才会存在。上文表述三难困境的关键假设是:能干者一定会选择20000美金年薪的园丁或者50000美金年薪的医生。但是如果能干者真的接受运气均等主义,那么他就会选择20000美金年薪的医生。柯恩并不需要否认这种选择使能干者变差了:这是出于他的道德承诺,因此是合情理的。柯恩的关键假设是:当能干者按照运气均等主义行事时,他是自由的。这里的一般意义是: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道德原则行动,我们是自由的。柯恩认为,反对此点的人面临着一个二难:道德对谋杀的禁令要么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要么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如果它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那么信守均等主义承诺也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但我们不想要一个有约束的道德是不对的。如果它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那么个人信守均等主义承诺也不是对人们自由的约束。因此,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讲,我们都不能用自由来反对均等主义的约束。(cf.pp.192-194)
5.自由主义者还有一种反驳:自由的意义在于自我实现,即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不是决定做什么,而是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据此,柯恩上面对三难的反驳就不再适用。柯恩对此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就不能说,平等与帕累托最优的联合牺牲了“自我实现”的自由,而只能说有些公民失去了这种自由,有些公民则得到了更多的这种自由。柯恩承认,能干者在平等社会中的生活确实没有在不平等社会中那么有吸引力。但是限制能干者生活的利益的意义在于增加最不利者的利益。当医生在相对的意义上受损时,其他人得益了。均等主义者承认,绝大部分在现实社会里能获得高报酬的人在均等主义社会里会承担更多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干者被奴役了,因为他们(在综合意义上)过得并不比任何人差。均等主义社会要求能干者生产得更多,但不要求他们牺牲得更多。(cf.pp.206-208)
对此可能还有一种反驳,即自我实现与其他利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它是词典式优先的。也就是说,个人不能为了任何他人而放弃这种自我实现。柯恩对这种反驳有一个很好的回应:在这种前提下,能干者要求更高的工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做并不能抵消他从事这个工作所带来的自我实现的损失。因此,或者自我实现是一种与其他利益可通约的利益,那么我们只是将其放到一般的效用加总中去计算平等;或者自我实现是不可通约的,并且具有词典式优先的地位,那么收入差别作为激励就无济于事。(cf.pp.209-212)
三、动机悖论的蕴含
柯恩上面的论证表明:认为差别原则只适用于制度而不适用于个人选择的观点是无法证成的。一旦我们认可由激励所引发的不平等,动机悖论就产生了。这个批判表明:差别原则并不是无条件成立的,而是要看引起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柯恩后来认为,这种对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的批判实际上也适用于差别原则本身。(cf.p.152)科恩的“动机悖论”反驳揭示了罗尔斯证成差别原则的根本问题:两种理由的两阶段论证。罗尔斯承认了两种理由:(1)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或选择,所有人应该过得一样好;(2)帕累托原则——欢迎有益于所有人的变化。尽管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证成考虑了这两种理由,但他分别只让一种理由在一个阶段上起作用。柯恩对此的反驳与德沃金对起点平等理论的反驳(德沃金,第92-93页)如出一辙:无论是什么理由,应该要么总是起作用,要么总是不起作用,而不能人为地让它在一个阶段起支配作用,在另一个阶段却完全不起作用。
1.柯恩认为,帕菲特从契约角度对差别原则的论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该论证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正义要给予所有人同样多,因此,我们从平等开始,每个人都有权坚持它。这解释了为什么最不利者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但是当不平等有益于所有人的时候,所有人都会一致地接受差别原则,再坚持不平等就是不理性的。柯恩对此有两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是认为不利者有否决权的理由与由此导致的结果之间具有不一致性。假设开始的分配状态是(5,5),A对转向状态(4,6)具有否决权,但对转向状态(5,6)则没有否决权。柯恩认为这里有不一致性,因为尽管前一种转变是绝对意义上变差,但后一种转变却能在相对意义上变差,因此A对这两种转变应该要么都有否决权,要么都没有。只有当我们坚持平等的理由是人们不能掉到某个绝对水平之下时,上面在否决权上的不同才是说得通的。但罗尔斯坚持平等的理由是人们受到了相对剥夺,而不是要保证人们不掉到某个绝对水平之下,因此这里否决权的不同是说不通的。(cf.pp.164-165)
第二个回应是:尽管后面的转变是所有人一致同意的,但如果一致同意可以使得后面的分配是正义的,那么一开始我们就可以采用一致同意的原则作为正义的原则。由此,一致同意的原则就可以使得一个让最不利者更为不利的分配也是正义的。柯恩认为,既然开始我们就坚持平等原则,而不是一致同意原则,那么后面即使有一致性同意也不能使得这种状态是正义的。(cf.pp.165-166)
2.阿内逊对柯恩的批判思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反驳:他认为差别原则只需要推定(assumed)平等而不需要确立(establish)平等。(Arneson,p.18)这有点类似于法院对人们所做的无罪推定:它并没有确立某人无罪,只是假设他无罪。阿内逊由此认为,差别原则的转变并不存在动机悖论。(ibid,p.16)笔者认为,柯恩对此其实可以作出如下回应:有充分的文本证据表明,罗尔斯在对差别原则的讨论中是确立了平等状态的,如他对自然的自由体系、自由主义体系和公平的机会等原则的讨论(参见罗尔斯,2009年,第56-69页),以及他把天赋当作共同资产的讨论(同上,第77-78、139、463页),都表明他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
笔者认为,面对此种回应,阿内逊可以说即使罗尔斯的文本有此预设,但差别原则在论证上不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而柯恩则可以做如下反驳:罗尔斯认为只有帕累托改善这种理由才可以使得我们偏离平等。如果开始的状态是D1(5,5),那么我们只有权利向D2.1(5.1,7)转变,而没有权利向D2.2(4,9)转变。如果平等原则没有被确立而只是被推定,那么任何理由都可以使得我们偏离这种推定的平等,这正如任何罪行都可以使得原来被无罪推定者不再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并不能取消任何罪行。这也就是说,如果只是推定平等,那么后一种转变就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总效用增加了。笔者认为,可以从柯恩的观点做这种推论的根据,在于他接受帕菲特的以下说法:如果罗尔斯没有接受起点的平等,那么我们很可能接受的是效用最大化原则而不是差别原则(cf.p.167)。不仅如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帕累托最优在没有起点状态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比如,可以假设一个皇帝极为残暴并且极有能力,能够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如果接受帕累托最优的基本含义,则有这样一个皇帝的社会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任何改革都会引起这个皇帝状况的变坏,从而不是帕累托改善。据此可以认为,既然差别原则认为帕累托标准非常重要,那么它就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
3.上面的讨论进一步表明:要么罗尔斯所讨论的政治共同体的人都接受了运气均等主义,这时只要不出现动机悖论,那么作为激励的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必要的;要么人们没有接受运气均等主义,那么差别原则的起点平等状态D1就是没有力度的,从而认为需要帕累托改善才能改变D1就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无论人们是否接受运气均等主义,差别原则都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差别原则,它代表着两种理由的妥协:一种理由是运气均等主义,即人们在没有选择和过错的情况下,应该过得一样好;另一种理由是帕累托最优,即人们在绝对意义上过得好是很重要的。柯恩的批判表明:差别原则的这种妥协是错误的,因为它让两种理由分别只在一个阶段上起作用,而在另一个阶段上完全不起作用。这就是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4.那么,这种困境的出路是否在于接受平等,即如柯恩所说的,需要把平等从差别原则之中拯救出来呢?假设起点平等状态D1是(5,5),并假设由于信息、组织而不是动机的原因,使得收入差别对于改善最不利者是必要的。那么,按照差别原则的词典式解读,向D1.2(5,7)的转变就会是帕累托改善(不损害最不利者)。根据帕累托原则的经典表述(要有益于最不利者),向D1.3(5.1,7)的转变也是帕累托改善。按照柯恩的理解,为了理由的一致性,平等在两个阶段上都要起作用,因此差别原则肯定要做出改变,但改变的幅度取决于平等具有何种权重。如果平等在分配正义中具有绝对的权重,那么向D1.4(6.999,7)的转变是不正义的。这实际上是柯恩的观点,下一节会重点考察。如果平等只具有一种相对的权重,那么尽管向D1.3的转变是不正义的,但向D1.4(6.999,7)的转变很可能就是正义的,甚至向D1.5(6,7)的转变也是正义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认为平等在分配正义中具有绝对的权重,那么差别原则只要变成平等-差别原则即可。当然,除了补偿性的收入差别之外,作为激励的差别依然是不正义的。因此,尽管科恩的“动机悖论”反驳确实否定了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但它所揭示的差别原则的困境对差别原则所代表的妥协的杀伤力并不大,罗尔斯妥协的基本精神依然能够成立。
5.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回应科恩关于差别原则应用限制的“动机悖论”反驳。“动机悖论”的存在实际上是因为罗尔斯接受了休谟的正义环境论(罗尔斯,2009年,第98页),从而无法承认后面所谈到的充分正义感。休谟正义环境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的仁爱不足。仁爱不足的一个含义是,无论你的原则多么有道理,但由于这个行为要求我的牺牲过大,所以我无法自愿地遵守。(参见葛四友,2012年c,第96页;2013年,第80页)换言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社会是不可能会有充分的正义感的。但罗尔斯后来对良序社会尤其是对于正义感的强调,让我们容易忽略这一点。而一旦意识到罗尔斯实际上接受了仁爱不足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罗尔斯关于基本结构的论证。按照这种解释,基本结构只能是强制性的结构。尽管人们没有足够的动机自觉遵守正义原则,但可以通过强制使得所有人都遵守正义原则,因为不遵守会有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不需要有充分的正义感就可以遵守正义原则。但对于个人选择行为,则只能给予个人足够的激励才能让他们努力工作。所以,这种应用之中是没有动机不一致的。同样,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帕累托论证。如果大家都只有有限的仁爱,那么靠强制我们只能获得起点平等状态D1(5,5),而不是D3(7,7)。如果人们只有有限的仁爱,那么利用收入不平等作为激励就可以获得D2(6,9)。而相对于D1而言,D2是帕累托改进的。因此,尽管柯恩的“动机悖论”反驳对于理想意义上的正义有影响,但考虑到现实的人性状况,罗尔斯对差别原则的应用限制仍然可以成立。
6.尽管以上分析可以回应柯恩的批判,但差别原则本身的困境要更为严重。由于柯恩如同罗尔斯一样误解了帕累托标准,所以他没有挖掘出差别原则的根本困境。为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帕累托标准的意义。帕累托标准由于经济学的影响日益增长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罗尔斯尤其是柯恩都臣服于这种标准。然而,从道德层面上讲,帕累托标准实质上远没有如此重要。帕累托标准的兴盛与近现代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倾向发展有莫大的关系。经济学实证主义使得经济学与道德哲学渐行渐远,其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经济学家否定了效用在人际间比较的可能性。(同上,2006年a,第16页)由此,经济的效率评估就只剩下了帕累托标准:当一种状态相比于另一种状态来说,其中没有任何人变坏,至少有人变好,那么这就是帕累托改进。然而,作为经济学中效率代名词的帕累托标准本身并没有什么道德力度:它要么是无用的,要么必须借助其他更为根本的道德标准。(同上,2012年a,第271-273页)上文已经阐述过,如果没有一个起点,那么帕累托标准几乎适用于所有状态,因而是无用的。帕累托标准之所以在罗尔斯与柯恩那里如此重要,正是因为他们都假定了平等是一个正当的起点。
然而,以状态的平等作为起点恰恰在根本意义上否定了帕累托标准的适用环境,因为它承认了效用的人际间可比性。由此,依赖帕累托标准的差别原则就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效用在人际间是不可比的,那么起点平等就是没有意义的。由此帕累托标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有太多的分配状态都能满足帕累托标准,即使有些状态(如上述残暴皇帝的情形)在直觉上极其令人反感。这样一来,差别原则就根本无法成立。另一方面,如果效用在人际间是可比的,从而我们能够具有起点的平等状态,那么帕累托标准就面临着困境:要么平等具有绝对的价值,则从D1(5,5)向D4(6.999,7)的帕累托改善都是不许可的;要么平等只具有相对的价值,则从D1(5,5)转向D5(6,9)的帕累托改善是可以的,即符合上面所讲的平等-差别原则。但同时,从D1(5,5)转向D6(4,15)也应该是可以的。因此,无论我们赋予平等什么价值,差别原则都是不能成立的。
不仅如此,由于假定了人际间的可比性,柯恩与罗尔斯在应用帕累托标准时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帕累托标准中,“不能变坏”指的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变得比前一种状态更坏。但无论是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应用中,还是在柯恩的批判中,他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最不利者在不同的体系中很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因此,罗尔斯所说的帕累托改善不是在真正的帕累托标准的意义上讲的。从而,与柯恩所理解的不一样,不是动机悖论的问题,而恰恰是帕累托标准的问题,才导致无论平等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差别原则都不能成立。
四、消除动机悖论的出路:均等主义还是后果主义?
1.在面对差别原则的根本困境时,我们有两个选择:或者坚持均等主义,即平等的绝对权重观,或者走向后果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讲,柯恩想当然地认可了前一个选项:分配正义就在于完全平等;一旦背离这种平等,不管原因是什么,都是不正义的。(cf.p.155)然而,柯恩对此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来自罗尔斯也接受的道德任意性论证。但他也明白,道德任意性论证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解读相当于前面所说的“不应得”解读,实际上就是运气均等主义解读。尽管差别原则预设了运气均等主义,但实际上从道德任意性论证是得不出运气均等主义的,因为人们是平等的还是不平等的在道德上是任意的。对道德任意性论证的另一种解读是“非应得”解读。据此,偶然性因素既不是我们应得的,也不是我们不应得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种利益与负担,需要其他的理据。(cf.p.166)因此,尽管差别原则确实如柯恩所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但只要人们不支持差别原则,那么也就不需要预设运气均等主义。
不仅如此,由于柯恩坚持充分的正义感动机以及共同体的人际间检验,他的平等观面临着巨大的麻烦。假设一个社会里由于信息或组织等其他原因,只能做到效用的两种分配:(5,5)与(5,9)。根据柯恩的说法,从第二种状态转变到第一种状态是正义的。这里,我们可以采用柯恩自己所提出来的共同体内的人际间检验,来看其平等观是否行得通。如果社会里的所有人(包括最不利者)具有充分的仁爱(充分的正义感),且低效用者知道高效用者尽了一切努力来改善他的效用,那么他如何还能够对高效用者说:“尽管你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因为我的效用只能达到5,而你的效用有9,所以你应该变得跟我一样差”?恐怕不能。为了表述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可以想象极富亲情的一家人,如果其中有一个成员因为先天疾病而无法得到高效用,他会因此要求全家人跟他过得一样差吗?恐怕也不会。如果低效用者在这种情况下真的要求高效用者过得和他一样差,那么很可能只是因为其不把自己当做共同体中的一员,或者出于嫉妒或恶毒等心理。
如果情况是后者,则问题在于:为什么出于嫉妒或恶毒的要求也是正义的?如果正义真的这样要求的话,那么正义就是一种很低端的德性,是在人们具有的仁爱不足的情况下才需要的。但前面柯恩对差别原则的批判表明,实现平等要求能干者具有充分的正义感,具有很强的仁爱精神。这样一来,科恩的平等观就具有了一种动机悖论:平等本身是因为人们的仁爱不足才需要的,但这种平等的实现又要求富裕者或能干者具有充分的正义感来实行它,而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仁爱,也就不会有充分的正义感。由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困境:要么人们的仁爱有限,因而平等是需要的,但这种平等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要么人们有充分的仁爱,因而平等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时平等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换言之,平等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不需要的。
2.一旦我们放弃这种绝对的平等观,那么正如柯恩也承认的,一种自然的选择就是后果主义。(cf.p.167)不仅如此,柯恩的平等观与后果主义之间的差别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一,两者均强调结果,只是前者强调效用的平等分配,而后者强调效用的最大化。第二,前者接受效用的人际间可比性,而后者也要求这一点。第三,前者否定前制度的道德应得或资格,而后者也需要如此。
第四,柯恩的运气均等主义如同后果主义一样否定了自我所有权,由此两者都面临着同样的反驳:忽视个人分立性(参见诺齐克,第217、231页)。运气均等主义否定自我所有权是为了使所有人过得一样好,而后果主义否定自我所有权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让所有人过得尽可能好。面对“忽视个人分立性”的反驳,柯恩可以作两种回应:一种回应是承认否定自我所有权确实违背了个人分立性,但强调个人分立性在资源的分配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过得一样好。就此而言,后果主义对“忽视个人分立性”的反驳可以做同样的回应:后果主义确实违背了个人分立性,但个人分立性在资源的分配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过得尽可能地好。柯恩的另一种回应是:否定自我所有权并没有真正违背个人分立性,因为只要我们按照平等的正义规则行事,我们就对每个人表示了尊重,由此也尊重了个人分立性。就此而言,后果主义依然可以做同样的回应:否定自我所有权并没有违背个人分立性,因为只要我们按照后果主义的正义规则行事,我们就对每个人表示了尊重,由此也尊重了个人分立性。可见,在面对“忽视个人分立性”的反驳时,无论柯恩如何回应,其运气均等主义的分配正义都并不比后果主义的分配正义做得更好。
3.尽管如此,后果主义还需要回应一个有力的反驳:平等观具有强大的直观合理性。柯恩认为自中世纪之后,人们就接受了这样一个原则: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或过错,不应该过得比其他人差。(cf.p.156)换言之,人们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或过错,应该过得一样好。但这个反驳存在几个问题:首先,这种直觉很可能只有平等主义者才具有;其次,即使人们都有这种直觉,但柯恩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直觉不是因为平等的工具性价值,而是因为平等本身的内在价值;第三,即使人们的直觉真的是平等具有内在价值,但这种平等观具有“水平下降”的推论,即:假如分配状态为(4,7),那么如果不能把前者提升到7,就应该把后者降为4,而反对这种“水平下降”推论的道德直觉似乎更强烈。
后果主义承认平等具有直觉吸引力,但认为这种吸引力来源于其工具性价值而不是内在价值。由此,它既能解释平等所具有的直觉吸引力,又能避免平等观所包含的反直觉的“水平下降”的推论。
首先,后果主义能够解释我们要求资源大致平等分配的直觉。假设有这样一个社会,人们的分配只能是两选一,一种是A(5,7),另一种是B(4,9)。如果把这些数字看成是钱或资源的代表,那么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平等分配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也完全可以用后果主义加以解释。当然,这种解释取决于我们具有的边际效用递减倾向。过得越差的人,一元钱具有的效用越大。同样的十万元钱,对于亿万富翁来说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赤贫的人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马尔根所做的基本需要与目标的区分对解释这一点很有帮助:“基本需要”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生理上的生活必需品(衣食住行),而“目标”则是指我们选择的追求、计划与事业等,它们赋予我们生活以主要意义。(cf.Mulgan,p.173)这一区分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需要领域的事情容易观测到,而目标领域的事情则很难观测到;另一个含义是需要领域的事情我们很难有调适空间,过得不好就是不好,而目标领域的事情则有很大的调适空间。关键在于一旦我们满足了基本需要,我们能过的生活就可以有很多变化。这两个含义表明,越是处于低端,尤其是基本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效用的损失就越大,且个人的自主能动性作用不大;而富人有很多资源,只要他们愿意调适,那么一定程度的再分配对其福利是不会造成多大损失的。拉兹甚至认为:“相当富裕的人可以给他人很多钱,而不对他们自己的福利带来任何损失。”(Raz,p.28)这也就是说,后果主义会支持非常强烈的资源平等分配方案。
其次,一旦我们把数字不再看成钱或资源的代表,而是看成效用的代表,直觉就不再支持平等观,而是支持后果主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是我们的日常行为。人们大概都不会反对在公交车上应该给老、幼、病、残、孕让座。这种让座行为是比较孤立的行为,不会在效用上产生太多的因果链条,容易判断,因此对其效用的考虑可以比较直接简单。后果主义很容易解释让座这种行为,这就是:让座给让座者造成的效用代价不是很大,然而,得到座位的老、幼、病、残、孕者获得的效用却是很大的。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关注老、幼、病、残、孕者的总福利是不是一定要比让座者低。而如果是平等主义者,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事实上,有些时候老、幼、病、残、孕者的效用比让座者的总体效用高得多,但我们依然不会改变这种直觉。第二个方面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假定一个人有两个人生阶段,可以有两种选择,分别是A(5,5)与B(4,9)。如果数字代表的是效用,我们一般会认为,个人会选择B。由于“忽视个人分立性”的反驳在此是无效的,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把个人的选择推广到社会。
4.需要提醒的是:在此不要把利他主义与充分的正义感相混淆。有充分正义感者会按正义行事,而利他主义总是想有益于他人,而不管这样做的整体效用如何。(参见葛四友,2013年,第79页)利他主义者与利己主义者一样,都会在某些情境下陷入囚徒困境。比如,一对夫妇做间谍被抓了,这两个人都想让对方好,而不考虑自己,结果就会面临这样的处境:如果两个人都不招供,那么两个人都坐4年牢;如果一个人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么自己坐12年牢,对方无罪释放;如果两个人都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那么都坐8年牢。如果夫妇俩都是利他主义者,他们的推理过程将是这样:要么对方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时我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方会从12年变成8年;要么对方没有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时我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方会从4年变成无罪释放;无论对方是否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对对方都是好的;因此,我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结果最后两个人都坐8年牢,而这显然是一个对双方都不好的结果,其原因就在于双方都只想着对方,没有想着自己。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模拟思考,则既解决了利己主义者的麻烦,同时也解决了利他主义者的麻烦;它只要求我们按照正义的方式行动,这样动机与结果之间的悖论就能得到消解。
5.后果主义除了能够解释收入和资源分配方面的平等主义之外,还能够解释现代的机遇平等观。首先,它能解释自由至上主义者所强调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自由权,即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机遇平等。这种平等不考虑社会偶然性与自然偶然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人尽其才的第一阶段:人有机会实践其能力。这显然比阻止人们实现其能力能更好地增加效用。其次,它能解释公平的机会平等观。这种平等观主要是要消解社会的偶然性,尽力保证有类似抱负和努力的人,在天赋差不多的情况下会有大致差不多的前景。这可以看作人尽其才的第二阶段:人们能够有机会发展其潜能,同时有机会施展其发展出来的才能。在智力资源稀缺的今天,这种平等显然是有利于效用的增加的。
6.当然,后果主义无法解释近现代诸多义务论者所看重的运气均等主义,因为这种观点是某种形式的结果平等:只要人们有类似的抱负和类似的努力,他们就应该具有大致相当的生活前景。但是,这种彻底的结果平等观一方面具有很多反直觉的推论,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无法做到融贯。(cf.Anderson,pp.308-311;参见葛四友,2006年b,第85-86页;cf.Hurley,pp.69-71)本节开始的分析也说明它有着深刻的动机困境。因此,后果主义无法解释它也许是一个优点,至少不是缺点。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是目前影响最大的一种分配理论,它代表了从义务论的角度对自由与平等的综合。然而,柯恩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动机悖论、特别是差别原则在应用帕累托标准时的悖论的揭示,表明这种义务论式的综合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不过,与柯恩的意图相反,消除这种悖论的出路并不在于坚持运气均等主义,而在于转向后果主义:后果主义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方面关注个人在绝对意义上是否过得好,另一方面又关注个人在相对意义上是否过得好。罗尔斯的根本意图正是试图从义务论的角度对上述两个方面做一个妥协式的综合,然而,后果主义不需要做出任何妥协,就可以很自然地解释这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