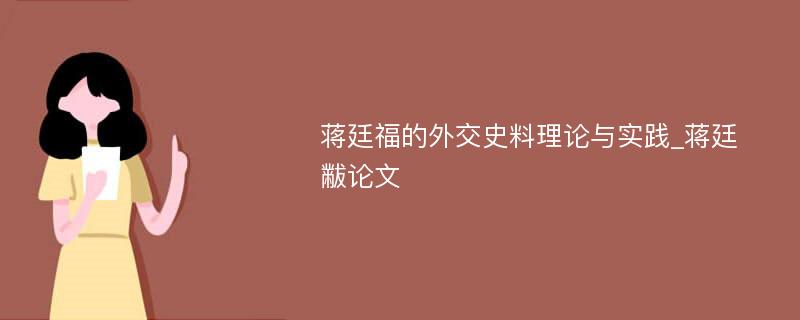
蒋廷黻外交史料学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外交论文,学理论论文,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08)01-0174-04
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宝庆)人。早年留学美国,后归国任教于南开和清华,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教学与研究。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致力于外交史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被认为是“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1]前后十余年浸润于外交文献工作,在科学外交史料学理论指导下,他构建了一套鲜明的研究范式。以往学术界对其外交思想多有阐发,而对其外交史料理论与实践,则着墨不多,故本文不揣浅陋,作一初探。
一、通过史料评论来阐述其史料观
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外交档案层出不穷,卷帙浩繁,价值巨大。特别是以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代表的官纂史料的面世,为外交史学界带来了“学术革命”。作为长期从事基础文献工作的外交史专家,蒋廷黻以极大的热情,对这些新材料分析评论,拣优裁汰,并通过史料评论的特殊方式,阐述自己的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以及其与外交史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将之切实转化为推动外交史研究和编撰的基础性力量。
(一)“信、新、要、通”——史料评价及编纂标准
蒋廷黻对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基本都有所寓目,对其中重要者都有独到精当的点评。他认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当时出版的外交史料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录;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就其可信度而言,“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2]此处的论述已触及史料评价及编纂的两条标准——“新、信”,原料属于新材料,研究者最应重视;而无论是原料还是次料,不能因为其“新”或二手,就简单肯定或否定之,应甄别裁选,确定其“信”。
接着蒋廷黻在评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和《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类史料时,又对以上阐释进行了发挥引申,并确定了四字标准。蒋认为“史的编撰大概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历史原料的编撰。”那么“就外交史论,国与国交换的一切的文件,一个政府计议外交的记录,外交部与其驻外代表往来的文件,外交部给国会或国王的报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记,皆是外交史的原料。”[3]上述前两类史书就是这种原料的编撰。蒋氏认为这个体裁有其特殊条件,“第一须求其信”,何能使其信呢?他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出处,俾读者能于较短时间内覆按原文。(二)每件史料必须注明年月日。外交的文件大半均有发给的年月日及接收的年月日。至于电报,尤其国际关系紧张时候的电报,还有收发的时分。这些均不可缺,缺了则文件就丧失其作用了。(三)每件史料必须保存其原来面目。无意的校对错误应竭力避免;有意的删改简直是史界的罪恶。”[4]据此考察上述二书,于此条上遗憾颇多,《中日史料》的上谕、密寄及电报均只注明“上谕档”、“洋务档”和“电报档”,而且此三档的来源及状况无一字相告。《清季史料》作为私人修史,对其中史料来源一字不提,更无取信于人了。同时二书在时间的注释上“幼稚万分”,年月日记载的不完全及错讹者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中外照会全无年月日。因此二书很难符合“信”的标准。[5]
“第二须求其新。所谓新者,即文件是新的,是未出版过的;读者可从其得新知识。倘若前人所出版的未达到上文所讲的求信的条件,则可重刊。倘若前人出版的太零散了,而新刊的是一种史料全集,则亦不妨与前人有几分之几的重复。”对于“新”,蒋认为上述二书做得比“信”的条件要高些,《清季史料》全书的新材料约占百分之六十,《中日史料》新材料的成分还在《清季史料》之上。[6]蒋对此一标准尤其关注,他就非常激赏道光朝《始末》所提供的新材料和新知识;同时在评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时,认为“有许多新知识的发现。其有二分之一是曾未出版过的,且皆是必不可缺的史料。”[7]评论第六卷时,“我们不能问其完备与否,我们只能问其有无新材料的贡献。”“编者能于材料缺少的情形之下,替我们找着这么多有价值的新材料,这真是有功于学术。”[8]对此书其他几卷及其他史料时,都以此为基本原则来审视,可见其对“新”的重视。
“第三须求其要。所谓要者,即文件有关紧要。”蒋氏认为此条颇难实用与把握,由于编撰主体及时代移易,对“要”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但他肯定“有些文件绝无出版的价值。如公使的任书及辞书,都是应酬之语,无须出版。”而“反过来说,有些文件无论何人都认为有绝等的价值,如编辑者不能搜收这种材料,则其出版品就减色了。”如近代外交史中李鸿章出使俄国的文件,庚子年增祺与俄国所订的草约等,就是代表。[9]蒋氏认为《清史稿·邦交志》中的许多材料都不符合“要”的条件,对于其中“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的史料“轻重颠倒”的弊端提出严厉的批评。[10]
最后蒋氏在论述“史料的历史”时阐述了“通”的条件。他认为史的撰写的第四类是“日本人所谓史料的历史,西人所谓Documentary History。《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属于这类的。”他将此类撰著譬喻为一种“完成的建筑物”,但与普通史著不同,墙及板柱不加任何粉饰,其目的“务使观者欣赏一方面原料之美实,一方面全建筑之有节调。”因此此类史书,“编撰者不但要作到上文所谓信新要三个条件,且须作到通的条件。所谓通者,即原委要清楚,贯连要紧接,章节的长短须有权衡。事实不可漏,亦不可滥。倘信新要三个条件未做到,则原料必不美实;倘通的条件不作到,则全建筑必无节调。”蒋氏认为《中国与日本》一书线索分明,叙事有条理,于“通”上做得不错,唯有其中几个关键问题的忽略,致读者仍不能明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11]。
以上四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了蒋廷黻史料评论的四条核心标准,同时也是外交史料编撰者必须遵循的四条基本原则,蒋氏自己在编纂外交史料时就是如此而为的。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两书就是主要成果。
(二)史料与外交史书的编撰
蒋廷黻将史的编撰分为四类,除上述与史料直接相关的两类外,“专题研究的报告”和“史之正体”是另外两类。史料、专题研究报告及正体史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蒋氏譬喻为“土、木、金”“砖、柱、板”与“完成的建筑物”的关系。[12]外交史也是如此。
虽然蒋廷黻对之前外交史著中的史料运用“西化”倾向进行了批驳,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武断地认定以后的外交史著只能以中文资料为中心的观点,蒋氏在对中西史料联动考察的基础上,为当时外交史学界的学术现状指明了两个努力的方向。他认为,“甲午以前,我们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已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工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完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如何往往无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13]若干年后,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仍然坚持这种学术观点,认为“在一八八四年以前,只需仔细研究中国文书资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后,则需中外资料并重。”并主张以前学者撰写的外交史著中“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写”,这是因为“早期的作者写到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时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资料而不涉猎中国的资料。”[14]正是在以上认识的指导下,蒋编写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则中外兼收。”后由于时间及精力有限的缘故,只出版了上中两卷,下卷没有完成。
以上是蒋氏对晚清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辨析,那么对民国外交史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如何呢?在全面了解民国外交史料的出版情况后,他认为,“时至民国,我们外交史的学术状况就大不同了。”这种不同在史料上的表现是,“基本文件已经出版者很少,且极零散。作外交部长如王宠惠、陆征祥、孙宝琦、顾维钧、王正廷、伍廷芳、伍朝枢、胡惟德、颜惠庆诸人,或未发表文集,或未到发表文章的时代。我方如此,日本方面亦大致如此。”面对如此史料缺乏的状况,蒋主张先做好史料层面的工作,不能一味追求外交史的定论和定本,“民国的外交史事实上现在不能有定本,不问著者是谁。所可能者仅史料的探讨。”在史料基础上作些专题方面的研究报告,这样“有了数十人继续数十年的努力,各人都有些贡献,然后我们才能有科学的完备的民国外交史。”[15]
由以上论述可知,蒋对史料与外交史的研究和撰写的关系的阐述,非常具体而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二、近代史料搜集法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时,就系统地接受了近代史料学的科学训练,在他回国任教之后就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外交史料。同时,他认为历史研究首要在资料,故其又从史料编撰入手,来切入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拓性研究。
由于他受过系统的史料学训练,因此,他的史料搜集工作更多的带有西方学者治学的特点。这种近代意义上的史料搜集工作,在当时中国外交史学界,还是开风气之先的。它具有选点准确、及时跟踪、亲历亲为的特点,将传统人力与现代影像技术结合,因此非常有效和科学。
早在清华任教之初,正逢故宫博物院着手影印三朝《始末》,此书的巨大价值也引起了蒋的兴趣,并立即跟进,于1929年秋至1931年秋,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到故宫博物院抄录军机处档案。[16]同时他又留意当时作废纸卖的一些清朝老衙门的档案,他为清华图书馆购买了成吨计的关于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17]。另外,还注意搜寻晚清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文书信札,如曾国藩、李鸿章、文祥、曾纪泽、郭嵩焘等人。此类是先将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史料缺陷和薄弱点选准,然后有的放矢去搜寻,经常有意外收获。[18]
重视中国资料,同样不忽略外部资料,主张“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为了能搜集到真正有价值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蒋氏还亲力亲为,利用清华的休假制度,到苏联和欧洲诸国搜集档案。
1934年7月下旬,蒋动身前往苏联。在未到苏联之前,他按照苏联所定的章程写信给莫斯科文化交换局,请求参观他们的档案库,同时将想要查档的资料分成四组:“咸丰年间中俄黑龙江北岸及乌苏里江东岸之交涉文件;咸丰末年伊格那提业夫与肃顺交涉之文件;同治末年与光绪初年间关于伊犁问题之文件;咸丰八年关于天津条约之文件。”[19]但蒋氏的这份请求和清单却命运多舛,在苏联文化交换局、外交部远东司及档案保管处三机构间往复推诿,几经交涉,始于双十节后看到其中一种,“但都是第四种的文件,且均系英法美三国之来往函件,无一件为重要的。”就是蒋的随手笔记,也以规章制度为由暂扣。[20]蒋的第一站可谓出师不利。到了德国的柏林,情况就不同了。柏林大的中央档案馆主要有普鲁士档案馆和帝国档案馆两家,蒋氏主要查阅一八九五年以前中德关系的档案。先到普鲁士档案馆,正好机遇不巧,主管人员告诉蒋,此类档案两三年以前是可以公开的,但现在不公开了。所以蒋氏只能阅看一些通商部分的档案,其他档案也就无缘一见了。[21]到了英国,蒋的收获就更大了,他要求查看的外交档案,除一八八六年以后的档案按照制度不予公开外,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档案则完全公开。且研究公开的档案是极其方便的,笔记、抄录或照相均可,蒋就拣选紧要的档案,请人影照,共得有一万六千余页。其中除中英交涉的史料外,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内政的好材料。[22]
综观蒋廷黻的史料工作,其最大特点就是“中西兼顾”、内外并重。这个特点是与其治学特色一脉相承的。蒋自认为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决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23]重视外部资料的表现之一就是上述的亲自搜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他还注意搜集有价值的“次料”,这样的“次料”以日、俄为重,这与其重视日、俄史有关。“原来日本外交最守秘密;外务省所发表的文件亦极少。研究日本外交的人与其向日本政府出版品中找材料,不如多注意于日本私人的文集和传记。[24]因此蒋氏对一些日本要人的文书信札非常留意。而由于近代帝俄对中国西北疯狂经略,因此蒋氏也将不少精力投向俄国,对俄人的回忆录、著作及史学家披露的重要信息等予以关注。如《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附录之一即为“资料评述”,共提及西文史料十二部,其中大多是俄文史料,而蒋氏在文中引用的俄人著作远不止于此。又如利用俄国史学家罗曼诺夫(Romanov)的著作《帝俄与满洲》一书,考察俄国与满洲的关系。[25]再如其利用苏俄外交官伯沙达甫斯奇(Bessedovsky)在英国出版的回忆录《一个苏俄外交官的披露》一书中的史料撰写了《鲍罗廷时代之苏俄远东政策》一文,蒋氏在中方史料阙如的情况下,根据俄国史料,勾勒出民国十五、十六年苏俄鲍罗廷时代之远东政策的大致轮廓。[26]
综上所述,蒋廷黻从史料评论入手,辅以近代史料搜集法,不仅从理论上阐发了外交史料评价及编撰的四字标准,同时在实践上编成了《补遗》及《辑要》两部史料专著,卷帙浩大,编审精详,成为近代外交文献汇编中的代表作,为后来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奠定了初基。
收稿日期:2006-10-12
标签:蒋廷黻论文;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论文; 资料搜集论文; 学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