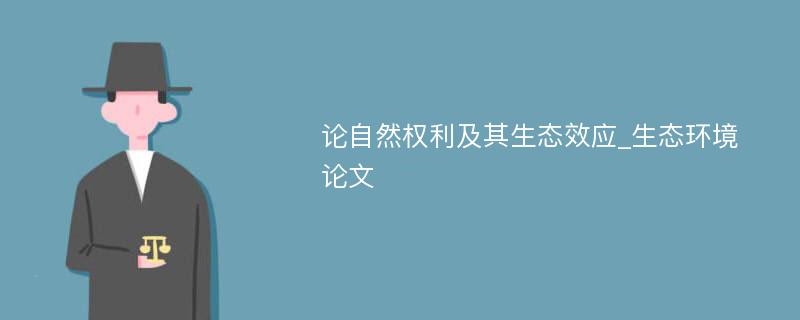
论自然权利及其生态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权利论文,生态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环境伦理上,是否承认自然权利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水岭。因为默迪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已突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未必就要求只有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也不拒绝相信自然之物的内在价值。”(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第14页,章建刚译)但他却不承认自然权利的存在。“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物种有平等权利,那么就没有任何物种应该在遗传学方面受到控制,或者是为了其它物种的福利而被杀死。”(同上,第13页)而非人类中心主义不仅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同时提出自然权利的主张。这一主张承认人之外的自然物都有与人绝对平等的权利。它涵盖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等学说,而这些学说的不同仅在于把权利赋予自然存在物的不同层面。动物权利论者认为我们应当把“平等地关心所有当事人的利益”这一伦理原则扩展到动物身上去(P.辛格持这种观点);“理性——不是情感,就迫使我们承认,这些动物也拥有同等的天赋价值。而且由于这一点,它们也有获得尊重的平等权利。”(T.雷根:“关于动物权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第30页,杨通进译)生物中心主义主张一切生命有与人绝对平等的权利,“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或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深生态学家阿兰·纳斯持这种观点,引自R.F.纳什著,杨通进译:《大自然的权利》,第177页,青岛出版社,1999)生态整体主义认为“所有事物和自然系统都拥有它们自己的目的或目标,因而都拥有内在价值和存在下去的权利。”(同上,第185页)
中国学者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学术前沿进行了积极跟踪与讨论,余谋昌等人译介了W.T.布拉克斯顿的《生态学与伦理学》,并在“人与自然关系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一文(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中介绍与阐述了“人与自然协调的价值取向”、“生态意识”、“自然界的权利”、“生态伦理学的道德原则”等环境伦理学的基本思想。由此环境伦理意识在我国学术界开始产生影响。1999年杨通进翻译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德里克·纳什(R.F.Nash)所著的《大自然的权利》。该书详细阐述了西方自然权利论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各种自然权利论的基本主张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分歧,并把环境伦理思想解读成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最新发展和逻辑延伸。自然权利论成为环境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我国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是在环境科学界、伦理学界和生态哲学界对人与自然关系定位的争论,从而逐渐形成了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并不断促使人们对自然的理念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转变,自然权利论被我国部分学者所接受。
邱仁宗在“脱离人类中心论”一文(载《伦理学》,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3期)中指出,“对动物来说,自然界的东西只分两类: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动物从不,也永远不会承认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这是“动物中心论”。而如果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采取同样的态度,认为自然本身没有内在价值,它只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资源,自然天经地义地要为人类所用,则就是一种与“动物中心论”没有多大区别的人类中心论。但当人类认识到“人类不过是自然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我们与其他物种都是自然的儿女”,正是自然孕育了人类并无时无刻不在支持着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时,人类就应该脱离人类中心论,承认自然母亲有自己的内在价值和权利,人类对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只知道“向大自然母亲无限地索取、榨取、剥削,从不想为她做些什么,好比一个不肖子孙”。
叶平在“非人类的生态权利”(《道德与文明》,2000年,第1期)中提出人类应尊重生物生存、自主、生态安全的权利,并把这视为人类生态文明的新进展。
王晓华在“建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大伦理学”一文(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2期)中指出伦理学有两次根本性转折:第一次是“从敬畏神灵到敬畏人类”,第二次是“从敬畏人类到敬畏万物”。并在最后指出:“在未来的时代里,人们将意识到敬畏万物是人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经过一条漫长的文明之路后,人类将恢复敬畏万物这个古老的信仰,这不是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彻底的拯救之路,由此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
二
尽管自然权利观念被我国部分学者所接受,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但还有待深入研究,主要应探讨这样的问题:自然拥有权利意味着什么?自然权利的源泉何在?究竟为什么要有自然权利?自然拥有怎样的权利?
A.J.M米尔恩指出:“权利概念的要旨是资格(entitlement)。”(A.J.M米尔恩著,王先恒等译:《人权哲学》,第165页,东方出版社,1991)比如儿童有资格接受父母的关照与保护,也就是说,他有这样的权利。所以我们说自然拥有权利也就意味着自然被赋予了某种资格。比如当人们说要人道地对待动物或者说要尊重生命时,就是说它们有资格,也即有权利得到这种尊重。
那么是什么赋予了自然这种资格呢?也就是说自然权利的源泉何在?米尔恩谈到能赋予资格的是“规则和原则。因为,凡对某物有权利时,必有规则和原则存在”,比如年满18岁将取得公民权就是一个规则。而包含了规则和原则的是法律、习俗和道德。作为个人权利源泉的这些法律、习俗和道德属于权利主体组成的共同体。“每个共同体都由一群依据一定关系生活在一起的人组成,这些关系使每个人都知道他应给予其他成员什么以及他们应给予他什么。作为一个成员,他的义务就是他应该给予别人的东西,他的权利则是别人应给予他的东西。”(同上,第191页)环境伦理学正是以建立人与整个生态系统及其他生态子系统和谐相处关系为宗旨,以维护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利益为原则,把道德纳入人与自然的关系考虑之中,使道德生态化,即对自然界的道德义务逐渐成为道德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自然界遭受迫害时,人的良心将受到谴责。从而使人与自然构成一种权利的主体际关系。
“没有成员就不可能有共同体”,而其成员要拥有权利,没有权利的维护也不可能有共同体。拥有权利是任何形式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要素。所以,如果要有任何人类社会生活的话,就必须有权利。(同上,第217页)这是米尔恩在回答究竟为什么要有权利时所作的阐释。我们认为这对整个生态共同体同样也是适用的。“没有任何逻辑的或法律的理由能给伦理共同体的范围划定边界。”(R.F.纳什著,杨通进译:《大自然的权利》,第154页,青岛出版社,1999)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作为生命共同体的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人类的某种不负责任的活动也会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存在和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危机;同样,生态系统中某个子系统微小的变异都可能对人类进一步生存带来不良甚至灾难性影响。因此,人类应给予其他生命成员和自然存在物以健康存在的资格。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不能不说是人类凭借自身优势剥夺自然这种资格的恶果。最近生活在西非丛林中的一种红猴正式宣告绝种,这是18世纪以来有记载的第一种绝灭的灵长类动物。更让科学家们担忧的是将来愈发高涨的绝种浪潮。研究指出在经历了数百万年进化历程的608种灵长类动物之中,至少有1/5可能会很快绝灭。其他生命形式相对于人类从智力上来说是无法比拟的,但是,是否有只有人类存在的生态系统呢?绝对没有。所以人类需要整个生命共同体和生态系统的存在,而这个共同体的健康存在的基础是存在着维护生态大家庭的各个成员利益的权利,没有对自然权利的承认与维护也不可能有和谐的生命与生态共同体的存在。所以承认自然的权利不仅体现了人类道德观念的突破(生态化),也是人类真正对自身生存负责的富有理性的选择。
自然应该拥有怎样的权利?在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所主张的自然权利中,我们更赞成从生态整体利益出发的各自然系统健康存在下去的权利和自然保持其洁净的权利。因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权利主体间的某些冲突,如某些病毒的存亡危害了其他生命形式的健康生存,也可能造成生命的生存危机,所以人类从维护整个生命体的利益考虑可以对其予以消灭。叶平教授所谈到的生物有生态安全的权利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我们必须同时指出,自然权利所要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必须也与人的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受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的制约。哈贝马斯说:“我们不把自然当做可以用技术来支配的对象,而是把它作为能够(同我们)相互作用的一方。我们不把自然当做开采对象,而试图把它看做(生存)伙伴。……在人们的相互交往尚未摆脱统治之前,自然界的那种仍被束缚着的主观性就不会得到解放。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往,并且每个人都能在别人身上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人类方能把自然界当做另外一个主体来认识,不把自然界当做人类自身之外一种他物,而是把自己作为这个主体的他物来认识。”(哈贝马斯著,李黎、郭官义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45页,学林出版社,1999)
现在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正从正反两方面为自然权利意识的形成提供基础。一方面,科技进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人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提供着更完备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旧的发展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正迫使人们不断认识到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自然保护法律的制定,道德生态化、自然权利观念的建立就是这种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成果。
三
理论依托于实践,同时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自然权利论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生态严重危机背景下的产物。而我们提出自然权利论的目的在于指导人们在改造自然活动中的行为。所以根本的任务在于把自然权利论与人类现实的活动结合起来,在现实的实践中确定其实现的步骤与途径,从而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
树立自然权利观念,走出生态危机,首先是要提高认识,使人们认识到自然权利论对克服生态危机的价值所在。我们认为从自然权利意识出发的对自然的保护运动将与传统的自然保护运动形成鲜明对照,其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比如,对河流的保护,从自然权利论来讲,河流有其保持自身清洁水质的权利,如果人类社会肯定了这种权利,那么任何对其清洁水体污染的行为都侵犯了河流的权利,理应受到“自然权利法案”的制裁,从而对河流任何形式的污染行为加以制止。这样,解决水质污染问题就从最终意义上确定了理论依据。而从传统自然保护理论作为出发点来保护自然,必然受到经济等理论的制约。我们知道,当污染程度很高时,降低污染可能成效显著,但在低污染水平时,再降低1%的污染将可能要付出巨大的物力与财力。那么经济学的效益与成本理论就不会为进一步的治理污染提供理论依据,因为经济要追求效益最大化。而且,人们还会采取补救措施,比如生产药物以治疗人类因污染而出现的疾病。同时,我们还会注意到,这种污染水平受人们认识、经济状况的制约,会处于变动之中,从而使得污染不能根除,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加剧。
一旦接受了自然权利论,那么可持续发展就不仅仅是人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存在着其他物种生存、自然界存在的可持续问题,而且这种可持续性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有机的统一,自然权利的维护将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生物的可持续生存与自然界的可持续存在提供可靠的保障。
所以,我们认为采取以自然权利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保护运动是一种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观念。
从实践上来说,在保护自然的运动中,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主张采用一种逐渐让与的方式把人占有自然的权利归还给自然。主要包括扩大自然保护区,保护生物从濒危物种到一般物种。在防止环境污染方面,实现从有污染到无污染的根本性转变,恢复自然的洁净状态。制定自然权利的相关法律,但法律的制定将不以任何人或集团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整个生命共同体和生态共同体的利益为根据,一旦法律制定下来,任何人与集团都不能脱离法律的约束,任何侵犯自然某种权利的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制裁。如何维护自然的权利呢?比如河流、树木和生态系统不会代表自己起诉,它们的要求如何才能在法律面前得以体现呢?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法律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斯通指出:“可通过援引监护人或受托管理人这个广为人知的法律概念来回答这一问题。婴儿或弱智者的利益就是由合法的监护人来代表的。”(R.F.纳什著,杨通进译:《大自然的权利》,第155页,青岛出版社,1999)
事实上,人类在这方面已开始了行动。现在各国在保护濒危物种和设置自然保护区方面,从道德约束到法律制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国际社会也在积极探索环境保护、防止大气污染的具体措施。固然,人们可以从人类利益、从功利主义去看待这些做法,但从理论上很难解释清楚人们究竟为什么这样去做。我们认为,濒危物种法的制定、自然保护区的设置乃是人们对野生动物、自然生命有其自我生存权利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使人们感到人类之外物种的灭绝并不是使人类窃喜的事情,相反,人类对由于自身活动而造成的物种灭绝、环境退化应感到不安并进行深刻反思和采取行动。比如我国对藏羚羊的保护就已经有法可依,从道德上讲,人们对肆意残杀藏羚羊的行为深恶痛绝,对藏羚羊的生存命运倍加关注,并以具体行动为保护藏羚羊做出贡献。那些远在全国各地的人们为什么要保护藏羚羊呢?如前所述,最为合理的解释是它体现了人们对这种生命生存权利的尊重与维护。我们有理由相信,物种保护的范围将会越来越宽泛,尽管这种物种并不处于濒危状态;自然野生保护区将逐渐扩大,人类为能够给野生生命提供它们自己的生存家园而感到欣慰。
自然权利既有绝对性的一面,又有相对性的一面。我们说它是绝对的,是指一旦社会承认自然权利,那就不能依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能为某些人的利益而忽视它、取消它。但它又具有相对性,权利观念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我们说自然有权利,谈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必然受人与人关系的制约。在社会中,人的权利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则自然权利也必定要界定其范围,并根据具体的情况有所变化。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越出社会的经济结构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2)西方激进的环境伦理学者对自然权利有绝对化的倾向,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家巴尔德克里考特(J.B.Callicott)说:“我愿意杀死一个人而不愿杀死一条蛇。”(同上,第186页)布鲁克林学院的保尔·泰勒(P.W.Taylor)提出:由于人类在历史上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一直是有害的,因而,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人类的完全消失并不是某种道德上的灾难,而是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如果它们会说话的话——会以一种“满心欢喜的心情欢呼雀跃的大好事”(同上,第187页)。这种激进的观点,笔者认为不仅无助于甚至会窒息环境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试想,如果人们连拿走道路上的一块石头、打死一只苍蝇和消灭对人类和其他生物有害的病毒也怕侵犯了自然中某物的权利而不敢做的话,那么这样的自然权利论在现实社会中将有何意义可言呢?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自然权利的取得难道要以人类的灭亡为代价吗?这同样是不道德的。实质上,这仍然是把自然与人类关系对立起来的一种思维模式。
自然是我们人类的家园,动物等一切生命是我们的生存兄弟,在这个小小星球上,人类无权成为自然的主宰,人类的进步也使得在地球上人类与其他生命不再是那种弱肉强食的达尔文式的生存进化方式。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荒野及其生存于其中的生命时,让我们说,你们有自在生存的权利,人类将与你们走向和谐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