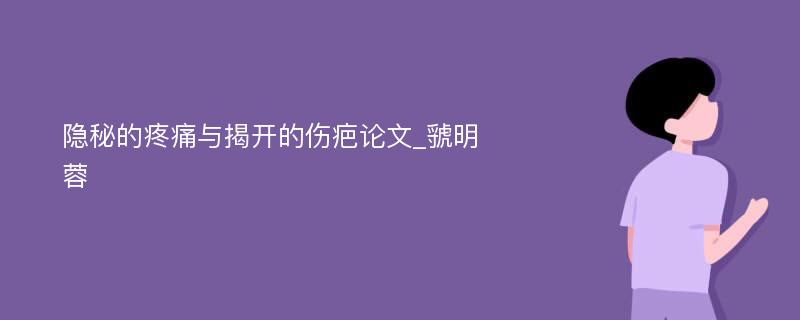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0)
本文为第十五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影评大赛(本科生组)优秀奖获奖作品
摘要:通过对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代表性呈现,影片《相爱相亲》书写了大量女性意识的表达。对于守了一辈子贞节牌坊的阿祖,追寻的不过是男权话语下的身份认同;对于人到中年的慧英,也开始在欲望寻求与婚姻关系中摇摆不定;对于“爱情至上”的薇薇,在爱情与自我中找到了自我意识。本文将从女性意识的三重维度:身份意识、婚姻意识、自我意识阐释该片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相爱相亲》;女性意识;身份;身体欲望;觉醒与挑战
一、身份意识的认同:女性在男权话语中的“他者”位置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的主权强加给对方。如果其中一个类别的人以某种方式取得了特权,有了某种优势,那么这一类别就会压倒另一类别,准备让他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影片《相爱相亲》虽然以女性为主要叙事对象,但影片中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男性才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真正“主角”。也就对应了“自我”与“他者”意识中父权将女性定义为“他者”。
影片表面上看是一出相亲然后相爱的大戏,但在种种温情的表面,是一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关于身份确立的争夺战。最明显的就是阿祖与惠英关于薇薇口中的“外公”到底该和谁合葬的问题。“生为伴侣,死即同穴”是中国众人皆认同的社会伦理。于是“与谁同穴”的争执实际上代表的是两位女性——阿祖与薇薇口中的外婆追寻身份认同的一场争夺战。阿祖作为一个结婚不满一年丈夫就离家的妻子,她留在岳家一辈子,为丈夫的父母养老送终,就像村口那座伫立了半个世纪的贞节牌坊一样,近乎可怕地坚持着,这种坚持下是阿祖对于身份认同强烈的执念。
迁坟事件的争执终于在阿祖的放手下告终,胜利的天平倾向了以外婆为代表的女性一方。阿祖最后的放手实际上是对于身份失落事实的一个被迫醒悟,意识到束缚着自己的不过是一个符号,她发现最后执着的并不是那个男人,而是拥有那个男人所带来的身份认同。这是阿祖的意识觉醒。从情理角度来说,外公这一男性所代表的男性权威在最后被透明化与轻描淡写,变得不那么重要,阿祖的放手也是放过了自己。所以,与其说阿祖守着的是一座棺材,倒不如说守着的是一个身份。而最后的放手,也是阿祖对于身份认同的放手。叙事结尾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一群孩子爬上旧社会中象征着女性身份的贞节牌坊,时代已经变化,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已然发生转变,贞节牌坊变成了一个历史遗留。
二、婚姻意识的困惑:被禁锢的身体欲望
“幸福的家庭主妇”曾成为二战后的美国女性追求和效仿的模板。“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成了当时美国文化中一种为人珍爱、自由生长、恒久存在的核心。” 与之相同的是,这种思想现在也根植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家庭女性必须要三从四德、具有父权制社会规定的女性气质,才是男性褒扬和赞颂的理想女性形象,这类女性被称为“天使型女性”。而另一类家庭女性往往自负好强、能言善辩,在略显软弱的丈夫面前行事果决,被认为是异类,被称为“恶魔型女性”。影片《相爱相亲》中就有这两种典型女性形象的代表。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从表面上来看,阿祖岳曾氏属于“天使型女性”,惠英就属于“恶魔型女性”。当年老尹在部队服役,慧英每个礼拜都去他爸妈家,替他伺候老人。即使在大夏天,慧英也是长衫长裤的装扮。换句话说,在这段关系中,慧英如此奉献的目的不像是由爱驱使,而更像是不甘付出没有回报的执念。惠英正是用了封建传统“伦理纲常”的那套规则对自我加以约束,或者说慧英最终是带着一具隐形的贞节牌坊征服了老尹。结合后半段叙事我们会发现,慧英对于这段婚姻的强势也显现出来她对婚姻的不完全信任,对于与老尹的婚姻,她是困惑的。这种困惑也表现在她对老尹与王太太关系的猜疑上。所以,这场婚姻表面上是由慧英强势主导,实际上却是慧英作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妥协,也饱含了女性对于婚姻意识的迷茫和困惑。
尹岳两人婚姻中的爱展现不多,但是欲望在其中却清晰可见。这场婚姻中的欲望呈现地最彻底的一次来源于惠英的欲望。惠英试图通过种种方式来证明自己在婚姻中的强势地位。但隐去这层,婚姻中最应该出现的“爱情与欲望”却不见踪迹。以致于惠英人到中年,竟然做起了“春梦”,产生了“性欲望”。在这一场戏里惠英躺在病床上,梦见一个男人的身影在烟囱上,男人的脸模糊不清。伴随着意有所指的声音,观众马上就明白了这是一场“春梦”。另一处与此呼应的一场戏是惠英路过一个烟囱,那个男人的脸又出现了。巧合的是,这两场戏都有一个角色的介入——惠英学生的爸爸卢明伟。叙事到了结尾,导演终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个男人的脸原来是年轻时的老尹。这三场戏也就构成了欲望的三种情态——欲望的出现,欲望的消解,欲望的归位。与老尹的婚姻开始地过于约束与克制,这也就注定了在这场婚姻中“身体欲望”是处于最底层的,在经历母亲去世等一系列变故后,惠英身体深埋的欲望才开始苏醒,而恰好在旁边的卢明伟就成为了惠英欲望的投射对象。在这之后惠英都带着一种靠近却又审视的眼光来看待卢明伟,直到终于想起梦中人的脸是老公尹孝平。于是马上抛弃掉犹豫,与卢明伟划清界限——“学校你以后可以不用来了”,婚姻中正常的身体欲望终于归位,惠英的困惑解除,婚姻意识开始觉醒。
三、自我意识的觉醒:放弃依附男性的幻想和希望
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在漫长的父权制下,这种意识是沉睡的、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女性主体成长中的空白,显露了不仅是女性自身,而且也是整个现代史上新文化的结构性缺损。” “波伏娃”认为女性处境的改善的先决条件是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影片为我们呈现了三个年代的女人的状态,在其中,最年轻的薇薇同样身陷自我意识的迷失,却又是觉醒得最早的一个。薇薇与男友阿达的关系以爱情为主导。在这个人物线索中,薇薇作为独立个体的观感被弱化,她在这段关系中早期所表现出的爱情意识远远大于自我意识。
片中第一次展现薇薇的情感生活,是她身为观众坐在台下角落,听男友阿达和他的乐队唱《海阔天空》。镜头一开始对准台上,随后转至台下,随着镜头的变化,观众发现已经被带入了薇薇注视男友的主观视角。这个镜头语言中,男性处于“被看”的状态,而薇薇属于“观看者”。与平常男性是“观看者”的姿态刚好相反。这时薇薇沉迷于爱情中,自我意识还未被发掘,依旧痴迷爱情。而《海阔天空》这首歌也很有意思,后来还多次出现在阿达口中,“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薇薇眼中的亲密恋人已经早早地把自我与爱情分离开来,但薇薇还是把爱情当做全部。
这样一对心思各异的情侣最终的结局当然是分开,随着阿达在舞台上唱起《陌上花开》这首歌,两人的感情也走到了分叉口。“陌上花开,不忍不开,等浪蝶归来”。阿达以女性的视角写了这首歌,“等浪蝶归来”,分明意味着阿达认为女性作为留守者的形象会一直持等待的姿态,在潜意识里他觉得薇薇会等他。但是在分别的时候,薇薇却好像心知肚明般地说,自己不会再等他了。至此,薇薇才从爱情意识的局限里跳脱出来,开始认识到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创作者正是在以女性的观点来审视女人如何在不自知的情况所自愿遭受压制与屈服,试图探讨女性解脱束缚的可能性,借此希望女性反思。这也让人惊讶,在如此温情的外壳下竟然包裹着创作者如此暗流涌动的反抗意识。
参考文献
[1]西蒙娜·波伏娃(法):《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49年,第69页
[2]贝蒂·弗里丹(美):《女性的奥秘》[M].黑龙江:北方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4页
[3]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论文作者:虢明蓉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9月3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8/8
标签:女性论文; 薇薇论文; 意识论文; 欲望论文; 婚姻论文; 身份论文; 牌坊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9月36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