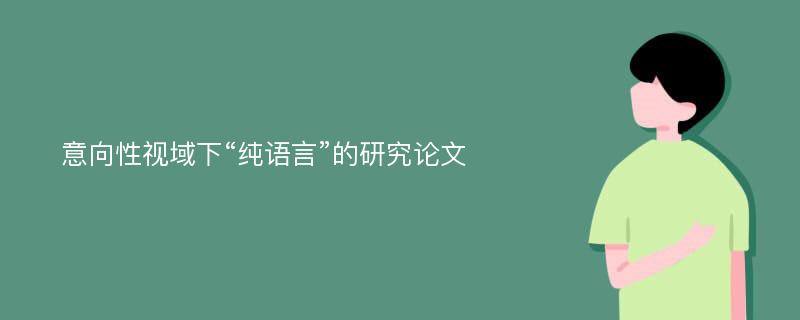
意向性视域下“纯语言”的研究
刘 彬
摘 要: 自本雅明提出“纯语言”术语以来,引发了诸多有关其本质内容的讨论和研究。立足于心智哲学范畴,引用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对于“纯语言”进行剖析和解读,特别是从“网络-背景”理论视角合理解释“纯语言碎片”的相关描述,可以发现意向性与纯语言存在定义和概念上的共通性,“纯语言”与涵盖心智哲学的认知科学研究的关联。从意向性角度深入剖析“纯语言”的趋同性、整体性、历时性以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实质内容,对于语言学的指称问题和翻译学的源语意向性问题可提供新的理论来源和诠释方法。
关键词: 意向性;“纯语言”;趋同性;不可译性;可译性;整体性;历时性
一、“纯语言”的起源、价值与阐释
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一文中将世界上仍在使用的语言称为“纯语言的碎片”。他指出,“意向并不是某种语言可独立表述清楚的,其实现(途径)有赖于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向——纯语言”[1]。可以看出,“纯语言”概念从被提出之时就与“意向性”建立了一定关联。《译者的任务》作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发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许多著名学者对其价值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保罗·德曼(Paul de Man)就盛赞道,“谁不就本雅明《译者的任务》写点什么,那他就一文不值”[2]。而德里达(Derrida)更是窥见了翻译活动的本质:“没有比翻译更为严肃的事情了。我宁愿强调这样的事实,译者直接参与翻译过程,这比任何其他间接、次等的位置都重要。”[3]
(1)观察并记录100例门诊患者与护理人员之间发生纠纷的次数;(2)观察并记录100例门诊患者对导诊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
自“纯语言”概念被提出以来,学界对其本质内容的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抽象”类,如认为其是语言所代表的意义,或是意向总体[4],抑或绝对、永恒的普遍理念[5]。二是“具体”类,如将其描述为神学意义上的本体语言[6],或一种用来把握语言的差异性与互补性的手段。笔者认为,本雅明将每种自然语言描述为形状各异的“碎片”。其中关于“碎片”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叙述即指个体语言间的差异性,具体来说,就是不同个体在将集体意向性转化为个体意向性的过程中围绕概念本身所产生的差异化运动,此处描述与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有异曲同工之妙。就翻译而言,译文和原文同为“纯语言”的碎片,两者相结合才能展露出潜藏在自然语言中的“纯语言”,翻译就是找到相互对应的碎片并将它们结合和关联起来。在本雅明的描述中,纯语言已不再是某种自然语言,而是语言间的相互补充关系,是一种抽象的“总意图”,即意向性。译者解读源语的意向性,正是因为各种语言之间有超越历史的亲缘关系,每种语言自身都具备特有的意向性表达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当源语向译入语转换时,这种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不同语言对于某一类意向性的相似表达方面。
二、塞尔意向性理论研究的概况
1.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研究
美国心智哲学家约翰·塞尔(J.R. Searle)认为意向能力是一切生物,特别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意向性是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一种性质,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7]在塞尔意向性理论体系中,有一些观点与“纯语言”乃至翻译研究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塞尔强调语境在语言表征意向性的构造和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此塞尔还特别构筑出“网络—背景”理论来具体阐述影响过程;因为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是基于言语行为(Speech Act Theory)理论而构建的,所以主要用于分析人物语言(言语行为)的意向性。每个言语行为都包含着以下七个因素:意向状态(intentional state)、满足条件(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意向性网络(intentional network)、前意向性背景(pre-intentional background)、因果关系(causality)、适应指向(direction of fit)和真诚性条件(sincerity condition)。塞尔认为背景是“前意向性的”,也就是说,尽管它不是意向性的一种或多种形式,却是意向性的一个在先条件或一个在先条件的集合[7]。笔者认为“前意向性背景”是指意向性形成之前的前提条件,包括人类个体的性格、心理、行为方面的特征,通过生活经历、工作实践、教育背景和家庭环境等内化的因素,也包括人类个体生活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外部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所汇聚成精神层面的背景能力,共同推动和导致了意向性的产生和发生。这些背景因素虽然不是意向性本身,但可以为人物的意向性提供可能的解读方式和理论解释。一般认为,前意向性背景是指形成和影响人类意向性的个体主观因素。塞尔认为所有意向状态以网络的形式存在,每个意向状态的具体内容受到其他意向状态的牵制,它们各自的网络位置决定其特有的满足条件[8]。在宏观语境下,文学作品中通常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意向状态,这会使得作品结构显得错综复杂,同时也能增强作品的可读性,使故事情节发展耐人寻味;意向状态互相依存,共同组成故事梗概和情节框架。因此,每个意向状态要确定自己在意向性网络中的位置,就必定要借助与其他意向状态的关系来厘定“坐标值”。通常,意向性网络是指人类意向性,特别是居于中心位置的意向状态在趋于完形过程中受到牵制和定型的客观因素。于是,在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观照下,言语行为基本都会包含意向性网络信息语句,提醒译者和读者关注言语行为的诸多细节中隐藏着一定信息,这些信息必须要借助相关的言语行为才能理解和厘清。那些明显不属于同一个言语行为的指称现象就会提醒译者此处涉及其他言语行为,必须要结合其他网络信息才能清楚解释正在分析的意向性整体信息。
2.意向性研究与认知学科研究的联系
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来源于心智哲学,植根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开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之门,这些理论体系实质上都属于广义的认知科学范畴,与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息息相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得知,学术术语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与意象(Image)和象似性(Iconicity)之间也存在着理论联系。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意向性指引意象的生成,且限制译者对语言符号的选择、排列和组合,以此产出因人而异的表达方式。译者的感觉和感受映射外界物体的影像图画,经由译者的大脑机制加工和处理升级为意象,最终通过语符在译作中阐释出来。“象似性”不仅指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外界的客观事物(映像符),以及“摹仿”客观世界实物形态和事物发展过程,而且主要是指语言形式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体验感知和认知方式,语言符号在此过程中是意向性的载体;只有立足于具体的语言符号,才能逐步剖析出附着于上的意向信息。语言符号被当作研究对象,是因为塞尔认为它是意向性的外在物质形式,胡塞尔认为它是意向性的物质外壳,“象似性”理论认为它是对于客观实在世界的仿拟。而在当下认知学科研究之中,也有很多学者谈及了与意向性研究的关联,如魏在江曾定义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境是一种心智现象,它是以身体体验为基础并通过意象图式、范畴、概念等元素而识解的[9]。Van Dijk认为,大多数隐喻,来自具有一定意向的规约性语言表达,使用隐喻是因为我们想表达如此的意义而已[10]。郭春贵、安军认为,隐喻思维具有某种超越实在世界的意向[11]。倘若语词的字面意义表述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语境拥有相对独立性,则隐喻语言更加依赖语境[11]。束定芳论述了语境知识在隐喻理解中的作用,认为隐喻的理解可以被当作辨认说话者发出这句话时的意向,话语理解的过程是通过利用交际双方的共享知识、信仰和假设而完成的[12]。
Priamus系统技术公司把注意力集中在模腔内的传感器上,该公司德国部负责人Erwin Konig认为注塑工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造过程,需要不断调节,所有的调节都会对注塑部件的质量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此外该工艺过程还会受到多变的外部影响,这些外部变化对部件质量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纯语言”的意向性解读
1.意向性与“纯语言”的趋同性
在意向性信息网络中,每一种“意向状态”都有各自特定的位置;在纯语言的整体性中,每一种“真理”都有其形态和对应的解读方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纯语言”的整体性并不是说简单地用单一整齐的白瓷砖把墙体装裱,而应该有如七巧板拼出预设图画一样,每一块彩色瓷砖的构成都具有其独特位置和图案。当人类看到某一特定形态事物时,就知道启用适当的思维逻辑和描述方法建构话语模型,去与具体实物匹配,这种话语模型与实物匹配的精度随“纯语言”的整体性构建程度和个人语言水平发展程度而成正比。
当前我国反腐败过程中存在的法制不协调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立法跟不上国内外反腐的实际客观需要。二是执法困难与执法不严成为反腐法制建设不相协调的又一症结所在,如刑法中的有关反腐法条规定往往偏松偏宽,未能充分发挥出刑法的应有反腐效用。三是一方面反腐立法上难以满足反腐司法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司法领域又未能用足已有的立法资源,长期存在立法难、执法难、督法松等操作性的法制不协调问题。对此,有必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四是国内反腐法律与国际先进的法治反腐理论不相协调。
纯语言由“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两部分组成,“可译性”实质上是指全人类认同的、涉及各个领域的知识体系。相比之下,更重要的是不可译性,即由于地域文化、民族独特性、社会阶层、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导致的超文本差异,需要译者找到“和语言的异质成分达成妥协的权宜之计”[1]。其根本在于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阶段性和历史性,以及“纯语言”自身发展的历时性,而“在译作里,原作本应进入了更高、更纯粹的语言境界……但是它不能在此永生,也远没有达到原作的整体性……其核心原因是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成分”[1]。当译者顺利转换了可译性部分,解读并阐释了不可译部分以后,译者才能以纯语言最仿真的文字形式输出译文。
目前,对于语际异质成分的研究一直在发展,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具体翻译活动的发生与译者生活年代的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带有很深的历史印记。语言表达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带有历史局限性,译者也只能站在历史某一阶段,采用当时主流诗学形式去处理意向性整体中相异部分;而这种处理方法因为语言发展的历史阶段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当前的任何译作,倘若从未来某个时间点回溯,永远只是翻译策略与语言异质成分之间相互妥协而产生的权宜之计;而我们阅读以前某个特定历史时段的译本,也会发现许多表达方式具有意识形态或者阐述方式的烙印而对其产生“陈旧”印象。这也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在不同时代,译者觉得有必要更新译本的原因之一。
2.“纯语言”的构成: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不同语言对于同一意向性的表征,无论是句法结构,还是信息量排布方式都存在差异性,它们都是对于意向性表征方式集合的有益补充。译者在仔细深读并领会源语意向性之后,还要考虑译入语读者的接受性问题,必须摆脱源语句法结构的束缚,采用纯粹译入语陈述方式清楚明晰地表达这种意向性。实际上,这种方式可以认为是译者采用译入语的语言表征形式对于源语意向性进行追求圆满和贴近真实的表述和补充。从这个意义层次上来比对意向性和纯语言,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共通性。
客观派阐释学翻译理论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做到译文与原文在哲学、思想和语言层面的统一[13]。本雅明则认为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某部作品的时候将囚禁在该作品中的纯语言释放出来;他设定翻译标准非常简单抽象,即“无限接近纯语言”。词句的表层形式与真实语义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译者必须紧扣语境,通过逻辑分析,做出正确判断[14]。真正的译作(real translation)就是透过源语的表征形式,深刻认识和形象反映原文创作的意向性;意向性是原文作者必须叙述清晰的原创信息,也是译者不断追求且努力表达清楚以利于读者接受的内容;意向性才是文本的真正精髓,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都只是“意向性”的映射(Projection)。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建构特殊语境,将言语行为施为人的意向性心智指向具体的环境、人员或者事件,将心智转化到语言符号,使语言符号去具体实施这种指向性。
塞尔认为整个意向网络只在非表征性心理能力的背景下才能发挥作用[8]。任何形式的意向性都预设了某些做事情的基本方式以及有关事物运作方式的特定类型和方法,同一作品中的所有意向状态以网络构架相互依存,每个意向状态都要依赖网络中的其他意向状态以及相应前意向性背景才能共同确定其具备真值的满足条件。塞尔认为意向状态并不是以彼此独立(孤立)的状态展示出来的[15],而是由一些信念与其他意向状态所构成的“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先在决定的[15]。这种关于“意向性网络”的观点一般被称为“整体论”(holism)。我们可以把意向状态从整体上视为一个构造精致、相互影响的网络。正如塞尔所指出的,仅仅在语义层面的组合内容是远远不能弄懂“乔治·布什想竞选总统”这个句法结构以及理解其中包含的言语行为[16]。对于这个意向状态的解释,可以罗列出一长串与此相关的,但是数目不定的意向状态清单。虽然清单涉及的内容对于理解原句并非核心关键,也不是“总统”一词所包含的语义,但确实是竞选总统程序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我们把某一意向状态涉及到的知识、信念、观点或者预测都统称为“网络”。
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因为普世价值、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等诸多人类社会基本构成因素的不同,“纯语言”内容也会呈现出历时多样性。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纯语言”的可译性是有限的,异质部分(不可译性)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如果去梳理处于历史某阶段的“意向性”所涉及到的所有意向状态之间的关联性,就会发现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的:其一,数目不定的意向状态存在于意向性网络中,使得网络构成具有更多形态以及复杂层次性。整体上,是以立体动态的结构存在的,提取其中任何一个意向状态,都将牵涉到其他若干意向状态。其二,因为它们相互之中联系紧密,不可分离,相互联动,形成整体板块,尚缺乏有效办法去按照常识区分意向状态的单位数量。其三,当我们整理和罗列某个意向状态可具备的真值条件时,就会发现所要面对和处理的是一个命题集;若干意向状态会共享真值条件和满足条件,命题集之间也会产生重叠部分。
3.“纯语言”的内在联系:整体性
在关于“纯语言”整体性的论述中,本雅明提到,“任意一种语言都无法实现整体意向性,只有将所有语言中意向互补成总体——纯语言,方才可行”[1]。他继续补充道:“当两个(异语)词的意指方式相互抵触时,来自这两种语言的意向和意指对象却促进和产生了语言互补。”[1]塞尔的意向性体系中也有类似的理论阐释,而且对于“纯语言”的解读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从塞尔的定义得知,意向性是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的虚拟物质,是人类心理机制的产物。对比本雅明的“纯语言”定义与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可以看出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特征,都同时提及客观世界中的“语言”与虚拟世界中的“意向(或意图)”之间的关系,只是塞尔更加突出了这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辩证联系。
那天,他打回电话来,说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公司的同事过生日要聚一聚,恰好糖果哭得厉害,我对着电话大声喊:“李伟翔,我天天在家累死累活的,你倒有闲心出去风花雪月……”
可译性是人类意向性中相互认同的部分,比如“对与错”“好与坏”等基本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人类日常生活所涉及物品的分类。因为在人类语言中都共存着有关此类事物的诠释与说明,所以原作中的某些特定意义都会通过可译性而“不言自明”。虽然有些语言现象超越理解能力,使人们难以接受;但是随着语篇的发展与完备,这种特定意义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
本雅明将“纯语言”定义为“意指集合”,任何单一的语言体系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和实现这种意指(intention),而只有通过各种语言互为补充的意指集合才能实现。同时他还提及“译者持续努力发掘作用于译入语的意图效果,以便在译入语中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以及“语言间超越历史的亲缘关系存在于跨语际的总体意向中,而这是使每种语言拥有完整意向体系的基础。”[1] 这与塞尔意向性的相关理论表述存在共通之处,如:塞尔认为语言是意向性的表现形式,意义的界限就是意向性的界限。更加显见的是,本雅明在行文过程中使用的术语“意图(Intention)”“意图效果(Intention Effect)”“意指方式(Intention Modes)”和“意指对象(Intention Object)”都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和渊源[1]。纯语言代表的是居于语言体系核心的整体意图,它实际上是每种语言意指方式的集合。因此,翻译需要明确译入语的意指方式,同时补充源语的意指方式,从而使翻译所关涉到的两种语言显现为“纯语言”的一部分。
4.“纯语言”的沉淀与发展:历时性
可译性关涉到原作与译文共享的双语文化部分,这体现出原作的部分本质;但是相较而言,“不可译性”涉及到的双语文化异质成分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在翻译需要解决的原作系列问题中,那些“不可译”的本质部分显得更加具有难度和深度,所以才导致和形成原作与译作之间相互依存、生死攸关的联系,译作才不会被视为简单复制原作的异语作品,而是延续原作生命的来世之作。
从处理前后渡槽槽身细裂缝情况看,由于未在处理前进行断水减载,2018年槽身碳纤维贴片加固处理完成后,渡槽细裂缝有较大程度的缓解,处理部位裂缝得到抑制。
源语意向性在创作初期就已经基本设定完整,但是作品是否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涉及到隐性的意向性与显性的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作用。如同汉语世界中的文言经典著作,其语言表达模式与当今主流诗学形态差异较大,导致受众面比较有限;但是源语意向性也因为“纯语言的历时性”而带来不同解读方式:有些观点至今奉为圭臬,有的也不免因为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在今日读来已是糟粕。所以本雅明说:“意义不可能独立存在于个体词句中,而总是处于连续关联变化状态中,直到它能作为纯语言从各种意向模式相互协调共融中浮现出来。”[1]随着历史的发展前行,纯语言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持续演变和更替,各个历史时期的文本意向性通过纯语言历时性的解读,最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都是译者权衡各方面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语言生命与作品生命是相互补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人类语言是在不断进化、不断更新和渐进演变的;而作品语言具有历史性、稳定性和暂时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带有很深的历史痕迹。语言生命必定延续,它的变革是由全人类在使用中不断推进的;但是作品语言的生命是由其主旨决定的,也就是纯语言历时性决定的。
作品经历的时间越长久,解读其意向性所需条件就会不断增多,读者和译者会回到原作产生的或者描述的历史时期去探寻解读的条件,为意向性的解读铺就和预设各种主客观语义逻辑链。而在翻译过程中,当源语意向性与译者解读结果耦合时,意义就达成一致,文字也就自然表达清楚,译文读者也方便理解作品内涵。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转化,而且是一种文化的再生[17]。译者通过翻译行为不断扩大纯语言中的可译性,努力确定不可译部分在语际间近似的对应部分并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就对于译者百科知识水平和双语运用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只有在此前提下,译者才能不断在有限篇幅中运用自己的知识水平和语言功底,找到相似或者近似的对等表达方式去有效显露隐藏的意向性。
四、结语
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人类意识的共通性或者类似性,那么翻译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挖掘潜隐于文本中的意向性,并在译入语中使其显化出来,让译文读者可以读懂文本信息;使作品具有其独特性、完整性,并使其语义逻辑顺畅。亲缘性并非同一性,只有通过母语纯粹自然的语言形式,才能无限接近被封闭于源语之中、有时只可意会感知的、不可触及的意向性。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适当语言去再现源语和译入语中的可译性部分;更进一步,译者围绕意向性这个中心,采取合适的表达方式,在翻译过程中,逐步找到历史的权宜之计,阶段性解决“不可译性”问题。源语意向性只能通过一定的语言结构表征才能在译文中得到实质性的再现,获得来世生命;但是对于它们的解读是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所以无论是纯语言关涉的语言之“碎片拼接”还是源语意向性重构都说明翻译工作的艰难所在。因此,分析具体实例必须深度结合历史文化背景,人类逻辑常识以及语言学范畴在概念化进程中内化的规则。
在语言进化过程中,追求表现和创造自我恰好是纯语言的真正核心所在。尽管这种核心深藏鲜露且支离破碎,但它以被语言表征事物本真面貌出现,是文学作品生命繁盛的积极推动力;但在语言作品中,它只是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然而,这种终极本质,即纯语言,在各种语言中仅仅只和语言成分及其变化紧密相连,在文学创作中则承载了深沉、异己的意义。按照本雅明的观点,翻译的突出功能就是将“纯语言”释放出来并加以重塑,使之从表征语言核心实质变成通过语言文字被表征,并在语言不断渐进演变过程中重构出全新圆满的“纯语言”——它不再是表达或者意指任何具体内容,而是那种不可名状但具创造力、贯穿于所有语言的“语辞精髓”[1]。
参考文献:
[1]Benjamin, W.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 In Venuti, L. (ed.) .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18, 19-20, 18, 18-20, 19, 19, 18, 18, 18,22.
[2]保罗·德曼. “结论”: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任务”[A]. 郭军,曹雷雨,编.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C].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73.
[3]Derrida, J. Des Tours de Babel[A]. In Anidjar, G. (ed.). In Acts of Religion [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118.
[4]张琳. “悬搁”上帝如何?——从现象学含义论看本雅明的“纯语言”[J]. 现代哲学, 2017(5): 91-98.
[5]喻锋平. 从“理念”到“纯语言”: 论本雅明的语言哲学[J]. 求索, 2009(11): 109-111.
[6]陈影. 喀巴拉神秘主义视角下的本雅明元语言论[J]. 外国文学, 2018(7): 103-111.
[7]约翰·塞尔. 意向性: 论心灵哲学[M].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1.
[8]Searle, J. R.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66, 143.
[9]魏在江. 认知语言学中的语境: 定义与功能[J]. 外国语, 2016(4): 39-46.
[10]Van Dijk, Teun.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 -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郭春贵,安军. 隐喻的语境分析[M]//郭春贵,贺天平,编. 现代西方语用哲学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6: 124-134.
[12]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09.
[13]张幼军. 阐释学与儒家经典英译[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1): 112-116.
[14]曾克明. 正确理解是翻译的关键[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6(2): 120-122.
[15]Searle, J. R.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2-173,186-190.
[16]Searle, J. R. 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6.
[17]蒋洪新. 新时代翻译的挑战与使命[J].中国翻译, 2018(2): 5-7.
On “Pure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tionality
LIU Bin
Abstract : The concept of “pure language” proposed by Benjamin triggered many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on its essential contents. Based on the category of mental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cites John R. Searle’s Intentionality Theory to analyze and interpret this term, and in particular, the relevant description of “pure language fragments” is reasonably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Background” Theory. It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commonalities between intentionality and “pure language” in the aspect of their definitions and concepts, and further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re language” and cognitive science research covering mental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ntional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source and interpretation method for the reference problem in linguistics and the intentionality of the source tex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fter a focused and thorough analysis of essential contents of this term, such as its intentionality, convergence, integrity, diachronicity, and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Key words : intentionality; “Pure Language”; consensus; untranslatability; translatability; holism; diachronicity
作者简介: 刘 彬,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7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语言哲学视域下文学翻译的意向性重构研究”(18FWW008);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翻译研究的新视角:意向性重构”(18YBA012);湖南省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课题“意向性:翻译单位认知研究的新视角”(XSP18YBZ0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590744)
DOI: 10.19503/j.cnki. 1000-2529. 2019. 06. 016
(责任编校:文建)
标签:意向性论文; “纯语言”论文; 趋同性论文; 不可译性论文; 可译性论文; 整体性论文; 历时性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