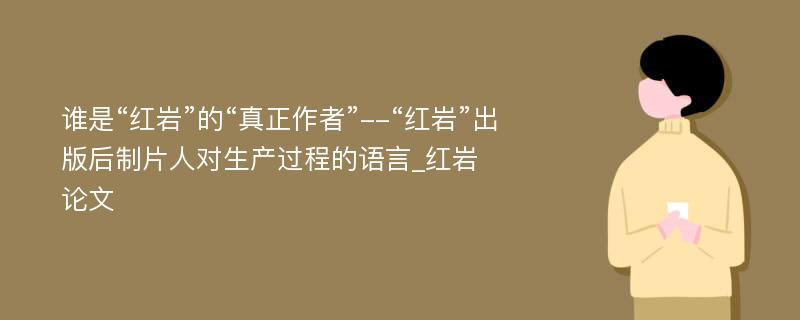
谁是《红岩》的“真正作者”——《红岩》出版后生产者们关于生产过程的措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生产过程论文,措辞论文,生产者论文,谁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2年前的两三年,《红岩》的修改是沙汀、马识途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们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这个和自己无关又有关的事情上。1962年《红岩》出版后,沙汀开始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但却更难产的长篇创作,但有关《红岩》的事情还是他总是挂在嘴边的话题。看1962年的沙汀日记,很多日子尤其是前几个月都有和《红岩》有关的事情发生。尤其是这年的三月份,沙汀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在会上会下和李劼人、王朝闻、周扬、韦君宜等人都谈到了刚刚出版的《红岩》,听到大家对《红岩》大多表示肯定的态度,曾经付出过巨大劳动的沙汀的心里肯定也有一丝的安慰。但是,当某些知情者对他帮助修改《红岩》所做贡献表示钦佩和肯定时,他也表现出很是谨慎和谦让的态度。如1月11日的日记说到在重庆和组织部副部长雷雨田等人聊天时的情形时说:“回家的路上,我记起雷的这句话:‘他帮罗广斌他们修改过嘛!’没有做什么申明。因为事实上我只提过一些建议,并未动笔。到了家里,一想起这件事,就感到一点歉然。”①3月31日,中青社的同志们拜访沙汀,对他在《红岩》创作过程中的贡献表示感谢,沙汀在日记中说:“但我赶快把话题拉开了,谈到党委的领导和作者本人的努力。”②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怀疑作者们的才能和出版社在作品写作中的帮助到底有多大时,沙汀还是肯定了罗、杨的才能。
这年的3月以后,《红岩》逐渐成为人们读书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中的热点,报刊杂志开始主动组织评论文章,与《红岩》和《红岩》作者有特殊关系的沙汀、马识途也成为人们约稿的对象。5月,《红旗》杂志向沙汀约稿评论《红岩》,这件事让沙汀犹豫了好几天,“考虑到自己的健康情况,文章的分量,结果还是没有把握承担下来。”③最终还是回信推掉了约稿。与此同时,马识途也接到《中国青年》《红旗》《河北日报》等报刊的约稿,开始马识途也是想办法拖延和推辞,但终于经不住编辑们的软磨硬泡,在6月13日《河北日报》上发表了《〈红岩〉是怎样写成的?》,在1962年第11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且说〈红岩〉》。
作为参与过《红岩》写作的当事人,马识途的评论文章没有像其他的职业评论家一样论述《红岩》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是主要叙述别人还很少说到的《红岩》写作的经过和取得成功的原因。在叙述了《红岩》作者们“不怕失败、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后,作者主要给我们讲述了作品成功的客观原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党的关怀,群众的支持,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作者的生活经历,给《红岩》这一本小说的成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④在说明这些外在因素、客观条件的重要性的同时,马识途指出作家主观条件、写作技巧是第二位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红岩》正是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接下来似乎马识途要论述《红岩》的“不足之处”了:“是的,《红岩》仍然是有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的,应该给作者指出来,使他们知道百尺竿头,如何更进一步,应该在哪些方面去继续努力。”但是马识途的文章在此“骏马收缰”、突然结束了:“但是我的‘壳子’已经‘冲’得很不少,我又已经把这本小说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之处写信告诉了作者,我就不再在这里优点、缺点的进行分析,浪费篇幅了。”⑤
马识途在《且说〈红岩〉》中欲言又止的《红岩》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可以从他本人的一份写作提纲中得到解答。这份提纲的名字叫做《〈红岩〉评论(大纲)》,很可能这个“大纲”就是《且说〈红岩〉》的底稿,只是在后来正式写作的时候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这份“大纲”中关于作品的“成功之处”只有很短的几行:“成功之处,在于真实,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举世闻名中美合作所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真实地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反映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博大胸怀,那种先能舍己、视死如归的伟大人格,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无畏精神,那种革命乐观主义和高度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⑥第二部分作者写的是《红岩》取得成功的主客观原因,也即是后来《且说〈红岩〉》的主要内容,而写得最多的是《且说〈红岩〉》中没有说出来的第三部分“缺点(或不足之处)”:
“1.作品已经从回忆录升高得多了,脱胎于回忆录而作了很大的加工,使之丰实完善、突出,但是似乎还有一些回忆录限制性的痕迹,……
“有人说写的是群像,群像是写的不错,可惜还是没有写集中的典型人物,没有一贯到底的中心人物,人物的集中塑造不足……
“2.人物性格的发展不够,特别是在监狱里发展不够,除了刘思扬有一些发展(但是刘的发展并不鲜明突出,有些勉强),要算‘小萝卜头’了,‘小萝卜头’的进步显然体现了牢里党的教育的成功,其余则很少发展了。……
“3.历史背景写了,内外结合了,且写得很好,但是和当时历史实际情况比仍有不足,对于当时党所领导的各条战线的群众斗争,除学校外,都是采取侧写、隐写办法的,气氛是有的,但不过瘾。城市农村斗争中的工人、农民英雄人物没有一个清楚面貌,其中写了陈松林等人,还不够血统工人的模样,其它就更少出现。……
“4.人物个性不足,都是英雄,人物不够鲜明深刻,不在于群像问题,而在于赋予英雄人物以个性,也有,但不够,如丁地平、刘思扬、如‘小萝卜头’,如龙光华,如华子良等,都开始有,但是不足。
“5.语言是流畅的,有些章节写得很深刻鲜明,描写心理比较深刻,但也有些写得一般化,特别是没有形成一种风格的语言,这是要求过高了,须长久锻炼才成……
“6.两个监狱地点,长期冷下去,受具体事实限制,这正是回忆录的影响,当中通过刘思扬联系上了,但又冷了那一个。”⑦
马识途在这里所说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几乎每一点都在《红岩》写作过程中召开的讨论会上指出过,这些到最后也没有解决的老问题对马识途来说当然是知之甚深,但他还是从维护作品声望的角度考虑把话收了回来:“缺点是微小的,但可以提出,原因是缺乏生活的某些感性知识,和艺术能力的限制,有的是对将来的希望,以客观分析不能算作这本书的缺点的。”⑧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不是因为“壳子已经冲得很不少了”,所以在《且说〈红岩〉》中才没有把这段本来想好的文字写进去。虽然《红岩》在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当中已经得到高度评价,但参与过写作的人们在阅读同一本作品的时候却有很不相同的感觉和体会。如重庆市委秘书长、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在选看了一些段落后就“感觉并不精彩”。这时候,沙汀提醒他说:“这很可能是书中不少重要事件,他早已知道了。他承认这个看法,说:‘收集材料的时候,我参加工作了呀!’”⑨与这些写作的参与者相比,作者们更清楚他们的小说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奇书”,马识途对《红岩》缺点的意见通过信件告诉了罗广斌,也通过《中国青年》的编辑宋文郁转告了罗广斌。在到文联从事专业创作的前夕,罗广斌给马识途回信说:“《红岩》有许多毛病,有缺乏经验的问题,有艺术表现能力的问题,有些是旁人提到的,有些是我们目前正在思索,尚未清楚的。”⑩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红岩》却还是在一夜之间成为人们争相抢购的“奇书”。沙汀、马识途和中青社的张羽等参与过劳动做出过贡献的人们为了避嫌,都很有意识地避免说起自己和《红岩》的关系,马识途在八十年代还说:“我给《中国青年》写《且说〈红岩〉》,又给《红旗》写文章,发表后很后悔,人们会以为(我)利用写文章窃取荣誉……我做了为党做的工作。”(11)
《红岩》的成功让罗广斌和杨益言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一夜之间成为名人。但他们在高兴之余还是很谨慎地有意避开一些社交活动,以至造成马识途两次到重庆都没能找到罗广斌的“事故”。(12)当然,对于公开的表态发言他们更是小心,因为老领导肖泽宽曾经及时提醒过他们要:“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发言。”为此罗广斌和杨益言还商定了几条他们共同遵守的章约:“一、少做报告;二、少出头露面;三、少写文章,特别是创作谈一类文章;四、多听取批评意见,注意自己的不足。”(13)因此,当调到重庆当副市长的陈荒煤要他们总结写作经验时,他们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反应:“陈荒煤同志调到重庆作副市长,和我们见过几次面,他也说要我们总结经验。我们素来对此胆怯,没有多吭声。”(14)1962年,他们的确是按照他们保持低调的想法,用很长的时间在北京广泛听取文艺界人士对小说的意见,而并没有对外发表任何文章。1963年,已经是市文联创作员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组织要求下进行了《红岩》创作的总结,经过组织多次审阅通过后定名《创作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发表于5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署名罗广斌、杨益言。
如果说此前的少发言是保持低调的话,在《红岩》事实上已经成为畅销书的情况下,如果还一直保持沉默就显得是对名人光环的默认和“贪天之功以为己有”,(15)因此,作者们在这篇调子很低的文章中把自己确定为“学写小说”的人,而把小说的“真正作者”归结为创作者之外的三个集体:先烈、群众、党委。这种写作者的自我否认在文章的第二段就开始了:“大家知道,《红岩》这本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那些在‘中美合作所’里为革命献身的许多先烈,是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无产阶级战士。我们只是做了一些概括、叙述的工作。”(16)这里的“大家知道”表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削减作家能动性和想象力的创作理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原则。在这种创作理念中,作家、知识分子只是创造了历史的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这种创作理念也是集体创作和“三结合”创作方法的依据和源头,“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工农兵创造的’,如果‘工农兵不参加反映他们生活的文艺创作’,‘也很难反映出生活的本质来’。”(17)《红岩》的作者也“曾在美蒋反动派的集中营‘中美合作所’里被囚禁过”,也是当年地下党革命斗争的参与者,这也是他们获得“发言权”和成为“代言人”的原因,但他们经历的生活并不就是群众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是很有限的。直接经历的斗争虽然有一点,也是非常不够的。”(18)所以从解放开始,他们就通过参加烈士追悼会筹备工作和报告会,“搜集参考了一千多万字的资料;又访问了许多革命前辈,向他们学习了不少革命斗争的知识。”(19)当然,群众不光是生活的创作者,他们还是作品的“收件人”和服务对象,他们的接受倾向也是作者们创作时的依据:“为了适应群众的需要,不得不一方面舍弃一些现成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去补充搜集未曾掌握的材料。”1956年初,罗广斌还和马识途开玩笑说,他们的写作也就是“一本书主义”,写完便了。但到他们开始小说修改的1958年,“一本书主义”和这个“主义”的发明人丁玲已经遭到严厉的批判,作家的个人名望和私人利益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看了下面这段出自多位大人物执笔、经毛泽东三次审阅的文章中的话,也就很能理解罗广斌所说的《红岩》的“真正作者”是“为革命献身的许多先烈”和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家知道”的不言自明的事情:
“一本书主义”者把写书看得比一切都更高贵,好像作品只是依靠个人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他们不了解,任何天才的创作,离开了当前人民群众的斗争,离开了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劳动人民,只有那些用自己的劳动、智慧和生命创造历史的人们,才是不朽的。书的不朽也只是因为它真实地记录和描绘了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绩于万一,表达了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说出了人民心里的话而已。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首先是立德、立功,然后才是立言。没有人民之德、之功,又哪里有什么“言”可立呢?(20)
既然“功”和“德”都是群众的,作者能做的也就只是替群众“立言”,而这个“立言”的成功也主要是因为“领导”“为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这些“好主意”,一是学习《毛泽东选集》;二是坚持劳动锻炼,做基层工作;三是到北京参观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对这些“主意”和“办法”的作用,作者逐一进行了详细的陈述,而对于写作也即作者说的“学习”的具体过程则只有一句话:“领导上采取的这些办法,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提高。然后,再次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反复重写、修改,前后共写了约三百万字。这些重写、修改的过程,是我们学习写作的具体过程,也是我们在政治上、艺术上得到锻炼的过程。”(21)那些所谓“好主意”中只有第三项即到北京参观革命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是沙汀的建议,而其他两项虽然不是无中生有但也显然是做总结的固定套式。
虽然在总结文章中把创作的主体推让给了无名的烈士和群众,但实际工作还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小说热销所产生的真实收益也是由具体的人来享用的。作者们的创作总结虽然很是谦卑和谨慎,但《红岩》出版后产生的大笔稿费和他们明显变化了的生活方式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批评,为此,1964年秋天,重庆市文联党组召开扩大会议,罗广斌代表他和刘德彬、杨益言对稿费的使用情况做了说明和检查,并由三人署名写了书面检查,三人一致同意把剩余的2万元上缴党费。虽然在他们的总结文章中只是说“省市领导”曾经给他们“多次校阅稿件”和“提出宝贵意见”,而并没有出现任何人的姓名,但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曾经给《红岩》提供过帮助的“省市领导”们多数都被打倒后,还是给《红岩》作者们造成了直接的麻烦,到最后,当《红岩》的作者本人罗广斌也成了“披着革命作家外衣”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时,罗广斌他们却没有办法把《红岩》的“真正作者”推卸给他们之外的烈士、群众和党委。
①②③⑨吴福辉编:《沙汀日记》,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第167页,第211页,第204页。
④⑤马识途:《且说〈红岩〉》,《中国青年》1962年第11期。
⑥⑦⑧马识途:《〈红岩〉评论〈大纲)》,《罗光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红岩〉过程中我参加讨论时写的发言要点》,没有正式发表。
⑩罗广斌:1962年4月16日写给马识途的信,未发表稿。
(11)《四川文联主席马识途同志谈罗广斌》,1980年10月6日晚张羽对马识途的采访记录,未发表稿。
(12)罗广斌:在1962年4月16日给马识途的信中说:“因为我们有意避开一些社会活动,结果便产生了你找不到我们的‘事故’,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13)(14)王维玲:《走向成功之路——记成名作〈红岩〉的诞生》,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第246页,第248页。
(15)(16)(18)(19)(21)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过程学习的过程——略谈〈红岩〉的写作》,《中国青年报》1963年5月13日。
(17)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转引自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08页。
(20)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转引自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上),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