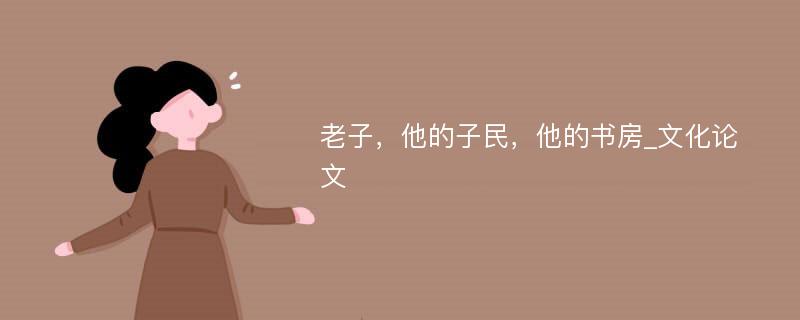
老子其人其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人论文,老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子春秋末期人,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记载过的。司马迁说:“老子者,楚若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之史也。”其实,司马迁在这里给老子明确地作了一个小传,肯定了老子本人就是“姓李,名耳,谥曰聃”的老子。后人有关老子是老莱子或太子儋之说,亦源于司氏,这只是后人对其疑笔误解。由于这种误解引起的争论达200年之久。
关于老子的争论直接涉及到《老子》成书时间问题。关于《老子》成书的时间大致有五种观点:一如果承认了老子是春秋末期人,那么《老子》书的写作年代也就不言自明了。二《老子》书的内容不成系统,不可能成书于一人一时,包括了许多道家人物的经典思想。三春秋时期,在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论语》是第一部私人著作,所以肯定《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四思想史发展的规律已证明,先有一种思想,然后才有对这一思想进行批判的其它思想。老子批评仁义礼智,反对天命鬼神,所以《老子》成书应在《庄子》以至《吕氏春秋》之后。五《老子》书的文体没有《孟子》那样的内容体,应在《论语》、《孟子》之后;是一种简明的“经”体,可见其成书应在战国时代或其后世。此五种观点除了第一种观点之外,其它四种观点均肯定《老子》书成于战国时代,因此很多有关著述中,都将老子及其道家学派的思想放在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之后。
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在言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则逢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老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我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孔子世家》又载:“鲁闻宫敬叔言于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学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一个实质性问题:老子早于孔子,《老子》书是老子所作(老子对孔子赠言似《老子书》)。
老子把自己对春秋末期的观察上升为哲学的概括,得出万物皆从于“道”的结论。他给“道”下了一个定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众妙之门。”这一段话可有这样几层意思:一道本是道路,千千万万的道路是可变的,其共同本质是恒常不变的,这是非可道的常道;二名是名称,名称与具体事物相联系。老子所说的名是所谓的具体名称背后的那个“常名”,这个“常名”是所有名称的共同本质的根据。三老子把可道之道与常道,可名之名与常名区分开来,显然是对道与名的本然性的追寻,是对世界万物本质的终极性阐释。所谓常道、常名,是不可用语言称谓和名状的。无名之道之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它是一种混沌,故无名。有名是指有名称,语言可以称谓的,即可名,有名称把指称的对象固定下来。名称标示事物的差异和特征,便是有规定,所以有名是万物之母。常道、可道、常名、可名、无名、有名是对待的两极、两者,在时空上无先后,它是众多奥妙的门户,贯通天、地、人。道可体验、认识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