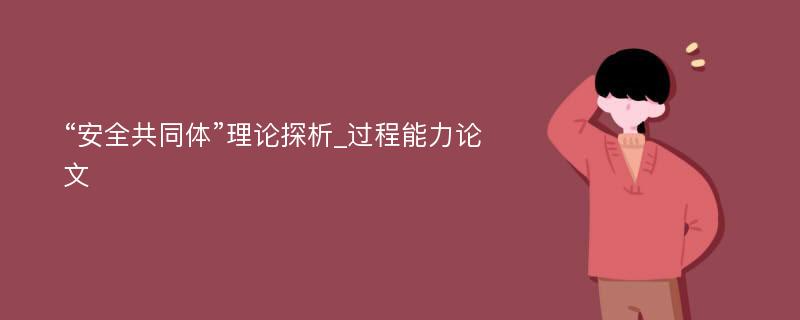
“安全共同体”理论探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理论论文,探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随着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迅速兴起,一个沉睡了40多年的概念——“安全共同体”,开始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视野中,并成为当前国际和平研究、安全研究和区域主义研究的最新发展和核心理论之一。事实上,“安全共同体”正以强大的生命力直接进入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前沿。最新的现实表现是,2003年10月7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的《东盟第二协议宣言》(简称《巴厘第二协议》)把2020年建成“东盟安全共同体”作为东盟区域安全合作的新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这意味着“安全共同体”理论首次以相同的名字出现在安全区域主义的实践之中。(注:“ASEAN Security Community Concept to be Brought Before ASEAN's 9th Summit Bali”,20 September 2003.http://www.rsi.com.sg/
eglish/view/2003092018349/1/.html)然而,面对“安全共同体”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主义实践中这种明显的互动发展,无疑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深入剖析。
一、“安全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核
“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y)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Richard W.Van
Wagenen)提出。(注:Richard W.Van Wagenen,Research in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ield:Some Notes on a Possible Focus,Princeton,N.J: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rld Political Institution,1952,pp.10—11.)并由卡尔·多伊奇(
Karl W.Deutsch)等人随后从理论上和实证上对“安全共同体”进行了全面阐述。在其看来:“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integration)的集团,而该集团内的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进行物质上的争夺,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注:Karl W.Deutsch and Sidney A.Burrell,et a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p.5—6.)
“安全共同体”分“合并”(amalgamated)和“多元”(pluralistic)两种类型。“合并型安全共同体”是指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单位正式合并成一个较大的独立单位,合并后存在某种形式的共同政府。该共同政府可以是单一的或者联邦的。今天的美国就是合并型的例子。“多元型安全共同体”是指各成员仍保持法律上独立的共同体。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即属此一类型。相比较而言,“多元安全共同体”较易实现和维持,因此在其成员间往往是维持和平的较为有效的工具。(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5—6,30—31.)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安全共同体”成员之间不存在利益差异和冲突。将“安全共同体”与其它类型的安全关系区别开来的标准不是冲突的消失,而是和平管理冲突的能力。所以,“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在操作上能够通过成员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有组织的战争准备或大规模的暴力来验证”(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31—32;Deutsch,“Security Community”,in James N.Rosenau (ed.),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Free Press,1961,p.99;Deutsch,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Problems of
Measurement and Definition,Archon Bools,1970,pp.33—34.)。所以,他们定义的“安全共同体”被称为“和平或非战共同体”。(注:Raimo Vayrynen,“Stable Peace
Through Security Communities?Steps Towards Theory-Building”,http://www.nd.
edu/ekrocinst/ocpapers/op—18—3.pdf;Ole Weaver,“Insecurity,Security,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Security”,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ed.),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71.)
就“安全共同体”而言,重要的是它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这既是该理论的核心,也是它能否产生现实解释力的关键。对此问题,多伊奇等人既没有用当时国际流行的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来解释,也没有用在欧洲兴起的联邦主义和功能主义等一体化理论所主张的制度建设来分析,而是从科学行为主义的独特研究视角,广泛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乃至地理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在《政治共同体和北大西洋区域》一书中,他们考察了历史上的德国、哈布斯堡王朝、挪威与瑞典、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试图通过比较的实证性研究构筑更大范围内建设“安全共同体”的宏伟图景,并对“安全共同体”实现的条件进行了分类。其中,有两个前提条件是两种类型安全共同体必须具备的:一是主要价值观的一致性(包括宪政主义、民主等政治观念和自由经济观念等);二是共同的反应性(包括共同的同情和忠诚、共同的“我们感”、共同的信心和考虑、对自我形象和利益至少部分的认同、预测彼此行为并按照这种预测行动的能力等)。有八个条件有助于“多元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而对合并型“安全共同体”则是必需的,即与众不同并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存在有能力的核心区、较高的经济增长、共同的经济报酬预期、较大范围的相互交流、不断增多的精英分子、一系列社会沟通关系和大规模的人员流动等。另有四个条件对两类共同体的形成有所帮助、但不是必要的,即拒绝“自相惨杀”的战争、外来的军事威胁、有力的经济联系(即经济相互依存)和道德与语言融合(包括家族间内部通婚、共同文化形式和包括共同语言在内的社会交流的有效共同习惯等)。(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43—161.)
“安全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就是建立共同的沟通与交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核心区和社会学习。一体化进程往往起源于某一个核心区。一体化的过程通常就是一个核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社会学习来实现。一方面,普通公众在交往中将一些特定的政治行为习惯重新整合;另一方面,通过核心区的政治精英,即政府和政治领导人将特定传统与制度重新整合。二是“起飞”(takeoff)与一体化发展。在这一阶段,这种小的、零碎的、无力的变化汇成了有显著力量支持的、强大的、更协调的变化,“起飞显示出走向一体化的政治进程明显加快或加强”。三是跨越“门槛”(threshold)与共同体的形成。一体化的共同体的实现可以用跨越“门槛”来表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旦主客观上都能够达到要求时,就可以认为跨越一体化的门槛,“安全共同体”就已经实现了。(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31—32,37—38,83—85.)后来,多伊奇本人又专门论述了“多元安全共同体”建立所需要的三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其政府、社会精英及民众认识到在其政治单位之间增加了战争的厌恶性和不可能性。第二个过程是,传播赞同一体化的知识运动与传统,并为其准备政治气候。第三个过程是,发展和实践相互关注、沟通和反应的习惯与技能,以便使参加单位自治和实质性主权的保持成为可能,也使他们之间保持可靠的和平期望与和平变化成为可能。(注:[美]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郑启荣等译:《国际关系分析》,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45页。)“安全共同体”这些过程的实现与其背景条件密不可分,“共同体意识”就是在背景条件不断成熟和过程不断推进中培养出来的。(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70,95—96.)
“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必定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不是一个不可扭转的线性演变进程?多伊奇等人用经济学的博弈论对此做出了解释:将“安全共同体”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它可以因一体化实现而生成,也可能因一体化逆转而解体,这犹如“能力与负荷的竞赛”。与一体化进程和“安全共同体”发展相联系的“能力”(capacity)有两大类:一类是决定政治单位行为的规模、实力、经济发展和管理效率等能力,它与反应性相联系;一类是政治单位控制自身行为、调整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它与克服外部障碍的能力连在一起。所谓“负荷”(loads)或“负担”(burdens)既包括军事或财政负担、人力和财富消耗、政治或军事责任的风险负担、社会和经济调整的成本及其他物质类型的负担,也包括政府所承受的诸如管理交通运输和信息交换等无形的负担。这些“负担”是“安全共同体”建立或维持所依赖的重要资源。由于针对更大地区和更多人口的决策不得不由较少核心机构做出,这导致“安全共同体”运行的总趋势是增加政府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决策能力的负担。这样,其成功和失败就依赖于两种变化的关系,即核心政府所承受的需求和负担的增长幅度与共同体的政府机构能力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功维持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共同体成员间这种“负荷”与“能力”平衡的程度。(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39—43;Deutsch,Political Communit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pp.43—44;Deutsch,“Security Community”,in Rosenau,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Foreign Policy,p.103.)
具体而言,“安全共同体”是否会在上述竞赛中解体还取决于一些关键的背景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两类,即增加共同体负荷的条件和削弱共同体处理这些负荷能力的条件。以下六项条件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促使“安全共同体”走向解体:一是共同体政府和参加单位因承担过多的军事、经济、政治责任所增加的过度的负担;二是代表各类人、地区和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大幅增加,而原有的政治决策体系对此不能做出及时而充分的反应;三是参与方的区域、经济、文化、社会、语言和种族差别的增加快于并多于任何补偿性的一体化发展;四是共同体内政府和政治精英必要而及时的行为或反应能力明显削弱;五是原有政治精英的相对封闭使新成员与新观点的进入大为减慢,促使种族或文化的“外人”集团(outgroup)或非核心区中的敌对精英的兴起;六是过分推迟人民所期待的社会、经济或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已经不时在邻近集团或地区推行),或对强大的原来拥有特权的集团或地区的优势地位的损失未能做出及时的调整等。(注:Deutsch
and Burrell,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s,pp.59—64;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344—345页。)
综上所述,多伊奇等人主要借助科学行为主义“三论”即一体化理论、沟通理论和博弈理论讨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分类及其重要特征,并探索走向这一重要政治共同体的有别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经验的、社会学的和种种沟通的、多元主义的道路。他们的“安全共同体”理论由此被称为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广泛相互交流和多样性为基础的“交流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民主安全共同体”。(注: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in Security Communities,p.9;John A.Vasquez(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3rd ed.,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
Hall,1996,pp.288—289.)就理论内涵而言,其意义在于把国际关系从传统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冲破以下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桎梏:主权国家是国际舞台上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是单一实体;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毫无关系等。阿伦·利派特(Arend Lijphart)说,多伊奇的理论代表着国际关系研究所取得的一项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范式”。(注:Arend Lijphart,“Karl
Deutsch and the New Paradig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Quarterly,March 1978.)就方法论而言,其学术价值在于广泛吸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多种研究成果,并把现代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与传统关注的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国际关系概念性分析与思维框架,如将追求高度的“精确化”和“实用性”视为理论发展的基础;注重数量分析和规范的实证研究;关注社会学方法的积极作用等。这种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伸张性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灵感,对学者和决策者而言,这是一种“最持久的贡献”。(注:[美]肯尼斯·W.汤普森著,耿协峰译:《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9页。)奥特勒等建构主义者关于“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就是对这一研究的最重要的延续。
二、建构主义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重新解释
由于冷战时期两极对峙的特殊环境和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巨大影响,多伊奇等人的“安全共同体”长时间内并没有受到各界重视。只是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兴的建构主义学派在多伊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安全共同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带动“安全共同体”研究的全面兴起。伊曼纽尔·奥特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纳特(Michael Barnett)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奥特勒等人重点研究了“多元安全共同体”,并将其定义为:“由其人民对和平变化保持可靠预期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跨国区域。”而根据共同体内的信任程度、治理体系制度化特征及程度,“多元安全共同体”又可分为“松散的”(loosely)和“紧密的”( ti ghtly)两种类型。在“松散的安全共同体”内,由于其成员拥有相同的意图和认同结 构 ,所以,他们不会想到来自其他成员的好战行为,并始终保持着自我克制的习惯。“ 紧 密的安全共同体”在两个方面要求更高:一是拥有一个“互助”的社会,在其中建构 起 了集体的体系安排;二是拥有共同的超国家、跨国家和国家间的规划以及某种形式的 集 体安全体系。这种规则体系类似中世纪拥有“共享”主权(“pooled”sovereignty) 的 它治状态(heteronomy)。具体说来,“多元安全共同体”通过三种特征来定义:一是 其 成员拥有共享的认同、价值观和意图;二是其成员拥有多方面直接的联系和互动;三 是 该共同体展现出一种在面对面接触中产生的、通过某种程度的长期利益和利他主义表 现 出来的互惠性。这种长期利益源于互动产生的知识,而利他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义务 和 责任。将“安全共同体”与其他形式的共同体区别开来的方法,是该共同体成员保持 和 平变化的可靠预期。“可靠的预期”可以由社会互动理论来解释,即稳定的预期可以 来 自拥有共同的认同、其认同和利益由环境决定的行为体。“和平变化”是指行为体既 不 预期也不准备把有组织的暴力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手段。所以,“安全共同体”内 可 以不存在高度发达的战略联系或正式联盟,但必须有禁止通过战争手段解决国家间争 端 的法律上的或正式的规范。(注:Adler and Barnett,“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o f Security Communities”,in Security Communities,pp.30—35.)
与多伊奇等人一样,奥特勒等人把研究的重点投向“安全共同体”的实现过程,但不同的是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梯级论”和“阶段论”,并将研究对象从北大西洋区域扩大到包括西亚、东南亚和南美洲在内的世界其它区域,从而使该理论更具代表性和解释力。他们用“三级阶梯”(three tiers)来解释促进这种和平变化产生的因素和“安全共同体”生成的过程。第一级阶梯是突变性的基础条件(precipitating conditions),包括科技、人口、经济与环境中的变化、社会现实新解释的发展以及外来的威胁等。这些因素促进国家扩大面对面的互动、对话和合作。第二级阶梯是结构变量(
structurevariables)与过程变量(process variables)。前者包括权力和知识等变量;后者包括交易、组织和社会学习等变量。而权力和知识是“安全共同体”发展的结构性“大梁”。过程变量中的交易包括经济、材料、政治和技术等各种类型,它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重塑着集体实践、改变着社会现实。国际组织和制度通过提高互信和集体认同创建可能的国家行为,并由此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包括与交易及社会交流、制度化的组织、权力或核心权威等相伴的社会学习,则不仅可以通过彼此交流自我理解、现实观点和对规范的预期等改变个人和集体的理解与价值观,而且可以通过促进意图、共同的规范和理解在国家之间的扩散来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形成。第三级阶梯是相互信任(mutualtrust)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信任可以理解为尽管不确定但仍然相信,它依赖于对另一行为体将按与规范性预期一致的方式行事的估计;集体认同被定义为行为体之间个人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互动和联系,它可以限制共同体内国家的权力,也可以赋予他们行动的力量,并有助于共同反应性的发展。总之,上述结构变量与过程变量之间积极的、动态的、互惠的互动,促进了相互信任和集体认同形式的发展,反过来催生对和平变化可靠的预期,从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注:Adler and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pp.29—49.)
据此,奥特勒等人把“安全共同体”的发展过程清楚地分为创始(nascent)、上升(
ascendant)和成熟(mature)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主要是共同的威胁、从跨国经济中获利的期望和文化、政治、社会与观念的同质性等因素推动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进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出现。一个核心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是该阶段可靠的推进者和稳定者,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才能被指望提供通常需要的领导、保护、物质利益和目标意识。“安全共同体”进入上升阶段的标志主要有:日益密集的网络、反映紧密军事协调和合作的新制度与组织、促进联合行动的认知结构、互信程度的深化、对和平变化可靠预期的集体认同的出现等。“安全共同体”走上成熟的标志则主要有11种,即多边主义(即决策程序、冲突解决和冲突裁决进程主要通过国家间的共识解决)、不设防边界(即现行的边界检查和巡逻不是针对有组织的军事入侵)、军事计划的变化(即彼此不做最坏的军事设想、任何军事活动不以彼此为假想敌)、威胁的共同定义、存在共同体的语境和语言、合作安全(用于对付内部安全问题)和集体安全(用于对付外部安全威胁)、深度的军事一体化、对付内部威胁的政策合作、人口的自由流动、权威的制度化、多视角的政治形态等。前五种变量对松散的和紧密的“安全共同体”均适用,而后六种变量只适用于紧密的“安全共同体”。(注:Adler and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pp.49—58.)
建构主义者对“安全共同体”如何衰落的解释也更具说服力。在他们看来,“安全共同体”可以被建构,也可以从内部或外部瓦解,因为其发展所必需的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同的一致性不是静止的,而是易受变化影响的。“建构安全共同体同样的力量能够将之拆毁”。所以,“许多促进安全共同体再造的社会进程,也同它的衰落紧密连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是互信的丧失”。最终,安全共同体成员之间再现战争行为即标志着它走向解体。(注:Adler and Barnett,Security Communities,pp.58.)在这方面,阿米塔弗·阿查亚(Amitav Acharya)的解释更为深刻:“安全共同体在扩展和深化其合作的时候就可能解体。安全共同体提出的新形式的合作或对现存形式合作的深化会面临这样的处境,即它们可用的资源或规则在管理涉及新任务的合作行为时证明是不充分的。同样,现存安全共同体的扩展可以改变其社会化动力,因为安全共同体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进程,原先‘非社会化’的行为体的加入会给共同体增加新的心理负担,并考验它的处理内部冲突的能力。而且扩大的安全共同体势必涉及新行为体的具体安全问题。”(注: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in Security Communities,pp.34—36,102—209.)
具体而言,建构主义从四个方面对改变“安全共同体”研究的新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安全共同体”的社会建构,即“安全共同体”是社会建构的过程,避免战争的惯例主要来自互动、社会化、规范和认同的建构。二是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和制度的作用,组织和制度在导致国家间和平行为的社会化进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三是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超越了改变国际政治的物质力量的影响。它认为,尽管物质力量仍然重要,但观念、文化和认同等主体间因素在对外政策的互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四是超越了欧美中心的地域界限和自由、民主、相互依存的理论模式,在缺乏民主和较低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第三世界里依然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以“东盟规范”和“东盟方式”著称的东盟,就为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而丰富的领域。阿查亚说,东盟虽不是多伊奇所说的“安全共同体”,但符合“创始的安全共同体”概念,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注:Acharya,“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in Security Communities,pp.198—227;“Strengthening My ASEAN Security Community”,Jakarta Post,14 June 2003.)
三、“安全共同体”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多伊奇等人与奥特勒等人关于“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是相通和相似的。有学者说,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被重新提出来主要是对安全研究历史的一种注解,对后来的学者而言,它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新造词”。(注: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47.)也有学者说:“多伊奇关于安全共同体的定义仍然给安全共同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出发点。”(注:Raimo Vayrynen,“Stable Peace Through Security Communities?Steps Towards
Theory-Building”.)与多伊奇等人明显不同的是,奥特勒等人将“共同体感”等社会学观点用认同和规范等更理论化的形式表述出来,并对“多元安全共同体”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使这一理论摆脱一体化理论的遮掩而以独立的面目出现在国际和平、安全和区域主义的研究之中。安全问题专家奥利·维夫(Ole Waever)评论说,奥特勒等人对多伊奇等人“安全共同体”定义的“修正版本”,是“建立在认同和共同体之上的非战的形式”,所以,他们是“建构主义者的多伊奇主义”。(注:Ole Weaver,“
Insecurity,Security,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Security”,in Security Communities,pp.79,105.)
正是这种承上启下的研究使多伊奇等人和奥特勒等人关于“安全共同体”的基本观点成为广为引用的最具权威的理论,他们所描绘的“安全共同体”的美好蓝图不但被认为是国家或国家集团走出“安全困境”的理想之路,也成为许多学者所阐述的区域安全秩序的最佳形式,(注:参见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University Park,PA:The Pennsylvania State
niversity Press,1997;Bajorn Hetnne,“Regionalism,Security and Development: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 Bajorn Hetnne(ed.),Comparing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opment,Houndmills:Palgrare,2001,p.13.)而“安全共同体”本身已成为区域安全研究的核心分析工具之一。(注:参见N.Ganesam,“
Rethinking ASEAN as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Vol.21,issue 4,Winter 1995,pp.140—171;Michael Leifer,“
ASEAN as a Model of a Security Community”,in Hadisoesastro ed.,ASEAN in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Jakarta: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5,p.132;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2001.)这正如阿查亚所言,多伊奇等人的研究“为考察跨国问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有利且受欢迎的概念化工具”,而奥特勒等人的研究成果“为理解安全共同体为何、何时会产生以及将之同其他类型的安全体系区别开来的互动本质提供了有用的根据。”(注: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in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35—36.)
然而,尽管多伊奇等人和奥特勒等人的理论已经成为“安全共同体”研究的主流理论,但他们的理论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这种“安全共同体”并不能完全解决当前形势下的重要的安全问题。在多伊奇等人和奥特勒等人看来,“安全共同体”就是“和平或非战共同体”,这是摆脱以冲突和不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安全困境”的一种途径。但这种观点易于遭受这样的质疑:如果“安全共同体”是和平或非战的,这就意味着这里的“安全”关注的主要是传统的军事或政治安全,而在目前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诸如经济、环境、社会、贫穷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时,非战的“安全共同体”还能保障成员的安全吗?在这种声音中,最重要的当属巴瑞·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等人。布赞认为,人类安全主要受到五个领域的影响,即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它们并非孤立地起作用,而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2nd ed.Boulder:
Lynne Rienner,1991,pp.19—20;更详细论述见Barry Buzan,Ole Weaver and Jaap de Wilde,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Boulder:Lynne Rienner,1998.)维夫认为,多伊奇等人的“非战安全共同体”指的是“有意义的”但“脆弱的”“偶发事件”,而“不是一种稳定的秩序”。他说,一个“完全的安全共同体”应该是“军事和非军事安全共同体”,而后者正是“安全共同体”演化的方向。(注:Ole Weaver,“
Insecurity,Security,and Asecurity in the West European Non-War Security”,in Security Communities,p.104.)比约恩·赫特纳(Bajorn Hetnne)认为,这种“非战安全共同体”只是一种“消极的和平”。(注:Bajorn Hetnne and Fredrik So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in Shaun Breslin,et al(ed.),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2002,p.47.)显然,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种“非战共同体”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
第二,认同等观念因素在“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决定作用令人怀疑。多伊奇等人重点从交流带来国家间和社会间的互动过程来理解“安全共同体”,他虽然暗示交流和互动产生互惠、信任和新的利益乃至集体认同,但没有对利益和认同的关系做出详细解释。奥特勒等建构主义者非常明确,成员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意图是“安全共同体”的首要特征。建构主义者的这种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尔·迈克斯威尼(Bill McSweeney)认为,认同理论扩大了认同的因果性,“不把利益的纬度作为学习过程的影响因子,就不可能解释认同的变化如何发生。设想被习惯和历史社会化的、具有特殊自我感的个人或集体,在没有自我利益刺激或施加压力的情况下选择变化是理想化的。”(注:Bill McSweene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p.210.)拉伊莫·韦于吕宁(Raimo Vayrynen)认为,就方法论而言,建构主义者认为共同的认同是“安全共同体”产生的必要条件,反过来,其存在又是共同的认同和意图存在的标志,这使人怀疑他们是否“陷入重复的陷阱”或者“不败的循环”。(注:Raimo Vayrynen,“Stable Peace Through Security Communities?”,http://www.nd.edu/ekrocinst
/ocpapers/op—18—3.pdf.)我的看法是,虽然集体认同等观念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国家利益来影响国家行为和区域合作,进而推动“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但由于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仍然是以利益为基点的国家间和集团间的竞争,所以,如果没有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恐怕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决定“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力量中,利益等物质因素永远是第一位的,认同等观念因素不可能取而代之。以被称为“安全共同体”典范的欧盟为例,试问:如果没有由美国主导的北约安全力量的存在和各成员国在利益上的共同让步,它的安全秩序能达到今日这种程度吗?
第三,这种“安全共同体”理论忽略了国内因素对区域安全的影响。从多伊奇等人和奥特勒等人的观点看,“安全共同体”主要被定义在国家间或跨国关系的框架内,而国家内部情势甚至国内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被排除掉了。所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莫汗米德·艾羽伯(Mohammed Ayoob)认为,领土满足、社会内聚力和稳定在国家内部占支配地位,这些国家特征的缺乏就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注:
Mohammed Ayoob,“Defining Security:A Subaltern Realist Perspective”,in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Williams,ed.,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Concepts
and Cases,Minneapolic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p.135—137.)戴维·莱克(David A.Lake)认为,在一个由互动的国家组成的区域安全体系(包括“安全共同体”)中,“安全外部性”(security externality)(包括经济、环境、信息和国民价值观等)会超越边界“外溢”到邻国,从而对体系内的其他成员中的个人和政府的安全构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注:David A.Lake,“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A System Approach”,in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pp.48—57.)韦于吕宁认为,一个其成员的内部充满暴力和不稳定的区域不能称之为有意义的“安全共同体”。他强调,一个“安全共同体”必须是其成员的内部和平至少达到国内不稳定不外溢到该区域其他成员的程度。(注:Raimo Vayrynen,“Stable Peace
Through Security Communities?”,http://www.nd.edu/ekrocinst/ocpapers/op—18—3.pdf.)可见,在国内冲突和其他不安全因素大量存在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全共同体”不可能存在。所以,“安全共同体”研究也需要采用莱克提出的“三层博弈”的替代性分析方法,即对国内、区域和国际(全球)互动进行分析。(注:David A.Lake,“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es:A System Approach”,in Regional Orders,p.50.)
总之,一个真正的“安全共同体”不仅应该是非战的或和平的,而且随着冷战后军事等传统安全因素的下降和经济、环境、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明显增多,它无疑又不能仅限于非战或和平的内涵;“安全共同体”的存在应该要求各种安全威胁不管是在成员间或是在成员内部都是较低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国家间和国家内部都是和平与安全的;在决定“安全共同体”发展的利益和认同关系的处理中,客观的做法应该是寻求利益和认同在互动中共同发挥作用。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安全共同体”目前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在许多区域内已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所以,它过去已经是、将来更应该是安全区域主义的分析工具或未来发展的方向。有理由相信,“安全共同体”的理论今后还会继续发展,所以,它应该有自己丰富的理论内涵,更应该有适合现实变化而不断修补这些内涵的能力。这也是“安全共同体”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