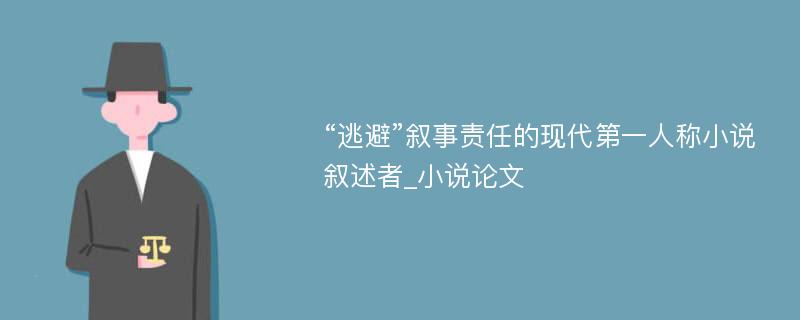
“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叙述者论文,人称论文,责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5-0141-06
五四之后的现代小说家,基本明确了第一人称叙述的虚构性,由此带来了第一人称小 说的繁荣。但是,传统的影响仍然强大,读者往往把第一人称叙述者看成是作者的化身 ,乃至就看成是作者本人,而作者对这一点的态度也是充满矛盾的,如郁达夫,经常直 接用自己的名字入小说,多少是希望读者把同名的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当成自己;但是 当读者因此而谴责作者本人行为不检时,郁达夫又利用小说的虚构性做挡箭牌为自己辩 护。郁达夫的情形并非个别,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典型的自叙传小说和身边小说的作者群 多少都有这个倾向。与其这样在叙述者与作者本人之间纠缠不清,不如尽可能减少第一 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的责任,这就形成了现代第一人称小说的一类特别叙述者 :“推卸”叙述责任的叙述者。这类小说有两个特点:1、较多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表现 为“听故事者”或者“读者”,形成“我听故事”或者“我读日记书信”的叙述模式; 2、出现了大量的分层叙述,这主要体现在日记书信体小说中。与读者关系最近的超叙 述者往往并非日记书信正文(主叙述层)的叙述者,超叙述者只做简要的陈述,介绍正文 (主叙述层)的来历,提供正文的叙述者。“我听故事”或者“我读日记书信”的“我” 以及超叙述者成为作者与故事讲述者/主叙述者的中介缓冲,与作者保持若即若离的关 系。
一、第一人称的“听故事”叙述者
“我听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模式现代作家并不陌生,《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这种 模式。五四之后译介过来的一些外国小说也采用了这种形式,如《柏林之围》([法]都 德)、《百愁门》([英]吉卜林)、《梅吕哀》([法]莫泊桑),《白璞田太太》([法]莫泊 桑)、《忍心》([英]夏芝)、《豢豹人的故事》([美]贾克·伦敦)等。而中国的文言第 一人称小说,也大都属于“我听故事”的模式。五四之后出现了一批“我听故事”的第 一人称小说,最早的大约是郭沫若的《牧羊哀话》(1918)。这些小说又可分为三种情形 。
第一种情形:听者与讲者都与故事没有情节联系。小说中的“听——讲”形成一个超 叙述框架,用来容纳故事。如王统照的《山道之侧》(1922)中驴夫讲述奎元的不幸爱情 故事,王统照的另一篇小说《青松之下》(1923-1924)中芸讲述同学吴镜涵的不幸婚姻 故事;陈炜谟的《狼筅将军》(1925)中白棣讲述“狼筅将军”一家的不幸遭遇;老舍的 《听来的故事》宋伯公讲述孟智辰无能反而节节迁升的故事;庐隐的《父亲》中绍雅念 日记体小说《父亲》;巴金的系列小说《长生塔》(1934)、《隐身珠》(1936)和《能言 树》(1936)都是父亲给儿子讲述民间故事,等等。这些小说由于这种“听——说”关系 而形成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我”与讲故事者形成复调双声。在“我听故事”的模式中,“我”与讲故事 的人往往在身份或者观点上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我”看待故事的观点往往与讲述者看 待故事的观点互相制衡,形成张力,从而使小说形成复调双声的特点。例如,《山道之 侧》的听故事者“我”是从北京来游八达岭长城的学生,讲述奎元故事的跛脚驴夫却是 个从来没有出过山的闭塞农民,而奎元的故事却属于五四之后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个 从北京回乡的青年奎元,爱上了神婆的女儿,神婆不同意奎元的求婚,打掉女儿的胎儿 ,带女儿远走了,奎元抑郁寡欢,就在“我们”碰见他的第二天跳崖被火车压死了。如 果不是听故事者“我”的存在,读者几乎要认同跛脚驴夫的观点,认为奎元的不幸在于 他在城里中了洋人的“邪”。但是,说话不多的“我”的存在,暗示了看待这个故事的 另一种视角,从而使小说形成了城市与乡村、文明与愚昧、进步与落后、人与神、爱情 自由与家长专制、钟情与冷漠等等复杂的对立,产生了复调双声的效果。《父亲》中念 小说的绍雅的诘问与听小说的“我”与逸哥的反应互相隔膜,《听来的故事》中,听故 事的“我”的提问与讲故事的宋伯公的看法不同,《长生塔》等三篇中,听故事的儿子 “我”的幼稚天真的提问与讲故事的父亲的严肃意图互相错位,最后小说就在这种对立 、隔膜或错位中结束,从而使小说传达出不同的声音,引起读者的思考。
其次,取得相对客观的叙述效果。一方面,由于讲故事的人讲述的是别人的故事,较 少涉及故事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故事本身显得比较客观;另一方面,由于第一人称叙 述者“我”在小说中相当程度上放弃了叙述的职能,由另一个人来讲故事,拉开了“我 ”与故事的距离,使“我”在小说中比较得体地获得了沉默的权利,尽量避免了道德评 价和抒情议论。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小说相对客观的叙述风格。奎元的故事、吴镜涵 的故事、狼筅将军的故事、以及《父亲》中的同名日记所讲述的故事,都是极为惨痛的 ,试想前3个故事如果换成主人公叙述,就很可能获得浓厚的抒情性。但实际上这些故 事是由局外人来讲的,总是有隔膜存在。特别是,奎元的故事竟然由一个愚昧自得的驴 夫来讲述,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在这八达岭的高山深处,竟然连奎元的跳崖殉情也被 视为走路不留神或者“新鲜的经验”。讲故事的人不大动感情,听故事的“我”也不多 加评论感慨,因而小说显得比较客观,取得了含蓄的美学效果。
第二种情形:听者与故事没有情节联系,讲者是讲自己的故事。如郭沫若的《牧羊哀 话》中老妈妈讲述自己一家与主人家的悲惨故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1919) 中程叔平讲述自己爱而不得、得非所爱的故事,王统照的《钟声》(1922)中T君讲述自 己被命运所迫,有家难归、恋爱不成的伤心故事,鲁迅的《在酒楼上》(1924)中吕纬甫 讲述自己违背初衷、敷衍度日的悲凉故事,郁达夫的《杨梅烧酒》(1930)中“他”讲述 自己悲惨无奈的生存境遇,蒋光赤的《鸭绿江上》中李孟汉讲述自己的恋爱史,老舍的 《歪毛儿》中仁禄自述经历,施蛰存的《桃园》(1931)中庐世贻自述多年遭遇,小酩的 《妻的故事》(1925)中妻子讲述自己从前与小和尚两小无猜的故事,沈从文的《猎野猪 的故事》(1927)中宋妈讲述自己猎野猪的故事,苏青的《歧途佳人》中符小眉自述身世 ,许地山的《商人妇》惜官讲述自己寻夫被卖、颠沛流离的遭遇,庐隐的《灵魂是可以 卖吗?》荷姑讲在工厂的非人遭遇,巴金的长篇小说《海的梦》(1932)中,“她”叙述 自己的解放奴隶的奋斗,等等。这类小说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听者“我”与讲者他/她形成潜在的对比。“我”虽然没有讲述自己的故事,但 “我”并非没有故事,只是没有讲出来罢了,而且“我”的故事潜在地与“我”听的故 事形成一种对照或者对比,共同形成小说的意义。听者“我”与讲者“他/她”具有某 种可比性。《牧羊哀话》中“我”与老奶奶的国家都遭到日本侵略,两人互相尊重,互 相同情;而接下来的8篇小说中,“我”与讲故事的人原来都不约而同是同学,共同的 起点使对方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使读者在对比中领会“ 我”的潜在故事。如《在酒楼上》中,吕纬甫是“我”的同学,他曾经激进,具有社会 抱负,最终却违背初衷,去教授自己反对过的东西。“我”的故事是没有讲出来的,但 从零星的透露中,也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我”也离开家乡外出谋生,“我”也从家 乡“搬得很干净”,回到家乡后,“我”也无处可投,一样住旅馆,一样手头不宽裕。 “我”这个没有讲出来的故事仿佛是吕纬甫故事的伴奏,使小说显得蕴藉丰厚。而巴金 的《海的梦》的《前篇》中,作为犹太人的“我”也以较短的篇幅叙述了自己民族的反 抗故事,正好与她在岛国领导的解放奴隶的斗争呼应,“伴奏”的效果更明显。鲁迅说 :“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注:鲁迅:《怎么 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5页。),此话用来 解释这种情形再合适不过了。
第二,利用“我”拉开读者与故事的距离。在这种“我听别人讲故事”的第一人称叙 述中,“我”虽然对小说中的讲故事者态度不一,有同情乃至完全认同的,如《牧羊哀 话》、《杨梅烧酒》、《商人妇》、《海的梦》,也有持批评态度的,如《妻的故事》 、《在酒楼上》,但这些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我”的存在拉开了读者与小说主人 公及其故事的距离,使主人公的故事处于被观察的客体位置,也就使读者能够采取比较 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它。如果小说中的听故事者“我”本身就持批评态度,这种效果就更 加明显。如《在酒楼上》,如果没有“我”的存在与对比,读者很可能对吕纬甫更多一 些同情而更少一些批评;又如《妻的故事》中,如果没有“我”(丈夫)的存在,读者会 以更加单纯的态度去欣赏妻子与小和尚两小无猜的纯真,而不会考虑妻子的讲述中是否 含有故意报复丈夫的成分。这是一种使叙述客观化的努力。
第三种情形:“我听故事”的一个变体——“我读日记书信”。庐隐的《丽石的日记 》、《曼丽》、《蓝田的忏悔录》都是这样,而巴金的《海的梦》的《后篇》也是“我 ”读里娜的日记。有意思的是,“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仍然可以在《巴黎茶花女遗事 》中找到。在“我听故事”的模式中,“我听”的过程也就是展开故事的过程;与之类 似,在“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中,“我读”的过程也就是展示日记书信的过程,这是 它们和一般的日记书信体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丽石的日记》中,“我”发表丽石的日 记,以证实丽石死于“心病”。在丽石的日记后面,小说又接上开篇的话:“我看着丽 石的这些日记,热泪竟自觉的流下来了。唉!我什么话也不能再多说了”(注:庐隐:《 丽石的日记》,《庐隐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58页。)。《曼丽》和《 蓝田的忏悔录》都是友人带来“我们”共同的朋友曼丽或者蓝田的日记书信,“我”阅 读——即展示日记书信,然后回到小说开头的情境,“我”发表读后的感慨。日记书信 赋予了这些小说抒情感伤的情调。
这两种“我听故事”及其变体“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都使叙述形式更加自然,取 得了逼真性效果。郁达夫曾经抱怨第一人称叙述“我我我”地一大篇,并不自然。相比 之下,“我听故事”与“我读日记书信”却显得比较自然,因为一个听故事的“我”或 者读日记书信的“我”显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又铺垫了故事或者日记书信的出场,避 免使读者感到突然;同时,由于“我”在形式上只是听故事者或读日记书信者,故事是 由另一个人讲或写出来的,这就使故事真实性的责任很大一部分落到了讲或写的人身上 ,然而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可追究的,因此关于小说真实性的疑问也就可以“悬搁”起来 ;另外,“我”往往还具有“证实”故事的功能,从而实现小说对逼真性的追求。在《 山道之侧》中,“我”见过死前一天的奎元,《松树之下》的“我”也偶然瞥见过吴镜 涵,《听来的故事》中的“我”也偶然与孟智辰打过交道,在后二种模式中,“我”与 讲故事或者写日记书信给“我”的人一般都早有交情,就使故事或者日记书信更加具有 可信性,从而增加小说整体效果上的逼真性。
二、“获得手稿”模式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获得手稿”模式的第一人称小说在现代第一人称叙述中大量存在,尤其日记书信体 小说对这种模式运用得多。这种模式的小说存在两个叙述层次:超叙述层(关于如何“ 获得手稿”)与主叙述层(“手稿”正文)。根据超叙述层与作者关系的不同特点,又可 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借用作者名字的超叙述者。超叙述层以序文或者后记的形式出现,超叙 述者以作者的姿态并借用真实作者的名字。如沉樱的《某少女》(二十年代)、郁达夫的 《迷羊》(1928)、茅盾的《腐蚀》(1941)、巴金的《第四病室》(1945)等。
沉樱的书信体小说《某少女》(58封书信),前面有一个署名“沉樱”的《关于<某少女 >》,介绍超叙述者与C君(受信人)的交游、对C君的印象、以及获得书信的经过。后面 有一个附言,说明书信的发表获得了C君的同意并改了名字。《关于<某少女>》看似一 个真实的序言,实际上不过是对序言的戏仿,因为它里面记录的人事实际上是后面的书 信提供的虚构性人物,而且它在情节上也与后面的书信相连,因此,只能把写序言的“ 沉樱”理解为超叙述者。
茅盾的日记体长篇《腐蚀》也有一个仿真的序言。日记前面的序言介绍获得日记的经 过及日记原本的大致情形,落款是“1941年夏,茅盾记于香港。”它在形式上完全像一 个真实的序言,难怪当时颇有些读者信以为真,写信询问茅盾日记主人公赵惠明的下落 。实际上,这是超叙述者借用了作者的名字。有趣的是,1954年《腐蚀》再版的时候, 增加了一个署名“茅盾”的《后记》,却是一个非虚构的后记,两个“茅盾”性质不一 ,前者仅仅依赖《腐蚀》而存在,是“纸上的生命”,后者则是现实中的作家。
无独有偶,郁达夫的《迷羊》也有一个仿真的《后叙》,《后叙》里介绍“我”获得 手稿(主叙述)的经过,以及手稿的主人公王介成后来的事情:王介成被抛弃后大病一场 ,写下了自己荒诞行为的忏悔录,后又到欧洲学画,画作《失去的女人》(隐射女主人 公月英)进入沙龙画展,也算是浪子回头成正果了。在这个《后叙》的结尾,署名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达夫志”。这个“达夫”同样是只与《迷羊》相关的超叙述 者,而不是现实中的作家。
巴金的日记体长篇小说《第四病室》的超叙述《小引》则更复杂一些。《小引》是两 封信,一封是日记主人公陆怀民写给“巴金先生”的,介绍“病中日记”的来由以及其 中主要人物杨木华医生的未知下落,一封是巴金写给“怀民先生”的,介绍寻找杨木华 大夫的多个线索,实际上是升华小说的意义:杨木华这样的大夫不只一个,而有很多。 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这个与小说人物陆怀民通信的“巴金”看成作家本人;另一方面, 这个《小引》中的“巴金”又难以与现实中的巴金难以真正分开。陆怀民的信中有这样 一段话:“直到桂柳沦陷后,我读到你的新著《憩园》时,我才知道你又回到了四川, 而且还继续做你的‘发掘人心’的工作。因此我想起了我那本尘封了的‘病中日记’。 ……我决定把它寄给你看”(注:巴金著:《巴金选集》第6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3~4页。)。这一段话完全符合现实中的巴金的情况,怎么理解呢?本文以为,如 果彻底承认小说的虚构性,就必然承认《小引》的虚构性,不管《小引》中的“巴金” 与实际的巴金多么相似,也只能是一个借用了作者名字的超叙述者。也许是为了平衡《 小引》过于“实在”的意味,陆怀民的信在末尾又荡开一笔,说是去找小说中人物朱云 标的同事、同乡和朋友,询问朱云标母亲的地址,“奇怪,他们都说不知道。”这句话 极有意味,为什么奇怪?无论是按照虚构世界的逻辑还是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都应该 是知道的,然而却不知道。不知道的根源,在于《小引》本身打乱了虚构与现实的游戏 规则,将现实与虚构混成一体,使《小引》的文体属性发生了危机。“奇怪”二字,跨 虚构与现实两界,是站在现实的此岸来关照虚构的彼岸而产生的疑问,意在挽救《小引 》的虚构性,以免误会。
冰心的书信体小说《遗书》的小引虽然未署名,但是里面的16封书信,抬头却都是“ 冰心”,都是宛因寄给“冰心”的信,这就是说,其实超叙述者与主叙述都借用了作者 的名字。
这种借用作家名字的超叙述会以一个比较独立的序言或者后记的形式出现,与正文截 然分开。这些在序言或者后记中出现的超叙述者,他们之所以被赋予作者的名字,一方 面是因为序言等历来是进行真实性叙述的文体,署上作者的名字是自然的事情;另一方 面,超叙述者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真实的作者确实非常接近,真假难辨。这种超叙述 者极力淡化自己在主叙述中的作用,尽量使主叙述以“本来面目”的姿态出现,增强小 说正文的逼真性。他们造成作者只是主叙述的公布者而不是主叙述的作者的效果,减少 自己(作者)对小说正文真实性的责任。
第二种类型:无名的超叙述者。超叙述者不提及自己的名字,这种情形比较多。如鲁 迅的《狂人日记》(1918)、张维祺的书信体长篇《致死者》(1926),郭沫若的《落叶》 (1925)、吴组缃的《两只小麻雀》(1931)、章衣萍的《桃色的衣裳》、沈从文的《崖下 诗人——摘自一个庙老儿杂记》(1925)、白采的《被摈弃者》(1923)、叶灵凤的《女娲 氏之遗孽》(20年代),等等。
超叙述者在这些小引或者后记中(放在中间的很少,我只见到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 》),一是交代如何获得“手稿”,如“狂人日记”是狂人之兄提供给“余”的,《致 死者》中的书信是写信者龚君蕴真寄给“吾”的,《两只小麻雀》则是友人张兆佳从太 太的日记里摘抄给“我”的,等等。二是说明自己对“手稿”的编辑加工,一般都不过 “撮录”、更改人名、或者竟一字不易,或者翻译,尽量使日记书信以“本来面貌”呈 现在读者面前,但像章衣萍的《桃色的衣裳》那样夸耀自己的修改水平的超叙述者(注 :《桃色的衣裳》的小引说:“呜呼,原稿模糊杂乱,不能卒读。经我整理以后,谁还 能看得出我的补写的痕迹,与原稿的真面目呢?”章衣萍著:《情书一束情书二束》,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7页。)极为少见。三是引导阅读,有的是非常含蓄的 “以供医家研究”,或者任读者评判;有的则表示出明显的倾向,对阅读作引导,如《 被摈弃者》的超叙述者“我”表达了对溺死孩子的弃妇的谅解:“伊或者已在上帝那里 得救了。圣处女马丽亚定然证明伊的圣洁,赦免伊的无罪。但这是一件何等悲惨的故事 呢!”(注:白采的《被摈弃者》,赵家璧主编、郑伯奇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3 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422页。)《崖下诗人——摘自一个庙老儿杂记 》的后记中则还有对批评家的要求:“不要写骂人文章,(因为你们太会写文章了,同 诗人一样。)说这庙老儿竟轻视了艺术而看重妇人一件颜色衣!”(注:沈从文著:《沈 从文文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与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第21页。)
这些超叙述者虽然没有署名,但他们力图达到的效果与借用作者名字的超叙述者一样 :与作者尽可能靠近,与主叙述者尽可能疏远,从而“推卸”主叙述的责任。《两只小 麻雀》的超叙述者还表现得煞有介事,在正文中夹一句“(此重复句疑衍)”,俨然确实 与主叙述无关。但实际上,当然不能离开超叙述者来理解主叙述,因为小说是由超叙述 与主叙述共同组成,而不仅仅是主叙述。以《狂人日记》为例,凌宇先生有一个非常透 彻的分析(注:凌宇:《<狂人日记>人物形象与主题的生成机制》,《鲁迅研究月刊》1 992年第11期。)。他将《狂人日记》分为两个叙述层:小说的“题献”(即小序)为第一 叙述层,日记正文为第二叙述层。他认为题献叙述者对日记正文叙述的介入不可忽视,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结构方面,“正是经由‘题献’的叙述者的选录与编排,狂人 的发病——看病——病态抗拒——被关押隔离,构成第二叙述层即狂人日记里的叙事链 条。”二、意蕴方面,题献叙述者对日记人名、物名的虚拟,所谓古久先生、赵贵翁、 大哥、陈年流水簿子云者,具有象征性,其象征意蕴规范着读者阅读的基本方向。三、 叙述立场方面,题献叙述者之所谓“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乃是对狂人叙述立场的一种 认同。题献叙述者即超叙述者对日记正文的介入,是《狂人日记》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 保证。总的来说,虽然各篇小说的超叙述者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超叙述者与主叙述者 的疏离都只是一种假象,一种“推卸”叙述责任的技巧,一种使主观叙述尽可能客观化 的努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听故事”还是“我读日记书信”中的叙述者,以及借用或者不 借用作者名字的超叙述者,他们表面上都把叙述的责任推给了“讲故事者”、日记书信 的作者以及主叙述者,但是实际上,“我听故事”不过是“我”又创造了一个讲故事的 人,“我读日记书信”不过是“我”又创造了一个写日记书信的人,而主叙述者也是由 超叙述者创造的形象,因此,听故事、读日记书信的“我”以及超叙述中的“我”才是 小说文本的实际叙述者。“推卸叙述责任”仍然只是一个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 。这些“推卸责任”的叙述者在理论上有各种可能性,但在实际上却大都表现得比较接 近于真实作者的某些特点,乃至借用作者的名字。他们是一群虚构的、与作者若即若离 的叙述者。
标签: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第一人称论文; 父亲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迷羊论文; 在酒楼上论文; 腐蚀论文; 海的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