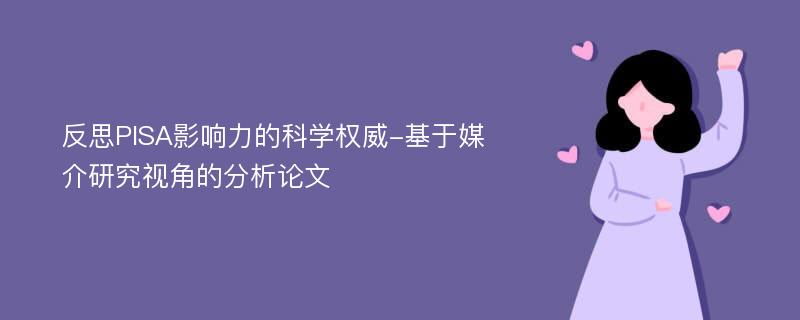
反思PISA影响力的科学权威
—— 基于媒介研究视角的分析
王 熙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 已有的针对PISA影响力的反思大多围绕PISA测评技术本身的科学性,本研究重点关注PISA发挥社会影响力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PISA测评结果的意涵并非既定、也非固定,而是在情境化的解读中不断得以建构和发展变化。由于当今媒介力量的参与,从PISA公布其测评结果到各国各地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变革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直达”与“刺激反应”过程,而要经过复杂的意义阐释与再阐释。媒介所受的外在影响,媒介自身的兴趣与利益诉求,以及媒介受众做出的被动或主动的意义阐释都会增加这种意义流变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PISA发挥影响力的过程远超出实证科学话语的解释力。
关键词: PISA;大众传媒;教育政策;意义阐释;实证科学
一、问题提出
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PISA(国际学生水平测评项目)近年来发展成为国际大规模学生测评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PISA的初衷在于为参与国家或地区提供有关其教育发展状况的客观数据,因此“科学性”成为PISA测评的价值内核,构成其合法性基础。这里谈及的“科学”概念为实证主义范式中的科学,也就是以可观察、可量化且价值无涉的数据,即实证证据,来说明教育质量的层级与程度。由于PISA所使用的Rasch测量模型克服了传统测试样本依赖及缺乏客观等距测试的缺点,解决了大规模测评中的横向可比问题,其测试结果的权威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空前认同。(1) 王蕾,景安磊. 我们从PISA学到了什么——基于PISA中国试测的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72-180.
白内障小切口手法超乳术为标准治疗方法,以超声波为媒介粉碎发生病变的眼内变形晶状体,再以灌溉系统将粉碎组织清除体外,并植入人工晶状体,能够有效帮助患者恢复视力。但手术过程中应用高温裸露针头,操作不当可灼伤切口;而灌溉系统有发生外漏风险[3]。因此术前优化准备、术中优化配合、术后优化管理十分必要,改革护理方案对于保证手术效果意义重大。
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权威,作为教育测评工具的PISA获得了直接影响各国教育发展的力量。PISA在每一轮评估后提供的教育综合排名被视作科学可信的跨国横向比较。对于排名位次不理想的国家和地区来说,PISA排名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压力,促使其开始一系列教育改革。除衡量某国或某地的教育质量水平,PISA还可以基于特定的测评标准说明该地区教育问题的根源,并给出“最佳实践”应有的样态。可以说,PISA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PISA之所以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基于以下逻辑:既然PISA的测评技术是科学的,那么其测评结果就是科学的,所以根据其结果进行的改革就是科学的、合理的。这套逻辑推演凸显科学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技治主义”的理念,即以中立、客观和政治无涉的知识(科学技术)进行社会治理,以实现工业社会的高效运行。(2) 刘永谋.论技治主义[J]. 哲学研究, 2012,(3): 91-128. 不过,这套逻辑推演中有两点值得推敲,一是PISA测评技术本身的科学性是否无懈可击;二是技术层面的科学权威能否为PISA发挥社会影响力的过程提供充分的合理性基础。
针对第一点, 彼得·莫提摩尔(Peter Mortimore)等西方学者指出,PISA试图用同一套标准,甚至同一套测试题目,去反映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生的学业成就并阐释原因,没能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各国各地参与PISA测试的动机。(3) Peter Mortimore, “Alternative Models for Analyzing and Representing Countries' Performance in PISA,”http: //download.eiie.org/Docs/WebDepot/Alternative%20Models%20in%20PISA.pdf. 伴随参与PISA测试的国家及地区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大量非OECD成员国的加入,这种漠视诸多非学校系统因素(特别是文化)的做法无疑存在很大问题。(4) 马健生, 蔡娟.全球教育治理渗透:OECD教育政策的目的——基于PISA测试文献的批判性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9,(3):3-11.
本研究主要针对第二点展开论述,深入探讨PISA发挥社会影响力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人们所采取的政策变革行为是根据其对PISA测评结果的主观解读进行的。这种主观的意义阐释不可能剥离掉个体的经验与价值判断,也无法脱离复杂的社会情境,所以基本不能做到价值无涉,也无法排除各种非确定性因素的影响。PISA发挥其社会影响力的过程可以用拉维兹(Ravetz)提出的“后常规科学时代”(5) Jerome Ravetz,“What is Post-normal Science?”Futures 31, no.7 (1999): 647-653. 的特点来表述,即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当我们考虑到事实和价值相互混杂的复杂性后,就不得不关注“扩大的人员”(包括专家群体之外的各种参与者及利益相关者)和“扩大的事实”(包括实证科学之外的事物,如文化、意识形态等)。(6) Silvio Funtowicz and Jerome Ravetz,“Three Types of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normal Science,” in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 ed. Sheldon Krimsky and Dominic Golding(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92), 251-274.
Clouds approach from southern mountain, heavy snow will fall right away.
二、PISA测评结果的意义生产、分配与消费
除OECD自身对媒体施加的影响,也要看到各国政府或政党对媒介的控制力。为加强对参与国教育政策的影响,OECD一向注重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与合作。除发布测评报告外,OECD邀请参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已完成的、正在开展的和即将开展的PISA测评对本国教育的影响展开集中会议讨论。但即便存在这种紧密合作,各国政府也并没有成为OECD的传声筒,它们有可能基于自身政治或党派目的,借助媒介对OECD的声音进行改编。
PISA发挥影响力的过程就是其测评结果进入社会的意义生产、分配与消费链条的过程,而媒介正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近年来已有一些西方学者借鉴媒介批判理论探讨大众媒介之于PISA的影响。(15) Jill Blackmore and Stephen Thorpe,“Mediating Change: The Print Media’s Role in Mediating Education Policy in a Period of Radical Reform in Victoria, Australia,”Journal of Educational Policy 18, no.6(2003): 577-595.;Paul Warmington and Roger Murphy,“Could Do Better? Media Depictions of UK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esults,”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9, no.3(2004): 258-299.在探讨大众媒介的作用时,一方面要关注媒介被谁控制,为谁发声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关注媒介自身的兴趣与利益诉求,同时还应考虑媒介受众在消费媒介文本时所表现出的被动性与能动性。
首先,媒介往往与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相连,谁能争取到媒体,谁就获得了控制意义生产的话语权。OECD近年来一直争取与媒体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同时向媒介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它向媒介发布测评结果时,并不仅仅列出一串抽象的统计数字,也发布对这些数字的官方解释及政策建议。以2012年英国PISA测评结果为例,OECD发布的报告包括“PISA2012测评结果焦点”(16) OECD,“PISA 2012 Results in Focus: What 15-year-olds Know and What They Can Do with What They Know,”http: //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osa-20120results-overview.pdf. “‘以公平促卓越:给每个学生成功的机会”(17) OECD,“PISA 2012 Results: Excellence through Equity: Giving Every Student the Chance to Succeed,”http://www.oecd.org/pisa/keyfindings/pisa-2012-results-volume-ii.htm. “‘焦点中的PISA’:绩效工资是否提升教学”(18) OECD,“PISA in Focus: Does Performance-based Pay Improve Teaching?”http://www.oecd.org/pisa/pisaproducts/pisa-in-focus-all-editions.htm. 等一系列报告,以及PISA创始人兼教育与技术项目主管安德烈斯·施莱克尔(Andreas Shleicher)在公布PISA测评结果时的演讲稿与幻灯片。其中第一份文件是在OECD正式发布测评结果之前发给媒体工作者的,简要介绍相关的背景信息、英国参与测评的结果、排名及其值得关注的进步或退步内容等,以方便媒体记者提前准备撰写有关PISA测评结果的报道文章。上述报告都尽量做到“媒体亲和”,列有“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对教育实践及政策的启示”等通俗易懂的小标题,还包括一系列简单易读的图示、图标。(19) Sue Grey and Paul Morris,“PISA: Multiple 'Truth' and Mediatised Global Governance,”Comparative Education 54, no.2 (2018): 109-131.可以说,OECD试图在更大程度上掌控媒介的报道口径。
一些实证研究证明,不少国家(如土耳其、以色列、加拿大、英国等)的教育政策变革并不完全符合OECD根据PISA测评结果提出的建议。(20) 吕云震,高益民.PISA结果利用于教育改革的三大误区[J].教育探索,2018, (2):27-31. 例如,施莱克尔解释英格兰2012年PISA测评结果的演讲强调了学校分轨体系(过早根据学生学业水平对其进行分类)对教育公平造成的负面影响。时任英格兰教育部长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虽然也注重OECD提倡的教育公平理念,但在将这个理念具体化时,他更多强调的是增加学前教育拨款和加强对中小学的问责管理,基本不涉及改变现有的学校分轨体系的问题。(21) Sue Grey and Paul Morris,“PISA: Multiple ‘Truth’ and Mediatised Global Governance,”Comparative Education 54, no.2(2018): 109-131.这种对PISA测评结果的意义再阐释,虽然在宏观理念上看似没有脱离OECD的声音,但在提出具体策略时融入了一定的“自创”成分。此外,不少西方学者指出,西方国家的诸多主流媒体控制在保守的右翼势力手中,如英国的《每日电讯》和《太阳报》都带有非常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 保守的右翼势力往往是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他们一方面笃信教育质量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强调竞争对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性。在这类媒介看来,没有在全球教育竞争中取胜,就意味着教育质量已经出现危机,而保持现状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基于这种视角,不少带有右翼色彩的媒体习惯建构“教育危机”的话语,特别是利用PISA排名的直观性来刺激民众对“有危机,必改革”这一逻辑的认同。针对这种现象,公共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断强化某种特定的政策观点,而不是为大众搭建参与政策协商及制定的公共平台。(22) Aspa Baroutsis,“Media Accounts of School Performance: Reinforcing Dominant Accounts Practices of Accountability,”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1, no.5(2015): 567-582.
观察标准由治疗依从性、健康教育知晓程度、住院时间以及护理满意度组成,以患者是否能够遵循医嘱为指南。治疗依从性:对患者进行复查,并选取Likert4级评分标准,为其进行打分,总分数为20分,分数越低表明治疗依从性越低[5];健康教育知晓程度:发放该院自制的健康调查问卷表,主要内容包含病人发病原因、诱发原因、血压、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等8大方面,每一方面的满分设定为10分。
三、PISA测评结果的媒介及大众解读
媒介对政策的影响不容小觑。首先,在政策形成方面,基于金登的“多源流政策分析框架”,PISA测评结果的发布必然借助各种媒介,进入问题流(重大事件及公众情绪)、政策流(既有政策背景)和政治流(政党力量、意识形态等)相互交融的意义漩涡中,形成一种巨大的舆论力量,以触动有关问题进入政策议程,也即开启“政策之窗”。(10) 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22. 当然,历经复杂的意义漩涡,政策文本建构的意义很难与PISA官方报告的“原意”保持一致。其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教育实践者与参与者(校长、教师、家长及学生)往往会根据自身经验与价值偏好对政策文本及相关媒体报道做出更复杂的“再阐释”,这种再阐释的结果很可能不同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更谈不上和最初的PISA官方阐释保持一致。采取后常规科学的立场,我们不能因普通公众的观点不够科学、不够专业,而将其忽略不计。公众所秉持的那种不同于专家的“理性法则”(11) 胡娟.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4,(8):21-26. 承载着普通人对社会伦理与价值的体悟和思考,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力。适用到政策领域,正如斯特恩所说, 政策是全社会各个群体进行意义协商的产物,是一种充满修辞性的“文化建构物”。(12) Sandra Stein,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Policy (New York and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1), 1. 相比于其他政策要素,政策文本的意义是最难以掌控和命令的。(13) Ibid.,6. 由此应认识到,PISA发挥影响力的过程并不完全掌握在OECD或各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手中,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还是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及媒介传播问题。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明这种复杂的意义发展与变化过程,本文借鉴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的概念,将话语实践定义为文本意义的“生产”“分配”与“消费”。(14) Norma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3), 79.这是有关意义从哪来、到哪去、经历何种变化的过程性与情景性问题,其焦点问题是:什么人,凭借何种身份参与到意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中?他们如何对各种意义要素进行选取、剔出或重新搭配组合?何种社会力量参与锻造了特定的意义要素间的搭配组合?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实践”对传媒研究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为媒介运作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社会情境中的意义生产、分配与消费。
PISA测评结果是一系列数字及文字说明,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符号或者最为广义的“文本”。哲学的语言转向使我们看到,文本并不是一种用来呈现先在、外在于它的所谓客观世界的透明介质,其意义并非既有、固定,而是在个体情境化的解读中被赋予的,并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在描述PISA产生的影响时,众多学者聚焦于各国教育政策的变化,因为PISA似乎触发了一个所谓“全球教育政策领域”的形成。(7) Youl-Kwan Sung and Yoonmi Lee, “Is the United States Losing its Status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pariso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3, no.2(2017): 162-179.如果我们秉持一种线性的、封闭的政策研究视角,就会将这个过程描述为:OECD发布的PISA测评结果首先影响到政策制定者的观点和行动,形成新的政策文本,而后通过一种“教学式的、家长式的”政策传播与执行路径影响广大的教育实践者与参与者。(8) 胡娟.专家与公众之间:“后常规科学“决策模式的转变[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8):21-26. 这种“信息直达、刺激反应”的逻辑忽视了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性,同时忽视了在当前这个大众传媒时代中意义流转的新特点。诚如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言,生活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不可能亲身感知到所有与其相关的事物,只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信息供给机构——公共媒介,依赖公共媒介对社会现实的再现。(9)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22),20.
本文借鉴了王建,张卓《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一文中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研究金融支持的产业影响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假设生态经济产业中的企业生产近似的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综上,在PISA发挥影响力的过程中,任何数字、文字及图表的意义都会与特定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每个社会成员的经验和动机发生碰撞。这些都有可能使PISA发挥影响力的过程偏离实证科学的轨道。既然各国教育变革受到了PISA之外诸多要素的影响,那么PISA测评自身的科学权威无法独立支持各国教育变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媒介作为单纯的政府或政党传声筒。媒介生长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无论是出于迎合受众的需要,还是受媒体人自身的文化心理的影响, 媒介做出的价值选择都带有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文化色彩。例如,韩国学者分别在2001、2009年PISA测评结果公布的后续三年中对韩国主要纸质传媒进行研究,发现尽管美国在PISA排行榜中表现平庸,但其教育政策及实践依然是韩国媒介报道的主角,且多为褒扬之辞,认为有关特许学校等政策可以为韩国自身的教育改革提供重要参考。相比之下,取得优异成绩的芬兰和中国上海,尽管其排名得到了韩国媒介的报道,但具体教育政策与实践很少被提及。(23) Youl-Kwan Sung and Yoonmi Lee, “Is the United States Losing its Status as a Reference Point for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parison? The Case of South Korea,”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43, no.2(2017): 162-179. 为什么韩国媒介如此偏好美国教育呢?研究者推测,这与战后韩国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一直追随美国有关。“学习美国”似乎成为一种文化惯性,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追求。媒介的文化视角不但影响它选择去报道谁、不报道谁,还影响到其具体报道视角与遣词造句。在有关PISA测评结果的报道中,如何阐释本国与他国的成败一向是关键议题。弗洛里安·沃多(Florian Waldow)等人针对澳大利亚、德国和韩国的几份重要纸质媒体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对芬兰及上海在排行榜上所处的冠军位置具有不同的报道视角。澳、德两国主流媒体大多将上海的成功与一位华裔作家的畅销书《虎妈战歌》联系起来,认为上海学生取得的好成绩正是这本书中所推崇的灌输型与重压型的东亚式教育的产物,虽然看起来光鲜,却违背基本教育理念,甚至违背人性,因而并不可取。相比之下,芬兰这种强调教育公平、强调学生能力培养的教育才应该被视为学习的榜样。作为排名同样比较靠前的东亚国家,韩国在描述上海和自身的教育质量时没有完全倒向负面,但也存在不少贬低的声音,且与澳、德两国的批评角度相似。(24) Florian Waldow et al., “Rethinking the Pattern of External Policy Referencing: Media Discourse over the ‘Asian Tigers’ PISA Success in Australia, Germany and South Korea,”Comparative Education 50, no.3(2014): 302-321.在媒介报道中,他们对PISA测试结果——抽象统计数据——的解释基本是一种经验性的评论,没有列出系统的科学证据,也缺乏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不少学者及媒体人似乎很难跳出传统东方哲学的文化思维,即把非西方世界视作与西方决然对立的文化体系,二者之间毫无共性可言。上海所取得的成绩似乎只与东方文化传统及所谓的民族性格 (如勤奋)有关,对西方不具任何解释性,亦无可借鉴性。这种东方学立场无疑是一种并不理性的刻板印象。(25) Keita Takayama, “Beyond Orientalism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Challenging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American Education,”Asia Pacific Journal of Education 28, no.1(2008):19-34.
首先,水资源的商品化未必与公共信托存在必然的冲突,譬如,水资源的商品化可以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借此降低人们开发新的地下水资源的动力,进而实现水资源的环境保护目标,因为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一定会减少水资源遭受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缺乏水权交易市场,那么政府想要减低地下水资源的抽取量以保护水资源环境,必须采取强制性的限制措施,但是这通常会遭到现有的水资源使用者的反对。借助水权交易市场,政府的环境保护和用水者的用水需求之间的矛盾可以化解。比如,为了保护水资源环境,政府可以从用水者那里购买多余的水,并将这些水引入河流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励用水者节约用水,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河流的水资源环境。
出于对符号之积极建构性的理解,我们应意识到,媒介对事物的呈现并非完全受控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既有社会文化等外界力量。事实上,媒介并不总是处于被利用的状态中,其自身的兴趣及发展逻辑也是参与建构媒介文本意义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甚至影响到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便其影响方式很可能非常微妙。一味迎合大众品味必然损害媒介报道与评论的专业性,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列举了媒介非专业性的具体表现。例如,根据费尔克拉夫的观点,区别于学术报告,媒介文本习惯于用“表现逻辑”(如通过直白易读的数字、图表表达意义或在文本中使用排比等修辞手法)替代“解释逻辑”(即枯燥的证据阐释与逻辑推演过程)。(26) Norman Fairclough, Analyz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zing for Social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2003), 94-98.以“表现逻辑”为主的意义表达擅长鼓动情绪,而不是阐明证据、论证观点。媒介文本会对相关事物的复杂描述进行缩减、浓缩,使因果关系简单明晰,达到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效果。相关实证研究指出,媒介在判断新闻价值时通常会偏向那些能够给读者带来惊讶的,具有鲜明褒贬色彩的,与社会或政治精英高度相关的信息。(27) David Weaver, “The Importance of Rhetoric,”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no.1(2007): 142-147;Robert Entman, “Framing: Towards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no.1(2007): 163-173. 具体到有关PISA测评结果的报道和评论,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多家电视及纸质媒介的研究指出,相关文本往往把重点放在有关排行榜名次的描述上,凸显进步或退步的幅度,夸张“危机”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渲染责任问题,对既有政策或特定政党及政治人物的执政理念提出批评。这类媒介报道缺乏的是系统的数据分析,深入的情境分析以及批判性思考。(28) Aspa Baroutsis and Bob Lingard, “Counting and Comparing School Performance: An Analysis of Media Coverage of PISA in Australia 2000-2014,”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32, no.4(2017):432-449.媒介“刺激眼球”“吸引眼球”的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受众的阅读与文化欣赏习惯。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理论,长期消费简单、轻松、刺激的媒介文本,受众极易养成一种“懒得费力”和“心不在焉”的心态,无意识地回避严肃的、带有批判性的阅读与思考。(29) Theodor Adorno,“On Popular Music,” in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4th edition),ed. John Storey(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1998), 64-72.当每个普通人的媒介消费习惯不断固化去严肃性、去专业性、去批判性的社会文化时,大众媒介就更难跳出这种眼球逻辑。
上述引用的文献大多针对传统媒介,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较少关注新兴的社交媒介。埃玛·罗恩(Emma Rown)指出,PISA测评日益受到关注的影响力正巧伴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网络传媒技术大发展。(30) Emma Rown,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 the Intangible Economy of Education Reform,”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40, no.2(2019): 271-279. 相比传统媒介,社交媒介为受众提供了很多的自主选择信息、传播信息、分享观点的机会。这种高参与度看似能够帮助受众摆脱媒介的控制,获得思想的自由,但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让我们认识到社交媒介的非理性色彩。例如,一项针对受众心理的研究指出,社会媒介具有一种“过滤泡”效应(filter bubble effect),即人们在行使自己的选择权时,通常会寻找那些符合自己兴趣与价值立场的文本来阅读和转发,而极少关注自己兴趣之外的主题。(31)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o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2011), 33. 滤泡效应有可能导致个体观点的盲目与狭隘,成为刻板印象的温床,同时也容易造成社会观点的两极分化。社交媒介带给人们一种“点击一下就知道”的便利,但这种便利更容易将受众拖入“懒得费力”的媒介消费状态中,使他们乐于消费那些轻松、易读,带有感官刺激的“软信息”,而远离那些严肃的、较难理解的“硬信息”。(32) Eli Pariser,“Did Facebook's Big Study Kill My Filter Bubble Thesis?” http://www.wired.com/2015/05/did-facebook-big-study-kill-my-filterbubble-thesis/. 这些由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消费习惯很可能使普通人有关PISA测评结果的解读更加碎片化、表面化,甚至娱乐化。以笔者的一项有关中小学教师如何理解PISA的研究为例,教师们大多通过微信朋友圈及公众号中的信息了解PISA测评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说出芬兰和东亚一些国家及地区排名非常靠前,而不清楚更多国家和地区在排行榜上的位置,甚至包括美国、德国和法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访谈过程中,多位教师谈到了他们曾经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的《中国老师来了》这部由BBC拍摄的纪录片。有些教师指出,中国之所以在PISA排名中高居榜首,主要是因为教师的严格负责,正如这部纪录片所展示出的中国教师形象。普通教师是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力量,如果他们对PISA测评结果一知半解或在毫无反思意识的状态下被动接纳媒介的声音,那么PISA对各国教育实践的科学指导作用必然要受到质疑。
四、结语
PISA测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影响力的合法性基础是其测量与统计手段的科学性。不过,尽管科学的测评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测评结论的科学性,却不足以保障其结论之应用(也就是各国具体教育实践)的正当性。在大众传媒时代,文本的意义流转相当复杂,远超出实证科学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名义上基于PISA测评的所谓科学的教育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来左右的。本研究质疑PISA影响力的科学权威,不是要完全否定以PISA为代表的诸多教育测评技术的合法性,而是要正视教育测评技术的合法性边界。有关教育质量的把控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仅依赖封闭的专家群体,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价值无涉。借鉴后常规科学理论对技治主义的反思,我们若要PISA测试结果对教育实践产生更理性、更有效的借鉴与指导作用,还须加强公众与专家的沟通,须提升公共媒介的沟通理性和公众的媒介素养。
A Reflection on the Scientific Authority of PISA ’s Influ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Studies
Wang Xi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 100875)
Abstract :Most of the existing reflections on PISA’s influence focus o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PISA assessment technology itsel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ISA exerting its social influence, especially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e meaning of PISA results is not pre-established or fixed, but constantly construc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 Due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media forces nowadays,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PISA results to the reform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not a simple process of “direct information” and “stimulus response”, but a process of complex interpret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The external influences on the media, the interest and interest demands of the media themselves, and the passive or a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made by the media audience will all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such meaning evolution. It is this complexity that makes PISA exert its influence far beyond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empirical scientific discourse.
Key words :PISA; mass media; educational policy; meaning interpret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中图分类号: G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9)05-0091-06
DOI :10.14138/j.1001-4519.2019.05.009106
收稿日期: 2019-07-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路径、方法创新研究”(12JZD00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北京市基础教育对外开放的文化安全隐患与应对策略”(13JYC024)
作者简介: 王熙,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价值观教育和政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