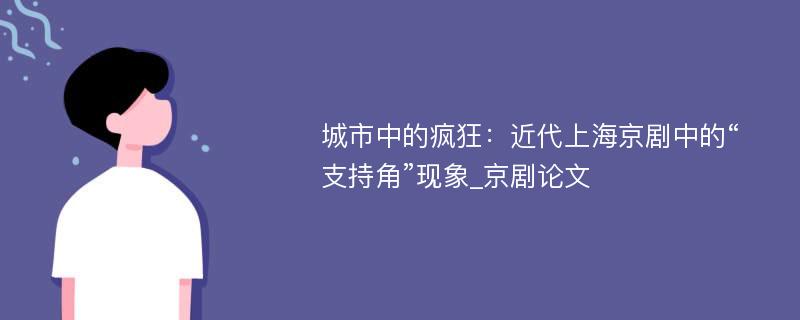
都市里的疯狂:近代上海京剧捧角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剧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都市里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上海,京剧流行,京剧名角云集,捧角是市民一大娱乐,捧角人群之广泛、热情之高涨令人叹为观止,对这一社会现象,罕有学术上的研究。本文从捧角群体、捧角的社会心理、捧角成为都市大众娱乐等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试图借此加深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为发展大众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服务。
一、捧角群体及捧角方式
1867年,京班进入上海,他们演唱的皮黄戏,被上海人称为“京剧”,京剧流行,茶园兴起,上海自晚清开始,“梨园之盛,甲于天下。”[1](P101) 此种态势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80多年间,南北京剧名伶云集上海,粉墨登场。上海市民,对京剧,趋之若鹜,对名角,追捧有加。京剧初期是一种集体型体制,各行当伶人集合为一个整体来完成演出,伶人互相配戏,不分主次。程长庚掌三庆班时,开始组织自己的琴师、鼓师。1896年,谭鑫培通过宫中太监介绍,第一次以戏班台柱角儿的名义,私人聘请场面艺人组班,一般认为这是京剧演出中名角制形成初期的一个标志。[2](p149) 于是京剧中名角开始为观众瞩目,成为戏迷追捧的对象,尤其是旦角崛起后,社会上捧角成为一时风气、潮流,上至达官贵族,下及平民百姓,捧角狂热的情势,上海尤甚。
商人是捧角的中坚。京剧在近代上海发展的80多年里,观剧主体经历了从富商、豪绅、权贵到市民阶层的变化,但是商人一直是戏院观剧的重要成员。除在戏院捧角外,还想要和名角时有往来,是需要一定经济实力的,因而商人捷足先登,上海开埠后迅速成长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各地来沪商人很多,他们成为捧角的中坚。清末,由于富商们在戏园挥金如土,戏园即有“销金窟”之称。商人捧角往往一掷万金,花费惊人。张文艳为南方早期享誉最盛的坤伶,二十年代初,煊赫一时,好事者册封为“文艳亲王”,张文艳在共舞台时,富商曹某是捧她的健将,最有趣的是,与曹寓住一栋楼的各地客商,不管曹认识与否,曹均一律请到共舞台观剧。客人少的时候,则叫茶房厨役去充数。曹因为经常在“新利查同兴楼”宴请客人,久而久之,那里的侍役下人都与曹很熟,曹也经常送去戏票数十张,让他们前往共舞台看戏。“总计张在共舞台出演数年之久,曹氏所耗折资殆不下两三万金矣。”[3]
银行界的金融巨子也是捧角的急先锋。近代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金融人才云集,他们醉心于对京剧名角的追捧活动,如梅兰芳的经济支柱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冯耿光,梅兰芳获冯耿光赞助得以出国。银行界的领袖人物,生活优裕,举止豪阔,要想捧什么角儿,只要打电话到戏院留几排座,或几个包厢,戏馆老板必定检优等座留下来。
文人是捧角的又一重要力量。文人虽然没有商人那样强大的经济实力,以金钱为后盾,但文人有笔墨作为杀手锏,他们喜欢舞文弄墨,挥洒风流。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因为有一批文人追捧,所以也能跻身名旦行列。在上海捧荀的人被称为“白党”(荀慧生艺名白牡丹),而“白党”中坚人物如沙大风、杨怀白、鄂吕弓、舒舍予等都是一介书生。文人的力量不可小觑,它既能使一个名伶声誉陡降,又可使落泊者一举成名,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言菊朋在上海的遭遇颇能说明这些文人的能量。1931年5月,言菊朋与荀慧生来上海同隶大舞台演唱,当时苟慧生已跻身“四大名旦”之列,且有“白党”力捧,声势惊人。而言菊朋演唱时,捧荀的戏迷故意姗姗来迟,所以场面冷清。言菊朋深感无用武之地,加以家庭多故,颇有侘傺之叹。后在谭瓶斋(泽阖)、严独鹤、周瘦鹃、吴性栽、刘豁公、步林屋、汤叔鸾、徐慕云、胡梯维、郑过宜、徐小汀、张丹翁等文人帮助下,借《上海画报》出了一期“言菊朋特刊”,众文人分别画画、吟诗、著文捧言菊朋,免费赠送给观众,于是观众争看言剧,言菊朋因此扭转败局,声势大振。
文人把捧角当作一种陶情冶性的娱乐,所以总免不了吟诗作赋,互相唱和,造成捧角弥漫着一股书香之气。1925年,徐碧云、马连良来沪,徐碧云出场时,台下观众,纷纷投赠银盾、花篮、匾额、书画等物,花团锦簇,错落台前,种类繁多。更有一批文人墨客以书画相赠,步林屋赠匾曰“海风碧云”,刘山农赠联“自怜碧玉亲教舞,为有云屏无限娇”,峪云赠画竹,刘海粟赠画菊,吴昌硕、郑苏戡、朱古微、伊竣斋、唐少川各赠手书挂屏一帧,林屋、峪云赠马连良“白眉最良”四字,[4] 这种捧角方式甚是壮观。
捧角的另一个群体是新闻界。近代报纸作为传播媒介诞生后,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上海看报纸的人相当普遍。报纸刊登的关于京剧名角的花边新闻、逸闻轶事、技艺水准、拿手好戏等都吸引着市民,左右着市民对名角好恶的倾向,从而决定着角儿在上海戏院是大红大紫还是寂寂无闻。1924年,梅兰芳在“新舞台”演出一个月,当时《申报》“自由谈”专栏增辟“梅讯”,逐日跟踪报道有关梅兰芳的言行、生活起居、人际交往、舞台内外的活动、以及家世和逸闻趣事,戏迷们的心跟梅兰芳走,如此密集的跟踪报道,难怪上海人喜欢上了梅兰芳。有如许报界文人为梅兰芳张目,梅之足迹未到,报纸已经开始为梅摇旗呐喊作开路先锋,这么看来“梅之红半得色相歌舞、半得力于捧梅派之鼓吹者”[5] 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普通市民也是捧角重要力量。普通市民没有雄厚的资金来与名角周旋于酒馆、也没有金钱购买银盾、花篮、匾额、书画投赠名伶,有的只是饱满的热情,他们购买低廉的戏票拥挤在戏园的第三层楼上,为自己喜欢的名角鼓掌击节,有了三层楼上的观众的掌声,捧角成了近代上海一种普遍社会现象。
捧角者中还有一群特殊的人,这个特殊捧角群体包括当红权贵、失意政客、遗老遗少、海上闻人、流氓大亨、著名票友。这些人利用自己权利、金钱几乎控制了上海的所有京剧名角,他们捧角的独特方式是收名角为徒弟、义子、干女儿。
捧角囊括了社会各阶层,捧角方式也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
二、捧角现象反映出的社会心理
如此众多的人群津津乐道于追捧名角,这绝不是偶然现象,捧角风气必定有它深层的社会心理。近代中国遭受内外巨大冲击,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变动剧烈而深刻,频率繁复,它对民众日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捧角的社会风气无疑是这种影响的心理反应之一,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较早的一个大都市,市民的心理更能较全面反映出社会变革对他们的影响,察波观澜,可以略窥一二。
其一,在捧角的狂热中借曲解忧抒怀。寄情丝竹、音律、歌舞是人们解忧的一种传统方法,让自己沉浸在音乐歌声中,随着它忽喜、忽怒、忽悲、忽乐,在张弛之中,身心得以“补偿”。京剧在北京兴起、传到上海、又在上海发展,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集之秋,生灵屡遭涂炭,国破家亡,生存艰难,民族和个人的前途无不使国人忧愁,捧名角、听京戏成了人们发泄情绪、寄托情怀的消遣,京剧发展初期的态势与此大有关系。
昆曲衰落和京剧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已经厌倦了雅部靡丽之声,而对花部中“喊似雷”的“黄腔”产生了兴趣,这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有关系的,“简单地说,是时正处于两次鸦片战争前后,面对外侮内患,抗敌御侮成为普遍的民族的心声,程长庚所具有的‘雄风’,其气势自然也就适应了社会心理而成为了一种主流。”[6](P68—69) 后来谭鑫培崛起,程长庚曾经对谭鑫培着意培养,谭也刻意苦学,进步很快,一日千里,程长庚已经感受到谭的潜力,对他说:“子之将来,当一往无前,子之声太甘,近于柔靡,为亡国之音。予死后,子当独步矣。”[7](P42) 随着“前三鼎甲”的去世,“于是幽咽柔嫚代表女性之音之谭窥机乘隙而现矣。”[7](P43) 谭鑫培由此轰动北京剧界,风靡国内,遂出现“有书皆作垿,无调不成谭,”(因当时山东王垿的书法与谭调同为清末二大流行品)庚子事变后,狄楚青慨叹道:“国家兴亡哪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7](P44)
“‘叫天儿’所以能赢得‘满城争说’,正在于他那‘两泪如麻’(《秦琼卖马》词)的亡国之音、衰世之音合于了一种‘世纪末’的情绪,接通了普遍的社会心理,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乐记》)。百姓们对于国家的兴亡,何曾不想管?实在是管不得,便只得在‘叫天儿’的‘近于柔靡’的一唱三叹中寄寓‘谁管得’的痛切之情,而聊以解忧罢了。”[6](142—143) 《李陵碑》、《失街亭》、《打棍出箱》等为谭鑫培代表剧目,这些老生剧的特色“在哀怨悲凉之处,在苍老凄凉之处,而谭之特色,亦在此处。”[7](P54) 屡次的民族反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烽烟四起,民生凋敝,放眼神州,何不起悲愤之情,苍凉之绪!1909年,谭南下上海,以月包银9000元到上海南市新舞台,大受欢迎,“盖沪上人士,久为名大声宏之孙菊仙所饱。一听彼之新调,则不觉眉飞色舞,惊喜交集。”[7](P45) 时世变易,上海一隅,亦非世外桃源,市民心态是一样的,也倾向谭调,孙派因此在上海凋落,孙菊仙本为避谭之锋芒而离京南下上海,而今只好又北返,回到京城。谭调受欢迎,新舞台只得将谭鑫培月包银涨至12000元,打破剧坛历史记录,上海报界尊称谭为“伶界大王”。
20世纪初,帝制灭亡,民国肇造,这样的社会巨变,给民众带来希望,尽管这时军阀混战不断,并没有出现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但是经历了半个世纪动荡折磨,人心思定;“更寄望于新朝诞生后的复兴,更有一种‘政通人和’的心理普求。那么,在‘与政通’的‘音乐之道’里,企求以‘安以乐’的‘治世之音’”来取代“‘怨以怒’、‘哀以思’的‘乱世之音’、‘亡国之音’也就成为必然了。”[6](P144) 于是,梅兰芳取代谭鑫培成为人们追捧的京剧名角。
其二,捧角反映出市民的趋美心理,对美的追求就是对和谐盛世、安居乐业生活的渴望。梅兰芳1913年第一次到上海,一炮打响,声誉鹊起,渐成名角,由此引起京剧审美变革,旦行崛起,京剧由素重生行而为生旦并重。1927年,“四大名旦”经过社会评选而诞生,进而由男旦及于女旦,1930年,“四大坤旦”经过社会评选产生。不管是捧男旦还是捧女旦,它们都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心理,这就是趋美心理。
社会心理的变化是渐进的,旦角逐渐为社会欢迎,适应了民众对祥和、美满、安定生活的向往、憧憬心理。先将谭鑫培与梅兰芳作一对比:1913年5月,广德楼有一次义务戏,谭鑫培还没出场,观众已经鼓噪起来,等梅兰芳赶过来才压住台。[8](P112) “正是因为梅氏的中和之声能普遍适应社会心理的‘治世’要求”,[6](P144) 他得以为各阶层民众欢迎。再将杨小楼和梅兰芳作一比较:三十年代,杨被奉为“国剧宗师”,但是梅杨合作的同一出《霸王别姬》,在1922年首演时,观众在看毕虞姬自刎之后,还会饶有兴味地看下去,因为后面有杨小楼的大战开打,戏一直演到乌江自刎才完;然而到1933年再演,虞姬自刎一过,观众就纷纷“起堂”,[9](P52—53) 人们只欣赏梅兰芳,“国剧宗师”被冷落一旁了,这是北京的情形,上海亦复如此。
20年代《申报》有一篇文章谈到上海人对梅兰芳的喜爱:
“一有梅兰芳到上海来的消息,上海的茶馆酒铺里,大家兴高采烈,谈论的无非是梅兰芳。家人聚话,店伙闲谈,谁也不要提及他?而浴堂里的扦脚匠,搁起了人家的脚,理发店里剪发司,揿住了人家的头,尤为津津乐道。
梅兰芳一到上海,居住的旅社门前,聘他的舞台阶下,人头济济,都想一瞻他的风采,究竟比天上安琪儿胜过几分?
梅兰芳不来上海便罢,梅兰芳既来上海,上海人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所以当去包脚布,也要去看他一回。梅兰芳一到上海,上海人有儿子的,就发生教儿子将来也要唱戏,做第二个梅兰芳的心思。”[10]
这是何等的疯狂,这种社会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重要原因在现代群众的心理趋于爱美的途径,而他的扮相装束做派等项是恰合于美的原则的。”[11] 上海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先锋,它得风气之先,近代科技的发展,声光化电广泛应用,改变着京剧表演的场地、环境,使之日趋美观,这种变化涉及剧场设施,舞台布景,伴奏音乐,伶人服饰、化装,伶人阵容中行当配置等等,并因此改变着京剧欣赏习惯、心理。上海观众形成了自己的戏剧审美心理,“大约沪人士观剧之心理,无论生旦扮相,总以漂亮为第一要义。有色有声方为上选,色胜而声次之,尚在欢迎之列,声胜而色不佳,便入落选之中。”[12]
爱美的心理促使上海观众极端注重伶人的行头是否美观。在京剧界,早期伶人以私制行头为耻,那时,观众也只重伶人唱工。京剧到了上海,为适应上海观众,“沪上伶人,多半着重行头,争为华美,以无美丽行头即不能称为名伶”。[13](P25) 有一年,谭鑫培来沪演《盗御马》,他饰黄天霸,所用的帽冠服装,都很陈旧且为老式样,谭登台后,观众大哗,大有不承认其为黄天霸者然。[13](P25)
20世纪初期的革命狂飙停息后,市民又回到为生存而忙碌的世俗生活状态,捧旦角是市民追逐世俗生活的心理流露。忽视人们的社会心理,认为上海观众喜爱旦角是因为上海懂戏的观众少,这种看法当然失之偏颇。“上海人看戏,先要注重女角,尤其要扮相美丽,举动灵活,行头漂亮,眼锋传情,一家子老老小小、大太太、姨太太都要来赏光赏光。”[14] 这是世俗的审美心理使然。
三、捧角:都市大众娱乐
近代上海商业繁荣,文化发达,城市基础设施完善,人口密集,在都市化过程中,各种娱乐活动也蓬勃而生,捧角是伴随京剧流行而兴盛起来的。捧角群体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捧角已经成为都市社会的大众娱乐,不管是上层社会的名流还是中下层社会的市民,都疯狂地投身捧角这一娱乐大潮中。
有钱有势的名流把捧角视为高尚娱乐,捧角成为他们业余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满足虚荣心理的手段。那些驰骋商场的商人通过捧角放松紧张的神经、缓解疲惫的身心、消解落寞的情怀。而其他诸如政客、闻人等名流们捧角更是为了寻欢作乐,为此,他们花钱如流水,像杨虎这样的捧角家,把公馆当作捧角俱乐部,可以喝酒,也可以唱歌,出入的大多是上流社会的人士;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刘航琛、《申报》社长潘公展、闻人范绍增等等,他们都是捧坤角言慧珠、顾正秋的健将。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请她们吃饭、请她们看戏、赠送昂贵行头、陪她们赌钱玩。1943年,童芷苓与言慧珠打对台时,范绍增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地购买整排整排的票捧场。言慧珠与童芷苓结束了台上的对垒,而台下各自的支持者仍在较劲,捧童芷苓的戏迷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捧言慧珠的戏迷也出钱让她拍了一部电影。[15](P155) 这些权贵以捧角来附庸风雅、竞奢夸富,借此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所谓花钱买乐子。
一般市民把捧角当作闲暇里的消遣,譬如都市里的广大妇女。清末年间,“桂园观剧”[16](P112) 是上海一大娱乐,戏园里士女纷纭,此时期,上海妇女已经是戏园重要的观众,妇女对京剧的痴迷在于它的娱乐性。有自己喜欢的角儿,她们是决不放过机会的,早早就做好准备,甚至彻夜难眠,不管是那些大家闺秀,还是那些小家碧玉,个个梳妆打扮,有如相亲约会。“演戏刚逢二月朝,家家妇女讲深宵。看台宜与戏台近,吩咐奚奴预作标。邻家姊妹各商量,明日如何作晓妆。小婢点灯亲检钥,隔宵翻出好衣裳。一夜芳衾睡不成,晓鸡齐唱报天明。先挑锦帐窗前望,果否何如昨日晴。胭脂微点粉匀粘,早起忽忙启镜奁。”[17](P387) 妇女们的兴奋来自对名伶风采的羡慕和崇拜,她们不仅捧女伶,更捧男伶。“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18] 像杨月楼一样的京角很多,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矫健、英武的形象,吸引了很多女性观众,她们涌进戏园,以致“每当白日西坠,红灯夕张,鬓影钗光,衣香人语,沓来纷至。座上客常满,红粉居多。”[19] 在近代城市化大潮中,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她们成为捧角这种都市娱乐的积极参与者。捧角到极点也会闹出乱子,粤商之女韦阿宝与杨月楼结婚,遭到粤人反对,在上海滩上演一幕风流悲剧。钦差大臣黄开甲遗孀朱桂珍与李春来同居也遭广东人控告,李身陷囹圄,这都是疯狂之至,乐极生悲。
市民捧角娱乐性是很明显的。女伶登台演剧扩展了戏剧舞台对美的展示范围,进一步增强了戏剧娱乐功能。于是人们对女伶演戏趋之若鹜,以求声色之娱,此种享乐迅疾风靡沪上,君不见“红氍贴地,翠袖场(扬)风,绕梁喝月之声,拨雨撩云之态,足使见者悦目,闻者荡心。……名园宴客,绮席飞觞,非得女伶点缀其间几不足以尽兴。”[20] 再以妇女为例,就整个女性群体来说,她们进戏院看戏的历史是很短的,艺术欣赏水平自然低,娱乐是主要目的。“女看客是刚刚开始看戏,自然比较外行,无非来看个热闹,那就一定先要拣漂亮的看。像谭鑫培这样一个干瘪老头儿,要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看了是不会对他发生兴趣的。所以旦的一行,就成了她们爱看的对象。”[8](P115) 在女性观众捧男伶的同时,很多男性观众去捧女伶,“寻常一辈少年郎,喜为坤伶去捧场。金字写来如斗大,崇衔唤作某亲王。”[21](P285) 这同样是为了娱乐。梅兰芳在他的回忆中曾引述过观众常对他说过的话:“我们花钱听戏,目的是为找乐子来的。不管这出戏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险恶,都不要紧。到了剧终总想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把刚才满腹的愤慨不平,都可以发泄出来,回家睡觉,也能安甜。要不然,戏是看得过瘾了,这一肚子的闷气带回家去,是睡不着觉的。化钱买一个不睡觉,这又图什么呢?”[8](P258) 这说明一般观众看戏是为了娱乐消遣,在现实世界里产生的所有烦恼忧愁,在捧角过程中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捧角,让他们暂时忘记了现实的苦恼;捧角,让他们尽情享受世俗的快乐。
人的快乐无非是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方面的快乐也有高雅低俗之别;捧角是娱乐,它也有格调高低之分,捧角为艺术而乐,这是一种高雅娱乐,快乐来自参与。捧角者直接参与到京剧创排之中,捧出了名堂,是一种快乐,成功的快乐。清末民初的闻人大多集新学和旧学于一身,他们凭新学安身立命,借旧学寻求精神寄托,他们喜欢京剧,无非是可以藉此附庸风雅,消遣娱乐。梅兰芳定居上海后,“梅党”人物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梅的戏里,对梅兰芳的剧本、舞台表演、服饰、化装、伴奏的音乐等进行详细讨论。梅兰芳的成败除关系他们的经济地位外,还影响他们的精神生活,梅兰芳的进步就是他们的快乐。
将落魄的伶人捧红也是捧角家的快乐。刘鸿声隶春仙茶园时,甚是潦倒,包银仅为450元,几乎难以生活,戏园园主以其卖座太低,时有怨言。当他与孙菊仙双演空城计,捧刘者台下狂喝其彩,最力者为海上著名票友管海峰,如是三天,连售满堂,刘的包银增加,自此刘走红,“津沽以千金包银聘去,后丹桂第一台又以一千六百元包银重聘其南下,名驰南北,疾革于大舞台,时包银已经挣至八千五百元矣。”[22](P74)
喝倒彩也能找到乐子,尽管有些残酷,却也是捧角家乐此不疲的事业。上海人捧角是捧角的能力,一旦角儿唱做不遂人意,即刻翻脸不认人,管他是谁。京剧大王谭鑫培1912年在新新舞台被上海观众喝过倒彩;黄派武生领袖李吉瑞1925年在上海大新舞台遭遇滑铁卢,观众先是喝倒彩,继之扔以橘皮,最后楼上楼下观众,几走一空。
近代上海是一个商业都市,“商业社会是享乐主义的社会,它需要丰富而刺激性的文化娱乐作为生活的佐料,需要文化为消闲、享乐服务。”[23](P134) 捧角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金钱支配下的娱乐难免出现低格调,低格调捧角是为色而乐,这里有一位观众记录在女丹桂戏园看戏的见闻:入园后即闻喝彩声、掌声,相继雷动,真有一字一叫好,一句一击节之概。他很是奇怪,以为坤班演技之高超过了谭鑫培,友人笑告曰:彼辈俱以目当耳者。其叫好也,用意在五声六律之外,非局外人所得窥测也。[24]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批观众是从娱目而非娱耳角度进戏园,而且是冲着女伶去的,即是为娱乐放松而非欣赏戏剧。女伶的表演引来一些游荡之徒,他们“专务胡调吊膀,不问唱做如何,惟以好姆妈、好妹子献媚。”[25] 从上海市民对四大名旦的态度也可窥一斑,1930年8月,《戏剧月刊》发起征文评论四大名旦艺术高下,1931年1月1日,《戏剧月刊》公布结果:梅兰芳第一,程砚秋第二,荀慧生第三,尚小云第四,原来的梅、尚、程、荀的排序变为梅、程、荀、尚了。有人认为:原因是尚小云所扮演的女子都是良家妇女,在舞台上不能卖弄轻俏曼妙的身段、娇媚艳华的音节、轻巧玲珑的腔调、清丽媚俏的白口了。可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花花世界的上海,人心浮薄,端庄、贞节、朴质、肃静的贤妇,自然不及虚浮、轻佻、放荡、流动的交际花有刺激,也不如活泼、委婉、玲珑、温柔的大家女容易受欢迎。当市民阶层普遍贫困时,他们要求以最廉价的投入获得最大的娱乐,这时,如果社会没有健康力量加以引导,观众的审美情趣就会日趋低下。在商业原则至上,金钱利润驱使下,戏院经营者企图用“有很充分的刺激性或者带着一些肉感的意味”[26] 的戏来招揽观众。1923年和1937年,荀慧生分别在上海亦舞台和天蟾舞台演出了《盘丝洞》,他饰演的蜘蛛精身穿肉色紧身衣,外系红肚兜,妩媚诱人,大受观众欢迎。1941年,吴素秋在黄金大戏院演出《纺棉花》,评剧人说她扮演的王氏“一脸春色,浑身媚骨,两眼流波,双靥含醉”,把《纺棉花》一出小戏演得“七荤八素,弄得万人空巷,春光满园。”[27] 以至《纺棉花》在黄金大戏院演唱了十次左右,场场爆满。
由是,在坤伶崛起后的上海剧坛,不捧男儿捧女儿,蔚然成风,从早期的张文艳到后期张文娟、毛剑秋、金素琴、言慧珠、童芷苓、曹慧麟等众坤伶,捧者甚众。有首新乐府嘲讽捧角家说:“林黛玉十八扯,怡园电灯亮如水,大家争把正座包,万头耸动如毫毛,齐齐心,喊声好,喊破喉咙我不老,眼波溜,眉峰锁,右之右之左之左,老哥适才瞧见否,黛玉分明望着我。”[28] 穷形极相,捧角者寻欢作乐的心态直露无遗。捧角是在商业氛围中成为都市大众娱乐的,这种娱乐文化是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内容,捧角到极端不可避免的与色情相撞,这是通俗文化为追求消费效果的必然结果。
对捧角现象的分析,是从一种独特的角度研究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上海市民的心态,它不仅加深了对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理解、认识,也可为研究今天“追星”、“超女”等都市大众娱乐文化提供借鉴。
标签:京剧论文; 梅兰芳论文; 谭鑫培论文; 京剧演出论文; 上海论文; 申报论文; 纺棉花论文; 言菊朋论文; 戏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