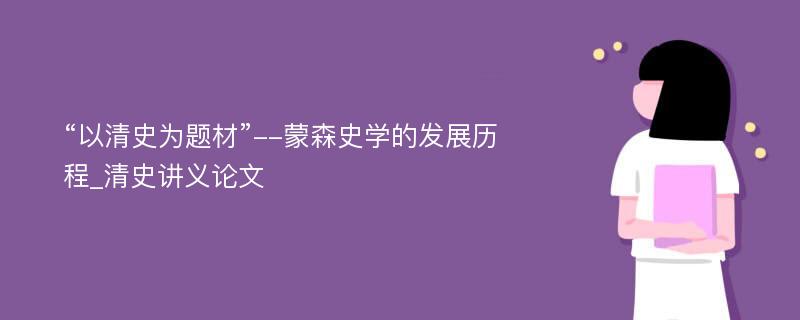
“列清史为学科”——孟森史学的展开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史论文,史学论文,学科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1-0115-11
孟森于1931年执教北京大学史学系①,在此前后,孟森治史特点、旨趣与史学观念皆有重大差异。本文倾向于认为,1931年任教北大,为孟森长达三十年的治史历程之转捩点。为叙述便利计,兹以任教北大以前,为其史学前期,或称孟森早年;而以1931年受聘北大史学系,直至1938年初辞世,为史学后期,或称孟森晚年。在解读孟森前后两期所撰论著的过程中,本文尤其注重孟森相关论述的时间关系,据以展现孟森清史研究得以展开的逻辑过程,并探讨孟森“列清史为学科”之主张的含义,以及孟森在“列清史为学科”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官书私记之间
自来史家所接触与处理之史料,大抵可分为官书与私家记述两类。二者各有优劣,互为短长。傅斯年曾论及二者关系:
大凡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此犹官报与谣言,各有所缺。后之学者,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即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史料不可一概而论,然而此义是一大端矣。②陈寅恪亦有论述:
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幕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类。③按傅陈二人所论官私史料之弊,一一符合于清史史料之实状。在孟森看来,有清一代两百余年特殊的政治与文化环境,导致清代官书忌讳与私记诬枉之病,甚于以往各朝。是以评价官私史料之价值,处理官私史料之关系,轩轻其间,斟酌去取,几乎贯穿孟森史学研究的全部过程。
在1931年受聘北大史学系以前,孟森治明清史,言必称官书隐讳涂饰之病,其所看重之史料,大抵以明清私家记述即所谓明清“士大夫之著述”为主;而在讲学北大以后,孟森对于官书私记之评价去取乃发生剧烈变化,转谓私记“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竟由前期之偏爱私记,一变而为后期之全面倚重官书实录。孟森史学前后两期对于官书私记价值评价取向之重大差异,及其演变转化之迹,实为研讨孟森史学展开过程之关键;苟不明乎此,则近代清史学科产生与建立之过程亦不能厘清,故不能不详加探讨。
1.1931年以前:清代官书“远于事实”
孟森史学前期所撰论著中,其治史重私记、贬官书之强烈倾向,往往可以考见。而在清代官书中,孟森又尤其痛斥《清史稿》《清实录》与清修《明史》隐讳涂饰之病,至于屡以废止《清史稿》与《明史》为言。④
《心史丛刊》所收诸文为孟森初入史学领域从事考证的一批作品,孟森自序该书曰:“兹刊多网罗轶事,非史家必取之资,要于襞绩野史,不为一鳞半爪之谈,譬如博弈,犹贤乎已。”⑤此《序》撰于1916年2月,此处自道《心史丛刊》所收考证文章之旨趣,乃在于“网罗轶事”“襞绩野史”,则《序》已暗示该书对于官书私记取材原则,乃以私记为主。
如果说孟森在《心史丛刊》一书中对于官私史书之选择去取,为所从事之题材所限定;那么十四年之后出版的《清朝前纪》一书,则体现出该时期孟森对于官书私记两种史料之斟酌去取与轩轾好恶的自觉倾向,且与《心史丛刊》相较,更加言之凿凿。《叙言》论:
吾党今日尚能考见清代一二真象,皆前人冒死藏匿,以为我后人稍留根据。易代之后,禁网尽除。吾辈不能继先民忍死留待之意,为之胪列发扬,以成信史。徒据清世矫诬捏饰之本,作成一代之史。是国民果可欺,而国史真无足轻重,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⑥孟森认为,清代屡兴文字大狱,史部典籍遭受空前劫难;清帝又大肆修改《实录》,累朝不断,故此处称《清实录》为“矫诬捏饰之本”。又论:“今从诸家文集中,推考数端,可见清代官书之远于事实。故易代以后,纂修《清史》,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文中所称“一代之史”“清史”,盖指当时甫修成之《清史稿》一书。⑦
1931年以前孟森任教于中央大学之时,认定仅据清代涂饰篡改之《实录》等官书修成的《清史稿》不能成其为信史,否定其作为史书的基本价值,并首次阐述其修史理想,即将来须以清代焚书劫余之私家著述为主要依据,“为之胪列发扬”,修成清代信史。言外之意,即是《清史稿》一书理应废止,将来须另纂《清史》以矫其病。夫子自道之言,透露出该时期孟森治史特点与旨趣,而其要端,则在于承认私记之价值,为作史与治史之所应据;而痛斥请代官书之肆意隐讳史实,甚于以往各朝,应予摒弃。
孟森于其史学前期,治史重视私记,批判官书,不仅载之《清朝前纪·叙言》之空言,而且见之该书考证之行事。观该书,几全为摘抉《满洲源流考》与《明史》等清代官书之颠倒隐讳清先世与明朝往来之事实而作,全书于清修《明史》之严厉谴责,处处可见。如:“《明史》竟隐没净尽,岂得尚为传信之作!”⑧
历来史家多视《明史》为二十四史中上乘史著⑨,而孟森在书中乃倡为《明史》不能传信之说,则将来不仅重作《清史》,即《明史》亦须重修。
尽管孟森在考证清代具体史事时,始终与革命时代的政治宣传保持相当距离(详下文)。但其史学前期对于官私史料的这种态度,却显然部分受到此种宣传的影响。王汎森在其著作中,曾注意到同时代的史家陈寅恪、傅斯年“幼年时代受晚晴革命宣传影响,认为清代官书实录经过历朝改窜,极不可信……”⑩陈、傅二人亦因此认定将来改修《明史》,修纂《清史》,决不可依据清代官书实录,而应利用明清档案,恰可与孟森在史学前期贬官书之倾向相对照。
当时史学界本有轻正史、重野史之倾向。邓之诚在其通史著作《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中曾言及:“若之诚不敏,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之中,则所谓废铜耳。然废铜不为人所重也久矣。”(11)民国史学界风气,于此可以概见。罗志田先生也曾指出,北伐前后的民国史学界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这两种现象并存的诡论现象”(12),史料得到扩充的同时,常见文献反而遭受冷遇。而孟森早年严厉贬斥《明史》《清实录》《清史稿》等正史官书,重视私家著述,与当时学界风气,当不无关联。
2.1931年以后:“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
孟森在史学后期,对于清史史料之利用,已由明代士大夫之私家记述全面转向官书,尤其重视官修实录。
孟森任教于北大时所编《明元清系通纪》(以下简称《通纪》)一书,乃有关清先世史事之史料长编,取材以《明实录》《朝鲜实录》为主,二者虽非清代官修,但一为前朝官修实录,一为清朝属国史料,皆为官书;私家记载则仅仅偶见于《通纪》正编正文下孟森按语、评论或考证之中。单就该书体例而论,其治史特点已与前期迥异。《自序》交代其取材原则:“所取之材,皆刊版行世之书,或官修之《实录》。钞本、秘笈难为征信者,皆不敢随意根据,更无论委巷传说之语……”(13)《自序》撰于1934年9月该书前五卷刊行之时,此时孟森任教北大已有三年。而短短三年中,孟森对于官私史料价值之判断,已发生根本转变。《实录》固为官书,“刊版行世之书”虽包括部分明代士大夫所撰史著在内,但在史料取材上已不占优先地位,仅仅与官书互证而已。对于革命以后出现的清代禁书或其他私家史书之难以征信者,尤其警惕;对于私记中的荒诞流言,则弃置不取。《通纪》为孟森平生用力最深、自负最高之巨著,晚岁精力毕萃于是,则《自序》所言,不仅为《通纪》一书取材之原则,亦可视为孟森晚年治史之旨趣所在。
孟森晚岁讲学于北大史学系,开设明清史课程,编著《清史讲义》与《明史讲义》。前者开篇处即指出作史者取材之原则:“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謏闻野记,间资参考,非作史之所应专据也。”(14)“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盖指档案、科钞、日录、起居注以及实录等官方史料,而非珍本秘笈野史私记。与之相应,孟森在其史学后期还曾指出:“……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15),则孟森此期所立作史者取材之原则,与其史学前期所执“纂修《清史》,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等观点,不仅截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所可异者,在于以上引文所定官私史料去取之原则,竟曾于1931年以前被孟森本人严诋为“是国民果可欺,而国史真无足轻重,非学人治历史者之本怀也”。以上转变,为本文以1931年孟森始任教于北大为时间断限,划分孟森史学前后两期的最重要依据之一。
何龄修曾总论孟森终生治史特点,认为“孟森是重视以正史、以官修史书作为基本史料的清史学家”(16)。若以孟森史学后期治史特点为言,则所言不误。但孟森在史学前期,不仅未曾“以官修史书作为基本史料”,甚且认定“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则孟森三十年史学历程,似不可一概而论。
二、信史理想:“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
孟森在其史学历程中,对官私史料及其史学价值之高下优劣始终持有鲜明的评判标准,对于清史史料中“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的弊病,亦有清醒认知。但在其前后两期的史学研究中,孟森似从未如陈寅恪所言,“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反而在字面上始终给人以厚此薄彼、畸轻畸重之感。尽管如此,于官私史料“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亦即史家得真相、求信史之理想,无论前期后期,孟森竟矢志不渝,一以贯之。
1.传信存真:“列清史为学科之意”
辨析史料,求得信史于“诬讳二者之间”,本为史家治史一题中所应有之要义。但孟森在其长达三十年的史学历程中所反复重申、孜孜以求的信史理想,却有其特定的语境与内涵。
孟森至迟于20世纪30年代初,即已将建立清代信史目为清史学科得以存在的最重要依据与宗旨,将传信史、存真相视作清史学者最重要的职责,信史观念已被孟森提高至建立清史学科的层面上加以论述。根据清史史料之特点,孟森冷静地指出,建立清代信史,一方面固须揭发清代官书涂饰隐讳之病;另一方面,揭发清代所讳之史事,并非以攻击清朝为本意,乃以实事求是、“维持史学”是为本,防闲私记诬枉之弊。孟森尤其反对“快种族之私”,一方面与当时不负传信之责的小说家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与辛亥革命后清史领域的民族革命史观保持相当距离。
孟森甫踏入史学领域,即于《心史丛刊序》中首次阐发其信史理想:
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盖无一事敢为无据之言,此可以质诸当世者也。(17)落实在具体史学问题的研究之中,则须言必有据,防闲荒诞不经的野史传说。孟森盖欲以《心史丛刊》一书之绵密考证,作为学界得清史真相,传清代信史的典范,展示其传信史之法,是亦为孟森撰作《心史丛刊》诸文的主旨所在。十余年后,孟森撰成《清朝前纪》,重申信史之旨:“故易代以后,纂修《清史》,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此吾党所以列‘清史’为学科之意也。”(18)又以此为依托,首次提出“列清史为学科”之主张,盖将以矫《清史稿》“仅据官书为底本”之病,与“加甚其爱”于清朝之倾向保持相当距离,置清史于严谨客观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使之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与学术声誉,而治清史学科之学者,亦当承担传信存真之责,以期将来修成可以传信之《清史》。
孟森于其史学前期,首揭信史之旨于《心史丛刊》,首倡“列清史为学科”于《清朝前纪》,交相辉映,一脉相承。而《清史稿》隐讳涂饰清代史事,则成为孟森重申信史之旨、建立清史学科的重要契机与刺激。
但孟森从事清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又不止官书讳饰之病而已。两百余年的文化高压,造成清亡以后的剧烈反动,民间歪曲污蔑清代史事人物的委巷传闻、荒诞流言纷纷兴起,层出不穷,而且也波及当时的学术界;加之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在史学中催生出民族革命史观。(19)对此,孟森指出:
且“清史”一科,固以纠正清代官书之讳饰,但亦非以摘发清世所讳为本意。……总使史书为征信而作,不容造言生事之小说家破坏历史大防。其为保护清室之意少,而为维持史学之意多。故虽不信官书,亦不轻听世俗之传说,尤不敢盲从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怂流俗好奇之听。此意愿与我党共勉之。(20)则清史学科又与民间污蔑歪曲清代人物史事之流言传闻区以别矣。该时期孟森治史,虽以偏爱私记为基本取向,但对于私记中羼入的以猎奇妄造为能事之委巷传闻、小说家言,仍予以高度警惕。从史学前期的《董小宛考》《丁香花》到晚年所撰《香妃考实》《海宁陈家》诸文,辟附会传闻、破荒诞野史,构成孟森全部治史历程中的重要题材。
革命前后,史学界出现过一批清史著作,如陈怀《清史要略》(1910年)、吴曾祺《清史纲要》(1913年)、汪荣宝等《清史讲义》(1913年)、刘法曾《清史纂要》(1914年)等。(21)从内容上看,以上著作皆响应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秉持民族革命史观,试图论证清朝必然灭亡与共和国即将诞生兴盛,但却“将反对清朝专制与反对满族混淆起来”(22);又大量充斥委巷传闻与荒诞流言,如《清史要略》一书中,即有世祖出家、乾隆帝抱养于海宁陈家、雍正帝“讳为病殁,实则为某女侠所刺也”等内容(23),按此即孟森所指出的小说家“冀怂流俗好奇之听”,“破坏历史大防”。与孟森同时代的另一位清史学者萧一山,于1923年完成《清代通史》上卷,成就超出上列各书,但以上诸病亦为该书所不能免。(24)当时清史学界之实状,可据以窥其一斑。
孟森自称“不敢徇一时改革之潮流,有所诬蔑于清世”,即是须将严谨客观的学术研究与革命时代的反满政治宣传严格区分,摒弃私家记述中“加甚其憎”于清朝的无根流言。则孟森于学界首倡清代信史一说,迥异于时流,可谓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明乎此,方能充分理解孟森“不欲随波逐流”“列清史为学科”诸语之真切含义。孟森终身所致力的近代清史学科,与严谨的清史研究,乃是在官书与私记(尤其是私记中的委巷传闻)、清代官方对于自身历史之隐讳涂饰与清亡以后民间流言传闻对于清代史事之污蔑歪曲的高度紧张中逐步展开的。
孟森对清代信史之追求,至晚岁亦不稍懈怠。孟森晚年撰成《明元清系通纪》一书,自信早年反复阐发的信史理想业已实现,两百余年以来尽遭清代隐讳的清先世信史业已完成,称此书“于清室之神秘,业尽发之”,可“与举世认识此一朝之真相矣”。(25)《清史讲义》论及清修《明史》所隐讳之史事,亦曰“此今日始大发现,而以余为发现最多”(26),自负之意,溢于言表。可见建立清代信史,祛除清史史料中讳饰诬枉之病,为孟森终生史学历程最重要的学术追求与精神动力之一。
2.钩剔贯串的传信之法
孟森在具体的史学研究过程中,“驰骋于官私记载之中,求断于讳诬二者之间”,逐渐形成其钩索沉隐、成就信史的严密方法。简言之,即针对清史史料之特点,于“旁见侧出之文”,或“不经意而流露者”,“随处留心”,极尽钩剔之能事,最后“贯串成编”,以成就清代信史。此法实贯穿于孟森终生史学事业之中,但与前述孟森对于官书私记去取与评价倾向的前后转变相应,在1931年任教北大史学系以后,孟森钩剔信史之法,亦由前期之依赖明清士大夫著述,转而问津于清代官书。
较早论述该法的是孟森早年所撰论文《奏销案》:“奏销案既不见于官书,私家纪载自亦不敢干犯时忌,致涉怨谤。今所尚可考见者,则多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而亦间有具体纪载之处,盖为文网所未及,仅见于清初士大夫之笔记,今当披沙而得宝者也。”(27)又孟森早年曾在《朱方旦》一文中,曾谈及清初史事“首尾不详”的现象:“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28)孟森认为,清代士大夫或惑于谬说,以讹传讹;或惮于文网时忌,诸多史事不能形诸有首尾之“具体”纪载,又不止朱方旦一人一事而已。《心史丛刊》诸文罗列旧说,爬梳史料,钩剔摘抉,加以贯串,正为详其首尾,成就信史。孟森以此法考证清初史事,在当时即有一定影响。梁启超曾谈及孟森治史成就:“顺治十八年之‘江南奏销案’……官书中并丝毫痕迹不可得见。今人孟森,据数十种文集笔记,钩距参稽,然后全案信史出焉。”(29)“数十种文集笔记”即孟森所披之“沙”,而留心“旁见侧出之文”,排比贯串片言断简,出信史于其中,则为所得之“宝”。
孟森史学前期形成的这一方法,在《清朝前纪》中得到总结:“其尤难者,乃在清入关以后,所有文人学士无敢有牵涉时忌者,惟于诗歌题目、友朋书札之类,无心流露,当时亦莫有知为犯忌者,随处留心,乃得贯串数事。”(30)则直至1930年前后,孟森仍将钩剔贯串的传信之法,施于明清私家记载。依孟森之意,因当时作者“无心流露”,故后世史家须“随处留心”;因其“旁见侧出”、散见各处,故需“贯串成编”。(31)所谓贯串成编,即是将所勾稽之史料排比缀合,比其辞,属其事,使其成为有首尾的“具体纪载”。孟森此期治史,依赖于私家记述,留心于“传状碑志中旁见侧出之文”,或“间有具体纪载之处”,实为清代“官书远于事实”、信史惨遭摧毁之后的不得已之举。
孟森任教北大以后,该法施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晚年所撰《八旗制度考实》中论勾稽八旗信史之法:“但言清事,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于官书中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32)考诸孟森同期其他论著,可知孟森所言,不仅为其史学后期成就八旗信史之法,亦为其晚年据清代官书治清史之通法。(33)与前引文字对照,可知该法之形态与施行步骤,孟森史学之前后两期均未稍变。但孟森传信之法施用之范围,已由私记转向官书。其中原因,在于孟森自信清代官书虽累经有意篡改涂饰,但自撰伪史不能不留下蛛丝马迹,其中必有“不经意而流露”,可供后世史家钩剔贯串者,读史者“随处留心”,即可集腋成裘。
其中,“非从清官书中求之不足征信”,为孟森晚年认识;而“旁见侧出,凡其所不经意而流露者,一一钩剔而出之”,则为孟森早岁治史经历中所形成、而贯穿于其终生史学历程之方法,只不过早岁所“钩剔”者,乃是清代私家记述中旁见侧出之文,而晚年所“钩剔”者,乃是清代官书中旁见侧出之事而已。金毓黻1937年阅及《八旗制度考实》该节文字,称孟森“不惟考八旗事,考其他清初史事亦皆用此法也”(34),是仅仅符合晚年孟森治史路数;其早年并不如此也。察乎此,则孟森三十年治史经历与其清史研究之逻辑展开过程,庶几可以明了。
乾隆时修成的《明史》一书,虽极力隐讳抹煞《明实录》中有关建州女真与明廷征战来往之史事,但因成书后疏于检核,书中仍偶见建州史事数处,而清帝竟未曾发现。如《明史·地理志》《本纪》《列传》未见建州之名,而《兵志》竟有之;明廷与女真征战诸事,偶见于张学颜、李成梁等人《传》中;《朝鲜传》亦有女真史事多处。(35)对此,孟森曾感叹,“当时之君若臣,皆于意想之外,留其所甚讳者于简册”(36),则《明史》漏笔,一一符合于孟森所谓“旁见侧出”“不经意流露”之特征。前文已述及,《清朝前纪》一书钩剔贯串之主要对象,乃在私家记述,符合孟森史学之前期特征;但另一方面,编撰《清朝前纪》之时,孟森已措意于清代官书《明史》中“无心流露”“侧见旁出”的关键处漏笔与前后矛盾,并一一钩剔而表出之,又提前透露出史学后期之旨趣。孟森后此诸著述,取材乃一以清代官书为主,遂将该法由清修《明史》扩展至清代其他官书,至《八旗制度考实》一文,乃有施该法于清代官书的全面论述与总结。由此可以断定,孟森钩剔清代官书中旁见侧出之文字以成清代信史的方法,最先施于《明史》;发现《明史》中建州史事之漏笔,竟成为孟森钩剔贯串之法施用范围由私记转向官书的契机。
三、晚年定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
以上所论孟森史学在1931年任教北大以后发生的重大转变,与孟森晚年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一事有重大关系。由整理档案,孟森始注意于史与史料之区分,遂提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论断;由区分史与史料,又导致孟森对于清代官书尤其是《清史稿》之态度发生剧烈转变,“列清史为学科”在孟森史学后期亦随之重获诠释。
1.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
1922年5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请求将其所辖历史博物馆藏明末及清代内阁档案全数拨归北大,获得批准。6月,总计达62木箱、1502麻袋的档案运抵北大,以史学系师生为主力,北大对明清档案的整理得以轰轰烈烈地展开。(37)孟森1931年执史学系教席以后,即主持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室,除继续整理教育部所拨档案外,又购进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六十余万件,1933年始整理刊印这些史料(38),杨向奎(39)、弟子单士元等亦参与其中。(40)
参与整理明清档案,为孟森晚岁治史经历中最重大事件之一。利用新出档案,诸多清史难题得以解决,随之带给孟森学术眼界、治史眼光及史学观念之变化亦甚钜。通过整理档案,孟森于清代“严正完美”之官方修史制度始有真切体认,由此而认定档案大体可信。档案既可信,则以档案作为(直接或间接)源头的实录、方略、国史、《清史稿》等各类官书,虽因“故意作伪”而有局部隐讳涂饰之病,但就整体而言,仍大致可靠。是为孟森晚年治史由私记全面转向官书之根源。明乎此,则前引晚年孟森“真正史料,皆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所构成”一语之确切含义,方有着落。
孟森晚年曾述及整理档案之心得:
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中国史之系统,乃国家将行一事,其动机已入史,决不待事成之后,乃由国家描写之。描写已成之事,任何公正之人必有主观,若在发动之初,由需要而动议,由动议而取决,由取决而施行,历史上有此一事,其甫动至确定一一留其蜕化之痕迹,则虽欲不公正而不能遇事捏造,除故意作伪之别有关系者外,国事之现象,如摄影之留真,妍媸不能自掩也。……中国有史之系统,严正完美,实超乎万国之上。(41)晚年孟森在接触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日渐认识到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于后来人记当时事,其主观色彩大为减少;档案之发生与形成,除开少数“故意作伪”之特例,大体仍“如摄影之留真”,“不能遇事捏造”。
王钟翰曾回忆孟森于1936年秋赴燕京大学与邓之诚、洪业座谈一事,会上三人论及档案史料之价值,孟森“大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而邓、洪则指出“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42)孟与邓、洪二人争论之焦点,在于档案可信与否。王氏回忆,恰可与上引孟森对于清代档案价值之论述相参证。
何龄修曾指出,孟森所以倚重官书,在于清代官书有两大优点,其一为“一朝大事基本齐备”,二为“纂修多本档案,有较高的准确性”。(43)何氏所强调的两点,前者即孟森所论“出于史中某一朝之本身”之义,为官书相对于零散片断的私家记述之优长;后者则来自档案“如摄影之留真”的特点。
晚年参与整理北大档案,孟森学术眼界亦大为扩展。素以清朝入关前史为主业的孟森感叹道:“社会风俗之史料,向来无人注意,今者整理档案,始知其重要,异日编史大可利用之也。”(44)可以假设,若非病逝于1938年初,假以时日,孟森史学或将有新的突破,是或为孟森晚年于病榻上所作诗句“卅年襞积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之暗示。(45)
2.史与史料之区分
孟森因整理明清档案,而有“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观点。该说酝酿于晚年,于孟森官书私记去取倾向之转变,所关匪细。孟森任教于北大以后,一改旧日所持摒弃废止《清史稿》之主张,转而表彰该书,措意于其所蕴藏之丰富史料,以为将来编纂《清史》之准备。孟森史学之重心,亦由前期屡屡重申以修成清代正史为理想,向后期以汲汲于搜集保存整理清代史料为职责转变。
1931年以后,孟森对于史与史料之关系等问题,始有较深刻之思考,并留下系统论述:
所谓史料,又分无数等级。其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者,有如塘报,有如档案,有如录供,此可谓初级史料。至入之章奏,腾之禀揭,则有红本揭帖,汗牛充栋,已为进一级之史料。……至修《实录》而一朝编年之史成。逮修正史,则《实录》又成史料。其间尚有《方略》之为纪事本末史,与编年之《实录》,如骖之靳,皆明明史矣,而至正史既行,又退居史料之列。……明乎此,则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46)细绎之,要点有三:其一,史料可分为不同等级,其原初未经史官点窜,即当时人记当时事者,为初级史料,而后屡经整理修纂,则为更高一级之史料。其二,史与史料之关系有相对性,其中“史”为广义,即史馆修纂完成的各体史书。塘报、档案、录供等为最低一级之“史”,而正史为最高一级之“史料”;史书修成后,其所据之“史”书又退居“史料”之席。其三,史与史料之关系又有绝对性,其中“史”为狭义,特指经史馆修纂而成、官方颁布后悬诸令典的正史。即正史一经颁行,所有史书皆退而为史料。以上所引,于孟森早年著述中绝不可见。若非亲身参与清代档案之整理,详悉清代“史之系统”,则孟森于史与史料之关系,或不能有此体认。
其中第三点即“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之义,尤为重要。由“史自史”一义,推出修成清代正史之理想;由“史料自史料”一旨,则引出史家搜集保存整理史料之职责。“不偏废”,盖指修成《清史》,其先必竭力搜罗尽可能完备之史料,以为修史之基础;而搜集史料,又须以修史为目的。“不可求全”,即指纂修正史,自有笔削去取之法,史与史料截然有别,史料整理者与作史者之责,亦泾渭分明,尤不可将所有史料堆砌于正史之中,以坏史法;孟森治史,推重欧阳修、司马光,正在于宋贤作史之法,足当笔削与法戒之责,断非堆砌收合史料于一书之可比:
作史固以笔削为职责,非以保存史料为职责也。……断无收合史料,责史家麕聚于一书之理。自唐以下,史家眉目,终以欧阳、司马为标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47)弟子商鸿逵曾评述此节文字:“窥其旨趣,即撰史必须广征史料,剪裁精当,而后成书。”(48)所谓“剪裁精当”即是史家“笔削”之责,所论甚谛。
“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说,发于晚年,导致孟森史学前期对于清史领域诸多问题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即是孟森史学后期对于《清史稿》一书态度之转变。
1931年孟森北上以前,并未见及《清史稿》其书。据孟森弟子商鸿逵回忆,可断定孟森始见该书,在1932年初。(49)
孟森任教北大后不久即得见《清史稿》,晚年遂有诸多迥异于早年之论述,其荦荦大端,不外乎两点。其一,有清一代,未成正史,而惟有《清史稿》约略接近正史之规模,具备“史”之轮廓。将来修撰《清史》,可以《清史稿》为底本,而参以清代其他史料以为损益。如:“清史今皆只可谓之史料,未成正史。惟《清史稿》为有史之轮廓,后有修订,大约当本此为去取。”(50)其二,《清史稿》一书虽接近正史规模,然于将来《清史》修成以前,则止可视之为“史料”,而不可径认其为“史”,则该书于史学之功用,乃在于蕴藏丰富史料,“供百世之讨论”,供治史者之考订。即使在《清史》已然修成之后,仍不可将《清史稿》束之高阁,只因“史自史,而史料自史料,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如:“总之,《清史稿》为大宗之史料,故为治清代掌故者所甚重。即将来有纠正重作之《清史》,于此不满人意之旧稿,仍为史学家所必保存,供百世之讨论。”(51)以上所引,与孟森早年所持《清史稿》“仅据官书为底本,决不足以传信而存真”之看法相较,不啻霄壤。而贯穿以上所有论述的,恰是“史自史、史料自史料”的观点。孟森于史学前期,直以《清史稿》为“史”,故以信“史”标准衡之,认其不能当传信之责;于史学后期,孟森以《清史稿》为“史料”,故而不再以信“史”作为评价该书之惟一准绳,亦不再以信史观念苛责于国史馆诸人,转而注重发掘该书所蕴藏之丰富史料,以为将来纂修《清“史”》之准备。则“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论,发于晚岁,实贯穿于孟森史学后期有关《清史稿》价值的所有论述之中。
《清史稿》修成颁布以后,社会上因其有“诽谤民国”“反对革命”与“体例不合”等项嫌疑(52),而有查禁《清史稿》之主张。为回应此种潮流,晚年孟森为《清史稿》辩护,不遗余力,又曾作《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开篇即指出“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53),是恰与孟森史学前期要求摒弃废止该书,形成鲜明对比。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较而言,孟森晚年所发诸论,则明显要公允得多。孟森对于《清实录》之评价,亦经历过类似转变。其中根源,在于孟森已认识到《清史稿》《清实录》之源头,为清代档案,档案既可信,则《史稿》《实录》自然亦大体可靠。
总之,孟森“列清史为学科”,以认定《清史稿》隐讳涂饰、不能传信发其端,而以保存《清史稿》,发掘其中丰富史料,“供百世之讨论”总其成。清史学者不可忽略《清史稿》所蕴藏的丰富史料,亦是“列清史为学科”应有之义。承认《清史稿》的史料价值,实际上也强化了清史作为学科的依据与清史研究的严肃性。
前文已述及,孟森早年曾以修史事业深自期许。来北大以后,孟森负责北大史料室,醉心于搜集清代史料,转而以史料之搜集保存与整理者自居,是固与革命后“禁书档案,日出不穷”,(54),新史料不断涌现有关,但晚年体认出的“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之观点,无疑是促成以上转变更重要的因素。
晚年孟森曾感叹:“若夫生今之世,为今之人,有尊重史料之世界潮流,有爱好史料之学者嗜欲,身负保存职责者,宜如何求餍人望,固应惴惴从事矣。”(55)其搜集保存整理史料之热情溢于言表。又尝为国家修史制度献策:“保存史料之职责,今由故宫文献馆专任之,而他学术机关,亦有分任者。尽其力之所至,整理排比,使有秩序,刊布流通,使不放失,供修《清史》之用,并供《清史》成后补苴纠驳之用……”(56)孟森于史学后期已不复侈谈修史之事,而屡以搜集保存、“整理排比”史料,以为将来修纂《清史》之准备为言,前述孟森所谓史与史料“不偏废”之意即指此而言。
《明元清系通纪》即为孟森践行其晚年史学观念之典范。1936年至1937年度,孟森为北大研究生开设“满洲开国史”课程,“课程纲要”中孟森拟定开课办法两种,其一曰:“就《明元清系通纪》已成之部分,加以整理,提纲掣领,将《通纪》作为长编,而成更有系统之一史,或一教本。”(57)该书《自序》亦称:“盖此为清先世长编,后有执史笔、操笔削之权者,就此取材……”(58)则孟森编纂《通纪》之旨趣,在于效法司马光《通鉴》长编之法,为《清史》搜罗史料。二者合并观之,与前述孟森所论史与史料关系之相对性,一一符合。依前文所述孟森晚年史学观念,相对于《通纪》所据以取材之《明实录》《朝鲜实录》中零散的女真史料,《通纪》已为“进一级之史料”,或“更有系统之一史”。及将来《清史》告成,则《通纪》又“退居史料之列”。
孟森晚岁史学观念之萌生,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转变,除了与其参与整理北大明清档案有重大关系外,亦受到北大史学系、国学门教学与研究风气之影响。北大国学门素来注重搜集整理包括明清档案在内的新史料(59),20世纪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因受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影响,亦强调学生史料整理辨析之训练,而放弃朱希祖主持系务时期强调基本知识灌输的做法。孟森北上任教的当年,史学系正在经历由常识教育向学术教育转变的课程改革。(60)1931年9月,史学系公布新的课程指导书,其中即谈及:“史学的步次是什么呢?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61)1935年至1936学年度的《史学系课程一览》也强调史料之搜集辨析等环节在史学教育中的重要性:“(本科)三四年级则注重专门训练。学者选习各专史及专题研究,以充实其知识,培补其学力;更由教者指导,选择题目,从事于史料之搜集、排比、钩稽,史实之比较、考证、论定诸工作,以培养其研究能力。”(62)孟森在史学系所授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明清史、清史研究等四种课程(63),亦是在史学系课程改革与整体风气转变的背景下开设的,在此期间,孟森撰成《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满洲开国史讲义》等授课讲义,以及《明元清系通纪》等论著。作为现代教育学术机构的北大史学系、国学门,其教学与研究,并非以修史为目的,由此推测,探讨孟森晚年在史学上所经历的诸多转变,不能忽视北大学术风气的影响。
要之,“史自史”可对应孟森史学前期之修史理想,“史料自史料”可概括孟森史学后期搜集保存与整理史料之事功。“史自史,史料自史料”一说,不仅预示晚年孟森史学观念之突破,亦可目为孟森终身治史历程之写照。而“不偏废,亦不可求全也”一语,不啻孟森“列清史为学科”终身事业之晚年定论。
收稿日期:2013-03-20
注释:
①有关孟森受聘于北大之月日,今尚不能确指。但孟森于1931年北大新学年开始、秋季学期开学之时,始在史学系讲授明清史,则可以断定。
②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③陈寅格:《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1页。
④《清史稿》修成于民国时期,但其所据实为《清实录》等清代官书,故仍可与《明史》《清实录》视为同类。下同。
⑤孟森:《心史丛刊·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⑥孟森:《清朝前纪·叙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⑦孟森此时尚未见及《清史稿》其书,此事本文第三部分正文及注有考。
⑧孟森:《清朝前纪》,第48页。
⑨参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三一“明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21页;《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二》“明史”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6页;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编第一章《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⑩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58页。
(11)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一《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页。
(12)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3)孟森:《明元清系通纪·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14)孟森:《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15)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清史讲义》第一编第四章,第21页。
(16)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清史论丛》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17)孟森:《心史丛刊·序》,第1页。
(18)孟森:《清朝前纪·叙言》,第2-3页。
(19)有关早期清史领域的民族革命史观,可参见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萌生》,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等论著。
(20)孟森:《清朝前纪·叙言》,第3页。
(21)对于早期清代断代史著作之研究,可参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萌生》一文,收入《五库斋清史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8-23页。
(22)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23)陈怀:《清史要略》,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21、72-73页。
(24)有关该书完成与出版时间等问题,可参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
(25)孟森:《明元清系通纪·自序》,第1页。
(26)孟森:《清史讲义》,第12页。
(27)孟森:《奏销案》,《心史丛刊》一集,第4-5页。
(28)孟森:《朱方旦案》,《心史丛刊》一集,第22页。
(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30)孟森:《清朝前纪·叙言》,第3页。
(31)借用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一文中语,原文为:“禁书档案,日出不穷,贯串成编,亦谈明、清代嬗者所乐闻也。”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32)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清史讲义》第一编第四章,第21页。
(33)可参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3966页;吴相湘:《我的业师:孟心史先生》,《传记文学》(台北)1962年第1卷第1期;孙家红:《师之大者:史学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书品》2007年第2辑。金说之辨析,详下文。
(34)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5册,第3966页。
(35)参见孟森:《清朝前纪》,第2、6页。
(36)孟森:《清朝前纪》,第2页。
(37)郭卫东、牛大勇主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初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资料室藏,第76页。
(38)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39)参见杨向奎、何龄修:《孟森学案》,《百年学案》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40)参见《单士元自传》,转引自单嘉筠:《先父单士元从师孟森先生二三事》,收入何龄修编:《孟心史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2页。
(41)孟森:《清史讲义》,第3-4页。
(42)王钟翰:《孟森先生与邓洪二师》,张世林编:《学林往事》上册,北京: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43)何龄修:《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试论孟森的清史研究成就,为纪念他的诞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惟何先生并未发现,孟森之倚重官书,仅限于其史学后期,本文第一部分已述及。
(44)孟森:《中国历代史料之来源并拟现代可以收集之方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771页。
(45)罗常培:《孟心史先生的遗诗》,《治史杂志》第二期,1939年。尚小明先生《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一文结尾处亦曾引及该诗,以孟森不克完成《明元清系通纪》全书之本事笺释此句,固确,见《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
(46)孟森:《史与史料》,《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765-766页。
(47)孟森:《史与史料》,第766页。
(48)商鸿逵:《述孟森先生》,《清史论丛》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49)商鸿逵:《述孟森先生》,《清史论丛》第6辑。文中回忆:“先生很重视工具书,1932年初到北京大学任教得见《清史稿》,即开始编辑《清史传目通检》……”其中所述孟森赴北大任教之时间不确。但孟森得见《清史稿》在1932年初,则大致可以确定。
(50)孟森:《清史讲义》,第5页。
(51)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711页。
(51)参见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所附故宫博物院呈文,第712-716页。
(53)孟森:《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第690页。
(54)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上,第18页。
(55)孟森:《史与史料》,第766页。
(56)孟森:《史与史料》,第766页。
(57)《史学系课程一览·课程纲要》,《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6年至1937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BD1936015。笔者最早见及该材料,乃在尚小明先生《孟森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一文中。
(58)孟森:《明元清系通纪·自序》,第1页。
(59)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406页。
(60)尚小明:《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61)《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民国20年至民国21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BD1930014。
(62)《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一览》(民国24年至民国25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BD1935008。笔者最早见及以上两条材料,乃是在尚小明先生《抗战前北大史学系的课程变革》一文中。
(63)孟森在北大所开课程,参见尚小明:《孟森在北大授课讲义三种编撰考》。
标签:清史讲义论文; 孟森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清史稿论文; 明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自序论文; 清实录论文; 明清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