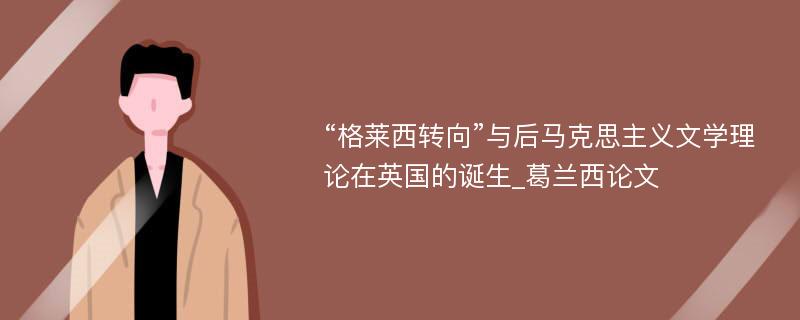
“葛兰西转向”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英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5)07-0125-07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5.07.018 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葛兰西转向等三次理论范式转换。1980年前后,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正是因为受益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才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扬其分别力主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所长,并规避甚至抛弃其所短。与此同时,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与发展也与葛兰西转向有直接关联。很多研究成果尽管注意到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葛兰西转向,但却没有注意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也是追随葛兰西转向出现的。本文正是基于此,考察了葛兰西转向与英国两个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之间的关系。 “葛兰西转向”,最早是斯图亚特·霍尔和托尼·本尼特等理论家在梳理文化研究的历史时提出的重要概念。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指出:“文化研究通过运用葛兰西著作中探讨过的一些概念,试图从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著作的最好要素中推进其思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这一研究领域的需要。”①这是因为,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在‘文化主义’当中,经验就是特定的场地——‘亲历的’领域,意识和产生意识的条件在其中相互交叉;而结构主义则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场所,因为人们只能在各种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感受’和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②与霍尔的观点相似,本尼特也指出:“从更为一般意义上来看,葛兰西著作中的批判精神完全没有大众文化批评家让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态度,同时也不会发展成为一种广受赞誉的民粹主义,在避免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明确的反对。”③针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所存在的不足,霍尔与本尼特都认识到葛兰西转向能够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本尼特指出,葛兰西将大众文化“看作是一个由各种压力和倾向所建构的关系的角力场。这样一种理论视角能够使处于危机之中的大众文化研究在理论与政治方面获得实质性的重构。”④ 当然,正如“文化研究原来起源于文学批判传统”⑤的观点所断定的一样,“葛兰西转向”其实早已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文学研究领域,并以雷蒙德·威廉斯与特里·伊格尔顿之间关于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论争为开端。伊格尔顿在1976年突然以一副阿尔都塞忠实信徒的面孔对其学术引路人威廉斯展开了理论围剿。他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指出:“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作为唯物主义美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之一,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本主义’和唯心论的瑕疵。”⑥伊格尔顿之所以敢于提出如此大胆的论断,是因为在他看来,威廉斯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外,早期还受到利维斯学派的影响,并以利维斯学派的自由人文主义为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观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因此,威廉斯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探索个人感觉经验背后的隐含意义,并将这些意义有机地转化为方法、概念和策略;这也是人们对一个由剑桥学派所培养出来的最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最为自然的期待。威廉斯也像考德威尔,几乎没有使用构建社会主义批评的文献材料——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因追溯社会传统而导致的这种缺失,却成为他在政治上一以贯之的保守表现之一。”⑦ 面对伊格尔顿的批评,威廉斯并没有做出明确回应,但“在1978和1979年出版的两部小说却是对伊格尔顿的最好回答”⑧。这两部小说分别是《志愿者》与《为马诺德而战》,主要论述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借助文化认同保持团结的重要性。《志愿者》主要描写了记者刘易斯·瑞费恩自愿秘密调查一场凶杀案的过程。在为公正而不断追寻案件真凶的过程中,瑞费恩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地下组织——志愿者世界。他从此经常面临在道德良心与对组织的忠诚之间做出抉择的难题:他一方面是凶杀案的局外人和地下组织的揭秘者,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弃原本的志向,自愿成为地下组织的合作者。威廉斯藉此意在说明,人与其所处的社会是无法分离的,即使有时试图保持独立,努力作为“志愿者”或“局外人”,那么这种自愿只是一种“潜在可能,也存在着某些障碍”⑨。在《为马诺德而战》中,威廉斯主要描写了针对在威尔士的新城市规划过程中出现的腐败与投机,马修·普莱斯和罗伯特·雷恩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通过两人对当地人的未来生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威廉斯指明:“为了再次确证某些或者某一可能性,必须紧紧抓住不太明确的文化认同的概念,因为它在稳定性日渐消失且群体无法共享的历史时刻能够带来团结和共同体。”⑩ 与威廉斯的反应不同,安东尼·巴奈特在《雷蒙德·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对伊格尔顿的反驳》中对伊格尔顿提出了强烈批评。他认为:第一,伊格尔顿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只以威廉斯的早期著作为依据对其提出批评。“伊格尔顿的文章显然只对威廉斯著作中的‘第一类’做了评价。”(11)其实,威廉斯的学术著作按时间先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出版于1960年前后的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变迁的著作;第二类是出版于1968年及其之前的论述戏剧的著作;第三类则是出版于1968年以后的研究语言与社会的著作。“戏剧研究著作事实上受到极大的贬斥,因为伊格尔顿似乎将威廉斯的戏剧理论看作是他对其学术兴趣的极不严肃的转移。”(12)第二,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经验”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伊格尔顿尽管正确指明了“经验”对于威廉斯而言在认识论层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方法论层面所存在的缺陷,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问题。因为,“威廉斯对经验概念的使用是从利维斯以及《细绎》继承而来。但是,与利维斯不同,在威廉斯看来,经验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或形而上的价值——主观判断所依赖的唯一发挥规范作用的标准。经验也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他指的是‘突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13) 伊格尔顿与威廉斯及其拥护者之间的论争尽管开始时轰轰烈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还推动了新的理论范式——葛兰西转向的到来。当然,作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理论范式转换,葛兰西转向既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也促进了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首先,葛兰西转向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成功地摆脱了当时所面临的困境,为此后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经过这场论争都意识到,无论是文化主义还是结构主义都存在着无法弥补的缺陷,只有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才可以使他们既能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又能将这两种范式各自拥有的理论活力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因葛兰西理论的独特性及后结构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葛兰西转向也成就了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在关于霸权的本质的争论中,葛兰西确实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水岭:走向一种‘结合原则’。”(14)受这股思潮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本尼特等一批理论家开始解构超验主体、强调话语分析,表现出与威廉斯、伊格尔顿完全不同的理论旨趣。因此,受葛兰西理论的启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有效创新。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则通过解构葛兰西的理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也昭示了葛兰西所开辟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路向的失败。 葛兰西转向使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抽象思想体系向日常体验和话语实践层面转化,并更多地与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结构与功能分析相联系”(15)。葛兰西认为的霸权是:“1.人民大众对于主要统治集团强加给社会的总体趋势的‘自发的’赞同;这种赞同是由统治集团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和职能而享有的‘威望’(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历史地’促成的。2.国家机器实施强制性措施,它‘合法地’把命令强加给那些既不积极也不消极的‘赞同’的集团。然而,它是在自发赞同不能实现、控制和管理处于危机之时在整个社会中发生的。”(16)从宏观上看,霸权理论指明了不同阶级的协商要涉及到经济、政治等复杂的社会结构问题;从微观上看,霸权理论深入到日常生活层面,分析了不同阶级为形成自发“赞同”而在语言与体验等层面所进行的权力协商。霍卢布指出:“霸权这一概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强制性地运用政治社会的国家机器维持现状的方式,并且能够使我们理解,政治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包括教育、宗教和家庭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的微观结构等,如何以及在何处有助于促使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这些意义和价值指向并维持社会上的各个阶层‘自发的’赞同同一社会现状。”(17) 从宏观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带有凝固性质的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的观念”,“这些术语的物质凝固性的意义一直在阻碍着我们”。事实上,基础“是一种动态的、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包含着现实人们和由他们构成的阶级所进行的种种具体活动,以及一系列从协作到敌对的活动方式”,以此为基础才能“推导出‘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18)。威廉斯的这一分析尽管更为符合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无论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动的复杂社会关系,但却为进一步阐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带来困难,因为传统的决定论“不过是使那些具体的、总是相互关联的决定因素变得神秘化而已”(19)。在分析了决定、生产力等相关概念的缺陷之后,威廉斯认为,霸权作为一种“探究方法可以应对同样的问题,而且这种方法更直接地定位于文化过程和文化关系的研究”(20)。这是因为,霸权作为“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构形和文化构形。这种构形确实有效地扩展到并包容了生活经验的全部领域,它确实形成了这种领域,又从这种领域中形成了它自身”(21)。 与威廉斯借助霸权的动态性探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不同,伊格尔顿则从获取赞同的具体方式这一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发挥的作用。在他看来,“我们可以把霸权定义为整个实践策略,统治权力则通过这些策略从被统治者那里获得对其统治的认同”(22)。由此出发,伊格尔顿对上层建筑做了明确分析。“上层建筑把政治的一定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具体化为固定的本体论范围。而且仅当某一习俗或社会机制通过一定的方式支持一系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时,它的行为才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因此,某一社会机制这一时刻是上层建筑的,但在另一时刻却又不是。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一机制的各种功能也许是相互冲突的。”(23)作为具有本体论性质的社会领域,上层建筑能把可能发生冲突的各种意识形态实践集中起来,共同维护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与物质利益。上层建筑之所以能发挥这种作用,是因为“基础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政治力量所不可逾越的外部界限或最终障碍,它既对政治变化所需的动力发挥抵制作用,也在其动力匮乏时揭示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它不论在其他方面对政治产生何种影响或者直接与其达成妥协,但其作用却一直存在”(24)。 从微观上看,葛兰西霸权理论所包含的存在于意指层面的协商意义,促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从语言和意义等层面对日常体验与文学批评展开分析。“霸权或多或少总是由各种彼此分离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价值和实践适当组织结合而成;依赖这些,霸权具体地组构为有意义的文化和有效的社会秩序。”(25)在他看来,霸权既涵盖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又通过将两者融合而形成对它们的超越。因为,霸权一方面“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又不能不总被看做是那种实际体验到的、特定阶级的主导和从属”(26);另一方面又注意到这些主导和从属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实践意识,它们实际上渗透了当下生活的整体过程——不仅渗透到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中,也不仅渗透在明显的社会活动中,而且还渗透在由也已存在的种种身份和关系所构成的整体中,一直渗透到那些压力和限制的最深处——这些压力和限制来自那些最终被视为某种特定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的事物”(27)。霸权在指明文化自身存在权力分配及主导和从属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将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引入现实生活,并强调作为实际被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既涉及到社会的公共领域,也存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因此,霸权“是指一种由实践和期望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覆盖了生活的全部——我们对于生命力量的种种感觉和分配,我们对于自身以及周围世界的种种构成新的知觉体察”(28)。 伊格尔顿主要借助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话语实践的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葛兰西著作对文学批评的重要启示是“把注意力从分析名为‘文学’的客体转向对文化实践的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一趋势在不那么灵巧的生手那里可能很容易被拜物化,正如对一个文学文本中的部分‘假定性’作忸忸怩怩、漫不经心的漠视会为一种新的时尚——把产品分解成过程——大开绿灯。”(29)在提出把文学当作文化实践并分析其背后社会关系的同时,伊格尔顿也意识到其中所隐含的风险是只注重分析文学艺术的物质性,而不关注文本的社会建构过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要关注文学艺术的修辞问题。“‘修辞’这一术语既指有效话语理论又指这种理论的实践”。话语理论“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要把话语和权力的表述进行系统地理论化,并且以政治操作的名义进行:丰富意指的政治效应”(30)。在《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充分贯彻了这种文学批评观念,从政治批评的立场上审视了20世纪的重要文学理论流派。“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我用以对抗本书所阐述的这些理论的并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话语——叫它‘文化’也好,叫它‘表意实践’也好,或无论叫它什么,都并非十分重要——它会包括其他这些理论所研究的这些对象(‘文学’),但它却会通过将其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改变它们。”(31) “葛兰西转向”在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开启新的探索空间的同时,也与后结构主义的接合而形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拉克劳指出:“对于我们所喜爱那种特别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来说,葛兰西的中介是至关重要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建构的所有基本范畴都起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解构,而重新阐发葛兰西的范畴一直是我作品的主旋律。”(32)葛兰西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点,是因为霸权作为一种宏观的结构关系,其内部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多重实践。“对于葛兰西来说,即使多样化的社会要素具有惟一的关系同一性——通过连接实践得到的——在每一个霸权形态中必定总会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统一原则,而且它只能是基本的阶级”。“这是葛兰西思想之中持续存在的本质内核,为解构霸权逻辑确立了界限。”(33)霸权中的阶级一旦遭到解构,对其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经济基础也将遭到抛弃。如此一来,“把经济视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就被完全拆解了。因此,后马克思主义“极大地仰赖‘霸权’概念(同样,尤其是拉克劳和墨菲所阐述的霸权概念)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和描述的政治和文化的接合逻辑,以及意义、价值、关系、身份、取向和制度所赖以建立的活动和过程。”(34) 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并解构经济决定论的同时,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霸权看作是一个话语集合,认为其主要发挥主体建构作用。“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和霸权政治理论显然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中获得了灵感,拉克劳和墨菲也是这么公开宣称的,但葛兰西的模式和拉克劳与墨菲的理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强调每一种政治身份都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在围绕对抗性建构起来之前,身份是不存在的。”(35)这与英国接受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独特路径有很大关系。与美国直接受德里达的影响不同,英国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借助阿尔都塞的理论接受了后结构主义理论。“阿尔都塞以去中心化的方式探讨社会构成,将知识看作是话语建构,将主体看成是一种后果。这一切都对英国的后现代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的著作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36)因此,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后结构主义看作是批判超验主体的激进话语。同时,他们在批判超验主体的过程中,“对主体的解构也重构了主体得以生成的话语组织过程”。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以此为基础,“反对广为认可的语言是清晰无误的观点”,“要通过分析心理学的知识话语以及电影、电视、绘画史和音乐、小说、戏剧、诗歌等的具体表意实践详细而又具体地证实话语以及话语构成的物质性”(37)。 霍尔借助拉克劳提出的“接合”概念对超验主体展开批判,并指出其与外部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一种话语的所谓‘统一’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这种十分重要的‘统一’是被接合的话语与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连合环节——一种话语可能在某种历史条件下与某一社会力量连接,但并不是必然地与之连接。”(38)接合既是一种理解特定历史条件下话语聚合的方式,“同时也是询问方式,即询问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何以在特定的事态下接合成或没有接合成某一政治主体。换言之,接合理论询问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何以发现其主体,而非询问主体如何去思考那些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属于它自己的思想”(39)。因此,一种意识形态在建构主体的同时,也“使人们开始去理解或领悟他们自身的历史境遇,而不是把这些理解形式还原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地位或他们的社会位置”(40)。霍尔的接合理论主要凸显了主体建构的动态性、过程性与未完成性,其所谓的主体根本不是一个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主体,而是一个处于永无休止的话语建构过程中的主体,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只能永远处于建构过程中的空洞的能指。 当然,霍尔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解构主体,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探寻主体的话语建构。经过解构,他根本无法再使用“主体”这一概念,而是“转用了‘身份’这个词条。”他指出:“我使用‘身份’来指会合点,即两个方面的缝合:一方面是企图‘质询’、责令或欢迎我们作为特殊语篇论述的社会主体的语篇论述和实践;另一方面是产生主观性的过程,建构我们认为能被‘表达出来’的主体的过程。这样,身份就成为暂时附着在话语实践为我们建构的主体位置上。”(41)作为一个有待分析的意指实践,身份在打破以往相对统一、固定的主体的同时,更为强调主体是随着历史、文化与权力的变化而不断得到建构的。西蒙·弗里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音乐与身份建构的关系:“我想在这里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在讨论身份的时候我们其实讨论某一类体验,或者是处理特定类体验的方式。身份不是别的,仅是一个过程——一种以音乐作为鲜明特征的实验过程。对身份而言音乐似乎是一把钥匙,因为它提供一种如此热情的感觉,对自己和他人、对集体中的主体的感觉。”(42)托尼·本尼特也指出,美学作为一种建构主体的技术,可以“被看作是建构个人的一种方法,它就像普通的政府机关及其规程一样,积极而又富有成效地规范着绝大多数人的内在品性,用福柯的话来说,现代公民也因此而被建构成功了”(43)。 除此之外,托尼·本尼特还借助话语理论分析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阅读构型理论。“所谓的阅读构型,我的意思是指能够有序组织并有效激活阅读实践的存在于话语与文本间的一系列的限定作用,其能够通过将读者转化为一种特殊类型的阅读主体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文本转化为有待阅读的客体,从而使读者与阅读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44)这一理论在强调文本与读者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努力分析具体的阅读过程所涉及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权力斗争。在他看来,文学文本理论总是将文本看作是一个客观结构、一个拥有有限的内在意涵的生产性空间,读者无论处于何种阅读环境以及对其做何种阅读,都无法跳出文本有限的内在空间,否则就是对文本的扭曲性阅读或误读。基于这样的文本理论,读者要么是处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经验性读者,要么是在具体阅读过程中不断发掘文本的生产性空间的理想读者或隐含读者。文本与读者在此只能作为抽象实体存在,文本及其阅读、读者及其体验都是分离的,根本无法实现相互交融。与之相反,阅读构形理论则强调“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的文本与读者及它们的相互作用。“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45) 注释: ①②[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4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317页。 ③④Bennett,T.1986.Introduction:Popular Culture and "The Turn to Gramsci".Bennett,T.,C.Mercer and J.Woollacott.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Open University Press.p.xiii. ⑤[澳]透纳:《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唐维敏译,亚太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⑥⑦Eagleton,T.1978.Criticism and Ideology.Verso.p.44,p.23. ⑧⑩Inglis,F.1995.Raymond Williams.Routledge.p.252,p.255. ⑨[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11)(12)(13)Barnett,A.1976.Raymond Williams and Marxism:A Rejoinder to Terry Easleton.New Left Review.99.5:p.54,p.52,p.62. (14)[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5)汪正龙:《马克思与20世纪美学问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16)[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译文有改动。 (17)Holub,R.1992.Antonio Gramsci:Beyond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Routledge.p.6. (18)(19)(20)(21)(25)(26)(27)(28)[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89、95、115、120、123、118、118、118页。 (22)Eagleton,T.1991.Ideology:An Introduction.Verso,pp.115-116. (23)[英]特里·伊格尔顿:《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张丽芬译,载刘纲纪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 (24)Earleton,T.1989.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Raymond Williams.Eagleton,T.Raymond Williams:Critical Perspective.Polity Press.p.175. (29)(30)[英]特里·伊格尔顿:《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的批评》,郭国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128、134、133页。 (31)[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206页。 (32)[英]欧内斯托·拉克劳、保罗·鲍曼:《政治、辩论和学术:欧内斯托·拉克劳访谈》,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33)[英]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本文除注释外,统一将“领导权”改译为“霸权”,译文有改动。 (34)(35)[英]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36)(37)Easthope,A.1988.British Post-structuralism since 1968.Routledge.p.21,p.209. (38)(39)(40)[英]斯图亚特·霍尔:《接合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斯图亚特·霍尔访谈》,周凡译,载周凡等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6、196页。 (41)[英]斯图亚特·霍尔:《导言:是谁需要“身份”》,载斯图亚特·霍尔编《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2)[英]西蒙·弗里兹:《音乐与身份》,载斯图亚特·霍尔编《文化身份问题研究》,庞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43)Bennett,T.1990.Outside Literature.Routledge.p.181. (44)Bennett,T.1985.Texts in History:The Determinations of Readings and Their Texts.The Journal of the Midwest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8.1:p.7. (45)[英]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9、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