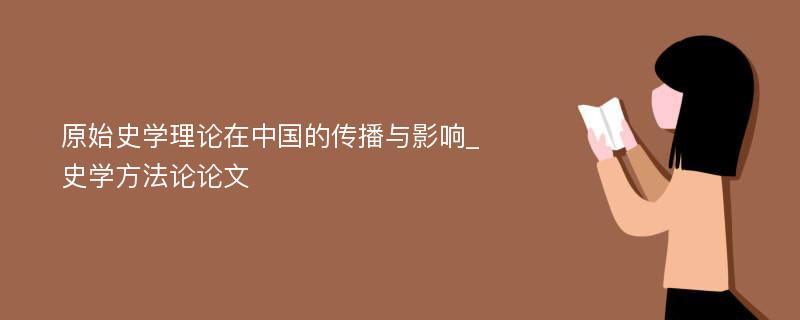
《史学原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7)03—0062—08
在史学专业化进程中,史学研究法或史学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下半期西方史学界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逐渐专业化、学科化。兰克(Leopold von Ranke)通过文艺复兴以来发展形成的语言考证学方法,吸取尼布尔(B.G.Niebuhr)的成就且更进一步有系统地加以应用,而后人又将这些治史方法整理出规范的教本,流行最广的是德国伯伦汉(Ernst Bernheim)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朗格诺瓦(C.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使得培养专业史家有一个基本程序可循。五四前后,我国史学开始追随西方,在走向学院化、学科化、专业化道路的同时,也将西方的史学研究法全面引介到中国,而法人所著《史学原论》则是五四史坛认识西方史学方法论最主要的读本。这本教科书在民国史学界的流传和影响的具体情况,目前人们尚不十分清楚,本文拟对此作较为全面的梳理。
19世纪,西方史学界出版过不少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如德罗森(J.G.Droysen)的《史学纲要》(Grundris der Historik,1867)、道诺(P.C.F.Daunou)的《历史研究讲义》(Cours d' etudes historiqus,1842)、弗利曼(E.A.Freeman)的《历史研究法》(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1886)。但这些作品有的高谈哲理,有的只是讨论修辞,与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史学颇有距离。首次对19世纪科学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作系统整理的,则数伯伦汉于1889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1897年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鉴于伯伦汉之书太过深奥,而又过多讨论理论问题,于是合著了一本专门讲述如何搜索史料、如何鉴别史料、如何综合史料的教材——《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8年G.G.Berry又将其译成英文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出版。《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享有近代史学“双璧”的美誉,成为兰克的“科学”史学的方法论经典。此外,如鲍艾(W.Bauer)的《历史研究法导言》(Einfii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文森的(J.M.Vincent)《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An Outline of Theory and Practice),约翰森(A.Johnson)的《史家与史料》(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弗领(F.M.Fling)的《历史方法概论》(The Writing of History),也都奉前者为圭臬。
《史学原论》的著者秉承了兰克学派严谨的史料批评的治学传统。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以研究法国中世纪的文献和历史而驰名。1887年获博士学位。1909年任巴黎大学教授,讲授古字体、文献学和中世纪史。1913年任国家档案馆馆长。著有《腓力三世的统治时期》(1887)、《历史文献学手册》(2卷,1894—1904)、《中世纪法国生活:从12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3卷,1925—1927)和《法国历史档案》(1891—1893)。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生于法国阿尔代什省(Ardeche),早年就读于法国南部小镇多罗(Tournon)的一所公立中学,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890年被巴黎大学聘为专职讲师。他曾在德国研习史学,后又师从法国史家莫诺德(Gabriel Monod,1844—1912),而莫诺德又是兰克高徒威次(Georg Waitz,1813—1886)的学生。1897年他出版《欧洲现代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 Europe contemporaine)而一举成名,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著作以开阔的视野和客观的风格而著称,如《西洋文化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1886)、《古代东方史》(Histoire des anciens peoples de l' Orient,1890)、《应用于社会科学之历史方法》(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 sociales,1901)、《第二帝国》(Le Second Empire,1921)、《帝国的衰落与第三共和国的建立》(Le Decline de l' Empire et l' Etablissement de la Шe Republique,1921)、《法国史》(Histoire sincere de la Nation Francaise,1933)、《欧洲各民族比较史》(Histoire compare des peoples de l' Europe,1938)。
伯伦汉和瑟诺博司的教本在19世纪末传到日本,20世纪初年又通过日本传到中国,国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史学方法论,但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当时中国史学专业化尚处于酝酿阶段,只有到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建立,现代史学才有了实质性进步。作为衡量现代史学专业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史学方法,在五四前后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不少学人认为:“史学方法就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绩的标准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谬误,他的结论,就可不言而喻了。”[1]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大学的历史系都开设了与史料搜集、史料考证、史料整理等内容相关的课程,如“历史研究法”、“史学通论”、“历史教学法”等,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课程除了讲授中西史学演变大势之外,往往辅之于史学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径。其他一些专史课程也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与甄别。史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基础知识外,还应该进一步认识这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民国史坛方法意识普遍觉醒的背景下,《史学原论》在学人之间广为传阅,成为相关课程的教科书,国人自己编纂的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著作亦以其为参考。
《史学原论》在中国知名度的提高,不能不归功于胡适。1919年胡适运用《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实证治史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成为现代史学的开山之作。在胡适之前,我国通过日本间接对西方实证史学略有所知,然而从来没有人将这套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胡适则系第一人。国人作哲学史的,在胡适之前不乏其人,如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但对材料无所考订,无所剪裁,更谈不上系统。胡适则不同,他具有明确自觉的方法意识,提出史料学的基本规范。首先敢于“截断众流”,撇开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传说,因为这段历史尚不能提供可靠的史料。把史料分为原料和副料,相当于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无论原料还是副料,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史料的方法,就是依靠证据。证据可以从几个方面搜寻:史事的真伪、文字的特点、文体的特点、思想的鉴别、旁证。史料散见于经、史、子、集各书之中,所以需要整理的功夫。整理的方法,有校勘、训诂、贯通。[2] (导言)胡适认为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2] (P22—23)这不仅是做哲学史的方法,也是治史的一般途径。胡适这套方法取于《史学原论》。《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附参考书举要说:“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看C.V.Langlois and Seignobos' 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2] (P23)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由《史学原论》首先提出,而审查史料方法的“校勘”,相当于外形鉴定,而“训诂”即内形鉴定,“贯通”相当于综合工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在现代史学史上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缘于它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现代史学界方法意识的觉醒大半受胡适之书的影响。尔后,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胡适的影响。《史学原论》经过胡适的宣扬,在中国暴得大名,开始在学界迅速流传。
李泰棻的《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于1920年5月,1921年4月武学书馆再版。中国人自己写的史学研究法,第一部应属李氏之著。① 次之即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往研究只注意梁著,而忽视李著。《史学研究法大纲》不仅早于梁著,而且梁著也参考过李著,两者对照,自可窥见一斑。《史学研究法大纲》分为三部分:第一原史,论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史之进化五个阶段:口碑时代、史诗时代、说部时代、史鉴时代、史学时代。而史之目的,则在明变、探原、求例、知来。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阐发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李泰棻在此后不久出版的《西洋大历史·绪论》和《中国史纲·绪论》对这部分内容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述。②《史学研究法大纲》的出版融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旧学新知。李氏对日本史家如濑川秀雄、浮田和民、箕作元八、坪井九马三诸人的史学研究以“幼稚”、“无所表见”形容之,然他在写作过程中对日人著作仍有所参考,尤其坪井《史学研究法》,取鉴之处颇多。如对于“史之进化”,则是坪井氏“物语、鉴、史学”三阶段说的“变种”;又如分叙12类史学之辅助科学,其中如考古学、古泉学,从坪井之书译述而来。I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被李氏列为参考书,讨论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法、史料整理法,就是参考了《史学原论》(英译本)。当然,正处于如日方中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被他列为参考书之一。
民国史坛出版过不少史学研究法著作,然能垂之久远的,莫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3] (P5)这是较为客观的评价。探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论文,数不胜数,不复赘述。此处仅对梁这本书形成的理论来源作一分析。据台湾学者杜维运研究报道,《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少理论本之于《史学原论》,他对两者作了细致的比较,摘出若干段颇为相似的文字,但对梁从何渠道获取《史学原论》一书的理论和方法,没有提供十分过硬的材料。[4] 1918年12月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欧,1921年他开始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恐怕不是应急之作,应该是经过精心准备的结果。1921年前后,《史学原论》在史学界已经相当流行了,成为论史学方法者的必参之书。梁应该不会遗漏了这本重要的书籍,从梁著内容来看,他参考过《史学原论》,是不容置疑的。时人就已指出这点,陈训慈在《史学蠡测》中说:“西史家于内校雠中此点考审甚精,如朗格罗之书详列十条及二十事,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举之若干条多有取于西说而加以融通者。”[5] 他虽过中年始习英文,但尚无法直接阅读英文原著,梁吸收《史学原论》的渠道应是间接的。他在游欧期间,居法时间最长,请了许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学问,“讲义皆精绝,将来可各成一书”,不排除史学方法论为其中之一。同时丁文源又回忆说,他哥哥丁文江曾设法助梁习英文,并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6] (前言)梁启超在给弟启勋信中亦道:“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7] (P822)丁文江曾为梁详解《史学原论》,抑未可知。对于梁如何获取《史学原论》一书的理论和方法,以上也只是一些揣测,但他在写作过程中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梁早年在日本期间就阅读过坪井的《史学研究法》,不过当时他对此书的方法论部分内容没有引起重视。梁氏将史料分为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以内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三类,在文字记录以内者,区分为旧史、关系旧迹之文件、史部意外之群籍类书与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它镂文诸类。这种史料分类法与伯伦汉密切相关,而不是源于《史学原论》,梁是从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获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蕴涵的新知,梁氏从日文本间接吸收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史学原论》日译本《历史研究法纲要》由村川坚固、石沢发身合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当年这个时候,梁正热心于新史学理论的建构,阅读了大量日本史籍,他所读之书大部分出自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在当年就可能拜读过《历史研究法纲要》,只是20世纪初年他热衷于“玄理问题”,而这本书又恰恰排斥理论问题,所以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没有留下此书的痕迹。同样,他对坪井《史学研究法》借鉴也不多。可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方法热的影响下,梁氏准备“裒理旧业,益以新知”,[8] (P2)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所谓“旧业”应该是重读早年看过的《史学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纲要》,而“新知”指的是李凯尔特《什么是文化》。当然,对于近人新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他当不会遗漏参考。③
20世纪20年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的《史地学报》在传播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王庸的《欧史举要》对“史学研究”一类列举了六种著作:Robinson:New History; Langlois and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Nordain: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Seligma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Woodbridge:The Purpose of History; McMurry: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史学原论》榜上有名。他认为研究国故,整理国史,应师法西洋的“探讨编著之法”。[9] 陈训慈在《史地学报》连载的《史学蠡测》,可以“专著”视之,在当时史学界可谓体大思精之作,所举西洋论史学之书籍达22种,包括《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论述了史学定义、史料之审别、史法之运用、史学与其它学科、中国史学史、西洋史学史诸方面。史料之分类循英史家文森(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分类法,区分三类:有意传沿之材料;无意流遗之佐证;碑铭档案。而论史学之运用“皆略遵西说”。[5] 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和张其昀《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两篇文字则是借西洋史法以解读传统史法的先行之作,其意在于张显本土之法,而与罗家伦、李璜、齐思和之辈,一味崇尚西法,其旨趣略有不同。缪凤林指出,自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出版以来,论史法之书日多,朗格诺瓦、瑟诺博司、文森、弗领(F.M.Fling)等人作品“其尤著者”,返观中国,除刘知几、章学诚,“余无闻焉”,因此他为雪耻而“参酌中西书籍”,略述研究历史方法。全文分通论、审判、综合。尤其审判一章言之甚详,理论和方法参照西法,而假以中国典籍中的实例。④ 张其昀做法与缪凤林颇为一致,他在文中说:
余近读西洋史家朗格Langlois,辛诺波Seignobos,文森Vincent,鲁平生Robinson,法林Fling诸氏之书,觉西人所研究之史学问题,二君(指刘知几和章学诚——笔者注)多已道其精微,其不逮之处,则在近世西洋史家能吸收科学发明之精华,故于人类起源、演进及未来诸观念,皆有实证以张其新理,二君则为时代所限,故阙而不详,无足怪也。⑤
张氏以西洋史法“新立条章,区分类聚”,从典籍之搜罗、校雠与考证、论记载之真确、史之义例、史之述作诸方面,综述《史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三书。文末所附“历史事实分类表”,则取历代正史之志与《三通》、章学诚《湖北通志》之类目,与《史学原论》相比较而做成。
五四前后我国史学界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史的呼声愈来愈烈。李泰棻、梁启超、陈训慈、缪凤林、张其昀等人著书立说,无不抱有此理想。李泰棻感叹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着手,认为“欲改旧图新,求合科学方法,则研究法尚矣”,[10] 要整理出一部有系统的国史,只有借助于科学的研究法。1920年9月刚从美国留学回国任教于北大史学系的陈衡哲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现在中国的学界,对着西洋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希望“把最新的历史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做一部通史,和各种分代史及专史,做一部欧洲通史”。[11]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一代学人对史学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要求。传统史学方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然终不能以此开辟出现代史学的一条康庄大道,需要依仗西方“最新的历史方法”,而最后学人多数选择《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作为治史方法的依据。如古史专家徐炳昶回忆1915年在法国读到《史学原论》,“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历史的目的”。[12] (P1—2)所以,这两部书是“现代最流行的历史学著作”,[13] 不仅缘于其方法的可操作性,同时也与乾嘉以来所形成的“土法”,颇有默契之故,一方面可以延续乾嘉时代的考证学风,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史学界企求“科学”的愿望。
五四前后《史学原论》英译本已经在我国史学界十分流行,⑥ 作为著者之一的瑟诺博司也因此在学人间知名度日高。不过,他的名字出现于中文,最早可推至1908年《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文中指出法国现存史学大家有三人,拉维斯(Lavise)、朗波德(Rambaud)、塞纽波(Seignobos),“皆以著述名于世者”。[14]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译刊《现代文明史》,著者署名“法国薛纽伯”。陈独秀认为瑟诺博司是“法国当代第一流史家,本书乃欧土名著之一”。指出著者乃法国文学博士,巴黎大学教授,出生于一八五四年。⑦ 我国史学界早期对瑟诺博司知之不多,但五四以后不少青年学生如李思纯、李璜、黎东方、周谦冲、陈祖源等赴法留学,拜读在他的门下,并且他的大部分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有的被大学选为教材使用,这些多半缘于《史学原论》在国内声誉盛隆之故。
李璜(1895—1991),字幼椿,成都人。1909年入成都英法文官学堂。1918年8月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年底赴法留学,跟随瑟诺博司习史学,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他在法读书期间写了一篇《法兰西近代历史学》,发表在国内杂志《少年中国》,叙述19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发展的概况,尤其对他的老师瑟诺博司等人的“写实派”,多所着墨。李璜转述古朗治(Fustel de Coulanges,1830—1889)的治史方法:
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并且在评定往事里也避去令人所有之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或其它仇雠观念,这些观念不惟无益,而且容易变更遗文的意义。⑧
在古朗治看来,“历史就是遗迹的安排”。而瑟诺博司本古朗治遗说,极力向文件中用功夫。他们以为历史只是安排遗文,成为有统系的叙述,其余皆非史学家所应当闻问。《史学原论》则对古朗治这种著史的方法加以总结。文中还介绍《史学原论》一书的主要观点,如“历史只是遗文的安排”;“历史不是观察的科学,而是推理的科学”等。1924年李璜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祖述师说。1925年他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特别强调近代欧洲的历史研究法,以《史学原论》和《史学方法论》为参考书,讲授史料搜集、批判与综合的基本知识,着重阐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15] (P6)1928年东南书店出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即他在武大和北大所编写的讲义,凡四篇: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历史学方法概论、欧洲文化史导言、历史教学法旨趣。前两篇的理论完全取自瑟诺博司,《历史学方法概论》可视为《史学原论》的一篇“导读”文字,简而得要,颇能体现原著精华。1926年10月这篇文字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
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⑨ 李思纯在巴黎大学三年半,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随瑟诺博司习历史方法。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1926年他将《史学原论》译成中文出版,自己也曾在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论史”课程,所用教材就是《史学原论》。当年金陵大学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课程,讲授历史之重要原则、编纂方法,尤注重史材之分析,研究史学家之理论,并选读其名著,所用教科书即李译《史学原论》。[16] (P182)
1929年清华正式改制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方法”一课,请孔繁霱和雷海宗担任讲授。⑩ 孔繁霱在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等课。他的史学方法课主要介绍《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17] (序)凡重要的历史辅助科学、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孔长期留学欧美,专治史学,继承西方实证史学传统。1922年他在给梁启超信中指出:“史无目的,治史专为治史,不必有为而为。有为必失真,失真则非史。”[18] 他的治学影响到了新一代史家,如黎东方、张永贵都是他在清华的学生,“同受孔先生的影响而服膺史学方法权威拜儿音哈埃姆与瑟诺博司”。[17] (序)稍后,黎东方留学法国,师从瑟诺博司,习西洋史和史学研究法,便受了孔氏的指示,希望他“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于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19] (P259)周谦冲,号天冲,湖北黄陂人。巴黎大学研究院毕业,随瑟诺博司专攻现代史。回国后历任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史学史、西洋近代史、历史方法。又译意大利史家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的《史学家与科学家》(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20世纪40年代在成都协助顾颉刚办《史学季刊》。陈祖源,江苏吴县人,北京大学肄业,毕业于东南大学,后又获得巴黎大学博士,专研史学。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开设“西洋文化史”课程选其师瑟诺博司的《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世文化史》、《现代文化史》作为参考书。[20] (P26)瑟诺博司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多数执教于各地大学,纷纷宣扬老师的史学思想,使这位西方史家在民国史坛声名远播。民国时期瑟诺博司的著作中译情况,介绍如下: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第三卷中译本有3种:(1)王道译,《欧洲现代文明史》,内务部编译处1920年出版,翻译自日本文明协会译本;(2)王慧琴译,《现代文明史》,上海东亚图书馆1933年出版;(3)陈健民译,《现在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陈健民还翻译瑟诺博司的《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代文化史》,这三本书构成了一部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韩儒林译《西洋文明史》(上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图书出版委员会1931年发行,只译了半部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此外,瑟诺博司的成名作《欧洲现代政治史》,毛以亨翻译了这部书的上编,(11)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12) 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 sociales有两种中译本:(1)张宗文译,《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出版;(13)(2)何炳松编译,《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
《史学原论》由李思纯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26年10月初版,后多次重版。这本书凡三篇:初基知识,包括搜索史料、辅助之科学;分析工作,由外形鉴定和内部鉴定组成;综合工作。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系何炳松据《史学原论》英译本选编而成。全书共十章:(1)史料之搜罗(The Search for Documents);(2)史料考证之重要(General Condi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3)版本之考证(Textual Criticism);(4)撰人之考证(Critical Investigation);(5)史料之诠释(Interpretative Criticism);(6)撰人之是否忠实(The Negative Internal Criticism of the Good Faith and Accuracy of Authors);(7)史事之断定(The Determination of Particular Facts);(8)史事之编比(The Grouping of Facts);(9)历史之著作(Exposition);(10)结论(Conclusion)。何炳松撰写了一篇中文导言,对史学的性质、中外史学的异同,加以说明,以便读者。《历史研究法》系英译本的节选本,流传似不如李译本之广。
《史学原论》之所以受到我国史学界的青睐,在于它为史学的专业化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基础。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被教育部定为专业必修课,[21] (P49)这不仅反映了一般学人自觉方法意识的形成,也说明了历史学科自身认同感得到强化,史学乃“专门家之技术,而非普通人所能为力”,治史者需要“特别的技术及特别的训练”,“凡作史者必如此而后为专业化,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22] (P9)所谓“技术训练”,不外乎《史学原论》所提出的那套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各地大学开设这类性质的科目,所讲授的内容基本也是如此。中国公学大学部历史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讲授搜罗、鉴别、整理史料的方法。[23] (P43)20世纪30年代雷海宗在清华大学开设的史学方法,主要讲授史料“搜集、批评、鉴别、综合、叙述各种能力”。[24] 北平大学文史系的历史研究法,“以示治史之途径”,治史最忌空谈,故每论一义,必广举例证,以资参考。[25] (P71)河南大学史学系所设的史学研究法,讲授“史料之认识、史料搜集及整理、史料编纂”。[26] (P90)郭斌佳在武汉大学讲授史学方法,指示学者如何用科学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凡研究一问题必经之步骤,如史料之搜集、真伪之甄别、事实之编比,以至最后著成史文,皆依次讨论,辅以例证。[20] (P26)30年代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为有志作高深之研究或充当历史教员者而设”,内容包括历史之意义及目的,过去史学界,“史料之种类,史料之搜集,史料之鉴别,史事之比较”。[27] (P46)40年代柴德赓在辅仁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内容分史料、考证、著作三部。史料则论其分类、搜集、来源之大概,考证则论校勘、辨伪、考异之方法,而多举其史实。著作则论古今著书之体例,历代著述之风气,与今后作者应取之途径。[28] (P59)不仅各大学历史系的史学方法论课程所授内容大致相同,而且30、40年代出版的“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著作论方法内容多根据《史学原论》,大同小异,如卢绍稷《史学概要》、李则纲《史学通论》、罗元鲲《史学研究》、杨鸿烈《历史研究法》、齐思和《史学概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以及刊物上发表的数量繁多的关于史学方法论文,如李承廉《史学方法论》、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都祖述西说。(14) 史学方法“技术”层面内容日趋固定化,一方面反映了现代史学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史学原论》所提出的一套治史方法逐渐与传统乾嘉以来的“土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史学方法论体系,其中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为典型,虽以本土面目出现,实具西学背景。
要之,《史学原论》作为一种西方译著,不仅是民国史坛中一本流行书,也是“现代历史研究法名著中推为最完善佳本”,[29] 在我国现代史学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李著之前,张尔田的《史微》(1912)和姚永朴的《史学研究法》(1912),都没有脱离传统史法之范围,似无甚精义。周希贤的《历史的研究》(1913)仅述人种、地理、政治、学术、宗教、风俗之要素。这三书都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法著作。《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1期(1914年6月15日)所发表的《历史研究法之研究》,虽有“历史研究法”之名,实为历史教授法内容。
②《中国史纲·绪论》专论史学研究法,柳诒征曾指出,“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中国史纲·绪论》仅次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征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是无需怀疑的。张荫麟认为梁著“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壬公先生》,《大公报·文学副刊》第57期,1929年2月11日)陈训慈以为梁著“长于融会西说,以适合本国,虽非精绝之创作,要为时代之名著”。(《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5期,1925年4月,第42页)而对于西洋史法有比较深刻认识的学人,对梁著则并不那么看好。五四时期在学界颇为活跃的罗家伦说:“梁先生看外国书的范围和了解程度,实在使我怀疑。我的怀疑或者错误,但是近来看他的几种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实使我增加这种印象。其实梁先生在中国学问方面,自有他的地位,不必有时带出博览西洋群籍的空气。并且有许多地方,若是他公认不曾看过西籍,我们只是佩服他的天才。若是说他看过此类的西籍,则我们不但以另一种眼光批评,而且许多遗误不合,或在西方早已更进一步之处,梁先生至今还以‘瑰宝’视之,则我们反而不免笑梁先生西洋学问之浅薄。”若是以看梁著的时间“去看Bernheim、Shotwell等关于历史方法的书,岂不是比看梁先生的书所得多了多”?(《罗志希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9日)在罗家伦看来,梁著似乎只是拾西洋史学方法之余唾而已。李璜认为梁启超对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其谨严处,又不及胡适之先生之能寻根究底,一枝一节的都非内证外证的求其水落石出不可”。(李璜:《学纯室回忆录》,香港明报社1982年版,第64页)留学哈佛大学、专治史学的齐思和也认为梁著“虽于中国史学所入极深,而于西洋史学则似犹隔膜。故其书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犹未能令人完全满意”。(齐思和:《史学概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油印本,第73页)各家对梁著不同的看法,反映了时人对西洋史法的不同价值取向。不管是称许还是不满,对于梁启超未得西洋史法精髓,似乎是一种共识。罗家伦、李璜、齐思和曾留学欧美,对西洋史法有透彻的认识,则对梁著就颇为不满了,他们主张建设现代史学应该完全取法西洋史法。
④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刊登于《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1922年4月。全文并未登完,尚有内审判及第三章综合,因缪凤林对前部分多不满意,故弃置重撰。(《缪凤林启事》,《史地学报》第1卷第3号,1922年5月)
⑤张其昀的《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发表于《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5月)、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同时这篇文字又改名《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发表于《学衡》第5期,1922年5月。
⑥如张荫麟的《评近人顾颉刚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引英译本《史学原论》第254—256页关于“默证法”的论述,批评顾颉刚所用方法之误。
⑦译文篇幅极少,只是《现代文明史》第三章第一节“十八世纪之新思想”,未见续译。见《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⑧李璜:《法兰西近代历史学》,《少年中国》第3卷第1期,1922年1月1日。李璜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指出,古朗治的信条是:“只去寻求”,他曾说“我不立成见,不作假设,不但不取哲学的假设,就是科学的假设也不取”。(第4—5页)这些话很自然让人回想起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两者观点何其相似。虽然没有材料表明傅受过古朗治的影响,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⑨李思纯等人赴法留学,《少年中国》有专门的报道,见《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15日。
⑩孔繁霱(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县人。1917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格林奈尔(Grinnell College)大学。192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1927年回国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
(11)毛以亨,浙江江山人,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法科大学、北京大学的教授,一度从政。1949年迁居香港,任香港大学教授,1968年在香港病逝。著《俄蒙回忆录》。
(12)据黎东方回忆,他曾翻译瑟诺博司的《现代欧洲政治史》两巨册,译稿交给胡适,然不知所终。(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
(13)张宗文,字定中,曾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攻读社会学、历史学。著《东北地理大纲》,杭州中华人地舆图学社1933年出版。
(14)《史学方法论》发表于《江汉学报》第1期,1933年4月;《史学方法的任务》发表于《华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
标签:史学方法论论文; 中国法国论文; 中国哲学史大纲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胡适论文; 读书论文; 中国历史研究法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