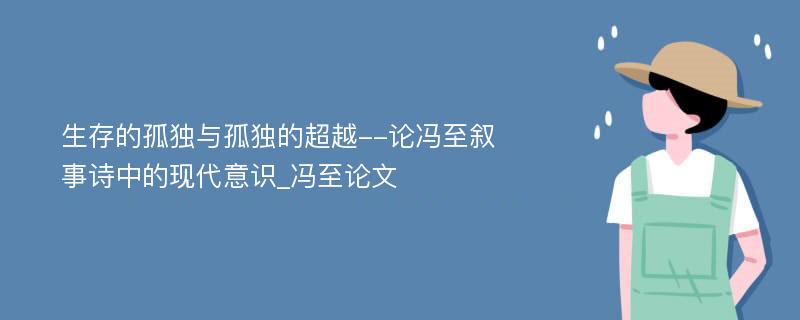
存在的孤独和孤独的超越——论冯至叙事诗中的现代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孤独论文,诗中论文,意识论文,论冯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冯至20年代的叙事诗数量不多,只有《吹箫人的故事》、《帷幔》、《蚕马》、《寺门之前》4首以及剧诗《河上》,但其质量之高,却足以担当朱自清先生的“堪称独步”(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第28页,上海良友公司1935年版。)的评价。长期来,由于为其抒情诗与《十四行集》的声名所掩,冯至这些叙事诗的成就没有受到广泛的重视,虽有一些研究成果,然而也多少存在“浅读”的倾向,大多以个人悲欢、忧郁感伤、浪漫情调一以概之。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除了这些社会层面的意义之外,冯至20年代叙事诗中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带有浓厚哲学意味的主题,以及从这些主题中透射出来的现代意识的萌芽。看不到这些意义,对于冯至后来《十四行集》哲理诗所达到的辉煌高度,就无法做出合理的阐释。
一、追寻:虚化的爱情对象
冯至的几首叙事诗,除了《寺门之前》外,表面来看都是以爱情诗的形式出现的,然而细细品味,这其中并没有充实的爱情内容,反近似于一曲曲单恋之歌,甚至爱情对象也被无形中虚化。伴随着恋爱对象的缺席,指向具体对象的“单恋”上升为生命意义的“追寻”,而作为存在意义上的人,“追寻”则是生命历程的起点乃至永恒境遇。
在这几首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脉络。《帷幔》中,少尼想象中的对方容貌的变迁竟可决定她的命运,难以从中看出什么爱情来,何况婚约是父母包办的。《蚕马》就更是一曲典型的单恋之歌,不能将其简单地概括为“人兽相恋”。诗歌中的少女根本就未曾表示过对白马的爱恋,人兽身份的殊异也使他们的相恋成为一种幻影。白马被杀后,少女的悲伤似可视为同伴逝去后寂寞的哀感。诗歌中浓墨重彩描述的是白马对少女至死不渝的痴情,这不过是一种单相思的表征。冯至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处理,目的或许在于表现自己对理想、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与不被理解的悲剧。同时也恐怕与诗人本身饱受单恋折磨的情感经历有关,冯至几度追求、几度失恋,其心理苦况可想而知。即使是在《吹箫人的故事》这样具备完整恋爱过程的故事中,也由于缺少一种真正爱情中的互动感而难以触及到爱情的本质,给诗中的“爱情”蒙上了一层朦胧虚无的影子。
构成爱情中双方的人物也是如此。在这几首叙事诗中,所有的人物形象,单独看来都并非个性鲜明,反倒有些类型化的倾向。对这些人物形象作一类型化的划分,无非是“追寻者”与“被追寻者”两类。吹箫人、少尼、蚕马、狂夫无疑属于前者,而以水中央之女为代表的系列人物则属于后者。“追寻者”与“被追寻者”之间表面上形成爱情中的双方,实际上后者已被无形中虚化,成为“追寻者”心中人生理想的替代物。也就是说,爱情的不完美只是形式、是幌子,是人生不完美、理想永难圆满的象征,冯至真正想要表达的却是“追寻/幻灭”的人生体验与哲思。因此,与其说冯至的叙事诗是在具体地描述一些爱情故事,不如说他是在抽象地表现一种爱和梦想的失落与忧伤。这正好符合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在多数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物常常是抽象的人,不是典型环境中的人,不是性格典型,而是人的原型。与之相应的,现代主义作品中的情节设置往往也是象征色彩浓厚的,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情节的丰富、完整和典型化,而在于通过人物和情节的设置表达心中的某种情绪或某种情结。在冯至的叙事诗中,人物(类型)和情节(爱情)的设置正是如此。这种设置背后的“情结”,很明显是一种“自恋情结”,表明他生活在自己所构建幻影中。在这种幻影中,追寻没有结果,等待没有回报,人与人之间不能真正相互呼应,甚至人的存在也是一种悖论,永远陷于无法解脱的困境中。与之紧密联系的“情绪”则是孤独感——不仅仅是单相思的孤独,主要还是人的存在的孤独。这样,虚拟化的爱情抒发,不妨看作是冯至的一种自恋方式:在无爱的寂寞和孤独中,使自己在作品中经历一番伤痛,然后在伤痛中自恋自艾,以此来咀嚼一种“悲哀的味调”。
实际上,整个20年代,冯至都或浓或淡地沉浸在一种“自恋情结”的包围中。自恋的中心体现为自怜自艾,因此它内在地蕴含了强烈的孤独感。自恋情绪是对幼时理想自我的顽强维持,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逐渐消失,人才能适应并参与到环境活动中去。一般人在接触社会以后,理想自我开始破灭,才能认识到一个无法控制的自我。人与自我、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幼时的和谐幻想中被打破,面临越来越离自己远去的我,以及与自己愈加不相容的环境,感伤的情绪于是弥漫起来。自恋情结表现在青春的感伤与寂寞上,是每个个体的人必经的阶段。
理解了冯至的这种“自恋情结”,也就理解了他似是而非的“爱情诗”。就拿《蚕马》一诗来看,抒情主人公是一个情意缠绵、热烈执著但又不无寂寞忧郁的青年,他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的自况。与始终热烈倾诉的“我”相对应的,是第二人称的“你”。“我”总是在依恋、追求着“你”。“我”不断地通过种种方式、手段向“你”暗示,倾诉“我”的衷心,如同白马千里迢迢为姑娘寻回了父亲、完成她的心愿,而“你”总是那么矜持,与“我”若即若离、态度暧昧不明,因此给“我”带来了许多难以言说的烦恼与苦闷。对“我”的叩问,“你”从不应答,但无论“你”如何,“我”对“你”永远是一往情深,即使遭受挫折也不改初衷。冯至的青春之火在爱情的追求与折磨中燃烧,他的歌喉反复地在自己空幻的对象——“你”的面前感喟,流注笔端,凝成热烈而又忧郁、一唱三叹的独特倾诉。在诗中,独立于情节叙事之外,有三段以第一人称来倾诉的诗句隔行呼应,可以看作是全诗的情绪线索。诗句从“蚕儿正在初眠”到“三眠”,再到“织茧”,景物的更替对应着“我”的情绪变化:从“我的心里燃起火焰”到“正燃烧着火焰”,再到“还燃着余焰”,直到最后白马被杀。在这首自我孤单无奈的倾诉之歌中,“我”从追寻到幻灭都是自我行为,在“你”与“我”之间,只有一方的默许、聆听和另一方的恳请、倾诉。“你”与“我”之间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对话性,正如诗中所唱的:“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门问我,“你是谁?”与其说这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痴情,不如说是自我倾诉而又自我倾听接受,这与其深切的孤独体味而又无从摆脱孤独境遇的苦闷是一致的。
在“我”与“你”的二元对立中,“我”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意义上一个孤独者的原型,生命中唯一的动作就是“追寻”,其意义远远大于“追寻”的对象乃至结果,因而“你”的存在只是为了印证“我”的“追寻”必然幻灭的一种设置,进而强化无从克服孤独的精神苦闷。诗中的恋爱对象如同“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中的那位水中央之女一样,若有似无,若隐若现。它的被虚化是必然的,因为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作者自己情感的抒发和渲染,是他对人的存在困境的哲理之思,而不是对某一次具体的失恋遭遇的追悼。而在这种虚化的背后,则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到,那种单向度的独语,不仅是冯至“自恋情结”的产物,而且在形式上成为对冯至孤独感的一种补充。
二、幻灭:现代型的悲剧意识
孤独者的追寻必然幻灭,这就是冯至在他的几首叙事长诗及剧诗中所揭示出的现代人的命运困境。具体来看,他所叙述的故事中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追寻/幻灭”模式。
先看《河上》。《河上》是一部颇富象征意味的剧诗,取材于《诗经·秦风》里的《蒹葭》和汉魏乐府中“公无渡河”的《箜篌引》。诗中那个“樱唇娇嫩”、“乌发如丝”的水中央之女,如影似幻,令人迷狂;可当“青年狂夫”不顾一切地迎上去时,却“立即幻化作,/一缕青烟消没。”“狂夫”的追寻最终以触礁而亡终成幻灭。水中央之女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的象征,年轻的冯至把她处理成一种幻象,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注定了狂夫的追求从一开始就要破灭,让人深感现代人对绝美理想所怀抱的那种永世的单恋与缺撼。由此,这种“追求/幻灭”的故事模式上升为一种人生模式,体现为冯至对人生悖论的哲学之思。
同样的思想在其它几首诗中各有体现。《吹箫人的故事》在传统的爱情主题背后,深刻地表现了现代人对爱情与个性、自由无法两全的困惑。诗中那位隐居深山、超凡脱俗的吹箫人,在爱情叩开心扉之后,“好像着了疯狂”,因为他从人间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女郎。然而就在他们牺牲了“尽藏”自己“精灵”的洞箫,换来爱情的时候,相伴而来的却是因失去自己的声音而产生的悲伤。于是,“剩给他们的是空虚,/还有那空虚的惆怅。”如果把箫看作是个性的代替物,诗中吹箫人与女郎由于个性而相互吸引,却无法获得爱情与个性的两全,在牺牲个性成全爱情的两难选择中,人生难以圆满。对理想爱情、理想人生的追寻,仍然是以幻灭而告终。类似的主题也在冯至这一时期的梦幻剧《鲛人》中出现:海女三爱上了远方来的鲛人,被他无爱的哭泣和冰凉的唇打动。鲛人由于得到爱情,不再哭泣,嘴唇也不再冰凉,然而海女三却因此不再爱他。因无爱而哭泣,由此得到了爱;因爱停止哭泣,反而失去了爱。海女三追求绝对、圆满,这原是悲剧性的。冯至表现的是人生残酷的悖谬。
在《寺门之前》中,主人公老僧和他的经历,如同是从一泓死水中上升起的蜃楼。传统解读中所谓“人性的觉醒”、“宗教的桎梏”等等都不是主要的,解释人与生俱来、不可抑灭的憧憬与生命渴望,才是这首叙事诗体现出来的主导价值观。“我不久死后焚为残灰,/里边可会有舍利两颗?/一颗是幻灭的蜃楼!/一颗是女尸的半裸!”“幻灭的蜃楼”和“女尸的半裸”作为僧人全部的生命憧憬,在生命的老去和浪费中逐渐淡出。它把人生的缺憾以“轻悲剧”的面目展示出来,虽未毁灭了美好的,却总让其蒙上一层阴晦,以不完满破灭所有的憧憬。
这种缺憾,不是性格的,而是命运的,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支配着他们——这种命运式的悲剧,虽难排除是受到了德国谣曲中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但也不可否认它正暗合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生在世就是一种“被抛状态”:人被无缘无故地抛掷在世,绝对的孤独无助,从根本上没有任何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但又不得不把已经在世这一事实承担起来,这正是人的存在的荒诞性之所在。在这一生存过程中,性格只能帮助决断,而命运(存在的无意义)是难以更改的,当社会中的人对自己孤独的存在困境感到绝望时,就很容易将它绝对化、普遍化为人的永恒处境,从这个角度说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无疑带有悲剧性的品格。以《帷幔》为例,主人公少尼只因偶尔听说“将来同我共运命的那个人,/是一个又丑陋、又愚蠢的男子”,便“情愿在尼庵里消灭她的青春。”哪知未婚夫却是一个多情少年,为她“抱定了终身不婚的志愿”。只因一次误信人言,便断送终生的幸福。少尼凄婉的命运悲剧,并非是简单告诉人们一个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实际上诗人着力表现的,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及性格,展示出现代人对于自我精神的张扬与追求,以及固守这种人的必然要求在现实中的错位与失落,从而传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自由精神及现代价值观念。
可以这样说,冯至的现代叙事诗,从理想追求与现实失落、精神憧憬与人生错位等现代人意识到的现实矛盾与精神冲突中,将“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主题,拓展到了对于人的命运本身及现代社会的人生困境的反思方面,而这正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意识。虽然20年代的冯至还主要处在感伤的幻美阶段,浪漫主义仍是其风格的主导因素,但由于他独特的生存背景与性格,他已经更多地从哲学层面来表现一种现代型的悲剧意识,而这些都植根于他对孤独感的深刻体认中。进一步讲,孤独感本身也就是现代意识的核心之一。
冯至作为一位关注生存的诗人,他的生存状况涵盖了他的作品。“我生长在衰败的国,衰败的家里,免不了孤臣孽子的心肠。虽说世界需要进步,人要勇往直前,但想来想去,总不太像是我所能办的事。”(注:冯至:《智慧与颓唐》,载1930年12月31日《华北日报》副刊。)这段“夫子自道”,是对他自己青年时代生存状况的最好阐释。冯至童年的不幸经历,培养了他深沉内向的性格和如影随形的孤独感,这使他在个人禀赋上,更适合写沉思、冷静的现代作品。在创作这些叙事诗的1923到1927年间,正值冯至人生的浪漫期,对人生、对社会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和期待,然而适值“五四”退潮,现实不能使他如愿以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苦闷中彷徨,面临着“歧路”与“穷途”上的重新选择与定位,青年们常在口头的一句话是“没有花,没有光,没有爱”(注:冯至:《西郊集·后记》,《冯至选集》第一卷第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以冯至的敏感,他比一般人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荒凉和寂寞。因此,对冯至来说,孤独感应该是个人经历与时代气氛相融合的产物。
当然,冯至对于孤独的思考并非仅限于此。克服孤独才是他内心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的外部表现则是寻求爱,寻求理解,渴望改变人间的冷漠,进而摆脱孤独。然而,冯至因失去母爱而形成的人生无常、世界悲凉的意识,以及在爱情上求之不得长期陷入单恋的个人经历,必然使他悲剧式地理解人生。一方面感到人生应该有追求,另一方面又觉得人生是虚幻的,永难如愿以偿。冯至思想中全部的矛盾皆来源于此,体现在创作中就表现为追寻时的挥之不去的幻灭感。幻灭之后,所体味到的则是更深层次的孤独,于是,便形成了“孤独—→克服孤独—→更深的孤独”这样一种宿命式的循环。由小体味到大观照,冯至的诗自然有了强烈的现代意味。
总之,在对孤独感的深刻体认上,冯至的叙事诗体现出一种现代型的悲剧意识,即觉醒就是痛苦,追寻必然幻灭。这是一种人的存在的悲剧,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悲剧,它既不是社会悲剧,也不是伦理悲剧,而是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人的存在本身的悲剧。“它表现了人对其存在的终极意义之源的困惑与迷惘,显示了人对其存在的最深切的根本的关怀。”(注:解志熙:《生的执著》第2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在这个基点上,冯至勾画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人的觉醒过程和醒来的痛苦。
三、逃离:矛盾的死亡观
冯至感性地体验到了人的存在的困境,那么他又如何从困境中突围,以实现对孤独感的超越呢?年轻的他所做出的选择是逃离。
在冯至的叙事诗创作中,“死亡”成为逃离的一种主要形式。《帷幔》中少尼的幻梦在笛声中破灭,“尼庵内焚化了这年少的尼姑”,死亡成为她枯槁生命的最好解脱。《蚕马》的结尾,“马皮裹住了她的身体,/月光中变成了雪白的蚕茧。”永不分离的实现仍然是以“死亡”为代价换来。至于《河上》,青年狂夫的触礁而亡既作为追求的幻灭形式,同时也代表了作者为这种幻灭所安排的最终归宿。可以看出,死亡、毁灭在冯至这里被有意地强调,他幻想一切挫折都在死亡之中得到最终解决。
比较一下冯至后来的《十四行集》,可以发现,死亡虽同样成为超越孤独的一种形式,然而对死亡的态度,前后却有很大的差异,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冯至对人生存在之思的发展轨迹。在20年代的几首叙事诗中,萦绕着一种视人死如幻灭的低沉悲伤,到了《十四行集》,生与死已相提并论,一并为诗人所认同,死已从生之归宿地带逃开,而被视为生命最辉煌的完成,也即死亡已成了另一种意义的生,人努力求生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觉地“支配死亡”的过程。在这里,死与生统一起来,从一种大宇宙的包容与达观上实现了对孤独的超越。冯至这两个阶段对“死亡”的理解,其实正构成了存在主义死亡观的两个层次。让我们来看看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的死亡观:“对从生存论上所筹划的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特征标画可以概括如下:先行向此在揭露出丧失在常人自己中的情况,并把此在带到主要不依靠操劳操持而是去作为此在自己存在的可能性之前,而这个自己却就在热情的、解脱了常人的幻想的、实际的、确知它自己而又畏着的向死的自由之中。”(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第305—306页,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死亡对人来说是不可回避不可超越之物,它能够在任何时刻突然降临从而剥夺人的生命及其一切计划,任何人从出生开始的存在都是走向死亡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把人称为“向死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死还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死亡的畏惧,不仅向人展示出他的日常生活的虚无性、不真实性,而且也向人展示出他的最极端的可能性。因此,畏死能使人反跳回来,获得生的动力,自己承担起自己的命运。海德格尔把这种由死亡反顾生命、更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存在的人生态度,称之为“先行到死”。20年代的冯至已经强烈意识到死亡是生命的界限,他的叙事诗展示了一幅悲观的人生图景,在这里生命与死亡终归是对立的,死亡则成为生之终点。如果说这时的冯至仅仅感受到人生是“向死的存在”(注:冯至:《蔡元培》(《十四行集·十》),《冯至选集》第一卷第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那么40年代他已经把“先行到死”的观念完美地融入了创作和人生态度之中,倡导一种“正当的死生”,认真地为人。这一发展变化,有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冯至远在他接触西方存在主义之前,就在自己的诗作中,反复提出了“死亡”这一与玄学紧密结合的主题并赋予它更高的象征性意义,的确是在他“自己的园地”中培育了现代意识。
然而,冯至的“死亡”似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他的一篇散文《记克莱恩特的死》进入到他对死亡的深层理解中。在这篇散文中,冯至将克莱恩特的死描写得神圣而美丽,并以“甜蜜的忧伤”来形容。死亡毁灭中的悲凄色彩被大大淡化了,死亡成为一种美丽的情绪,冯至既排斥它,又品味它,既怨尤它,又欣赏它,正如他所有的叙事诗在悲剧的宿命中总萦绕着一种幻美的色彩,哀而不伤。面对理想幻灭之后无法摆脱的孤独,冯至虽然已经选择了“死亡”——“逃离”来作为最高形式的抗议,然而本质上的理想主义又决定了他不甘心就此放弃、就此绝望,对死亡所作的大量唯美的渲染本身就给予了一种希冀、一种憧憬。这样,就可以理解,《帷幔》中少尼焚化的同时,“一个牧童剃度在对方的僧院”,象征少尼全部幻梦的帷幔,至今“还珍重的藏在僧院里”,等待着“左方的一角”有人能够补起。可以看到,冯至对幻想的破灭是悲观的,但还不曾绝望。这一点更集中地体现在《寺门之前》老僧最后的话中:“什么是佛法的无边?/什么是彼岸的乐国?/我不久死后焚为残灰,/里边可会有舍利两颗?/一颗是幻灭的蜃楼!/一颗是女尸的半裸!”“舍利”就是死亡的残灰中未曾放弃的人生憧憬,象征着重生和延续。逃离之中仍存在希望,在追寻中失落,又在失落中追寻,这才是冯至“死亡”主题的全部含义,同时也是他在超越孤独时所做出的辩证性的独特选择。正是在这一点上,暗示了冯至后来思想上趋至成熟的内在根据。
逃离的另一种形式是逃遁或隐世,在生命的消耗与浪费中,显示出对超越孤独的无能为力。同样,这种逃遁不是绝望的逃离,其中仍包含了丰富的暗示性,隐含了一种对希望的苦苦追寻。《吹箫人的故事》的尾声,诗人这样写道:“剩给他们的是空虚,/还有那空虚的惆怅--/缕缕的箫的余音,/引他们向着深山逃往!”逃往深山或许会有新的奇迹,这里,诗人并没有以极端的方式来斩断一切,而是让生命的延续本身来提出一种对未来不可知的期待。
可以这样说,在冯至20年代的叙事诗中,他试图超越孤独而作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他选择了逃离这样一种方式,而不是更加成熟的自觉承担、忍耐和等待。然而,这其中已有了许多存在之思的闪光,这里,冯至以少年式的早熟对整个人类的生命进行了思索,其意义早已超出了这思索的结果本身。
四、结语
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经指出,叙事诗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歌唱一个故事。这可以说一语道出了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冯至的叙事诗正是中国现代叙事诗中的珍品。撇开它的为众人所称道的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显著特征,我们从对其内在精神涵蕴的发掘中,也可看出,在这一点上冯至的叙事诗不仅在当时无人比肩,而且经过将近80年的岁月仍不减其光彩。当然,我们无需拔高其叙事诗的思想艺术水平,诗中那些有关整个人类命运的重要命题的思索,也许并不都是自觉的,也并不成系统,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众多叙事诗,大都是情节型叙事诗,而冯至笔下的叙事诗则一律是象征型叙事诗,而象征正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表现方式。正是在这一点上,冯至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现代转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朱自清先生曾称“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从冯至的叙事诗看来,或可算作例外,至少在略带幼稚的深思中表现出一种哲理倾向和现代主义气息。
冯至20年代叙事诗的自我展示,笼罩着对孤独的强烈感受与超越之思,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就转化为“追求/幻灭”、“死亡”等现代意识的萌芽,而绝不仅仅是“一掬渺小的情感”。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哲理性的思考,也就不会产生后来《十四行集》那样纯粹的现代主义哲理诗作的高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至20年代的叙事诗创作所作出的贡献,不仅在中国叙事诗的现代转型及创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哲理诗、冥想诗进入叙事诗体裁的开拓这一方向上,也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