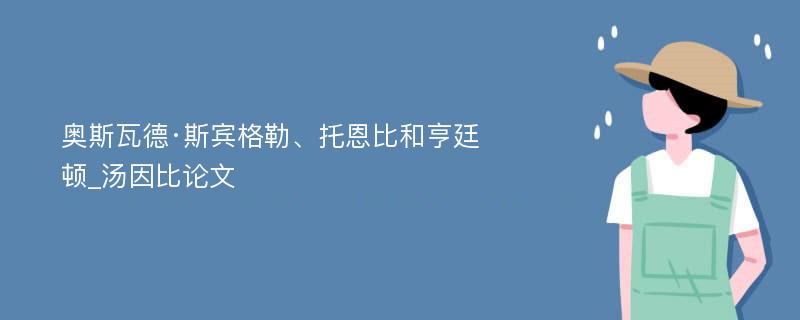
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庭顿合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勒论文,亨庭顿合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值跨世纪的转折点,我们生活在充满裂变的历史文化转型中。一方面无法拒绝世纪初期待创造的激情与诱惑,另一方面又无力挣脱世纪末寂寥空疏心态的困扰与折磨。人们生于忧患,也在忧患之中描述生存主体的现实状态,表达对精神家园的永恒渴求。为了期待,也为了延存,人们不免要追思怀想文明的起源、生长、停滞、解体以及衰败。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紊乱》,福山《历史的终结》,奈比斯特《金球悖论》,都竞相描述国际秩序、文化格局的现状,力图建树规范人类文化的范式和历史叙述的元话语。一九九三年六月《纽约时报》、《外交事务》杂志推出哈佛大学奥林战略研究所政治学家S·亨庭顿(S·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即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两篇洋洋大作,集中表述“未来政治冲突即文明冲突”这一核心观点,并寻找当代国际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式,用“文明冲突”来填充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无主导、文化无中心以及意识形态衰微之后的真空。
我们试图在中心主义没落、后现代多元文化共生的景观中,回应西方学者“文明冲突论”的挑战。在下面的考察中,我们将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看作是一种“政治文化学”。为了探究这一学说的精神渊源,我们将它同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汤因比的文明个体论进行对比,借此以显示亨庭顿、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历史观中的精神延续性,揭示西方历史哲学中虽变种迭出却又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
一、政治文化学:冷战后传统文化范式
亨庭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有其广阔的世界性政治文化背景。其一,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经济秩序的转移,原有政治秩序与权力格局的瓦解、尤其是利益重心的转移,都导致了利益与权力表达失去了平衡,而且,“种族文化”也在这单一中心去势的时代正以历史上极大的力度和极快的速度多中心、多取向地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范式。其二,普遍生长于世纪末的全球性“后现代主义”运动,使文化景观日益“迷乱”与“狂乱”,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回家”,但是“我们缺少地图”。几乎所有的传统文化都“绝子绝孙”,而现代文化又“无家无根”,后现代主义又释放俄狄浦斯情结而疯狂地“杀父弑君”。传统留给我们的“文化绘图法”不能让我们定位作为生存主体的时空,而现代、后现代提供给我们的思想范式也不能给我们作为阐释主体以合法、合理的视界,流转不息、律动不已的文化现实又让我们困惑于“是是非非”,“存在还是不存在”成为切实的忧虑。人们根本无法获得一种元话语或合理范式去制服转型中的动荡与裂变,主体由于丧失立场而陷入了“人的死亡”之境地。正如伯特曼对于后现代美学经验的描述:“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存在主体、阐释主体的渴望与期待都无所指向、无所安置。其三,也是最明显的是,冷战后国际秩序中冲突缓和,对抗消解或改变方向,人们发现进步/落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民主/专制等等二元对立范式都不能定位文化秩序;西方的没落、美国的落伍都成为主权易位、霸权失势的表征,这使得西方学者忧患尤深,那几近雪上加霜的痛楚表现在重建政治主宰、文化轴心的欲求中。正好是在重心转移、狂欢迷乱以及冷战后失范的文化语境中,亨庭顿的政治文化学以文化的名义发言,为政治强权招魂,重祭冲突战旗,虚设出中心/非中心、西方/非西方的对抗模式,以期匡范人类文化的未来。
亨庭顿的基本观点有三点:一,他断言“文明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二,他预言未来文明冲突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三,他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虚假分析模式”,又反对普世文明的“非现实模式”。
关于第一点,亨氏有如下论证:(一)文明的差异不仅实际存在,而且是根本性的;(二)世界的距离缩小,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这种日益加深的影响反过来又加剧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敌对情绪;(三)全球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进程正把人们从长期以来的地方属性中分开,削弱民族国家的属性。在世界的部分地区,宗教的兴起填补了这个真空,西方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佛教、伊斯兰教都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四)西方以其独特的双重作用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五)文明的特点和差异不易改变,不象政治和经济特点那样容易冲淡、缓和、消除;(六)经济地区化进程在蓬勃发展,也推动文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归根到底,文明的冲突随着世界化的发展成为最实在也最残忍的冲突。霸权不是体现在对市场的占有、武力的征服和贸易的顺差额上,而是体现为文明意识对生活世界价值主导的争夺。亨氏认定在世界的未来格局中将有八种文明相互作用、争夺对人类领域精神世界的主宰:(1)西方文明;(2)儒家文明;(3)日本文明;(4)伊斯兰文明;(5)印度文明;(6)斯拉夫——东正教文明;(7)拉美文明;(8)可能的非洲文明。其中,(3)、(5)、(6)、(7)、(8)属于动摇不定的“精神分裂式文明”(Schizophrenic Civilization),它们对西方文明有“亲和性”又有“离心力”,既借重西方又抗拒西方,从根本上不构成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唯有对西方基督教主导文明抗争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伊斯兰文明将席卷穆斯林世界,延续对西方文明的抗争;冷战后汉语文化圈内羽毛渐丰的国家已经表现了儒教文明崛起与蔓延之势,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对抗;而且,儒教文明还与伊斯兰文明携手合作,与西方基督文明分庭抗礼,争夺未来世界人类灵魂,而这将引发更加残酷的冲突与战争。关于第二、第三点,亨氏发挥出来未来八大文明的相互作用将形成“未来世界政治轴心”,即西方与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的对抗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调;这种“文明冲突”的范式超越了国家中心主义又超越了普世文化观:一方面反对以国家利益、国际权力制衡作为政治秩序的杠杆,认为相反应当认清人们最终的依托与关注在于信仰、宗族、血缘与信念等文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又反对视文明为促进交往、增进沟通、加强协调的力量,认为相反,文明反目成仇、引发冲突的力量才更为根本[①]。
不难看出,亨氏提出的是一种“政治文化学”,这一理论文本的要旨在于建树“冷战后传统文化模式”(Post-traditional Model of Culture)。这种模式必须超越地域、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等价值标准,重新标画世界政治地图,重新范定国际秩序。这种模式还超越了君主对峙、国家利益竞争、意识形态对抗以及超级大国冲突,趋近于文明的、信仰的冲突、抗争以至战争。一方面,它否定了从维柯至黑格尔、雅斯贝斯的有关精神统一的元话语,在统一、协调、和解之外激励文明的差异、对抗与冲突,进一步消解了种族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它又再造冲突的机缘,力图重建文化霸权以抑制文化主权,否认了文明间交往中的平等性涵化(acculturation),着意于文明间差异并存的对抗。因而可见,这种模式放弃了历史文化沉思中追求至善至美、圆融和合的天地良知,反而认定差异必然导致对抗,对抗必然走向血淋淋的冲突,其中尼采的强力意志、马基雅维利的文化暴政意识都昭然若揭、呼之欲出,也显示了亨氏对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非理性主义钟情之致。亨氏弘扬文明差异旨在激励文明冲突,宣扬多元并存却又想救助日益衰落的西方中心。亨氏政治文化学文本表面显示西方中心偏失,多种文明并存竞技,在其文本深层却顽固维持主宰地位、运作文化极权的暴力,这里又可见一种剪不断的对光荣悠久的美国梦的依恋。冷战已成历史,但其幽灵未息,尚徘徊不去。
二、文化忧患论:斯宾格勒与汤因比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是西方人普遍忧患的时代。穆西尔论精神的颠覆、神秘的时代病蔓延,席梅尔论文化与生命、结构与动因之间令人苦恼的冲突,马克斯·舍勒论价值的毁灭,超人狂徒尼采论上帝的死亡,使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主体和阐释主体沉陷在一派末日学的情绪中,尽染凄迷之雾。这种忧患与凄迷之中,实质上涌动着一股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一统天下的反叛,人的宗教情怀对自然科学真实关切的苦难控诉。但把对文化危机的忧虑上升到哲学的神圣忧思,并尖锐地将文化衰败提升到主题化高度,却是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及其在烛光下艰难地书写出的《西方的没落》(1918年)。于是,一种呼应尼采“上帝的死亡”的“浪漫的、悲观的、末世的”文化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也敲响了对西方文化进行最后审判的钟声,启蒙了一代又一代文化感伤主义者(包括存在主义一系哲学家)和文化虚无主义者(现代、后现代主义运动)。
斯宾格勒对历史的观照就是对精神的瞩望,也是对人类历史意义世界的“诗性直觉”,而“蔑视有机经验无限乐观精神”。斯氏以植物生长象征文化的生长,以植物群聚隐喻文化类型,认定文化是一种生动活跃的创造性力量与激情样态,而文明则是一种相对滞迟的结构性范式与理性样态,文化发展到文明,正如植物由荣而枯、由盛而衰;正如植物群聚经历春夏秋冬,由繁茂至于肃杀,人类文化也有发生、兴盛、败落以至死亡的行程,而这正是人类存在所无法征服与超越的历史“命运”。这种“西方文明由盛而衰的‘宿命’”[②],正是西方没落论(文化忧患论)的形而上学根据,也是文化生长、成熟、衰败、死亡的内在节律与原始动因,最终成为文化忧患论的内隐价值线索。斯宾格勒写道:“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影象印在它的材料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烁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祗、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由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③]在斯宾格勒视野中漫涌的文化时空中,流转着埃及文明、中国文明、阿波罗(希腊)文明、枚斋(犹太、早期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文明、古典(成熟的基督教)文明、浮士德(近代欧洲)文明,它们都由盛而衰,走尽历史的大写宿命,而在古典时代的衰落与浮士德精神的衰微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契合、平行与呼应,古典的衰落与浮士德精神十八世纪以来的秋气萧瑟、十九世纪的渐渐式微,似乎是一次历史循环的再现。十九世纪以降,西方世界进入了冬天,浮士德精神发展到文明阶段,历久千年的文化期已经逝去,其创造能力也荡然无存。斯氏认为,浮士德精神的去势、萎靡、死灭,迎来了一代新的暴君,浪漫地发动血腥的帝国战争,西方步入了后传统的裂变,正象黑格尔之后绝对精神不可挽救地支离破碎了,“新凯撒时代”养育了金钱暴政与末世狂徒,人类似乎踏上了“启示录”预言的苦难时世。
文化的忧患与感伤体现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身上则更是令人怆然和迷茫。汤氏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犹如圣约翰目击人类启示的末日异象。索罗金指出,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最后篇章“出现了几乎是启示录的声调”,“人类的全部历史或是文明的全部发展过程都变成了一种‘创造的辩神论’(theodicy)[④]。汤因比自己也写道:“作为天体行程的力量,它虽然是美丽的,而对于人类的肉体来说却是个不尽的苦难。”[⑤]受难的主人公是人的存在,文明史就承诺苦难存在的最后救赎,历史就成为拯救史。汤因比以“文明原子——社会”为单位,追寻文明起源、停滞、生长以及衰败、解体的内在节律,最后皈依高级宗教,托负苦难深重的灵魂,透过冲突与矛盾、和解与交流的繁复表象,忧思深远地观望文明的未来。汤氏认为,环境对人类生存主体的挑战,激荡着生存主体的求生意志,刺激主体对挑战作出应战,使社会由“阴”到“阳”转化,永恒地进入生成与解体的运动之中。文明的生长是向“自决”前进,即克服物质障碍与环境挑战而在精神上升华,这种升华不是直线单传的,而是具有一种动与静、易与固、复出与隐退的内在节奏,通过这种节奏人类精神向着高级宗教的雅致灵魂进行对流运动。文明的解体是指其内在丧失控制能力,失去自决能力,以致社会体流散分裂,灵魂苦难裂变,行为、情感与生活世界都被分裂为二,必然引出差异、对抗、冲突以致暴力,进而导致文明解体、衰败。汤氏认定,最强的挑战来自道义,最大的悲剧在于灵魂,最深的冲突发生在文明内部,文明的衰落与死亡不是谋杀而是自毁。所以他忧心于第三次世界战争,又追思二十一种文明的停滞与自杀,把文化史写成获得启示的历史,写成灵魂在苦难中朝圣的体验,汤氏皈依宗教,颤抖的沉思渺茫地叩响了形而上学的意蕴:“我们应该祈祷,我们也必须祈祷,上帝曾对我们的社会恩准过一次缓刑,现在如果我们再次以负疚认罪的精神和哀求怜悯的心情向上帝呼吁,他是不会拒绝我们的。”[⑥]就这样,汤因比从文明的真与善走向了十字架上的信念,护卫人类信仰的灵旗,努力让生存主体有所期待和回应,正如索罗金所说:“文明的现状并不是正在走上什么死亡的道路,而只是走上一条痛苦的伟大改变的道路。”[⑦]
三、简短的比较
斯宾格勒的文明形态学是一曲抒情的挽歌,唱给“浮士德精神”隐退后的现代荒原,铺开T·S·艾略特长歌浩叹的宏大背景。其中,“历史即下行之路”成为这一抒情诗章的主调。但在浓郁的悲怆之中,这种“挽歌体”理论文本寄寓着西方近代精神无限的执着和西方中心主义永恒的渴望,这种执着与渴望采取了末日学的形式。
汤因比的文明史是一部戏剧化的拯救史,这种启示录式的文本投射了人类生存主体不灭的生命渴望,表现了在逆境中求生存的至高美德,也表现了在挑战面前顽强应战的权力意志。汤因比亲历人类在二十世纪经受的苦难冲突,试图以西方为中心传播高级宗教,象福音使者一样期待世界和平与精神的升华,引导普世的忏悔、虔敬的祈祷,超越自我、地域、种族,向神圣进行对流运动。这是典型的悲观进取。如果说斯宾格勒铺陈着西方没落后的现代荒原,那么汤因比便开启了现代荒原上灵魂的家园重访。
再看亨庭顿的文明范式,它无疑是一种漫画式的政治预言。这种策略家的言论体现了急功近利、野心勃勃的政客心态。一方面,他力图控制失范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他又为冲突煽风点火,其结果只能是开启了一种血腥的争战,演成另一次冷战或热战的痛苦故事。亨庭顿预见未来由文明冲突主宰,这是进行“圣战”动员,激励主权与霸权、中心与边缘、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对抗、冲突,似乎人类的裂变永无尽头。
斯宾格勒是忧患诗人,汤因比是福音使者,亨庭顿则象末日狂徒。三者之间有同曲隐的学理上承继关系。这三种历史观、三种文化书写方式显示了忧患没落发展到救赎愿望,由救赎愿望再发展为冲突预言,其间隐含的线索是西方中心主义,共有的背景是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作为对理性传统的反弹,往往透过虚幻的大全与绝对、完满与统一,显示出文化败落的深重危机;非理性具有一种灵遇方式,总是无法回避生活世界的异化和信仰领域的空虚,往往曝光文化历史的忧伤、悲剧和冲突的可怕景色。
西方没落论、文化救赎论和文明冲突论还有两个显著的共同点。第一,三种历史观都未曾参照统一的世界精神历史构架,而是动摇了文化历史发展的元叙述模式和先天阐释视野,都谕示着西方文明无可奈何的衰微,也暗示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将会长驱直入征服西方生活世界——文化前景的荒原化在所难免。第二,忧患、希望与冲突的预设都暗示了更大范围、也更加残酷的冲突。斯宾格勒预言“金钱与血的冲突”[⑧]。汤因比认定分裂是文化衰落和解体时期特有的现象[⑨]。亨庭顿则咄咄逼人地反问他的批评者:“如果不是文明冲突,又是什么?”总之,在西方文化语境里的忧患与伤感之中,文化历史观内蕴着一种精神冲突的前意识情绪,西方文化的代言人每每会呼吁文化“圣战”,引爆文明冲突,加速其自身文明的衰败与自毁。
注释:
① 亨庭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事务》,一九九三年夏季号。
② ③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见“导言”,及P39。
④ ⑤ ⑥ ⑦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三卷“附录”,第二卷P13,第三卷P457,第三卷“附录”。
⑧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卷,P474。
⑨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卷,P156、157。
标签:汤因比论文; 斯宾格勒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文化论文; 文明冲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西方的没落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范式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