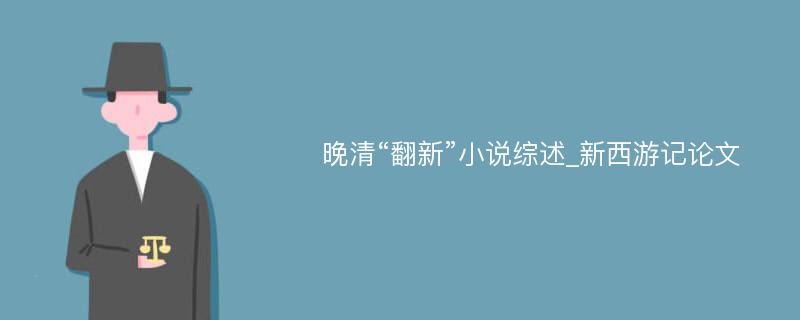
晚清“翻新”小说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时期出现了一批特殊的小说,它们的书名大都袭用古典名著而冠以“新”字,如《新水浒》(有西冷冬青、陆士谔写的两种)、《新三国》(有陆士谔、珠溪渔隐写的两种),《新西游记》(有冷血、煮梦写的两种)、《新石头记》(有吴研人、南武野蛮写的两种)、《新镜花缘》(有啸庐、萧然郁生写的两种),《新金瓶梅》(慧珠女士)、《新封神传》(大陆)、《新野叟曝言》(陆士谔)、《新七侠五义》(治逸)等。书中的角色多是原著中读者熟悉的人物,只是所写的事情,却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这类作品,阿英《晚清小说史》称之为“拟旧小说”,似不甚当。作《新水浒》的西冷冬青说:“《水浒》所演的一百零八个人物,其中虽有忠臣,有孝子,有侠义,然究竟算不得完全国民,况且奸夫淫妇,杂出其间,大有碍于社会风俗。所以在下要演出一部《新水浒》,将他推翻转来,保全社会。”作《新西游记》的冷血在《弁言》中说:“《新西游记》虽借《西游记》中人名事物以反演,然《西游记》皆虚构,而《新西游记》皆实事,以实事解释虚构,作者实寓祛人迷信之意。”“翻转”、“反演”云云,带有翻案、翻新的意思,从尊重作者的创作动因出发,名之曰“翻新小说”,可能更为贴切。
阿英对此类作品评价很低,以为“窥其内容,实无一足观者”,断言它们的出现“是当时新小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晚清谴责小说的没落”[1]。由于阿英在晚清小说研究界的权威地位,这一批作品遂长期处于被忽略、被漠视的境地。除了个别作品(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多数作品至今尚不曾进入阅读和研究的领域。
广义地说,翻新小说属于续书的范畴。对于续书,有人说是“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刘廷玑:《在园杂志》)。对于《新石头记》一类的翻新小说,也有类似的评论。如《忏玉楼丛书提要》云:“作者为卖文家,欲其书出版风行,故《红楼》之名,以取悦于流俗。”其实,续书乃至翻新小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自有其产生的内在机制,至少有下列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结局的失望和不平。写作《三国志后传》的酉阳野史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引》中说:“及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刘汉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这就触发了他续写《三国志后传》的创作冲动。陆士谔的《新三国》,更是借以翻《三国演义》的旧案,通过“歼吴灭魏,重兴汉室,吐泄历史上万古不平之愤气”为由头生发出来的。翻新小说不同于以往续书的地方是,它们往往采用“蹈空”的虚构手法,利用时空的错位来制造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以达到宣扬自己对于时代的新见解的目的。陆士谔将“欧风美雨卷地来,世界顷刻翻新”的形势引入三国,让周瑜、孔明等穿戴古代衣冠的人物,登上改革开放的新舞台,演出亦古亦今、亦庄亦谐的活剧,以其对于晚清改革的“言皆有指,语无不新”的深沉思考和“局度谨严”、“气势蓬勃”的艺术样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二,植根于读者对于原著人物的热爱和关注。这些成功的典型人物,往往使读者忘却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感到他们仿佛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和自己同呼吸、共哀乐,有时甚至会忽发奇想:如果他们活到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王蒙的《红楼启示录》称贾宝玉为“病态环境中的病态人物”,并且作过这样的推想:“如果生活在今天,送去劳动教养三至五年,或许有救”。有趣的是,“贾宝玉假如还活着”这样的意念,吴趼人90年前在他灵心独具、异想天开的《新石头记》中,就作了充分展开的描写。吴趼人当然是深知“傍人门户”的局限的,他之借用《红楼梦》,只是因为这样写,能够同长期蓄积读者心底的感受相契合,因而能够更好地抒写“自家的怀抱”。
人物是旧的,环境则是新的,这是晚清翻新小说的共同特征。而从小说的主要人物同他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着眼,又可以将晚清翻新小说分为三种类型,并且从中体会出三种不同的韵味来。
第一种类型的特点是:让人物脱离他们原先的环境,来到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之中。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不走《红楼梦》续书“每每托言林黛玉复生,写不尽的儿女私情”的路子,而是另辟蹊径,写贾宝玉出家以后,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所炼五色石头中,单单只有自己未曾酬得补天之愿,凡心一动,热念如焚,便重新来到尘世。贾宝玉在他那个时代里,堪称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人物,一旦降临20世纪初的现实社会,却成了一名大大的落伍者。报纸上的“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月□日,礼拜日”字样,他竟浑然不解;比火镰灵便得多的“洋火”,已让他惊喜不置;取代了牲口的可以直通天津北京的轮船火车,以及与这些事物相关的买办、西崽、洋人,更令其惘然若失。幸好宝玉有极好的悟性,当他听说轮船是用机器驾驶时,就想到从前在怡红院中亦有“西洋自行船”……面对这些“都是生平未曾经见的”种种事物,这位既灵且痴,既能“悟彻前因”,又存“补天之愿”,既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史圣训,又一向不大安分、追新好奇的人物,不是简单的仰慕与崇拜,而是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既是中国的船,为什么要用外国人驶?”当听到“中国人不会驶”的回答时,宝玉道:“没有的话!外国人也不多两个眼睛,也不多两条膀子,有什么不会的!”“新”“旧”宝玉最大的区别在于,旧宝玉是“养尊处优中的颓废”(《红楼启示录》),新宝玉是内忧外患中的探索。宝玉下决心缩短时间悬隔造成的差距,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我既做了现在的‘时人’,不能不知些时事”。通过现实的学习和考察,使他充分认识到“以时势而论,这维新也是不可再缓的了”,从而完成了由厌恶“禄蠹”到喜谈“经济”的转变,成为具备新型品格的人物。尤其难得的是,宝玉在提倡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坚持了民族的自尊。洋行买办柏耀廉(不要脸)声称“中国人都靠不住”,宝玉反驳道:“难道连你自己都骂在里头?”柏耀廉竟厚颜无耻地答道:“我虽是中国人,却有点外国脾气。”宝玉大怒道:“外国人的屎也是香的,只可惜我们没有福气,不曾做了外国狗,吃它不着!”作者没有染上当时人所特有的急功近利的轻文化、重物质的毛病,更没有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必须以彻底牺牲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的错误观念。在小说虚构的“文明镜”中,既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更注意充分发挥中国文化本有的精神资源。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历久而弥新的成分,在未来的文明世界中,将长期存在下去。
和《新石头记》的格局类似的还有两部《新西游记》,但其命意不是宣扬正面的理想,而是通过主人公来到全然陌生的“新”世界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来讽刺世风的恶劣。冷血的《新西游记》写唐僧自从取了佛经,成了正果,过了一千三百馀年,忽又奉到如来佛旨,要他到西牛贺州去考究新教流行的缘故。神通广大、见多识广的孙悟空,一个筋斗,翻到上海,迎头就碰上了许多前所未见的新的器物和新的制度,闹了不少笑话。他首先来到四马路老巡捕房门首,看见一所又高又大的房屋,四周没有墙、柱、桷、檐,上下都用红砖砌着,门前站着一个黑髯大汉,心中纳罕道:“这是个什么所在?这又不是南天门,为什么王灵官替他守着门在这里?”当他重演以往在如来佛掌中做记号的故技,沿着壁撒了一泡尿时,那大汉竟把他一把拉住,责问他可知道“租界的章程”,怎么在马路上撒尿?孙悟空道:“奇了奇了,什么撒尿都有章程!”“四马路行者显神通”,写孙悟空被无数红头大汉围困,便与之变相斗法。他先是变了一只金毛狗,向人丛里钻去,红头大汉见金毛狗没有带嘴套,也没有挂牌子,便一齐道是“野狗”,闪出一个捉野狗的巡捕,拿着绳子就捉;孙悟空一吓,忙往地下一滚,变成一堆马粪,恰好又碰上扫马粪的前来打扫;孙悟空跳上一个房屋变了一个露台,不料工部局的人说这人家没有禀报,便自己添造,喝令拆去;孙悟空转身倒在地下,变成一辆东洋车,又来了一个巡捕,拿着木棍便打车夫,原来这车别的都变全了,单单少变了车后的马口铁(车照)……世界的变迁,就这样使神通广大的孙悟空处处失算,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小说还道出了如来佛开首要唐僧去考究的“西方新教”的实质:“以前只听得人说往西方去取佛经;如今往西方去取的却不是佛经了。”那么是什么呢?一位老者风趣地说:都去取那妖怪了。“妖怪”是什么?就是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
煮梦的《新西游记》则说三十三层天上,近因学术晦暗,国势衰颓,玉皇大帝便立了一座大学堂,招了一班八洞神仙三世诸佛来研究新学术,灌输新文明,以为富强根本。孙行者、猪八戒耐不得寂寞,跑到下界去了。小说里的孙悟空、猪八戒,依然会七十二、三十六般变化。猪八戒更是一个活跃的人物,他一会儿变女学生,一会儿变男学生,一会儿变官员,一会儿变警察,一会儿变留学生,一会儿变嫖客,一会儿变妓女,神怪的种种变化,基本上成了将散乱的情节贯串起来的手段,从而结成一部“学生现形记”、“官场现形记”、“教学现形记”、“选举现形记”、“警察现形记”、“嫖客现形记”、“青楼现形记”(一琴一剑主评话)的大总汇。《新西游记》继承《西游记》玩世主义的传统,其神怪的变形,更赋予小说以特有的滑稽趣味。如猪八戒变成姑山知县朱紫墟后,正在与姨太太鬼混,忽报真的老爷持刀杀回来。猪八戒摇身一变,变成了那统属文武的薛抚台,朱老爷不由的怔了一怔,便请安道:“刚才卑职眼花,错认了人,累大人担了一场惊,求大人饶恕则个。”猪八戒微笑道:“这也难怪你动气;戴了绿顶儿不动气,那不成了凉血动物了吗?”将官场人物的无耻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作者自叙道:“比者入世渐深,阅历渐裕,人世间一切鬼蜮魑魅之情状,日触吾目而怵吾心,吾愤吾恨,吾欲号天而无声,欲痛哭而无泪,吾乃爽然返、哑然笑,抽笔而著《新西游记》。”镜我生的序赞扬《新西游记》道:“其禹鼎乎?世间魑魅魍魉之形状,铸之尽殆矣。”他评论此书之铸奸,“以学界为最著,毋乃因魑魅魍魉以学界为最多乎?昔英国迭更司著《块肉馀生述》一书,以描写监狱中惨无人理之状,而英国之监狱乃为改良焉。他日吾子之书出而问世,彼教育家读之,其亦将改良吾国之教育乎?”小说的命意是暴露,而暴露的目的,则是为了疗救,其积极意义还是应该肯定的。
翻新小说的第二种类型的特点是:书中的人物并没有脱离所处的环境,只是悄悄地对历史背景作了“进化”的处理,将它整个儿地搬到新时代中来了。陆士谔的《新三国》依旧保持着三国鼎立的格局,依旧遵循着原书的事理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但形势已非昔日可比。小说写周瑜说孙权曰:“现今世变之亟,非特东吴开国以来所未见,抑亦皇古至今所未有也。夷风蛮雨,横卷东来,大秦、乌孙、月氏、身毒诸国,挟其轮船火炮之利,迫我通商,吸我膏血,若听其自然,必至同归于尽;至起与相抗,又虑力不堪支。”这里的“夷风蛮雨”,就是“欧风美雨”,大秦、乌孙、月氏、身毒,就是英、美、日、俄等列强,而周瑜提出的“臣愿主公奋发有为,创万古未有之法,应万古未有之变,而成万古未有之功”的建议,也正是那一时代的热点话题。陆士谔对《三国演义》的“翻新”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虚拟的“歼吴灭魏,重兴汉室”的“蹈空”的结局,与同样是虚拟的吴、魏、蜀三国对待改革的不同的态度及不同的改革模式直接挂上了钩,从而表达出作者对于现实的改革的种种不足乃至弊端的批评。在作者笔下,三国尽管还是三国,但它的历史大背景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旧的框架之中,恰到好处地融进一点新的内容,适如其分地做一点翻案文章,从而形成旧与新的既有强烈反差而又融浑一体的艺术效果。
在思想倾向上,《新三国》坚持了原书拥刘反曹、对吴则褒中带贬的立场,但褒贬的标准,却由传统的正统观或仁义观,演化为现代的改革观。蜀汉之所以值得肯定,主要不是因为大汉皇叔的正统,或是仁民爱物的仁君,而是因为是真正实行改革的模范。邓芝指出:“吾国之于吴、魏,非力不及而兵不逮也,然而每次出兵,终不能有所胜,何也?彼维新而吾守旧,彼知变而吾泥古也。”该如何实行改革?孔明的回答是:“变法亦大佳事。然法有本末之殊,吴、魏所行者,均新法之皮毛,虽甚美观,而无甚实效;吾国变法,须力矫此弊,一从根本上着手。”小说比较吴、蜀改革的不同道:“看官,你想吴国的变法先于魏、蜀,并且君臣合德,并无因循泄沓恶习,为什么周瑜、鲁肃一死,竟就人亡政息,弄到这般地步?错来错去,只因不曾立宪,不曾开设上下议院,不曾建立国会,凭你怎么聪明智慧,终不过君相一二人相结的小团体,如何可敌立宪国万众一心的大团体呢?否则以孙亮的智慧与后主的庸愚相比较,又岂可同日而语乎?只因一国立宪,一国不立宪。立宪的国,是聚众人的智慧以为智慧,其智慧就大得了不得;非立宪的国,只靠着一二人的小智慧,休说孙亮,就是周公、孔圣,恐也抵当不住。所以国而立宪,即庸愚如后主不为害;如不立宪,即智慧如孙亮也靠不住。”采用“翻新”的艺术手段来宣传改革,启发民智,同读者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完全合拍,由此产生极大的感召力量。
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新三国》对原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如对于孔明的“智而近妖”,世人向有微词,《新三国》则作了翻案文章。《新三国》还在孔明的性格中增加了新的成分,如七出祁山,派关兴率领气艇队前往眉雍两城侦察,众将见气艇上升,不胜羡慕,孔明笑道:“但愿诸军努力王事,俾天下早归一统,某当以此气艇队,作闲游之具,与诸君分乘之,以遨游乎云汉之表,遍察乎天下之奇,为御风之列子,骑鹤之仙人也。”表现出一种博大的胸襟。全书结束,写孔明见宪法尊严,学术昌明,社会进化,遂上表陈情,归隐南山,仍与崔州平、司马徽一班老友往来。这种处理,已非旧式的“急流勇退”可比,可说是具备了自觉废除终身制的意识。这些描写,既有新思想的色彩,又不与其本来性格相乖违。
珠溪渔隐的《新三国志》叙孔明病愈,思先帝托付之重,若不奋发有为,力图自强,则锦绣江山,不久将沧于异族。他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出在专制政休,故欲图自强,莫若庶政公之舆论,大权集自中央。但富于政治经验的诸葛亮,入手处却以教育为先,并逐步实行一系列变法,诸如改建警察,征集新兵,兴办路政,创办报纸,制定法律,办理农桑,设立银行,发展科技等等,格局都与陆士谔相仿佛。书中颇多关于办学校、练新军、筑铁路、种桑养蚕等等具体方法的介绍,读来不免枯燥,但作者之用意乃在提倡科学与教育,正是晚清新小说启蒙性质所规定了的。如孔明说:“‘蜀道难’三字遍传天下,我想改良道路,一雪此耻。而行路最便者,莫如铁路。”作者眼光之远大,令人感叹。小说以主要篇幅正写蜀国,吴、魏二国只作为陪衬,略写而已。
在情节叙写中融进新的审美情趣的是司马懿派韩寿潜入成都的故事。韩寿交结宦官黄皓,用催眠术催倒后主,让后主用剑砍伤北地王,又下诏开去诸葛亮丞相职务,为其南侵排除障碍。孔明乃派侦探福尔摩斯赵大,及聂格卡脱钱二、马丁休脱张三、海卫李四、多那文王六、雷斯屈兰陈九等,扮作魏国商人与官差,一举侦破此案。其时后主医治罔效,孔明乃大会群臣,请北地王暂摄国政。既饶有现实的兴味,又满足了读者的心愿,可谓神来之笔。
翻新小说的第三种类型介于一、二种之间,它的特点是:让小说的人物以集团的方式进入一个新的大环境,而其相互之间则仍保持固有的关系。进行这种尝试最早的是西冷冬青的《新水浒》。小说把宋江一心招安,同朝廷实行新政联系起来,于是众位头领陆续下山,各干各事,“将原书旧有人物一一妆点附会起来,若嘲若讽,且劝且惩,欲使人人知道今日新政上之现象,如是如是而已”。小说在纠缠旧作中,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如写雷横当了侦探,一心要捕着几个革命党,便可升官发财。他到书场听唱书,忘了带钱,有人认识雷横,说他是一个捕头,堂倌发话道:“目下是个强盗世界,那一处不可横行?就是一个捕头,也值得几文钱!”雷横分辩起来,堂倌道:“你么,平白时便做强盗,到得急了,假投降充捕快,卖送几个自己弟兄,巴结上司讨好,有时强诬陷几个平民,成就你升官发财的念头。到得街上,白吃的吃,白听的听,白看的看,拿进去的钱,供那妻子烧香拜佛,送给和尚道士尼姑去;到得人家做正经买卖,反欠着不给,还要爱听人家称老爷少爷,那一个耐烦你猪狗养成、豺狼狠心的等明日钱使!”与原书白玉乔不同,骂得真是义正辞严,痛快淋漓,极富时代气息。
在西冷冬青的《新水浒》中,梁山众人不免各奔东西,虽有宋江提议开一招待所,其间的联络仍是松散的。陆士谔的同名小说则不然。故事写林冲、鲁智深、戴宗到东京探听消息,方知朝廷已经维新,众人如大梦初觉,方晓得“众弟兄此刻都是新世界人物了”。吴用于是倡言变法道:“我们既处在新世界上,则一切行事自然不能照着旧法了,必须要改弦更张,大大的振作一番。”花荣因建议众兄弟离开梁山泊,各逞所长为本山谋利益。吴用则提议成立梁山会,于是忠义堂初行选举,以宋江为会长,卢俊义为副会长,萧让为书记,花荣、柴进、董平、阮小七、石秀、燕青、朱武、朱贵为庶务员,吴用为庶务长,蒋敬为会计员。宋江乃指派众会员下山,经营各种新事业。各人所得利益,提二成作为会费,二成作为公积,馀六成即为本人薪金。《新水浒》的人物情节,在细部上尽管是从社会现实中撷取来的,但其总体的构想,更多的是作者的发现和首创,因而不能不令人慨叹历史进程的回环往复和作者关于民主富强之路的探求的深邃和超前。在晚清时代,民族工商企业尚处于步履艰难的起始阶段,自然谈不上什么大型集团的体制改革问题。梁山泊实行的本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分贵贱”、“无问亲疏”的政策,过的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平等生活,这种带有“现代平等要求”色彩的社会集合体,它的经济运作是依靠“打家劫舍”来维持的,因而是难以持久的。对于这种类似“吃大锅饭”形态的社会集合体的改革,是绝对不可能在20世纪头一个10年提出来的。然而,陆士谔偏偏就在《新水浒》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吴用所建议的以提成为机制的近似于承包制的改革模式,无疑是具有极大的超前性的。
尤其令人叹服的是,承包制的试验虽然是陆士谔个人的主观臆想,然而他却确确实实预见到了推行此种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它固然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造成个人收入的不平衡,导致社会分配的不公。陆士谔关于梁山会员收入的多寡的叙述,透露了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所造成的社会分配的差别及其内在原因,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和预见性。搞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在于他们是依靠勤劳致富还是投机暴发,这才是一个社会肌体是否健全的关键所在。梁山泊一百单八人,在同一时刻投向社会,然而他们的起点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既有个人秉赋与素质的差异,又有社会联系不同,但他们的最终效益,不只取决于经营之是否得法,更与其所从事之行业密不可分:孟康的船政差使和卢俊义的承办铁路等,其奥秘无非是以权力作为原始资本,利用法律和体制的不健全,靠浮支公款、收受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成了暴发的权贵;扈三娘的夜总会、孙二娘的夜花园之类娱乐业,尽管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简单劳动(撇开其肮脏的一面),却由于商业化程度极高,迎合了市民社会的较低层次的(甚至是庸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竟获得极高的经济效益。梁山中人,只有李逵“一块天真,不识些儿诈伪,世路崎岖,人情叵测,他都不晓,只道天下人都似自己一般的直,一般的真,这种人到新世界上来,怎么不吃亏?”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在新的条件下,道德和竞争的二律背反,尖锐地提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效益和金钱为标尺的商业竞争激烈展开的情势下,是不是只有“利”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而“义”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道德的沦丧是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市场经济应是有规范的,这里既有法律的规范,也有道德的规范。从道德上讲,就是要正确处理“义”和“利”的矛盾。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荀子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2]社会上还有弱小者需要人们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去进行救助,公众还有许多有益的事业需要人们慷慨解囊,“仗义疏财”去加以支援。从《新水浒》的反面,是否可以悟出这些道理来呢?
注释:
[1]阿英:《晚清小说史》,177页、1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荀子·荣辱》,见《二十二子》,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