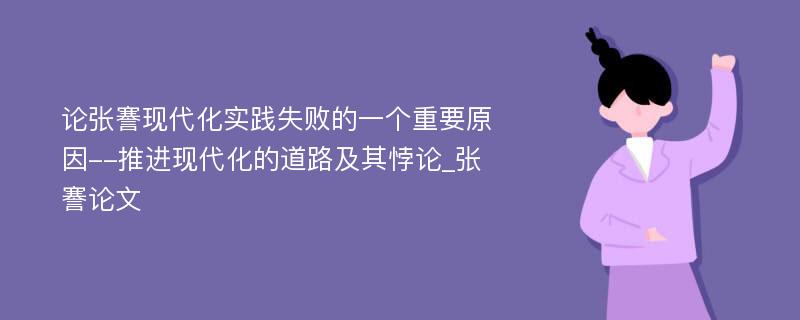
“急进务广”的现代化推进方式及其悖论——论张謇现代化实践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急进论文,悖论论文,一个重要论文,原因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2)03-0131-08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探索中,张謇为他心目中的全国试验田式的南通区域现代化选择了“突进型”、“一揽子”的推进方式,做成了许多开创性的业绩,留下了许多个“全国第一”。但是,屡屡出现的“坍江式”的事业危机证明,从整体上看,这一方式选择是一种失误。事实上,任何现代化目标体系的健康运作,都是以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合理的时序为支持的,毕其功于一役,就会出现大量的紧张、失衡、错位和阵痛,反而欲速不达,甚至还可能导致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张謇在这方面可说是吃足了苦头。
一、“突进型”、“一揽子”的战略推进方式
1922年大生危机全面爆发,张謇本人曾作如下精辟反思:“厂步艰难,一由于事大本小,一由于运筹失策,固无可讳;而时际之花贵纱贱,动受束缚,亦一大原因也。环顾国内纱厂,又孰不感此痛苦。”[1](P113)张謇投身实业30载,经营纱厂感受困辱挫折不胜繁多。大生危机在1922年突然爆发,本有其很特殊的历史根源(欧战结束,帝国主义掀起了新一轮对中国的侵略狂潮)和灾难性巧合(天灾),但是张謇并未完全归之于客观,而是抓住了主观上的要害:运筹失策。他对运筹失策主要解释就是“急进务广”:“南通实业,三五年来,急进务广,而致牵搁。”[2](P837)这里的“急进”也即战略推进中的“突进”方式;“务广”也即战略推进中的“一揽子”方式。
(一)实业发展的“突进型”战略
张謇在创业阶段办事十分谨慎、踏实。他从1895年开始筹建大生纱厂,从原料、市场、劳动力到经营方针、办厂方略,从筹资到管理部门的设置、《厂章》、《厂约》的制定,殚精竭虑,反复掂量,脚踏实地,务求周全。凭借这样一种谨慎务实的风格,他历经5年,忍讥蒙侮,克服了多次流产的危机,终于创立大生纱厂。为了防备纱厂原材料“供不应求之竞争”和“意外之变幻”[3](P882),他竭力主张办棉垦业。他于1901年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荒地进行植棉,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历经10年,获得显著效益。大生纱厂一度之所以能够以劣势地位与外资纱厂和洋纱洋布倾销展开力量悬殊的悍战并取得巨大成功,关键之一也正在于凭借通海垦牧公司的棉花生产基地,稳定和保证了纱厂的原棉所需,从而创造了被日本中井英基所称为的“原基的工业化论”道路,“这种‘原基’(proto)工业化论,是以农村工业与人口间的互相关联的机制,以及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地域间分业论为基柱,提供了后来农村工业化所无的崭新角度。”[4](P225)
但是,张謇创业初期的稳健的战略推进思想,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支撑而不能持久。初步成功之后,当基础并不牢靠时,一种激进思想快速地发育起来,开始较大幅度地扩张实业,形成了“突进型”实业推进方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大生一厂为原点的纱厂扩张。当大生纱厂初战告捷后,光绪三十年(1904)6月,张謇即决定建立分厂,规模2.6万纱锭。[5](P183)分厂建立后,设立了统管正(一厂)、分(二厂)两厂的大生纺织公司。自1914年至1921年,大生一、二两厂获利1000万两以上。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社会资金大量涌向纺织工业。这时通海垦牧公司的棉田逐渐成熟,大生收购垦区棉花有优先和赊购的特权,原料供应充足。张謇认为,扩大纺织企业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于是在1913年张謇当上北洋政府的农商总长之后,大生纺织公司拟定了一个庞大的纱厂扩张性发展计划,即要把棉纺厂从两个扩展到9个。除大生厂一、二厂外,增设三厂于海门,四厂于四扬坝,五厂于天生港,六厂于东台,七厂于如皋,八厂于城南江家桥。此外,还打算在吴淞设大生淞厂。[6](PP143-144)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列强卷土重来;加上大生历年盈利分配过多,积累薄弱;最关键的,张謇的扩张计划没有充分的科学合理的论证,因而这一扩张计划没有完全实现,只建成了三厂和八厂(后称副厂)。就是这样,大生纱厂从1899年1个增加到4个,资本增加近6倍,纱锭设备增加近7倍,固定资产增加18倍,遂使大生纱厂固定资产增加速度超过资本的增加速度。而投资资金全部是借贷而来。这种超过自身实际经济力量的扩张,导致企业基础十分脆弱,市场稍有风险,企业便险象环生。[7](PP143-144)
2、以纱厂为中心的企业多头扩张。在扩张纱厂的同时,张謇发展了以通州为枢纽的交通运输业,同时又建立了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复兴面粉公司、颐生酿造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隆皂厂、懋生房地公司、颐生罐诘公司、大昌纸厂、大聪电话公司、资生铁厂等。举办这些工厂企业,张謇也是经过构思的。比如,发展交通运输业是为了解决大生的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建油厂是为了利用棉籽榨油、压油籽饼;建皂厂则是利用油厂的下脚;建酒厂是为了利用当地的高粱、大麦,改善生活;建印书局是为了教育、宣传,也是企业印刷一些文件,如账略、说略等等的需要;建资生铁厂是为了给纱厂、垦牧农场造机器、农具,建电话局是为了加强公司间的联络。但这是一个从封闭小社会设计企业的思路,缺乏大市场竞争和协作的科学理念。尽管有的企业对大生纱厂的发展起了帮助和促进作用,如交通运输业。但多数企业的兴办,由于缺乏合理性论证,建成以后发展非常困难。如资生铁厂,从1905年建成到1930年垮台,基本没有造出什么好的机器。同时,短期内办如此多的企业,造成了资金的困难,给大生的发展设置了障碍。
3、以纺织工业为基础的垦殖业扩张。张謇曾一再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发展近代纺织工业“不兼农事,本末不备。”[8](P385)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棉垦业。应该说,这是对的。问题在于他推进棉垦业发展的速度太快。1911年后,经张謇兄弟广泛宣传,专营垦牧和兼营盐垦的公司风起云涌地办起来了。北至阜宁的陈家港,南至南通的吕四,东滨黄海,西界范公堤,先后办起了40多个盐垦和垦殖公司。张謇兄弟直接创办的就有通海垦牧、大纲、大佑、大有晋、大赉、大豫、中孚等多家;张謇亲属、门生、大生董事等与张謇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创办的有新通、新南、阜余、合顺、大丰、华成、合德、耦耕、泰和、裕华。垦殖公司一般是筹集资金,进行大规模农田开发。除最早成立的通海垦牧公司外,后来的公司因资金短缺,农田水利设施标准低,劳动力不足,采取封建租佃制度,严重影响佃农生产积极性,各垦区生产水平极其低下,最后只得借债维持。截止1920年,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5公司所负巨额债务,决非大生纱厂临时调汇能弥补。于是陷入极大的困境中。[9](PP166-174)
(二)经济教育社会事业“一揽子”推进
张謇把实业看作是教育和慈善之“本”,但是,他在这个“本”并没有完全牢固的时候,超越实业所能负担的限度发展教育和社会事业。我们从张謇给北洋政府的一个呈报中可知,张謇在10多年的时间里,办了大量的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南通教育慈善之发端,皆由实业。创办自始,或以謇兄弟朋好所得于实业之俸给红奖,或由謇兄弟朋友于实业有关系之人展转募集。教育除地方各村镇公立私立之初高等小学校二百四十余所外,凡专门之校六:曰男初级师范学校;曰女初级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附焉;曰甲乙种农业学校;曰甲乙种商业学校;曰纺织染学校;曰医学校。其缀属之事三:曰博物苑,曰图书馆,曰气象台。慈善除旧有恤嫠、施棺、栖流诸事外,凡特设之事六:曰新育婴堂,曰养老院,曰医院,曰贫民工场,曰残废院,曰盲哑学校。总凡十有六所。”[10](PP406-407)为此,他不仅自己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而且违背一个实业家应遵从的起码的准则,随意抽调大生企业的积累办他欲办的大量的事业,从而使大生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正是在这样一种“突进型”、“一揽子”的推进方式作用下,大生企业集团的基础已经极其薄弱,一有市场风险,就难以抵御。果然,当1922年中国市场发生棉贵纱贱的逆转,大生企业几乎毫无招架之功,纱厂从上年高额盈利一下跌入大量亏损。当年,大生一、二纱厂共结亏100余万两银,账面负债额高达835万余两。[11](P219)这是整个大生系统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自此,大生的经营持续恶化,连年亏损,引起债权人和股东的一片恐慌。大生信誉因此一落千丈,企业迅速陷入周转不灵的危境,不得不靠抵押贷款勉强维持营运。1925年张謇兄弟年老告退,大生纺织企业交由债权人上海银行团组成的“维持会”接管经营。[12](P226)
二、战略推进方式展开中的悖论与困境
张謇在全面快速推进他的南通区域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时,陷入了一系列的背反、冲突中,虽“力求精进”也无济于事。
(一)战略推进中的重重悖论
悖论之一:“本小事大”的矛盾。“突进型”、“一揽子”的推进方式,首先造成的一个悖论是“本小事大”。所谓“本小事大”,即指大生资本原始积累的薄弱,同时又要大规模和快速度地发展。张謇办实业20多年中,对资本的积累一直不予重视,基本采取竭泽而渔的经营方式。大生从原始资本不足45万两银子起家,发展到后来的拥有4座棉纺织厂、40多个企业、事业单位,总资本达3400万元的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资本集团——大生企业系统,其扩展的资金却建筑在极其脆弱的信用膨胀的基础之上。[13](P151)更有甚者,张謇还要在这样一种“本小”的情况下办“大事”,不断从企业抽调资本投向社会事业。这就使得企业本来脆弱的基础更为脆弱,从而根本经不起市场波动,一旦经营失利,随即陷入周转不灵之境,并不得不走上以厂抵债维持营运的险途,最终导致银团接管。
悖论之二:“营志营利”的冲突。有人说,大生不重视资本积累,这不是张謇的错。张謇一直坚持要加厚厂本,只是股东们不同意。其实,这只是一种现象。实质的问题是,张謇为了实现“突进型”、“一揽子”战略推进方式,无视经济原则,无视股东利益,导致股东的抵制,结果张謇只得以牺牲积累来保全继续实现激进主义的推进方式。1905年,立宪运动的热潮在全国掀起,张謇成了立宪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也随之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转变为“自治救国”,并开始对实业、教育、慈善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多管齐下。但是,张謇本身并无雄厚财力,实施方案的捷径只能是借助大生的资金和融资渠道。张謇动用大生的巨额资金去创办、扶植诸多的子公司和文教慈善实体,使当年的对外投资额比上年增加3.5万,对外债权额激增36万,次年又净增28万,总额达大生自身总负债的37%。而且,资金的抽调全是张謇一人作主,这直接违背了经济规则,威胁到股东利益,从而引起股东的责难。张謇为了换取股东们对他的既定决策的同意,竟在利润的分配上向股东作出让步。大生从该年起停止提取存余,有利尽分,而且把以往的存余也分光用光,人为地把当年红利率拔高到22%。[14](P737)张謇的这一决策埋下了极大的隐患:一是大生股东只重厚利,不顾企业的长远前途,凡赢利之年,股东得利全分,绝不肯加厚厂本;亏蚀之年,宁借债发息,也不愿停息以资营运。二是张謇既要满足股东的利益欲,又要扩展企业,还要大办教育和慈善公益,为此,不仅堵死了大生资本积累的途径,而且敞开了资本外流的口子,活力大受削弱。
悖论之三:“任重能浅”的尴尬。张謇采用“突进型”、“一揽子”的战略推进方式,所创事业的起点低、规模大、速度快。这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多方面的现代化任务突然一起提出来,从而造成了突然提出的大量新任务与主体能力发展之间的异步性。这种异步性首先表现为张謇等管理阶层的能力不适应。习惯于传统管理方式的张謇以及下面的管理人员,很难一下子理解、接受完成新任务所必须的新的操作管理方式,不要说适应和运用了,他们对新操作管理的适应有个过程。这与他们的阅历和经历有关。这批人大多出身于封建士绅和官僚,又没有具体学习和接触过现代管理方法。所以,只得一直沿用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因而,当这些任务全面展开以后,他们就经常陷入管理困境当中不知如何是好。[15](P739)
李升伯的成功正好反证了张謇等能力的不适应。债权人上海银团接管大生企业集团后,派29岁的李升伯接任大生经理之职。李升伯曾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纺织学院攻读纺织工程学,后又考察了美、英、法、意、瑞士和日本等6国纺织工业。他使大生企业集团重新转机的关键,就是在管理上超越张謇。得力于李升伯现代管理能力,在其任职大生期内,从工厂的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设备更新到原料、生产、销售等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调整。1927年至1932年企业均获赢利。副厂还清全部借款,大生一厂也偿还了100万两债务。[16]濒临破产的大生重现复苏之态。
这种任务与主体能力间的异步性,还大量地表现为突然提出的新任务与社会成员能力不足的矛盾。社会成员能力的提高,不仅是通过教育提高素质的问题,而且是通过实践增强能力的问题。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实践也必须有一个过程,所以,社会成员能力的不足和新任务的繁重构成了明显的不平衡。而张謇早期的创业中,也已经深深感到人的能力跟不上去,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的工人几乎全是文盲,目不识丁,下层管理者,也都识不了几个字。大生纱厂的技术长期受制于外国技术人员,且难以快速提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普通人员能力跟不上去。而农科学校在通海盐垦垦区试验棉花新品美棉,技术力量也跟不上去,屡屡失败。好不容易培育了国产优质鸡脚棉(这种棉品质虽好,但只能适用于16纱支以下的生产,20纱支以上仍靠进口美棉),因垦区农民都是文盲,推广困难,许多年后才得以小范围推广。张謇感到人的能力方面的压力,下决心抓人的素质。但是,由于步子太快,精力和财力过于分散,事实上是欲速而不达,所有的事业都只能在低水平上“铺摊子”。人的素质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新任务。
悖论之四:“济民劳民”的背反。张謇办慈善,是为了“救民”和“济世”。但是事实上,他的纱厂和垦区中的剥削十分残酷。张謇在低水平上的广铺摊子,使纱厂、垦区的管理、技术改造都缺乏足够的财力和精力的支撑,因而使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为了维持一定的利润率,于是就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大生纱厂全盛时期的工资,男工日工资2角5分至6角,女工日工资2角至4角,童工工资则更低。一般难以维持生活。每天劳动时间均在12小时以上,有的高达16至18小时。除此而外,还有种种超经济的强制和压迫。残酷剥削引起工人的极大不满,终于在1921年,爆发了一次全厂规模的怠工,斗争的结果是工人工资每天增加2分。[17](PP152-164)垦区的剥削更为残酷,交租时,先付给公司农田收获之四成外,再向代为筹措费用的公司人员偿付三成或四成。这样,佃户辛辛苦苦一年只能得二至三成,加上高利贷的盘剥,佃农也很难维持基本生活,因而反抗不断。[18](P132)这些都说明当时大生和垦区的穷富矛盾极其尖锐。所以,当张謇大规模地扩大垦殖事业时,招工已远不如通海垦牧公司的初期那么顺利,劳动力数量远远不足,这严重影响了后来开办的垦殖公司的正常经营。正如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指出的,低层社会对现代化反映的“迟钝”,实在是因为“公平互换”的缺乏。[19](PP453-478)
(二)战略推进中的逆向效应
“突进型”、“一揽子”的推进方式,引发了发展中的重重悖论,从而带来了战略推进中的一系列逆向效应。
1.形成了对成功目标再发展的严重制约。按照合理性的思考,目标的展开必须瞻前顾后。张謇恰恰违背了这一原则。张謇的各项事业的扩张,基本上是在大生纱厂有利尽分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大量挪用大生的资金进行的,这就使原本发展得较好的大生一、二厂后发无力,失去了财力的支持。根据姜伟对大生年度财务报表的统计分析,1920年,一厂的余利50万被划为航业公司股本,余利36万被转为八厂股本,多年公积近17万被转为三厂股本;1921年,余利44万被划为八厂股本。同时,大生还大借外债,并转给子公司和教育、慈善、公益等事业。单筹办12个垦牧公司,张謇兄弟从1916年至1921年就从大生集资款中挪走近1千万元。而大生对子公司的短期债权额成倍增加,债权额达到311.57万,占自身负债总额529.78万的58.8%,已接近于净资产378.6万。这时,整个大生集团拥有69个企业(包括垦牧和有关事业单位),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全靠囊中已空的大生一、二厂支撑。这不仅使大生企业集团这棵大树完全建立在毫无养分的沙滩上,经不住任何风浪,而且项目的急速启动,严重扼制了大生一、二厂的发展,大生一、二厂直到上海银团接管前,设备较开办时几乎没有更新,技术也没有一点长进。
2.过早地调动了现代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目标的展开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不宜把难度大、阻力大的问题放到前面解决,否则过早地调动起不利的因素,会延误甚至破坏发展的进程。在这方面,张謇也是没有考虑的。改造中国的传统农业,这是经济目标中一个最难的子目标。如果张謇出于对纺织原料的考虑,先进行试验,逐步推开,那是可以的。比如先搞个把通海垦牧农场;但是大规模地过早推行,则使传统农业中的许多不利因素调动起来,如封建佃农制在垦殖公司的复燃,资金缺乏引起的落后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的不可避免、生产率低下和剥削的沉重、过重的债务,等等,不仅使垦殖公司的现代化成为泡影,而且对整个区域现代化造成财力和精力上的拖累。
3.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化因素没有成长的条件。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理智的做法在于,当某些现代化的因素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得小心呵护,千方百计为之积累条件,使之能够成长起来。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式国家,因为没有现代化因素的深厚积累,更要稳打稳扎。否则,在一些现代化的萌芽未长成大树之前,就会被传统的因素吞噬。由于张謇的急进的推进方式,常常使花了很大的功夫刚刚有所发端的现代化因素又倒退回去。比如,他按照大农的思想创建通海盐垦公司,花了10年的功夫把零碎分割的土地连成大片,为机耕大农业准备了前提条件。但后期由于各项事业铺的摊子太大,没有经费支撑,更由于制度跟不上,大片的土地后又被分割成犬牙交错,连后来资生铁厂为垦区生产的水泵都用不起来。张謇花了10年功夫集田成片搞机械大农业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张謇创办了同仁泰盐业公司,试图仿照日本盐场利用新法集中制盐,他投资4万元使日式制盐法试验成功。但是由于张謇投资范围太宽,囊中虚空,只得加紧对盐工剥削,盐工运用新法集中制盐,收入不如在家用老法制盐高,而且在家制盐可以兼做其他副业以贴补家用。因而,同仁泰盐业公司不容易招到足量的工人。从1911年起,以集体聚煎为特征的新式煎盐法虽投入大量资本试验成功,也只好搁置,恢复了传统的分散生产方式。[20](PP83-86)像这样的事情,在张謇的一生中是很多的。
三、激进方式与合理性精神的缺失
上述种种悖论和困境,一直困扰着张謇后期的事业。张謇是以慎于出处而著名的,在办纱厂的初期更是谨小慎微,为什么后来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在不具备“突进型”和“一揽子”战略推进的条件时,却这样强行推进战略呢?
人们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往往认为初期源源而来的利润;一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向中国出口减少,为国内民族工业发展让出了一些空间;民国期间张謇的权力上升,等等,是导致张謇推行激进方式的主要原因。[21]笔者认为,这些原因都是直观层次上的。致使张謇强行贯彻激进务广的推进方式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在战略把握上的合理性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为:
1.在战略前提的审视上,缺乏市场理性。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早期现代化推进战略的选择就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条件: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客观地说,张謇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他办实业,就是要应对世界市场,应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利益剥夺。针对欧美日本向中国倾销棉纺织品,直接威胁中国的经济利益,张謇提出,应该“迅速在此地建纱厂”,“塞漏”,以“杜民间权益之外溢”;[22](P42)纱厂生产需要棉,需要机器,又提出“棉铁主义”[23](P784)主张,并付诸实践。但是,张謇对世界市场缺乏理性的超越。他曾说,世界市场的进逼态势使他“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如行深山,临悬崖,榛莽四出,披而始识无路;如泛雾海,见一岛屿,若隐若现,而始得所趋。”[24](P784)他的这种直观感觉十分可贵,但他没有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进而获得对世界市场的理性认识,即把握世界市场的竞争态势和规律,寻求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律推进民族工业的科学思铬。因而,他办实业的思维始终停留在“塞漏”的基点上,他与当时许多以“工业救国”的有志之士一样,试图通过建立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实现进口替代,夺回被列强占领的市场,摆脱贫困和被奴役的状态,而茫然不顾世界市场的竞争态势和规律。市场理性的缺乏,加上以“塞漏”为目的的民族工业主义思想激励,很自然地引导到对工业规模和速度的追求。而国外的竞争对手早就看到了中国人的这一弱点,当中国人把大把大把的钞票用于低水平的工业规模扩张的时候,他们却把大把大把的钞票用于技术改造和新领域的投资。这就预示着,中国人的低水平工业规模越是扩大,在未来的世界市场竞争中就越不堪一击。战后,日本正是挟其精良的技术,加上雄厚的资本和在华种种特权,垄断中国的棉产市场,大肆掠夺中国廉价纺织原料、倾销纺织品,日资纱厂几乎遍及中国沿海沿江各大城市。仅止1925年,日在华投资棉纺织业就达15家公司、48个工厂,纱锭突破150万枚,织机7000台,占中国全部纺织设备的1/2和1/3。[25]日本棉纺织业的扩张,迫使中国纺织业走上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面对20年代的这种新形势,华商纺织企业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管理竞争、技术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模实力的竞争(集团化)。作为当时国内最大企业集团的大生纺织系统,其实已是外强中干。它在1920年前后的大规模扩张行为,恰恰错失了这一时代的起跳点,从而导致了随后的迅速衰落。
2.在战略要素的思考上,缺少数字理性。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称为“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26](P38)他曾经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金钱可生金钱”,[27](PP33-34)的话来说明这种数字理性。为了使“钱生钱”,西方资产阶级认真地研究资本的运作规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操作资本,理智地使用每一分钱,以达到不断孳生金钱的目的。张謇在推进战略的最基本要素的思考上,明显缺乏数字理性。中井英基曾说到当时中国人办纱厂与日本人办纱厂的不同。日本最初只有2千纱锭试生产,反复研究世界市场上纱布的技术竞争和销售竞争情况,进行试验性生产,经过13年才发展出一个1万纱锭的大阪株式会社。而中国人不经过实验阶段,洋务派办纱厂,一开始就依托于中央政府财政,不惜代价大张旗鼓地搞规模,刚上马就是几万纱锭,并迅速扩张,其实是低水平重复。中国的棉纺织业与日本虽然几乎同时起步,但以后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日本进展神速而占优势,中国却落后了,处处受制于人。[28](P226)日本人这种小规模实验、谨慎地推进的做法,正体现了这种小心翼翼追求“钱生钱”的理性精神。在这方面,张謇未能接受洋务派的教训。他被初次的成功而鼓舞,也被资本蜂拥而来的假象所蒙蔽(这些资本是由大生盈利并付股东厚息而刺激起来的),从而觉得可以通过大量拆资来大规模扩张,而并不论证这样干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营志,而不计算获得的多少。事实上,由于违背资本运作的规律,他却陷入了本小事大的陷阱,一步步走向信用危机的深渊。在战略要素的思虑上缺乏数字理性,使张謇的激进务广的推进方式缺少了基础性的制约机制。
3.在整体战略的谋虑上,缺少决策理性。后发现代化国家与原发现代化国家不一样。原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任务是逐步提出来的,而且全部现代化任务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逐步完成的。而后发国家现代化的任务一般都是一起提出,并要在较短期内完成。但是,后发国家尽管不允许如原发现代化国家那样用很长的时间慢慢地去完成现代化的各项任务,但事实是,顺利地推进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较合理的时间跨度,并在这个时间跨度内合理有序地展开目标。这里牵涉到两大问题,一是目标展开的时序问题(所有目标同时展开,还是一个个地展开,一个个展开的顺序是什么),二是达到目标的时间问题(是短期达到全部目标,还是较长时间达到)。按照何种时序,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根据本国本地的实际情况,极其理智地作出分析判断,而后作出合理性选择。这需要决策理性的驾驭。如果缺乏这种理性把握,就可能引起急躁情绪,产生整体战略筹谋中的急进思维。
在张謇的全部战略当中,我们无处不见到直追三代、经世济民的伦理追求,无处不见到一种伦理上的激励与鞭策,而见不到合理性决策思维的牵引。20世纪的实践表明,在官绅推进现代化的国家中,激进、冒进的灾难每每发生于这种缺少决策理性的伦理激励的内心冲动。张孝若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的一段话,准确地说明了张謇在这一方面的思维特征。他说:“他只认定凡自治先进国应有的事,南通地方应该有,他就应该办;他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29](P375)“不问困难不困难,只问应有不应有”,尽管表达了张謇对南通区域现代化的强烈追求,一种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意志,但是,正是这样一种缺少决策理性的纯粹意志,促发了他整体战略构思上的激进思想。张謇构思了一个“四元”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提出了南通的现代化发展的多方面的任务,试图把南通建成“新新世界的雏形”。尽管他告诫人们:“救世之道,功不必期其速,事不可遗其小。日本之自治,五十年而后成。美国则几及百年……唯事贵有恒,非一蹴可几。得寸积尺,得尺积丈,各本固有之地位,以谋发展之机会,必能有济。”[30](P440)但是,由于缺乏决策理性,他茫然不知如何根据客观条件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目标,而是“只问应有不应有”,“不问困难不困难”(实际是“不问可能不可能”),极其迅速地、“一揽子”地整体推进。用他自己的话说:“南通实行自治二十余年,雏形虽具。”[31](P440)日本用50年,美国将近100年,而南通只20年,可见速度之快。但是,这种快速却埋下了祸根。
耐人寻味的是,由于战略运筹中决策理性的缺乏,主观上的政治热情、客观上的先进国家的示范效应,都能在战略上导致急躁、急进的情绪。
缺乏决策理性制约的政治热情,最容易导致整体战略构思中的激进主义。由于后发、落后、被欺负,因此怀着强烈的爱国、自强的民族主义热情。我们决不否认这种爱国自强民族主义热情的历史价值,这种热情甚至激情,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可宝贵的精神动源,它会激励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艰苦奋斗,顽强开拓,赶超先进,努力使自己的国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热情也好,激情也罢,不管其多么崇高,如果没有决策理性驾驭,很容易鼓荡起人们的一种激进情绪,因为他们做梦也盼望着国家的振兴,这种急切的期盼,会使人们不经过科学决策,不顾条件是否允许,无视事物发展的规律,强行推进他们想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以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摆脱被帝国主义列强欺负的局面。而这种强行推进,往往就是失败的开始。张謇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强烈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他办大生纱厂和盐垦公司,就是为了结束那种“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无疑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拥有4万万人口之中国,而衣食所资,事事物物,仰给别人”[32](PP1-2)的落后挨欺的现象。由于缺乏决策理性,所以,当大生纱厂和垦牧公司初战告捷,这种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急于扩大规模,以期及早实现“每岁输入一万二三千万两之棉类,皆可以国内人力之为之,而不必仰给于舶来货物”[33](P3)的愿望。在他当农商总长时,这种心情更是迫切。他曾向袁世凯呼吁说:“自我国奖励植棉条例颁后,各国颇为重视,而日尤甚。日本和印度有十年内在中国地方增设纺机一百五十万锭之约。其在日本本国,上冬今春已增锭三十万,在我上海已增锭十万。悍战可畏!果如所计,我国枝节进行,已病驽钝;若更迂滞,则市场充塞,十年之后我棉业岂有伸展之余地?”正是这样一种御侮、自强的强烈冲动,使他拟订了大规模发展棉纺织业和扩大改良棉田等计划,并且首先在南通推开。由于没有经过理智的决策,对当时世界棉纱业市场因新一轮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新的竞争态势缺乏必要的敏感和有效的应对措施,低技术水平的生产规模扩得越大,失败得也就越惨。
缺乏决策理性,加之先进国家的示范,会刺激后发国家开拓者在整体战略构思中的激进情绪。把自己的落后与别国的先进比,常常会激发出一种加快步伐追赶的激情,这种激情如果缺乏理性的超越,就会转化为整体战略构思中的激进主义。比如,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经济示范,会大大增强落后国家的开拓者们对尽快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强烈期望;其教育文化示范,也会激发后发国家的开拓者们努力地去效法和追求;城市化的示范,也使他们渴望有更多的财力投入城市建设。如果有决策理性的驾驭,示范效应再强烈,人们也会在一个有理有利有节有序的规划中,一点一点地去实现。张謇1903年东游日本,日本国明治维新后的繁荣,对他触动很深,他尤其羡慕日本“三四十年之间,由小国而跻于强大矣。”[34](PP6-7)他在参观北海道时有一首诗,题为《一人》:“一人有一心,一家有一主。东家暴富贵,西家旧门户。东家负债广田地,西家倾家永歌舞。一家一嘻嘻,一龙而鱼一鼠虎。空中但见白日俄,海水掀天作风雨。”这里东家比日本,西家比中国。他非常羡慕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日俄战争日本的胜利证明了日本的确很强大。而中国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旧有水平上,他感到一种深深刺激。从日本回来后,他一方面完善了南通实业教育慈善公益发展的目标体系,另一方面,加快了实施的速度,但是,这种速度的加快,却没有理性决策的依据,而只是一种盲目的急进行动。
标签:张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