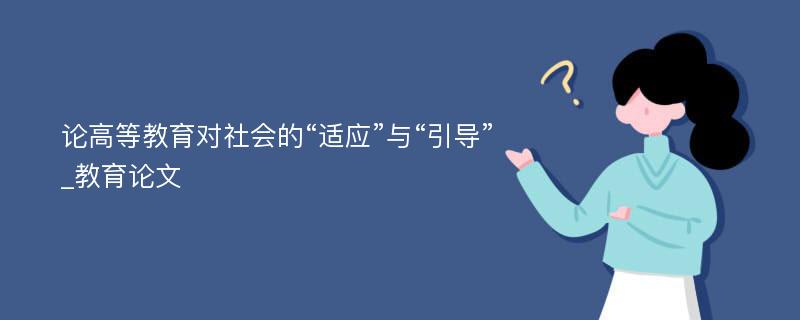
论高等教育对社会的“适应”与“导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与高等教育角色定位
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与本世纪60—70年代相比,正呈现出以下共同的趋势:(1)从主要依靠资本和物质的投入求得发展,到主要依靠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科技含量的增加;(2)从单纯的经济增长到综合的社会发展;(3)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 (4)从追求一时的繁荣到重视可持续的发展;(5)从被动的依附性的发展,到通过对外开放、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并最终实现“内源性 发展”,等等〔1〕。与以上趋势相关联、相一致的另一个趋势是:教育、科技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作用不断增强。
经过1978年以来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已经或将要出现上述战略转变。在1995年5 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正确决策。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要求我们重新考虑高等教育在社会变革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角色定位问题。对高等教育而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首先,意味着教育、科技的发展要服从、服务于“兴国”大业,高等学校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摒弃脱离现实而一味追求学术卓越的传统,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其次,“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比较特殊而又十分关键的重要角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当它被劳动者所掌握并运用于生产实践,才可能由潜在形式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与训练,正是这种“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又是新的科学技术诞生、发展的“温床”。这样,高等学校由于一身而兼二任—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再生产”与“转化”,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在“兴国”过程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当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作用。第三,“科教兴国”战略要求高等教育更积极地参与现代化进程,不仅主动适应社会变革,而且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影响、规范、导引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协调的过程中,在注重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促成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的过程中,在追求“可持续发展”与“内源性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全局性、先导性影响。
既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日益增大的能动性;既要主动适应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又对这种变革与发展产生全局性、先导性影响。这就是我们对高等教育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地位、作用与角色的新的定位,也是“科教兴国”战略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这一定位的“新”,就在于明确提出高等教育除“适应”社会需要之外,还有“导引”社会以促其发展进步的功能与使命。
那么,这一定位能否成立?高等教育“适应”与“导引”社会的观点有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
二、有关教育社会功能的理论评析
1.社会学家的观点
—认为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是随着社会的进化、变迁而变更的。社会学的奠基者E ·涂尔干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决定论者”。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在于使个体“社会化”与“专门化”,而决定教育发挥这两大功能的,还是整个社会以及特定的社会环境〔2〕。
—认为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美国社会学家L·F·沃德在其《动态社会学》一书中认为,人类有足够力量控制自然力和社会力以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主要因素〔3〕。
—认为教育既是业已发生的社会变迁的结果,又是出现新的社会变迁的潜在条件。一些社会学家既把教育视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又把教育作为促进社会有控制地变迁,有秩序地流动,尤其是纵向、垂直流动的一种变量。
2.教育哲学家的观点
—杜威的见解。“进步主义教育哲学”的领袖杜威主张教育要以“儿童为起点,为中心,为目的”,但又“相信受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因而将在教育过程中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视作“一切教育的根本问题”,将“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作为他的教育信条之一〔4〕。在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杜威又提出“教育必 须参与社会的改造”〔5〕。杜威的这一观点后来被他的学生、 “拓荒思想家”团体的代表人物G·康茨奉为圭臬,并经过康茨和T·布拉梅尔德等人的阐发光大,终于形成声势颇壮、影响深远的“改造主义教育哲学”思潮。
—“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的宗旨。“改造主义”者主张以明确的社会改造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认为决定教育工作计划的基础是“理想社会的形象”,学校应力求为“正在形成中的”而不是现存的社会培养教育公民。G·康茨在《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的著名演说中断言,教育机构可以领导社会去探求、实现社会的价值标准和理想,成为社会变革的“起动者”。他要求教育“有勇气断然正视每一个社会争论问题,千方百计地解决其全部现实生活问题……形成有关人类命运的有力的使人信服的和挑战性的远见”〔6〕。很显然,G·康茨过分夸大了教育的社会改造的作用,忽视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而“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的另一个旗手布拉梅尔德对“教育改造社会”这一命题的界定与阐述,就较为理智、客观。首先,他把教育看作“广泛的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过程”。其次, 他认为教育不是单义的或单边的文化适应过程,它既是“一种稳定、传递和保证文化连续性的过程”,又是“一种纠正、改进和变更所获得的前辈人特性的过程”〔7〕。 也就是说,教育在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传递给新一代的同时,也在“修改”着、更新着文化。第三,他强调“危机时代”教育的“修改”作用应当强于其“传递”作用,因为强调“传递”的教育难以完成改造文化的职责,必须使教育成为文化改造也就是社会改造的必要因素〔8〕。
—“永恒主义教育哲学”的主张。以R ·赫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教育哲学”,从另一个角度反对教育对社会的“适应”,而主张教育的使命是“改造世界”、“批判社会”。赫钦斯认为现代社会始终处于持续不断的剧变之中,职业的更替更是变幻无穷,学生实际上永远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适应”。他又认为,尽管社会的外观(“事实”)在不断变化,但人类社会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念都是“永恒”的。因此,他主张“以不变应万变”,应当通过实施“普通教育”,通过对“永恒”观念的理解和掌握,培养有理智的、完整的、充满活力的人,使他们有能力去认识并改造变化中的社会。赫钦斯对大学教育的彻底“世俗化”、“功利化”表示强烈的不满。在《学习社会》一书中,他十分尖锐地质问:“大学究竟是为社会服务还是批评社会?是依附于社会还是独立于社会?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是迎合眼前的实际需要还是传播及光大高深文化?”〔9〕赫钦斯不加分析地反对大学对社会的适应与服务,无视社会对教育的制约作用而主张大学完全独立于社会,倡导“永恒”的经典名著教育而排斥应用性、职业性课程等,无疑是失之偏颇或守旧、迂腐之见。但是,赫钦斯的教育思想中仍然有许多精辟见地,诸如大学应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大学不应一味地迎合眼前需要、追求功利而放弃自己的理想,大学应当通过对社会的批判和培养新人来改造社会等等,至今仍有其深刻的启迪作用。
—当代高等教育哲学家的认识。美国高等教育哲学家J·S·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以追求高深学问为宗旨的“认识论哲学”,一种是以对国家发展有实际效用和深远影响为宗旨的“政治论哲学”。60年代以后的美国是“政治论哲学盛行”的时代,大学“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它是新思想的源泉、倡导者、推动者和交流中心。”〔10〕其他一些学者也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智力城”、“思想库”、“精神圣殿”、“轴心机构”等等名称;来突出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当今和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虽然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可以有多种解释,但它已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因,这是不可否认的。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对教育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但并没有忽略教育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力。马、恩把“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视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之一;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11〕。此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都通过所摘录的“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一段评断”,表述了他们对教育对社会形态变革的能动作用的理解。摩尔根这段话把“普及的教育”作为促使那“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历程终结,同时“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还特别在“社会的下一个更高阶段”这段话旁加注是“高级社会制度”。很显然,马、恩把教育因素当作促进资本主义“自我消灭”和共产主义最终实现的一种力量,一种手段〔12〕。此外,马克思还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高度评价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这“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3〕。
毛泽东早年赞同“社会本位教育说”,并曾多次付诸实践。1919年他撰写《学生之工作》,认为世界的改造、进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同时他又认为学校教育的改良一定要与家庭和社会的改良同步进行,相互配合,方才有效,否则就是“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14〕。1920年7月, 毛泽东倡导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在由他起草的“宣言”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教育作用的见解:“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1921年前后,由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对教育的认识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他听取并笔录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长沙的演讲,对于罗素通过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以求社会进步的主张表示异议。他在写给蔡和森的长信中表示:“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通过教育的方法使资本家“回心向善”、“自己收场”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他的最终结论是:“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共产党人非取政要,是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15〕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识到社会的根本变革不是教育所能独自承担的重任,认识到政权和社会性质对教育的制约、决定作用;但又并未否定教育对社会改造与更新的功用。他在1921年8月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宣言”和“入学须知”中,仍然强调求学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为革新社会作准备”〔16〕。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已将教育纳入整个中国社会革命的总目标,将教育视为革命的重要一翼。
三、高等教育“适应”与“导引”社会的辩证统一
1.教育既意味着重复、再生,又体现着创造、更新
教育既是历史的产物,又是面向未来的伟大事业。这是人们审察教育活动看到的一个貌似矛盾其实统一的事实。
教育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教育最初始、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存和传递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就是重复与再现。即“重复地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并且“再现当代的社会和现有的社会关系。”〔17〕这样的教育体系有助于巩固现有的社会结构,并促使受教育者适应现有的社会生活。然而,教育又是着眼当代、面向未来的事业,教育还意味着创造和更新。就受教育者而言,“学习是把个人目前的情况同过去的经验统合起来,准备使这一统合所产生的潜力应用于未来的一体化过程”〔18〕。人们所受的教育越多,他们就越能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就整个社会而言,无数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教育从而获得更新、提高的个体,无疑将加快社会的更新与改造。在新知识层出不穷、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教育的前瞻性和创新能力,已经超越其重复、再现能力而得到空前强化。
2.教育既受社会的制约,又不无能动作用
教育是在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错综复杂的社会联系中,对社会的发展变革施加自己的影响,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教育的受制约程度与反作用强度,是随着一定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救亡图存的战争年代,“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论者之所以碰壁,是因为单靠科学与教育的力量不足以消除民族、社会的危机。而且旧中国的统治者不允许科学与教育的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近半个世纪的今天,“科教兴国”之所以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决策顺利实施,是由于发生了3 个根本性变化:一是社会主义的自我革新与自我完善,为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大展宏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新的科技革命和信息社会的临近,使教育、科技的能动作用成倍增强;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指出了明确的目标,制订了清晰的蓝图。目前,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已经指明,道路亦已开通,由教育推动社会变革的设想正在成为一个逐步展开的伟大现实。
3.高等教育“适应”与“导引”社会的辩证统一
所谓高等教育对社会的“适应”,包含两层涵义。第一,要求高等教育摒弃那种自我封闭、自我欣赏,漠视社会变革,只求学术声誉的过时哲学,把自己的发展与沸腾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第二,要求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与现有的国力。许多学者、专家已认识到,一方面,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的,高等教育不应也不可能一一适应并满足所有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及其对高等教育的制约,既有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又有消极的、负面的作用。因此,人们又提出不应一般地、不加分析地“适应”。而应当主动地、有选择地适应其积极的一面。这就强调了教育作为主体的自觉的判断和选择作用。
然而,我认为仅仅提高等教育对社会的“主动适应”还不够全面,还不能充分表达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常常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政府或有关方面总是要求高等教育更多地“着眼于国家的经济需要”,“更有效地为经济发展服务”。这固然是正确的,但如果看不到高等教育应当有更加长远的、广阔的目标,看不到经济发展应与社会进步相一致、相互促进,则这种社会需求就未免失之于狭隘和短视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还常常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压力,他们往往重视实用技能的掌握而忽视人格素养的培养,往往过分追求个人择业的成功而忽略对社会的服务与贡献。对这两方面的“需求”若不加以导引,仅仅强调“适应”,将有悖高等教育的理想,既不利于高校的健康发展,也难以妥善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诸多精神、道德和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的变革和经济的增长常常是一柄“双刃剑”,除了可能出现失误,导致混乱无序外,还可能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伴生一些消极、负面的东西。高等教育的积极参与和批判、倡导作用,将会减少决策的失误,抵销负面影响,缓解社会矛盾。当然,高等教育的导引作用,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对它的制约性而无限膨胀;高等教育改造社会也决非是单干独闯,而必须与社会的其它机构、活动相互配合;高等教育不是社会改造的充分因素,而只是社会改造的必要因素,它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越俎代疱,包揽一切,或者凌驾于其它社会结构之上。
既主动适应社会需要,又积极参与、导引、规范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这就比较全面地表述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恰当地体现了制约性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
四、高等教育“导引”社会的基本方式与途径
第一,培养既能适应当今世界,又能创造未来社会的新人。高等教育的“导引”作用首先体现为对跨世纪人才培养的主导作用,要造就千百万全面发展、富有理想和创新能力、充满活力的改革者与建设者。他们跨出校门之后将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志向、抱负、气质、才干将对更多的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带动更多的人生气勃勃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要看明天的社会,先看今日的校园。”高等教育对社会进步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性、先导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塑造新人来实现的。
第二,参与民主决策,保证社会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战略、原则和基本构想,但要付诸实施,还需结合实际进行具体规划、科学论证。高等学校要成为思想库、智力城,组织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参与并影响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决策过程,以避免其出现大的偏差与失误。
第三,促进科技进步,加快产业改造和经济增长方式变换。美国的斯坦福一硅谷创造了教育、科技生产一体化模式,预示着信息时代新的社会结构形式,我国北大“方正集团”带动全国印刷排版行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清华大学研制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正在引发机械制造业的深刻革命……这些都是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联袂导引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
第四,价值澄清与文化批判。我国正处在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文化转型和社会转型时期。价值准则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抬头,都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显得分外紧迫,分外艰巨。高等教育要承担起文化批判与价值澄清的任务,通过倡导与歌颂、批判与鞭笞“双管齐下”,激浊扬清,分辨是非,规范社会价值体系,重塑社会共同理想,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第五,通过校园文化影响、提高社区文化。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决不能随波逐流,和光同尘,让商业文化、低俗文化侵蚀、消融校园文化,决不能降低大学的格调去迎合低级趣味。高等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加快、加强,并通过开放和辐射,带动周围社区文化的健康发展。
1995年7月在昆明举行的“’95 高教研究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上,有同志对我关于“适应”与“导引”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不适应”问题是主要矛盾,对教育而言,应抓住主要矛盾,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投身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确实,高等教育游离或落后于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象依然存在,高等教育的“主动适应”仍然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盲目“适应”、无所适从和放弃自己对社会发展应当负起责任的现象,也已经相当普遍,而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又迫切需要高等学校的介入。因此,我不认为只有当“不适应”的主要矛盾基本解决了,才可能提出“导引”社会、改造社会的任务。事实上,高等教育对社会“适应”与“导引”的双重任务已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注释:
〔1〕孟宪忠、李今朝:《面向21 世纪的社会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
〔2〕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二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47—752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73—174页。
〔4〕〔5〕崔相禄:《20世纪西方教育哲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7页。
〔6〕〔18〕[美]理查德·D·范斯科德等:《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中译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416页。
〔7〕〔8〕〔9〕赵祥麟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第三册),第117—122页,第90—102页。
〔10〕[美]J·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中译本),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1〕〔12〕《马列著作选读·科学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84、162页。
〔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页。
〔14〕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
〔1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16〕转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 990年版,第165页。
〔17〕《学会生存》(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