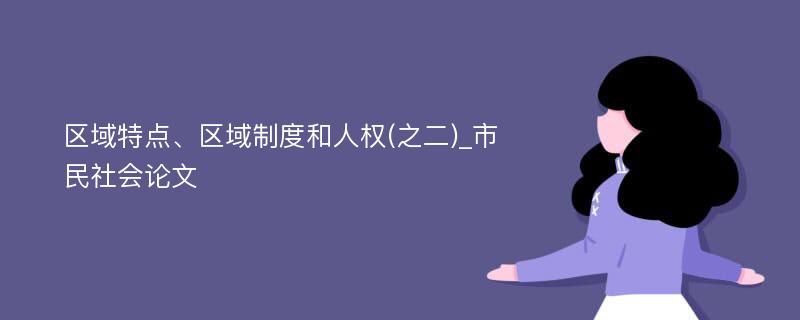
区域特征、区域制度与人权(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论文,之二论文,人权论文,特征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中间,一些因素近来已有所松动,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在口头上承认这些权利,只是力图用一种其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它们:“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涵义、范围和界限有其自己的解释。但就国际人权体制本身而言,它在中国政府1991年来所宣告性的政策中已经逐步得到肯定。”然而,中国仍在抵制出于人权目的的多边干预,除非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实施严重的、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情况下。(注:Andrew J.Nathan,“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9.) 相似地,在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会议上充斥着有关不干涉和明确反对“强加一些不兼容的价值”的呼吁。(注:A/Conf.157/ASRM/8/A/Conf.157/PC/59/7 April 1993.)区域规范对国家行为影响的另一个例证就是, 亚洲集团对于建立国家人权制度持明确的保留意见(交由国家来判断)。
一些东亚领导人和分析家则走得更远,他们不仅拒绝“权利对话”,而且赞成一种推定的、不能用统一标准比较的东西:根植于儒家集体主义、社会和谐、善意自治权威等观念的“亚洲价值”。(注:Zakaria Fareed,“Culture is Destiny: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73:2 (March/April 1994).)他们主张,这些“亚洲价值”有时要求压制。而内部批评者则反对说,这套规范否定普遍标准,阻碍了变化。(注:Kenneth Christie,“Regime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in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XLIII,1995, pp.204—218; Amartya Sen,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What Lee Kuan Yew and Le Peng Don't Understand about Asia”, New Republic 217:2—3(July 1997).)这一对话和挑战原始价值的简单的过程正在改变这些国家。亚洲价值派的设计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最近说:“由于卫星技术,我看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即国际社会就哪些是不可接受的行为达成共识,无论这些行为是发生在科索沃,还是东帝汶。它不是西方界定的,也不是东方界定的,而是一种普遍标准。但民主的形式将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异。”(注:Los Angeles Times,12—5—1999, M3.)
就像东亚一样,在非洲和近东,区域性人权规范的缺失妨碍了该地区落后的人权状况的改善,至少为这种落后状态提供了合法性。区域精英把人权和西方文化错误地(有时是操控性的)联系在一起,以此阻碍有关标准的制定。(注:Jack Donnelly,“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1,1999,pp.608—632.)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主张,非洲传统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规范可以取代自由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否定了普遍主义、个人主义、人权的不可剥夺性以及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即便是承认人权规范基本合法性的中东国家也倾向于优先考虑社会和经济权利。(注:1998 General Assembly, UN Press Release.)正如一位埃及人权学者和活动家总结的:“……许多阿拉伯人把国际认可的人权理解为某种西方舶来品,因而不适合我们的社会……在阿拉伯世界对人权信任的缺乏将会限制相关国际体制在这方面的潜力。”(注:Bahey El Din Hassan, “The Credibility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 the Arab World”, Human Rights Dialogue 2(1),9—10,2000.)
在非洲,规范讨论因为文化和殖民传统,因为许多非洲国家的软弱而复杂化了。尽管许多区域领导人以及如《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等区域文件都在援引传统规范,非洲传统还是不能提供一套单一的、连贯的价值,而非洲国家内部的种族差异,引发了应当采纳何种“非洲传统”的冲突(例如,尼日利亚和苏丹的伊斯兰法争论)。如同《非洲宪章》,世界人权大会非洲区域会议强调不干涉、集体权利、发展权以及权利和责任的平衡。(注:A/Conf.157/AFRM/14/A/Conf.157/PC/57/24 November 1992.)许多非洲国家都过于弱小,因而,多边主义常常只是背景条件,而不是对话主题。非洲区域会议与亚洲区域会议不同,它赞同非洲国内人权机构之间的合作,呼吁加强区域机构(非洲人权委员会)。相似地,虽然非洲国家政权侵犯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的现象促使人们要求在肯尼亚这样比较成熟的政体中限制权威,但是许多非洲国家无力控制侵犯人权的准军事组织和犯罪分子这一事实又使得人们呼吁加强而不是限制权威。因而,在非洲无论主权,还是意识形态,都没有(像亚洲和近东那样)提供一套可用以替代人权规范的清晰的东西,但人权规范也并没有得到广泛或彻底的支持。
从规范出发,看来真正反常的区域,惟有南亚而已。在那里,自由普遍主义在原则上得到了接受,但在实践中却遭到了违反。然而,即使在那里,区域规范和实践仍是互动的,规范仍有助于解释时代带来的变化。南亚人权在过去十年无疑是恶化了,这是因为,各种宗教和种族原教旨主义——印度的印度教、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伊斯兰教、斯里兰卡的佛教和泰米尔教——的崛起,压倒了自由主义的殖民传统。(注:Michael Anderson and Sumit Guha (eds.), Changing Concepts of Rights in South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对多边主义的态度同样倒退了,这表现在区域军备竞赛、 反对克什米尔和其他争议区域的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巴基斯坦对国际上要求其民主化的呼声的对抗态度。就整个区域来看,民族冲突使残存的有关人权普遍性和不可剥夺性的自由主义规范很快被中止了。
(二)网络。人权规范同时允许和激发维护权利的市民社会的成长。许多假设试图把市民社会和人权行为联系起来,正如它们试图将全球经济因素与人权行为联系起来那样。首先,市民社会的密度和增长就有助于向公民赋权,增强他们对抗政府压制的能力。其次,社会的特定性质也甚是重要:人权运动的数量、大量的成员、神职人员等主要文化人士的参与、无权阶层的维权途径。在区域层面上的跨国的区域市民社团,或者是这些社团的一些特殊类型,如区域人权联盟之类的存在也是有好处的。最后,市民社会和跨国网络间的联系,将会有助于建立“自上而下”地改善人权的渠道。(注:Alison Brysk,“From Above and Below: Social Movement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Human Rights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26, No.3, October 1993.)
作为记录其中某些特征的首次尝试,表4 考察了各区域内现有的一些国际非政府团体、区域组织以及区域性非政府组织。这些区域的平均数,即该区内国家数目的加权数,因为所有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接纳国家成员。此外,我还对每一区域参与的跨国社会运动做出了评价,以此来衡量这一地区跨国运动的参与程度和市民社会的密度。最后,在人权组织一栏,还粗略给出了一些数字,以描述以区域为基地或主要在区域内活动的、保护安全权利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为主要任务的非政府组织。
表4 区域特征:网络(注:来源: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gional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Smith, Jackie,“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Sector”,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olidarity Beyond the Stat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7。资料来源没有区分南亚和东亚。)
区域 国际非政府组织 区域政府间组织 区域非政府组织 社会运动的区域参与 人权组织
西欧 2353
19.6
1134.6 425 49
北美 2153
17.7
874.7 325 13
南美 635.5 15
178.4 300 34
东欧 1062.8 9
401
225 15
东亚 242.7 3.7
188.7 300 19
南亚 141.2 5.4
218.3 300 4
近东 456.6 8.3
103.7 200 14
非洲 224.4 15.3
107.8 275 28
一定程度上,一个区域同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联系越紧密,人权状况似乎也就越好。这个推论与社会学制度论所作的全球化预言是一致的,因为同世界体系的联系允许普遍的自由主义规范更大程度的国内化。人们假定一个国家与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能够反映和传达区域意识。但是,单纯这方面的数字并不能像一个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一样很好地反映人权行为。偏离这种假定最远的当推东亚,在那里,人权表现还是低于人们根据这些指标所预测的水平。拉美国际和区域非政府组织比预想的要少,但人权组织却比预想的多。
这些数字基本印证了一些个案和区域定性研究的结论。这些研究显示,在拉美和东欧活跃的市民社会推动了民主化和改革,而非洲和东亚在这方面则相对较弱。以人权为中心对区域非政府组织归类后,就很明显了:拉美强而北美弱。据以推断区域非政府组织存在的指标,来自前述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区域人权会议的纪录:参加亚洲会议的非政府组织为数不多(134对168),而非洲和拉美区域非政府组织(分别为12和17),要低于拉美(22)。意外的是,以非洲为关注对象的人权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却很大,这讽刺性地反映出,该地区所需要的是改善而不是区域市民社会。
近东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强度有悖于直觉,同时亚洲和非洲数据又是混合性的,这些都强调,有必要对市民社会和区域内跨国联系的性质和特征做进一步的定性分析。这种分析表明区域网络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非洲仅有少数几个非政府组织。其中有一个在消除盛行整个区域的、在文化上很敏感的女性生殖器残害方面取得某些进展。它就是非洲委员会(Inter-African Committee),一个区域非政府组织网络。(注:Claude E.Jr.Welch,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frica: Strategies and Rol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类似地,区域网络亚太人权非政府组织促进会(Asia Pacific Human Rights NGO Facilitating Team)在1994年公布《曼谷非政府组织人权宣言》后,即改变了该区域规范议程。
(三)机构。最后,各区域在制度化程度和种类上,也存在很大不同。即便对相关区域制度的性质而不是数字做些粗略分析,也能够看到,在区域风俗、机构和人权表现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机构的存在常先于人权改善,因此它们可以塑造和反映国家行为。波力和托马斯(George M.Thomas)关于区域机构创立日期的材料说明,各区域在区域组织的建立日期的先后与这些地区目前区域性组织在人权方面力量的强弱是一致的。(注: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INGO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orld Culture,” in John Boli and George M.Thomas(eds.), Constructing World Cultu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33.)但单个的以维权为目的的区域组织,未必就比其他类型的区域性组织历史更长。表5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区域组织:这些组织在人权方面的任务、委员会或法院之类的人权组织结构、机构成员是以独立还是官方身份任职、是否可以为个人和非政府组织之类的非国家受害者利益倡导者利用,以及是否拥有做出有约束力的制裁的权力。
表5 区域人权制度(注:来源:A.H.Robertson and J.G.Merrills, Human Rights in the World,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1996; A.Glenn Jr.Mower, Regional Human Righ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est European and Inter-American System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91;网址:EU(http://europa.eu.int);NAFTA(http://www.naalc.org); OAS(http://www.oas.org); ASEAN(http://www.aseansec.org); OAU(http://www.oau-oua.org)。)
机构是否有人 组织结构 成员是否以
是否可为个人或 制裁
权任务
个人身份任职 非政府组织利用
欧盟有委员会、法院
是
是
有约束力
北美自由贸易协会
劳工
委员会
准个人身份
是
罚金
美洲国家组织有委员会、法院
是
某些
罚金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有少数民族高级专员 是
是
调解
东南亚国家联盟
无无-
否
无
阿拉伯联盟 未批准
委员会
否
否
无
非洲统一组织弱委员会
是
有限的 无
西欧高居榜首,它不仅有最多的制度,而且是最好的制度。欧盟权力广泛,成员众多,人权任务明确,人权机构综合实用,制裁具有约束力。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委员会已有判例数千,职员和制度设施齐备。申诉被受理比例相对较高,其中不少部分还被提交到了法院。所有其他区域制度均缺乏其中某些要素;一个地区的区域制度越接近这一理想状态,其人权表现也就越好。而且,成员国通过欧洲法院的判例法所发展出来的人权规范显示了区域主义影响区域人权表现的一种重要机制。(注:Imke Risopp-Nickelson,“Integration Through the Back-Door: Ho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 Influence European and Domestic La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14—18 March 2000).)
其次是拉美的美洲国家组织,欧盟身上的许多特点,它都具有。美洲国家组织尽管经济作用有限,但却从事着军事干预和广泛的职能活动。像欧盟一样,美洲国家组织也拥有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委员会除接受国家来文外,也开始接受个人来文,每年审理上百个案件。美洲国家组织人权法院不具有国家自动执行意义上的约束力,但它可以并且在实践中也确实实施罚款制裁。美洲法院可以应那些希望国内立法更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成员国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并且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的确,拉美区别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地方就是其强有力的区域性人权机构及其日益接受人权规范的态度。美洲国家组织1991年《圣地亚哥决议》以及对压制民主的国家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的做法,尽管实行得并不平衡,但也为区域机构增加潜在的压制者们的顾虑以及减少他们的国内支持,指明了另一条途径。
东欧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逐渐采取了一个能动的人权日程,包括1990年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与1992年少数民族高级专员。(注:虽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拥有来自整个欧洲以及前苏联的55个成员国,但是其人权活动集中在东欧(其次是各中亚国家)。)就像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一样,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的人权和选举监督被与由联合国和区域性军事机构(在这里是北约)实施的维和与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联系在一起。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也像欧盟和美洲国家组织一样开展一系列人权教育和促进活动,但这种活动很大程度上已经延伸到了制度建设和冲突结束后的管理方面(如在科索沃)。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已经克服了据说造成非洲区域制度软弱的两个因素:建立时间短以及成员众多纷杂。
如前述,北美的特点是低水平的多边主义。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实现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该地区已经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劳工委员会(北美劳工合作委员会),开始在小范围内处理权利问题。劳工小组的职责仅限于处理有关“长期不遵守卫生和安全标准、童工、最低工资等方面的立法”的问题。(注:Morales, Isidro, Guillermo de los Reyes and Paul Rich,“NAFTA,”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565,1999,p.47.)该委员会具有准政府组织结构,下设一个由各成员国劳动部代表组成的理事会、一个三国秘书处以及半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和仲裁小组。来文递交各国劳工办公室,而不是递交委员会本身。自从1994年以来,只收到了很少一些申诉。在22件案子中只有3件带来政策变动。委员会有权罚款。
与欧洲和拉美相比,东亚和非洲的区域制度常受到主权和治理问题的困扰。非洲统一组织作为一个组织,软弱得出名,1981年《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先天不足,在该地区内也不常被援引。其所建立的委员会收到的国家报告寥寥无几,受理的申诉也很少(每年几十个);不管怎么说,它根本就没有实施条款。只有满足了苛刻的条件的个人申诉才能被受理。(注:Claude E.Jr.Welch,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in Africa: Strategies and Roles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5, pp.158—159.)尽管南非、卢旺达和乌干达等成员国国内都有人权活动(主要是审判过去所犯下的侵犯人权的罪行的国内审判庭),但是区域人权协调机制薄弱。美洲国家组织经常在本区域内采取干预行动促进民主和加快人权改革,而非洲区域维和努力多通过次地区组织实施并且由于区域武装力量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陷入泥潭[如在塞拉利昂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西非维持和平部队(ECOMOG)]。
总之,“非洲人权委员会在四个主要领域(条约标准、报告记录、审议深度和后继行动)都受到了强烈的批评。与其他区域(如欧洲和美洲)的文件和机构相比,非洲机构和文书显得很薄弱。但客观地说,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作为世界一半人口的故乡的亚洲以及中东和太平洋国家都缺乏人权机构”。(注:Ibid.,p.148.)
东亚区域人权制度也不发达。由十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是该地区最大、最广泛的区域性组织,而东盟公开回避柬埔寨和缅甸的人权问题。(注:Amitav Acharya,“Human Rights and Regional Order: ASEAN and Human Rights Management in Post-Cold War Southeast Asia”, in James T.H.Tang(ed.),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ew York: Pinter,1995,pp.167—184.)1993年,在联合国维也纳人权大会召开之后,东盟通过了一个建立区域性人权机制的呼吁,但该呼吁从未被付诸行动。(注:Frank Ching,“Asean's Unkept Promis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2, August 1996.)
在南亚和近东,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具有适当的政治特征的区域性机构来作为促进人权的论坛。像非洲一样,阿拉伯联盟在国际社会关注该地区的时候(1971)起草过一份人权宪章。但该宪制随后就被遗忘了。该宪章也缺乏制度性实施机制。其所建立的人权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只关注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人权的问题,而不关心其成员国国内的人权问题。
综上,各区域在风俗、制度和市民社会等方面都有着系统的差别,并且这些差别与这些区域内各国人权行为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关系。在研究这些差异的确切性质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更具体地阐述区域特征和国家压制或改革之间的联系。
五 结论
这一初步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揭示受政策控制的区域规范因素可以影响区域内发生恐怖和压制的可能性。虽然本文对原始数据、二手研究以及定性因素的综合回顾无法揭示侵犯人权的清晰的或单一的原因,但它充分说明了一系列全球和区域模式的有用性。民族多样性、独裁和软弱的市民社会,在全球和区域层面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挑战。但民主、区域规范以及区域制度,似乎可以将人权状况改善到发展、历史以及其他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水平之上。地区因素会改变全球规范和制度的有效性。而且,区域变化往往比全球共识或全球治理更容易受到影响。
“新区域主义”绝不仅是一些贸易集团。即便在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我们也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关注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社会溢出效应的呼吁。正如国家间的稳定的经济交易有赖于这些国家内部的法治一样,国家间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有赖于这些国家内部的安全质量。而安全权利和法治反过来也可以成为区域合作的焦点和结果。民主的传播,惟有在营造出正义地带的条件下才能造就“和平地带”。
周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