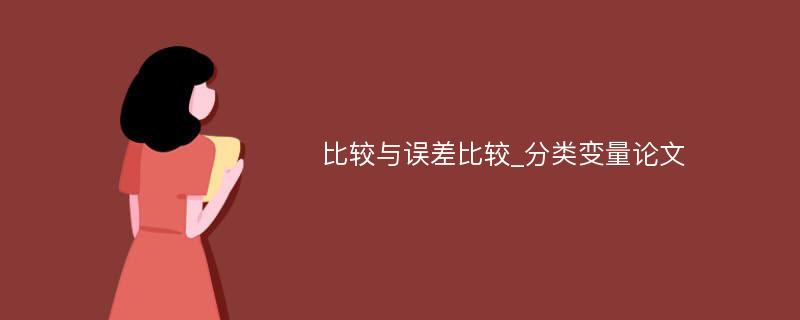
比较与错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错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2)06-0128-10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开创者罗伊·马克里迪斯(Roy Macridis)对传统比较政治分析最主要的批评是,它“在本质上是非比较的”(Macridis,1953,1955)。实际上,因为这一领域经常把自己界定为外国研究,所以,时至今日,类似的情况仍然在重复。一个研究美国总统制的学者被称为美国研究的学者,而另一个研究法国总统制的学者则被称为比较研究的学者。这一点是不符合逻辑的。一个被称为比较政治的研究领域却充斥着许多对比较缺乏兴趣也缺乏训练的非比较主义者(non-comparativists)。最关键的是,比较政治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独特性应该主要体现在其方法上。正如阿伦·利普哈特(Arerld Lijphart)所指出的,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比较政治学应更多地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方法论意义的而不是一个实质意义的标签”(Lijphart,1971:682)。同时,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T.Holt)和约翰·特纳(John E.Turner)也指出,“比较一词的常识意义……主要指向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个实质性知识的实体”(Holt and Turner,1970:5)。
人们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比较往往潜含于一般的方法之中,或者科学的方法本身就是比较的。可以说,某些国别研究本身就嵌入在一个比较的情境之下。换言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可以说是未经过显性比较的隐性比较者。但是,这样的情况常见吗?笔者认为并不常见。研究者可以从文献浏览中很容易证实这一点。多数的国别研究都忽视其所在主题的比较分析框架和文献。笔者也同意,在一定程度上讲,科学方法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比较。假如一位学者潜在地运用比较方法,那么该学者无疑会是比较优秀的学者。但是,这种显性比较和隐性比较的区别不能缩小到,人们自动地会认为“非自觉的比较主义者(unconscious comparativists)”就是比较主义者。
一、为什么比较?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目前存在一种共识,即比较研究的特征并不是比较而是解释。跨国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去理解政治现象”(Przeworski,1987:35)。查尔斯·拉金(Charles C.Ragin)也指出,比较的知识“提供了理解、解释和解读政治现象的钥匙”(Ragin,1987:6)。劳伦斯·迈耶(Lawrence C.Mayer)将比较政治定义为一个目标是“构建经验上可以证伪的、解释性的理论”的领域(Mayer,1989:12)。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在寻求一种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所以对于上述的“比较政治解释论”,人们可能很难提出反驳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要比较呢?比较路径所独特的地方又是什么呢?人们使用比较进行研究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控制。
以两个判断为例:“革命是由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导致的”;“总统制会导致强力的政府,而议会制则会导致虚弱的政府”。这两个判断成立吗?我们如何判断其是否成立?我们通过比较性的检验就可以得出结论。比较控制(comparative control)是控制的一种,①虽然它并不是特别有力的一种控制。实验控制(experimental control)是比较有力的控制方式,而统计控制(statistical control)也可能会比比较控制更有力些②。但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存在限度,而统计方法则需要非常多的案例③。我们在研究中经常面临如利普哈特指出的“变量太多、样本太少”(many variables,Small N)的问题(Lijphart,1971:686)。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最佳选择便是运用比较控制的方法来研究问题④。
二、什么是具有可比性的?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具有可比性的?我们经常会说,苹果和梨是不可比的。但是,人们又很容易反问道:假如我们不去比较它们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它们是不可比的?转移到另一个问题:石头和猴子可比吗?假如我们用一两秒钟时间把它们比较一下,我们可能也会说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假如被比较的实体之间没有共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比较,这也是我们说石头和猴子之间不可比的原因,即这样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比较终于其开始之时。回到梨子和苹果的讨论: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可以比较?笔者认为,就其共享的某些性质而言,它们之间是可比的,反之亦然。因此,作为一种水果、一种食物、一种长在树上的东西,苹果和梨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但就其各自的形状而言,它们之间是不可比的。当然,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事物之间哪些性质和特征是可以比较的?哪些性质和特征又是不可比的(例如,它们之间完全不相像)?
被比较的两个事物之间应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相异性。假如两个实体在所有的特征上都表现为一致,那这两个实体基本上是同一类实体,它们之间的比较也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如果两个实体在所有的特征上都完全表现为不一致,那这两个实体之间也缺乏比较的意义。我们所要进行的比较应该是在那些部分特征类似但部分特征又有差异的事物之间展开。
以上这些讨论将问题推回到奥斯古德问题(Osgood question)上,即“什么时候同一的事物是真正同一的?”,或者相反的问题:“什么时候相异的事物是真正相异的?”(Osgood,1967:7)。许多研究者纠缠于这一问题,而且许多研究也正是从这一问题出发的。然而,假如我们记得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通过分类或者属加种差(per genus et differentiam)模式来完成的话,那么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理想的答案。分类是将一个给定的总体分成许多相互排除的、并且加总起来无所遗漏的多个种类。分类需要确定何为相同与何为相异。“同”则指将那些可以放入同一种类的个体集中在一起,而“异”则指那些可以放入另一些种类的个体们⑤。需要提及的是,种类所产生的是一种相似性(similarity),而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同一性(real sameness)。分类会产生一个相似程度的问题。在一个分类中,种类的数量越少,种类内的差异就越大(这些种类整合了许多不同的次类别)。反之,种类的数量越多,种类内的差异就越小。假如我们仅把世界分为君主制和共和制,那么这两个类别的范围是比较大的,而且它们内部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另外,不管种类的范围如何之小,任何种类存在的意义都在于标明其与其他种类之间的差异,而分类者则需要决定他的分类到底是包容性的(宽的)还是歧视性的(窄的)。
什么是可以比较的?这一问题需要放在以下的形式中才可以回答:在哪些方面它们是可以比较的?在这一框架下,梨和苹果在某些特性上是可以比较的。同理,人和大猩猩也是可以比较的(它们都是可以使用手、并且直立行走的动物)。甚至,人和鲸鱼也是可以比较的(它们都是哺乳动物,并且都不能在水下呼吸)。当然,从第一个例子到第三个例子,它们的不可比性在逐渐增加。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进行比较政治研究的唯一途径就是依赖分类式排序(classificatory orderings)。然而,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者在二十年间选择的路径明显是有问题的。笔者把这一路径称为“猫—狗路径”(cat-dog route),并为之编撰了一个故事(笔者希望它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猫—狗”路径
故事是这样的:窦先生在准备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导师多次告诉他,他的论文必须是独创性的,也必须有一个假设。之后,他将他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猫—狗”(似乎单独研究猫或者狗都很难是独创性的)。他的假设是,所有的“猫—狗”都发出一种“啵喔”(bow wow)的叫声。导师说非常有趣,然后某一基金会资助他十万美元进行世界范围的研究。三年后,窦先生得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一些“猫—狗”发出“啵喔”的叫声,而另一些则没有。这样,假设就没有得到证实。然而,他说,“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假设:所有的‘猫—狗’都发出‘喵欧喵欧’(meow meow)的叫声。”另外三年过去了,另一个十万美元的资助又得出一个假设没有被证实的结论:一些‘猫—狗’发出“喵欧喵欧”的叫声,而另一些则没有。在极度绝望中,窦先生在傍晚去求讨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恰巧这时,神庙的女祭司在一天的预言工作之后已经很疲惫。所以,女祭司直白地对他说道:“我的朋友,我应该对你讲真话:这个‘猫—狗’是不存在的。”故事结束,然后我们回到非虚幻的研究当中。
这个“猫—狗”路径到底指的是什么?下面笔者用四个概念来对这一故事进行分析:①地方偏见(parochialism);②错误分类(misclassification);③程度主义(degreeism);④概念延展(conceptual stretching)。
(二)地方偏见
地方偏见是指处于真空中的一国研究,其忽视常规理论或比较分析所认可的通常类型,或者在一时冲动之下就可能发明某个特别的、自我裁剪的专业术语。例如,詹姆斯·桑奎斯特(James Sundquist)最近一篇文章的研究主题是“美国的联盟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在目前的世界中,联盟政府基本存在于议会制政体中(不是美国的总统制政体)。在议会制中,政府由议会选出并对议会负责,所以有时会出现非单一政党的政府。因此,很难说在美国会存在联盟政府,而桑奎斯特所描述的美国联盟政府的特征也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猫—狗”(或者更糟糕的是“狗—蝙蝠”)就产生了。只要这种用词不当(misnomer)进入我们的电脑之中,它便注定会干扰我们对联盟政府这一概念进行正确的理解。
(三)错误分类与程度主义
“猫—狗”案例产生的第二个来源是错误分类。以政党体系领域的一党制分类为例。目前对于一党制的通常分类包括:①像日本、瑞士、挪威、印度这样存在政党竞争的一党独大国家;②像墨西哥这样存在有限政党竞争的一党独大国家;③像苏联和东欧这样基本完全限制政党竞争的一党国家⑥。这个一党制的分类实际上涉及三个完全不同的动物。笔者把这个分类称为“猫—狗—蝙蝠”。假设我们现在要去分析产生一党制的原因。例如,亨廷顿等人指出:“一党制产生的社会原因需要被考察,但其中存在分歧。……一党制……可能是社会分野积累的产物……也可能是社会分野中的一方压过另一方的结果”(Huntington and More,1970:11)。亨廷顿等人的这一观点是对还是错?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他的假设或者其他假设都不能通过“猫—狗—蝙蝠”的检验,因为没有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可以经受起这样一个三头怪物的联合攻击。对“猫”适用的理论对“狗”可能仅仅部分适用,而对“蝙蝠”可能完全不适用。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为什么罪魁祸首是错误分类?分类是从单一变量衍发出的次序排列。在这一案例中,一党制的正确分类应该将那些实际存在两党(或者多党)的案例排除出去。因此,日本和印度等案例不应该放入一党制的大箱子中。产生“猫—狗”组合的第三个原因是程度主义。在这里,笔者用程度主义来描述对以下观点的滥用:种类的差异可以被视为一种程度的差异。但是笔者不同意程度主义的观点。
(四)概念延展
发生比较失效或者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概念延展(Sartori,1970)。以“宪政”这一概念为例。假如这一概念延伸为指“任何国家形式”,那么“宪政制约暴政”这一普遍性结论(这一结论实际上对宪政采取了狭义的定义)则会与这一广义指称产生冲突。再以“多元主义”为例。假如所有的社会在一定意义上都宣称自己是多元主义的,那么“多元主义与民主保持一致”这一普遍性结论也就很难成立。另一个例子是“动员”。假如将这一概念延伸到同时包含自我驱动(即参与作为一种自愿行为)和外力驱动(即被外力动员,实际上也是动员的确切含义),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的“猫—狗”案例,并且我们可能还会在这两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吞没中结束这一讨论。“意识形态”也是这一类型的经典概念,其通过祛除教育式的合法性内涵和可检测的特征,将自身的含义延伸到一个无意义的状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经常被滥用:每种事物都可能被称为意识形态。这样,一个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就变成了一个“猫—狗”组合之类的概念。
三、如何比较?
关于如何进行科学的推断,有许多可能的方法。笔者比较喜欢斯梅尔赛的理解。他写道:一个社会科学家试图去解释的任何现象的初始图景,“是一种环境所展示的多样性,是一种它们对因变量影响的组合,是一种某一条件的效应或多个条件综合效应结合在一起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为了减少条件的数量、将这些条件分离以及明确他们的作用,调查者需要从事以下工作:①将不同的条件变为自变量、干预变量和因变量;②将一些因果性条件作为假定不变的参数或是给定的数值,同时将另一些条件作为允许其变化以便于观察其对因变量影响的操作变量(operative variable)(Smelser,1976:152~54)。诚然,没有一个变量可以从本质上说就是自变量或因变量,“在一个调查中作为参数的因素在另一个调查中可能会变为操作变量”(Smelser,1976:154)。
一般而言,“比较研究者有时会强调共性,有时也会强调差异。他们试图在相似的情境下寻找不同,或者……在比较政治系统时试图发现相似物”(Dogan and Pelassy,1984:127)。重点的不同会导致几乎完全不一样的研究方法。多数比较研究者采取一种“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的设计。同时,如普沃斯基和亨利·图纳(Henry Teune)指出的,研究者也可以采取“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的设计(Przeworski and Teune,1970:31)。在最具相似性系统的策略下,研究者将那些在许多方面都尽可能相同的系统集中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在研究中忽视一些变量的存在(基于的假设是这些变量是相同的)。最具相似性策略认为,同类国家相对同质的那些因素与它们的差异是不相关的。在这一策略的实践运用中,最好可以选择那些在被调查的因素之外所有变量都尽可能一致的实体。最具差异性系统则是另一个路径上的策略。这一策略所针对的案例要求是,除了被调查的现象一致之外,其他因素尽可能地不一致。在普沃斯基和图纳的例子中,他们假设祖尼人、瑞典人和俄罗斯人的自杀率是一样的(这些案例属于完全不同的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因素在解释自杀率方面就是不相关的(Przeworski and Teune,1970:35)。
(一)规则与例外
像法则一样的普遍性结论往往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但是例外的案例可能会推翻普遍性结论。例外在何时以及何种程度上可以推翻普遍性结论,这是一个较难回答的问题。假如我们假定法则是确定性的,那么只需要一个例外情况就足以推翻它。但是假如我们宣称像法则一样的普遍性结论是概率性的,那么我们将会比较容易地摆脱前面的困境。概率性的结论意味着我们在试图得出一个趋势性法则(tendency law),即一个或少数几个例外并不能推翻普遍性结论。此外,克服例外状态发生的办法之一是通过限定某种必要条件,来减小规则适用的范围。例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法则只有在满足落体在真空中下落这一必要条件之后,才能得到证实。解决例外情况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将例外情况整合进法则的表述当中。然而,如果表述说,某一法则“是确定性的……在某些例外被注明的情况下”(Riker,1982:761),这也是有问题的。这一表述内部具有逻辑性的冲突。
(二)个案研究
另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是个案研究如何作为一种比较方法而得到运用。哈利·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和利普哈特对个案研究进行过一些重要的分类。笔者将他们的分类综合起来提出个案研究的五种分类:①轮廓特征型(configurative-idiographic,Eckstein);②解释型(interpretative,Lijphart);③假设生成型(hypothesis-generating,Lijphart);④关键型(crucial,Eckstein)或是理论验证型(theory-confirming,Lijphart);⑤异常型(deviant,Lijphart)。第五种类型的最重要案例是西摩·马丁·李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所研究的国际印刷工会(Lipset,1956),这一案例是对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寡头统治铁律的一种反证。笔者必须强调,个案研究不能被归入比较的研究方法之中(虽然它可能具有某些比较的价值)。另一方面,比较和个案研究可以相互加强和相互补充。笔者的感觉是,对于比较研究者而言,个案研究在假设生成阶段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不能验证某一个普遍性结论(某一案例的证实能够增加信度,但是这些信度却不能加总为一个对假设的验证),但是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伪某种规律性。探索式的个案研究(heuristic case studies)为普遍性结论的构设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土壤。然而,个案研究却只是最初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理论构建的一部分(如埃克斯坦所强调的),而不是理论控制的一部分⑦。
(三)不可测量性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这一最重要的、但也是最棘手的问题。我们回到那个最基础的问题:进行真正的比较研究是否可能?对这一问题的否定性回答有许多种形式。目前多数的否定回答都主要集中在“概念的不可测量性”(incommensurability of concepts)这一标签之下。按照笔者的理解,不可测量所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没有测量的标准,或者说没有同一的标准。然而,目前“不可测量性”这一标签却暗示,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嵌入情境中的(context-embedded),并具备一种无法从情境中逃脱的性质⑧。按照这一说法,概念就是一种伪装下的普遍性抽象,是一个装满许多具体感知和认识的精神容器。应该说,这种指称有点殃及无辜。
但是,反对不可测量性的指称并不是要反对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和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hhey)在一个世纪之前提出的特殊科学和普遍科学的区分。在他们的理解中,历史学家陈述一种具备特殊性的东西,我们将其称之为构造性的、情境嵌入的关注。相反,自然科学则是普遍性的,通过寻求法则将单一性融入普遍性之中。在这里,笔者强调,我们并不是封闭的、不可测量性的囚徒,而是在得失之间进行权衡的选择者。案例研究牺牲普遍性:研究者需要对“少”的东西(在范围上的“少”)理解更多。相反,比较研究牺牲理解的情境:研究者需要对“多”的东西理解得相对少。能否在两者之间构筑一个桥梁?在理论上,就方法论而言,我们不得不在不同的调查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在实际中,比较研究者需要对单一国家研究所提供的轮廓性信息进行认真研读,而单一国家的研究专家如果忽视比较则可能在研究中受到某些限制。
(四)个体化与普遍化
我们需要在个体化与普遍化之间做出一种选择。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选择并不是很难处理的,而且也存在一些帮助我们从普遍性向情境转化(或者相反)的桥梁。在一篇经常被引用的文字中,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把这两者的相互转化看成是一个自我挫败的漩涡、一种相互压制的纠缠:“在比较中,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去寻找那些在所有的案例中都适用的普遍性结论或法则……但是这些普遍性法则在哪里呢?当我们在研究那些具体的案例时,普遍性结论就会消退。我们在已有的干预变量之外又增加了干预变量。因为案例的数量较少,我们经常修改解释以适应每个案例。结论也往往是特殊性的或是构成性的。……当我们力求得出某个可以支撑一系列政治系统的普遍性结论时,我们会把越来越多的变量放进我们的分析,最后我们放进的东西太多,以至于我们在构成的全体中都很难发现一个符合条件的个案”(Verba,1967:113)。
以下是笔者尝试将两者整合起来的一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不一定能作为我们未来推进研究的指导性方针。“这些普遍性法则在哪里呢?”即使我们有能力去构建它们,那些“猫—狗”研究也会把它们统统消灭掉。“我们在已有的干预变量之外又增加了干预变量”,这一点是比较研究的错误路径。笔者的建议是,将普遍与特殊联结在一起的有序路径是沿着“抽象之梯”(ladder of abstraction)来管理我们对研究对象的分类。“抽象之梯”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看成一对倒转的关联。为了让概念更具普遍性,我们必须减少它们的属性和特征。反之,为了让概念更加具体(满足情境),我们必须增加它的属性和特征。如笔者前面所提到的,这一问题并不是很难处理的。虽然一些问题的处理可能比另一些要困难些。笔者建议的路径需要艰苦的思考,而那些仅仅用不可测量来回避问题或者是简单地交由计算机来从事我们应做的工作,则明显要容易得多。
四、结论
与30年前人们的较高期望相比,目前比较政治的研究状态有点让人失望。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埃尔伯特·索米特(Albert Somit)和约瑟夫·塔纳豪斯(Joseph Tanenhaus)的调查发现,比较政治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完成了许多杰出工作”的领域(Somit and Tanenhaus,1964:55~57)。但是,仅仅几年之后,维巴就自问道:“为什么这一领域有如此多的运动,但却很少有向前发展的运动?”(Verba,1967:113)然后,他又回答道:“答案是这一问题本身的困难性”(Verba,1967:113)。实际上,这一问题的另一半答案应该是,一个缺乏逻辑、方法论和语言学基础的学科不仅不能解决它所面对的问题,而且也不能为其自身集聚相关问题。
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革命:行为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批判的、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的,等等。但是革命(科学意义的)仅仅留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必须对它们进行跟踪研究,同时这些研究也必须结出果实。相反,我们却仅仅让这些革命消退。新的开始意味着新的诺言,同时那些旧的诺言仍然未实现。戴维·科里尔(David Collier)对20年来比较方法的争论进行了回顾(Collier,1991)。从回顾中可以发现,目前,研究中比较的控制目的被遮蔽起来。研究的复杂性在增加,但同时却以日益消失的内核为代价。越来越多的比较研究者并不比较任何东西,甚至连潜在的比较也不进行,从而放弃了标准性的标签、共同的准绳和共享的参数。让我们直面这一点:规范科学无法发挥其效用。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方法,“比较”所定义的领域就没法繁荣。笔者的批评并不是暗示说,我们没有好的、甚至是杰出的比较研究。但是,即使是目前那些好的比较研究也无法回答我们所迷失于其中的问题:比较的目的是什么,比较的独特目的又是什么(what comparing is for,distinctively for)?
该文是萨托利在西方比较政治学领域引用最多的两篇论文之一。参见:Giovanni Sartori,1991.“Comparing and Miscomparing.”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3(3):243-257.需要说明的是,萨托利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成果尚未被国内政治学界所关注。编译者在编译这篇文章时,对文章进行了部分调整。譬如,将文章中一些重要的页下注放在文内,并把一些不太重要的页下注去掉。
——编译者注
注释:
①国内学者在讨论到比较方法时往往只注意到比较的归纳逻辑,而忽视从控制的角度来理解比较。归纳主要是政治哲学的逻辑,而控制更多是政治科学的逻辑。最常见的比较方法是相似案例比较,而在对这些相似案例进行比较时,这些案例中相似的变量实际上被控制住了。例如,在较为常见的地区国家(如西欧国家)比较时,我们往往假设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程度基本接近,那么在这一比较中,经济和文化因素就被控制住了,或者说这些因素与结果(因变量)是无关的。——编译者注
②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存在一些与这一判断相反的观点(Frendreis,1983:258)。拉金也指出,“在一些重要的领域中,比较方法优于统计方法”(Ragin,1987:15-16)。
③利普哈特和尼尔·斯梅尔赛(Neil Smelser)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利普哈特为,实验方法、统计方法和比较方法是不同的方法。而斯梅尔塞认为,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都是比较逻辑的运用(Smelser,1976:158)。笔者认为。这些方法之间的区别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④在一些案例中,我们可能会同时使用小样本的比较控制和大样本的统计控制。例如,我们假设:政党凝聚力(party cohesion)是政党间竞争程度的一项直接功能(政党间竞争越小,党内派别争斗的程度越高)。在这里,比较检验可以帮助提炼这一假设,然后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才能得以展开。
⑤亚瑟·科尔伯格(Arthur L.Kallberg)提出过以下观点:“真正的比较概念……仅在分类完成之后才能变得成熟。分类是一个‘非此即彼’(eilher-or)的工作;分类也是一个‘多少’(more or less)的工作”(Kallberg,1966:77~78)。笔者同意后一点,但是为什么比较是一项“多少”的工作呢?可能科尔伯格在这里是指种类内的比较(而不是种类间的比较)。
⑥作者的分类主要基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政党发展事实。另外,为了理解方便,译者在编译时对作者所用的案例进行了略微调整。——编译者注
⑦笔者对案例分析和比较的区分并没有暗示后者是更优选的调查形式。如埃克斯坦所指出的,“理论化的终点是实现某种规律性的表述”(Eckstein,1975:88),比较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对规律的验证而不是发现。当然,验证规律的方法有许多种,而比较方法只是其中一种。
⑧这种极端观点的例证是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观点。他的方法论立场是:一、理论决定概念;二、数据本身是理论的一种功能表现。所以,在理论A中描述的数据不能与理论B中表述的数据相比较(Feyerabend,1975)。对于这一观点的反驳,参见莱恩(Lane)的观点(Lane,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