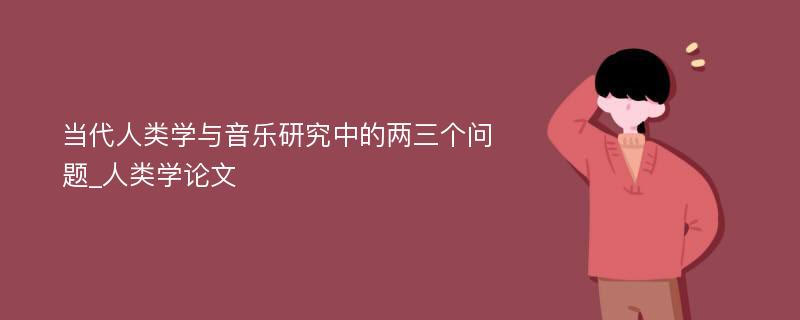
当代人类学与音乐研究二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二三论文,当代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于1997年5月至6月间分别在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福建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单位围绕有关课题举办了讲座或进行了座谈。此文由笔者据部分讲座录音整理而成。)
1、题解与说明
从音乐文化入手进行人类学研究,或以人类学方法来研究音乐文化,这样的学科在西方被称为ethnomusicology。对于ethnomusicology这个名称的中文翻译,中国国内的音乐学者们在近十年中有过许多讨论。大家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人类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各种译名都有;亦有另立学科名目者,如“中国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等。我个人认为,只要学界对于这一学科的范畴有个相对一致的认识,则不论将它译为什么“某某学”都好,在名称上不必过于钻牛角尖。早些年西方学界也曾对什么是“ethnomusicology”进行过讨论, 但主要是集中于讨论这一学科的范畴、任务、对象、方法等,却没有过多地把精力耗在对于具体名称的争论上。
西方至今仍有“anthropologyofmusic ”或“musicalanthropology”的提法,与“ethnomusicology”共存。 从名称上看它们似乎有所区别,但我们不能说这些名称指的就是不同的学科,而在学术研究中实际上也是难以对它们作出截然划分的。作为一个学科名称,今天国际上使用得最普遍的还是“ethnomusicology”。 我自己是喜欢把上述几种英文名称都译为“音乐人类学”的,认为它们没有根本区别。我现在所用的这个“音乐人类学”名称,就是基于这个认识的。
人类学在英文里是“anthropology”,其范围比音乐人类学要广得多。在很大的程度上,西方的音乐人类学(ethnomusicology )是跟在人类学(anthropology)后头跑的,人类学中的热门理论或课题往往在一段时间之后也成为音乐人类学中的热门理论或课题。实际上,音乐人类学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音乐人类学者是必须学习与关注人类学的理论与动态的。
传统的人类学与传统的音乐学原来是分家的。但在本世纪,由于音乐人类学的兴起,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类学与音乐学“两栖”的学者。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对音乐文化感兴趣,而越来越多的音乐学者也把自己的知识面与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人类学领域。人类学者与音乐学者参加共同的学术组织、人类学界与音乐学界共同举办学术会议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然而在中国,人类学界与音乐学界至今为止似乎还是泾渭分明。狭义地理解音乐而忽视其人类学层面,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音乐学界并不鲜见。我现在谈人类学与音乐研究并涉及西方其它姐妹学科中90年代的一些话题,就是希望在这一方面能为中国的学界起一点促进作用,让中国国内的同行们对国际上现代与当代的学术思潮有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学术研究要与国际上的学术研究接轨,就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国外的学术思想与理论。当然,西方的观点与理论也许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结果可能证实某些西方理论的合理性,但也可能足以否定这些理论。我这里所作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地介绍这些观点与理论,而不对它们作价值评判。下面我择取几个可能对中国学界的同行们较有参考价值的话题来谈。
2.关于社会文化进化论
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史中,对于人类社会文化的解释,有过多种不同的学派与理论。这些不同的学说有的互相重叠,有的互相对立,有的相当封闭,有的比较开放。社会文化进化论(sociocultural evolution-ism )就是在历史上曾经较有影响的一家之说。这必须先从人类学史上的生化论谈起。生化论是一百年前产生的理论,它从从生物进化、生理形态、基因遗传等方面来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异同及其成因。早期生化论的极端模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例如“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用于解释社会人文现象,认为人种也像自然界物种一样有优劣之分,劣等种族只能产生劣等文化,而这些劣等种族与文化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必将被自然淘汰。这种理论被后人认为是种族主义社会文化观,它为欧洲殖民主义以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当代人类学中,生化论仍然存在,但当代生化论早已避开了早期的种族主义内涵与简单化倾向,而着重于解释与生化相关的单一的文化现象。
继生化论而起的是历史论。该理论认为文化的形成及任何特定的文化性征的存在都基于历史的原因。代表性学派有两家:社会文化进化论(sociocultural evolutionism)与传播论(diffusionism)。社会文化进化论的前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而社会文化进化论的代表性人物为一百年前的摩根(L.H.Morgan)。 此论将生物进化论套用于解释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认为人类的社会与文化也是像生物界那样循着从低级到高级的单一模式发展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单线社会文化进化论(unilineal sociocultural evolution)。摩根认为, 整个人类社会与文化都是循着由蒙昧期至野蛮期再至文明期的单线模式进化的。蒙昧期的人类以狩猎与采集为生,在野蛮期则出现了农业畜牧业,而进化到了文明期的社会则出现了文字与国家。摩根的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一大批文化人类学者。然而,在人类社会中从古到今都实际存在大量不符合这一单线进化模式的例子。摩根学派把这些例子都以“残余”(survival)理论来解释,认为它们是“例外”,是人类社会文化进化过程中遗留至今的残存物。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澳大利亚土著人在数万年的传统社会中过的是狩猎与采集生活,他们既无文字,也未形成西方概念上的国家。他们的主要乐器,只是一种无法吹出音阶的碗口粗的空心长木筒,加上两根用以敲击节奏的短木棍。按进化论他们就应被认为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他们的文化相当“低级”或“原始”,是人类社会进化早期阶段遗留至今的残存物,是“活化石”。又如,按单线进化模式,人类婚姻家庭应是按照从母系制到父系制的“杂交—血缘婚—群婚—对偶婚—一夫一妻”过程进化的。于是一些地区或民族中存在的母系制、走婚制(类似于中国永宁地区摩梭人的婚俗),就都应被解释为是原始社会婚姻家庭形式的残余,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低级落后的东西,是应当予以废除的“陋俗”。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与民族音乐研究中,可举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我在《儋州调声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1 期)一文中谈到了海南岛儋州方言区的情歌演唱习俗。当地有“不落夫家”的婚俗。未婚青年与未落家的已婚青年均住于村中公房(当地称“后生家笼”〕中,通过情歌演唱寻找性偶,直至有了头胎子女之后才离开公房与法定配偶组成家庭。当地民众中素有“头胎子女众人生”之说。类似的音乐文化传统在中国不少民族或地区都存在。从现有的出版物来看,中国大陆的人类学者与音乐学者是毫无二致地根据社会文化进化论把这种传统解释为“原始群婚制的残余”的,认为它是人类婚姻家庭进化过程中低级阶段残留至今的东西。
在西方,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摩根学派的这种单线进化论就遭到许多人类学者的强烈批评。后来西方的人类学者们逐渐抛弃了这种单线进化论,认为这种单线模式只是由案头工作得出的推论,并没有足够的史实与田野调查实证的支持。经由调查发现的上述“残余”与“例外”太多,大大超过了“例外”所能允许的正常值,大到足以整个推翻该理论的程度。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这种单线进化论导致文化优劣论,即认为由于社会进化速度的不均衡,某些社会与文化还处于进化的低级阶段,其文化比“高度发达”的欧洲或其它某些文化低级落后。这是种族主义的文化观,它为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都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殖民行为、文化侵略以至对“落后民族”的文化灭绝,都被认为是合理的,是在“帮助”“落后民族”从“原始社会”“跃进”到“现代文明”。
人类学界反对社会文化进化论最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是现代美国人类学派创始人博蔼士(Franz Boas )。 他提出了文化相对论(culturalrelativism)的观念。这种观念至今仍在人类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相对论认为对于每一个社会、每一种文化,都应从它自身的逻辑来理解,认为把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都放在同一个进化模式的阶梯上来排高低、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评优劣的做法是荒唐的。现代人类学界普遍强调的是社会与文化的变化而不是进化,认为不应给各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安上一个全人类共有的、单一不变的模式。人类学者研究社会文化事象,研究它们在该社会中存在的情形与原因,并可能对它们的社会功能及其在该文化系统内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价值作出判断。但是,研究者却不应当以他(她)本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及道德标准为准绳来对该事象作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文化相对论本身不包含道德原则,它在人类学中所起的是方法论作用。它帮助我们在调查研究各种社会与文化时不把研究对象给摆到与其不相关的意识形态或道德天平上去。当然,这不等于说它暗示人世间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好坏标准或美丑共识。人类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同,另一方面又试图找出潜藏于其中的共同的东西。许多西方人类学者在生活中确有自己所持的评判事物好坏正误的鲜明见解,但他(她)们在学术研究中却是相当严格的文化相对论者,能抛开自己个人在生活中所持的政治、意识形态及道德成见,对研究对象不作上述类型的评判。西方当代人类学界中的一个共识是,人类学不能解答哪个社会哪种文化较好或较坏的问题,解答这类问题不是人类学的任务。
社会文化进化论在当代虽已衰微,但却仍然存在。所不同的是,今天即使马克思主义进化论学派也已抛弃了早期单线进化论的模式及其种族主义内核。当代社会文化进化论主要有两派:单线进化论(unilinear evolutionism )与多线进化论(multilinearevolutionism)。当代单线进化论主要通过人类对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发展轨迹来理解进化,这包括从采集狩猎到农业工业的发展、水利灌溉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等等。在这一方面,不论是否进化论者,当代学者们还是达成了某些共识的。比如说,某个社会或民族既无现代科技也无文字,那我们可以说他们在科技方面落后,但却不应当说他们的文化也落后。以有否文字或现代科技作为文化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那只是有文字或科技发达的社会自己所持的评判标准,是该社会以本体系规范为准绳的逻辑思维。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而已,却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别。多线进化论认为人类在社会结构方面是有一种大致相同的进化模式的,即:群体(band )—部落(tribe )—酋长制(chiefdom )—国家(state),但又认为历史、地理、 生态环境等因素都能导致不同的变体出现,重视了对大量的个例及变化形式的研究。而在当代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或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 )中所流行的文化进化观则是非单线的(non-unilineal)。 这种观点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其实已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单线社会文化进化论相对立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进化论是强调进化规律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认为人类社会是必定按照这种单一不变的规律来发展的。
与进化论共存的另一历史学派是传播论。传播论认为文化不是进化的而是传播的、互借的、扩散的。从表面上看,传播论似乎与进化论相抵触,但在实质上它们却有相似之处,二者殊途同归。早期的传播论者中的极端分子认为人类中的某些种族天生就是没有发明创造力的劣等种族,他们现有的文化都是借入的、外来的,倘无外来的传播,他们的文化是注定要灭绝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类学家开始偏重于对单一社会作详尽的调查研究而不太专注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历史性的解释,因而传播论也开始被冷落。但到了90年代,传播论则以新的面貌卷土重来。这得力于世界上现代与“后现代”现象的出现。例如高科技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现代传播媒介(例如广播电视、电脑互联网及信息高速公路)的作用、“地球村”现象、移民、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互融、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倾向等等。当然,新的传播论已摒弃了早期的种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内核,打出的是全球化理论(globalisation theory)的旗号了。
3.略谈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与两性研究
海外学界近几年来讨论得比较多的课题是新兴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后殖民主义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与两性研究(gender studies)。西方不少大学已开设了这类课程或有了专职教员。但这些研究还都未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因此我先前把它们译为“文化学”、“两性学”恐怕不太合适。在西方,人类学已是历史较长的学科,各家各派的人类学概论很多,但目前却还看不到“文化学概论”或“两性学概论”,书店里琳琅满目的还只是这几个领域内的各别专题研究以及文集。中国大陆也有以“文化研究”为题的刊物,例如《中国文化研究》,但这与西方的“cultural studies”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此类刊物较多地是对传统的、狭义范围内的书面文化的研究,例如研究文字、文学、文人艺术等等,而目前西方的cultural studies则是在广义的范围内研究各种文化事象,不受限于书面文化或有文字的文化,实际上还反而更加注重对非书面文化的研究,并且特别注意被早先的传统观念忽视了的边缘现象(marginal phenomena),例如移民文化、女性文化、亚文化(例如同性恋文化)以及不同文化的互动现象等等。与文化研究相随而兴、交汇融贯的是后殖民主义研究与两性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的话题之一是“殖民者走了之后的殖民现象”或“无殖民者的殖民现象”。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位同事研究澳州北方土著人的民间音乐,其主流是基督教音乐,现已成了他们的传统。对这类现象进行深层挖掘就很有意义。由此我联想到中国的类似情况。比如某些地区的苗族民间音乐就包括了基督教音乐,但我还没见到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发表。中国社会与文化中具象与抽象的后殖民现象以及有关的课题可能不少,其中也有与音乐文化相关的,应当是很值得深入研讨的。
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在传统上是侧重于研究“非我文化”,研究非西方、非工业社会的文化。但在当代人类学中,西方的工业社会与文化也成了研究对象,同时,一些非西方的人民中也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人类学者,他们不仅研究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也研究别人的社会与文化。这样,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变化,二者的关系成了可以互换的了。更进一步,人类学研究本身也成了研究对象。西方人类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了所谓emic/etic(中国学界将此译为“主位—客位”)的讨论, 而近年来则出现了“decolonizing
anthropologicalmind”(“非殖民化人类学思维”)的提法与作法。西方的音乐人类学界步其后尘,在80年代中后期也展开了对于“emic/etic”的讨论,而在90年代则也出现了所谓“decolonizing ethnomusicology”(“非殖民化人类音乐学”)的提法。说到这里,我想借用中国的例子来较具体地谈谈。中国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是否产生了自己的音乐理论与音乐审美体系?倘有,则它们可否用于研究、分析或解释中国音乐?如果只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音乐,那是否西方殖民主义心态的表现?中国有人提倡建立中国自己的音乐学、音乐美学或音乐理论体系。我认为,这从大方向来说是符合当今国际学界decolonizing ethnomusicology的思潮的。但同时我也认为,这里有两个课题值得讨论。其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中(注意我此处所说的文化,不是狭义的书面文化,而是前面所说的广义概念上的文化),是否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这样的体系?当代学者的任务是学习、挖掘、整理、总结这样的体系还是现在来从头创建这样的体系?其二,不论是整理总结还是创造建立,我们所持的原则、思路与方法是否在骨子里仍然是西方的一套?从小在殖民与后殖民环境中熏陶或教育出来的学者们是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循着西方文化的原则与思路去总结或创建中国的东西?与此类似的是,从小在汉文化中熏陶与教育出来的学者们会否循着汉文化的思路去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或沿此思路去试图总结或创建少数民族的体系?
简略谈谈两性研究(gender studies)。这里的“gender”是“性别”而不是“性”,两性研究侧重的不是性问题而是对与性别有关的社会与文化事象的研究。西方的两性研究中目前最热门的恐怕是女性课题的研究。在学术历史上,女性文化的研究常被忽略,但近年来在西方却出版了很多有关的学术文论与专著,一些大学也开设了此类专项课程。其实中国近年来也可见到此类出版物,例如对于女书的研究,或对于古代乐妓的研究等等。
4.民族、族性、国家主义、文化标识与文化身份
对于中国的“民族”一词及其概念,包括“民族”在中国的定义、指称范围与实际划分,西方人类学界近年来有所讨论。我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谈中国的民族识别与民族音乐的文章(《也谈“回族民间音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7年第1 期)中介绍过一些西方学界的有关言论。大致而言,越来越多的海外人类学者认为,“民族”一词在中国在概念与使用上都比较含混。如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民族作官方划分的国家之一,其民族识别在表面上的依据是斯大林的有关定义与理论,但在实际上则有的是侧重于文化标识,有的是侧重于血统,有的是侧重于政治上的考虑,有的是出于尊重民众感情与心理,有的是依循历史上的既成事实,有的则依凭被识别者的本人意愿,种种的具体做法,不一而足。
在由中国大陆学者翻译的英文文字中, “民族”一词常被译为“nationality ”, 其依据可能是斯大林的理论。 但在英文里, “nationality ”有“国籍”的意思。 在西方人类学概念中, “ethnicidentity”(民族身份)与“nationality”(国籍)是有区别的, 二者不一定对等。一个民族倘若有本族的疆界且此疆界与由该族自己统治的国家疆界相吻合,那可以把它叫做一个“nationality”。 但许多民族并没有一个由本族统治的、在政治、文化、疆界上都统一的国家实体(nation-state),而且也没有要建立并统治这样一个国家的要求。如果一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领袖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就成为国家主义运动了。中国现有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似乎并不符合英文里“nationality”的含义, 因此大部分西方学者是将中国的“民族”译为“ethnic group”。然而随着海外学界对有关课题的讨论及认识的深化,学者们已经认为中国的“民族”事实上与当代人类学中的“ethnic group”的概念也不相同,因此有人建议将中国的“民族”一词干脆就按其读音译为“minzu”,以示区别。
至于什么是ethnic group,当代西方人类学界有过不少讨论,也达到了一些共识。现在一般认为,如果某些人民认为他们是有别于其它人民的、可以自成一族的一个群体,而且成功地说服了本群体的人民以及本群体以外的人民,使得这些人对这一群体所选择的这种族体身份都加以认可,那么,这个群体作为一个ethnic group的身份就成了既成事实。在这种意义上,ethnic group应是一种人为的东西,是人工的产物,但这种“人为”指的并不是官方或学术界的划分,而是该人民群体与其它人民双向与多向的接触、交流与互动的结果。Ethnic group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流动性的、条件性的,其成员可能流动、交换,身份亦可能改变。
我至今为止还未找出一个恰切的中文名词来翻译ethnic group这个概念。中国有人将其译为“族群”,但我觉得此译仍有些不妥。因为,从中文字面上看,“族群”可以被理解为是由好几个“族”组成的“群”,而英文ethnic group从字义上看则仅指一个单数的人民集合体,这里边有“族”的含义,但并不表述这个集合体是否由几个“族”组成的“群”。由于一时找不到恰切的中译,在不导致太大误解的情况下, 我目前是将就使用中文的“民族”一词来翻译 ethnicgroup的。
与ethnic group直接相关的一个词是ethnicity。 中国的同行们告诉我,有人将其译为“族性”。这大概是至今为止我见到的较能达意的译法了,因此我也借用这一译法。
本世纪初,许多理论家预测,随着工业化、个人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族性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少,最后消失。现在看来,这个预测是错了。事实正相反,80、90年代世界上最明显的冲突既不是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国家间的冲突,而是民族冲突。从60年代末开始,族性成为西方人类学的一个中心议题,一直延续到90年代。而西方音乐人类学界到80年代才跟上讨论这一课题,到90年代它也成为中心议题。目前西方学界一般认为,族性与民族一样地是人为的、相对的东西。族性涉及的是民族的区分与各族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包括某一族有别于他族而之所以成为自己一族的所有方面,而这些区别,不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人为的,又都是通过该族与其它各族的关系显示出来的。倘若没有与他族的对比,族性就显示不出来,也就等于是实质上并不存在。这跟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是一样的。
跟民族与族性紧密相关的话题是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 民族标识(ethnic marker)、以及国家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与族性往往需要民族标识相辅,而文化又常常被利用来作为这样的标识。一个群体要维持其民族身份(ethnic identity), 就必须有一些对内对外都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文化的“独特”就常被用于作此证据。近年来, 西方人类学者越来越注意研究这一现象, 例如研究文化象征(cultural symbols)或文化标识(cultural marker )与民族身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文化与民族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构建的东西,是一种与意愿、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人为产品,它们是相对的、可变的、流动性的。民族及其文化有融合、同化、灭绝。复兴、繁盛等等多种可能性。此外文化标识还有时段性。某种文化在某一历史时期可能是某一民族的标识,而在另一历史时期却可能不是。唐代以前的西域乐器,在唐以后就可能成了中国汉人的乐器。作为音乐文化的一种标识物,它的身份就改变了。文化属性经常没有绝对明显的分界线,而且并不一定与民族分界线相吻合。同一民族不见得文化相同,不同民族不见得文化不同,族性与文化性征或特征并无绝对的因果关系或等同关系。大部分人类学家认为,在辨别民族与族性时,社会组织结构及其与外部的互动应是更重要的基本因素,而文化只是社会状况的外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文化差异其实是民族分界的果而不是因。
与此相似,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东西,不能绝对地看待它。传统也是有时段性的。随着时代变迁,某些传统可能变化,某些传统可能消亡,而某些已经消亡的传统却可能复兴,某些东西又可能成为新的传统。作为一个研究者,对文化与传统的变化应当十分敏感。比如说,研究民间音乐的,不宜仅仅着眼于所谓“原始的”、“真正传统的”东西而对当代的变化不屑一顾。有很多当代课题是很值得研究的,比如民间音乐与现代化、与工业化、与商业化、与都市化、与国际化、与经济、与科技、与旅游等等的关系、互动以及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意义,都是有研究价值的课题。
西方当代人类学界对民族、族性以及文化的这些新认识在音乐人类学中可能引起革新性的观念改变。音乐研究者需要重新全盘思考过去已被视为定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认识。比如“汉族音乐”这一概念,在中国音乐学界似乎早已取得了共识。但现在我们倘在上述新观念中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思考,可以提出的问题就可能很多。如果所谓的“汉族”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整体,如果民族、民族身份、文化标识等等都是可变的、条件性的,那么先前中国音乐学界对“汉族音乐特征”的归纳是否合适,就值得重新探讨了。
现代社会的迅速变化对传统人类学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新的方法要求。人类学界与音乐人类学界都需要相应地跟上时代的要求。与族性研究紧密相关的国家主义研究在人类学中就是一个新课题。国家主义研究多年来只是政治学、历史学及宏观社会学中的课题,但在本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它也成为人类学中的研究课题,对人类学的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多年以来传统人类学在对于族性的研究上有两个倾向:(1)偏重于研究小社区以及单一民族,而这是以传统方法对付得了的。 (2)偏重于研究“他我”,且常是边远地区的“他我”。但今天, 人类学的主流却是研究复杂的、无界线的体系,而不是那种被以为是孤立(实际上并不一定孤立)的小社区。目前对于“什么是国家主义”这一问题,人类学界尚有歧见。有的学者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想象的、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成员彼此从不相识,但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想象出来的社会共同体之中,一个成员可以为一个国家献出生命,就说明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有的学者则认为国家主义是统治民族的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实质上就是统治民族的国家,这个民族的国家主义意识则认为他们本民族就代表这个由他们统治的国家,而国家的标识物(markers of identity)例如语言、宗教等等, 实际上是由统治民族官方制定的象征性标志。大致而言,学者们都认为国家主义是与族性有关的,它是族性的延伸或是变体。在大部分情况下,国家主义在性质上是族性的。一种普遍的现象是,国家主义常常强调文化的统一,然而这种“统一”的文化实质上并不一定就真正是原来就属于该国全民的东西。人类学家艾里克森(Thomas Eriksen)在他的著作《族性与国家主义》(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London:Pluto Press 1993 )中举过一个例子。挪威于1905年从瑞典分离出来,就是先搞出一个有别于其它文化的“真实的挪威文化”,借此弄出个“挪威身份”来。实际上那是由当时的挪威国家主义活动家们到偏远的乡村去找出一些他们认为有特色的习俗、服饰、音乐、舞蹈并成功地在挪威各地推广为“挪威文化”的。这种文化身份,实际上是人为的。
艾里克森在上述著作的结语中谈到,族性的概念及研究为人类学拓展了视野及研究领域。可以预见,这方面的研究将继续为我们提供新的课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族性的研究,仅仅是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工具。与其它任何工具一样,我们必须持这样一种态度:当这种工具由于时代、情况等等的改变而不再适用、成为对孕育新观念、使用新工具的束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及时放弃或更新它。艾里克森的这种观点,是否值得借鉴?人类学是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它要求学者们随时准备根据新发现新证据来修正已有的观念与方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不是固守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并认为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万代适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