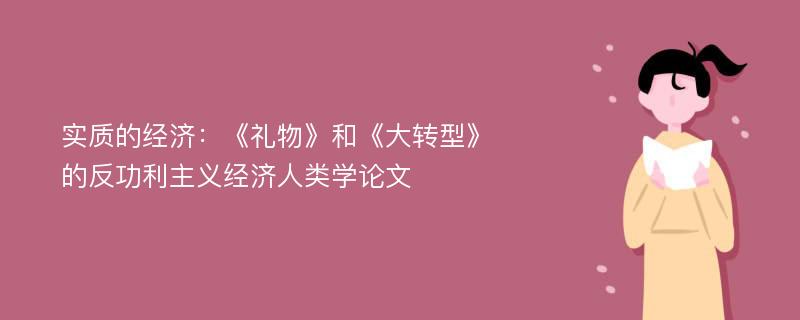
实质的经济:《礼物》和《大转型》 的反功利主义经济人类学
余 昕
摘 要: 莫斯和波兰尼在《礼物》和《大转型》中开创的经济人类学视角为反思当前状况提供了思想资源,但20世纪以英美人类学者为主的解读偏离了两位作者的真实意图并忽略了两者的相通性。这包括:对功利主义的形式经济概念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礼物与商品对立的反对;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形式性交换是对社会的实质性交换,即存在于社会深层结构和心智系统中的交换的组织和体现;莫斯和波兰尼在探索现代社会和个人观念的诞生问题上,可以构成互补。最后,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虚拟商品”“嵌入”的观点以及莫斯关于“总体呈现”的论述,都应置于他们对社会的整体性和实质性的坚持中来理解。莫斯和波兰尼的论述拓展了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提供了对个体自由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他们提出了一种以社会整体性为基础的关于“经济”的多元概念,二者共同奠定了实质主义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人类学基础。
关键词: 《礼物》 《大转型》 实质经济 市场 货币
市场和货币,似乎是大航海时代以来的现代世界毋庸置疑的基础。20世纪的世界历史,更可视为在不同的市场和货币型构之间的挣扎。进入21世纪,面对将近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带来的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建立在另一种市场和货币基础上的经济(alternative economy)的探索,成为目前思想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这一探索中,本文认为需要将两部著作并置——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原版于1925年出版,下文简称《礼物》)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原版于1944年出版,下文简称《大转型》)。它们为现下的困境提供了同一个答案,即经济人类学的反功利主义立场对现代经济和社会提出的洞见。
莫斯生于1872年,逝于1950年。波兰尼生于1886年,逝于1964年。在同样的78年人生和学术生涯之中,两人都曾面对19世纪以来传统社会瓦解、宗教权威衰落、追求个人自由、个体主义兴起、市场和货币日渐普及并成为人类关系的中介等一系列重大变迁;两人都不幸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两人都在青年时期热衷于政治,并且都为报刊撰写了大量政论性文章。两人都转向社会主义寻找出路,并在此找到了个人与社会之间深刻的相互依赖。[注] 应当注意,在19—20世纪初期欧洲存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本文是在当时的语境下使用这两个术语,不能和二战以后其他地区的发展和当下的情况混淆。本文引用的社会主义概念不同于今日科学社会主义,下同。 《礼物》和《大转型》希望理解的都是20世纪之交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而它们指出的方向都是如何在整体的社会和具体的人的实践中理解人性和历史亘古不变的社会之根。
尽管无论是著述还是作者本人都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迄今为止却很少有学者将波兰尼和莫斯以及他们的论著进行细致比较。[注] 目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莫斯和波兰尼思想的内在共通性。凯斯·哈特(Keith Hart)注意到,尽管波兰尼对市场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明显相关,但他对经济决定论缺少好感,而倾向于认同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这表明他对涂尔干和莫斯的理论情有独钟(Hart,2007);菲利普·斯特勒(Philippe Steiner)认为波兰尼的“嵌入/脱嵌”和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机械团结”很相似,并指出波兰尼和涂尔干学派的取向都在于从现代经济观念和社会意识的角度反思现代资本主义市场在漫长人类历史中的特殊性(Steiner,2011)。波兰尼的学生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的学生,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在《经济人类学》一书中屡次提到莫斯并予以很高评价,详见本文论述。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未有学者对《礼物》和《大转型》进行细致和深入的比较。 这或许是因为这种人生经历在世纪之交那一代学者中并不罕见,又或许是因为虽然波兰尼曾在著作中零星地提到了涂尔干的作品,但对当时涂尔干学派中经济社会学的领头人丝毫未提及,并且在论著中从未提起莫斯的《礼物》(Steiner,2011)。另外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位学者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不同态度:莫斯一直很小心地保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学术兴趣之间的距离,他用法语写作的政论性文章很晚才被翻译成英语并为英语学术界所了解(Gane,1992)。相反,波兰尼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与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论战剑拔弩张。学术和政治对于莫斯而言需要泾渭分明,但对于波兰尼而言,两者总是难分难解。但如下文所述,所有可能的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英语人类学界对两部著作的解读偏离了作者的本来意图,这种误解随着学术与政治的分隔、学术专业分工的加剧而愈演愈烈。而如果暂时悬置20世纪经济自由主义对我们视野构成的局限,学者和著述的整体性将成为我们重新思考的起点。
一、 时代的误解和国别的偏差
在“礼物为何要被归还”这一问题的指引下,《礼物》描写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集体之间、个体之间、人神之间的交往:从美拉尼西亚氏族之间的开放式的相互依赖,到西北美洲夸富宴中以首领为代表的个人竞争,经过古代罗马、日耳曼和印度法律的过渡,最后到现代西方社会的基础——个人之间的契约。莫斯以“交换”为关键词囊括了一系列遍布世界各处、具有相当差异的礼物流动现象。然而正是这种叙述方式构成了《礼物》自身存在的张力,也为后人有意无意地误读《礼物》创造了条件。
莫斯(2005:10)主要描写了原始社会中两种全然不同的“交换”形式,一端是氏族、部落和家庭之间的“总体呈献”,另一端是首领个人之间的竞争性的“夸富宴”,并将它们分别视为“基本的总体呈献”和“竞技式的总体呈献”。然而,在严格意义上,礼物交换并非缔结这两种关系的基础:前者是两个氏族之间并不会因为还礼较少或不还礼而终结的、永恒的开放式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礼物并非被归还,而是在拥有永久关系的双方之间不断流动;而夸富宴,正如莫斯自己承认的,是一种“相当罕见”的交换体系(莫斯,2005:9),其中礼物并非在对等地“交换”,而是基于超过或摆脱对方控制动机的个体竞争(Graeber,2014)。
更奇怪的是,莫斯并没有在“第四种交换”,即人—神献祭和不可转让的神圣之物的问题上着墨太多。这一点很不寻常,因为就涂尔干开创的神圣社会理论而言,社会存在的基础恰恰在于神圣之物的不可交换性以及人与神之间不断的献祭(Weiner,1992)。行文中对神圣之物的排除使得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可以在随后的解读中把社会描述为女性、财富和词语的三重交换(古德利尔,2007:72),这无意之中也就创造出了一种假象:礼物形式上的交换足以成为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后人的解读中,作为形式和制度的“交换”成为了《礼物》的核心,然而,根据希尔德(Sigaud,2002)的考证,20世纪30年代,“交换”这一主题并没有被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等评论者们视为《礼物》的核心问题,但在1946年列维—斯特劳斯为莫斯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作序之后,形势就开始发生变化。列维—斯特劳斯在序言中盛赞莫斯对于礼物交换的敏锐观察,宣称莫斯的洞见启发了自己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同时指出《礼物》中关于毛利人“豪(hau)”的观念实际源于作为研究者的莫斯的误解与本土观念之间的落差,并认为这一观念的起源应为人类的交换本性(列维—斯特劳斯,2003)。这进一步引导萨林斯(2009)在1972年出版的《石器时代经济学》中继续将《礼物》写作的重心引向交换、礼物之灵和对毛利民族志材料理解问题的讨论。
同现代市场一样,现代社会试图用一种“全能”(all-purpose)货币取代及整合上述所有职能和价值体系,这就是用于间接交换(indirect exchange)和买卖的商品货币,其最主要的作用是便于在两个拥有私有产权的个体之间完成交易(Hann and Hart,2011b: 95)。前现代社会的不同价值体系的货币流通限制在特定的社会领域,服务于特定的社会目的,由此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完成社会的分化和整合;而现代社会的商品货币,倾向于将社会组织成更为均质的形式,试图以“交易”的形式完成前现代社会不同货币领域的职能(社会区分、饥荒、战争……),其结果是对人类社会之中货币作为社会服务的遗忘(Polanyi,1977:120-121)。
庞大的足球教练员群体是保障社区足球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社区足球作为“双金塔”足球人才培养体系的纽带,对英国足球人口普及作用巨大。以此次赴英留学所在地英国足球超级联赛老牌劲旅斯托克城(Stoke city FC)足球队为例,该俱乐部下属的社区部(Community Department)具有英足总Level 1级以上水平的教练员共计125人,其中俱乐部全职教练员48人,兼职教练员77人。如果没有庞大的教练员体系,作为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链接纽带的社区足球就无法正常运行。
《礼物》对于“交换”的执着而产生的内部张力,因时代的误解与国别学术传统的差异而转变为后人解读与其原旨之间的“外部张力”,表现为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列维—斯特劳斯的交换理论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去神圣化”以及20世纪末期将礼物与商品对立。从20世纪初期到末期,从法国到美国,《礼物》走过了一条与莫斯本意完全不同的学术轨迹,使人遗忘了作者在开篇就提出的道德和政治主题。颇有意味的是,波兰尼的《大转型》也同样遭遇了类似的时代的误解和国别的偏差:在法国,《大转型》被视为20世纪最经典的十部社会思想著作之一,然而在北美学界,波兰尼的影响直到最近都仅限于人类学内部,即便有学者认为他的著作对于更广泛的社会思想有重大意义,这样的看法也在学界处于边缘地位(Baum,1996: vii)。与《礼物》类似,《大转型》遭遇的批评和误读同样与20世纪晚期英美人类学理论范式中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有关。
增强MRI联合CT的敏感度、特异度及阴性预测值明显高于CT扫描和增强MRI(P<0.05);而阳性预测值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2。
正如表面上波兰尼比莫斯更深入地参与了政治,相较于《礼物》而言,《大转型》的命运似乎更明显地受到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伴随着《大转型》写作的是波兰尼本人的颠沛流离。1933年,波兰尼从维也纳移民到伦敦,为英国工人不定期讲授经济学课程,并担任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项目助教,艰难为生(戴尔,2017:138)。与英国工人的近距离接触使得波兰尼有机会将英国作为自己的民族志田野(Hann,1992),并将之作为自己在《大转型》中反思工业革命对于人类社会意义思考的灵感源泉。
1944年《大转型》的出版并未为波兰尼赢得应有的声名,并且,作为对战后世界构造的期待和预测,政治经济现实亦未像波兰尼预测的那样发展。二战过后,波兰尼移民北美并受邀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这是因为当时该校经济制度主义学派发展势头强劲。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制度主义已经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取代(Yonay,1998),随之而来的是波兰尼的论述在经济学界的式微。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冷战背景之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阵营都对波兰尼的论述漠不关心,直到70年代末期,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以及持续的金融危机的到来,加之20世纪末期东欧的政治巨变,引导一部分社会思想家力图寻找一种不同的社会改革,此时波兰尼才再度备受关注(Block and Somers,2014: 6)。尽管如此,波兰尼从未获得如其对手哈耶克、弗里德曼那样的声誉。
如同铸币往往一面刻着国徽、一面刻着金额,货币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国家和市场、神圣和世俗的双重属性,它们也总是不断穿梭在匿名的交换和具体的社会情境之间(Hart,1986)。货币的这一特征,代表了“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不变的社会本性”(波兰尼,2007:39)。波兰尼晚年对古式和原始社会的研究,进一步证明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体系和商品货币在人类历史上的“反常”。在《货币对象和货币用途》(Money Objects and Money Uses)一文中,波兰尼对弗斯的指责让人想起莫斯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波兰尼指出,现代经济学家和以弗斯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误认为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交易”才是货币最根本的属性,由此造成对原始和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误解(Polanyi,1977:104)。而对作为商品的货币之起源的梳理发现,在很多原始和古式社会之中,执行支付职能(means of payment)、价值尺度(standards of value)、财富贮藏(storing wealth)、交换手段(means of exchange)的物质对象可能属于具有完全不同运作规则的价值体系。例如,这些职能可能分别由奴隶(支付领主)、贝壳(对外贸易支付)和贵金属(贮藏)担任。并且,与现代经济学家宣称的相反,偿付、贮藏、价值尺度等货币具有独立的、远早于商品货币的起源,而不是商品货币的职能衍生了货币的其他功能(Polanyi,1977:98-99)。在这些货币职能之中,逐利动机和占有财富的动机并不突出,例如宝物作为偿付手段,其赠送的动机在于社会力量和影响而非对等的“交易”(Polanyi,1977:109)。
这让人想起20世纪后期的学者们从《礼物》中“读出”的商品与礼物的对立。同样类似的是,这样的误读也不乏作者自身的原因。《大转型》中对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连篇批评以及波兰尼后来在美国转向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确实为后人的准确理解设置了障碍。同样也是波兰尼本人发起了经济的形式主义—实质主义的论战(Polanyi,1957),而恰恰是20世纪5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波兰尼经济学通史研讨会(戴尔,2017: 256)并自称为实质主义者的萨林斯,在结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帮助下,凭着《石器时代经济学》将经济过程视为文化观念的运作结果,物质生活被视为由地方符号体系组织,从而强调经济的文化、历史和制度基础,推动了至今仍然活跃的经济人类学的文化转向(Hann and Hart,2011b: 84)。自此,“市场理性”和“文化结构”的矛盾愈发被视为不可调和。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场论战的硝烟散尽,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时代,经济人类学的领域被局限于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要么不属于人类学研究范畴,要么被等同于消费或者流通(Appadurai,1988),波兰尼的作品愈发乏人问津(Hann,1992)。在“形实”之争过后,《大转型》的真义,即市场社会和经济理性人对于西方社会而言都是一个乌托邦,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到了20世纪末期,礼物与商品,非人性的市场与人性的社会交往,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已经成为横亘在我们理解《礼物》和《大转型》之间的障碍。越过这一障碍,不难想起几乎在开篇第一段莫斯就表明,在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对送礼动机的研究之目的,在于对“契约道德的恒定形式”的讨论(莫斯,2005:4-5)。而行文中之所以对人神交换一笔带过,则是因为莫斯认为,亡灵和诸神“才是世界上的事物与财富的真正所有者”(莫斯,2005:27),人神交换不过是人类对神灵的回礼。质言之,莫斯力图表明的是他身处的现代社会的契约统统有其集体或神圣的起源,而推动这些研究的是对当时社会的道德和现实关怀,因为在原始与古式社会中发现的道德与经济仍然在现代西方社会深刻而持久地发挥着作用。对这些社会的研究,“从中能够发现建构我们社会的一方人性基石”,可以“解答我们的法律危机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某些问题”(莫斯,2005:6)。他的回答,与其说是通过研究“他者”而对现代文明的实际情况进行批判,毋宁说是旨在质询现代文明的自我想象。
也几乎是在一开篇,波兰尼(2007:3)就表明,“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他笔下的“大转型”所指涉的,与其说是作为实际运作的市场的出现,不如说是自由主义市场的意识形态、对“人”之自然状态的想象及支撑它们的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换言之,波兰尼对自由市场之批判的力量,并非在于它指向的是作为实然存在的市场过程,而是作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市场迷障。波兰尼关注的,与其说是实在的社会关系,不如说是市场心智(market mentality)(Steiner,2011),他的主要目的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解构。
当莫斯和波兰尼身处一战后的废墟之中思考社会重建的问题,并将社会整体置于答案的中心时,列维—斯特劳斯则在二战之后积极反思诸如纳粹之类的“神圣”政权,并将社会做了“去神圣化”的处理,其方式是以人类交换本性作为社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莫斯、波兰尼和列维—斯特劳斯都在“经济”的基础中排除了个体之间的功利主义契约。然而20世纪下半叶,分别从列维—斯特劳斯和经济的“形实”论战中读到了莫斯和波兰尼的英美人类学界,一方面将两位学者奉为市场经济的讨伐者,另一方面又忘记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讨伐是将其作为经济形式而非社会实质,结果导致在相反的方向还魂了“经济理性人”。经济人类学的文化转向过后,对莫斯和波兰尼的误解,让人遗忘了这一视角开创之初的经典问题:“经济”作为独立于社会的领域,本来就是现代工业社会中自由经济主义者的乌托邦想象。在二战后发展话语的高歌猛进、苏联解体的动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光怪陆离之中,经济人类学似乎愈发缄默。
BIM运维平台可为改造和二次装修等工程提供可靠的信息支持和直观准确的空间分布关系展示,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保障施工安全。
二、同一场战争
《礼物》和《大转型》无疑都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族志材料相当倚重,但莫斯和波兰尼似乎都得出了与马林诺夫斯基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前所述,莫斯已经在《礼物》中批评了马林诺夫斯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还魂”;而据韩可思(Hann,1992)推测,20世纪30年代,身为难民的波兰尼从未有机会与当时已经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的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共事或深交,也未受到当时盛行的功利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于莫斯而言,英国的工团社会主义让他印象深刻。在1920年秋天去英国的途中,他惊异于“特别英国化的”合作社和工团主义运动组织,发现英国的劳工党这个“源于大型的、有组织的、受过教育的民主政治的合法政党”可以将纲领付诸实践(福尼耶,2013:221-229)。对于波兰尼而言,近距离与英国工人的接触和对罗伯特·欧文的推崇让他更倾向于基尔特社会主义(Hart,2007)。英国,对于莫斯和波兰尼而言,一边是需要反思的功利主义智识传统,另一边孕育着现代社会团结和改革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莫斯和波兰尼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智识立场上,都在经历同一场战争。
从亚当·斯密到斯宾塞,19世纪社会理论家认为,社会构成可能遵循着一条从国家强制和暴力到经济竞争和自由契约的发展路径。由日益细致的经济分工导致的现代经济发展构成了亚当·斯密所建立的英国经济学的基础,而经济个体主义则构成斯宾塞所推崇的社会进化论的核心。涂尔干学派的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看法的反驳(Graeber,2001: 153)。如果说英语学者们从“经济”的角度理解现代世界,那么“社会”及其相关的“社会学”“社会团结”等概念则是自卢梭以来的法国学者的贡献。因此,在涂尔干建立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当中,经济学属于社会学的一部分。在《社会分工论》中,涂尔干力图展示的是现代经济的社会基础。他认为,社会进化是分工和团结的辩证运动,在此过程中,社会和个人的力量和限度都得以扩张(涂尔干,2017)。英国学者对于个人契约的过分强调,模糊了社会的“非契约”基础(法律、国家、习俗、道德、历史等),而正是后者使得“经济”成为可能。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个体”是社会的结果,而不是如英国学者认为的,是社会的源头。社会学家的任务在于揭示这些“非契约”因素以及个体与社会共同演进的历史(Hann and Hart,2011b: 48-49)。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社会契约会成为莫斯长期以来关注的议题,《礼物》开篇即表明这只是“一项大型研究的一个片段”,这一大型研究致力于“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的各个分部或次群体之间的契约法律制度和经济呈献体系”(莫斯,2005:4)。这意味着,《礼物》的重点在于英国学者眼中的个人契约的社会起源及其各阶段形式,或者说,莫斯关心的是作为政治、宗教、道德混融的“交换”如何构成了社会契约或现代“经济”的前资本主义源头,而非这些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如何不同于现代社会。
作为对霍布斯、圣西蒙、斯宾塞或现代经济学家的反驳,莫斯发现,最初的社会契约并不需要国家强制力,这些契约也并非在个体之间缔结,而是建立在氏族、部落、家庭之间。并且,这些契约也并非由手段—目的的方式来指导,它们之所以被称为“总体呈现”(莫斯,2005),是因为它们是所有社会领域的——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混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的那样,交换的执行者既不是经济理性人,礼物交换也并非完全出于无私和慷慨:礼物赠与的确是自愿的,但是这里的自愿是自利与义务、利己与利他的混合。而功利主义社会理论家眼中的社会基础——个人契约,不过是建立在人物分离、私有财产和关于自我的观念之上的思想史演进结果。
也就是说,莫斯对个人契约论推崇者的批评在于,他们没有看到契约漫长的演进历史而倒果为因,误以为个人契约是全部人类社会的基础,从而导致对西方社会自身的误解。如果说莫斯认为经济理性和自我利益不过是现代西方社会不成功的发明,那么波兰尼批评这种假设的概念工具则是形式经济与实质经济的区别。
在学术与政治的平衡中,涂尔干倾向于科学家不过多参与政治的社会角色,莫斯则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党派人”(福尼耶,2013:266-267)。《礼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鉴析》集中体现了学术与政治兴趣的一次结合。它们都将“经济”视为类似于自然有机体的独立领域,而这一“自由”神话建基其上的私有财产和货币有着别样的本源,波兰尼关于市场和货币的研究路径与之不谋而合。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西方社会与非西方或古式社会毫无二致。下文将表明,波兰尼证明了现代市场社会的“经济学的幻象”(economistic fallacy)来自于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本体论意义上对人性的误解以及在认识论意义上对社会的误解,误以为自身的运作建立在人们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功利主义动机之上,正是这种形式经济的概念阻碍了现代西方社会完整地认识自身。如涂尔干和莫斯一样,波兰尼亦认为这种建立在个人利益和契约之上的社会观念远不能满足社会团结的需要(Block and Somers,2014: 30)。因此,经济概念的形式含义必须区别于实质含义,前者根本就是欧洲近代社会特有的幻象,而只有后者“才能产生对过去和现在所有经历过的经济体进行考察的社会科学所需要的概念”(波兰尼,2000)。
礼物的流动、互惠和再分配,对于莫斯和波兰尼而言,都是社会得以构成的制度性要素,他们都选择以制度的分析为起点,探寻经济的动机和逻辑,而不是相反。他们的发现不同于一脉相承的亚当·斯密、斯宾塞、马尔萨斯对于人类“利益最大化”的“自然本性”的预设,而认为人类社会的背后应当是一整套与功利毫无关系的混合的观念形态(Hart, Laville and Cattani,2010: 182)——“经济理性人”并非自然人。对《礼物》和《大转型》的重新阅读将发现,这一误解的形成需要经过漫长的思想史铺垫。
我国制定了很多关于基层畜牧兽医技术管理的法律法规,而且由于基层的设施条件存在欠缺,就使得工作落实非常困难。而我国正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期,畜牧业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多层次的体制改革。目前也有部分地区实现了良好的规划和发展,但相对来说这些情况大多发生在大城市里;而对于基层来说实施落实依然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例如,基层畜牧兽医治疗设备就难以企及大城市中兽医的治疗设备,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且大多数基层畜牧业仍然处于原始放养的状态,难以进行系统化的管理,自然也就无法将先进的理论概念进行传导,非常不利于基层畜牧业的系统发展。
三、人类社会的市场和货币
莫斯和波兰尼宣战的同一个对象是“经济理性人”,并不是因为它构成了西方社会自身的基础,或是因为它并不存在于非西方社会,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个稻草人。同样的,自由主义者眼中纯粹的商品经济和作为商品流通形式的市场和货币本身具有重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莫斯和波兰尼也同样对那些废除市场和货币的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莫斯重拾记者生涯,当时他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是国族主义,[注] 参见莫斯《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国族》、《诸文明:其要素与形式》等文,载于其《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一书(莫斯等,2010)。关于这些思考的评论,参见王铭铭,2018:1-53。 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福尼耶,2013:212)。《礼物》发表的前两年(1923—1924年),也是他参与政治活动最积极的两年。在《礼物》发表的同一年,莫斯发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鉴析》。在一战、俄国革命、国族、纳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中,这两篇文章同年发表并非巧合,它们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莫斯对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探索。
尼龙(Polyamide,PA)作为传统的工程塑料,是当今社会消费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品种最为齐全的产品。20世纪30年代,杜邦公司首先发明PA,1938年后尼龙产品开始正式面世。到2011年,全球PA生产总量突破750万t/年,其产量剧增。PA以其优异的力学性能、电学性能、耐磨、耐油、耐溶剂、耐腐蚀、易加工等特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1-3]。随着重工业向轻量化发展的进程加快,对塑料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尤其是具备优异性能的PA产品将引领生产趋势[4]。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社会学鉴析》一文,旨在提出莫斯心中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对莫斯而言,同功利主义者一样,它误以为市场和货币建立在纯粹功利的算计之上,而试图废除这两个对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元素,希望以军事的方式规划工业、消费和生产,导致破坏了对任何现代经济都不可缺少的工商业自由(Mauss,1992:183-190)。
在《礼物》的一个长段脚注中,莫斯表达了他对市场和货币的看法。他认为当马林诺夫斯基否认库拉宝物是一种“原始通货”(primitive currency)时,他仅仅是从狭义和“我们的货币”的角度理解货币,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宝物同现代社会的货币一样具有购买力,可用于偿付,并且是为社会所公认的、正式的和确定的,是度量价值的永久工具。宝物和货币的流通,打破了西太平洋各个岛屿的孤立状态,将人们带入更宽泛的互动范围之内,使得个人自由和社会团结在这种原始货币的流通当中不断发展(Hart and Ortiz,2014)。在这样一个由宝物、食物、声望的货币流动所构成的“市场”之中,货币具有人格的、社会的、精神的层面,它对内保证了社会的团结和利益,对外保证了社会依赖他者的供给和交互而延续(Hann and Hart,2011b: 15)。对莫斯而言,库拉交换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寓言(Hann and Hart,2011b: 51-52)。更重要的是,莫斯勾勒出了现代货币的谱系,即从具有巫术力量的宝物被赋予购买的权力而在部落内外流通,进一步发展出作为计算财富和使财富循环流通的手段。最后,货币脱离群体和氏族,成为度量价值的恒久工具,进而被当做普遍的或者理性的度量尺度(莫斯,2005:84-85)。
与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恰恰相反,货币并非源于扩大和普遍化的商品交换(马克思,2004),而是源于具有玛纳的宝物。这意味着,交换和货币在本源上并不是以手段—目的作为指导的行为,它们是由人类社会表现为玛纳的原初性所启动的行为。因此,波兰尼的徒孙,日本学者栗本慎一郎(1997:10-12)将莫斯奉为“在交换与货币的启动这种人类社会行为中发现无意识观念作用的第一位学者”。在波兰尼、多尔顿(George Dalton)、栗本慎一郎一脉相承的观点看来,正是长期共同生活的人群和组织中具有了一种结构化的生活方式,社会才有了“经济”;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并非源于稀缺,而是依赖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周而复始的财物与服务的供给。这才是美国、前苏联、特罗布里恩德岛都各有其“经济”的一个首要原因(Dalton,1961)。这种结构化的供给(structured provision),表现为莫斯笔下的赠礼习俗以及波兰尼分析的达荷美王国的祭祀等社会行为(栗本慎一郎,1997:11)。或许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莫斯发现,即便在现代西方社会和“非人性”的市场中,市场和货币被视为社会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但各种各样的慈善、合作互助、社会保险、礼物赠送行为依然存在,这证明现代社会的运作逻辑其实远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基于商品交换和理性的算计。市场社会远未实现,“经济人不在我们身后,而在我们前方”(莫斯,2005:173)。
财产所有权的混合情况构成了莫斯批评的另一个基础。如前所述,莫斯在《礼物》中对不可转让的神圣之物一笔带过,这表明他对“不可转让的财产”这一概念不感兴趣。根据古德利尔的分析,这可能是因为他想远离一种他认为是混乱的讨论——从19世纪末开始围绕着集体和个人所有权的种种观念进行的讨论,这种讨论又因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而重新点燃。1947年,他重申他的立场:
支配我们法律的主要区分,对个人法和不动产法的区分,是一个独断的区分,其他的社会对此相当忽视……所有权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我们为事物加上的术语不重要,集体拥有的财产由个人来管理的,如大家庭中的族长,等等……不管我们审视什么地方,我们都会看到在所有权上有多重律法的情况……国王的所有权、部落的所有权、氏族的所有权、村庄的所有权、某个群体的所有权、数代同堂的大家庭所有权,在同一个东西之上, 可能这些全有……(转引自古德利尔, 2007:45—46)
对于莫斯而言,集体所有权的概念显得含糊,笼统地概括了非常不同的各种情况。社会团结不应该建立在共同拥有财产的基础之上,是因为共有财产制度试图反抗的对象——“个人财产”,这一概念本身不过是罗马法之后才兴起的一种观念形态。《礼物》中关于“豪”的讨论指向的就是这种个人财产观念的基础——人与物的分离。“豪”作为礼物之灵,表明礼物中含有的精神本质并不会因为礼物的流动而与人分离。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难以分离,它迫使赠与之物回到原来的归属地。在美拉尼西亚的库拉交换中,在古罗马法、印度、日耳曼法律中关于物的表述中,莫斯发现现代法律制度中人和物的绝对分离的观念相当晚近,且甚为罕见。“豪”代表的是契约与交换得以实现的基础,即人与物的混融(莫斯,2005:41)。
王铭铭(2011:53-54)对此做出了精到的解读。正是“豪”这种力量,为社会提供生命源泉,使之不停留在固定的个体占有状态之中,而礼物正是在这种不占有状态中三种义务(给予、接受和回报)的不断循环,它表明人与物的“混沌”才是社会团结的基础。而人与物割离的情状,源自于一种个体主义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现代独有的观念不仅让个体凌驾于社会之上,其本身也因为没有继承历史遗产而险些迷失方向。在莫斯心中,再复杂的社会,其基本的品质都不过是在最简单的社会当中见到的人与物的难以割舍。
借由“反高潮”的叙事策略突转,张爱玲渲染出了悲悯苍凉的美学基调,带我们由世俗的外核进入到了生命的本质,达到对世俗生命和生存状态的审视:在那“呱呱啼叫的人性”里,越是追求彻底、完美、圆满,就越发会领悟到现实的不彻底、不完美、不圆满。在这些有意为之的“艳异空气的突然跌落”背后,张爱玲表达出了对人性的悲观意识、对生活的反讽意识,以及对社会的旁观意识。“反高潮”的处理,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召唤性,使人们的既定期待视野与小说的最终呈现之间表现出不一致性,作品的接受也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造成情感体验层面和价值判断层次的新变化,文学的功能也由此体现。
在货币和财产权的问题上,错误之处在于没能看到自己与古式社会共同的人性基石而难以理解自身的现代人。因为正是现代市场经济背后的功利主义观念,认为社会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让我们落入两种决定论的陷阱:要么遵循自由主义的决定论,要么用计划取代市场。莫斯眼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压制除一种所有权之外的其他所有权形式,或是除一种权力、一种群体之外的其他所有权力和群体,而是由专业团体、地方团体、国家共同构成的混合体。归根结底,“并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也不会有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唯一的可能是一种混合经济,即“资本主义、中央集权制、行政社会主义、自由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混合”(Mauss,1992:209)。更进一步,在一个社会之中,无论是道德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艺术的或是宗教的领域,都不应该占据主导地位,而研究它们的学科更不应该成为霸权——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个整体社会的概念分类而已。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同的领域只是共同生存的艺术(Mauss,1992:202)。
《大转型》出版之后,波兰尼转向了对原始社会和古式社会中互惠和再分配过程的研究,他希望从中寻找到区别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推崇的市场社会的、存在于真实社会当中实际运作的分配机制——实质经济。对他而言,研究前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价值在于,只有脱离了现有的社会,人们才能意识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行为可以被普遍效仿并且可以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这一假设是多么荒唐。换言之,波兰尼对形式和实质经济的区分,并非在于区分现代和前现代社会,而是意在表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过程以诸如互惠和再分配等各种形式和组织方式普遍存在于全人类社会当中,后者指引和规定了前者的运作(戴尔,2017:266-267)。如同莫斯所力证的契约的非契约基础,实质经济的概念意在证明现代经济的非经济基础,即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波兰尼,2007:40)。即便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换,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借以组织经济行为而实现相互依赖的人类生活的制度(Polanyi,1957)。
19世纪的理论家,无论是把市场作为文明的顶峰加以欢呼,还是把它作为癌变的发展而感到惋惜,都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出现是市场扩张的自然结果。在正统古典经济学教义中,市场的起点是个体交换的秉性,以此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然后推导出贸易,最终甚至包括远距离贸易在内的对外贸易的必然性。而当经济学家认为有证据表明原始人所拥有的心理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式的而非资本主义式的之后,他们的兴趣就限定在相对晚近的历史中(即在交换和交易具有一定规模的时期),原始经济则被贬入史前的范畴(波兰尼,2007:38)。在这样的脉络中,不难理解马林诺夫斯基会提出那个著名的对比:特罗布里恩德岛并不存在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人。
然而,波兰尼发现,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古典经济学刚好颠倒了市场演进的顺序: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产生了各种市场,不仅包含着以物易物,并且如果使用货币的话,还包含着买和卖,最终为某些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沉浸在那种自以为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即便如此,这也绝非必然(波兰尼,2007:51)。而远距离贸易,也往往以一种非市场交换的形式,如远征、战争、礼物交换的形式来完成。将视野从原始社会扩展到整个人类历史后,波兰尼注意到直到18世纪,西欧的经济体依然“嵌入”于社会之中,支配物质劳动和生计的不是独立自主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相互重叠的制度体系,市场往往发生在城镇远程贸易之间。直到15—16世纪欧洲重商主义政府有计划地将商业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国,才为国内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波兰尼,2007:57)。被自由主义经济学视为建立在人类自然倾向之上的独立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并直到19世纪才作为一个单独的知识系统出现。
波兰尼区分了市场和市场经济,前者是遍布于人类社会的分配制度,后者被视为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是现代的发明(Baum,1996: 4-5)。波兰尼在这里反对的远非前者,而是建立在想象的人类“交换秉性”之上的后者。换言之,市场体系的自然主义色彩建立在交换秉性作为人类天性的想象之上,这一市场体系继而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摇旗呐喊的自然发展趋势。如果说市场的起源并非交易(exchange),那么货币的起源亦非如此。同现代市场一样,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也是经由银行或国家金融机构形成的,这里波兰尼(2007:63)几乎用到了和莫斯一样的表述:“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它之所以和劳动力、土地一起被称为虚拟商品,是因为它和其他二者一样,不是为了出售或交易而出现的。
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区分了商品货币(commodity money)和代币。17世纪的西欧,在作为商品的货币出现之前,代币(token money)很早就被发展出来保护贸易免受强制性通货紧缩的危害(波兰尼,2007:165)。而19世纪的货币理论一直存在两种意见的争论:一方坚持国家作为代币价值的保护者,另一方则将货币完全视为经济范畴的、一种用于间接交换的商品。前者表明,在国家代币的意义上,货币的职能“不是交换手段,它实际上是支付手段,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什么效用,仅仅是一种筹码,体现着对可购买事物的数量化了的权利”,而按照这种货币观念组织的社会,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其中财物的分配依赖于对具有购买力的象征物的拥有(波兰尼,2007:167)。
正如对《礼物》的狭隘化解读,《大转型》在思想界受到的长久忽视源于人类学者自己的误读。在人类学界,波兰尼或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Halperin,1988),或被视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Neale and Mayhew,1983),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波兰尼要么是自由论的功能主义者(liberal functionalist),要么是不重视生产过程的流通论者(circulationist)(Seddon,1978),而其中最深刻的误解和最有力的批评则源于波兰尼的论敌:形式主义者将波兰尼视为“反市场”的浪漫化代表(anti-market mentality)(Cook,1966),认为波兰尼在《大转型》中表达的是对市场原则的批评,以及对现代工业经济中自私理性算计的乌托邦式的拒绝。在这一脉络下,《大转型》被解读成针对市场和商品化过程展开的批判,以及对两者所产生恶果的控诉(Lacher,1999;王绍光,2008;刘拥华,2011)。
围绕“交换”和“豪”的解读在20世纪80年代以反讽的方式达到高潮,学者们宣称自己在《礼物》的启发下建立了交换的两种理想类型:“礼物经济”和“商品经济”(Carrier,1995)。在很多情况下,这进一步被视为作为市场和货币经济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与反市场、无货币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礼物经济的对比(Strathern,1988)。讽刺在于,这两种类型的提出者们没有意识到,《礼物》所反对的恰恰是诸如将礼物和商品二分的幻象。莫斯自始至终想要表达的都是社会的整体性以及人性的混合特征,他在行文中实际隐含了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批评,他认为后者在批评经济理性人的同时,又重新引入了将礼物和私利二分并对立的资产阶级观念(莫斯,2005:167-168;Graber,2001;Hart,2014)。
按照栗本慎一郎(1997:108-125)对波兰尼的解读,原始经济或非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最初是先于任何功能而存在于社会中的一种对象物。这种对象物,必然是为人们所珍重和崇拜的拥有精神威力之物,有时甚至成为维持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只有这样的物,才是货币的原初形式。因此,货币的重要性在于其运动和性质是决定和表现一个社会基本性质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使得社会整合为一个统一体的是货币所显现的实质的社会深层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的货币的支付和财富贮藏功能更为突出,用于清付“社会性债务”的支付手段只是在它与起源于宗教威力的财富(treasure)合二为一的时候,它才开始获得包括交换手段在内的其他功能。而莫斯是最早注意到货币是一种带有宗教性威力的物的学者,这进一步成为经济伦理和社会约束的基础(栗本慎一郎,1997:140-157)。
因此不难理解,同莫斯一样,波兰尼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资源和财富分配方式组织的,现代社会的危机与其说源于市场和货币本身,毋宁说源于它们被认为建立于逐利动机之上,从而脱离于社会控制而具有独立的非人性的力量。由于自由主义市场带来的恶果而诉诸国家政治的制裁,不过是无视市场与货币本身的社会基底。由此,波兰尼选择了和莫斯相同的立场,即将市场和货币还给社会,而不是将其建立在逐利动机之上。
将以逐利动机为主的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独立领域的后果是:至此,人们相信,社会和谐是内在于经济的,只要个体尊重经济规律,那么个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最终就是同一的;同样,冲突也是内在于经济的,个体不尊重经济规律的后果就是冲突和斗争,不管是个体的竞争还是阶级的冲突。“人类被迫将自己托付给现世的永劫(secular perdition):他被注定了,要么停止自己种族的繁衍,要么有意识地通过战争和瘟疫、饥饿与邪恶来消灭自己”(波兰尼,2007:73-74)。自此,人类社会只能在这一经济决定论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或者主张借助非经济的力量强制排除市场,终止匮乏;或者主张借助自我调节的市场获得生存。前者意味着以集体的名义压制个人的自由,后者认为经济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这些仅仅是自由放任的经济决定论——这一19世纪唯物主义的遗产——的两种不同形式的信条”(波兰尼,2017:46-48)。试图在自我利益和经济理性的基础上建造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构想本身就是乌托邦,而其反面,即建立一个完全建基在利他和集体主义之上的社会同样是乌托邦。可以说,如果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将各种经济决策都归为个体利益存在问题的话,那么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同样因为把阶级定义为经济利益的集合体而犯了同样的错误(布洛克、萨默斯,2008)。
交换以各种形式和组织方式普遍存在于全人类社会当中,只有现代市场社会在想象中将自身的动力建立在个人的自我利益之上。现代市场及建基其上的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现代社会想象的产物。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把饥饿和自我利益看作自然秩序的基础,他们用二元对立的一组概念赋予“经济”以自然的光环。人被分解为一方面为饥饿与获取的、物质的、经济的、自然的,另一方面为荣誉与权力的、理想的、非经济的、文明的,由此导致的错误结论是:“经济的”人就是“自然的”和“真实的”人,所以经济体系就是一个“自然”和“真实”的社会(波兰尼,2017:41-44)。质言之,支撑这一幻象的实际是一对隐喻,一方面将市场等同于世界当中按照“自然”规律运作和调控的自成一体的生物有机体,另一方面认为构成这一有机体的是一个个“自然人”。莫斯和波兰尼反对的是这一幻象而非市场和货币本身。这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看法建立在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并非实际的动机,而是假定的动机,但这种对经济决定论的教条式信念已经成为理解哪怕是现代社会自身的障碍。要让这一稻草人出现在现代社会理论之中,需要经过漫长的思想史准备,而莫斯和波兰尼从“自我”和“社会”观念的演进中展示了这一过程。
本论文在重视理论连贯性的前提下,将采用地震波干涉法推定地下衰减构造这一目标的理论背景进行明确。首先详细证明衰减性介质中的空间自相关法和地震波干涉法的理论关系式,在此基础上,揭示了Prieto等(2009)提出的利用两者之间关系推定衰减构造的具体方法。
四、“自我”的诞生和“社会”的发现
《礼物》之中对于人物混融状态的解读已经多少涉及了原始和古式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不同的关于“人”的观念。在1938年题为《人文思想的一个范畴:人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下文简称《人的观念》)的赫胥黎讲座中,莫斯通过分析“自我”这个被现代西方社会认为天赋的观念如何在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和成长,彻底粉碎了经济自由主义者眼中作为人类自然属性的“自我利益”的观念之中关于“自我”的想象基础。
借用一个注释,莫斯表达了《礼物》与《人的观念》一文的紧密联系。莫斯指出,《礼物》中的夸富宴,除了交换男人、女人、遗产、契约、礼仪性赔偿外,还是“有关‘人’和人的权利与义务及宗教权利等现象,以及姓名的继承……而且还包括精神恍惚、被永存的精灵支配以及再生。一切,甚至战争和争斗都只在一些体现这些灵魂的继承的称号的拥有者之间发生”。夸富宴发生在代表氏族的首领之间,这些首领是灵魂的继承者和名字与称号的拥有者,作为其竞争对象和方式的宝物,不仅仅是面子的体现,其灵力的永久性“只有通过人、个人的名字的永久性来保证。人只在性质方面起作用,反过来他们对整个氏族、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部落负责”(莫斯,2008:60)。在这里,定义首领这个超脱于氏族其他成员的个体的是代表整个氏族的宝物及其灵力,首领通过夸富宴获得的荣誉和等级,又反过来确保了整个氏族共同体及其宝物灵力和生命的延续。首领、氏族、宝物之间难以割舍和相互定义,与《礼物》中表达的人物混融同出一辙。在夸富宴中,首领的“面子”与现代心理学的“自我”并不等同,亦与《人的观念》描述的起点——北美印第安普埃布洛和祖尼人个人观念与氏族相混淆的情况——构成差别。与《礼物》类似,夸富宴同样构成了人的观念的漫长发展中一个重要的中间过渡。
借助与《礼物》相同的思想范畴的考古学式研究,《人的观念》从“人”与氏族相混淆(北美印第安)、人与宝物和灵魂相互定义(西北美洲)开始,到“人”成为法律中的个体(拉丁)、人成为道德的个体(斯多葛主义)过渡,接着基督教的出现使道德意义上的人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即成为“个人的理性实体”。经过现代哲学家的发展,人的观念最终等同于自我认知和心理意识。莫斯指出,在人的观念的漫长发展历史中,人类在成为具有自我认知的人(person)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与氏族、宝物、灵魂、面具相互定义的人物角色(Persona)。而现代西方社会以人—物的割舍对人进行定义,进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社会契约的观念。莫斯所做的,正是指出现代社会契约的非普适观念前提。
如果说,“自我”“对我的崇拜”“我的尊重”只是晚近才出现,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关于“自我利益”作为人性基础这一想象也就无从谈起。这种观念的出现,首先要求人类将自己从万物中割裂出来,并将物作为财产进行占有,在此意义上,《礼物》和《人的观念》以不同的方式述说了人—物割裂的后果。可能在莫斯看来,《礼物》中的混融、《人的观念》中的“人物”,才是恰当的理解人性的方式,才是现代社会被遮蔽的真实。在这里,对古式社会的研究并不在于通过强调其不同而对现代社会进行批评。恰恰相反,当莫斯(2005:155)在《礼物》的结论中明言,“我们的道德以及我们的生活本身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也都始终处在强制与自发参半的赠礼所形成的气氛之中”时,当他推崇合作社、互助保险、家庭资助基金等仍然没有褪掉集体契约色彩的现代社会实践时,他想表明的无非是,在原始社会中看到的那方人性基石始终强韧,甚至包括最不人性化的市场社会。在任何社会中,礼物赠与从始至终都是一种“个人”行为,没有丧失它的个人性或自愿性的性质,礼物如果是真的,赠与的行为就必须是自愿的和个人的(古德利尔,2007:6-7)。因此,莫斯所批评的,并不是个体主义式的自我观念以及建基其上的自我利益观念,而是这些观念并不能代表真实的社会状况或是具有普适的人性意义。
馆藏与李铁夫相关的作品、账单、遗物较多,一部分为李铁夫生前使用过的家具、绘画工具、收支账单等,为单独建账。美术馆吴文洁等同志对这些藏品又进行了专门整理,相关图文已出版在《李铁夫研究》一书中。此外,有一部分是与李铁夫相关的书画、摄影藏品,当年纳入了李铁夫藏品的账本,故在此介绍其中四件:
然而,如果说“自我利益”表述的并非社会和人性的真实情况,那么作为一个幻象本身而言,它的真实性却毋庸置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从原始社会的“总体呈现”走到了“自我利益”的幻象?怎样从作为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实质的市场走到了作为社会组织原则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市场?研究原始和古式社会的莫斯,并没有对此做出回答。《人的观念》在对西方社会中关于人的自我意识分析之后戛然而止,没有继续探究“经济理性人”如何造就又如何参与了现代社会的运作。很大程度上,这个工作由波兰尼完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转型》构成了对《礼物》的补充,即政治经济学对人和社会的重新“发现”。对于波兰尼而言,英国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场现代世界观念大转型的起点和原点。具体而言,这场观念大转型是围绕着18世纪末期的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济贫法》展开的,其后果及相关讨论型塑了19世纪的文明。
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最活跃时期颁布的,原本旨在使劳动力免于无产阶级化,阻止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但最终却讽刺性地将英国劳动者推向了市场。该法令的失败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并不为当时的分析者所知,[注] 对于波兰尼而言,这一切都可以从该法令颁布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得到解释。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主要方式是工资补贴,即人们即便有工作仍然会被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总数低于法案确定他应有的家庭收入标准(波兰尼,2007:69)。首先,当时《反结社法》的存在使得劳动者无法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自由地结合在一起,否则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产生的后果可能不是如它实际所达到的那样压低了工资水平,而是提高水资水平(波兰尼,2007:71)。另外, 这一法令设计本身有诸多缺陷,例如它不区分暂时性和永久性的贫困,而将各种类别的赤贫者与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混为一群仰仗救济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农场主们由于向劳动者支付工资而得到补偿,表面上看有益于受雇者,最终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雇主,而济贫负担的压力却由乡村中产阶级来负担,以致许多救济费用缴纳者本身就是穷人。这不仅推动了雇主阶级的形成,更可怕的是,最终只有那些依靠救济的人才有被雇佣的机会,那些努力远离救济、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几乎不能保证有份工作。然而就整个国家而言,绝大多数人必然属于后者,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作为一个阶级的雇主们都榨取了超额利润(波兰尼,2007:82-84)。 但这一法令的后果却显而易见:乡间赤贫化、工资水平降低、劳动生产力降低、雇主阶级的诞生以及乡间大众的道德沦丧。
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工资由公共基金加以补贴并被无限地降低,当劳动者被迫出卖自己却又得不到应有的价值时,没有劳动者愿意努力工作而不依赖救济。短短数年之内,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的生产率水平。伴随着乡间赤贫化和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是劳动者的道德退化,波兰尼(2007:86)观察到,斯品汉姆兰法令不仅给逃避工作与假装匮乏以奖励,还在人们努力逃脱赤贫化命运的节骨眼儿上增加了赤贫化对人的吸引力,它使许多世代定居生活所造就的持重和自尊消耗殆尽,由此造成了普遍的道德退化。换言之,斯品汉姆兰法令以救助的名义对个体进行了道义剥夺(韩可思,2016a)。
市场社会的前奏和后果均由斯品汉姆兰法令开启,但其意义不仅在于促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如波兰尼所说,研究它的重要性不在于经济和政治后果,而在于“我们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正由此被型塑”,如果说工人从身体上被非人化了,那么所有者阶级则从道德上被降格了。“传统整合的基督教社会现在已让位于一个富裕者阶级拒绝对其穷困邻人的生存条件担负责任的社会”(波兰尼,2007:88)。这样的社会,是由政治经济学家们发现并阐述的。围绕着斯品汉姆兰法令及随后的《济贫法》的大量讨论,塑造了19世纪的精神之父们,如边沁、马尔萨斯、李嘉图、达尔文及斯宾塞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斯品汉姆兰法令的研究就是对 19 世纪文明降生过程的研究。
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一方面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财富,另一方面是乡间的赤贫化,当时的社会理论家在对这个矛盾的解释上争论不休。最终,是政治经济学带着令人惊讶的规整性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这就是它对人和社会之本质的“发现”。讽刺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建立在其门徒对被奉为鼻祖的亚当·斯密的误解之上。
近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迅猛,尤其是绿色经济,其作为一种新时代的经济模式,该模式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关注度令人叹为观止。它拥有环保、节能、低碳等诸多特点,在各行业中都深受人们的广大欢迎。绿色经济,泛指的是一种无污染的发展产业,比如使用风能、太阳能、水能而发展起来的各种产业,这些都是绿色经济理念下的产业形态。所以,若想要让绿色资源的价值得到最大化发挥,就必须将绿色理念放在资源应用过程中的第一位,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效果。
对于亚当·斯密而言,财富仅仅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方面和从属,是国家在历史的生存斗争中的附属品,并且不能与国家相分离。因此,只有在“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总体”的物质福利这一政治框架内才有可能来阐述财富问题。也就是说,对于他而言,经济领域还没有成为善恶标准的法则,社会中并没有一个可以提供道德法则和政治义务的经济领域,而自利动机只是促成我们去做那些本质上也有利于他人的事,人的尊严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最终,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波兰尼,2007:96-97)。当亚当·斯密断言“互通有无的倾向”是人之自然本性的一部分,市场会比其他任何手段都更有效地增加“国富”时,他的确彻底颠覆了惯有的智慧。但作为一位道德哲学家的亚当·斯密是人道主义的,他很清楚经济和道德之间的平衡,他并不情愿去为在市场交换中苦心孤诣追求自利的行为欢呼,但他认为宁可放纵大众身上的这一品性,也比将经济权力集中在所谓的高级精英人物手中为好。然而,很多人忘记了,他并没有声称,按照自身规则运作的市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利益是最有利的(Hann and Hart, 2011a)。可能首先忘记这一立场的就是十几年后的汤森。
工业设计是指与人们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工业与生活产品的制作和设计,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我国的工业设计开发区域逐步扩大,特别是在设计风格和设计理念的整合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占据一席之地,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人性化设计。设计师在体现人性化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产品的基本功能,从人的角度出发,设计满足许多不同人群需求的产品,全面推动企业的现代化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为何穷人宁愿徘徊在贫困线也不愿意努力工作,怎样鞭笞穷人工作的诸多解答之中,汤森断言,饥饿,作为和平的、安静的、永不懈怠的压力以及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不仅能驯服最凶猛的动物,也能够激励并驱策穷人去劳动(波兰尼,2007:98)。由此开始,经济被建立在人类的动物性之上。人类社会的驱动力和基础不再是宗教和神学,而是赤裸裸的动物性的稀缺和饥饿:一面是饥饿的折磨,一面是资源的匮乏,人类在恐惧和逐利的动机中与他人相处,二者最终获得的平衡并不需要国家的干预。汤森绕开了亚当·斯密认为无法避开的、关于政府统治的基础的问题,并由此将一个关于人类事务法则的全新概念引入进来,那就是自然法则。由此,政治经济学宣布自己揭示了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的贫困问题的真正意涵:支配着经济社会的法则并非属人的法则,贫困就是社会的自然选择(波兰尼,2007:108)。而人类实际上就是野兽,并且由于恰恰如此,需要最小程度的管制。
这就是波兰尼眼中政治经济学全新的起点,即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而与汤森的那些基础相结合,从动物性来理解人类共同体,来理解社会的基础(波兰尼,2007:100)。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市场模式的演进”一章中所描述的:在现代欧洲,当政治经济开始成为一门学科时,商业活动依然按照实际存在的物质需求和使用情况组织,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用真实存在的框架线条来阐述财富的概念。在诸多动机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波兰尼,2007:47)。围绕着对工业革命、斯品汉姆兰和其他法令带来的贫困问题的讨论,政治经济学重新解读了启蒙理性以来的“个人与契约”假定,建立了以逐利动机和经济理性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这一现代化理念(戴尔,2017:270-271)。
当饥饿的动物性和逐利动机成为对人性的想象,稀缺性和自然法则成为社会的基础时,经济也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从整体社会中割裂开来而获得了形式的定义。这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的最早定义,即从家户或“实质性”(或“社会”)的视角来看待经济构成了巨大差别(波兰尼,2000)。波兰尼(2007:47)指出,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近代西方社会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借助这种区分,经济终于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政治国家之外出现了,社会的“总体呈现”被“自我利益”取代了。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道出了莫斯的未尽之言,即关于“经济理性人”的想象是如何产生的。
不仅如此,这样的想象还在实际运作中参与造就了现代社会。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对人和社会基质的全新发现,使它获得了与17世纪的宗教等同的地位,这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名而拒斥人类团结的斯多葛式的决定论由此获得了世俗宗教的崇高地位”(波兰尼,2007:88)。政治经济学不仅为现代社会的构造提供了一套创世论式的解释,它还直接参与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和构建。马尔萨斯将工资铁律建立在人口生育率和土地肥率之上,边沁依据效用原则设计的圆形监狱、专利制度、人口普查制度等,李嘉图在稀缺性原则上建立的报酬递减定律(波兰尼,2007:104-107),不过都是政治经济学这一世俗宗教的布道场。通过它们,逐利和功效的原则成为社会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形式。
五、整体的社会和实质的经济
斯品汉姆兰法令对于《大转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型塑了19世纪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在于对它的研究同样驳斥了那种关于市场自然形成的论调:从17世纪重商主义国家对国内市场的推动,到19世纪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市场的形成之间的跨越,远非自然和自发,这一跨越由国家主导完成。波兰尼的论述围绕着斯品汉姆兰法令和《济贫法修正案》展开,前者在1834年的废除和后者的取而代之是中产阶级在1832年实现权力要求的结果(波兰尼,2007:64)。这表明,19世纪初期发生的变革并不在于市场从社会中的自发脱嵌,或是自发地脱离国家控制,而是在于通过政治过程将市场以另一种更不人道的政治、文化、观念的组织形式再次嵌入社会(Block and Somers,2014: 9-10)。只有借助政府的特殊干预,“自我调节的市场”才能出现和实现自身的再生产,而“市场社会”不过是一个被夸张了的理想类型,因为并不存在实际上脱嵌的经济(韩可思,2016b)。所谓“自由市场”,亦需要文化、观念、社会和政治法律条件的保障,社会的整体性超越了自由主义者的想象。
因此,应该从社会实质上的整体性与形式或想象中存在独立经济领域的这种断裂中,来理解关于双向运动与虚拟商品的论述。它们不仅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更是社会整体性的表征。 在“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两章中,波兰尼不厌其烦地阐述了社会整体性的坚韧:当自发调节的市场理想将经济脱离于社会并将后者置于危机之中,作为整体的社会将发起反向运动以避免自己的解体(Baum,1996:7)。保护主义并非源于个体或阶级利益,而是源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同样,波兰尼提出的“虚拟商品”批评的对象并非真实存在的市场体系对个体的影响,而是关于市场原则的观念层面的建构(Servet,2011)。如果人、土地、货币注定是社会的基质,那么将它们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对于波兰尼而言,“自我调节的市场”是涂尔干学派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即社会根据某种特别的逻辑呈现自身的方式,这种表征和想象引导实践以某一种方式进行,其结果就是“市场”。“市场”作为各种交换的集合体,其作为独立领域的真实性仅仅取决于其参与者的笃信程度,而宣称自己在研究真实事务的经济学家们不过成为了搭建这一幻象的不自知的推手。
本文模拟的流场处于湍流状态,因此采用标准的k-ε模型作为其控制方程[10-13]。标准k-ε模型中的湍流黏性系数可表示为:
双向运动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将阶级斗争视为利益的集合体之间的冲突的理解(Block and Somers,2014: 9-10)。虽然波兰尼在《大转型》中不断重复使用标准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范畴(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本人也极度赞赏工人组织合作社和工会进行自我保护的努力,但他并不把阶级视为利益的集合体,从而视社会变迁由利益驱动的看法(波兰尼,2007:129-139;Baum,1996:11)。对他而言,人类所有行为都是由社会塑造和定义的,片面强调经济领域的决定性作用会导致“经济主义的谬误”(布洛克、萨默斯,2008)。作为欧洲大陆智识传统中的学者,波兰尼严格区分了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源于黑格尔哲学传统中的历史辨证法(Baum,1996:6)以及卢卡奇对总体性的强调(布洛克、萨默斯,2008),他试图论证的是社会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波兰尼关于“嵌入”和莫斯的“总体呈现”的论述,这与波兰尼笔下的经济的实质含义有关。
“实质的经济”指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换(interchange),这些交换是人类社会的立身之本,而货币、市场、礼物、商品……是交换得以进行的方式或制度形式,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力量源于各种关系的联结之力、社会的深层结构之力,而非源于其自身。所谓“实质”,归根结底是一种存在于各种关系中的相对稳定的要素的复合体(栗本慎一郎,1997:43),货币和市场只有作为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各种关系的相对性“存在”,才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可以被定义的(栗本慎一郎,1997:185),而对货币、财物、市场的研究是去逼近社会的非经验整体性。换言之,货币是存在于社会结构、心智系统中的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是核心,而只是说存在于社会结构、心智系统中的核心通过财富的观念和货币的存在表现出来(栗本慎一郎,1997:71)。在此意义上的“嵌入”,简单而言指的是货币作为“形式”嵌入在社会的“实质”之中,或曰脱离社会实质无法更好地理解货币。或者借用波兰尼和莫斯的表述,经济嵌入在非经济基础,契约嵌入在非契约基础之中。经济、货币、市场、契约的存在并非其目的本身,因此,任何功能主义式的认为货币作为具有独立属性的功能嵌入在社会其他功能领域中的看法,无疑都是波兰尼和莫斯之前的经济人类学的误解(栗本慎一郎,1997:43)。
在这样的关照下,我们也可以更新对莫斯的“总体呈现”的理解。在《礼物》中,莫斯并不试图去描述市场运作的逻辑如何与礼物经济构成了对立,或者说礼物交换完成了其他社会领域的功能。莫斯希望表达的恰恰是,为何这种对立并没有实现,为何“商品经济”与“礼物经济”、市场与社会不能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莫斯替波兰尼说出了“双向运动”的真义,即社会的实质是在夸富宴中看到的那种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艺术的总体呈现。由此看来,波兰尼和莫斯的真正功绩在于,他们通过把文化的整体性变成科学,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比较经济的领域(栗本慎一郎,1997:48)。
如果说斯密通过探讨“公序良俗”的心理基础而回答了“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社会心理学大师米德(George Mead)则更为直接地论证了这一心理基础的人性普同性。米德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同情”和市场交换,他把市场交换更明确地表达为自我的构成和实现。米德力图表明,心灵与自我通过交流产生,而不是交流通过心灵与自我产生(米德,2018:56)。心灵不同于简单的反应,也不同于情感,它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反思的智能,其产生是在社会相互作用这个经验母体中社会交流过程在个体身上的内在化;自我亦是作为个体与整个过程的关系,与该过程中其他个体的关系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米德,2018:151-153)。而使生物个体转变为一个能够意识到本身是一个对象物的自我,需要语言、姿态等表意的符号,也需要宗教、经济过程等媒介制度。在后一种过程中,自我为了其所必需的物品而向他人提供盈余产品,在这里,需求的态度包含一种参与,各人置身于另一个人的态度中,知道交换对双方分别具有的价值,由此,交换某人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把他带到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关系中。换言之,在商品的交换中,某人的利益也是大家的利益,并为自我反身性所理解,个体之间因为采取彼此的态度而完全认同,而在个体自身则是作为对象化的“客我”和作为反应的“主我”的融合(米德,2018:291-309)。
六、余论:个体自由与市场
置身于19世纪的欧洲社会“大转型”,莫斯和波兰尼游走于古式与现代社会之间,穿梭于战争的动荡之中,上下求索于现代社会的市场形式中,探索自由与道德的可能性。他们都相信,社会内在于个人,社会团结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市场的形成和运作并不需要化约为功利主义动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动物性抽象为人类天性,这与其说是基于经验事实,不如说是一种自然神学(Block and Somers,2014:38-39),它因为将“作为完整而复杂的存在者的”具体的人割裂于其生活情境之外而错误地理解了个人与市场的勾连。
是否存在一个同样基于个人自由但不同于功利主义基础的市场观?如果将视野稍微拓展,不难发现这种可能性并存于从亚当·斯密一直到莫斯和波兰尼所代表的思想传统之中,却遗憾地被主流市场观念忽视。
亚当·斯密首先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不应忘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探究自利的人如何能够在经济领域的发展中实现道德领域的和平共存。《道德情操论》的核心是“同情”,但亚当·斯密并不是在利他主义情感意义上探讨这一概念,而是指来自于当事人对他人境遇的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换言之,斯密笔下的“同情”是人类的本性,它是指人类之间的情感、动机、行为的内心反应能力,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彼此的一种相互换位思考的心理活动和机制,它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存在“利己”与“利他”的区分(罗卫东,2005)。因此,斯密笔下的利己主义与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不同,它是与同情心伴随的一种“自爱”。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换建立于同情和自爱的人性基础上,它是人性中某种倾向的必然结果,这是一种互通有无,进行物物交换、彼此交易的倾向,并不涉及功利的目的(斯密,2008:17)。当斯密在谈论“互通有无”的人性倾向时,他实际上是在讨论具有“同情心”的个体如何构成市场的基础。通过对“同情心”的阐发,斯密在个人的私利追求和社会利益实现之间建立了逻辑关联。
通过对1986—2014年数据统计可知,本文涉及的样本户数累计达572400个,平均每年家庭户数在2万户左右。农村家庭收入均值逐步提升,标准差也随之上升,说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离散程度随着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为了消除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采用1986—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各个省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进行消胀,如图1所示,消除通货膨胀以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速相对缓慢,同时标准差也相对下降,即其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离散程度降低了。但是这些统计性描述分析仅能反映局部的农户收入不平等,要全面刻画问题,还需要更细致化的测量方法和指标。
能够置身于其他个体的经验中,采取他们的态度,从而发现和体会他人需求的“同情”的心灵和自我是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进而构成市场交换的基础。经济过程使得群体通过交流和参与其中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已成为我们整个现代社会最普遍的社会化因素,像宗教一样带有一种在人的自我中实现他人的深刻意义(米德,2018:325-333)。市场交换实现了个体,而非先验的个体实现了市场交换,换言之,个体、自我、心灵源于关系,这样的关系才是市场的前提。在此意义上,正如莫斯和波兰尼力图表明的,货币与宗教用品之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并无二致。在《礼物》和《人的概念》发表之前,莫斯已经完成了献祭、祈祷和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季节变化的研究(莫斯,2007,2008,2013),贯穿这五部论著的是莫斯的“中间性(intermediateness)”概念,具体指流动于天人之间、人人之间、神人之间的对象“物”或媒介。这些被称为“中间物”的东西,包括爱斯基摩人的狩猎、采集之物及其季节、房屋,人间的礼物,献给神灵的祭品和服务于人神交流的祭司及其祷辞。社会和个人正是在中间物的交换中得以可能。通过赋予中间物以神圣的创造性,莫斯实际上将“社会”的概念从个体主义式的“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扩展了“社会”和“人”的概念边界(王铭铭,2015a:101-109)。这样的“人”,其含义是由与“它”(他人、物、神)构成的世界赋予的,其存在只有当自我与“它”形成关系时方为可能(王铭铭,2015b)。
在莫斯这里,社会和个人涉及人神之间、人物之间、人人之间的紧密勾连和交融,而他对现代市场的批评,在于它试图在观念层面消解这些中间物。因此,莫斯笔下的市场,不仅是如上文所述所有权观念混杂的市场,同样也在于对各个层次混融关系的坚持,由此,市场的道德无所谓利己或利他,而是自由与义务的二位一体。莫斯坚信,任何形式的市场和货币都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理性的算计之上,没有任何社会能够摆脱市场和货币,并且任何社会中都是自由与义务、个人与集体、人与物的复杂纠缠,恰恰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个体必须在以市场为形式的社会交换中实现。
无论是亚当·斯密、米德还是莫斯,都展现了不同于功利主义个体的自我观念。如上文所述,波兰尼敏锐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家对亚当·斯密的误读,他发现并在某种程度上接续了亚当·斯密的道德经济传统。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对这种道德经济传统的背离,以及波兰尼自己希望开辟的继承方式,在于他笔下从基督时代到后基督时代的转向之中个体的诞生。由此,波兰尼为个体的自由和道德的维护提供了途径。对于波兰尼而言,政治经济学并非波兰尼笔下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唯一的源头,个体的诞生早就潜伏在基督教的转向之中。在《大转型》的结尾,波兰尼指出,现代社会中自由的问题在制度和道德宗教的层面同时浮现,而未来社会的基础必须要到后一个层面去寻找,这意味着对基督教教义的扬弃。波兰尼对罗伯特·欧文的推崇,在于后者发现了《福音书》所忽略的社会现实,他将此称为基督教对人类的“个体化”(波兰尼,2007:220)。
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便是世界宗教的发明,正是宗教最先通过单一的道德秩序将社会概念化。在众多宗教中,基督教向人类揭示,其精神本质是个人自由、道德自律和自我意识(戴尔,2017:76)。所有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他们无法在不与他人共存的情况下采取道德行动,而人类注定会建立一个共同体,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他人相互影响。因此,基督教提供了如何将普遍主义以及个体道德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戴尔,2017:50)。但是,耶稣的时代并没有人提出复杂社会里的自由问题,1500年后,基督教那种满足礼俗社会需求的方法无法应对社会的现实情况:随着社会经济越来越复杂,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在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人类无法避免支配其他人。面对这一复杂社会,基督教—犹太教那种关于追求个人绝对免于社会约束的自由的假定在引导意识变革上失败了(戴尔,2017:156-158),走向了波兰尼笔下的错误的个人主义的方向。
在这样的失败中,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趁虚而入,使得自由与义务脱离、个人与社会脱离。市场资本主义不仅繁衍了孤立个人的观念,而且阻碍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意识,从而不利于塑造履行个人责任的道德意识。由此,波兰尼宣布,“后基督教”时代已经来临,因为虽然基督教为世界主义全球社群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不能独自完成这一任务。对基督教个人主义的重新解释必须适应近代工业的现实状况,这一时代需要的是对整个社会关系的集体道德反思,而不是以市场为模型对社会进行再造。“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必须转向社群社会”(戴尔,2017:51)。
波兰尼在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谈论“社群社会”,这建立在他对个体的历史地位的理解之上。1930年左右,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当时身在英国的波兰尼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该书展现了马克思思想人本主义(humanistic)的一面。同一时期,波兰尼与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私交甚厚,其中深受涂尔干思想影响的麦克莫雷(John Macmurray)在坚持社会内在于个体的同时,提出“人格主义”(personalism)的道德社会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和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传统。波兰尼本人对于基督教在复杂社会的效力的论述以及后来构成《大转型》中一些观点的《法西斯主义的本质》一文都深受这一理论影响(Baum,1996:21-33)。在波兰尼看来,经济决定论之上建立的社会并不会为人们带来理想的自由,因为这种“脱嵌”的社会缺少道德基础(戴尔,2017:113-114)。对波兰尼而言,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因为良性社会正是人类得以履行责任的社会:要明白自己的行为将对他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才能使个人和社会同时受益。
(1)加强对品管圈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教育与知识宣传,向患者讲解内瘘穿刺的原理方法以及在穿刺时对患者的要求,并鼓励家属共同参与,提高护理人员及患者对内瘘穿刺点渗血的认识,以达到减少并尽量避免动静脉内瘘穿刺点渗血的效果。
当亚当·斯密和米德用个体的“同情心”来构建市场的基础时,莫斯和波兰尼则在个体的构成中纳入与“它”的交换关系,由此,他们都将“关系”置于个体自由的核心,从而为我们开启了对个体和自由的别样理解。可以想见,以这样的个体自由为基础创造的市场,将完全不同于基于功利主义个体的市场。通过扩展个人和社会的概念边界,莫斯和波兰尼实际上为现代社会开出了处方。
在波兰尼看来,良性的社会应当建立在自由、中间团体和工业文明三个基础之上。其中,自由的关键在于人性的完整和社会的道德,这具体表现为:首先,一个“保障自由的具体制度”,它既追求合作、和谐,也具有对抗性和竞争性,自由意味着一个普遍的、允许有多元思想表达的、受习俗和法律保护的多样性(波兰尼,2017:49-50);第二,波兰尼认为中间团体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关键,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由各机构团结一致实现各自功能的自然有机体过程”。基于日常生活的需求(或功能),个体形成了协会,如工会、合作社、教会、社区组织、市政委员会以及国家,个人在这些协会的中介下参与日常生活。对波兰尼而言,这样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或工团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机制,让整个社会来决定是否消费和生产(戴尔,2017:106-108);最后,正是因为在工业社会的各种社会机构和协会之中,诸多个体在集体实践中可能增进对个体之间真正关系的具体理解,生成“社会知识”,即作为有意识的社会成员对其他个体截然不同的需求的意识,设身处地地考虑其他人的情况,对他人的需求与无效劳动感同身受(戴尔,2017:115-116)。所以,工业文明的内在趋势有助于这种“将共同体视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式发展(布洛克、萨默斯,2008)。
在这里,波兰尼所表达的自由与莫斯类似,是承载义务的自由,是对他人充分承认和依赖的自由,而自由和道德的实现途径,是通过工业社会的行业协会或职业群体实现的工团社会主义。莫斯给出的处方与此惊人的相似:在资本主义语境之下,有必要建立一定数量的以职业群体为代表的亚群体,作为个人无政府主义与国家集权之间的一个中间力量(福尼耶,2013:321)。而莫斯正是在他推崇的互助保险、合作社中发现了这种工团社会主义,通过改革消费、生产和所有权制度的方式进行“来自下面的经济运动”(福尼耶,2013:120)。
莫斯和波兰尼都是社会主义者,[注] 如前所述,19-20世纪初期欧洲存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莫斯和波兰尼眼中的社会主义并非科学社会主义,他们两人之间也存在细微差别。 对他们而言,这代表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经由协会或合作社达成的社会团结。这种社会团结并非建立在占有性财产或阶级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作为道德主体的、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的个体之上。所不同的是,对于波兰尼而言,这样的个体迷失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基础的错误发现所导致的错误的个人主义转向之中,需要个体成员在互动中意识到彼此而重新觉醒;对于莫斯而言,这样的个体存在于宗教、巫术、献祭的信仰和行为之中以及现代社会的礼物赠送实践之中而从未走远。《礼物》和《大转型》都被它们的作者视为一场政治参与的行为,它们指出了,正是市场经济产生的幻象造成了道德个体的迷失或遮蔽,而社会学的原则与宗旨,就是要通过洞察个体和群体及其具体行为和生活实践来破除这种抽象的迷障。或者说,对具体的人的研究,是重现社会和人的整体性的途径(迪蒙,2003)。在《礼物》的结尾,莫斯说道:
我们已经触及到了根本。我们所讲的甚至已经不再是什么法律,而是人,是人群;因为自古以来经纶天下的乃是人和人群,是社会,是深埋在我们的精神、血肉和骨髓中的人的情感。(莫斯,2005:163)
……具体的研究也就是整体的研究,它对社会学家来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更加吸引人,更加富有解释性。我们所观察的是作为完整而复杂的存在者的人,是他们的特定数量的完整而复杂的反应。我们所描述的是有肌体、有心灵的人,是这样的人群的行为和与之相对应的心态:是群众或有组织的社会及其次群体的情感、 观念和意志……(莫斯,2005:179)
犹太—基督教教义、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观念、工业革命和现代市场的兴起共同搭建了独立的市场和孤立的个人这一幻象,而要在现代复杂社会中寻找自由,要在道德个体之上建立整体的社会,对于莫斯和波兰尼而言,首先要进行一场意识的重构,在解释现代社会中某种经济行为和心智得以扩散的基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识到问题的根源与其说是真实的社会情况,不如说是社会成员对现阶段社会的理解和想象,或者说现代人对自身的误解。在这里,权力从根源上而言,是一种想象的政治。由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方式,并不是去抛弃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例如市场和货币,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它对社会关系的观念表述,并从“自古以来经纶天下的人和人群”的具体感悟中去探究社会的实质。
在这样的关照下,我们可以回到开篇提出的经济人类学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正如波兰尼所发现,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经济”最重要的含义是家计和日常生活的营造。在资本主义扩张和工业革命中,“经济”愈发被等同于超脱于家庭和人们控制的“市场经济”。这一个由货币作为中介主导买卖、由理性经济人构成的领域,自18世纪开始逐渐被认为可以主导和组织社会(Hann and Hart,2011b: 24-25),与之伴随而起的则是一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其结果是,现代社会关于“经济”的想象脱离了真实的人的具体实践,而成为抽象和规律,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的独立领域。莫斯和波兰尼开创的经济人类学指向的是在人类整体历史发展和比较中,从具体的人的生活实践中探索经济的多元含义,或者说是探索现代经济的非“经济”基础。这一含义不仅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家计,也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合作社及货币流动中。
并且,这样的经济人类学还意味着对社会和个人的重新理解。礼物交换并不证实或证伪个人的理性的自我利益,它代表了与这种功利主义哲学完全不同的社会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并不建立在任何意义上的实体选择之上,而恰恰因为实体尚未形成。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分别将个人和社会视为先验的实体,而莫斯对涂尔干社会学的一大发展,是将社会和个人视为动态的生成过程,它们都需要在礼物交换和夸富宴的壮举中,在市场和货币的流动中形成(Hart,Laville and Cattani,2010:184)。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也是人性历史的发展过程。当波兰尼在讨论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发现和个体主义的错误转向时,他也是在讨论关于社会和人的观念的不断生成和演变。在这样的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含义的广阔和深邃。遗憾的是,这种力量多多少少随着20世纪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时空局限性,以及过快地将非西方社会视为经济理性人的对反而失落了。
当我们将这两部作品置于整体社会之中,置于学者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当中,会发现《礼物》和《大转型》可以被视为对同一个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回答:两部著作都在讨论同一个从未实现的自由主义神话。《礼物》和《大转型》的结论都是道德性的:《礼物》的最后章节呼吁现代社会破除市场经济的迷惑,《大转型》的最后一章充满激情的修辞和关于“复杂社会中的自由”这一问题的锐利思考亦反映了整体社会中对个人道德的追求。波兰尼和莫斯的著作,使我们思考社会变革的经验和可能,使我们去探索一个现在看起来很边缘甚至失落的世界,然而仅仅两三代人之前,这一思想还在整个政治和文化景观中留下深刻而独特的印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波兰尼,卡尔. 2007.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刚、刘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波兰尼,卡尔. 2017. 新西方论[M]. 潘一禾、刘岩,译. 深圳:海天出版社.
波兰尼,卡尔. 2000. 经济:制度化过程[G]//反市场的资本主义. 许宝强、渠敬东,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布洛克,弗雷德、玛格丽特·萨默斯. 2008. 超越经济主义的谬误:卡尔·波兰尼的整体性社会科学[G]//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 西达·斯考切波,主编. 封积文、董国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戴尔,加雷斯. 2017. 卡尔·波兰尼传[M]. 张慧玉、杨梅、印家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迪蒙, 路易. 2003. 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M]. 谷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尼耶, 马塞尔. 2013. 莫斯传[M]. 赵玉燕,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德利尔,莫里斯. 2007. 礼物之谜[M]. 王毅,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韩可思. 2016a. 道义剥夺[G]// 人类学的缺位:关于市场、社会、历史与人类学定位的思考.韩可思、凯斯·哈特、斯蒂芬·迈尔,编. 吴秀杰,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韩可思. 2016b. 市场与社会: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转型——我们能从卡尔·波兰尼学到什么[G]// 人类学的缺位:关于市场、社会、历史与人类学定位的思考. 韩可思、凯斯·哈特、斯蒂芬·迈尔,编. 吴秀杰,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栗本慎一郎. 1997. 经济人类学[M]. 王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克劳德. 2003. 马塞尔·毛斯的著作导言[G]// 社会学与人类学. 马塞尔·毛斯,著. 佘碧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拥华. 2011. 市场社会还是市场性社会?——基于对波兰尼与诺斯争辩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4): 62-89.
罗卫东.2005. 老调重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说起[J]. 博览群书(3): 34-42.
马克思,卡尔. 2004. 资本论[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米德,乔治. 2018. 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莫斯, 马塞尔. 2005.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 汲喆,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莫斯, 马塞尔. 2007. 巫术的一般理论· 献祭的性质与功能[M]. 杨渝东、梁永佳、赵丙祥,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莫斯, 马塞尔. 2008. 人类学与社会学五讲[M]. 林宗锦,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莫斯, 马塞尔、爱弥尔·涂尔干、亨利·于贝尔. 2010.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 纳丹·施朗格,主编. 蒙养山人,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莫斯, 马塞尔. 2013. 论祈祷[M]. 蒙养山人,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萨林斯,马歇尔. 2009. 石器时代经济学[M]. 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斯密,亚当. 2008. 道德情操论[M]. 谢宗林,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涂尔干,埃米尔. 2017. 社会分工论[M]. 渠敬东,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 2011. 人类学讲义稿[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2015a. 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 2015b. 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J]. 学术月刊(3): 129-140.
王铭铭. 2018. 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与文明研究的构想[J]. 社会38(4): 1-53.
王绍光. 2008. 大转型: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1): 129-148.
Appadurai, Arjun. 1988.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um, Gregory.1996. Karl Polanyi on Ethics and Economics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Block, Fred and Margaret R. Somers. 2014. The Power of Market Fundamentalism :Karl Polanyi ’s Critique .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rrier, James. 1995. Gifts and Commodities :Exchange and 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1700 . London : Routledge.
Cook, Scott. 1966.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 A Critique of the Substan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3): 323-345.
Dalton, George. 1961. “Economic Theory and Primitive Socie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2): 1-25.
Gane, Mike. 1992. The Radical Sociology of Durkheim and Mauss . London: Routledge.
Graber, David. 2001. Towards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raber, David. 2014. “On the Moral Grounds of Economic Relations: A Maussian Approach.”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4(1): 65-77.
Halperin, Rhoda. 1988. The Institutional Paradigm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Hann, Chris. 1992. “Radical Functional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7(2): 141-166.
Hann, Chris and Keith Hart. 2011a. Market and Socie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day .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nn, Chris and Keith Hart. 2011b. Economic Anthropology :History ,Ethnography ,Critique . Cambridge, U.K.: The Polity Press.
Hart, Keith. 1986.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 Man 21(4): 637-656.
Hart, Keith. 2007. “Marcel Mauss: In Pursuit of the Whole. A Review Essa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9(2): 473-485.
Hart, Keith. 2014. “Marcel Mauss’s Ecomomic Vision, 1920-1925: Anthropology, Politics, Journ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4(1): 34-44.
Hart, Keith and Horacio Ortiz. 2014.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 and Finance: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1): 465-482.
Hart, Keith, Jean-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David Cattani. 2010. The Human Economy . London: The Polity Press.
Lacher, Hannes. 1999.“The Politics of the Market: Re-reading Karl Polanyi.” Global Society 13(3):313-326.
Mauss, Marcel.1992. “A Sociological Assessment of Bolshevism (1924-1925).” In Sociology of Durkheim and Mauss , edited by Mike Gane. London: Routledge.
Neale, Walter and Anne Mayhew. 1983. “Polanyi,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Topics and Theories , edited by Sutti Reissig Ortiz.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olanyi, Karl. 1957.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 Glencoe: The Free Press.
Polanyi, Karl. 1977. The Livelihood of Man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Seddon, David. 1978.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arxist Approaches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 London: Frank Cass.
Servet, Jean-Michel. 2011. “Toward an Alternative Economy: Reconsidering the Market, Money, and Value.” In Market and Socie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day , edited by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gaud, Lygia. 2002.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Gift .”Social Anthropology 10(3): 335-358.
Strathern, Marilyn. 1988. The Gender of the Gift :Problems with Women and Problems with Society in Melanesia . San Francisco,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teiner, Philippe. 2011. “The Critique of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Karl Polanyi and the Durkheimians.” In Market and Socie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day , edited by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er, Annette. 1992. Inalienable Po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 -while -Giving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Yonay, Yuval. 1998. 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conomy in a Substantive Sense :Anti -Utilitarianism Economic Anthropology as Seen from The Gift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YU Xin
Abstract : Economic anthropology as seen from Mauss’s The Gift and Polanyi’s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rovides inspiration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discu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both works by English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20th century deviate from the real intention of the authors and largely ignore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writings and the authors. Through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is interconnectio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1) Both Mauss and Polanyi oppose to the formalist economic model based on utilitarianism, and the contrasts of gifts and commodities, as well as the utopian dreams of liberalism and communism. 2) A careful reading of Mauss’s and Polanyi’s writings also indicates that both authors tend to see private property, market and money as formal means of social substance, i.e means of express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ubstantial inter-exchange existed within society and frame of mind. Moreover, they regarded empirical studies of money, wealth and market as ways to approach the theoretical holism of society. By contrast,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reverses the cause-effect sequence by making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sphere under the formalist model and a natural individual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ety. 3) Mauss and Polanyi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on their studie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4) Polanyi’s double movement, fiction commodity and embedment, along with Mauss’s total presentation have to be understood in relation to their discussion on holism and substance of society.
Mauss and Polanyi have broad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well a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market. In their view, studies of people in their real and everyday life should be the starting point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In this respect, The Gift and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give us an alternative and pluralistic way of explaining economy in a holistic society, together they lay 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based on substantivism.
Keywords :The Gift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substantive economy, market, money
*作者: 余 昕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Author: YU Xi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University)E-mail:yuxin2017@cqu.edu.cn
本文感谢如下两个基金项目的支持:重庆市社科规划培育项目“渝东南道地药材商品化种植的生态社会过程研究”(项目编号2017PY15);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共和国时期乡村医药知识保护与传承制度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18CDJSK47PT02)。[This paper was sponsored by the two following projects: “Study on Ecological and Social Process in Commercializing Medicinal Plants in Southeastern Chongqing”(No.2017PY15) funded by Cultivation Program of Chongqing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 Circles, and “Study o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Practices of Rural Medicine Knowledge in PRC”(No.2018CDJSK47PT02) fund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of China.]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细致专业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田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