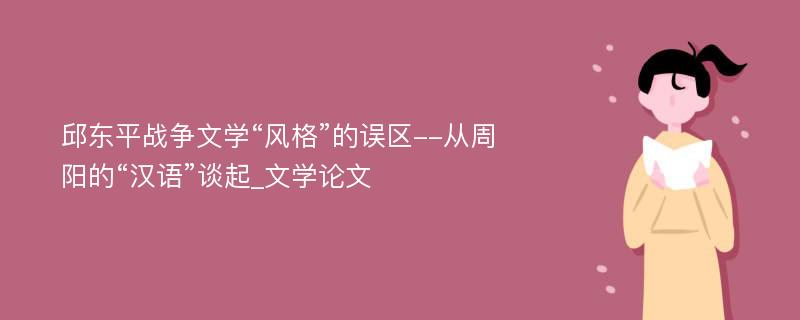
丘东平战争文学“格调”的歧途——从周扬的“话中话”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平论文,歧途论文,格调论文,战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0年3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京津文艺干部大会上,周扬批判胡风以及“他们小集团”。鉴于胡风和丘东平的特殊关系,又碍于丘东平的英勇早逝的事实,周扬只是附带评说被纳入了“小集团”的丘东平,认为他“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当做作家来看,那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①。周扬话中有话,充满着张力,更富有杀伤力。此后,以周扬为基调的关于丘东平的文学评价,一直是分裂的。三十四年后,一部以丘东平自杀为题材的小说《东平之死》②发表,再次呼应着周扬的“话中话”,将丘东平人与文的价值分裂评价凸显为热门议题。当然,人与文的价值分裂评价也算是一个古老的问题。③ 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关于丘东平的文学写作、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恰恰又多是基于上述文学史实和人事纠葛展开的,少有人能全面、综合地论及丘东平写作艺术特质、潜质和历史坐标的独异性。这一点,可以从丘东平诞辰100周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情况得见。这本名为《丘东平研究资料》的论文集,基本上呈现了既有的丘东平文学研究水准与格局。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丘东平的作家论。作家论,自然是基于文学史或文学思想史的背景,有从立场和群体归属讨论,如革命文艺战士说、革命作家或左翼作家说;也有从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发凡,如胡风的文艺理论与丘东平创作的关系、战场英雄主义问题等的辩驳。另一类,就是关于丘东平的创作论。创作论,则有从抗战文学立论,也有从现代战争文学立论,也有从叙事文学立论。此外,还有大量有关丘东平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 由上可见,丘东平的文学写作,迄今为止并没有因为他在战争题材上的非同寻常的密集度而获得标举,而是被迅速纳入了既有的作家论和作品论的研究格局中,因此一直无法更好地认知其艺术特质和文学史贡献。事实上,作为作家的丘东平,其特质正是其特异的、高密度的战争书写,以及其充盈着战火气息的战争经验传达。不仅如此,丘东平朴素战争情感的全面抒写、“奇诡狞美”④的战争叙事风格、模糊的战事处理模式,不仅凸显出了现代战争中的人欲之力、人身之蛮、人居之野、人性之美,也真实记录下了现代战争与现代东亚历史、现代人之间活脱脱的血水交缠与白刃战般的搏击,更从战争与人的关联——工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结合部——呈现出另外一个现代性的审视角度,在人性与文明的高度有着独到省思。 现代战争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但现代战争同样是野蛮的,其野蛮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其他许多战争文学作家一样,丘东平笔下的战争书写,有民族国家的立场,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但这不是他探究的着力点,他的“目标显然高于一般的爱国宣传”⑤。丘东平是主动沉入战争当中的写作者,正如林岗所言:“革命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日常生活……革命不是一种有待深入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⑥倘若把“革命”换成“战争”,基本上可以概括丘东平之于战争和战争文学的特殊关系。 除了“主动地选择战争,并以士兵的身份进入战争”⑦的独特姿态外,丘东平战争叙述的维度就与众不同——他特别敏锐而勇敢地看到了战争本身的野蛮和反人类、反文明的荒诞,也看到了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阳光与阴影”⑧。而关于战争的野蛮和反文明、反人类的一面,此前并非没有人发现,但在开掘现代中国战争的“蛮”性方面,在同代的中国作家中,丘东平实在是少见,甚至是仅见的一个。 现代中国战争的“蛮”性,体现为其爆发频仍,密度大、数量多、场域广。这自然是因为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权更迭迅易。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变迁则又异常沉滞与缓慢,循环往复。从地方军阀的成王败寇,到抗日战争的义旗辗转,从中国军队内部的自我倾轧,到异族铁蹄的灭绝摧残,期间所经历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战事,年轻的丘东平大都亲身经历过。在《沉郁的梅冷城》里,克林堡与华特洛夫斯基之间亲兄弟的手足相残,却导致了一百七十二个无辜的生命转瞬即逝;《马六甲和神甫》中,地痞马六甲和保卫队一样,肆意掠夺教堂和神甫的财产,甚至以掠夺和杀戮为唯一的生人之乐。许许多多的生命在戏弄、嘲弄和戏耍中变得毫无尊严和意义,盲目而且麻木。正如小说里写的:“人们传说着失踪的神甫已经死了,教堂里的神甫变换了一个,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了,大概他们以为失踪的事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上也有点关系的。”⑨叙述类似的惨剧连环,丘东平的笔调平稳沉郁,乃至是阴冷短促,无论句式还是词句,都呈现出对战争之蛮的直截了当、深入骨髓的把握和感知。《沉郁的梅冷城》里,面对一百七十二个鲜活人命陨灭的弹指一挥间,丘东平却仅仅用了两句话叙述,外加一句“独语”便戛然而止: 华特洛夫斯基是有着他的过人之处的,他命令保卫队驱散了群众之后,随后即把克林堡捆缚了,给五个保卫队送回家去。 因为,他说: “克林堡今日得了疯狂的症候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保卫队便枪决了那一百七十二个。⑩ 此类战争蛮性叙述,把一出出酷烈悲剧,写得像一阵风似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一样,麻木不仁。这一切又都呈现在叙述者刻意装出来的冷漠中。热铁与热血,刹那间凝聚在生冷的死水中,令人感到寂灭与痛楚。想必这就是丘东平战争蛮性写作的魅力与张力之所在。倘若抛开诸多因素,就战争本身而言,无非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命搏击,就是野蛮厮杀。其手段和惨烈程度,并不会因为源于文明世界就变得文明起来。丘东平的战争书写,敢于直视战争朴素的缘起与本质,不回避然也不止步于此,这就是他对战争之“蛮”的体味与传达,也正是他战争书写的平实有力、震撼人心的地方。 此外,丘东平对战争的蛮性体味,还在于他对战云逼迫下脆弱人性的揭示。这不仅表现为作品中出现大量神经质形态的人物、语言和故事,也呈现为一种峥嵘可怖的、抑郁阴冷的文本叙述风格。兹举一例,《十支手枪的故事》。瞎子赵妈的女儿小玛利,偶然瞥见绅士藏在放香糖的木盒里的十支手枪,从此就被编织进了不可摆脱的死亡之旅。而绅士掩藏十支手枪,同样也是出于偶然的一次接待,原因是他“一向便喜欢接待这一类的人物,有权威,有势力,只要他们肯在他的门口出入”(11)。最后,绅士扼死了小玛利,绅士杀人逃逸又被夜巡的哨兵抓住了。十支手枪也阴差阳错地由绅士的妻子缴到法庭,尽管绅士并没有供出关于手枪的秘密,一切不过是因为他的妻——“她是希望着能够减轻她的丈夫的罪状”(12)而已。类似吊诡的悲剧,与《一个孩子的教养》如出一辙。当然,就阴冷酷烈的战争蛮性书写而言,《通讯员》更为出色。战友纷纷战死或牺牲,通讯员林吉必须时时面对回忆的刺激和他人的不信任。最终他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在邻人诘问下愤而开枪自杀。 发掘并大量书写着战争的“蛮”,这不是丘东平的独到发现。可放眼中国现代文学的战争叙述,却极少有像他如此深入骨髓地了解、体验着战争的“蛮”性。这自然是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敢于正视战争的小说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战争起点本身开始体验、观察和书写战争的,一个眼睛向下和向前的参战者、观察者,而不是单靠着想象和文字阅读的后设小说家。 战争,无论是何种战争,总是群雄逐鹿,是角力争胜的行为。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3) “革命”其实就是“战争”。自命“革命”者,不过借宣示道德立场而妄图占据上风,希望获得自以为是的正义、自信或力量而已。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战争是野蛮的,但“革命”却不仅仅靠“蛮”,还必须讲“理”。光有蛮力而蛮干,那是一介赳赳武夫,实际上也不能叫战争,只是乌合之众的混战。现代意义上的战争,除却不能磨灭的蛮性,更要紧的是它的集约化、科技化和规模化。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再到高科技武器时代,战争已经不再是以往的人海战术。个中缓慢而无法遏止的战争渐变,从“蛮”的呈现到“力”的考量,一切都驳杂地呈现在丘东平的观察与书写中。如石怀池所论,“从‘底层’爬出来的作家,他们往往是‘力’的化身,给温文尔雅的文学圈子带来一颗粗犷的灵魂,一股逼人的锐气。”(14)看《红花地之守御》里的集体虐杀俘虏片段,情形固然惨酷,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现代战争和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区别。按理说,一百四十三个人仅仅凭着排枪来看押三百多个俘虏,如不是盲目自信,都应该知道双方时刻存在着局势逆转。面对这种难言的精神危机和情势紧张,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其转变为数量绝对优势——大规模剿灭俘虏,自然就是极端的选择。战争的角力本质便是如此。 量的消长是战争“力”的原始源泉。更令人心惊胆寒的,则是战争中由“智”生发、而又与“蛮”性绞缠在一起的“力”的角逐。古往今来的战争书写,精彩之处大多是在这方面的发掘。“武斗”固然血腥残忍,但毕竟是战争的本色当然,对战争文学来说,不过是理应如此而已;“文斗”隐蔽曲折,却是现代战争的文明表征。尤其是“文斗”加“武斗”的驳杂,足以令人掩卷沉思。因此,丘东平战争书写的另一特异之处,就是能够“集现代性与左翼倾向于一体”(15),在大大小小、形色各异的现代战争场域中,戳破久远的人性恶疾,刻画其现代的文明变态。例如《兔子》一篇。一个兵因为无意中发现排长贪污埋葬费,又在“排长的旁边有一位体面的客人在坐着”的时候,冒冒失失地报告了这件事,结果惹来了排长精心构陷的“搂草打兔子”式的杀身之祸: 他望见了排长正对他招着手。 他翻了起来,倾斜着身子,一步步踉跄地想着排长那边走,一条长长的脖子在空间里苦苦地挣扎着,仿佛给一条麻绳缚着狠狠的往前拉。 他没有忘掉那立正的姿势。 他的眼睛发射着异样的光,呆呆地直视着前头,双手拨开树枝,脚底踏上了那有着凹陷的地上时,那弯弯的背脊就在左右的摆动着,并且张开双手,竭力防备着自己的倾跌…… 但是,在他的前头,耸着高枝的那边,突然发出枪声。 那捉兔子的蠢货在第一下枪响的时候就倒下了。一下子结果了两个。(16) 这个兵的死,不难让我们迅速联想到阿Q、闰土等的同类死亡。不同的只有死亡的情景和场域。这是丘东平眼睛里看到的现代战争之“力”引发的死亡——朴素生命的被陨落和构陷。引发人精警之感的,其实还有丘东平对人性机心与贪婪的控辩。这一切,都在丘东平式的短促动作性短句里产生着别样的悲哀。 而在文本内外嵌入流窜不已的、庄谐互谑的情感,却是丘东平喜欢的。即便在战事胶着的叙述之际,丘东平也会抽出笔致,从容插入一大段颇为洋洋自得的“车大炮”(17)。事实上,这也正是丘东平对战争之“力”的本色观察和朴素发掘。战争并非单色体,它光怪陆离而且驳杂,譬如《多嘴的赛娥》。情报员赛娥到达了一个“梭飞岩的工作人员”和“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都在交叉活动的村庄。故事情节进入令人揪心的时候,丘东平突然在小说文本中阑入了一大段极具戏谑性的、针对这个地点本身的调侃—— 下午,赛娥到达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村子。梭飞岩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的巡逻,这两种不同的势力的混合,像拙劣的油漆匠所爱用的由浅入深,或者由深出浅,那么又平淡又卑俗的彩色一样,不鲜明,糊涂而且混蛋……这样的一个村子。但是从梅冷到海隆,或者从海隆到梅冷的各式各样的通讯员们却都把她当做谁都有份的婊子一样,深深地宠爱着,珍贵着……(18) 丘东平笔尖热辣,把战争用人类最原始的性事比拟,狠狠地嘲弄了许多战争自以为是的差别。多嘴的赛娥,其实在整个革命情报输送过程中并没有多嘴,始终表现坚决。革命大业最终崩解,是因为那个谁也没想到的老太婆的“多嘴”。而老太婆的“多嘴”,只不过是因为激烈的失眠症而发出的喃喃自语。于是,关于革命坚贞的神话,迅速消解在一系列毫无来由的偶然失误中。至此,我们似乎又听到丘东平特有的调侃——人犹如此,战争的滚滚烟尘又该情何以堪? 丘东平的战争叙述特别,还在于它的“野”。语言上有海陆丰地区的方言夹杂,战争体验则新鲜迅变、时地差异,还有那些战争中人的神经质的反应,以及他们时时刻刻生命攸关的幻觉,加上对新文学语言的不够熟练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一切都足以令丘东平的小说显得面目别致,“野性”十足。 平心而论,阅读丘东平的小说,那些非常个人化的战争观察和体验,那些极具现场神经质感的紧张,总是在不断地打断纯粹的文学欣赏。疙疙瘩瘩的文本,神经兮兮的体验,倏忽即逝的情绪转换,一惊一乍的生与死,灼目的粗暴,硬朗的爱憎,自嘲的勇毅,阴冷的抒情……一切都显得与众不同,确实“野”得可以。(19)正因为如此,对战争感受特殊性的留意和复杂性的聚焦,已是研究者对丘东平战争叙述特征的基本认同。有论者因此认为,这恰恰是丘东平小说在战争叙事中“注意防备‘单纯化’”的特殊追求,“其作品主题不是鲜明的而是含混的,其人物形象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其修辞色彩不是纯洁的而是暧昧的”。(20) 然而,一旦论及战争叙述的纯与不纯,就必然会生发“什么是战争文学”的讨论,也就必然要涉及思考革命文学的同质化问题。(21)事实上,战争文学也好,革命文学也罢,不过都是文学大观园的一部分,充其量只是题材和文学体验书写的差异,并非存在审美标准上的隔阂。丰富、生动、细腻、深入应该是文学的普遍追求。丘东平对此亦有着先见之明,他说:“战争使我们的生活单纯化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我不时的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最标本的战士应该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所谓战士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这显然是一种畸形的有缺憾的感觉,而我自己正在防备着这生命的单纯化,这过分的单纯化无疑的是从战争中传染到的疾病。”(22)可见,“纯”与“不纯”的问题,就丘东平而言,是对战争必然导致的简约划一与文学感受的多元复杂之间的张力与矛盾的警惕。以后设视野来看,就是对丘东平的战争叙述(更广泛地说,就是革命文学叙述)的路数正当与否的判断。对丘东平的战争体验是否同质化的思考,其实也就是对他的战争文学叙述的野味道、野路子、野风格如何评价的问题。战争和革命都是足以洗刷一切的洪流,对彻底性与集约化的要求是共同的,但并不等于战争文学必然是同质化和单一的——人是复杂的,更何况是战争情境中的人呢。 丘东平是个很好的革命战士,也是勇敢积极的直面拥抱战争的战士。但他更是一个坚持真切细腻地观察人、体察人与战争的纠葛的作家。他始终立足于以“复眼”来叙述表面上似乎整齐划一的战争,甚至强制自己以近乎热得发冷的激情来审视战争中的人情世态。丘东平这一点,与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对战争与爱情之间苍凉而荒诞的体验,就“直追人物的心里性格”(23)的力度和宽广度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来,人世悲凉并非只有张爱玲式的挥手,还有丘东平这种贴着战争世态娓娓道来的沧桑。举例而言,他人写战争都强调正义之别,立场鲜明,但丘东平不少小说偏偏看不出明晰划分,反而模糊处理,更多是反思战争本身。(24)比如《中校副官》就出现了对内战与抗战之间多线纠葛的思考。在寓言性的《骡子》一篇,又有对“中国军”、“日本军”以及战争、军队本身的朴素而深刻的思考。《白马的骑者》重心在于铺叙马夫谢金星人不如马的经历,足以尽显乱世凉薄。看完这篇小说,繁华落尽、循环往复,不由得感叹:幸亏谢金星他就是一个马夫。至于《运转所小景》里“百姓的无知和卑怯”与“兵队的残暴”;《正确》里的连长刻意用杀死“受处分的兵士”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尊贵的行为》写骄横的旅长让马夫去街上抢夺商家的豆子喂马,事后却又以枪毙马夫给自己增添“行高德厚”的美名……如此这些,都切切实实把庸众、弱者的“凶顽”镂刻得入木三分。 相对于许多战争文学书写中四处洋溢着的、令人乏味的政治正确的标举,丘东平“野”得别有滋味。之所以如此,在于他的写作都是从战争情势中起步。他的体验和观察,大多源于亲身所历和所见的战争情态。现场观感和亲历体验,与其新文学写作实践一起成长,共同生成别有风味的丘东平式的、原生态的“野”味十足的战争文学文本。《寂寞的兵站》为了表现兵士们“毫无意义的狂暴而放任的性格”、“毫无凭借的空虚”(25),丘东平随兴就大胆纳入了一首鄙俚的“酸曲”: ——莲角开花 满天青——罗, 妹你生好(美) 兼后生(年轻)——罗; 你要做——罗, 年年有——罗! 满天青——罗, 假唔知——罗; 你个屄——罗, 拾个钱——罗!(26) 丘东平的“防备‘单纯化’”,实际上并非仅仅因为他对“单纯化”的有意识的防备和理论明晰,而是源于他对驳杂、复色的战争现实、生活情境与个人体验的深刻感受,也源于他有限的新文学表现语汇、文字能力与充沛的战争实感传达之间的矛盾。“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苏轼是一种气势如虹的文才自信,在丘东平则更多是表达的焦灼与憋闷。有鉴于此,当读到丘东平战争小说文本中的为“颇多不大修洁”(27)的粗话糙话(28)、方言俚语,除了说能传达出人物身份与情感处境的生动一致,亦即丘东平所说的——“没办法,不像这样,不过瘾,他妈的,简直不过瘾”(29)——之外,也反映出丘东平的某种不得已为之的“野”路子和歪打正着。他自己说:“我最初写文章是用土话构思好了,再翻成普通话的。”(30) 显然,无论是书写战争的“蛮”,还是镂刻“力”与“野”,对于战争的文学书写,丘东平都是有着自己的“格调”追求的。他也是矢志追求这个境界的。丘东平曾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德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31)较之郭沫若对丘东平这些自我期许的记忆犹新,胡风也注意到了丘东平的战争叙述“格调”的重要意义。不过,急于求其友声的胡风,迅速把丘东平的“格调”定格在“革命文学运动”。胡风说:“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到我们的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到内容的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刻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特使把他的要求、他的努力用‘格调’这个说法来表现的。”(32) 可是,事实并非如胡风所说的那样简单和直接。丘东平不仅仅是革命文学运动里的作家,他的战争书写“格调”的真正所在,本质上是对于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开掘得非常有限的战争题材探索,即人性在战争的极端情境下的文学呈现。作为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本色军旅作家,丘东平的战争书写特质是高密度、原生态的战争经验传达。他那朴素战争情感的全面抒写、他的“奇诡狞美”的战争叙事风格、他基于人类立场的战争反思,不仅凸显出了现代战争中的人欲与人情,也曝出了人性的凶顽与愚陋。丘东平以自己的勇敢和执着,以战争亲历者的真实和鲜活,以新文学习作者的坦诚与朴素,真切镂刻出了中国大地浸泡于现代战争中的苦难酸楚与悲欢离合。 一个人的生与死,在中国现代漫长而驳杂的战争视域中,的确是稀松平常的事。周扬认为丘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基于的是革命本身的立场判断,也就是对丘东平参加战争的左翼立场的肯定,即革命与否的认定;但周扬断定丘东平“当做作家来看”则是“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33),显然是对其文学价值和才华的蔑视。 无疑,丘东平的写作才华主要呈现在大量的战争书写上。鉴于上述讨论,我们也可以明了丘东平战争书写的价值和意义,偏偏不在于对战争立场的选择和明晰,而在于对战争与人、战争与文明之类的关系反思,对战争本身的残酷野蛮的反思。道理很简单,丘东平亲身经历了太多的战争现实,而且他往往是沉浸于战争自身又能跳脱战争来反思。这样一个战争的文学书写者,在讲究和率先关注立场和动机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能被施之以“人”与“文”的分别对待,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无论如何都还算得上是丘东平的幸运,当然也是周扬在文学批评上的厚道和辩证之处。这也足以表明,周扬在文艺与政治之间,在评判丘东平上面,的确充分表露了他的非凡之处。 周扬相关合理而有分寸的判断,并不等于这些判断本身在文学价值上的批评正确。周扬的判断固然表露其作为党的文艺批评家的持重,但也说明他对丘东平文学价值衡定的“束手无策”。周扬可以敏锐感知作家在革命与文艺方面的“立场”,但他却没有办法判断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上的探索价值。换言之,周扬也许正是因为丘东平在战争文学上不够鲜明的写作立场和革命姿态,进而否定了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价值。这种先入为主的“盲视”与“洞见”,或许就是周扬这一评说的“经典”意义所在。 正如前面所论,长期以来,丘东平文学评价也好,人的判断也罢,基本上都以周扬的“话中话”为前提。至于说那部以丘东平自杀为题材的小说《东平之死》发表引发的再讨论,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篇小说不仅否定了丘东平文学上的价值,而且还否定了其本人在实际战争中的“革命”立场,也等于完全彻底否认了丘东平的“人”与“文”。这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比周扬的判断更为决绝。 事实上,周扬对丘东平的战争书写并非毫无了解。但就因为立场(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前提,阻碍了他对丘东平文学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对于周扬这一类的批评家而言,只要是战争,立场是第一位的,首先必须是战争的定性问题,其次才是文学。我们无法、也无意苛求周扬他们的历史局限,但随着时间流逝,或许可以提出更为丰富的看待人类战争的角度,可以有更开阔更深入的视野。毕竟,当战争的成败快感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是更漫长的人类文明自身的悖论与悲哀。而此时此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类文明的困境,往往就是文学的长处。 就此而言,丘东平战争叙述的“力、蛮、野”,更从战争与人的关联——工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结合部——呈现出另一现代性的审视角度:“从战士、战争和战争中的人这个真实而坚固的铁三角的视角进入战争”(34)。这也是林岗先生所论的,丘东平“不仅写得有真情实感,而且有很深刻的观察,有的还包含有哲学的思考在里面。这一层对左翼作家来说更加难得”(35)。是故,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中“对于现实的拼命的肉搏”(36),时刻“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37)的思考,才因此超越了一般的猎奇炫幻的战争写作,在人性与文明的高度上开启了一扇对战争进行文学开掘的“黑暗的闸门”(38)。 丘东平是亲历并曾经书写过现代中国多“类”战争的作家,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作家。丘东平战争书写的特质,不在于左翼立场本身,而在于其高密度的战争经验传达。“最讨厌庸俗的大众化论者”(39)的丘东平,是一个活跃在现代中国复杂战争语境下的革命作家。他用“自己的那种钢一样的笔锋”书写着“内容总是被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贯串着的”(40)战争文学。对丘东平来说,对战争的文学关注和心灵发掘,比立场本身重要得多。丘东平的意义更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力行者和先行者,他不仅是“知道到自己的作品里头去玩耍”(41)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新血液”(42),更是“一个新的世代的面影”(43)。 ①罗飞:《〈丘东平文存〉编校后记》,《丘东平文存》,罗飞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1页。 ②庞瑞根:《东平之死》,《当代》1984年第5期(《小说选刊》1984年第12期转载)。 ③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164页。 ④金钦俊:《丘东平:现代战争文学的推动者与杰出代表》,《丘东平研究资料》,许翼心、揭英丽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⑤[美]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三联书店2010版,第67页。 ⑥林岗:《论丘东平》,《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⑦姜建:《士兵·战争·人——论丘东平作品的特质与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 ⑧秦弓:《丘东平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东岳论丛》2011年第2期。 ⑨⑩(11)(12)(16)(18)(25)(26)《丘东平作品全集》,张业松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13、27、38、180、45、605、605~606页。 (13)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页。 (14)石怀池:《东平小论》,《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80页。 (15)刘东玲:《论丘东平的文学创作》,《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11页。 (17)“车大炮”就是吹牛之意。不仅丘东平在小说中喜欢用这个词,郭沫若在《东平的眉目》里也用这个词来调侃丘东平。 (19)草明说丘东平有“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闪灼的才华与豪放的热情”和“爱炫的癖好”。草明:《忆东平》,《丘东平研究资料》,第49页。于逢则说丘东平“充满活力,仿佛没有一刻安静”。于逢:《忆东平同志》,见《丘东平研究资料》,第51页。草明和于逢的回忆,颇可从人的角度映衬其文的风格。 (20)刘卫国:《丘东平“战争叙事”新论》,《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21)参见杨义、严家炎、王富仁、黄修己、吴福辉、刘增杰和秦弓等人关于“战争文学”问题的系列论文,《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22)《丘东平致胡风的信》,《丘东平文存》,罗飞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 (23)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24)古远清先生理解为“和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有关”和“情节的不确定性”。古远清:《得模糊处且模糊——〈沉郁的梅冷城〉小识》,《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38页。我认为“模糊”还有助于丘东平避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立场选择,可以将更多笔力置于对战争本身的哲学思考和审美开掘。 (27)茅盾:《给予者》,《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15页。 (28)张全之先生把“语言粗糙凌厉”特征解释为“不避污秽”,并认为这“使小说在感情基调上显得异常芜杂”。张全之:《丘东平:以五四精神之火炬烛照军人世界》,《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72页。 (29)(30)(39)(41)聂绀弩:《东平琐记》,《丘东平研究资料》,第6~7、5、5、5页。 (31)(37)(43)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77、178、176页。 (32)(40)胡风:《忆东平》,《丘东平研究资料》,第42、45页。 (33)罗飞:《〈丘东平文存〉编校后记》,《丘东平文存》,第381页。 (34)揭英丽、许翼心:《〈血潮汇刊〉述略》,《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25页。 (35)林岗:《论丘东平》,《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36)鹿地亘:《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纪录),《丘东平研究资料》第178页。 (38)据乐黛云先生所论,“黑暗的闸门”典出《说唐》,后因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广为人知。参见乐黛云《肩起黑暗的闸门——纪念鲁迅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90周年》,《新京报》2009年4月28日。后来,夏济安(Hsia Tsi-An)《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也为此说增色不少。 (42)胡从经:《东平小论》,《丘东平研究资料》,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