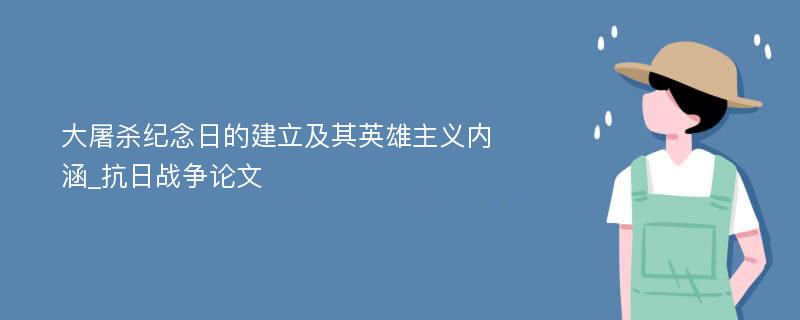
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及其英雄主义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英雄主义论文,纪念日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同胞,以色列建国后通过对其创伤记忆的控制、管理、运用,特别是建立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为国家纪念记忆场所、确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为国家法定节日,并凭借国家权力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层面,作为以色列人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奠基神话”,甚至成为一种为人们所崇奉与膜拜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①。在此权力运作过程中,纳粹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的确立即为一个典型案例。②通过对围绕该节日的日期与名称问题展开激烈的争夺较量之分析,可以借此揭示以色列建国初期政治生活中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之间交错复杂的关键面相。 有关设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最初提议 给纳粹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纪念日的想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已提出,这种活动最初始于对华沙隔都起义的纪念。1943年4月19日—5月16日发生的华沙隔都起义,为二战期间最大规模的犹太人武装反抗纳粹暴政事件。起义虽然被残酷镇压,但其所体现的英勇战斗精神之后被无限放大,作为犹太人争取自由、捍卫尊严的英雄主义典型事迹而为锡安主义者不断强调。实际上,华沙隔都起义从一开始就在纳粹大屠杀纪念安排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在有关设立纳粹大屠杀纪念日问题上的许多争论,便是围绕着要不要以华沙隔都起义日作为整个纳粹大屠杀事件的纪念日而展开。 早在1944年,发行于巴勒斯坦的《达瓦尔报》(Davar)呼吁将4月19日作为欧洲犹太人毁灭的官方纪念日,但伊休夫(Yishuv,即巴勒斯坦犹太社团)领导机构犹太民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没有就此做出任何决定。③然而,率先对华沙隔都起义开展集体纪念的行为来自1945年4月刚刚获得解放的华沙。这种活动随即扩展到巴勒斯坦,随后有关的许多纪念典礼与大型集会都放在4月19日。成立于1946年的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Yad Vashem Special Committee)在开展纪念活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46-1948年间,许多核心政治机构特别是民族委员会,通过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参与到4月19日的大型集会与纪念典礼中。④在当时的纪念论述中,对不久前的民族浩劫进行了选择性处理,很少提及集中营里的迫害、屠杀与幸存行为,而集中于军事斗争特别是华沙隔都的武装反抗,这几乎成为时人对大屠杀的主要认知。⑤ 随着纪念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必要专门为之设立一个纪念日。在当时的巴勒斯坦,4月19日象征着大屠杀期间的英雄主义行为已是普遍的共识。因而从一开始,以夏拉该(S.Z.Shragai)、祖克尔曼(Yitzhak Zuckerman)和舍纳哈比(Mordechai Shenhabi)为代表的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主要成员提议将这一天作为英雄主义纪念日,用来纪念大屠杀期间所有犹太人的英勇行为。然而,他们想在体现英勇抵抗和屠杀毁灭的纪念日之间进行区分,因而提议将针对所有死难者的纪念典礼放在阿布月9日举行,“届时前去我们丧生者的公墓朝圣”。⑥阿布月9日在传统中代表着犹太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例如第一、第二圣殿的毁灭,贝塔尔要塞的陷落以及犹太人从西班牙的大驱逐等等。这个日期在当时有着不小的影响,1946年的阿布月9日,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举行了纪念活动。⑦ 除4月19日与阿布月9日外,当时也有其他日期被人用来与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联系起来。1947年7月,在由亚德·瓦谢姆委员会主办的第一届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国际研讨会上,巴勒斯坦犹太民间文学协会负责人约姆-托夫·莱文斯基(Yom-Tov Levinsky)建议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放在希完月20日,⑧认为这一天意味着“为六百万死难者进行全面哀悼的一天”,而不是像专门纪念隔都起义者英勇反抗行为的4月19日,因此有必要从传统的哀悼节日中选择一个用来纪念那些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同胞。⑨在他看来,在设立一个突出英勇反抗的纪念日,与将希完月20日作为全国性哀悼日之间并不冲突,后者在犹太集体记忆中不仅象征着受难与毁灭,而且代表着犹太人愿意作为殉道者而牺牲,从而在纳粹大屠杀与犹太英雄主义之间找到了某种对称。 1948年独立战争的爆发,直接推动了隔都起义纪念日地位的提高。这一年的许多纪念典礼由于准备战争而被忽视,但以色列人习惯将隔都的反抗和当前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联系起来。亚德·瓦谢姆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写到,“隔都起义的日期之一,将成为我们人民纪念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的日期”。⑩随后,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民族委员会的宣传部门极力将4月19日作为全国性纪念日,并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组织了大型纪念集会。(11)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后,这一天作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已成为大多数世俗群体的共识。实际上,要求将华沙隔都起义日定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主要动力来自伊休夫的世俗领导层,他们认为此次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和此前流散犹太人遭受的屠戮、毁灭及其回应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些世俗锡安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公众的意识中,已将隔都起义视为锡安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即不再是被动地任人屠戮和殉道,而是主动地自我防卫和反抗,隔都起义者是“流散地的锡安主义者”。(12) 宗教与世俗阵营围绕纪念日期的争夺 以色列国建立后,加快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国家化进程。但就具体的日期问题,以色列社会内部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宗教阵营拒绝承认4月19日的合法地位。大拉比署很早即已开始讨论如何纪念欧洲犹太人,1946年初成立了纪念流散殉道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Memorial to the Diaspora Martyrs),并向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发表声明,称“大拉比署决定根据托拉的律法和希伯来传统的精神来纪念殉道者”,而这包括点燃蜡烛、诵读诗篇、学习塔木德经文和吟唱卡迪什祷文,来纪念受害者及其亡灵。(13)大拉比署并没有对抵抗活动进行区别对待,而是把所有纳粹受害者称为“所有那些为犹太人的上帝而牺牲的殉道者”,(14)显然是以传统的犹太殉道词的形式来加以描述。在日期问题上,战后初年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的拉比们以缺乏宗教依据为由,拒绝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日。 1948年12月17日,大拉比署联合宗教事务部在耶路撒冷召开特别会议,宣布以犹太历提别月10日作为大屠杀死难者的民族性纪念日:“有必要决定一年中的某个日期为犹太人哀悼(纳粹大屠杀中的)毁灭,以作为吟诵卡迪什悼词、点燃贾泽特蜡烛和学习塔木德经文的纪念日。因此,大拉比署决定将提别月10日作为几百万死亡日期无法知晓的欧洲犹太社团殉道者的永久性纪念日——对于他们的儿女和亲戚来说,它将被视为他们死亡的纪念日。”(15)提别月10日在犹太传统中为纪念死者的特定节日(General Kaddish Day),最初源自对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围困耶路撒冷的纪念。当时,宗教阵营的报纸《哈特索菲》对选择这个日期如此解释道:“这个为第一次毁灭而设立的节日直到最后的毁灭一直被作为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巴比伦王逼近耶路撒冷,而成为犹太民族丧失独立、被迫流放的灾难之始。德国刽子手是尼布甲尼撒的直系后代,来自巴比伦、罗马与柏林的猛兽企图摧毁犹太民族。”(16) 宗教人士认为,纳粹大屠杀是犹太历史上遭受的屠杀与毁灭链条上的又一环,大屠杀尽管有着空前的规模,但它只是犹太历史上众多灾难的延伸,应当根据传统来开展纪念活动。他们不仅在时间上确立了与世俗群体不同的纪念日,而且还建造自身独立的纪念场所来开展纪念活动。1949年,以宗教事务部部长卡哈纳拉比(Samuel Z.Kahana)为首的大拉比署在锡安山上建立起一座规模较小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室”(Martef HaShoah/Shoah Cellar),而成为以色列境内第一座纳粹大屠杀纪念馆。宗教力量选择锡安山作为其纪念场所的原因在于它靠近大卫王墓,犹太传统中弥赛亚出自大卫王的后裔,而这种选址安排象征着他们对弥赛亚救赎应许的期待。(17) 1949-1950年间,纪念活动主要在提别月10日与4月19日两个日期举行;宗教人士接受大拉比署的决定在前一日期开展纪念活动,而世俗群体的纪念活动通常在后一日期进行,双方互不妥协。为了消除这种纪念日期上的分歧,1950年,议会中来自马帕姆(统一工人党)的议员提议设立一个全国性纪念节日:主张将4月19日作为全国性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以确保隔都起义在以色列社会中占有持久的地位。兹斯林(Aharon Zisling)在解释这个提议时说,“我们不想这个节日仅仅属于某一部分人,而应当属于每一个人。”(18)在马帕姆议员的努力下,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一个具体的日期被正式列入议会的议事日程。1951年,内务委员会任命一个次级委员会来确定最终日期,它由来自联合宗教阵线的努洛克(Mordechai Nurock)领导,其成员包括马帕姆的伯格(Hertzl Berger)、右翼政党希鲁特的拉兹勒·诺亚(Esther Raziel-Naor)与马帕姆的兹斯林。(19)1951年3月该委员会重新召集时,所有成员都准备支持以4月19日作为纪念日,表明大多数议员认为隔都起义在纳粹大屠杀纪念中占有核心地位,它要比二战爆发(20)以及死亡营更具象征意义。努洛克指出,“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日期,以便与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的屠戮和发生在尼散月的隔都起义相一致。”(21)但马帕姆成员强调,不应当放在传统的纪念日举行,因为抵抗活动与传统的犹太殉道精神相冲突。由于隔都起义发生在犹太历的逾越节前夕,委员会成员与其他议员建议放在尼散月的其他日期。赫兹勒·伯格提议将纪念日设在独立纪念日之前,以便将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和以色列国的独立联系起来。兹斯林则强调隔都起义有着独特的教育意义,认为如果纪念日太靠近独立纪念日将使其重要性难以凸显,因而提议“将之靠近华沙隔都起义日,这将赋予它巨大的教育价值”。(22) 由于4月19日在犹太历中为尼散月15日,与逾越节重合而不为拉比署同意,委员会决定将纪念日放在逾越节与独立纪念日之间。但极端正统派代表向议会要求,整个尼散月都不能作为哀悼日。这一要求遭到前隔都战士组织的反对,他们想选择一个尽可能靠近隔都起义的日期。(23)因此,纪念日只有从尼散月15日(隔都起义第一天,也是逾越节前一天)与伊雅尔月5日(独立纪念日)之间进行选择。加上禁止在逾越节的那一周确定日期,同时又不能与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太过靠近,留给委员会的只有12个日期可供选择。(24)在此情况下,尼散月27日由于处在适中的位置,位于逾越节结束后五天、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七天,最终被确定下来。 在该纪念日的名称问题上,马帕姆的议员想称之为隔都抵抗日(Ghetto Rebellion Day),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委员会在咨询了其他议员后,决定将之命名为“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Yom HaShoah u-Mered HaGeta'ot/Shoah and Ghetto Uprising Remembrance Day)。1951年4月12日,以色列议会正式将每年的尼散月27日作为“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个以色列国家的永久性纪念日。”(25)这个纪念日的名称充分表明,隔都起义被凸显为整个纪念日名称的一部分,使大屠杀期间的抵抗活动获得了积极意义。正如委员会成员兹斯林强调的,“这一天象征着犹太民族在最近这场战争中的积极抵抗。它将象征着那里的锡安主义,那些从事战斗的锡安主义背景,尽管不仅有锡安主义者还有其他犹太人参与了战斗。”(26) 值得注意的是,在确立尼散月27日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过程中,宗教势力对此提案并未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在于这个提案并没有规定尼散月27日是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日,提别月10日仍然作为宗教人士纪念大屠杀的节日。1952年12月,宗教事务部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在议会确定尼散月27日作为纳粹大屠杀与抵抗的纪念日后,看来没有理由改变大拉比署自1949年决定的将提别月10日作为大屠杀死难者的哀悼日……因为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发生的最为糟糕的事情,设立两个日期来纪念它是完全可取的。”(27)然而,在宗教势力的阻挠下,新纪念日的推广并不顺利。由于议会选定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尼散月27日)没有任何传统宗教上的内涵,这在正统派当中引发了不满,并与两年前大拉比署的决定相冲突。大拉比署决定无视议会的决定,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犹太律法禁止在尼散月禁食与哀悼,因为它被视为喜乐之月,代表着逾越节之后的庆祝。(28)著名的卡勒利兹(Avraham Y.Karelitz)就认为,现在的人们无权为将来的世代设定新的哀悼或纪念日。(29)宗教群体特别是极端正统的哈雷迪派完全无视以色列议会确定的纪念日,在提别月10日依然正常开展纪念活动。(30)以色列社会围绕纪念问题产生巨大的分歧,形成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两个正式纪念日:世俗团体选择在尼散月27日纪念纳粹大屠杀,而宗教力量则在提别月10日进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宗教与世俗力量之间的激烈争斗。 “亚德·瓦谢姆法”与纪念日的最终确立 为了给予纳粹死难者以统一的纪念,在时任教育部长迪努尔(BenZion Dinur)的积极推动下,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正式通过“亚德·瓦谢姆法”(Yad Vashem Law/Law of Remembrance of Shoah and Heroism-Yad Vashem 5713/1953),也称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法,声明其目的在于:“将所有那些在……战斗与反抗中遇难的犹太人的记忆集中到故土上来……因为他们皆属于犹太民族”。(31)这项法律规定成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纳粹大屠杀殉道者与英雄纪念当局(Yad Vashem/Shoah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要求它建造一座纪念工程,搜集屠杀的相关证据并“向世人提供教训”;同时,由议会设立“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Yom HaShoah ve-HaGevurah/Shoah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以便“为其英雄与死难者提供一个整体性记忆”。(32)这部法律的出台表明,英雄主义被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抬高到与大屠杀本身同等的地位。 在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名称问题上,与此前两年的议会决议相比,这部法律更加突出了英雄主义的内涵。作为该法案的主要推动者,迪努尔认为隔都起义固然是大屠杀期间犹太人反抗的象征,但它的内涵太有限,“英雄主义”一词更能体现犹太人在面临被纳粹灭绝时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反抗行为。他强烈建议将纪念日的名称从原来的“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改为“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33)正如迪努尔解释的,它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讨论灭绝问题,另一就是探讨勇敢、英雄主义的价值问题。在他看来,“英雄主义”一词的使用将大屠杀期间的反抗斗争作了最为宽泛的解释,它对争取生存的消极抵抗行为表达了充分的敬意,因而代表着犹太人对于空前民族浩劫的不同回应方式。(34)实际上,这个法案虽然明确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日期和名称,但它并未对与纪念日有关的具体细节进行详细规定,例如没有强调降半旗、限制娱乐活动等等,因而在权威效力、实施程度等方面难免大打折扣。努洛克对此抱怨道,“(在尼散月27日)娱乐场所普遍对外开放,电台广播播放着婚庆与欢宴、舞蹈与戏剧的音乐……一片欢乐与庆祝而非哀悼与哭泣。”(35)而且在1950年代初,对纳粹大屠杀的纪念并非是以色列政府关注的重点,这可以从亚德·瓦谢姆纪念馆的建造一再被延迟体现出来。加上迪努尔自1955年后不再担任教育部长,有关纪念日的具体仪式等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 虽然政府对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没有太多的举动,但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在1953年成立后致力于赋予纪念日更多的民族特征。它在每年的纪念日举行隆重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典礼,一开始在殉道者森林举行,自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于1956年落成后改在纪念之山举行,而且还通过与地方当局和幸存者组织的合作在全国各地组织纪念活动。(36)尽管如此,纪念日并未成为全国性纪念日,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也清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尤其抱怨宗教事务部与大拉比署,在1951年的议会决议和1953年的亚德·瓦谢姆法之后,仍然在提别月10日开展纪念活动。(37)而且,大拉比署一再拒绝前往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参加活动,而坚持在他们位于锡安山的“纳粹大屠杀纪念室”开展纪念活动。 更为重要的是,宗教事务部一直试图加强提别月10日的重要性,并质疑尼散月27日,认为它是与隔都起义联系在一起的,武装斗争不应成为整个纳粹大屠杀纪念的焦点,因为几百万的犹太人并没有参与其中。在1956年亚德·瓦谢姆理事会举行的辩论上,宗教事务部副部长瓦尔哈夫提格(Zerah Warhaftig)坚持强调提别月10日即是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甚至还向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提议应当将全国性纪念日变更为提别月10日,并认为1951年议会通过的决议就是一个错误。(38)在整个50年代,绝大多数宗教学校无视议会决议,而坚持在提别月10日开展纳粹大屠杀纪念活动。 当时有许多尝试来解决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与宗教事务部的矛盾,但这种努力遭到后者的顽强抵抗。1957年,在安置来自波兰的纳粹受害者骨灰问题上,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与宗教事务部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前者要求将这些骨灰安葬在亚德·瓦谢姆纪念大厅,而宗教事务部则主张将他们安置在“纳粹大屠杀纪念室”,以与1949年来自奥地利、德国、波兰的骨灰毗邻。他们声称,将这些殉道者的骨灰葬在世俗的机构没有任何价值,并将亵渎他们的神圣性。(39)宗教事务部不断抬高提别月10日的行为,不仅威胁着尼散月27日的地位,而且对亚德·瓦谢姆作为全国性纪念当局的权威造成了损害。对于宗教事务部的做法,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负责人梅尔卡曼(Yosef Melkman)1958年在一份纪念仪式的报道中表达了担忧:“如果亚德·瓦谢姆是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的全国性纪念当局的话,一个政府部门怎么可以在没有获得我们允许和没有向我们咨询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的意愿组织纪念活动?我们是有政府还是完全无政府?……亚德·瓦谢姆无法忍受宗教事务部破坏前者地位与可信度的行为,将来在纪念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耶路撒冷的人口将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40)面对这两大政府部门不断升级的冲突,议会和政府其他部门不得不进行调解。 为了消除纪念日分歧而带来的政治分裂危险,(41)1958年6月,努洛克联合幸存者组织提出将尼散月27日作为官方的全国性纪念日的提案。其内容包括:在纪念日这一天,学校学习大屠杀历史、允许工人举行集会、关闭商店与娱乐场所等等。1958年底1959年初,议会委员会围绕此提案召开了多次会议,绝大多数代表支持颁布一部将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作为全国性纪念日并赋予其官方地位的法律。(42)尽管宗教势力不满,以色列政府和议会委员会决定坚持以尼散月27日作为纪念日。这既建立在1951年议会决议和1953年亚德·瓦谢姆法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如果改变日期,势必招致议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反对。但它并未要求大拉比署改变他们自1948年以来将提别月10日作为纪念日的决定。很显然,这种要求必将遭到宗教势力的极力反对,同时也反映了建国初期宗教与世俗政治力量之间的某种平衡:“我们不能忽视提别月10日的事实。这一天是传统上为死者祈祷的日子,在这两个日期之间并不存在冲突。”(43) 对于“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的名称,许多隔都战斗者组织并不乐意。梅查德基布兹(HaKibutz HaMeuchad)与阿里茨基布兹(HaKibutz Ha' Artzi)的成员极力避免使用这个名称,他们宁愿将之称为“隔都起义日”(Ghetto Uprising Day)、“纳粹大屠杀与起义纪念日”(Shoah and Uprising Remembrance Day),或“纳粹大屠杀死难者与起义英雄的民族纪念日”(the National Remembrance Day for Shoah Victims and Uprising Heroes)等等。(44)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在幸存者组织的特别委员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努洛克在提出议案时,将之称为“纳粹大屠杀与隔都起义纪念日”,与1951年的议会决议相一致,而完全无视1953年“亚德·瓦谢姆法”带来的变化。但他的提议遭到政府与议会的一致反对。一度有人建议将“起义”一词加入到名称中,构成“纳粹大屠杀、英雄主义与起义纪念日”(Yom HaShoah,HaGvurah,ve-HaMered/Remembrance Day for Shoah,Heroism,and Uprising),其中英雄主义代表争取生存的日常斗争,而起义专指反对纳粹的武装斗争。(45)这个提议被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否决,它希望在纪念日与纪念当局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为此这两者的名称应当保持一致。与“亚德·瓦谢姆法”相一致,1959年初政府决定该纪念日的名称仍为“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 1959年4月7日,议会通过“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法”(The Shoah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 Law),正式决定以犹太历尼散月27日为法定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决议如下:第一,尼散月27日为灾难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每年用来纪念纳粹及其仆从造成的犹太民族大灾难,以及那一时期的犹太英雄主义与反抗行为。如果尼散月27日是在星期五,纪念日就应当定在当年的尼散月26日。第二,纪念日这一天,全国应当遵守两分钟的默哀,在此期间路上的所有交通工具应当停下来。纪念仪式与会议应当在军营以及教育机构举行;悬挂在公共建筑上的旗帜应当降半旗;电台节目应当表达这一天的特别性质,娱乐场所的节目应当与这一天的精神相一致。第三,政府授权的部长通过咨询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为纪念日的遵守起草必要的指导。(46) 通过该法律的颁布,正式确立了尼散月27日作为全国性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官方地位,并对相关的仪式遵守进行了详细规定,还赋予亚德·瓦谢姆纪念当局充分权威以作为纪念日遵守的指导。在这一天,以色列政府通常在亚德·瓦谢姆纪念馆的华沙隔都广场举行重大纪念典礼。1961年3月27日,议会又对该法作了进一步修订,要求在大屠杀纪念日前一天所有娱乐场所必须关闭。 纪念节日序列的形成与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凸显 由前文可知,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最终确立的复杂过程,充分反映出以色列建国初期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宗教与世俗之间的较量。以色列作为一个再造的国家,其内部面临文化、种族、肤色、语言等方方面面的多样性,用诺亚·卢卡斯的话来说,以色列是“用欧洲的手术在亚洲腹地用剖腹产生的方法诞生”的新国家。(47)与“Shoah”的词语推广一样,(48)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重要时期,节日推广与认同建构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这些纪念节日序列凭借国家权力强制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成为以色列人集体认同的主要对象;同时,对纪念节日的遵守,往往伴随着英雄主义的价值灌输,号召牺牲与奉献,以期将形形色色的犹太人整合到新的国家认同中来。 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的最终确立,标志着大屠杀纪念活动得到了最高形式的法律肯定,从而将创伤记忆的国家化、政治化推向一个顶点。加上此前确立的独立纪念日(Yom HaAtzmaut)与阵亡将士纪念日(Yom HaZikaron),这三大新型政治节日一起构成以色列国的纪念节日序列。这些纪念日不同于传统的宗教节日,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新型政治认同的重要手段。作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尼散月27日在传统的逾越节(因纪念出埃及而代表获得自由)之后五天,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一周、独立纪念日前八天,(49)象征着纳粹大屠杀介于古代民族自由与现代民族独立的中间阶段,从而在两者之间搭建起一座象征之桥。这个序列的形成,使得“从浩劫到重生”(Me-Shoah le-Tekumah/from Shoah to Rebirth)在建国前后的主流话语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50)该连用扎根于“灾难与救赎”的传统主题,表达出大灾难后犹太人获得奇迹般拯救的思想。古代的自由是通过神的干预获得的,现代的独立则是靠民族自身的力量实现的,这种转换借助纳粹大屠杀得以完成,空前的浩劫表明上帝干预的古典模式不再有效,而必须通过武装斗争以实现自我拯救。正如时任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在1964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讲话中强调的:“殉道者与英雄纪念日处在古代的自由节(逾越节)和现代的独立日中间,我们民族的编年史围绕这两大事件为中心展开。通过从埃及的奴役中摆脱出来,我们获得了古代的自由;现在,通过追溯至纳粹大屠杀,我们再度存活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51) 实质上,在纳粹大屠杀纪念日—阵亡将士纪念日—独立纪念日庆典这个纪念节日序列的背后,英雄主义的价值观一脉相承。通过对英雄主义的强调,隔都起义者作为潜在的以色列人获得了空前的民族价值,而当下为国捐躯的国防军战士则是隔都起义者的英勇延续。(52)莫斯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纪念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对阵亡士兵的崇拜使民族得以神圣的仪式复兴、后辈得以效仿先烈的光荣:“对死者的召唤是为了使民族年轻化,因为‘战斗、死亡与复兴’即是民族的本质所在。从他们的死亡中,民族将得到恢复。”(53)以色列政府通过为阵亡将士建造国家公墓、确立纪念节日,实现了莫斯所说的“死亡国家化”(nationalization of death),死者得以进入国家的纪念序列之中,作为全体公民的道德典范和精神楷模而被想象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那些人长眠于其下。……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54) 另一方面,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确立与华沙隔都起义密切相关,充分反映出建国前后以色列社会对于流散地的排斥。阿肯松认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直到1959年才正式确立,是因为它“所纪念的行为正是以色列的神话制造者想要消除的对象:在外邦敌人面前顺从地殉道。以色列正要成为纳粹大屠杀的解毒剂。”(55)长期以来,奉行“否定流散地”(Shlilat HaGalut/Negation of the Diaspora)观念的锡安主义者极力推崇反抗异族压迫、从事武装斗争的犹太战士,在此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主流话语下,土生土长的“萨布拉”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困惑不解,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耻辱;同时,高度赞扬大屠杀期间的武装反抗并将之与流散犹太人区别开来,对以华沙隔都起义为代表的武装反抗的歌颂,几乎成为建国初期以色列关于纳粹大屠杀叙述的主导方向。他们将犹太人的反抗区分为要么是积极反抗、要么是消极顺从:前者是隔都战士及锡安主义者作为“新型犹太人”的特征,而后者则是与纳粹大屠杀及流散犹太人相连的。“游击战士与隔都反抗者因而从‘纳粹大屠杀’中脱离开来,以作为在流散地与现代以色列之间搭起的一座象征之桥。与马萨达及特尔哈伊的守卫者一道,他们成为以色列英雄般过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纳粹大屠杀的其他经历被降格为流散时期并与‘他者’相连,被称作是屈辱的流散犹太人。”(56)通过对大屠杀期间英雄主义事迹的不断强调与凸显,积极抵抗几乎成为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大屠杀纪念的叙述主体,以用来服务于以色列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必须看到,英雄主义的价值灌输,伴随着对绝大多数大屠杀死难者的压制与忽略,致使以争取生存为目标的幸存者个体创伤记忆只能在暗地里默默流传。(57)这种英雄主义价值观的内在不实性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就埋下了日后走向解构的致命隐患。 ①Charles S.Liebman & Eliezer Don-Yehiya,Civil Religion in Israel:Traditional Juda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Jewish Stat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00. ②有关纳粹大屠杀纪念日的研究在近年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热点,重要的有:James E.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 Orna Kenan,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Israeli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1945-1961,New York:Peter Lang,2003; Roni Stauber,The Holocaust in Israeli Public Debate in the 1950s:Ideology and Memory,trans.Elizabeth Yuval; 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7,etc。 ③Boaz Cohen,Israeli Holocaust Research:Birth and Evolution,London:Routledge,2013,pp.3-4. ④⑥⑦⑨(11)(15)(16)(18)(19)(22)(26)(27)(33)(34)(36)(38)(40)(43)(44)Roni Stauber,The Holocaust in Israeli Public Debate in the 1950s:Ideology and Memory,p.31,p.31,p.33,p.33,p.35,p.37,pp.37-38,p.39,pp.39-40,p.44,p.40,p.46,p.63,p.66,p.98,p.101,p.105,p.111,p.103. ⑤(13)(14)(35)Orna Kenan,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Israeli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1945-1961,pp.25-26,p.15,p.15,p.17. ⑧希完月20日作为哀悼性纪念日直到二战前夕一直在东欧遵守,始于1171年5月26日(犹太历为希完月20日)31名犹太人因血祭诽谤而被活活烧死。1648年的6月10日(犹太历为希完月20日),成千上万的东欧犹太人被哥萨克骑兵屠戮,使之与犹太历史上的大灾难再度联系在一起。 ⑩(21)(23)(42)(46)James E.Young,"When a Day Remembers:A Performative History of Yom ha-Shoah",History & Memory,Vol.2,No.2(Winter,1990),pp.60-61,p.60,pp.60-61,p.62,pp.63-64. (12)Roni Stauber,"The Jewish Response during the Holocaust:The Educational Debate in Israel in the 1950s",Shofar,Vol.22,No.4(Summer,2004),p.59. (17)(28)(37)(39)Doron Bar,"Holocauat Commemoration in Israel During the 1950s:The Holocaust Cellar on Mount Zion",Jewish Social Studies,Vol.12,No.1(Fall,2005),p.20,p.24,p.22,pp.29-30. (20)拉兹勒·诺亚反对4月19日的提议,建议设在二战爆发的9月1日,故而象征着毁灭的开始。 (24)(45)James E.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p.269,p.270. (25)E.Don-Yehiya,"Mem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Israeli Society and the Holocaust",in Ezra Mendelson,ed.,Studies in Contemporary Jewry,Vol.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0. (29)David Golinkin,"Yom HaShoah:A Program of Observance",Conservative Judaism,Vol.37,No.4(Summer,1984),p.57. (30)Ruth Ebenstein,"Remembered Through Rejection:Yom HaShoah in the Ashkenazi Haredi Daily Press,1950-2000",Israel Studies,Vol.8,No.3(Fall,2003),pp.146-147. (31)Jackie Feldman,"Between Yad Vashem and Mt.Herzl:Changing Inscriptions of Sacrifice on Jerusalem's 'Mountain of Memory'",A 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80,No.3(Fall,2007),p.1152. (32)Benzion Dinur,"Problema Confronting Yad Vashem in its Work of Research",Yad Vashem Studies,Vol.1,(1957),pp.9-10. (41)甚至在世俗群体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反对派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要求将纳粹大屠杀与英雄主义纪念日拆分为两个节日:纳粹大屠杀纪念日放在阿布月9日,而英雄主义纪念日放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参见James E.Young,The Texture of Memory:Holocaust Memorials and Meaning,p.271。 (47)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02页。 (48)有关“Shoah”词语在以色列建国初期的推广,参见艾仁贵:《“Shoah”的词源、内涵及其普及化:一项语义社会学的考察》,《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49)这个纪念节日序列还得到空间上的体现:独立纪念日与阵亡纪念日的纪念场所位于耶路撒冷西郊的赫茨尔山,而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作为大屠杀纪念日的纪念场所在毗邻赫茨尔山的纪念之山。 (50)“从浩劫到重生”的专用术语最初由迪努尔1953年4月向议会提出“亚德·瓦谢姆法”议案时使用,参见Dalia Ofer,"The Strength of Remembrance:Commemorating the Holocaust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Israel",Jewish Social Studies,Vol.6,No.2(Winter,2000),pp.38-40。 (51)Don Handelman,Nationalism and the Israeli State,Oxford:Berg,2004,p.97. (52)Avner Ben-Amoa,Ilana Bet-El & Moshe Tlamim,"Holocaust Day and Memorial Day in Israeli Schools:Ceremonies,Education and History",Israel Studies,Vol.4,No.1(Spring,1999),p.272. (53)George L.Moase,Fallen Soldiers:Reshaping the Memory of the World W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78. (5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页。 (55)D.H.Akenson,God's Peoples:Covenant and Land in South Africa,Israel,and Ulst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49. (56)Yael Zerubavel,"The Death of Memory and the Memory of Death:Masada and the Holocaust as Historical Metaphors,Representations,No.45(Winter,1994),p.80. (57)建国初期主流社会以挑剔的态度对待幸存者,谈论纳粹大屠杀成为禁忌。参见Gulie Arad,"Israel and the Shoah:A Tale of Multifarious Taboos",New German Crritique,No.90(Autumn,1983),p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