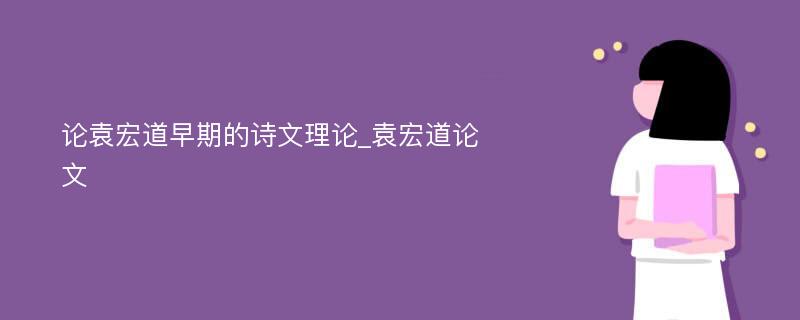
试论袁宏道前期的诗文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袁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宏道是明代诗文流派公安派的领袖,他的诗文理论经纬自成,构建慎密,基本上涵盖了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大端末节,成为这一流派诸多成员所尊奉的圭臬。对袁宏道的诗文理论,尤其是其前期的理论主张进行研讨,对于研究袁宏道,乃至公安派,甚或整个明代文学,都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将袁宏道的诗文创作与诗文理论的产生联系起来考察,更有助于问题的探讨。袁宏道的创作旺盛期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这段时间。在十五年左右的创作盛期内,万历二十九年是一道颇为分明的分水岭〔1〕。 万历二十二年到万历二十八年是袁宏道创作全盛期的前期,这一时期的创作量占其一生创作总量的百分之四十还要多(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二十五年属于袁氏诗文创作的鼎盛时期,其创作量竟占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强)。历经了差不多一年的中衰期之后,袁宏道又开始了他的第二个创作旺盛阶段,时间是万历三十年到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卒于万历三十八年九月),这一时期的创作量约略是总量的一半。这便是袁宏道一生文学创作的大致流程。如若再与他的诗文理论产生的过程作一参照,便会发现二者之间呈明显的正比例关系,即诗文创作的高潮期恰恰是理论产生的旺盛期。袁宏道一生写有四十余篇代表他文学主张的文章(除此之外,尚有一些专门阐述其文学思想的尺牍和诗歌等),前一个创作兴盛期就多达三十篇上下,而鼎盛期竟有二十篇之多。这就足以说明,袁宏道的诗文理论主要产生于前期,又以万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为极盛。
万历二十四年之前,袁宏道尚未形成自己具体的诗文理论体系,但是,这时的袁宏道在其文学道路上已经至少有三次重大的经历:其一,组织城南文社,初显身手于文坛诗苑;其二,数次谒访李贽,结识焦竑,自云为两家弟子〔 2〕,思想观念、文学主张多受其沾溉、滋养,并因之发生变化;第三,荣登进士第,入京谒选时,结识、交游著名文士江盈科、汤显祖等人,文学观念再受陶染。与此同时,袁宏道继公安派的第一个播火者袁宗道之后,将此派的信息公布于世。但总的说来,这时的袁宏道仍处于积聚能量、酝酿新变的状态,检阅他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有两首诗最能说明这一情况。第一首是他万历二十年作于公安的《狂歌》:
六籍信刍狗,三皇争纸上。犹龙以后人,渐渐陈伎俩。嘘气若
云烟,红紫殊万状。醯鸡未发覆,瓮里天浩荡。宿昔假孔势,自云
铁步障。一闻至人言,垂头色沮丧。
袁宏道于万历十六年中举,不久即首次谒访了流寓湖北麻城的李贽,中郎如遇畏友良师,愿执弟子礼。李贽遂将这位心性孤傲、英灵外溢的少年文士视为传薪接火的门徒。从诗中能看出李贽对袁宏道的影响,李氏把“六经”、《语》、《孟》斥为假人之渊薮、道学之口实,中郎则直言“六籍信刍狗”,后来更进一步说“‘六经’非至文”〔3〕。
袁宏道万历二十二年答赠好友李子髯的诗更值得注意,它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此时此地的袁宏道已向搦管作文的经生、展楮赋诗的文士时代告别。如果说此前的袁宏道只会赋诗作文的话,那么从现在起,他又开始了品骘往哲、议论时贤,即评说何(景明)、李(梦阳)的草昧创始之功及可师之处,同时亦不讳避其后学屈理修辞、模拟成弊的现实,可谓具体而微,语语中的。他又鸟瞰时下文坛,断言“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实属高屋建瓴之论。《答李子髯》(其二)之于袁宏道,无异于他即将登坛设坫的宣言书,对于整个公要派来说,创始者袁宗道从此后继有人,独木孤支的局面遂告结束,由他率先揭橥的公安派文学理论的两大主题——反对复古与求新创变——也被袁宏道张扬光大于天下。袁宗道使公安派由阒寂无闻变得初步震响文坛,袁宏道则为之注入活力,使之日臻极盛境地。全诗如下:
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
藻,屈理竟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
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
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袁宏道吏部谒选之后到任吴县,江进之此时担任长洲知县,二人仅隔一锦帆泾,了却公家事后,时常聚首唱和。正是他们两人并肩携手,戮力同心,把公安派推向极盛。袁中道这时南北游历,有时亦至姑苏驻足。其他的热心参与者和支持者尚有王百谷、曹以新、张凤翼、张献翼诸人,他们多是吴地多才多艺的诗文名士,亦时时集聚于袁宏道、江进之周围,推波助澜,摇旗呐喊,再与北京的袁宗道等人遥相呼应,互通声气,公安派因此盛极一时。就袁宏道本人而言,他在公安派的盟主地位已经确立,由此稍后的几个年头就是他创作的鼎盛期,因此他才说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而且是“无日不诗”〔4〕。江进之曾褒评袁宏道此时的诗词、 杂著,说:“大端机自己出,思从底抽,摭景眼前,运精象外,取而读之,言言字字,无不欲飞,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觉者。”〔5 〕创作的极为活跃,促使了文学理论的大量产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又基本上反映了袁宏道全部文学观念的主旨大端,因此,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吴县任上,袁宏道留下了两篇专论诗文的文章,一篇为《诸大家时文序》,另一篇是《叙小修诗》,这是他较早的理论文章。两篇文章的主旨相同,都是大力抨击诗文复古派,同时也提出了多具公安派特色的新变主张。《诸大家时文序》从有关“时文”的论述入题,自然论及“时”与“文”,并提出“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的观点。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立论,时文同样能与古文词一样并属不朽,明代的时文高手瞿景廊、唐顺之诸人,决不减价于首开初唐风气的卢照邻、骆宾王等。那么被复古派念念不忘的古文词又是个什么样子呢?文章从此切入正题:
且所谓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极矣。何也?优于汉谓之文,不文
矣;奴于唐谓之诗,不诗矣。取宋、元诸公之余沫而润色之,谓之
词曲诸家,不词曲诸家矣。大约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天地间真文
澌灭殆尽。独博士家言,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
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而卑今之士,反
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
安知有文!〔6〕
事实诚如袁宏道所言,由于诗文复古主义者只知道文优于汉,诗奴于唐,致使诗不成诗,文不成文。这些叫噪怒张的所谓文坛巨匠们,甚至不明白这样的道理:秦汉文只属于秦汉时代,就像唐诗只属于唐代,宋元词曲只属于宋元一样。他们不知“时”,更遑论知“文”,但却又党同伐异,对那些手眼自出、机轴各异的诗人作家大加摈斥,使之不见齿于词林。这样便只能有一种结果:“天地间真文澌灭殆尽”。因此李贽、徐渭以至公安派的成员们,前赴后继,向复古派营垒发起了越来越猛烈的冲击。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至文”、“真诗”、“真文”的讴歌与呼唤。尤其在公安派崛起文坛之时,此派的成员们更是将徐渭反伪、李贽反假的精神注入文学革新活动之中,使求真主变的文学观念更加凸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袁宏道就强调了“真”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复古派“假骨董”、“赝法帖”式的作品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唾弃。袁宏道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作品与书画等艺术品一样,贵在其真,唯在其真,只有真才能“理虽近腐,而意则常新;词虽近卑,而调则无前”,只有具备了“真”的作品,方能长存天地,流布后世。
袁宏道裒集袁中道诗作,刊刻行世,并作《叙小修诗》。若用同一个标准衡量,此文的价值和重要性远远大于《诸大家时文序》,特别是在揭示公安派的理论主旨这点上,前者较后者更为具体、全面。袁中道是公安派的主将之一,在公安派的兴盛期以及它走向兴盛的过程中,他之于袁宏道如同膀臂,为他的诗作叙,自然要深层次地触及到其文学理论的主旨大端。文章先写小修“少也慧”,“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书”,然后又写小修长大后的情况:
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马塞上,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胜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倾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7〕
从这段文字看,与其说袁中道在评价袁宏道的人格、作品,毋宁视之为一个文学流派的领袖在总体评判此派的作家、作品更合适。自视豪杰,卓立不群,视山林皋壤为文思奥府,引江山之助作诗兴灵区,览山观水,足迹遍天下,深得化育,神为之驰,思为之涌,其结果是诗饶文丰。中郎所言,决非仅仅指小修一个人。人格如此,文风若何?“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情与境会”、“从自己胸臆流出”、“不粉饰蹈袭”,这就是小修作品的特色,亦即其文风特征,这种特征甚至包括作家“本色独造”的“疵处”。不容忽视的是,袁宏道在这里最早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观点,其中“性灵”一词的出现更值得注意。袁宏道首倡“性灵”的同时,江进之亦频频提及“性灵”,在他给袁宏道写的一篇叙文中,“性灵”就出现了六、七次之多〔8〕。显而易见, 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建构中,“性灵”与“真诗”、“真文”、“情”、“境”、“趣”、“韵”等,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袁宏道代表公安派〔9〕标举的“性灵”, 要求诗文作家要具备灵悟颖慧的先天的资质秉赋,以及触物即发、灵动不拘的后天的卓异超群才能。具体到创作上,要捉灵感如逮亡逋,作诗为文,信心随口,如泉自涌,一旦形成文字,更要语直情切,不枝不蔓,意象活泼,灵动飘逸。
由议论小修,袁宏道的笔锋自然转向当时的文坛,他说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摸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然废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9〕
袁宏道仍在抨击复古现象,同时又提出新的见解。诗文复古与新变是后期古典文学创作与理论的重大主题,在明代,这两种取向的对立、交锋更为激烈持久。袁宏道之前,复古派气焰薰天,他们沉湎于“文准秦汉”、“诗准盛唐”的氛围之中,如狂如醉。面对这种现象,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的奋起排击,欲拯救诗文于“敝极”、“澌灭”的困境,并重新赋予其生命的活力,此重任的艰巨性可想而知。袁宏道一语中的,直陈诗文复古派不懂“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的道理,致使诗文“不传”。这正是袁氏“时”的观点的深化和补充,它揭示出文学的发展变化离不开时代的发展变化,秦汉时代产生了优秀的散文作品,盛唐时代又取得了诗歌发展的辉煌,明代已经不再是秦汉和盛唐,时代的更替必然引起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变革。基于此,明代的作家们要“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而不应该用一成不变的标准去与秦汉文盛唐诗争高下、较优劣。唯其如此,才能创作出体现明代特色、无愧于有明时代的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品自然会因为自己鲜明的特色而与秦汉文、盛唐诗共存于天地之间。袁宏道就是这样一位为实现这种目的而倾尽全力的作家。
诗文复古派使得诗不成诗,文不成文,当然无法让明代诗文像盛唐诗、秦汉文那样流传后世。难道明代就果真没有堪作楷模、传布后世的作品了吗?回答是否定的。被明代人称作“我明一绝”〔10〕的民歌,即袁宏道屡屡提及的《擘破玉》、《打草竿》之类,就正是这样的作品。正统诗文深陷厄运,在劫难逃,有眼光、有主见的作家早在袁宏道之前就把目光投向了具有远大前途的民歌俗体。袁宏道等人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之。他本人就曾身体力行地创作类似民歌俗体的《竹枝词》,并褒评这样的作品“不无过巧,趣却不乏”〔11〕。袁宏道重视并褒扬民歌,是因为他看重民歌的情趣,而“趣”在复古派的作品中却是踪迹尽绝的。“各极其变,各穷其趣”,“变”在袁宏道的文学观念中贯穿始终,而“趣”同样也是其理论主张中的要点之一。“变”、“趣”又必须有一个基础,有一个内容,这便是“真”。诗文复古派的作品有着明显的弊端、失误,其突出表现便是少变乏趣,而其病根就在于与“真”无缘。袁宏道之所以要称扬《擘破玉》、《打草竿》、《竹枝词》之类的民歌俗体,正是着眼于它们的“真”。民歌是真声,首先是因为作者,即“闾阎妇人孺子”们都是“无闻无识”的“真人”,唯其“无闻无识”,才不像诗文复古作家那样为了滥竽充数于诗文作者的行列而挦撦秦汉、生吞盛唐。民歌是“真声”,因为是由“真人”所写,那么它有什么特点呢?其一,“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其二,“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细究这两点,都与“真”密不可分。
“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12〕小修的诗作能否符合“真诗”的要求?袁宏道说: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金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沈湎嬉戏,不知樽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
感。〔13〕
这就是袁宏道笔下的袁中道形象,他贫病愁苦,又哀生失路,将如此遭遇运之于诗,因此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故是“真声”无疑。袁中道的诗歌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公安派诗歌的主流,因而便受到与此大异其趣的复古派的指责、唾骂。也许袁宏道听到了别人用“太露”来指斥袁中道的诗作,一向连小修等人“疵处”都喜欢的他,自然要为之辩护:“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14〕更何况“峭急多露”又是自屈原以来所形成的“楚风”呢!三袁昆季,尤其是袁宏道,向以“风骨棱棱”、狂傲不拘的楚人自我标榜,而以“楚人”为中坚的公安派,具备“峭急多露”的诗文风格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公安派的开山立宗者袁宗道倡言信于信口,何尝不是“露”。他重视“辞达”〔15〕,这“达”显然与袁宏道的观点同出一辙。
在上述理论主张出台前后,袁宏道曾致信丘长孺,自言“近作颇有得意处”,足以说明他此时的创作情况。袁宏道在信中称赞丘长孺的诗“无一字不佳”、“古质苍莽,气韵沉雄,真是作者”,并认为丘氏的诗“当为诗中第一,见在未来第一”。袁宗道也曾评论丘长孺的诗,说:“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丘长孺氏之诗也。”〔16〕这与袁宏道的见解颇为相似,与他下边的观点更是多有相同相通之处: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诗也,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钱、刘,下迨元、白、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宋亦然。陈、欧、苏、黄诸人,有一字袭唐
者乎?又有一字相袭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结绳鸟迹病《三百篇》耶?果尔,反不如一张白纸,诗灯一派,扫土而尽矣。夫诗之气,一代减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17〕
“物真则贵”,诗文亦然。“真”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犹如人各有面,面各有异。各个朝代的诗文也各有其“真”,因而可以并行不悖,而那种欲“概天下而唐之”的复古行径显然是错误至极的。最后,袁宏道进一步阐述古与今的关系:“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古不必高,今不必卑。
万历二十五年春,袁宏道不堪吴县任上的毒苦(他自比为“如猢狲入笼中,毛爪俱落”,“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连上七牍辞去吴令,暂时得以纵身大化,身心为之解脱。再加上遨游吴、越,仙山灵水助其文思,他的创作仍处于旺盛期,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也不乏佳篇,其中以谈“趣”为主的《叙陈正甫会心集》最为突出。“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这是袁宏道较为具体地谈到“趣”。得到这种“趣”无疑是很难的,时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虽然费尽心机,如“辨说书画,涉猎古董,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但往往仅涉及“趣”之皮毛,而与其精神多有睽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趣”在何处?如何得“趣”?袁宏道说:
……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于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以无品也,品愈卑故所求愈下,或为酒肉,或为声伎,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自以为绝望于世,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18〕
中郎所谓的“趣”,不外乎是一种先天、自然的情趣,最忌后天的尘污理障。得“趣”之人,应该不强己性,“率性而行”〔19〕。具体到作家身上,要求比普通人更高,他要葆有赤子、婴儿之心,率心而动,任性而发,不假雕饰,不事做作。“趣”不仅部分地反映出了袁宏道人生观念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基本上映照出了他文学追求中的审美情趣。
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提出“趣”之理论主张后,仍保持着诗文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旺盛势头。在此前后,他经过绍兴时,从乱文集中发现了徐渭的的作品,这对他十分重要,称扬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李为之短气。”〔20〕徐渭高洁兀傲、傀然独立的人格精神,以及猛烈抨击复古逆流的行动,都鼓舞、激励着袁宏道,他的创作因之发生变化。袁宏道评价自己此时的诗歌说:“其中非惊人语,则嗔人语,嗔人者为人所嗔也。”〔21〕他还说:“余论诗多异时轨,世未有好之者”,“凡余所摈斥诋毁,俱一时名公巨匠。”〔22〕袁宏道并未因为“为人所嗔”而畏葸裹足,而是依然如故地进攻“如今作假事假文章”〔23〕的复古派营垒。他在致文友张献翼的信札中说: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日博识;用得几个现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24〕
袁宏道旧题重提,主要仍围绕着创变和反对复古立论,如“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不曾依傍半个古人”等。对复古派的挞伐虽非首次,但如此切中要害,痛快淋漓,却又是袁宏道的理论文章中所少见。袁宏道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有“矫枉之过”的说法。他对复古文人的行径深恶痛绝,因此大力矫正,虽过而不辞。在这同时,他又为自己能创制出“中郎自有之诗”而沾沾自喜。与此相承接,袁宏道又提出了“古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古不可优,后不可劣”、“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等在于重申自己主张的观点〔25〕。由此而后,他又进入了创作前期的另一个阶段。
万历二十七年前后,袁宏道因兄召父逼,结束了决绝卸任吴县县令之后“一味以观山水为课”、“快活无量”〔26〕的纵放生活,再次偕袁中道进京候调,不久被授顺天府学教授。稍后江进之亦奉调入京,“酒坛诗社,添一素心友”〔27〕。一段时间里,北京城内可谓群贤毕至,众杰咸集,三袁昆季、江进之、黄平倩、潘士藻、谢在杭、顾天俊、李腾芳等人汇聚京华,济济一堂,蔚为大观,真正称得上是公安派主将、羽翼及其支持者的大聚会。此时的袁宏道思如泉涌,手不停笔,“野语街谈随意取。”,“新诗日日千余言”。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近日与舍弟日课诗文一篇,暇则读书,胸中浩浩,如涨水忽决,云卷雷奔。每一篇成,兄弟自相叹赏,如蜣蜣之自爱其转,人固以为臭秽,勿之恤也。家兄近作,比往大进。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28〕
在同一时期另外的文章中,袁宏道也不时流露出同样的想法,如他愿与江进之等人联手,“并力唤醒”被复古派“蔽锢已久”〔29〕的人们。他直面“摹拟之流毒”,决心“一易其弦辙”〔30〕。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此时的袁宏道雄心勃勃,信誓旦旦,大有不干出一番改变文坛局面的事业便不罢休的气势,纯是一副“末季先驱”、承天大任的派头。在他看来,“扫时诗之陋习”、“捣钝贼之巢穴”,舍我其谁?这个时候的袁宏道,确是“胸中浩浩”,文思“如涨水忽决”,光是评诗论文的文章就有六七篇之多,更勿庸提及那卷帙繁富的诗、文、尺牍、游记、叙文了。
在这一时期的理论中,袁宏道主要是指陈诗道的寝弱,即反对复古,同时仍在重复或重新提出新变的主张。在颇有代表性的《叙姜陆二公同适稿》中,袁宏道针对苏郡诗文深受复古流毒侵害的现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七子中的徐祯卿、后七子的执牛耳者王世贞,以及后七子后进王世懋等人,虽然“高自标识”,用“大声壮有恰当语”稍稍改变了“吴中绮靡之习”,但实际上仍与“济南(李攀龙)一派”同属一路货色,是“剽窃成风,万口一响,诗道寝弱”的根源性因素,是“递相临摹”,“共为一诗”,作“诗家奴仆”的始作俑者〔31〕。就事实而言,袁宏道这种观点的针对性意义已经超出了苏郡、吴地,因此其影响极为广泛、深远。钱谦益对此曾有的当的评论,他说:“袁宏道)论吴中之诗,谓先辈之诗,人自为家,不害其为可传;而诋诃庆、历以后,沿袭王、李一家之诗。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32〕与此相发明的是,袁宏道又借梅蕃祚之口,道出了诗坛的芜秽状况,梅氏说:“诗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妪之傅粉;其能独抒己见,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者,余所见盖无几也。”〔33〕在这一时期内,袁宏道还提出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观点,如:“善为诗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34〕、“穷新极变”〔35〕、“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唯识时之士,为能隄其聩而通其所必变”、“信腕信口”〔36〕,等等
袁宏道万历二十七年前后的文学理论中,有一点颇为引人注目,那便是他对宋代诗文的大力张扬,以及对以苏(轼)、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诗文作家的极力推崇,尤其是对苏轼的推尊有加。袁宏道的“每以长苏自命”,公安派后期健将曾长石就认为“中郎为子瞻后身”〔37〕。万历二十五、六年间,袁宏道就说“始知苏子瞻、欧阳永叔辈见识真不可及”〔38〕,并进一步指出:“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39〕袁宏道为官北京时,曾写信给梅国桢,其中一段有关欧、苏的言论更为详尽,移录如次:
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坡公诗文卓绝无论,即欧公诗,亦当与高、岑分昭穆,钱、刘而下,断断乎所不屑,宏甫选苏公文甚妥,至于诗,百未得一。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苏公之诗,出世入世,粗言细语,总归玄奥,恍惚变怪,无非情实。盖其才力既高,而学问识见,又迥出二公(李白、杜甫)之上,故宜卓绝千古。〔40〕
由此看出,袁宏道是何等推崇宋代的特别是苏轼的诗文。因此,袁宏道说宋人诗文“超秦、汉而绝盛唐”,为“巨涛大海”〔41〕,并认为以汉、唐相标榜的北地(李梦阳)、太仓(王世贞)辈“不敢与有宋诸君子敌”〔42〕,等等,都是情理中事。
袁宏道颂扬宋代作家及其作品,是建立在“遍阅宋人诗文”基础之上的,因而有的放矢,言之有据:
宏近日始读李唐及越宋诸大家诗文,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颦乎?〔43〕
袁宏道不反阅读宋人诗文,还加以评点,足见他对宋人及其诗文的钟爱之深。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更加深刻地体味到欧、苏诗文的绝妙之处。他说:
近日最得意,无如批点欧、苏二公文集。欧公文之佳无论,其诗如倾江倒海,直欲伯仲少陵,宇宙间自有此一种奇观,但恨今人为先人恶诗所障难,不能虚心尽读耳。苏公诗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变怪过之,有天地来,一人而己。……韩、柳、元白、欧、诗之圣也;苏,诗之神也。彼谓宋不如唐者,观场之见耳,岂直真知诗何物哉!〔44〕
“宇宙间自有此一种奇观”,“有天地来,一人而已”,真是无尚的褒评。
袁宏道为什么会对宋代作家及其作品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呢?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格精神多有相通之处。他们都追求放达自任、淡泊闲适、超脱俗世的人生情趣,可谓异代同调。第二,思想观念颇多契合。如他们有共同的倾向,即思想中杂糅儒、释、道诸家之精粹,对禅理尤其深研细究。第三,文学理论主张前后合拍。袁宏道主变求新,不事模拟,提倡有感而发、写己真情,要求诗文畅达显露,等等,与宋人尤其是苏、欧诸人,多有相通之处。第四,袁宏道看重“而宋之不唐法”,宋人确又能另辟天地。明代诗文复古派文准秦、汉,诗祧盛唐,大肆叫嚣“宋无诗”,作为反拨,袁宏道用抬高宋代诗文的做法与之对抗,亦即“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
以上所论,便是袁宏道万历二十九年之前,即他前期诗文理论的大致情况。经过万历二十九年短暂的沉寂之后,袁宏道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建树进入了后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袁宏道创作了大约十篇评诗论文的文章,以及一些相关的诗歌、尺牍等。综观这些作品,它们基本上仍在贯彻着袁宏道诗文理论的两大主题:反对复古和求新主变。但不可忽视的是,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中的进攻势头已明显减弱,求新主变的色彩也在淡化。甚至逐渐出现了变调、转向的苗头,其标志便是他对自己前期理论的反思和怀疑,这已属于性质上的变化,它直接开启了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端绪。
注释:
〔1〕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袁宗道因积累所致, 卒于北京任上,这对袁宏道打击很大,一段时间内,他不能从失去既是同胞兄长又是文坛师友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创作几近搁笔。大约过了一年,即万历二十九年后,其创作再入佳境,但风格、特征已与前期多有不同。
〔2〕《送焦弱侯老师使梁,因之楚访李宏甫先生》。
〔3〕《听朱生说〈水浒传〉》。
〔4〕《伯修》。
〔5〕《锦帆集序》。
〔6〕《诸大家时文序》。
〔7〕〔9〕〔12〕〔13〕〔14〕《叙小修诗》。
〔8〕《敝箧集叙》。
〔10〕陈宏绪《寒夜录》。
〔11〕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初集)第204页。
〔15〕《论文》(上)。
〔16〕《北游稿小序》。
〔17〕《丘长孺》。
〔18〕《叙陈正甫会心集》。
〔19〕《识张幼于箴铭后》。
〔20〕〔21〕《吴敦之》。
〔22〕〔33〕《叙梅子马王程稿》。
〔23〕《江进之》。
〔24〕《张幼于》。
〔25〕〔38〕《江进之》。
〔26〕《管东溟》。
〔27〕〔29〕与江进之廷尉》。
〔28〕《答李元善》。
〔30〕《冯侍郎座主》。
〔31〕《叙姜陆二公同适稿》。
〔32〕《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34〕《叙竹林集》。
〔35〕《时文序》。
〔36〕〔39〕《雪涛阁集序》。
〔37〕康熙本《公安县志》卷十一《袁宏道传》。
〔40〕《答梅客生开府》。
〔41〕《答陶石篑》。
〔42〕《答梅客生》(又)。
〔43〕《冯琢庵师》。
〔44〕《与李龙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