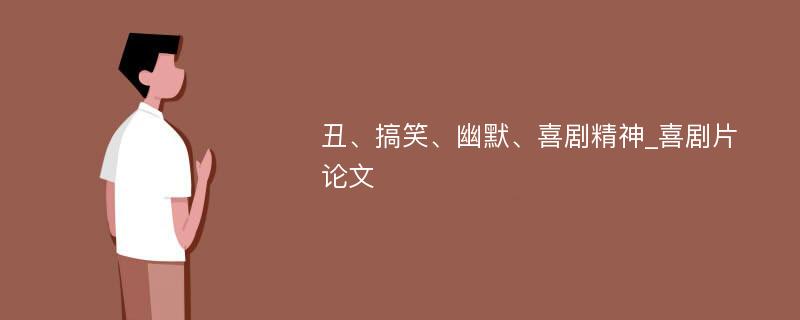
丑、滑稽、幽默与喜剧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滑稽论文,喜剧论文,幽默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作为喜剧性的三基因:丑、滑稽、幽默,其形式指归是以“笑”为载体,从而传达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滑稽是冲突事物的喜剧再现;幽默是一种超脱而萧洒的人生态度,如果滑稽以“肯定的事物”的方式出现,那么此非“讽刺”,而为“幽默”。现代“审丑”学,已不仅限于美丑对立关系,而以其哲学和宇宙的沉思与多元而开放的创作,为我们重新构建“喜剧精神”的内核。只有喜剧精神,才能将丑、滑稽、幽默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揭示客体对象的丑与环境的关系,使丑显示出喜剧性。
关键词 丑 滑稽 幽默 喜剧精神
笑的喜剧效应
无疑、丑、滑稽、幽默是构建喜剧理论的重要基因。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课题:什么是喜剧精神?它与丑、滑稽、幽默之间的关系如何?
作为喜剧性的三基因:丑、滑稽、幽默,其形式指归是以“笑”为载体,从而传达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喜剧精神包含各种不同性质的笑。那么笑又从何而来?自柏拉图到柏格森,众说纷纭。其中黑格尔的观点,颇有可取之处。他说:“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任何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对比,如果显出矛盾或不相称,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自我否定,或是使对立在实现中落了空,这样的情况就可以成为可笑的。”[①]即本质与现象之间以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必然引起滑稽可笑。因为本质一旦呈现,则丑恶事物就原形毕露。动机卑劣而又不择手段,在其目的实现过程中必然处处碰壁,贻笑大方。莫里哀《伪君子》中的答丢失,妄想霸占奥尔贡的家产和他的妻子,尽管用尽心机,到头来落个可耻下场。在果戈理《钦差大臣》中,百般逢迎赫利斯达柯夫的市长和家属以及当地官吏等,最后听说真的钦差大臣即将到来,才知自己上了大当,哭笑不得。
以社会矛盾为基础,组成了丰富多采的喜剧冲突。亚里士多德指出:“喜剧以下劣的人物为摹拟对象”(《诗学》),然而“‘下劣’不是指一切‘恶’而言,滑稽不过是‘丑’的一种,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诗学》)当然,喜剧中的矛盾,还可能包含着性格内部的不协调及自我矛盾。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丑强把自己装成美”则成为喜剧性的。这种“丑假装为美”的不协调,乃是“否定事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另一方,喜剧中的肯定人物身上,其性格中也不乏不协调的矛盾,如李逵自以为成竹在胸,实际上却是犯了错误(《李逵负荆》)。在这种矛盾中包含着性格内部的矛盾:正直、勇敢、果断而又偏信、鲁莽和粗率。《乔老爷上轿》的主人公是一个举人,满腹学问却又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刚直豪爽,却又迂腐笨拙。
喜剧效应的出现,固然与丑、滑稽、幽默三基因所产生的“笑”是分不开的,但这种笑是有着鲜明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从而构成所谓的“喜剧精神”。法国戏剧家博马舍在他的《费加罗的婚姻》里,站在被压迫的费加罗和苏珊娜一边,赞美他们坚定的反抗精神和机智的斗争艺术,讽刺伯爵机关算尽,自己反到落入陷井,从而构成一组生动的喜剧情节,使观众为费加罗和苏珊娜的胜利而欢笑;同时嘲笑枉费心机和丑态百出的伯爵的狼狈态和尴尬相。
滑稽的喜剧特质
西方美学家常把喜剧的要素之一“滑稽”当作喜剧的同义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把“滑稽”纳入喜剧的范畴。他认为“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但“丑”并不一定就是滑稽的,“只有当丑力求自炫为美的时候,那个时候丑才变成了滑稽。”根据此逻辑,他又指出:“一切无害而荒唐之事的领域,就是‘滑稽’的领域,荒唐的主要根源,在于愚蠢、低能。因此,愚蠢是我们嘲笑的主要对象,是滑稽的主要根源。”其实质是讽刺,将之称为“讽刺喜剧”,用来针对那些危害社会的各种弊病,揭露那些丑恶的、反动的、腐朽的社会现象。我国的传统,就没有把滑稽作为引起喜剧效果的唯一因素,没有把滑稽等同于喜剧性。“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崔浩语)“滑稽,犹俳谐也。滑读如字,稽音计也。以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也。”(姚察)[②]虽解释不一,但都强调言语善辩之意。
刘勰的《文心雕龙》已经将滑稽与具有喜剧性的诙谐作了明显区别。他列出专篇对“谐隐”进行系统论述,把滑稽主要理解为形体外表的可笑性,充分肯定其作用。鲁迅对滑稽的描述更接近于我国的传统。他说:“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的身份而出现了,把这件事变为滑稽。”[③]
那么,“滑稽”的主要审美特征是什么呢?它与喜剧性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滑稽作为喜剧形态,它不象讽刺、机智、幽默那样涵有较多的理性意蕴与审美主体的心理烙印。但是,它的审美特征仍然体现了主客体之间喜剧结构对应关系激活的基本特质。一方面,无论审美主体欣赏滑稽情境,还是创作主体创造滑稽情境,都或多或少地激发审美主体与创作主体的某种意志与感情。没有情感的审美与创作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审美客体的滑稽对象或多或少地与一定的社会意蕴有联系,或多或少地与对象的内在性格有联系。否则,滑稽仅仅滞留在可笑性上而不具备喜剧性,也就称不上具备所谓真正的喜剧精神。
柏格森在《笑》中引用了大量滑稽形态,以论证他的“生命机械化”说。康德曾举出印度人惊讶啤酒冒泡沫的例子,来论证其实是期望突然落空的理论。里普斯举出大人戴小帽,小儿戴大帽,来说明笑来自“大”“小”的悬殊。这些都具有滑稽性,但都是喜剧的初级形态,没有多少深刻的意蕴。如果把它们与卓别林某些滑稽情景对比更可以看到这一点。《摩登时代》里夏尔洛在厂里的工作是永不停地拧紧一颗颗螺丝帽,神经紧张、疲劳过度,走在路上竟把行人衣服上的纽扣当作螺丝帽去拧,结果被送到疯人院。这里,滑稽的深处蕴含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滑稽已经与讽刺、幽默等喜剧形态融合一起了。
幽默的自我超越
16世纪末,英国著名剧作家本·琼生将幽默带进艺术领域,并从人性理论上加以阐释。一百年后,英国威廉·邓波儿爵士在《诗论》中,不是单从生活结构着眼,而是从社会环境、自然条件和民族特性等方面,来阐述幽默的意义。1927年,弗洛伊德写了一篇《幽默》专论,试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研究这一喜剧因素,他认为幽默态度来自超我与自我的控制,就像父母对于孩子一样,幽默家对于人间的苦恼,有时也象大人对待儿童。他说:“我们如果承认幽默态度的根源在于幽默家已将自我的专注移置在超我身上,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关于幽默态度的动态解释。超我经过这样充实和光大之后,就会觉得自我渺乎其小,而自我的利益也就微不足道。”
把幽默作为喜剧形态研究的论说很多。别林斯基评论果戈理时谈到有两种幽默,一种是“苦辣的、恶毒的、无慈悲的幽默”,这实质上是讽刺;另一种是“一种平静的幽默,在愤怒中保持平静,在狡猾中保持仁厚的幽默”,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形态。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幽默的人天性委婉,富有激情而又善于观察,正直而又善于自嘲。这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弱点“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无非是因为在他看来,“它们是与一般的人类尊严相矛盾的。”[④]英国美学家梅瑞狄斯认为:“幽默之所以不同于它所属的喜剧性,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某种可笑的乖讹之处时,幽默在我们身上激发起来的是同情的感情。”[⑤]
幽默之所以成为构建喜剧精神的深层内涵,是因它是一种超脱而潇洒的人生态度。幽默的人在观察世界时从理性出发,但更带有丰富的感情;他遇事都要设身处地,在严肃中蕴藏着宽厚仁爱;心胸博大,处逆境而泰然自若;在嘲笑别人荒谬愚蠢的言行时,同时嘲笑自己的缺点错误;常存悲天悯人的心情,又有积极乐观的精神。他并不鄙视别人身心的缺陷弱点,所以显得豁达乐观。幽默并非单纯的滑稽或荒谬,虽然引人发笑,却在笑中蕴有更大的社会意义,令人浮想深思。
幽默与“滑稽”的对应关系在于,如果滑稽以“肯定的事物”的方式出现,形成无害的荒唐(如《李逵负荆》),那么这种“滑稽”并非就是“讽刺”,它的表现主要是“幽默”。“讽刺喜剧”和“幽默喜剧”虽然都以“滑稽”为特征,但后者却不是针对反动、腐朽的丑恶现象,而是或对生活现象中某种局部性的缺点进行善意的嘲笑,或表现人物的目的和行为方式的矛盾、人物性格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现象也可以构成“滑稽”,显得荒唐可笑。简括地说,“幽默”中往往渗透着对对象的更多同情心。不过“嘲笑性”的“幽默喜剧”也往往被列入“讽刺喜剧”的范畴。比如我国作家丁西林的喜剧风格,素以洗练明净机智幽默著称。他的作品不以热闹的情节取胜,而以隽永的语言见长,他所要求的效果不是哄堂大笑,而是会心微笑。从他的《一只马蜂》到《妙峰山》,他对剧中人物并非没有爱憎,但是他的正面人物既无丰功伟绩,他的反面角色也不罪大恶极。他常常是理智胜于情感,冷静多于热烈;虽歌颂而有节制,虽讽刺却不辛辣,加以他的喜剧结构严谨、语言机智,因此他的作品就给人以明快之感和幽默之趣。
从严格意义来说,幽默是喜剧诸因素中最基本的元素,不论讽刺也好,还是嘲笑也好,或是调侃、自嘲、怪诞等等,幽默之本身正是俯瞰这喜剧世界的审美心态,其目的如马克思所说“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审丑学发凡
喜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同“丑”结下了不同寻常的亲缘关系。丑很早便悄悄叩开艺术美的大门,显示出它的独有魅力。可丑是什么,却象幽灵一样扑朔迷离。亚里士多德说:“滑稽是丑的一个分支”,滑稽性的丑“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现成的例子为滑稽面具,它又丑又怪,但不使人痛苦。”[⑥]
正如里普斯断言,“丑”只是一种“美”的陪衬而已,这虽有一定道理,但毕竟不免单一,并未能揭示出“丑”的美学内核。雨果也同样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古老庄严地散布在一切之上的普遍的美,不无单调之感,同样的印象总是重复,时间一久也会使人厌倦。崇高和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于是人们就需要对一切都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稍息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更新鲜、更敏锐的感觉朝着美上升。”[⑦]一般说来,作为畸形、缺陷的断臂伤残人的形体是不美的,而维纳斯由于那断臂反而形成了难以言传的美。东施并不丑,西施之颦无疑是美的,但“东施效颦”的两者不谐调组合却呈现出丑。只有将丑放在主客体的社会实践关系中考察,才有可能使探索沿着正确的路线,逐步接近真理。如把丑放在特定的关系中考虑,可以看到丑与美的相互转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潜在着某种必然性。莱辛说正是阿芙洛狄特这位司掌着全部感情的美神,挥动着自己的美臂,化腐朽为神奇,化肃杀为蓬勃,化苦痛为欢乐,化激愤为微笑,……一句话,化丑为美。歌德宣称:“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⑧]所以在歌德笔下,就反映了人类感情心理两极的共存,虽然“美与丑从来就不肯协调”,却又“挽着手儿在芳草地上逍遥”[⑨]。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现代“审丑”学,已不仅限于简单的美丑对立关系,它远远突破了喜剧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其哲学和宇宙的沉思与多元和开放的创作,为我们重新组合了“喜剧精神”的内核。流行于西方的表现主义艺术、存在主义文学、黑色幽默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等,往往更富于喜剧性,其人物都往往滑稽地类乎丑角。当然,由于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这里的喜剧都是一种广义的象征主义喜剧,因而它所讽刺的,不是什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具体),而是普遍环境的普遍性格(一般)。
毫无疑问,现代艺术家们出于他们的逆反心理,在那个被他们认为是颠倒了的世界上,把自己的艺术注意力也颠倒一下,反古典之道而行,怀着悲愤的心情与努力重建人类的审丑力。他们要借着这种审丑力,把所体验到的被认为是本质意义的丑在诗行、画布、乐谱、舞台……上突出地反映出来,从而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诗情、画意、乐思、剧情的丑诗、丑画、丑乐和丑戏剧,总而言之,丑艺术!现代西方的艺术才情,恰恰表现在敏锐的审丑力上。他们决不愿意被囿于“美的圈”(鲁迅),而偏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传统以为不可以表现的鼻涕、大便、癞头疮、毛毛虫上。这样,“丑”的概念就具备了历史积淀于其中的丰富内涵,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迄今为止西方感性心理的总结。
正因为有了这种满眼皆丑的目光,现代艺术家们怎能不把他人看作地狱(萨特),把自我看成荒谬(加缪),把天空看作尸布(托马斯),把大陆看作荒原(艾略特)呢?他们怎能不把整个人生及其生存环境看得如此阴森、畸形、嘈杂、血腥、混乱、变态、肮脏、扭曲、荒凉、苍白、孤独、空虚,怪诞和无聊呢?正如尤内斯库所说,《秃头歌女》作为喜剧,表现的是不常见的事物,“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明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现实和一切语言都似乎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既然一切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使人付之一笑之外,还能剩下什么可能出现的反应呢?”[⑩]荒诞的戏剧家亚达摩夫在自杀前不久,曾惨淡地说:“一切人类的命运同样是徒劳无益的。无论断然拒绝生活或是欣然接受生活,都要通过同一条路走向必然的失败、彻底的毁灭。”正是这种毁灭感、末日感,使得人们在不同路上殊途同归,因而使得悲剧与喜剧殊途同归了。正是西方现代心灵中荒诞的现实,导致了这种荒诞的戏剧家对戏剧的荒诞认识,导致了这种为审丑学所独有的悲剧性的喜剧,喜剧性的悲剧。
走近喜剧精神
凡是丑的艺术作品,都可以说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作品,是从西方现代的、悲观感性心理中流露出来的“异化”世界的贴切象征。包含丑的喜剧形象的审美本质不是丑,也不是丑与喜剧精神的简单之和,而是丑与喜剧精神融合而成的新的有机审美形态。喜剧精神是使丑显现出喜剧美的火光,没有它,丑只能在美的阴影下徘徊。阿Q头上的癞疮疤只有在鲁迅的喜剧性精神的照耀下,才能在文学史上放射出喜剧性的光辉。否则,癞疮疤不论生在谁的头上,总为人所嫌弃和厌恶,更谈不上引起世人的注目,起到令人惊醒、感奋的审美效果。
诚然,喜剧精神是人类智慧的高度显现,人类智慧的发展与人类自我意识紧密相连。智慧是喜剧精神的必备条件,这正是世界上众多理论家把喜剧与智慧放在一起论述的内在逻辑。喜剧精神只在人类之间相互交往的活动中产生。人类在那异常艰苦的人与自然斗争的社会实践中发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孕育着自身的喜剧精神。
只有喜剧精神,才能将丑、滑稽、幽默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喜剧精神才能真实揭示客体对象的丑与环境的关系,使丑显示出喜剧性,就如罗丹所说的,喜剧精神是点“丑”为美的“魔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吞噬人们心灵的腐朽意识的霉菌、那种自大与自卑、排外与媚外,麻木与狂热、贪婪与自私……,无疑都是与社会主义阶段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丑恶现象。同时,又是人类从旧社会脱胎而进入新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善于认识自我、解剖自我的喜剧精神能够揭示出这些丑的灭亡的必然性。客观的丑就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世界历史发展变化趋向的联系中显露出可笑的喜剧性来。
只有喜剧精神,才能使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渗透在丑的对象之中,让丑的否定与理想的肯定统一起来。丑的客体经过创作主体加工而成的喜剧性的形象饱和着创作主体的审美理想、爱憎褒贬或溢于言表,或深藏底层,使人感受到丑的衰亡与理想实现的必然。出卖耶稣的叛徒犹大的灵魂令人颤栗,表现在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中,叛徒侧身后倾,右手紧握钱袋,神态惊惶、畏缩。作家的审美理想如聚光灯一样将丑笼罩,丑的形态在强烈理想之光的烧灼下失去原先的恶之力,丑被鞭挞得体无完肤,永远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丑的否定与理想的肯定使主体的心灵得到“美”的升华。
只有喜剧精神,才具有无情的自我否定力量。喜剧精神不仅要求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还要求人类对其本身存在着的一切丑的无价值的东西,进行无情的剖析和否定。巴尔扎克所同情的对象是他隶属的贵族阶级,但对于这个阶级暴露出来的腐朽、丑恶,他敢于正视,把它们撕破公诸人世间,并以“喜剧”的名称给予尖刻辛辣的嘲笑。鲁迅不遗余力地扫除积淀在民族心理上的污垢,纵横恣肆地刺破生长在人类肌肤上的一个个脓疮毒瘤,又时时毫不留情地解剖自我。这就是伟大作家所具备的无情否定自我的喜剧精神。只有否定自我,人类才能向自己的过去诀别;只有否定自我,人类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91页
②转引自任二白《优语集·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页
④《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4—95页
⑤转引自《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223页
⑥《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6页
⑦《西方文论选》下卷,第185页
⑧《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辑,第282页
⑨《浮士德》,董问樵译,第509页
⑩《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第168页
标签:喜剧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