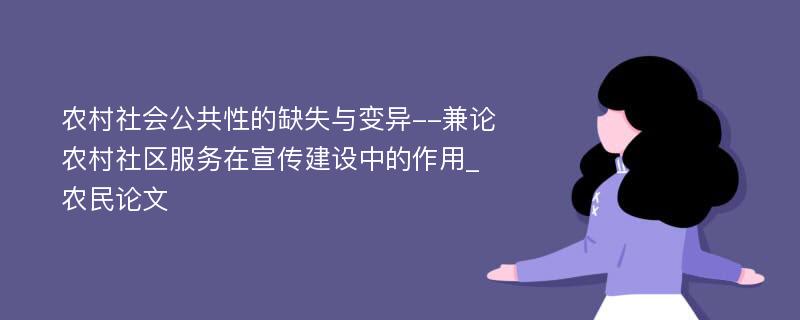
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与变异——兼论农村社区服务在建构公共性上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社区服务论文,社会公共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引发农村社会碎片化和农民群体原子化,农村社会公共性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失。农村社会公共性蕴含在它的外化或物化形式内,“细”且“无声”的流失一般不会即刻解构农村社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性流失将缩小农村社会公共空间,损耗农村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农村社会公共性是农村场域中不同社会主体协调合作的关联属性和建构有序社会结构的调节手段,它与政府、社会“同时在场”,并赋予它们诸多公共责任。农村社会公共性一旦流失,所有为农村社会繁荣稳定和居民生活幸福所做的努力都将付之阙如。因此,面对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变异及其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巨大解构力,农村社区建设者除了要慎重对待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变异外,还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建构农村社会公共性,以减缓公共性流失,恢复公共性活力。 一、农村社会公共性的识别 学者们对农业社会或传统农村社会有无公共性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在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共同性’(common)的内容,但是,却没有公共性(public)问题”(张康之,2007)。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农业社会中人的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的这种总体上的孤立性与分离性,并不表明其内部就没有公共性问题”(胡群英,2013)。面对如此迥异的看法,不能做简单的判别,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学者们认为农业社会没有公共性的理由是,农业社会的公共部门尚未完全从私人部门分化出来,公共行政服从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代表全社会利益。基于此,张雅勤(2012)强调,由于农业社会只存在统治集团内部的共同利益,没有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在农业社会阶段谈行政公共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观点从行政管理视角检视公共性是否存在,认为只有进入工业社会后,有了公共行政部门的政府,才出现公共性和公共性问题。而认为农业社会存在公共性的学者一般从公共哲学角度解读公共性的内涵,将公共性视为人类群体存在和开展群体活动的基本属性和必要条件。这个意义上的公共性缘起于人性,是一种社会公共性,具有普遍性、共享性、公平性等特性(袁祖社,2007)。 社会学中的“公共性”,不同于行政学与管理学中的“公共性”,其内涵较为宽泛,更接近公共哲学意义上的社会公共性,其简约内涵是在公共领域中“为人所见、所闻”的“任何东西”(阿伦特,1999)。在此,笔者有必要提及黄显中对公共性的解释。黄显中(2004)把公共性划分为自在的公共性和自为的公共性,认为自在的公共性作为一种性质存在于一切公共事务中,只要有公共事务的存在,就应该有公共性的存在;而自为的公共性是公共权威需要利用的或经专家智慧加工的,指“按公共性逻辑处理公共事务”。自在的公共性和自为的公共性并非对立,在日常管理中,公共权威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达到自为的公共性与自在的公共性相符”,实现“公共事务的自在自为的公共性”。自在的公共性与自为的公共性的划分,糅合、折中了行政、管理、哲学等学科的公共性范畴,使公共性的社会功能更具有普适价值,也便于将公共性引入农村社区建设与服务研究中。由此可以推定,无论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还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社会,农村社区原本就存在大量的公共性,并且,这些公共性是农村社会建设、农村社会管理等公共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公共性广泛存在于农村社区中,农村社区的温馨、和谐主要得益于公共性功能的彰显。相比于城市社区,中国传统农村社区自成一体,其特性类似于滕尼斯所描述的“天堂”共同体,是自然而生的,由具有同质性和共同性的熟人构成,居民“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有“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膝尼斯,1999)。它建立在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沾亲带故,在共同的风俗、习惯、礼仪的规约下相互交往,和睦相处,共同生活,从事着基本相同的农业生产劳动。恰如鲍曼(2003)所言,这个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如果“有人跌倒了”,其他人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重新站立起来”。因此,人们之所以能在农村社区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主要得益于共同体“合乎情理”的公共空间,以及社区共同利益和社区认同造就的“人情味”,它使社区居民自觉、自愿地从各个分立的私人空间或家庭走出来,参与公共事务协商,进行公共性活动。 二、农村社会公共性样态及其流失 根据对公共性概念的简约理解,本文从公共空间、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三个方面阐述农村社会公共性的样态及其流失。 (一)农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及其流失 农村社会公共空间是农村社会各关联主体基于公共性需要,按照农村社会人际交往规则进行社会活动和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并非固化不变,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空间存在形式有所不同。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公共空间主要有社区内的族田和祠堂,以及跨社区的寺庙、社戏场、茶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政治整合,一些老的公共空间在“扫四旧”①中被取缔或被改造,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转变为生产大队的队部、学校、商店、诊所,以及生产小队的“社屋”②、稻场、麦场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不再拥有组织生产功能,生产大队的队部和生产小队的“社屋”、稻场、麦场等从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中退出,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趋于小型化:集市、商店等成为村民经常进出的公共场所;大树下、河道旁的空地成为村民小范围聚集、交流和劳动休息的场所;一些农村修复或重建的祠堂、寺庙,也逐渐成为家族活动或村民烧香拜佛的主要场地。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载体与表现,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农村社区的公共空间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农村社会不缺乏公共空间,其公共空间也不缺少“人气”。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快速流动,农村社会公共空间日趋萎缩。人是公共空间的活性要素,公共空间规模的大小及其变化主要取决于人的参与和人的活动。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农村人口在城市化大潮中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公共空间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越来越少。过去农村社会中完全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例如河道旁和大树下的空地、村庄中心的广场是农村成年人聊天、娱乐、交流的主要场所,当中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后,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家务活和农活倍增,他们去这些地方的次数少了,这些地方已不再是村庄居民进行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公共空间;而那些半开放式的公共空间,例如学校、诊所、商店等,也由于人少而缺乏生气,慢慢丧失了公共空间的功能。因此,虽然中国农村社区还有学校、商店和诊所,但由于农村居民减少,其公共性功能已大不如从前。 (二)农村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及其流失 公共空间是公共性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基础,也是公共性实现的公共场域,但公共空间的公共性都要以公共利益为纽带,并以谋求其最大化为旨趣。没有公共利益,就不会有公共性的共同体,也难以形成人们的共同行为。正如郭渐强和刘薇(2010)所言,“公共利益是公共性的根本立足点,公共利益至上是公共性的显著特征”。 公共利益因区别个人利益或私人利益而有意义,即“公共利益并不是特定利益的简单加和,它当然也不是组织化了的特定利益的加和”(Schattschneider,1952),它源于共同价值的对话(Denhardt and Denhardt,2000),是多种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的“重叠共识”。这种“共识”非常重要,尽管有时候它比较抽象,当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和预测人们的行为的时候”,不一定需要知道它的具体内容,但这种“共识”是真实存在的(斯通,2006)。它不仅能协调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关系,使他们在社会共同体中同存、共处,而且它还是社会共同体开展集体性、合作性行动的基点和内在驱动力,促使人们不懈追求,以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公共性重要内容的公共利益在农村社会普遍存在,传统农村社会的家族利益和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利益都是公共利益,它们不曾因私人利益存在而减少。并且,这些公共利益已成为农村社区的公共性资源,推动了农村社区道路、桥梁、沟渠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农村社区服务于鳏寡孤独者的公益事业的发展。 威胁农村社会公共利益并使其大量流失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准许私有化发展,农民的“私性”由此被激发、唤起,但基层政权在农村社区仍具有较强的动员力和统摄力,农民基本上愿意在政府或村委会的安排下从事公共设施建设和开展农村社区服务。然而到九十年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兴起后,越来越多的农民流出农村,昔日炊烟袅袅、人声鼎沸的乡村渐渐地寂静下来,人们不再关心农村社会的公共利益,一些地方的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已经不再具有公共性功能。公共利益是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内容,它的流失让农民对农村社区的发展前景失去信心,也使一些农村社区失去了持续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三)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及其流失 在公共生活形态中,公共精神是道德规范的公共性,是公民个体与社群“摆脱利己主义而为绝大多数公共利益着想的精神”(凯尔曼,1990),具有“自主、公道、宽容、理解、同情、正义、责任、参与、奉献”等理性品德和公共理念(袁祖社,2006)。公共精神广泛存在于社会共同体中,它是公共性实现的主观条件。社会共同体建设需要弘扬公共精神,以帮助人们真实地感知共同体的生动图景和公共性魅力。 基于熟人关系的农村社会,其公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乡土社会中的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正是在地缘关系上产生的乡情和在血缘关系上培育的亲情,促成居民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形成共识。这些共识经岁月洗涤后,有些成为社区居民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和“土政策”,有些自然转化为社区认同意识,指导社区居民的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农村社会的公共精神包括团体精神、合作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等,它们铸就了农村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不仅能捍卫农村社会公共性,还能有效维护农村社会共同体的团结。 然而,农村社会的公共精神与公共空间、公共利益一样也在流失,其流失速度甚至比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流失还要快。在某种意义上,当前农村社会出现的疏散、空心、衰落现象,不仅仅在于公共空间的缩小、公共利益的私人化,更严重的是,公共精神的日渐式微引发了农村社会灵魂的丢失,以至于农村社区居民理性价值出现迷乱。“人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价值,无论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而且,越是集体行动,就越会突出价值的问题”(张康之,2003)。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的流失,影响居民对个人或集体行动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使农村社会乱象丛生。农村社会出现的人情冷淡、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等不良社会风气,都与公共精神流失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农村社会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是建房、修路,而应该是恢复公共精神③ 三、从三类社区看农村社会公共性变异 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并不一定导致农村社区公共性总量减少。农村社区公共性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可能发生以下情况:某一种公共性在流失中不是消亡,而是转变为另一种公共性;某一类公共性减少,而另一类公共性却增多;农村型公共性减弱,而城市型公共性却增强。农村社区公共性的这些变化可以从中国农村的村落社区、集中社区和城郊社区中看到。 (一)村落社区:农村社会公共性弥散 公共性弥散是指原村落社区整体的、统一的公共性在农村发展与变迁中逐渐变得零碎、分散,致使社区公共空间碎片化、公共利益私人化和公共精神利己化的现象。公共性弥散的农村社区一般为村民大量外流的空心化或过疏化村庄,村民的生产生活面临着一系列公共性困境。例如,在传统农业生产中,老农生产经验凝聚着村落公共性,它是播种、育苗、除虫、锄草等农业生产活动的公共权威。是否尊重老农生产经验,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农业生产能否有好收成。但随着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掌握科学技术的年轻人逐渐取代拥有公共性经验的老人,成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公共性人物,村民们在生产中遇到难题时更愿意向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知识的年轻人而不是向老农请教。然而,当打工成为一部分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后,越来越多拥有公共性技术的年轻农民离开了农村,农业又转变为以老人为主要劳动力的产业。当下的问题是,老人的生产经验已经不如以前好使,因为形成于传统农业时代的经验并不包括农药、除草剂、化肥的效能和使用方法等内容,现代农业生产活动迫切需要政府和有关社会团体为农民提供专门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村落社区的公共性困境还表现在社区治安上。集体化时期,国家权力下沉到农村底层,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使农村社会井然有序,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普遍较好。调研中,笔者经常遇到一些老年农民追忆、留念毛泽东时代的农村治安状况,说那时的农村真正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现在的村庄治安状况一年比一年差,不仅鸡、鸭等家禽经常被偷,而且猪、牛等大家畜也时有被盗。村庄小偷多,村民对抗小偷的能力弱,意味着农村社区公共性弥散程度加剧。 一位安徽的农村妇女曾向笔者讲述她所在村庄的治安状况。过去她们村没有这么多小偷,那时村庄中的道路全是小路,外地或城里的小偷担心道路不熟悉,不敢轻易进村偷窃。再者,村庄中的男劳动力多,偶尔有小偷进村,各家各户的男人们听到狗叫就会主动出门“赶小偷”。现在小偷多,并且胆子忒大,敢翻院子,甚至撬开门窗到屋里偷窃。其主要原因是:开展新农村建设后,“村村通”的公路为骑摩托车或开车的小偷进入村庄提供了便利条件——小偷进村、离村速度特别快,很难逮到他们;村庄人少,年轻男人们几乎都到外地打工了,女人胆子小,知道小偷来了,也不敢出来,有时听到村里喇叭喊“小偷进村了,请大家注意”的提醒,心里愈发恐慌,更不敢出门;近几年,越来越多村民全家都到外面打工,空户、空房子多,一到晚上,胆小点的女人不仅怕小偷,还怕鬼,尤其怕村庄中去世不久的“熟鬼”,因为鬼是看不见的,防不胜防。 这位村妇,家里有4口人,丈夫常年在江苏省常州市打工,婆婆带着她的儿子在县城中学读书,她整年一人在家从事农业劳动和做家务。她家的居住条件不错,主屋是两层楼房,底层有3间,上层有2间。并且,她家的安全设施好,主屋前后有2米高的院墙,房子和院子的大门都是用钢筋焊制的铁皮门,窗户也用钢筋加固,前后院子分别拴着两条狗。但即便如此,她心理还不踏实,几乎每天晚上都开着灯睡觉。 农村社会公共性弥散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一些公共性弥散严重的农村社区,已经出现了农民不能合作的迹象。虽然家庭是农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家本位”意识在一些农民思想中根深蒂固,但灌溉、治虫等农业生产活动仍需要农户彼此配合。有公共性存在,大家合作并不难;而现在,农民开展合作的难度大。例如,治虫就存在合作难问题——村民知道在一起的田地要同时打农药治虫,否则打药田地里的虫子就会飞到不打药的田地里,而现在有的农民只要看到自家田里有虫,就不打招呼各打各的农药,使治虫效果越来越差。 (二)农村集中社区:城乡社会公共性混合 农村集中社区包括中心社区,主要指地方政府对分散的农村社区进行拆、并改造而形成的或新建的农民集中居住社区。例如,江苏省淮安市“涟水第一村”的W中心村,将原行政村的37个村庄的365户人家搬迁到中心村居住。又如,山东诸城市把全市1249个村庄合并为208个大农村社区,每个农村社区以一个行政村为中心,将周边相邻的村庄连成2公里服务圈。农民集中居住社区打破了原行政村的地域边界,不管是原居民,还是新搬迁进来的居民,集中社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居住空间,不仅日常事务与过去有所不同,需要他们有新的处事和办事原则,而且他们面对的人也比过去多得多,其中有不少人是不很熟悉的“陌生人”,彼此之间并不容易和睦相处。 由于农村集中社区的居民来自不同的村庄,加上社区建设的主要主体是政府,因此,农村集中社区的公共性在一定时间里存在不确定性,它可能是多个村庄的混合公共性,也可能是政府建设社区和管理社区的政策公共性,还可能是农村集中社区在运行中自身形成的全新公共性。也就是说,农村集中社区的公共性在一定时间里是多元化的,有新的公共性和老的公共性,有国家的公共性和地方的公共性,有农村集中社区的大公共性和原分散社区的小公共性等。虽然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公共性在农村集中社区同在、共处,但在一定时间里,居民仍习惯按照自己认同的小公共性行动。李勇华(2009)在研究政府公共服务下乡时发现,宁波市和舟山市的农村居民在农村社区化进程中仍将村庄内的公共产品视为自己的,而将社区建设、公共服务等视为党委和政府的事情,一概“不管不问”。这表明,在农村集中社区里将长期存在公共性的“两张皮”现象,需要对农村集中社区混乱的公共性加以整合,以促使它们融为一体,进而使其在农村社区建设、社区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城郊农村社区:城乡社会公共性博弈 城郊农村社区主要指位于城市近郊,正在或将要被城市覆盖、包围的农村社区。例如南京市栖霞区的Y农民集中安置社区,它是把两个不同行政村的2787户、9556个农民集中安置到一个地方居住的社区。又如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的X社区,是为建设大学城将一个行政村全部人员集中安置的社区,有1384户,常住人口3987人,流动人口1000多人。这类社区原来都处于城市近郊农村,居民有责任田,主要劳动力既从事农业劳动又兼有其他职业,并且家庭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但是,随着城市范围不断向郊区延伸,村庄土地逐渐被部分或完全征收,政府将这些村庄的居民迁入到安置社区居住。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城郊社区有的将被城市覆盖,被改造为城市社区;有的将被城市包围,演变为城中村;有的仍在城市边缘延续,保留农村社会的诸多特色。尽管这三类城郊社区的居民主要来自农民,有的社区还保留着村委会,但它们的城市倾向比较明显,即使是城市场域外围的一些城郊偏农社区,由于居民就业、子女就学、看病就医等活动向城市聚拢,大多数居民的城市性正在快速成长。 城郊保留农村特性的社区可称为城郊偏农社区。这类社区具有很强的农村社会公共性,说话、做事“乡土味”浓厚。虽然其中有一部分人像普通农民工一样,在城市从事苦、累、脏、危险工作,工资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在社区内劳动和工作,要么种植蔬菜,起早贪黑地往城里送菜、卖菜,要么选择做小生意,办养殖场或加工厂。由于相关管理和监督没有跟上,这类城郊农村社区往往成为城市周边的脏乱差地区和制作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居民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公民意识正在沦丧,他们中有的人利用城乡结合部的有利位置生产、加工有害于人们身体健康的食品和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秩序。城郊农村社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居住人员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带有半工与半农、半城与半乡的性质,公共性比较混乱。但这类社区的农村社会公共性还没有被城市社会公共性取代,农村社会公共性仍在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但使人顺利完成任何行为,而且还使人有完成那种行为的倾向和趋向”(休谟,1980)。 城中村社区在很多城市都存在。尽管城市管理者对城中村及其居民给城市建设和管理造成的一系列问题都十分清楚,但鉴于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村民的“地界”,不便与城中村居民硬碰硬,使用“暴力”改造他们。由此,有人将城中村比作为城市中的“马蜂窝”。城中村社区的公共性有城市社区公共性,也不乏农村社区公共性,这两者既相互共处,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当城市公共性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会按照城市人的行动逻辑来谋求利益;当农村社会公共性对他们有利时,他们就会一如既往地按照农村人的生活方式追求私人利益的增长。在与城市管理者的博弈中,城中村社区居民学会了运用城乡两种公共性谋求社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例如他们中有人抱着“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心理,敢无视城市管理条例,私自加盖房子,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设想,将其租给城市人或进城打工者,甚至将其变为私人旅馆、钟点房,对外做生意。他们不担心居住条件差没有人住,他们可以到车站等流动人口聚集地方“拉人”;他们不怕管理部门检查,他们有时间、有办法与管理者玩“躲猫猫”游戏。城中村居民谋财路子多,只要能赚钱,他们没有不敢做的,他们中不少人是开黑车、倒票的高手。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一般不干缺德的“坏事”,例如偷窃、抢劫等。城中村的道德公共性禁止那些害人、坑人的行为,其理由是:开黑车、倒票是劳动致富,即使违法,也不丢人;而偷窃是不劳而获的懒人所为,即使富裕了,也会让人瞧不起。在城中村不少居民的心目中,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有它们各自的存在空间,但他们更擅于用民间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比只重视民间法的村落社区有一定的进步。 相比于城郊偏农社区和城中村社区,经过城市化长期、深度改造的城郊无农社区,由于城市管理者已经将其纳入城市中,加上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居民互动频繁,居民的乡村记忆几乎被全部磨掉,他们完全接受了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这类社区已经升级为与城市社会同构的城市社区,城市社会公共性基本取代了农村社会公共性。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一个老的农民安置社区就属于这类社区。这个社区建于1997~1998年,最初的居民都是被政府安置的农民,可如今它与“农”没有多少联系,俨然是一个纯粹的城市社区。十几年来,这个社区有接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流出,同时也有相等的城市居民流入,是一个城乡居民杂居的社区。整个小区除了东面响水河的河堤上有几块老人们开辟的菜地外,几乎看不到其他农村痕迹:社区广场上,早晨和夜晚都有成群的老人在跳广场舞;小区的体育健身器材旁,全天都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在锻炼、玩耍;就是河道下曾经长期出租给交警队停放违章、事故车辆的大片空地,也在2008年被社区收回,用于本社区居民停放私家车……在这类社区中,城市社会公共性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而农村社会公共性接近谢幕。 四、社区服务对建构农村社会公共性的作用 农村社会公共性蕴藏在农村社会的各种现实存在中,尽管它的呈现样态与表现形式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有所变化,但它始终是维系农村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支点和不可或缺的整合机制,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建构它。调查发现,作为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的农村社区服务,对减缓公共性流失和促进公共性成长具有较大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化解因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而产生的诸多问题,而且在新形势下它还是建构农村社会公共性的有效手段和工具。 发展农村社区服务,能拓展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随着农民不断从农村社区流出,农村社会公共空间缩小、变换、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多数留守村民的社会活动将部分地退回到私人领域,还有一些生活好起来的村民更喜欢到社区外寻求发展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村民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即使像村委会选举这类关系广大村民切身利益的活动,也有部分村民对它没有参与兴趣;私人领域的扩大,村民间社会交往活动的日趋家庭化,使村民们虽相互认识,但感情冷漠、关系生疏;来自社区组织、亲戚、邻里的关心、信任等社会资本因公共空间萎缩或转移而急剧减少,村民的生产与生活成本显著上升。鉴于此,农村社区可以通过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提供上门代办服务等方式拓展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以减缓公共空间缩小对居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冲击。 发展农村社区服务,能壮大农村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农村社区话语层面上公共利益的公共性与作为政治话语层面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公共性是不同的,前者的公共利益包容个人或私人利益,它们共享同一个公共性,而后者的公共利益居于强势地位,个人或私人利益必须服从公共利益——虽然它们也拥有相同公共性,但更多的时候是公共性对私性、个性的控制和掠夺。由此来看,立足于促进个人利益增长的社区服务,除了向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服务外,还需要引导居民关心社区整体利益,并为社区公共利益的增长添砖加瓦。换言之,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社区服务水平高,意味着社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公共性提高。 发展农村社区服务,能培育农村社会公共精神。农村社会公共性形塑了社区居民共同的认同感、安全感和责任感,它运用农村社会特殊的地缘、血缘关系将社区的私人领域最大限度地扩张至公共领域范围内,使社区的公与私、群与己的边界模糊不清,并将社区居民的个人品德提升为公共精神。这一凝聚个人品德的公共精神在社区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使社区中公共服务、团体服务、个人互助服务和谐相处,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发展。针对农村社会公共精神在农村社会转型中大量流失及其功能在某些社区逐步下降的现状,作为农村社区重要建设活动的社区服务具有建构公共精神不可推卸的责任,即农村社区服务可以培育社区居民的团体精神、合作精神、公正公平精神,以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 此外,农村社区服务的公共性能兼容农村社区的其他公共性。当公共性在农村社会转型和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大量流失时,包括公共服务、市场服务、社会服务在内的社区服务如能及时介入农村社会,不仅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而且能向农村社会输入另一种公共性,以填补公共性的缺位,并部分地替代所流失的公共性的功能。尤其是,农村社区服务的公共性还具有较强的“增殖”能力,只要给予适宜的生长环境,它就能扩张、渗透至农村社会的公共空间、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中,并与它们的公共性相结合,滋生出新的公共性,进而推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和城乡社会协调发展。 注释: ①1966年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倡导“破旧立新”,要求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 ②“社屋”是生产小队建造的公共房屋,生产小队成员开会和一些娱乐活动都在此进行。社屋一般有好几间甚至十几间房子,有的储藏粮食和种子,有的堆放农具,有的作为牛棚、马厩。 ③以团体精神、合作精神、公正精神、服务精神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精神在流失后可以通过发展社区服务、进行社区建设等途径得到恢复。标签:农民论文; 城市公共空间论文; 农村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社区服务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公共场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