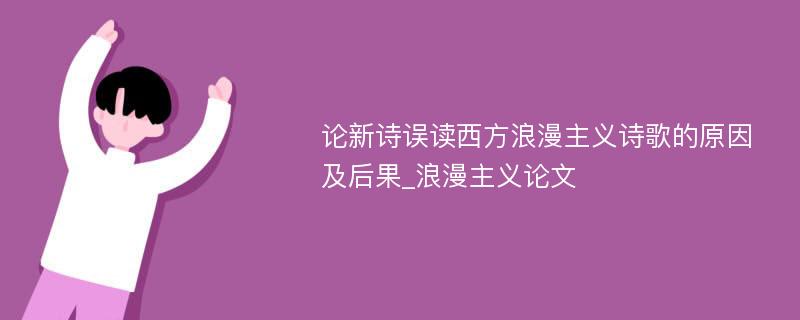
论新诗诗人误读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原因及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误读论文,浪漫主义论文,诗人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3)06-0061-07
20世纪是中外文化大融合的时代,很多外国诗歌流派都影响了新诗,如浪漫主义、现 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自白派等,其中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最大。“ 欧洲和美国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就是故意摈弃‘公认的’文学传统和风格”[1 ](p.643),“浪漫主义包括哲学和政治上的进化,在艺术上,它与古典主义的最大区别 是古典主义要求艺术形式有平衡、有比例,浪漫主义要打破这些限制,推崇灵感和激情 ”[2](p.23),“浪漫主义造成了革命……在英国和在法国,浪漫主义都是与某一些政 治见解有关联的”[3](p.6)。浪漫主义的这种反传统观念更是直接影响到新诗革命。孙 绍振主张把1917年到1927年的新诗分为流产的意象派、不完全的浪漫派和不完全的象征 派,认为浪漫派极大地影响了新诗初期的创作。他在《新诗的第一个十年》中得出结论 :“浪漫主义诗歌在中国新诗中取得了统治地位,不像在欧洲那样,经过和古典主义的 艰难搏斗,而是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全国几乎所有的阵地。不管是革命派的 诗人还是自由主义诗人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浪漫主义的方法,把生命投入艺术的探险, ……在想象和激情的,还有灵感的三大旗帜下,浪漫主义诗人的大军声势浩大地席卷了 整个中国诗坛。”(注:孙绍振:《新诗第一个十年》,未刊手稿,此稿为《二十世纪 新诗大系1917-1927年》序言。)浪漫主义诗歌不仅在新诗初期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 而且流行于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流行,在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 胧诗”诗人中尤为明显,“整个新诗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的演变过程”[4](p.60)。无论是在大中学的诗歌教育中,还是在诗坛上,浪漫主义诗 人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派的诗人,雪莱、拜伦几乎是家喻户晓。1980年江枫译的 《雪莱诗选》到1988年第2版共印刷了8次,印数高达384,250册。由于新诗诗人误读了 浪漫主义诗歌,夸大了浪漫主义诗歌从抒情内容到文体形式上对传统的颠覆作用,特别 是夸大了诗人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和诗体方式的“自由性”,助长了新诗诗人在做人 方式和作诗方式上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影响了新诗诗人的人格建设和新诗的诗体建 设。
一、浪漫主义诗人影响了新诗诗人的做人方式
由于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战争、运动和改革此起彼伏,既充满动乱又充满激情 的时代,特别是世纪初更是一个革命的浪漫时代,新诗诗人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特殊 时代的激情与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很容易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因此浪漫主义思潮流 行中国。浪漫主义诗歌很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受到了致力于中国政治、文化改革的精 英文人的高度重视。
浪漫主义诗人对国家和对人的重视,尤其是民族主义的爱国和自视为天才的爱人,格 外受到20世纪初中国青年及文人的青睐。“浪漫派诗人和哲学家是热情的爱国者”[5]( p.217),浪漫主义在新诗草创期受到中国诗人及文人的过分热情的欢迎,不仅是因为他 们渴盼个体的做人和作文的自由,像浪漫主义作家那样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更是因为 他们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患和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强烈的使命意识。深受儒家思想 教化的中国文人一向以“达则兼济天下”为己任,具有极强烈的爱国情怀,甚至还有狭 隘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以为是的济世救民感。20世纪初的中国政体混乱,国将不 国。乱世之际,文人们更不愿坐而待亡,便起而拯之。这与后期西方浪漫主义者由“唯 美的信徒”转向“政治革命的先锋”甚至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生存境遇有 共通之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和作家个性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性 格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五四文人一种格外积极的心态,并且把他同他的虚弱、衰老、抱 定传统的对手截然区别开来。当然,这种青春的力量锋芒所向,大都是去摧毁传统。… …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的,‘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的那种乐观和热情 ,与受法国大革命激励而出现的那一代浪漫派诗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6](pp.5 10~511)但是中国诗人的生存境遇比外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存境遇更差,严格地说,从 “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时期,甚至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不是中国诗人潜心诗 艺的时代,他们根本不可能远离尘嚣超然于世,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尽管中国文人渴望 艺术上的浪漫,追求诗意的生活,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现实。这是当时现实主义艺术流行 ,浪漫主义艺术变味的重要原因。“喜爱浪漫主义的中国作家们往往注重于欧洲浪漫主 义的那些‘现实主义’方面:……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 上。……一个典型的五四文学家大都具有这种三合一特点:气质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信 条上的‘现实主义’,基本观点上的人道主义”。[6](pp.530~531)
浪漫主义对人的高度重视,迎合并助长了五四时期国人的个性解放心理和革命激情。 华兹华斯认为诗人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向人们讲话,他是一个人,比一般人有更敏锐的感 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雪莱提出 :“一首诗则是生命的真正的形象,用永恒的真理表现了出来;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 在黑暗中,用美妙的声音唱歌,以安慰自己的寂寞。”[7](p.53)浪漫主义诗歌对诗人 创作主体的高度重视,更是对人的自我意识、个性解放的充分肯定,这与五四近乎狂热 地追求个性解放的激进思潮水乳交融,追求诗的“真”——情感的真实和书写的真实( 直抒胸臆的写作方式)在新诗草创期得到极端的重视。因此新诗诗人们深受浪漫主义诗 观的影响,如歌德主张“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凡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没有迫使 我非写不可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用写诗来表达它”[8](p.214),深受歌德影响的郭沫若 也主张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华兹华斯的“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9](p.17)的诗观更是深入人心,新诗初期甚至百年间中国诗人总是故意忘记这个诗的定义的 后一句话:“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9](p.17)新诗初期以郭沫若为代 表的很多诗人都过分推崇激情的力量,激情有余沉思不足,激情太盛扼杀诗美。这种强 调诗出自然、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直抒胸臆诗风严重影响了新诗的诗体 建设,诗人连情感都不愿意和来不及“纯化”,更不可能重视诗的音乐形式和视觉形式 。
19世纪席卷全球的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加剧了中国新诗革命的“激情化”、“政治化” 的极端,极大地从诗人的做人方式、写作姿态和抒写内容上影响了中国新诗诗人,刺激 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青年天生的偏激情绪。浪漫主义是最早介绍进中国的西方诗歌流派 ,具有捷足先登、先到为君的优势,并且在译介中还被“偶像化”(神化),很容易被渴 望新思想的国人接受。浪漫主义,特别是被译介者、倡导者“夸大了革命效果”的变味 的浪漫主义当时确实较适合中国国情,而当时西方正流行的后期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及 现代主义诗歌并不适合落后的中国,尽管也有译介,对中国的影响却没有像浪漫主义那 样占主导地位。1907年,鲁迅作了极大地激发新诗革命的《摩罗诗力说》,介绍的诗人 有印度的加黎陀莎(Kalidasa)、德国的瞿提(W.von Goethe歌德)、意大利的但丁(Dante Alighierti)、英国的斐伦(G.Byron拜伦)、司各德(W.Scott司各特)、修黎(P.B.Shelly雪莱)、弥尔敦(J.Milton弥尔顿)、穆亚(Th.Moore穆尔)、苏惹(R.Southey)、匈 牙利的斐多飞(斐多菲)、俄国的普式庚(普希金)、来尔孟多夫(M.Lermontov莱蒙托夫) ,还涉及到柏拉图(Platon)、尼佉(Fr.Nietzsche尼采)、鄂戈里(N.Gogol果戈里)、狭 斯丕尔(W.Shakespeare莎士比亚)、鄂谟(Homeros休谟)、勃兰兑思(G.Brandes)、受诺 尔特(M.Arnold阿诺德)等作家理论家,其中很多都是浪漫主义诗人。他对浪漫主义诗歌 极为推崇:“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 人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斐伦,终以摩迦。”[10](pp.788~789)鲁 迅对拜伦“偶像化”,用专节仔细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最后结论说:“斐伦既喜拿 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 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道亦在是。”[10](pp.800~801)五四运动以前, 浪漫主义诗歌就开始译介进中国,五四运动稍后,更是出现了浪漫主义诗歌介绍热。较 早译介的主要是爱情诗,如海涅的爱情诗译得较多。当“爱情”已经不能使青年救国救 民,创造、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日渐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拜伦、歌德、雪莱、普希金等思 想激进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思想性,甚至政治抒情性作品成为主要译介对象。如同斐多菲 的诗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极大地 影响了20世纪中国青年)“爱情诗人”海涅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较大的市场,歌德、拜 伦成为中国诗人崇拜的对象。如1923年1月14日,蒋光赤在《我的心灵》的最后两个诗 节写道:
我的心灵使我追慕
那百年前的拜轮:
多情的拜轮啊!
我听你的歌声了,
自由的希腊——永留着你千古的侠魂!
我的心灵使我追惋
那八十年前的海涅:
多情的海涅啊!
你为什么多虑而哭泣呢?
多情的诗人——可惜你未染着十月革命的赤色!
在20年代初,歌德、拜伦等浪漫主义诗人是中国译介和研究得最多的外国诗人。以歌 德为例,1920年3月13日,宗白华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天上曲》同Zueignung都 翻译得很不坏,很不容易,歌德文艺之入中国当算从你起了。”[11](p.18)1923年下半 年由成仿吾、郁达夫、邓均吾编辑的《创造日》刊载了邓均吾译的《歌德传》(原作者 是Paul Carns),分为“歌德之生平”、“歌德与妇人之关系”两章,在译文末,编者 写道:“《创造日》停刊了,本译稿只得在此中止,此后将继续译出,出一单行本以就 正于读者。亲爱的读者哟,我们再见。”(注:创造日汇刊,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上海书店1983年印行,第504页。原见1923年11月2日创造日。)歌德的译介工作一直 没有停止过,国内很多人都撰文介绍歌德,仅宗白华就写过《歌德之人生启示》、《歌 德的<少年维持之烦恼>》、《借<浮十德>中诗句吊志摩》、《<歌德之认识>附言》(注 :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载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0至222期,1932年3 月21日、28日和4月4日出版;《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之认识>附言》, 载《歌德之再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借<浮十德>中诗句吊志摩》,载《 诗刊》(志摩纪念号)第4期,上海新同书店,《诗社》1932年版。)等有关歌德文。1933 年宗白华还自费出版了他和周辅成编的《歌德之再认识》一书,由南京钟山书店发行。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外国作家的论文集[12](p.332)。《歌德之人生启示》是其中 代表作。宗白华在此长文中对歌德高度推崇:“歌德对人生的启示有几层意义,几个方 面。就人类全体讲,他的人格与生活可谓极尽了人类的可能性。他同时是诗人,科学家 ,政治家,思想家,他也是近代泛神论信仰的一个伟大的代表。他表现了西方文明自强 不息的精神,又同时具有东方乐天知命宁静致远的智慧。”[13](pp.1~2)宗白华这样 评价歌德的诗和人:“歌德的诗真如长虹在天,表现了人生沉痛而美丽的永久生命,… …而歌德自己一生的猛勇精进,周历人生的全景,实现人生最高的形式,也自知他‘生 活的遗迹不致消磨于无形’。”[13](pp.24~25)由此可见歌德在中国文人心目中的重 要地位和被偶像化的情形。
人类艺术总是关注着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对人的自由高度推崇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 ,很自然地成为在做人和作诗都不自由的生存境遇中挣扎的中国诗人的首选。“凡是抱 有革命见解的作家必然都是诗人”。[7](p.53)雪莱也自豪地宣称诗及诗人的力量是巨 大的,认为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要对思想和制度进行一番有益的改革,而诗便是最 为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以雪莱、拜伦为代表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的争自由于 革命的生存方式影响了新诗诗人,新诗初期很多青年诗人都自称是浪漫主义者,把浪漫 与革命相提并论,如郭沫若说蒋光赤在“浪漫”受到攻击时,公开宣称:“我自己便是 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 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情况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 漫派。”[14](p.244)茅盾在1930年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一书的《浪漫主义》专章中 说:“浪漫主义则尊重自由,要打破那些束缚个人自由的典则。……浪漫主义则注重内 容,打破那形式的桎梏。……浪漫主义则为情热的理想的。”[15](p.73)茅盾所说的正 是当时中国,特别是诗坛流行的中国式“浪漫主义”观念,也正是在新诗初期被很多新 诗诗人,特别是激进的、处在青春期写作和革命激情写作中的青年诗人全盘接受和大力 宣扬的观念。即使是否定浪漫主义是革命的文学的来源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浪漫主义的 “革命性”,如冯乃超在1928年6月12日写的《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 革命”》一文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文学》一节中说:“Rmoausique或许是孤独的巡礼 者,或许是热情的异端者……他们的主观主义是可以发展到革命,破廉耻,独断论,反 动等一切的事情身上的自己中心主义。”[16](p.15)拜伦(蒋光赤诗中为“拜轮”)为了 自由去希腊打仗的英雄行为确实影响了很多中国诗人。20世纪的中国诗人,特别是在二 三十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激烈时期,年轻诗人常常采用两种生活方式:一是拜伦式,像他 那样先是个人抒情、然后启蒙大众,最后投身革命,如蒋光赤、殷夫、胡也频、郭沫若 、成仿吾、柯仲平、黄药眠等。甚至连女诗人,如石评梅、丁玲的诗中也充满革命豪气 。这类诗人的最后结局如蒋光赤诗中所言“多情的诗人”“染着”了“革命的赤色”, “许多青年人通过文学艺术变得激进起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创造性文学艺术 ,开始了其激进化的过程。例如,这一倾向就清楚地表现在鲁迅的作品中,以及象创造 社这样的文学组织的转变之中。1930年3月,左翼文学运动的不同支派集合在一起,成 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其领导下的刊物,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批评家以及民族 主义的作家发起了挑战”。[17](pp.240~241)二是海涅式(海涅早期译介进中国的大都 是爱情诗),沉醉于爱情,如刘梦苇(写出了《吻之三部曲》)、邵洵美、徐志摩等,他 们更多地受到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的影响。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认为尽管革命 可以推动社会前进,但是女性和大地更是让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歌颂 女性的美和自然的美。徐志摩等人便大写歌颂爱情和自然的“浪漫诗”。
由于新诗革命是与传统对抗的破旧立新的革命,极端地反对对古代汉诗的“纵的继承 ”,外国诗歌自然成为了新诗的“参照系”甚至标准,因此过分强调对外国诗歌的“横 的移植”,也由于当时对外国诗歌了解不多,译介水平也极有限等原因,新诗草创期出 现了盲目引进外国诗歌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外国诗歌的优秀方法进入中国后也发生了巨 大的变异,被中国国情强烈地“同化”。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论述了新诗草创时浪 漫主义“引进”时的“误读”情况:“五四在表现方法上,也是清浅的,很少人谈到体 系和原则,触及根本概念的范畴……国人对浪漫主义的误解,以为披发行吟为浪漫,以 酗酒妇人为浪漫,以不贞为浪漫。”[18](p.12)即激进的中国诗人不但引进了浪漫主义 的作诗方式,而且更引进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放荡不羁的做人方式和离经叛道以“革命” 为荣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与中国古代才子文人的风流倜傥的生活方式合为一体, 更加剧了对新诗诗人,特别是青年诗人与社会伦理秩序对抗的“造反”心理。这种具有 “思想的先锋性”而非“艺术的先锋性”、“行为艺术的先锋性”而非“语言艺术的先 锋性”、做人的浪漫甚至大于作诗的浪漫的风气弥漫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新诗坛,在个性 解放的“革命”为主潮的新诗初期最为浓郁。甚至最早系统地介绍浪漫主义诗人进中国 的鲁迅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有的新诗诗人做人有问题,甚至有的浪漫主义诗人被称为“流 氓加才子”式的人。“尽管鲁迅对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妇女解放的可行性持有很大的保留 态度,但是正处于中年的鲁迅却同情甚至挂念着那些青年女作家。可是对一些男作家, 鲁迅却用冷嘲和蔑视对待他们。‘才子加流氓’这个词就是他的一句精辟之语,特别用 来称呼那些创造社人士。但是他还很乐意把这句话推而广之,用来嘲骂文坛上的一群暴 发户、得志者,这些人刚刚在一家新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或是一首诗,就大肆炫耀, 吵吵嚷嚷着要求马上就得到承认。他们的名声与其说是来自他们的作品,还不如说是来 自他们那种浪漫行为。作家个性与生活经历的这种高扬——过份专注于自我——对‘五 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性质和质量产生了一种关键性的影响”.[6](p.515)。
二、新诗诗人误以为诗体大解放是浪漫主义的一大特点
从1907年鲁迅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对拜伦、雪莱、斐多菲等浪漫主义诗人的极度推 崇,以及蒋光赤、郭沫若等诗人把“浪漫派”等同于“革命派”等诸多事例便可说明浪 漫主义敢于向权威、习俗挑战的浪漫主义精神成了新诗重要的“革命精神”。浪漫主义 诗歌,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歌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新诗的诗体建设,现代格律诗体 便是以19世纪中后期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为参照系的英语“格律诗”的“中国式写作”。 “早期新体诗成果(胡适、康白情、刘大白等)在形式上都较为粗糙,更不要说内容上的 浅薄了。20年代初期最有才华的诗人是郭沫若,他的作品受到意象派和瓦尔特·惠特曼 的影响。然而,郭沫若诗歌那种罕见其匹的生命活力是故意通过一种粗糙的形式来表达 的,直到徐志摩从英国归来并且在1926年创办他的《诗刊》的时候,那场严肃的革新— —特别是在诗歌韵律方面——才算是开始上路,这种努力主要是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的影 响下展开的。20世纪初期的几种先锋派——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等—— 也在20年代为人所熟知,并且得到探讨。因此,这第一个10年的文学局面有着某种历史 的反讽意味:虽然是文学革命,旨在废除旧形式,迫使中国一切现代作家都成为形式上 的实验主义者和汲取异域营养的人,但是他们实际上的文学实践在技巧的运用上却显示 出一种惊人的无能”[6](pp.534~535)。
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对中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却更多是源于中国新诗人对它的“误读 ”,特别是新诗人夸大了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做人的“革命性”和作诗的“自由性”,误 以为西方浪漫主义运动既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破旧立新的文体大革命 ,把“浪漫”或“浪漫主义”视为“自由”、“革命”、“解放”的同义词。当时很多 中国文人都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具有破弃传统的革命特质。如梁实秋写于美国,1926年发 表在《创造》月刊上的《拜伦与浪漫主义》一文总结出浪漫主义的三大特点是:自我表 现之自由,诗的体裁之自由和诗的题材之自由。他说:“总而言之,浪漫主义的精髓, 便是‘解放’两个字。浪漫主义者全是丛聚在这个新鲜的大纛下面,他们全都崇奉着这 解放的精神,而向不同的各方面去发展。”[19](p.14)他还称:“诗体的大解放是浪漫 主义最显著的一个特点。”[19](p.16)1926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重要的“诗体建设年” ,当时新月派诗人正在“重振旧山河”,收拾“作诗如作文”式极端强调作诗自由的新 诗革命对汉诗造成的“破”了未“立”的危局,开始强调作诗需要规范,倡导有“节的 匀称”和“句的均齐”的新格律诗。新月派强调的诗的“律化”受到了以郭沫若为代表 的创造社诗人和以李金发为首的象征派诗人的相对抵制。尽管梁实秋的思想并不激进, 他受过白璧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教育,但此文作于美国,又刊于当时中国文坛最富有“ 创造”意识的《创造》月刊上,其对新诗“律化”运动的消解力是巨大的。当时很多人 如同梁实秋一样,对浪漫主义的理解都是片面的,都太重视浪漫主义重视现实,强调自 由的一面,忽视浪漫主义重视诗艺,追求诗美的一面。如李欧梵所言:“浪漫主义美学 的那些神秘的和超验的层面,在赞成一种人道性、社会—政治性的解释时,大都被忽视 了。重点被放在自我表现、个性解放和对既定成规的叛逆上。”[6](pp.530~531)茅盾 在1930年版的《西洋文学通论》一书的《浪漫主义》专章中说:“因为是一般地要求着 自由,就造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破弃一切传统的束缚,自由地独创的精神。”[15](p.8 9)
曾经极大地影响了初期新诗的雨果尖锐地提出浪漫主义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的结论: “艺术中的自由,社会中的自由,这就是一切思想一贯的人和富有逻辑的人应该迈出同 样稳健的步伐走向的双重目标……文学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产物。这个原则是本世纪的原 则。”[20](p.85)尽管雨果很快放弃了“纯诗”,主张艺术为人类而不是艺术为艺术, 拒绝区分高贵词汇和粗俗词汇。这些诗观影响了新诗初期的中国诗人关注大众生活,接 受平民语言,有利于平民文学的生长,也使新诗人重诗的内容轻诗的形式,不利于诗体 的规范建设。但是由于法语与汉语的语言差异及诗歌的抗译性,译者和接受者新诗人又 都生活在打破无韵则非诗的革命时代,如同对其他很多外国著名诗人或流派、诗体的误 解一样,雨果的重视艺术,特别是诗的韵律的一面被中国忽略了。“雨果对韵律有一种 敏感的本能……最善于使用各种各样的音步和诗句,从单音节到亚历山大诗体。他对亚 历山大诗体有特殊的爱好……贝吉在评论《惩罚集》时说:‘他擅长他的艺术。他懂得 以字句制造出警钟声;以韵律制造出军乐声;以节奏制造出低音。’”[20](p.136)
在西方,浪漫主义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特别是以雪莱、拜伦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诗 歌,对英诗并没有作多大的文体改革。所有的西方浪漫主义诗人都没有在本国的诗歌文 体变革中摒除旧诗体,特别是没有完全打破无韵则非诗的作诗法则。西方的“自由诗革 命”(Free Verse Revolution)是在浪漫主义诗歌运动后的法国象征派诗歌运动和美国 意象派诗歌运动中才出现的,即使是最激进的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自由诗革命”也没有 像中国的新诗革命那样放弃诗的韵律。“自由诗(“free”verse)不是简单地反对韵律 ,而是追求散体与韵体的和谐而生的独立韵律。如果意识不到这样的‘第三种韵律’(third rhythm),就无法解释诗失去规则韵律为何不会沦为散文”[21](p.272)。1911年 英国政治学家罗布豪斯(L.T.Hobhouse)在《解放主义》(Liberalism)一书中得出结论: “十九世纪可以被称为解放主义(Liberalism)的年代,尽管深入观察那个伟大运动的结 局带来了最低潮。”[22](p.214)但是19世纪的西方多的是思想的大解放而非诗歌文体 的大解放。尽管浪漫主义诗人不像黑格尔那样过分推崇诗的音律,“用音律的散文不能 算是诗,只能算是韵文,正如用散文来创作诗,也只能产生一种带有诗意的散文。至于 诗则绝对要有音节和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 比所谓富于想象的富丽词藻还更重要”[23](p.68),却普遍重视对极端强调诗的韵律的 古典诗歌“改良”后的韵律。如歌德虽然主张不要把诗的语言看得太死,他在1827年4 月11日说:“一般地说,我们不应把画家的笔墨或诗人的语言看得太死、太狭窄。一件 艺术作品是由自由大胆的精神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就应尽可能地用大胆的精神去观照和 欣赏”[8](p.138),但仍然重视韵律,仍认为“韵”是表示诗句的终结。他说:“我重 视节奏和韵律,诗之所以为诗,就靠着它们,但是,诗作中本来深切地影响着我们的, 实际上陶冶我们的,却是诗人的心血被译成散文之后而依然留下来的东西。即是,这时 剩下的是纯粹的完美的成分,因为诗体是一种绚烂的外饰,缺乏这种成分时,诗体也会 假装冒充,当这种成分存在时,这种外饰只会把它遮盖住”[24](pp.79~80),“韵是 表示诗句的终结,行较短时,即便是较小的韵节,句读也可以看出来,生来练就的耳朵 还听得出变化和韵味来”[24](p.80)。与歌德同时期不同国度的华兹华斯的“诗的韵律 ”观也具有改良色彩:“如果一首诗里,有一串句子,或者甚至单独一个句子,其中文 字安排得很自然,但据严格的韵律法则看来,与散文没有什么区别,于是许多批评家, 一看到这种他们所谓散文化的东两,便以为有了很大的发现,极力奚落这个诗人,以为 他对自己的职业简直一窍不通。这些批评家会创立一种批评标准,读者将从而得出这样 的结论:如果喜欢这些诗,就必须坚决否认这一标准。我以为很容易向读者证明,不仅 每首好诗的很大部分,甚至那种最高贵的诗的很大部分,除了韵律之外,它们与好散文 的语言完全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最好的诗中最有趣味的部分的语言也完全是那写得最好 的散文的语言”[25](p.10),“诗人只是从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进行选择,换句话说, 他正确地依据这样的选择原则去作诗,自然就踏上稳同的基地,我们知道他会得到什么 。关于韵律,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读者要记住,韵律的特点是整齐、一致,不象通常 所谓诗的词汇的所有韵律是硬造的,随意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是数也数不清的。在一 种情况下,读者就完全受诗人的摆布,听任他高兴用什么意象和词汇来表达热情;在另 一种情形下,韵律遵守着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是诗人和读者都乐于服从的,因为它们 是千真万确的,一点也不干涉热情,只是象历来所一致证实的那样提高和改进这种与热 情共同存在的愉快”[9](p.17)。在中国新诗人心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浪漫主义诗人拜 伦虽然在生活方式上与传统伦理格格不入到被正人君子驱逐出英国,但是他并没有完全 放弃诗歌传统和已有法则,不仅从英国传统诗歌中吸取营养,而且还从其他国度寻找适 合于自己的诗体,如他采用了意大利的韵律为abababcc“八行诗体”(ottava rime)。 “拜伦在使用这种诗体创作他的喜剧和讽刺性作品的代表作《唐璜》中显示出这种诗体 的巨大潜能,这部作品分为16个诗章,在1819年到1824年间分为四个部分写出”[2](p.48)。
拜伦、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如同中国“诗界革命”的诗人黄遵宪、梁启超等人 ,只是在“旧风格中写新意境”,对英语诗歌传统的格律诗体形式的改造不大。尽管雪 莱宣称诗歌跟那种一味着眼于调节和限制诗歌之功能的艺术是不能并存的,但是他的诗 歌改革更多在诗的内容、题材和功能上,在语言、体裁上仍较保守。所以他说:“我决 不赞成仅仅在文字上别出心裁,致使读者忽略我可能已经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线索,却 一味根据文学批评的原则去折磨他们探索我的技巧。一个熟悉自然、熟悉人类最杰出的 著作的人,在语言的取舍方面,根据直觉办事总是不会错的,其实,直觉本身就是熟悉 了这种情况而产生的。”[7](p.48)以他的享誉全球,特别是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西风 颂》为例,这首诗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诗人的政治革命热情和文体革命激情,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成为百年来中国新诗人的口头禅。但是,这首诗却是韵 律齐整的传统型英语诗歌,以最后一个诗章为例:
Make me thy lyre,even as the forest is:
What if leaves are falling like its own!
The tumult of thy mighty harmonies
Will take from both a deep,autumnal tone,
Sweet though in sadness.Be thou,Spirit fierce,
My spirit!Be thou me,impetuous one!
Drive my dead thoughts over the universe
Like withered leaves to quicken a new birth!
And,by the incantation of this verse,
Scatter,as from an unextinguished hearth
Ashes and sparks,my words among mankind!
Be through my lips to unawakened Earth
The trumpet of a prophecy!O Wind,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雪莱坚信世界和自然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种信念是雪莱哲学乐观主义的基础 。……在《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里,雪莱描写秋冬之来临。严寒覆盖着整 个大地,暴风雪在怒号;可是,另一个季候将起而代之,那时便会星移物换,万物欣欣 向荣。这首诗的最后几行是充满乐观主义思想的”[25](pp.335~337)。在“颂歌”体 诗的思想内容上,雪莱作了较大的改革,但是在诗体上,雪莱虽然也作了改革,却是极 有限度的改良,“虽然‘商籁体’(sonnet)是意大利诗体中最成功地输入英国诗歌中的 诗体,同时也有其他诗体传入英国,最受欢迎的是但丁在《神曲》中使用的‘三韵体’ (terza rima)……英语中也许最有名的‘三韵体’例子是雪莱的《西风颂》,但是,雪 莱将‘三韵体’与‘双韵体’(couplet)融为一体,由五首相似的十四行诗组成,使雪 莱的颂歌(ode)成为‘三韵体’诗与‘商籁体’(sonnet)系列的组合体”[26](p.634)。 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雪莱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对传统诗体的重视,特别是对传统的诗 家语是有韵律的语言的充分肯定。雪莱十分重视诗的语言的韵律特质,他在《诗辩》中 说:“语言、色彩、形状以及宗教和文明的行为习惯,是诗的全部工具和素材;倘若采 用果即为因的同义语这一说法,那么语言、颜色等等都可以称为诗。然而,较为狭义的 诗则表现为语言、特别是有韵律的语言的种种安排”,“诗人的语言总是牵涉着声音中 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假若没有这重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并且即使不去考虑那 个特殊的规律,而单从传达诗的影响来说,这种重现之重要,正不亚于语词本身。此所 以译诗是徒劳无功的”。[7](p.52)
中国的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更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带有较深的思想文化运动,甚 至政治运动的烙印,即新诗革命具有明显的非诗生态和非诗特征,因此重视人和国家的 现实生存的浪漫主义比重视艺术技巧的现代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尽管新诗革命适值西 方现代派诗歌取代浪漫派诗歌,本来中国诗歌更应该与世界诗歌同步,更受以法国象征 派和英美意象派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现代诗歌运动 (Modern Poetry Movement)的组成部分,“中国新诗产生之际,浪漫派时代已过,而流 行于欧美诗坛的是象征派所影响而形成的现代主义”[27](p.200)。但是,中国新诗诗 人却跳过了20世纪初的现代派诗歌,更多地接受了发端于19世纪初中期甚至更早的浪漫 主义诗歌,把它作为中国诗歌革命的主要动力。这既与中国人的厚古薄今的“经典意识 ”有关,更与当时中国需要极端的革命范例的时势相关。“浪漫主义并不存在于完美的 技巧中,而存在于和时代道德相似的观念中”[28](p.217)。这种观念导致受到浪漫主 义极大影响的新诗太具有时代精神和道德意识,对“革命”(政治的)的高度重视和对诗 体的建设(技巧)的极度轻视,轻使在某个阶段重视诗体建设,也常常是与“时代道德” 相似的文体革命。白话诗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类似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并不是 真正追求艺术技巧的运动,尽管胡适等纯粹的文人在新诗革命时确有这样的理想,但更 多的汉诗改革者,特别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政治革命者和思想启蒙者,更是视思想解放 和政治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及新诗革命的首要目标。即使是坚持艺术改革的诗人,生活在 国弱民贫的困境中,也不得不直面人生社会,由唯美主义者转变为为人生而艺术者,甚 至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诗人成为革命者。
夏志清针对20世纪上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创作所面临的那种激励所有主要作家的“道义 上的使命感”论述说:“中国文学进入这种现代阶段,其特点在于它的那种感时忧国精 神。那时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够发愤自强,也不能够改变它自 身所具有的种种不入道的社会现实,“这种感时忧国精神继而又把主要目光集中到文学 的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集中到得天独厚的‘现实主义’上——因为中国现代作家力图 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中的那种社会—政治混乱有所了解”。[6](p.481)由于20世纪初 的中国确实太需要浪漫主义式英雄来进行社会大变革,无论是在宣传译介还是在中国诗 人的实际生活中,雪莱、拜伦、雨果、歌德、席勒、莱蒙托夫等外国浪漫主义诗人在中 国都被人为地“拔高”,被英雄化甚至神化了,特别是他们的做人方式和作品的激进思 想更比他们的艺术成就受中国人重视。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少提及他们的艺术 成就,而是大力赞扬他们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激进行为。苏曼殊是最早翻 译外国诗歌的中国人之一,他为浪漫主义诗人英雄在中国的传播和神化起了巨大的作用 。1908年,他的第一本译诗集《文学因缘》在日本东京出版,后为在国内重印题为《汉 英文学因缘》,由英译汉和汉译英两部分组成,其中不少古诗由外国汉学家翻译。1909 年4月,苏曼殊译完《拜伦诗选》并作自序,同年9月,《拜伦诗选》在东京出版,后由 上海泰东书局翻印。1911年他在日本出版了第三本译诗集《潮音》,在序言中他比较分 析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大师拜伦和雪莱。1914年他编译的中英诗歌合集《汉英三昧集》 又在日本问世。“苏曼殊花很大的精力来介绍拜伦,有其特定的时代因素。从某种意义 上讲,这是清末中国掀起‘拜伦热’的必要产物。拜伦一生始终勇于同反动势力做斗争 ……这样一个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士,自然会受到饱经忧患的近代中国人的景仰和摧崇” [29](p.82),“在他翻译出版的《拜伦诗选》(1909)里,特别是他译的拜伦那首《哀希 腊》中,苏曼殊使这位英国浪漫派诗人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英雄,也许应当说是中国现 代文学中最负盛名的西方作家。苏曼殊把拜伦偶象化并且与他认同,这也为中国人接受 西方文学创立了一个有趣的先例:正如拜伦被苏曼殊崇奉为闪闪发光的拜伦式的英雄形 象那样,从此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的那种形象就要用他的一生和人格的那种传说来要求 和衡量了;而他的作品的那种文学价值则几乎很少受到注意”[6](p.527)。正如鲁迅所 言拜伦被中国人所知的原因是他的帮助希腊的独立,因为当时正值清末,在一部分中国 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拜伦很容易引起呐喊复仇和反抗的青年的感应。苏曼殊正 是其中之一,因此他译过雪莱、歌德、彭斯等多人的诗,却特别偏爱拜伦,所译的拜伦 诗也最多。尽管在他之前有人译介过拜伦,如1902年梁启超在他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 来论》里用词曲形式译述了拜伦的《哀希腊》的部分章节和《渣河亚》(《不信教者》) 的一段。1905年,马君武将《哀希腊》全诗译出,但是早期让拜伦被国人熟知甚至被“ 神化”的主要译介者是苏曼殊。
因为中国本土文化长期具有巨大的稳定保守性和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尽管有“外来 和尚会念经”的俗语,但排外的力量长期巨大。由于20世纪中国国弱民困,导致很多人 失去自信。甚至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因此这种把外国诗人,特别是浪漫主义诗人偶像 化的现象在20世纪十分流行,“在‘五四’时期,徐志摩和郁达夫以及创造社的其他成 员继承了苏曼殊的遗产,苏曼殊的这份遗产成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传统:外国文学被 用来支持中国新作家自己的形象和生活方式。由于他们自己那种膨胀了的自我和对英雄 的狂热崇拜,这些领导潮流的文人建立起一种个人认同的偶象:郁达夫与E.道森,郭沫 若与雪莱、歌德,蒋光慈与拜伦,徐志摩与哈代、泰戈尔……对西方作家的这种带有感 情色彩的偶象崇拜,还产生了一种相关的倾向,那就是把外国文学看作是思想的源泉。 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以及新浪漫主义这些概念,在这种狂热的精神支配下 ,和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科学、民主这些词一样满天飞。 对‘主义’这样极受欢迎的词的浅薄知识,就象对外国作家的那些鼎鼎‘大名’的了解 一样,马上就会带来显赫的地位”[7](pp.527~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