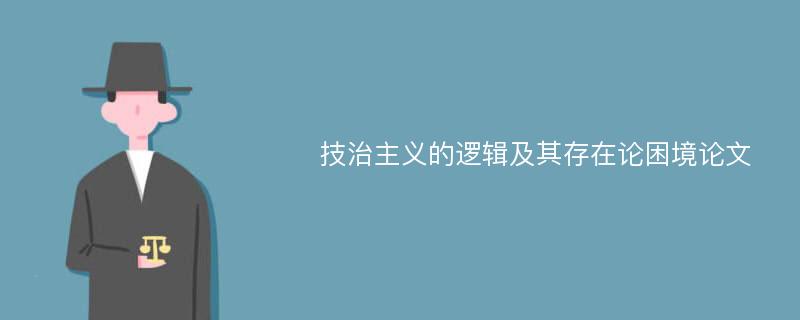
技治主义的逻辑及其存在论困境
滕 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在以必然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人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工具极致地拓展了主体生存实践的边界。与此同时,工具理性也深刻影响了社会文化结构及人的生存方式:政治模式完成了从前现代超越性的权威政治到现代功利性的技治主义的跨越。以技治主义为基础,传统社会也完成了向“规训”社会的过渡。在“规训”社会中,人完全被物化异化成为技术管理和支配的客体,辩证存在的主体面临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处境。为了克服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化状况,人在尊重必然性逻辑的前提下亦须积极建构交往理性,重建社会领域的规范性要求,以此为中介改变技术发展的方向,摆脱技治主义发展的存在论困境。
关键词 :现代性;工具理性;技治主义;存在论
柏拉图的《斐德罗篇》用埃及的古老传说讨论了技术工具应用的后果。神灵塞乌斯向国王萨姆斯显现他的各种创造,要求他向埃及人推广这些创造成果。萨姆斯根据自己的喜好逐一评判各种发明,亦臧亦否、毁誉两见。其中,谈到书写时,萨姆斯说,一旦人学会了书写,就会在灵魂中播下遗忘。他们放弃了过去依靠内在的资源积极训练并获得记忆能力的方法,而是利用各种符号来辅助。结果是人们自以为知识广博,但却很无知[1]。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所产生的各种成果显著地改变了社会文化结构:技术在创造优渥生活的同时逐步改造现代人的世界观,结果是现代人与传统政治和精神的纽带变得松散,即便技术和传统的世界观在对立中紧张地共存[2],但技术将致使其他超越性的选择无影无形、失去意义,形成极权主义的技术统治。因此现代人在惊叹科技成就之时,在欢欣鼓舞地拥抱现代性之时,亦须追溯社会结构发展史,谨慎应对“沉沦”现代性“无家可归”的存在论困境。
一
所谓的启蒙,就是指确立“人将自己确立为根据”这一思想事件。这一事件并非仅是几个伟大哲学家的凭空理论构设,而是一段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是日心说的提出、开普勒三大行星运动规律的发现以及伽利略的杰出贡献,他们共同构成了摧毁中世纪神学及纯粹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后牛顿“顺水推舟”将其推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连带着亚里士多德的万物有灵论也无法“幸免于难”。《圣经》失去了以往的神圣权威,甚至人的生存意义同样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最终以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观念在西方世界才算完成了它的“成人仪式”,至此人的生存意义才算真正失而复得——人成为主体、成为根本目的。在启蒙主流精神看来,人是主体,意味着人在观念中被理解为根本目的的同时被理解为自我决定者。主体不再怯懦地否定现实,而是敢于以对象化活动的形式与现实发生关联,或者说自己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而现实则成为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平台。在存在论的视域,这就意味着万物不再是遥远的、与自身对立的陌生他者,而是通过将他者纳入主体的生存体系,要在生存实践的具体境遇,在充分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征服他者,将万物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和工具。以此为契机,曾经一度被中世纪神学和形而上学所掩盖的理性、利益和欲望再次作为主体的意识被充分肯定、焕发生机、介入现实,并且要求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中不断被实现。
逐步建立遍布全国的地质灾害监测网络和预警信息系统,及时发现险情和隐患,及早应对。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加强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快速采集和处理灾害信息,建立灾害防治信息共享平台,实时共享信息。
启蒙的祛昧过程完成,即意味着超验原则的崩塌和世俗性原则的确立。既然个体的理性、利益和欲望都获得了正当性,世界也就不再从超越的、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上帝(他者)获得存在的指令,上帝(他者)不再成为价值根源。当新技术、新技艺涌现以及伽利略、牛顿和培根等人为自然科学奠基的时候,传统神学和形而上学对物质世界的权威记述便黯然失色,失去神圣信仰的世界被迫寻找“一个替代性的道德权威源泉”[3]。尼采指认上帝已死的这一命题准确表达了曾经统治世界的超感性世界的毁灭,以人作为根据的世俗生活获得了根本的意义。在世俗世界,超越的、与现实尖锐对立的彼岸预设被取消。在世俗世界中,宗教信仰反倒成为道德情操的修养方式,而不再是强制实行的教化条例。与之相呼应,政治权力不再从属于神圣的宗教权威,世俗的根本规则形塑了政治的基本形态,曾经高高在上的神权政治“偃旗息鼓”、彻底陨落,并成为世俗权力走上神坛的历史祭品。以世俗原则确立的现代社会,政教分离已经成为固定下来的现象,宗教不再成为个人生活的尺度,国家政治和个人生活都通过平等、民主等现代社会的观念获取了自身的世俗基础。在世俗化时代,个人不再倚重于宗教等超验原则,而是以自身全部的感性特征为存在的依据。
一旦人获得了世俗性的存在基础,个体性原则的确立就成为人存在的基本特征。个体将自身确立为世俗世界存在的中心,也就意味着将自身理解为存在论意识的依据。世俗世界确立人而非神作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之后,个体性原则进一步将自身从以神为依据的宗教权威统治中解放出来:人首先将自身看成目的,因此成为存活于世俗世界的独立个体。所谓现代,就是个体性成为存在原则的时代,就是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主体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对世界的理解并将其作为开展实践活动的依据。一旦主体意图在世俗世界中实现自己,即世俗化原则和个体性原则得到确立,实用性原则也就被提升为主体存在的基本原则,主体间的关系锐变成为以个体利益为轴心的现代生存体验。实用性作为世俗性的基本要素,就是说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逾越了超功利的信仰、道德和审美的界限,成为理性的内在要求。在这样一种内在意识的指引下,现实的存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金钱和利益构成了“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主的价值”,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4]。在这个充斥着冷冰冰的利己主义打算的现代社会,实用性原则成为现代的基本精神。人的生存被迫屈从于各种可计算性的价值衡量,科学、教育、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背地里都流淌着实用主义的血液。实用性成为时代精神的内在灵魂,而曾经高扬的理性也单向度化为工具理性。与实用性相适应,实证性成为认识的主导原则。在现代社会,人总是在充分领会世界物质性的基础上重构对其的深刻理解。人以物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同时看待自身,对象性意识指向了事物的必然规律。按照实证的要求,必然性的正确规律成为根本的时代精神基础,现代世界也就被重新组织和理解为按照必然性原则构造起来的物性世界。
以必然性为基础的物性世界培育了唯物论的世界观。按照世界的必然性规律理解、把握并改变世界,这就是以必然性规律为基础的现代性存在论意识。但是唯物论以绝对的物质和规律同唯心论以绝对的精神和意志理解世界一样,本身仍属于抽象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抽象的、绝对的唯物论以绝对的物质性、机械性和规律性来理解社会和历史,压缩了构建超越价值的可能空间。也就是说,它只看到了社会历史和物质世界抽象的同一性却忽视了具体的差异性,并形成了机械的社会历史概念。从“动物是机器”“人是机器”顺畅过渡到“社会是机器”,逻辑层次各异的结论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任何的“逾越”,而是必然规律性概念的顺次拓展,它们共同为技治主义的社会治理和权力体系提供了稳固的思想基础。人和社会完全按照必然性规律来理解和解释,前现代社会超越的神秘的命运范畴被必然性规律所取代,研究必然性规律的现代科学成为现代社会的新“神学”,成为指导现实生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规则。
3.5.3 拔管方法 应备齐用物,并按照推荐的流程操作[8]。用物准备:包括一次性使用污物盘或弯盘、垃圾袋、注射器及手套。操作流程:①检查所使用导尿管的气囊容量;②将污物盘放在患者的两腿之间;③用注射器连接导尿管的活瓣并且吸出气囊的所有液体;④解开导尿管固定装置;⑤将导尿管放入污物盘,并用纸袋覆盖;⑥从床边撤除集尿袋;⑦记录拔管日期及患者第1次自行解尿的情况。
二
在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存和实践方式发生了革命式改变,对其的存在论领会也随之革新。建基于必然性的现代社会,人将世界看成契合一定规律的物性世界,并且善于利用其规律实现目的,自由也就表现为规律性与目的性的耦合和统一。合规律性意味着对物性世界的规律性认识成为自我实现的基础。不同于追求真理意义的超功利主义认识模式,现代人将认识的目的设定为自我实现和自我展开的根本方式。因此,人开展实践、实现目的的首要前提就是正确的知识。人按照科学规律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必然性规律则构成了一切对象化活动的行为底线,唯有充分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利用规律才能实现人的本质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一方面成为客观化描述世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人的存在原则。正是在人以生存的目的将必然性规律纳入其生存的过程中,规律的存在论意味得以充分彰显,这种统一也是工具理性的基本内在逻辑。因此,科学认识转变成了目的性认识,理性则转变成为工具理性。以科学认识作为认识的基本原则,世界就不再是超越于主体之外的上帝的副本或表象,而是现实存在的物性实体。主体不再将从属于个人的超越性评价贸然加之于客观必然性的物性世界,而是如其所是地呈现物性世界的客观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成为主体描述客观世界的观念建构。科学知识提供了契合必然性规律的世界运行图景,因此具体的人生存于现实的世界就必然要求按照科学的精神或科学规则生活,一切生存实践都受到严格规定,人的身体、大脑和灵魂均被技术支配[5]。一时之间,科学成为主体存在的基本装备。过去,我们迷信宗教的权威;今天,我们无论什么事情都相信科学,是否符合科学成为存在论的首要追问。
传统意义的统治衍化为现代的治理,政治也就从超越性变成了技术性。在前现代社会,现实政治表现为以超越性特征为基础的政治,政治理论和政治叙事也就以超越实存的意味具体阐释政治的本质、功能和理想状态。在现代社会,政治完成了从超越性向功利性的关键跨越。对于现代政治而言,社会被重新理解和解释为按照必然性规律运转的机器,政治的功能和特征也就是按照自然科学范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综合治理,从而确保社会运转机制的顺畅和高效。曾经作为超越价值领域的信仰、德性等范畴不再是政治管理的核心内容,而是被强行驱逐到私人领域,变成了从属于个人生存实践的叙事基础。政治挣脱了宗教权威、道德权威的束缚,而是衍变成为纯粹的技术治理,技治主义成为统治现代世界的政治形式。政治不再追求与神性、德性的耦合,而是将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作为其根本的精神,合理、客观、高效成为政治实践的基本要求。政治研究沿用了自然科学的范式,政治行为的认识和分析方法服从于自然科学的逻辑。政治研究不再是传统的神学、诗学或哲学,而是科学,是将社会调查、行政关系、国际关系等纳入其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研究体系。政治研究不再青睐超越性的思想,转而寻求安全可靠的实用知识。社会的管理人员不再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而是善于利用技术工具、掌握科学理论的社会工程师。政治不再追求超越现实的伦理价值,而是现代治理能力的技术场域。技治主义实践的关键就是将实践奠基于关于社会现象的完善信息和充实而完善的管理技巧,技术治理成为当代政治的基本观念,技治主义成为当代政治的本质形态。
在现代,技术将对人的统治消融于物化关系的管理[11]。在技治主义看来,社会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行和发展的有机体,它的各个部分都存在着结构和功能的耦合关系。结构和功能的研究旨在恰当地掌控规律。传统意义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差异被彻底取消,“实证、实验的自然科学取得了本质性的地位”,并且“规定了对于科学的普遍理解”[12],凡是违逆自然科学范式、不能提供实证实用知识的学科都不具有科学的性质。传统学科研究通过提出暗喻、意象和理念等方式满足人类理解自身和社会的需要,但是却难以满足物性世界的实证化要求,超越物性世界和实存意义的人文学科或者被排除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围之外,或者被按照实证逻辑加以改造,因此大量学科都被转换成为符合自然科学范式的“科学建制”。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运行状态等等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事件描述分析、动态跟踪、任务分解落实、工作效果检查成为政治治理的日常内容。政治不再具有超越性的伦理价值,而是被切进社会有机体,成为维系后者良好运转的要素。因此,政治成为依据科学知识管理社会有机体的技术性活动,政治完全遵守科学性和技术性的要求,正确的技术知识和完备有效的管理技巧成为政治活动的可靠保障。
在媒体融合之前,在电视和报纸中很难发现新闻编辑的身影,他们最为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和记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对于各种新闻信息的加工处理等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受众的想法[3]。而在媒体融合时代下,新闻传播的主要阵地就是新媒体,并且很多人习惯用手机或者是电脑等接收信息,这也导致很多新闻编辑转战台前,还有一些直接担任公共论坛的主持人,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观众。
在必然性世界,科学知识成为把握客观世界的装备,实证性与实用性成为现代科学的本质要求。实用性与实证性同样规定了科学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原则,技术则一跃成为科学的具体指导规范,或者说技术就是科学知识对世界进行量化计算订制世界生产的能力,科学降格为技术生产的首要环节。在主体的具体生存实践中,技术的快速推广与应用成为科学的目的和意义,成为科学活动确证自身的首要论据,必然性的世界也就通过技术的运用被变革为技术世界。世界通过规律而存在,进行生存斗争的主体则通过运用规律进行生产实践。这个世界不再是外在于主体的自在存在,而是中介主体的技术化实践得以具体展开和呈现。所谓技术世界,本质上就是属人的世界,主体合理运用技术改造客体以符合主体的需求。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生产时代,是利用科学知识创造和改变世界的时代。这种依据科学知识生产和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成为现代人领会主体性及其自由的存在论维度。以技术作为依托,工业生产改变和创造新的物质以满足现实的人的需要,其本质是通过改变客观自然以创造新的价值。
“‘不与进口肥比价格,敢与进口肥比质量。’新洋丰这句宣传语还真不是盖得,这肥我要定了!”随着一位种植大户慷慨激昂地表态,现场出现了一阵抢购潮。农户们带着丰收的希望满载而归,新洋丰百倍邦套餐肥也将扬名东方。
三
当人将自身的存在论基础再次回归冰冷的世俗现实,回到绝对的物性实在,技术胁迫现代文化到其存在场域去“赚取权威”“享用指令”。彼岸的超越的精神被瓦解,被视为多余的、消极的或没用的东西排除在现代世界之外。现代社会完成了从超越统治到世俗统治的辩证发展过程,个体的所谓“解放”也就意味着超越价值空间的堕落和衰败。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对将政治理解为依据科学和技术手段研究社会和治理社会的技治主义的存在论批判成为重要主题之一。从这个世俗化的世界中再次燃起超越的光辉,重新在实在性的基础上建构起超越的意义价值空间成为现代人不应舍弃的理想追求,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追求“自我的超越性”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当下生存状况切实的存在论抽象。
1.2.5 目标设定 QCC小组按5分、3分、1分进行评分,得圈能力为86.7%。参照QCC目标设定公式:目标值=现况值-(现况值×改善重点×圈能力);目标为降低MDRO感染终末消毒流程缺陷率,目标值≈25%。
然而,工业生产的逻辑并非局限于物质世界的生产与再生产中,现代人将这一套逻辑全面拓展到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生产自然且生产社会的观念,当代表现形态就是技术对主体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斯·韦伯用合理性概念准确说明了服从于合理标准的社会领域扩大的趋势。不断拓展的各领域“合理化”与科技进步的固定化、制度化趋势相一致[6],技术不仅成为改变世界的手段和力量,而且成为理解世界的根本思维方式,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基础逻辑。必然性世界变成了技术世界,传统社会也就变成了现代技术社会。技术以追求精确而非真实的知识为目的,以及其非人格化的“优势”,能够有效地解决主体两难的问题。萨特说,人和事物互为“中介”[7],但实际上,人在实现超越的过程中被异化,作为物来处理,技术掌控了人-技术关系。在19世纪大工业时代,马克思曾预言人将演进为监督、调节生产过程[8],随着现代社会技术的发展,人不断放弃监督使用技术手段的角色,代之以被整合进技术系统的人的部分行为。人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悖谬性地实现自我否定,使用工具的人客体化[9],而劳动力分离并主体化[10],人类利用自身禀赋完成技术创造却最终解构了自身的独特性,即在实现自由超越的过程中自我瓦解。
社会有机体是技治主义的理论预设,主体是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程师。他们拥有社会管理所需要的知识,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治理社会的技巧,因此他们只须依据自然科学的规则运用知识和技术处理问题,就能确保社会治理的科学、高效和有序。技治主义一贯主张专家治国,而治理行为则始终追求科学、理性和中立。在治理过程中,主体变成了治理系统中抽象的存在者,主体的具体生存状况通过运算机制转变成为数字和图表,管理系统依据抽象的数字变化趋势和系统的图表分析结果确定灵活机动的管理策略。现实中具体的个人总是“被注视、观察、描述”[13],通过把个体的现实的生活客体化,管理者避免面对现实中具体生存的个人,而是精确地掌握数据并做出干预和调整。社会治理变成了抽象的数字游戏,依据客观数据和科学决策机制的政治实践不再是主体间的交往行为,而是知识信息的技术化生产和处理流程。管理人员对政治管理技巧的“中立性”运用使政治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在前现代社会,承担超越性意义的政治实践蕴含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现代社会,政治以技术为根本,在将世界看作自在的物性实体的同时,政治实践变成了以事实合理性和技术合理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治理活动。政治实践不再建构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空间,而是恪守事实性基础,统治的合理性以维护社会系统为标准[14],即政治也就从超越性的伦理活动变成了维护既定现实和秩序的活动。由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合法性机遇”,统治实体不但不会因为技术的力量而瓦解,反而利用了技术力量来维护统治的持存,祛除了意识形态纠缠的技治主义,运用合理性逻辑规避了政治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危机”。
由于个人和社会都被当作技术支配的对象,技术社会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管理监控网络,将个人的生存空间压缩为制约自由、限制生活的监控领域。现代社会的工业异化实质是更为普遍的文化异化的变异表现,是“规训”社会的特征,用福柯的话说就是,规训“造就”个人[15]。在这个“规训”社会,科学和技术在新的社会制度框架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福柯说,“监控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16],实际上,在当今无处不在的监控社会,个体行为正是被监控技术手段压缩塑造为标准化、规范化、同质化存在物,监控构造了现代社会的权力基础。依托于当代的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现代社会成为真正的无形的“全景敞视监狱”[17],社会管理机构对社会成员实施了无处不在的、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相比于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现代无形监狱的特点在于完全感受不到“需要被了解的事情的汇聚点”(监视行为)和“洞察一切的眼睛”(监视者本体)的存在。并非我们被无形的监控捕获,事实上是监控行为构成了现代人的存在样态。技术社会就是一个全面监控的社会,监控成为政治治理的运作机制和存在样态。在监控社会,科学知识和技术成为“可见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权力,成为统治(治理)的手段,社会监控和社会治理维持着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机制。具体生存的主体始终处于监控的范围并成为技术社会权力支配的对象,通过全方位的社会监控体系,技治主义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技术社会对个体实施的全方位监控实际上与个体的自我监控并存,也就是说,社会不仅对我们行使监控,我们同样通过技术对自身实施监控,将自己作为管理和支配的对象,以保障安全、维护持存。监控社会导致人时时刻刻生存在看似真实实则虚无化、荒诞化的生活镜像之中,主体本身处于“被隔绝和被观察的孤独状态”[18],而技治主义通过完善的监控社会形式达到了自身治理的目的。
以必然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依赖于正确的科学知识以及技术的广泛运用,主体的“自我超越性”颠覆了自在的自然,世界也就成为技术生产和监控的人造空间。在这个人造空间中,超越实存的意义及价值被还原成必然的物性实在,科学技术的必然性规律成为主体超越的底线。因此,超越的价值和精神尺度不再成为主体对象性活动的限制因素,也不再成为主体生存的目标和旨趣。事实层面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主体行动的底线及限制,科技伦理的拷问并不完全限制、阻止科学进步的步伐,也就是说必然性虽然构成了主体自由的底线,但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主体不断趋向这个底线,不断瓦解曾经的价值要求和伦理规范,社会形态的差异也就具体表征为事实和规范的“龃龉”。
四
主体面对自在的世界并非仅受必然性约束,后者仅是主体敞开生存体验的一种方式,后者的限制也就构成了主体自由的边界和底线。然而,在技术社会,必然性的限制掩盖了其他所有可能,表现为唯一值得遵守的行为底线,其底蕴就是现代技术社会的工具理性将人物化,用梭罗的话说就是,我们已经沦为工具的工具。在现代技术社会,“人的自我客体化”似乎已经通过物化、“有计划的异化”[19]等形式不可避免地完成。这也就是所谓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事实上,在分析层面,主体的交往实践由现实的制度框架决定,也就是说主体的行为规范受到法律的消极限制或道德的积极倡导;主体的生存实践由技术系统决定,即主体通过对象化活动主动适应客观的自在自然,摆脱自然的限制。而在现代技术社会,文化世界的超越性制度框架被整合进技术系统,遮蔽了制度框架的文化历史联系,抹杀了人类经验的规范性和技术性之间一切重要的区别。技术不再是所谓的中性的工具,而是属社会的。技术在当代的社会制度框架中不是边缘性的决定因素,而是起着核心作用的支撑力量。现代技术社会的制度框架牢固“焊接”在技术系统及其成果之上,而非前现代社会那样,由超越性的宗教权威或意识形态力量支撑。
科技本质上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表明了主体存在方式的独特性。科技的发展表明主体能力的增强,乃是在世的一种方式,科技不是也不应成为现实生活之外的统治人的现实力量,也就是说,主体“具象化”的生存实践除了受必然逻辑限制的同时必须享有规范层面的约束,事实的必然性逻辑同样需要中介规范性才能得以完善表达。事实必然性虽然是主体生存实践的底线,但绝不能构成生存的唯一规则或最高规则。人将自己确立为生存的根据和目的,而在交往活动的领域却不再适用必然性规则。在交往实践过程中,主体之间不再是以必然性规律认识和改造他者,而是以基本的平等和自由作为存在的基本方式。为克服工具理性单向度化状况,实现对合理性“恶托邦”的批判,马尔库塞希望将主体的超越价值整合进技术结构。但是即便现代人对技术统治越来越不信任,现代人的技术依赖性却不断增强,当下的现状就是虽然“没有把异化伪装起来,但也没有从系统中逃脱出来,没有能够集聚和动员非异化的历史主体的各种能量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避难所”[20]。因此当前理论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彻底摧毁限制主体生存的技术系统,而是通过建构交往理性,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21],利用新策略改变技术的发展方向,以摆脱当前的存在论困境。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5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6-137.
[2] [3] 波斯曼:技术垄断[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8,95.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5] [10]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6,36.
[6] [14]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38,40.
[7]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1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0.
[9] [11] [19] [21] 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61,367,379,379.
[12] 罗骞.告别思辨本体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9.
[13] [15] [16] [17] [18] 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215,193,194,224,226.
[20] 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0.
The Logic and Existential Dilemma of Technocracy
TENG T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is based on necessity, man has perfectly used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to extend the boundary of the subject survival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lso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social 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way of living of man: the political model has spanned the jump from transcendental authority politics of pre-modern society to utilitarian technocracy of modern society. Thus, traditional society also become a "discipline" society. In "discipline" society, man have completely been materialized into the object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domination, dialectical subjects face the existential dilemma of self-denial and self-destruction. To overcome the one-unidirectional situation of tool rationality, man should respect the logical premise of necessity and actively construct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reconstruct normative requirements in the social domain. As mediation, it may change the direction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get rid of the present existentialdilemma.
Key words : Modernit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echnocracy; Existentialism
收稿日期 :2018-07-26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资助项目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滕藤(1989-),男,汉族,江西省丰城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及现当代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N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2815(2019)01-0027-06
标签:现代性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技治主义论文; 存在论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