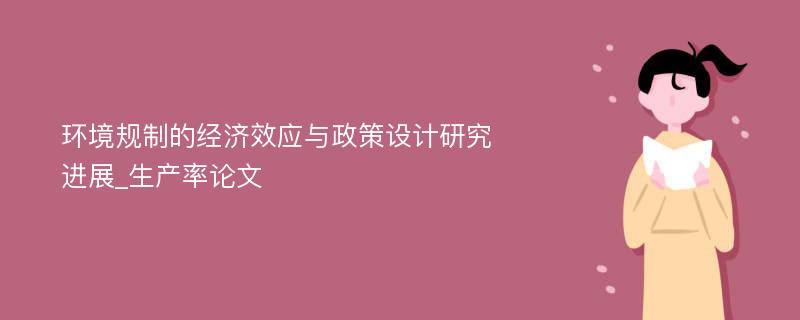
环境规制经济效应及政策设计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效应论文,规制论文,环境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4)01-0070-07
在全球环境公害事件频发和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日益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环境恶化问题。因此环境规制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或者效果的研究,其二是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因素及规制工具设计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各国环境规制政策实践和评价环境规制政策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环境规制与其他经济变量,主要是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等关系的研究。
(一)环境规制与生产率
关于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评价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目前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诸多争论。一些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于生产率无显著相关关系,另一些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会降低生产效率,还有一些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提高生产率。
Brannlund选用1913~1999年瑞典制造业部门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和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并没有显著关系。他认为导致这种结论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本身就不相关,二是测度环境规制的变量没有对环境规制强度进行真实反映。[1]Kenneth J.Arrow和Michael D.Inteiligator就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分析和总结,认为在前人关于环境管制政策与生产率的研究中,都发现美国的环境规制政策与生产率的下降有直接关系。尽管许多其他因素也造成了生产率的下降,但环境管制政策的确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关于环境规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妨碍生产率的增长,尚未得到任何可靠的量化评估。[2]Alpay等对墨西哥食品加工业的生产率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墨西哥食品加工业面临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但该国食品加工产业的生产率在不断增长。他们对环境规制与食品加工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0%就会导致生产率增长2.8%。[3]谢垩关于环境规制对于中国工业生产效率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和减少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对于工业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影响。[4]王兵等将环境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应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方法,对1980~200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17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包含二氧化碳排放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进行了测度,并对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5]叶祥松和彭良燕对无、弱、中和强环境规制4种情形下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1999~2008年间的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规制成本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测定,并应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方法对各地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和分解,最后应用面板数据对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会提高。[6]张三峰、卜茂亮在2006年对12个城市的中国企业进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就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不同区位的企业在环境规制下生产率的增长存在较大差别。[7]李静、沈伟应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析方法,选用1990~2009年的数据,对中国除西藏和重庆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包含工业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排放的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从实证角度检验了三种污染物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中国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维持较高的环境技术效率。[8]
关于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到的结论有所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和选用的数据有关。但不管实证研究结果如何,我们应当承认,在人们对于环境质量需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之下,政府应当积极采取一些环境规制措施以维护公众利益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也应在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通过有效的制度、技术和管理创新,推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资源消耗成本,积极主动化解环境规制压力。同时政府应当通过税收、补贴和银行信贷方面激励和引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环境规制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对个别企业和地区的生产率和利润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却有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和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二)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
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一个多维度复杂性的问题。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生产成本、贸易模式、产业选址和贸易得利等指标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国为保护本国消费者利益和国内生态环境,制定了各种环境规制措施。但由于各国制定和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严格程度有所差别,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有些甚至成为自由贸易的环境壁垒。
关于环境规制与贸易比较优势的研究有两个著名的假说,即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和要素禀赋假说(Factor Endowment Hypothesis)。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若一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其贸易伙伴,那么该国具有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而环境规制的强度与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成正相关。要素禀赋假说认为,一国的贸易比较优势由该国的要素禀赋决定,资本密集型产品往往是污染密集型的,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资本比较优势,因而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这两种假说为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提供了相反的解释。Cole等采用日本41个产业1989~2003年的数据,构建了产业层面的回归方程,研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这一变量是日本从中国的进口、从非OECD国家进口和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这3个被解释变量的决定因素。环境规制对发达国家贸易流的影响小于发展中国家。[9]Busse讨论了WTO规则下的贸易与环境规制问题,他采用了大样本分析法对5个高污染行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但对于钢铁行业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净出口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10]黄顺武对就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研究结果表明,GDP等宏观经济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11]郭红燕、韩立岩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环境规制的双向关系进行了验证。其研究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经济规模、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环境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扩大中国经济规模而使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加剧了环境恶化程度。但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进而可以提高环境质量。该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总效应是正的,但这种效应并不明显。[12]尹显萍对中欧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之间的关系应用一元回归模型进行了验证,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指数与进出口指数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相关性。[13]陆旸选用2005年52个国家的总样本和42个国家的子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eamer(1984)和Tobey(1990)运用的HOV分析框架,使用环境规制内生变量和环境规制外生变量,对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并没有降低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相反,较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还使部分污染密集型产品(如化工和纸浆等产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得到了提升。其研究结论某种程度上验证了Porter和Vander Linde关于环境规制可以使污染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比较优势得以提升的观点。[14]赵玉焕选用1992~2000年我国纺织业的数据,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环境规制标准的变化与纺织品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纺织业作为环境敏感型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在短期中会加大纺织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从长期而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有助于我国纺织业企业突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增强其国际竞争力。[15]李宏兵、赵春明在对贸易部门分类和工业部门分类并对23个制造行业进行重新归并的基础上,选用1998~2010年中国和美国的行业面板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两种环境规制指标进行了测算,并阐述了环境规制对于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水平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和实际污染物综合排放指数来度量,而二者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中国对美中间产品的出口,但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小于清洁行业的作用。[16]傅京燕、李丽莎使用我国24个行业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环境规制指标和污染密度指标,对环境规制与比较优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并非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因为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不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同时该研究还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倒U型”。[17]
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对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的观点不尽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研究国别、研究行业、研究方法和研究数据的差别。尽管如此,我们应当承认,环境规制可以提供明确的产品质量信号,有助于保护进口国消费者的利益。另外,进口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出口国企业存在“环境倒逼”机制,这种机制有助于出口国企业提升产品的环保标准,刺激出口国企业改进技术和改善管理。但是如果环境规制政策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则会对在自由国际贸易产生损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其环境规制政策建设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中国的国内环境规制政策对于进出口贸易的促进和阻碍作用有限,而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多边合作对于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贸易收入流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但是国内外的严格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促进我国外贸结构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作用从长期而言更加明显。
(三)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
环境规制是企业生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也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区域科技政策有重要影响。如何通过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企业和地区的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意义重大。因此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逐渐兴起。
Hamamoto通过对日本制造业的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和治理污染支出的增加,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也会随之增加,进而会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18]Wagner应用负二项和二进制离散选择模型,对德国制造业的环境管理和专利申请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专利申请活动与环境管理体制的实施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9]李平、慕绣如就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能源使用效率较高,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相反,在能源使用效率较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同时,该文应用行业面板数据就环境规制对于不同污染密度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对中度污染产业的技术创新影响并不明显,对轻度污染产业的技术创新有阻碍作用。[20]黄平、胡日东分析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棘轮效应,即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时期效应和强度效应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博弈规则推进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也可以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对环境规制产生反作用。[21]沈能、刘凤朝利用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从全国与地区两个层面进行了判断,并且就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不同,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波特假说”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得到了验证。同时该文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波特假说”只有在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特定的门槛值时才成立。[22]王鹏、郭永芹以中国中部6省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环境规制与中国中部六省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科技经费支出和科技人员数量对于中部六省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环境规制水平与专利授权、专利发明等技术创新指标存在负相关。[23]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影响因地区、行业的不同,其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会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什么地区、何种行业都应当积极适应环境规制的要求,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和发明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清洁生产,降低环境污染。这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无论是企业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利益,为了短期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
二、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因素及规制机制和工具设计的相关研究
(一)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因素
Blondia和Rousseau构建了规制部门和被规制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部门的目标函数与环境规制标准实施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环境规制部门在实施环境规制过程中,不仅要考量如何将环境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要考量减少对被规制企业的惩罚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但该文献没有量化这两种因素对于规制部门决策的影响程度。[24]Eckert对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从而为分析地区的环境污染历史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启示。Eckert以加拿大马尼托巴省1981~1998年储存数据为依据,对政府规制行为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某地区实施环境规制的概率与其附近地区环境违约的历史之间存在相关性,附近地区环境违约的现象增加会使该地区被实施环境规制的概率提高。[25]Earnhart对污染物排放设施的特性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以美国1995~2001年的化工设施数据为依据,检验了化工污染物排放设施自身特性与废水排放量限制标准对政府环境规制效率的影响。该研究认为规制部门在对被规制企业实施环境规制时应当充分考虑排放设施自身的特性对规制政策的影响。[26]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从规制部门的目标函数(环境损失下降与环境规制的社会成本)、临近地区环境违约的历史以及污染物排放设施的自身特征等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中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外生变量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同时,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发达国家环境规制政策影响因素的分析。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环境规制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基本上出于空缺状态,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环境规制政策本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是将来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环境规制机制和规制工具的设计
Hueth和Melkonyan在对环境风险监管标准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若环境规制部门了解足够的技术,则新的环境设计标准就可以有效改善福利。他们在环境规制工具的设计方面非常强调对被规制企业的监管、过程核查和监测的信息传输。Hueth和Melkonyan对电力污染企业的环境规制设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规制部门实施环境污染治理时,被规制企业往往会采取隐藏污染信息的行为,因此规制机构必须加强信息核查和传输。[27]Bontems等对外部环境下私人生产合同的优化调节进行了分析,认为规制者、被规制企业和代理人之间的三层结构中存在双向道德风险问题。规制只有在对内生性组织的选择有重要影响时,这种规制才会被明确考虑。该研究构建了环保部门、承包者和代理人的三方博弈模型,并假设产量和污染具有可观测性和可核查性质,主张通过激励理论克服道德风险。[28]Malik构建了关于环境规制的委托—代理模型,模型认为规制者可以获得被规制企业减排的两种信号,即企业排放信号和企业行为信号,但获知这两种信号要付出成本。Malik的研究结论认为,当环境规制部门获知被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水平时,其最优的规制政策选择是不论被规制企业对规定的遵守程度如何,只要其有违约行为发生都应对其进行最大惩罚。当环境规制部门获知被规制企业减排的两种信号时,其最优规制政策依然选择最大惩罚。当环境规制部门观测到被规制企业初始信号的中间值时,规制者应对被规制企业进行调查。[29]Bayranoglu研究了国际环境协定的设计和协定的设计如何激励私人部门对环保技术的投资问题。该研究认为,以可转让协议的实施为基础的统一标准对于协定参与的两国更可取,因为它可以为公司创造更大的投资于减排技术的激励。[30]Rousseau对于环境代理的合理检查时间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环境代理检查对于企业的约束作用。该研究认为,环境检查代理商通过非随机方式对企业进行检查虽然可以解决大部分环境问题,但如果政府对企业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和制裁措施将会进一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31]易伟明、李志龙认为,地方保护主义和环境规制部门规制的缺失是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他们通过构造博弈模型,从政府对环境保护部门的再规制方式出发,通过对环境规制部门的规制行为选择和被规制企业的行为选择进行分析,认为将环境规制部门纳入国家环保总局的垂直管理体系会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同时政府对环境规制部门的再规制政策,可以有效提高规制部门的积极性。[32]马士国对于基于市场化的环境工具进行了阐释,认为诸如排污费和可交易排污许可等市场化环境工具可以推动排污技术的进步并可以节约成本。同时马士国认为不同的环境工具在减排效率和减排技术激励等方面存在差异,应多方权衡才可以制定出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33]
国外学者对于环境规制机制和工具的设计主要通过构建模型来进行分析,强调信息因素对于环境规制机制设计的影响,重视规制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其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注重规制中激励机制的设计。通过对国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机制和规制工具的设计可以看出,环境风险的规制标准、最优规制机制的设计和国际环境协定的设计逐渐成为国际环境规制研究的重点。同时,制度分析、数理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相互结合逐渐成为环境规制研究的主要特点。然而,国内学者关于环境规制工具的设计研究相对于国外研究而言较为落后,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在数量分析和计量分析上和国外学者相比存在差距。
三、研究展望
随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推进,对于环境规制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关于环境规制政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仅要重视分析外生变量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也要重视内生变量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不仅要重视经济因素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也要重视非经济因素,如习俗和文化对于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
第二,关于环境规制工具和机制设计的研究,不仅要注重区域内部环境工具的设计,同时也要注重开放经济下环境规制工具的国际合作。环境问题不仅具有地域性,而且具有全球性,环境博弈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全球博弈,一些跨国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环境政策对单个国家的环境规制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研究不仅要重视短期效应,也要注重长期效应和社会效应。同时要特别注意环境规制的滞后效应,因为有些环境规制政策效应的发挥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