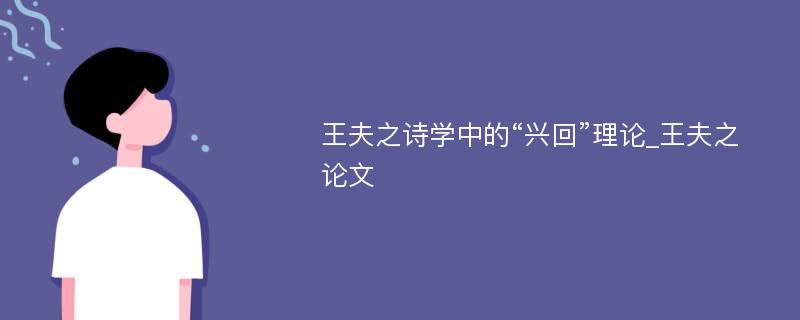
王夫之诗学中的“兴会”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会论文,诗学论文,王夫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兴会,作为我国古代文艺创作传统中锤炼出来的审美范畴,通常是指审美感兴或艺术直觉中的灵感。魏晋六朝以来,沈约、颜之推、张怀瓘和李善等人直接在文艺评论中使用“兴会”这一术语,在他们那里,“兴会”主要是指文艺家在瞬间直觉中对自然山水或宇宙人生进行深刻的、本真的体会和把握。如李善所说的“兴会,情兴所会也”(李善《文选注》),就是对“兴会”的简要定义。但直到明清时期,“兴会”才成为文艺家常用的范畴。
王夫之的兴会说是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灵感或直觉理论的总结和阐发,他在诗学论著中直接运用“兴会”这一术语达十次以上,他还常用与“兴会”同义的“即景会心”、“寓目警心”、“触目生心”、“即目成吟”和“适目当心”等术语评诗,而且用“现量”对其兴会说加以理论阐释。在艺术灵感或直觉这个领域,王夫之比以往的和同时代的文艺家更自觉,更深刻,更系统,更富于创见(注:在中国古代,皎然、韩愈、孟郊、贾岛、白居易和李贺等人都曾主张作诗需要“苦思”或“苦吟”而钟蝾、王昌龄、司空图和严羽等人主张“即目”、“直寻”、“目击其物”、“妙悟”。王夫之反对在格律和词句上的推敲或苦心积虑,主张“即景会心”的艺术直觉,从而继承和发展了钟嵘以来艺术直觉论的优良传统。与钟嵘等人的艺术直觉论相比,王夫之的兴会说具有多侧面、多层次或兼容性的特点,更深刻地揭示了诗歌艺术思维与创作的性质。“即景会心”、“现量”、“灵心”、“会通”或“心目”,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王夫之的兴会说的博大精深。)。
很多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灵感理论给予高度重视,但却常把“兴会”与艺术直觉等同起来(注:兴会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艺术直觉。我们可以说兴会是直觉,但不能说直觉是兴会(灵感)。从一般的理论上说,兴会不能等同于艺术直觉,但在王夫之那里,兴会与“即景会心”和“现量”基本上是同义词。)。很多学者把王夫之的兴会说称为“灵心”、“会通”、“现量”和“即景会心”等。我以为,把王夫之的灵感理论称为“兴会”比较恰当。
艺术直觉是文艺家在物我合一的情境中基于感性直观的超理性的审美感受,时常体现在文艺创作过程(艺术积累、艺术构思和艺术表现)中,甚至贯穿于创作过程的始终。而灵感则像闪电(很多中外文艺家如尼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不约而同地把灵感比作闪电)一样爆发出来。可以说,灵感是具有高度创造性的瞬间直觉,是文艺家在艺术构思或创作中所获得的高峰体验和促成伟大创造的契机。
王夫之非常重视兴会(不同于一般直觉)的直接性、突发性、创造性和言与意的统一性等方面的特征,他的兴会说散见于其诗学论著中,与他的哲学思想和诗歌创作与鉴赏的经验相贯通,显得微妙、深邃而又丰富。
一、兴会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王夫之说:“一用兴会标举成诗,自然情景俱到。恃情景者,不能得情景也。”(《明诗评选》卷六)他历来认为情景妙合,不在刻意,情与景是诗的二要素,情景交融是意象或意境的基本规定。所以,若无兴会,即便情景兼备,也难有佳作。而“兴会成章,即以佳好”(《明诗评选》卷五)。
风格是作家成熟的艺术创造力的标志,而兴会直接关系到作家风格的创造(在诗的领域尤其如此)。王夫之非常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兴会不亲而谈体格,非余所知也……”(《唐诗评选》卷四)因此,他常以“兴会”为标准来衡量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兴与艺术表现的能力,“吾特赏其兴会”(《唐诗评选》卷四)等词语是他给予来鹏等诗人的高度评价。
诗歌创作的基本条件是体物、感兴、达情,而兴会与此息息相关。王夫之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这就是说,灵通之句源于诗人即景会心的灵感或直觉,而非技巧或字句的苦心经营。若仅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求巧,即便能“巧”,也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同上)。这样,只有通过兴会,诗人才能达情、会心、得景、传神,才能有灵通之句,从而实现“参化工之妙”的伟大创造。
总之,从诗的情景、风格或灵妙创造的角度看,兴会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二、兴会的基本涵义
王夫之在不同的地方谈论兴会,通常各有所指,各有侧重,这要求我们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以免误解。大致说来,在他那里,兴会是诗人即景会心、意无预设、呈现神理的瞬间直觉。
王夫之诗学的核心原则是:“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乃为朝气,乃为神笔。”(《唐诗评选》卷三)他认为此中尽有文章之道、音乐之理。兴会是诗人直观景物时的心领神会(即景会心)。对天地间流动的绮丽的“自然之华”,诗人以心目观照,“文情赴之,貌其本荣,如所存而显之,即以华奕照耀,动人无际矣。古人以此被之吟咏,而神采即绝”(《古诗评选》五卷)。王夫之由此继承了古人观物、感兴、传神的传统,确立其兴会的逻辑起点,在高扬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同时,注重主客合一的艺术体验。诗人以“广目细心”,观审“天壤之景物”,“灵心巧手,磕着即凑”(《古诗评选》卷五)。兴会体现为“心中目中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这要求诗人具有深邃、广远的审美心胸或怀抱,王夫之经常强调,若诗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则难以求得与情怀相迎之景。
所谓“意无预设”,主要是指诗人在审美感兴时不带成见或先人为主之见。“鸟道云踪,了然在人心目之间,而要不可为期待”(《古诗评选》卷五),兴会乃不期而遇,“灵光之气,每于景事中不期飞集”(《古诗评选》卷四),在兴会的瞬间,诗人获得意料之外的独特感受和令人惊奇的创造性意象。针对预设法式或“分节目,起议论”之类的诗坛弊病,王夫之强调说:“意无预设,因所至以成文,则兴会尤为有权。”(同上)鲜明生动的意象或神理由兴会而得,可谓初无定景、初非想得,这与苏轼所说的文章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答谢民师书》)似有相似之处。“意无预设”的兴会,唤起惊奇、新鲜、微妙的高峰体验,导致独特的意义生成。在即景会心的富于创造性的瞬间直觉中,诗人“获得一种新奇的力量,一种初次发现的力量”(帕乌斯托夫斯基)(注:参见帕乌斯托夫斯基《面向秋野》,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那有意味的境界好像是“第一次被召唤出来似的(海德格尔)(注: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7页。)。
王夫之对严羽的“诗有妙悟,非关理也”这一命题颇有异议,在他看来,“非理抑将何悟?”(《姜斋诗话·诗译》)他反对于理求奇或以“名言之理”(逻辑概念之理)人诗,但非常重视以理居胜的诗,把理看作诗歌意蕴的主要因素,主张诗歌呈现“神理”。他认为足人风雅的诗说理而无理臼,通人于诗不言理而理自至,古今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是“神理、意致、手腕三绝”(《唐诗评选》卷三)。这种对“理”和“神理”的赞赏在他那里不胜枚举,可谓无以复加。而诗人在兴会中体悟并呈现神理,可谓深入之至。
在王夫之那里,“理”与“道”一样,主要是指万事万物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理寓于万物之中。诗中之“理”与意象交融,隐含于浑成的诗境。王夫之说:“理关至极,言之曲到。人亦或及此理,便死理中,自无生气。此乃须捉着,不尔飞去。”(《古诗评选》卷五)这就是说,对诗至关重要的理,应由诗人含蓄自然地加以表现。理在诗中一旦露出形迹,诗就会了无生气。
王夫之所说的“神理”是非常微妙的概念,从一般的美学、诗学辞典和学者的著述中,我们难以找到关于“神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果把“神理”看成是艺术作品中的自然神妙之理和作家在审美观照、艺术创作时的思理、条理,就难免有失偏颇。如果把“神理”看成是与“理”一样的客体属性,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以为,在王夫之那里,“神理”不仅关涉着人性、物理和诗意,而且是就主客合一的艺术境界而言的。
王夫之说:“天地之生,莫贵于人矣;人之生也,莫贵于神矣。神者何也?天之所致美者也。百物之精,文章之色,两间之美也。函美以生,天地之美藏焉。”(《诗广传》卷五《商颂》)由此看来,宇宙人生与艺术之美要由“神”来把握、发现或观照,宇宙人生与艺术之道也就是“理”,“神理”是宇宙人生与艺术之美的内在根据,寓于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神理流于宇宙间。王夫之说:“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落笔之先,匠意之始,有不可知者存焉。”(《古诗评选》卷五)神理和对神理的艺术表现具有不可知的神秘性。这与其说是他的局限,不如说是他的高明之所在。即便在今天,谁能把“神理”一语道破?宇宙人生与艺术创作的神秘性,也许恰恰是其永恒魅力的重要原因。从宗白华、泰戈尔到雪莱、布莱克和马利坦,很多文艺家都从对宇宙人生的观照中体悟到无限的神秘。如马利坦曾说:“诗人就是在诗性直觉中领会到世界的神秘中的某种独特的神秘的。”(注:转引自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3页。)而艺术家通常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创作中参见化工之妙,寻求意义的瞬间生成。
神理寓于人的审美心胸。王夫之赞刘基诗《旅兴》:“其韵其神其理,无非《十九首》者。总以胸中原有此理此神此韵,因与吻合。”(《明诗评选》卷四)由此说来,伟大的艺术创造从来不是因袭与模仿的产物,而是文艺家心中神韵妙理的外化。这与济慈等欧洲诗人的看法基本一致:“我曾在天堂中受到教诲/让我胸中的旋律自由自在。”(注:转引自雅克·马利坦《艺术地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21页。)“诗来自内在的源泉,在一个概念形成以前,它完全反映了外在的无数意象的韵律。”(马拉美)(注:转引自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7页。)“灵魂中没有乐感的人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天才的诗人。”(柯尔律治)(注:转引自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占1991年版,第217页。)
神理蕴含在诗中。王夫之说:“霏微蜿蜒,嗟吁唱叹,而与神通理。”(《诗广传》卷五《商颂》)诗的形气与神理交融,而“神理”可谓与神通理。诗的形神兼备导源于主客合一的审美感兴。“神则合物我于一原。盖耳目止于闻见,唯心之神彻于六合,周于百世。”(《张子正蒙注·太和篇》)王夫之由此强调神思或审美想象的重要性。这也是兴会的基础和前提。
王夫之在描述兴会时曾说:“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这就一方面指出兴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或无意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诗中看似无关、无理的情思与景物在因神理而沟通契合时,显得自然恰切。同时也表明,神理并非“神妙之理”(有的学者由此望文生义),神在于主体,理在于客体,神理凑合唤起诗人即景会心的灵感,达成情景妙合的艺术创造。
诗人在兴会中对神理的呈现可谓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在天合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不用意而物无不亲”(《古诗评选》卷四)。总之,兴会是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无比活跃的状态,是在“空微想象中忽然妙合”(《明诗评选》卷八),源于景物又发自内心,不涉思辨又合乎神理,是审美感兴达到极致的瞬间直觉。
三、兴会的基本特征
限于生理学、心理学和诗学等方面的局限,20世纪的中外学者在艺术灵感问题上虽做过许多探索,但难有重大发展。以至于提起艺术灵感的特征,人们通常想到突发性、直觉性和创新性(这是艺术灵感与科学灵感共有的特征),而如此简明的看法远非众所周知。很多文艺家善于描述灵感,但难以说清灵感是什么。也许,灵感像美、爱和幸福等问题一样,始终是难以界定的。
王夫之在把握前人学说的基础上,结合他本人的诗学观念,着重从诗的角度出发,对兴会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看法。
其一,偶然性或突发性。王夫之认为,诗的灵通之句或化工之笔来自于即景会心的瞬间直觉。换句话说,佳妙诗句通常是“偶然凑合”或“偶然凑手”的结果。情景妙合、匠心独运的诗通常由“天籁之发,因于俄顷”(《古诗评选》卷四)的兴会而得,可谓“笔授心传之际,殆天巧之偶发,岂数觏哉?”(同上)
诗人的兴会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以物我合一的审美体验和即景会心的艺术直觉为基础,诗人超拔的体物、达情和传神的能力是兴会的前提条件。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多次表明这个看法:诗人的想象游于古今上下之间,诗人的情怀可谓“心悬天上,忧满人间”(《古诗评选》卷五),诗人的风神思理可谓“一空万古,共求伯仲”(《古诗评选》卷四),诗人的艺术才能可谓取神似于离合之间,韵脚中见化工。惟其如此,才有偶然突发的兴会。
王夫之评汤显祖诗《吹笙歌送梅禹金》:“搅碎古今,巨细人其其兴会。从来无人及此,李太白亦不能然。”(《明诗评选》卷二)他所推重的“搅碎古今”主要是指诗人能够言含万象,意通古今,诗人对宇宙人生须有整体把握(洞观)的能力。偶然突发的兴会来自于诗人通天下之情、尽古今之变的审美观照,此可谓瞬间关乎永恒。
其二,直接性和直觉性。在王夫之看来,诗是空微想象中忽然妙合的兴会的产物,而“想象空灵,固有实际”(《古诗评选》卷四),诗人的想象或兴会离不开对事物直接的审美观照。
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诗乃一目一心所得,不安排,不扯拽。这一重要的诗学原则表明:好诗并非道听途说或苦思冥想的产物,审美感兴也像认识活动那样可由间接的途径达成。
在直接的审美观照中,诗人即景含情,写景至外,心目不相暌离,从而“适目当心”,乃可入咏。由此出发,王夫之提倡诗应“立主御宾,顺写现景”(《唐诗评选》卷三),不因追忆。他说:“情感须臾,取之在己,不因追忆。若援昔而悲今,则为妇人泣矣……”(《古诗评选》卷五),这一看法的合理性至少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中国诗语言简洁、凝炼,篇幅短小,宜于即兴创作,能在兴会中达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语,参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的效果;其次,中国诗的抒情特色或形式因素使之适于“寓目吟成”,王夫之常说的“触目当心”、“触目生心”、“触目同感”、“触目得之”、“寓目警心”和“即目成吟”等都强调兴会的直接性和直觉性以及艺术表现时的“不因追忆”,如此赋诗,常常可以突破诗人的理性与诗的法度、格律或程式的拘束。应该说,王夫之对中国诗(乃至绘画和书法)的特性把握得很准确,很深刻,他的观点与西方的“诗言回忆”说大相径庭。这与中国诗的抒情传统和西方诗的叙事传统有很大关系。
兴会的直接性总是与直觉性相伴随,所谓即景会心、会景生心、触目生心和寓目警心等都是指诗人在直接的审美观照中产生瞬间直觉,或者说,兴会总是在天人合一的审美感兴中应运而生。
很多当代学者认为中国诗重表现,这一看法含混,至少摆脱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成见。而从王夫之的即景会心和情景妙合等诗学原则看,中国诗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其三,能动性或创造性。能动性主要表现为诗人的创造性想象、深远广大的胸襟怀抱和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中把握风神思理(或风韵神理)的能力。前面说过,神理并非神妙之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而是神(人之神)与理(物之理、诗之理或思之理)的沟通和合。神理通常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与诗的情景妙合的意境中呈现出来。
王夫之认为,心乃性之灵天之则,耳目止于闻见,而心之神彻于六合,周于百世,无灵心即无妙悟。在他看来,“心理所谐,景自与逢,即目成吟,无非然者,正此以见深人之致。”(《古诗评选》卷五)“真有关心,不忧其不能感物。”(《明诗评选》卷六),由此可见,心灵不仅制约诗意,而且决定着诗人感物、兴会、传神的能力。
“因云宛转,与风回合,总以灵府为逵径,绝不从文字问津渡。宜乎迄今两千年,人间了无知音。”(《古诗评选》卷一)王夫之对曹丕诗《秋胡行》的这段评语甚妙,把诗人兴会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一语道破。
王夫之常用“天巧”、“天授”、“天才”、“灵心”和“灵通”等词语赞赏诗人的伟大创造。兴会是创造性直觉的体现,也是大家(雅人、深人和天才)之作的前提。他在评谢灵运诗《游南亭》时说:“天壤之景物,作者之心目如是,灵心巧手,磕着即凑,岂复烦其踌躇哉?”(《古诗评选》卷五)可见,大诗人不仅有通天尽人之怀,而且有追光蹑景之笔,在“灵心巧手,磕着即凑”的兴会中,达成出神入化的艺术创造。
其四,言与意的统一性。很多普通人并不缺乏触景生情的审美感兴的能力,但缺乏兴会(或灵感),即便他们偶有兴会,也言不尽意。而真正的诗人在兴会时则可以达成言与意的统一。
王夫之常用寓目吟成和即目成吟等词语强调言与意(或意象)的统一。在他看来,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景尽意止,意尽言息,必不强括狂搜,舍有而寻无。在章成章,在句成句”(《唐诗评选》卷三)。在兴会的情境中,意不枝,词不荡,曲折而无痕,意、景、言三者妙合。
言与意的统一的最高境界是意在言外,意伏象外。换句话说,言与意的统一的充分体现是意境的生成。王夫之继承了“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境生于象外”(刘禹锡)和“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的古代诗学传统,他不仅多次以“言有象外,有环中”和“境语蕴藉”之类的术语评诗,而且在很多精彩的评语中把这个问题导向深远广大。
王夫之说:“‘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后,从容涵咏,自然生其气象。”(《姜斋诗话·诗译》)这话乍看起来有些玄奥,其实主要是指诗以从容涵咏达到意在言外、气象万千的效果,形成波势平远(或“咫尺有万里之势”)的意境。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王夫之对崔颢诗《长干曲》《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所作的评价:”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姜斋诗话·夕堂永目绪论内编》)这句话强调诗歌意境的深远广大的艺术空间。可以说,崔颢这首从开头到结尾都蕴藉生动的诗言有尽而意无穷,即:意在言先,亦在言中,又在言后。
总之,在人之里,兴会是物我合一的情境中言与意统一的瞬间直觉。这一看法,常在晚近的文艺家那里不约而同地得到印证。如拜伦、兰波和叔本华等人都曾强调灵感产生于物我合一的情境。法国作家戈蒂耶(1811—1872)要求诗人掌握一种高超的形式技巧,他认为,正是那种不容易达到的形式技巧赋予诗人以新奇而持久不衰的灵感(注:参看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王国维认为,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人间词话》),诗人能感之且能写之(镌诸不朽之文字)。
兴会的言与意统一的特征在诗人那里常常体现为即兴创作。禅宗言悟有顿悟、渐悟之分,作诗有“快吟”与“苦吟”之说(如苏轼主张诗与书法当由作者冲口而出,纵手而成)。王夫之显然推崇“顿悟”和“快吟”,这个看法主要是针对历代颓靡的诗风和僵化的诗学观念而言的,即便在一般意义上,这个看法也符合中国诗的艺术特性。
四、兴会说的理论阐释:现量
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说:“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这段话强调诗应来自即景会心的瞬间直觉,诗不是思想先行(“拟议”)和预设定景的产物(注:英国诗人柯尔律治曾指出,具有“最高度、最严格意义上的想象力”的华兹华斯,有时在幻想的运用上显然是“预先研究的产物,而非自然的流露”。参看R.L.布鲁特《论幻想和想象》,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而应该是在直接的审美观照中情景相生、自然灵妙的体现。对此,王夫之用“现量”来加以概括。
“现量”本是古代印度因明学中的术语(注:被大乘佛教列为印度五明这一的因明是关于推理、论证、知识和智慧的古代学问。“量”指知识,分为“现量”和“比量”。现量是由感官和对象接触所产生的知识。比量就是推理。参看沈剑英《因明学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社,第1—7页。),王夫之在研究佛教相宗义理的专著《相宗络索》中把“三量(现量、比量和非量)列为一章。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学养远非一般文人所能及。他把“现量”引进诗学领域,用来说明审美观照、艺术直觉(包括兴会)和诗歌创作的特性。(注:当代学者早已对王夫之的“现量”说加以高度评价。例如:刘畅认为,王夫之的“现量”说,有针对性地对传统理论加以矫正和改造,使之更加完备,丰富了我国的美学遗产。(《王船山“现量”说对传统艺术直觉诗论的改造》,《江汉论坛》,1984年第10期)叶朗认为,“现量”说是王夫之美学思想中最深刻的内容,也是王夫之在美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464页。)。
我们先看王夫之对“现量”的解释:
“‘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比量’,比者,以种种事,比度种种理。以相似比同,如以牛比兔,同是兽类;或以不相似比异,如以牛有角,比兔无角,遂得确信。比量于理无谬,而本等实相原不待比。此纯以意计分别而生。……‘非量’,情有理无之妄想,执为我所,坚自印持,遂觉有此一量,若可凭可证。”(《相宗络索·三量》)“禅家有三量,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审,便入非量。”(《姜斋诗话·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由此看来,“现量”有三层涵义。一是“现在”义,即:现量是由目前的直接感知而得,不依赖回忆;二是“现成”义,即:现量是由瞬间的直觉而得,不需要概念、判断、推理等抽象思维方式的介入;三是“显现真实”义,即:现量是对人情物理(或宇宙人生之道)的体悟。而比量则属于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的抽象思维方式;至于非量,纯属非理性的胡思乱想(或偏执的“妄想”)。三量之中,“唯现量发光,为依佛性”,唯现量与诗性相通。
在王夫之那里,“现量”可谓兴会说的理论阐释。从现量的三层涵义看,兴会具有“现在”、“现成和“显现真实”这三种特性:其一,兴会是物我合一的直接审美感兴;其二,兴会是瞬间直觉;其三,兴会是对人情物理(或神理)的审美观照或艺术表现。
现量,不仅是对兴会说的理论阐释,而且是诗歌批评的标准。例如:“只写现量,不可及。”(《明诗评选》卷一石宝《长相思》评语)“清婉则唐人多能之,一结弘深,唐人之问津者寡矣。‘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论者以为独绝,非也;……‘逾’‘更’二字,斧凿露尽,未免拙工之巧;拟之于禅,非、比二量语,所摄非现量也。”(《古诗评选》卷六王籍《入若耶溪》评语)从这类评语看,作为批评标准的现量,与兴会基础上是同义语。
“现量”在佛家哲学中原指主体由对事物的直接感知而获得的知识,具有直观或直觉思维的特性。经过王夫之的改造,“现量”成为诗学范畴,是指诗人即景会心、富于洞见(显现真实)的审美直觉。与严羽的“妙悟”说相比,“现量”说至少具有三个优点,一是强调审美直觉的客观来源(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对天地万物直接的审美感兴);二是强调审美直觉的三个层面,比以往的直觉论更明确、深刻;系统;三是既把直觉与经生之理(或名言之理)区别开,又强调直觉的理性内涵或超理性特征。因此,王夫之的现量说(或兴会说)代表着中国古代诗学在这个领域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