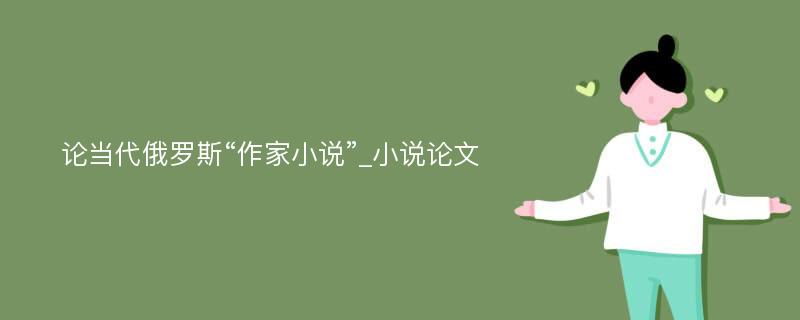
谈当代俄罗斯“作者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当代论文,作者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俄罗斯文学的发展画面异彩纷呈。有人将它形容为一幅光谱 ,五光十色,绚丽生动。要想在这缤纷的画面中寻找统一的原则几乎是无望的。然而, 近年来一种有趣的文学现象正在悄然形成,它能够把不同作家的众多作品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所谓的“作者小说”。
“作者小说”这个概念是针对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指的是主人公对于作 者-创造者的自主性、独立性退居后位,而作者的主观性获得了重要意义。这种小说表 面看来与自传体小说十分相似,同样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主人公同样具有作者的面貌 ——年龄,创作天才,甚至有非常相近的个人经历。但是这个主人公又不完全等同于现 实中的作者,而只是在心灵上、在存在状态上与之接近。这个主人公具有特殊的自传性 ,正如列·金兹伯格所说,是作者的“心灵自传”:作者赋予他以自己的精神结构,通 过他来展现自己的个性和可能的命运,以反省自我和时代。
当然,这种以展现自己的精神个性与主观世界为主旨的作品并不是文学史上的新现象 。著名文学理论家尤·洛特曼在上个世纪就曾经指出:“起源于卢梭的那种把自我本身 变成观察人类的实验室的要求,一方面促进了自传性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莱蒙托夫, 赫尔岑,托尔斯泰),另一方面又激起作家对个人经历进行无情试验的强烈渴望。”(注 :尤·洛特曼,《论文选》,第3卷,塔林,1992,第376页。)在苏联六十年代的“抒 情散文”中,作者——创作主体——的主观性成了作品完整性的源头,而六十年代文学 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流派“青年自白小说”,则建立在作者与主人公同一的幻想上。与此 同时,传统心理小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作者主观性的增强使俄罗斯评论界提出了 “作者小说”这个概念(注:“作者小说”这一概念是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娜·伊万诺娃 提出来的。她在1983年第3期的《文学问题》杂志上发表《自由的呼吸》一文,文中在 分析当时的小说状况时,指出文坛上“……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了两种新的流派:即‘ 幻想小说’和抒情散文的新形式,我们姑且称之为‘作者小说’”,这种小说“拒绝鲜 明的情节性,拒绝对于情节的传统理解,拒绝小说人物,总之,拒绝一切经过了检验的 美学特征……转而寻找新的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作家们好像为了伦理而拒绝美学, 为了在读者面前公开独白、袒露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而拒绝职业化的小说样式。”), 以概括作为叙述抒情形式一个变种的那类作品。
那么,这种源起六十年代的文学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得到广泛的发展呢?这与九十年代的 社会状况是分不开的。首先,苏联解体后原有的书刊检查制度被废止,在文学发展史上 可以说从此开始了一个质量更新的时代,一个当代文学流派和苏联时代未实现的文学体 系并存(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存)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往往是需要自我评价的时代 ;第二,世纪末刺激产生了一种决赛潮流,决定了这个时期是一个总结的时代,是作家 和文学对整个百年进行反省的时代。所以,九十年代的文学成了一面聚焦时代的历史问 题、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的透镜;第三,九十年代同二十年代一样,作家开始在新的、 极其混乱的历史空间中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对他来说,又一个鲍·艾亨鲍姆所说的“ 认知时刻”(注:鲍·艾亨鲍姆,《文学的日常生活》,载论文集《关于文学》,莫斯 科,1987,第430页。)到来了。应当指出,自我认知——这不仅是当代思潮,而且是俄 罗斯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尤·洛特曼认为,在俄罗斯文化特征中自我评价起着非同寻 常的作用:“与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相比,对自我的看法对于俄罗斯文化是首要的和基础 性的。”(注:尤·洛特曼,《尤·洛特曼和塔尔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莫斯科 ,1994,第407页。)正是由于世纪之交的自然感觉,由于八十至九十年代社会和文化的 巨大变迁,俄罗斯文学重又点燃自我认知的激情与冲动。
从老一辈“四十岁一代”(注:“四十岁一代”,指的是苏联七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一批 相当有才华的作家,他们成名时的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而作品主人公的年龄也大都在 四十岁左右,因此他们被称为“四十岁一代。”)作家的著名代表弗拉基米尔·马卡宁( 一九三七—)到年轻的当代俄罗斯文坛奇才奥列格·帕夫洛夫(一九七○—),都创作过 “作者小说”这类作品。颇为巧合的是,九十年代“作者小说”的作者中有许多都出生 于六十年代“解冻时期”,比如弗拉基米尔·别列津(一九六六—)、米哈伊尔·布托夫 (一九六四—)、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一九六五—)等,他们在停滞年代长大成人,这 样的年代与其说对他们产生了诱惑,不如说是激起了他们的怀疑。他们没有前辈天生的 动力,而是静静地等待重建天地,没有任何起伏动荡(只有个别例外)就平稳地进入了当 代文学的行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的面貌。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忧郁,还 有令人奇怪的消沉和虚弱。比起积极的行动来,他们对消极的旁观更感兴趣。他们的节 奏——中速;他们的思想——反省;他们的精神——讽刺;他们的呼声——可他们没有 呼喊……
他们具有精巧的文笔,也就是说他们毫不费力地就跨越了通往形式道路上的障碍。但 是他们并不总能找到写作的内容,这与他们不够丰富深厚的生活经验有关。作为天生的 坚定的性格内向者,他们准备永远仔仔细细分析自己主观感受的角角落落,轻视(可能 是不由自主地)客观存在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现实对于他们来说是别人的,这使他 们的作品具有了唯我主义的倾向。
当代“作者小说”的主要作品有:弗·马卡宁的《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一九九八) 、弗·别列津的《见证人》(一九九八)、安·乌特金的《自学者们》(一九九八)、米· 布托夫的《自由》(一九九九)、阿·瓦尔拉莫夫的《圆顶》(一九九九)、安·德米特里 耶夫的《合上的书》(一九九九)、安·科罗温的《暖房里的风》(一九九九)、玛·帕列 伊的《兰奇》(二○○○年)等。下面我们将以其中一些作品为依据,谈谈当代“作者小 说”的特点。
一、主人公——现实生活的见证人,而非参与者
阅读“作者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在具有传统现实主义客观小说结构的同时, 把世界想象为个人-个性意识的氛围,艺术家或者特殊个性被赋予了在艺术中无边的权 利。因此,“作者小说”主人公的存在成了一种诗化的存在,而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存 在:他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没有个人家庭。对于现实生活,他更像一个见证 人,而非参与者。
《地下人,或当代英雄》是马卡宁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评论界认为它标志 着马卡宁创作的最高峰。小说由一个年过半百、早已搁笔的作家关于时代和自己的独白 构成。主人公彼得洛维奇是一个没有成就的文学家,他在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后的时代 过着可怜的生活,没有住房,无以为生,沦为了一名公寓看守人。他和地下艺术家们交 往,和形形色色得意或者失意的女人苟合,还时常到精神病院看望自己的弟弟。为了找 回自己的尊严,他曾经两次杀人,后终因无法承受内心的压力而发疯,步弟弟的后尘被 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院里,他作为谋杀嫌疑犯经历了许多艰难的测试,却最终没有说 出真相。于是主人公又回到自己门卫的角色中去了。所有这些变故,都伴随着主人公对 时代和自己的深刻反省。
彼得洛维奇是无名氏的代表,同时也代表着每个人。在他的地位上连名和姓都显得多 余,于是作者故意略去了他的姓名,只称他“彼得洛维奇”——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父称 。他居无定所,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奇特的职业:看门。如果谁长期旅游或出差在外, 家中无人看管,他就住在谁家,替别人照看房屋。由于清高,他又是一个没有发表过一 部作品的作家:在苏联时代,他因不愿媚上而成为“受迫害的有才华的作家”;苏联解 体后,他又因不愿媚俗依然没有出书。因此彼得洛维奇就像无业游民一样,到处流浪, 过着卑微贫寒的生活,由此也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有知识分子,有流氓醉鬼 ,有精神病人,有在哪儿都无所适从的失败者,有高加索摊贩,有苏联解体后“新俄罗 斯人”。总之,特殊的职业角色使主人公成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见证人。
在“斯米尔诺夫-布克奖”一九九九年的获奖作品《自由》中,主人公“我”干脆断绝 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我”曾经工作过,先是在一个隶属于戏剧创作协会的编辑部里 整理出版戏剧教科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而被辞退,后又在教会里负责出版神学经典书 籍。“我”一直很想逃避周围的世界,于是把一个去往南极考察的好友的房子变成了自 己的隐居之地。“我”用最后一笔收入买了些罐头、香烟等日用品,把余款兑换成美元 ,就过上了孤独的生活。终日阅读思考,与昆虫为伴,一连几星期都不打开门。主人公 “我”好像从自己身上一层层地扔掉虚假的表皮,追求“赤裸裸”的实质。就像苦行僧 去到沙漠,期望找到边界,发现事物的实质。如果说看门人“彼得洛维奇”是见证他人 的生活,那么,离群索居的“我”又要见证什么呢?见证“自己”,见证退出了一切角 色之后的自由与孤独。这种退出一切角色之后的自由既是“我”的自由,也是每个人的 自由。因此,见证“我”的自由,也就是见证每个人的自由。所以,与其说《自由》是 一部作品,不如说是一次退出角色、面对自由、见证自由的自我试验。而弗·别列津直 接把自己小说的题目定为《见证人》。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将军,主人公无论如何也 不能忘记过去,他不明白现实,也不想参与其中,只好做一个被迫的观察者和见证人。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与异性的关系是很有特色的。女人在主人公的 视野中时隐时现,时而重要,时而无足轻重。在《自由》中,叙述者一方面好像抱怨与 他交往的女人不能舍弃依赖她的丈夫,另一方面,他并不怎么在意自己这个第三者的角 色,而当他们的关系最终了断的时候,他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小说《圆顶》中的叙述者 似乎在宣布着这种关系对个人命运的重要性。数学系大学生疯狂爱上语文系一个傻里傻 气的女人,并为了她而参与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游戏,结果他不仅被开除出学校,而且被 流放(在克格勃的监督下)到外省小城。到了流放地之后,他似乎一下子从火热的爱情、 从置身其中的生活中退身出来,以一种与生活不相干或者至少是有距离的身份出现,以 致那狂热的爱情还未曾褪色,他就很快和一个姑娘结成了令双方都很痛苦的关系,好像 那有过的爱情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几年之后,他回到莫斯科,遇到了初恋姑娘,他 们很快就结婚了。但是,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后,妻子忽然弃他而去,出国了。主人公 对于这样的事似乎也带着一种释然。对于主人公来说,发生这些事,就像在大街上瞥见 了一缕一闪而过的秀发,或者闻到了一丝漠然的芳香,虽然与你近在咫尺,甚至千丝万 缕围绕在你周围,却又与你毫无干系。
他们爱过这些女人吗?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物形象按照其逻辑就不被允许有完整 的情感。他们囿于自我的旁观者身份,除了自己的忧郁,他们似乎没有能力,也没时间 去爱什么。当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对自己怎么办的时候,女人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女人 就是现实世界!女人是他们与现实世界联系的一个直接通道。开始时,他们和她们不协 调。他们准备和她们和解,可这必须是在一定的距离内——让她们去做别人的妻子,而 他们则通过她们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却又不陷入现实世界。一句话,通过女人来 保持他们的旁观者身份。但女人是骨头和血肉做成的,她们需要的不是他们怀疑主义的 嘲笑,这种情感比生活本身更吓坏了她们。在和她们的关系中,他们不能永远都做一个 见证人和旁观者。和她们在一起就必须做一个参与者,必须选择自己,确定自己。女人 无法忍受不确定,和女人在一起就必须做一个男人,而不是具有不确定特性的男孩。可 是这些人物的旁观者状态阻碍他们成为男人。当然,这里指的不是性,而是理解现实、 参与现实的心理状态与存在选择。
这些人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不想要孩子,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想告别永远的童 年,还要孩子做什么?!他们总是倾向于非存在,而延续生命是与之对立的。这些人物对 世界充满怀疑,他们无法确定自我,确定自己的命运。他们就像温室里的植物,也像奥 勃洛莫夫的后人。他们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什么都不想要。他们异常弱小,没有保护; 却又十分强大,无坚不摧。他们是小人物:“我们是个子很小的勇敢的英雄”。他们害 怕现实,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表白自己。
二、“自我认知”——主人公一生的寻求
纳博科夫在《天赐》中说对上帝的寻找就像“任何狗对主人的思念”一样:“给我一 个主人吧,我会对他俯首帖耳的”。嘲讽归嘲讽,现代人的感受正像被逐出家门的狗, 无论怎样叫都无济于事。现代人意识到在世界的边界之外什么也看不到之后,忽然觉得 自己短暂地来到这个世界的毫无意义。“作者小说”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安排成一个现实 生活的旁观者,就是为了让他完成一个重大使命——寻找存在的意义,认识自我,确定 自我。他之所以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家庭,就是为了转向自我,转向自己内心深 处的“我”,在人的赤裸裸的本质基础上进行“自我认知”,因而思考成了这些主人公 的存在状态。主人公自愿遁入个人意识的世界中,成为一个绝对拥有主权的形象,能够 和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感受到作者的感受——在一个非理想的世界中对理想的思念 。这些主人公或者叙述者常常是作家、诗人或者艺术家。他们天性喜欢创作,内心世界 复杂,有着强烈的生活渴求和不断的反省精神。他们对于自己的个人生活描写甚少,却 更多地说明自己的个性。他们好像完全适应浪漫主义时代的精神,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 的东西,他们的诗化性格表现为能够理解普通事物中被掩盖的非同寻常的本质。
正如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在这种小说的底层是“某种形而上的忧伤和心灵的痛苦,俄 罗斯人的忧郁”。(注:伊·苏希赫,《声音。关于作家这个职业》,载《星》1994年 第3期,第186页。)是的,“自我认知”的道路是痛苦的,往往伴随着孤独、疑惑,甚 至是悲观、厌世。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作者小说”的主人公,与世界、与自己 的不和谐都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出路的。在《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主人公彼得洛 维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他的精神有时富有,有时堆满垃圾。他的行为永远无法捉 摸。他无所不知,懂得人以及人所有隐秘的欲望——因此许多人都在需要的时候找他聊 天,却对一切都失望透顶。他宣扬各种各样的真理,却又是一个十足的怀疑论者。他对 自己、对周围世界完全不满意,充满了渴望和忧患,他的生活由无聊的讨论和意想不到 的磨难组成。他就是这样一个情绪恶劣、神经有病、被生活折磨透了的单身厌世者。
正如《圆顶》的主人公所说:“也许我本来就属于那种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感觉不好的人。”主人公“我”生于苏联时代,在小说结尾时,也就是当他步入老年 时,成了生活在西方某个国家的侨民。可以说,在精神上他是一生都没有归宿的“侨民 ”。主人公从童年起就对周围世界充满了怀疑。作为数学天才,他轻松地考入莫斯科大 学数学系。在别人眼里,他将沿着硕士-博士-教授这条坦途走下去,其实他在内心里却 一直找不到人生的目标和信仰,对现实常常不满。他在讨论课上提出了与当局不同的政 治观点,又在宿舍等处张贴标语,终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赶出了大学校园,在克格勃的 监视下回到了家乡。苏联解体后,他作为极权制度牺牲品的代表、反克格勃的英雄而一 夜之间成了名人。在一段出入名流、喧哗热闹的日子过后,他引以为骄傲的历史不再受 人重视,他重又开始了冷清、穷困的生活。在一个越南朋友的帮助下他一夜暴富。这个 时候,在故乡突然出现了一座类似教堂圆顶的建筑,这里成了一块圣地,它在人们心目 中的位置不亚于珠穆朗玛峰之于中国。由于“我”是对这个圆顶研究最深的人,“我” 被作为俄罗斯难民引渡到西方。然而“我”在西方的日子并不好过。
主人公的一生都在寻找精神归宿,可是他没有在现实世界中找到,无论在自己的祖国 还是在西方。主人公不爱自己的故乡,也不爱他寄居的土地,他心中的美好世界在幻想 中的“圆顶”。“因为在地球上我们总是怪人,我们真正的故乡在那个没有阴谋、没有 对阴谋的恐惧、没有欺骗、没有杀人、没有痛苦、忧患和罪恶的地方。”
《圆顶》中主人公的思想探求反映了当今一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在经历 了国家巨变之后,他们开始反思历史,反思革命,反思在人间建立天国般国度的企图与 努力。他们在这种反思中走向绝对孤独,并在绝对孤独中开始面对上帝,打开在人世间 之外的另一种希望,另一种生活,认为只有在那里才是一片没有谎言、没有罪恶的纯净 之地。这类作品实际上重新回到了对基督教关于两个世界和两个人生的历史-生活观念 的阐释,即我们生活于人世间,而我们的最后希望在别处。
三、自由——主人公思考的主题
在“作者小说”中,与“自我认知”不可分割的一个主题就是自由。《自由》这部小 说直接从题目上就道出了主人公思索的中心。他从各个角度思考自由问题,也尝试用多 种方式(包括隐居)来获得真正的自由,但都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自由。而《地下人,或当 代英雄》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但惟独不能放弃的就是他的自由。你可以 对他进行任何谴责,就是不能说他没有个性,他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为之而付出了巨大代 价的原因,都来自于他在自由中展开的个性,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那个永不屈服的大 写的“我”(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大写的“我”字)。什么是“大写的我”?“大写的我 ”也就是“大我”。
这个“大我”之所以是个“大我”,就在于它是自由的,并永远保持和维护在自由中 ,“我”的每个社会角色(比如作家、商人、克格勃)都只不过是从自由的“大我”中自 由选择而开展出来的一个“小我”。人们通常说,“我”是个作家,我是个看门人。这 种通常意义上的“我”都是“小我”。每个人可以有许多个角色,因而可以有许多个“ 小我”。但是,不管一个人有多少个角色和多少个“小我”,它们的叠加也构成不出一 个“大我”。因为“大我”是自由的,它永远可能展开出更多的角色,更多的“小我” 。这就是“大我”之大的所在。如果说“小我”是相对的,可替代的,那么“大我”则 是绝对的:这指的是他的自由是绝对的,不可剥夺的,因而他的尊严也是绝对的。维护 “大我”也就是维护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反过来说也一样。
彼得洛维奇两次杀人,就是为了维护“大我”的尊严(我们得承认,作者的这种安排是 一种极端的试验)。第一次是彼得洛维奇认为一个高加索商贩侮辱了他,于是他在一个 夜晚约商贩出来,趁其不备用刀子刺入商贩的心脏。第二次彼得洛维奇与一帮地下艺术 家们畅所欲言,大骂那些“为了名声、荣誉和饱日子而离开地下的人”,后来他发现有 个克格勃分子混入其中,正在对这些谈话进行录音,于是他又用刀子杀死了这个密探。
彼得洛维奇的一切都服从于他的自由。为了维护他的完全自由,他显然不能有固定的 职业和住所。所以,他的无住所不仅是他作为底层人被迫的生存状态,而且是他作为一 个自由的人的生存状态。“地下人”的生存方式也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底层——是彼得洛维奇表面的生存状态,而“地下人”——则是他的灵魂身份。他(也 是每个人)必须保持着这种“地下人”的状态,否则他就无法独立自主和坚持自我。实 际上,“地下人”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大我”,即“自由的我”或守护于自由中的每个 人。每个人都有两个身份:地上的和地下的。如果说人的各种堂而皇之的社会角色,公 开行走在各个角落的一个个“小我”,是他在地上的、也是表面的身份的话,那么,退 出一切角色而守护在自由中的“大我”则是他的地下身份。“地下人”之所以也被称为 英雄,就在于他们是自由的真正守护者与坚定信仰者。他们在一个特殊年代里以特殊方 式承担起了守护自由的使命。所以,他们是自己时代的英雄。因为在这个人世间,还有 什么人比坚定地守护自由的人更有资格被称为英雄呢?小说的主人公真是想怎么活,就 怎么活。他不想担负持久的角色责任,不想亲近任何人。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他的被 诊断为患有精神病的弟弟。弟弟维尼亚曾经是个天才画家,他搞的是先锋派艺术,不被 当局容忍,历经克格勃的多次逮捕和审问,他都坚决不低下高贵的头,结果成了精神病 院永久的住户。弟弟被彼得洛维奇认为是惟一光明的象征,是他惟一可以袒露心扉,也 惟一可以随时为之服务的人。因为弟弟永远都生活在对童年的回忆之中,生活在由艺术 所维护的自由与尊严的世界里。所以当彼得洛维奇思考弟弟的现实遭遇时,他反倒认为 如果弟弟因在审讯时打了审问者而被送入监狱更好,那样就会逃脱更为可怕的事情。于 是,他从这个痛苦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不惜以杀人来捍卫自由。这反映了马卡宁经 常在作品中表露的一个极端的观点,即社会生活总是无情地消灭、损害、摧残着个性, 使之同化,不给它任何机会,而个性应当是永远自由的。于是马卡宁赋予了新主人公没 有限度的自由。
在“作者小说”中我们看到,它急于回答时代的主要问题,寻找对当代世界的新看法 。“作者小说”提出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作为“被意识到的自我”的个性概念,这种小 说的结构中心是作者个性的自由展开,他的自我意识的自然表达。通过自己的“我”重 建世界的原则,使得作家赋予了抒情-主观性结构的传统形式以不可重复的新特点。
当代“作者小说”的兴起表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拥有了绝对的创作自由, 他们呈现给读者的不再是要经得起意识形态上考验的作品,而是没有被制约、被刻意遮 蔽的自己,是在艺术空间里被展示出来的真实的存在状态——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艺术 的真理。“作者小说”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可以用布拉特·奥库扎瓦的话来表述:“… …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呼吸一样,不去努力迎合什么。”任何迎合——不管这种迎合是媚 俗,还是附势;也不管这种迎合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都必定妨碍艺术的自由,从 而妨碍艺术揭示真实存在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迎合都是对艺术所要展示的真实 存在的遮蔽。艺术的真理不是通过概念把握到的客观属性,而是在自由想像中展现的可 能性生活与可能性存在。因此,没有自由,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有艺术真理,而对自由的 任何限制,则意味着让艺术远离真理。因此,当“作者小说”的作者们获得了无需迎合 的自由并自觉到这种自由后,文学也就从“生活的教科书”变成了生活与存在的实验室 ,从直白的反映变成了对真实的可能生活的展示。也许我们可以说,“作者小说”因自 由而更接近了艺术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