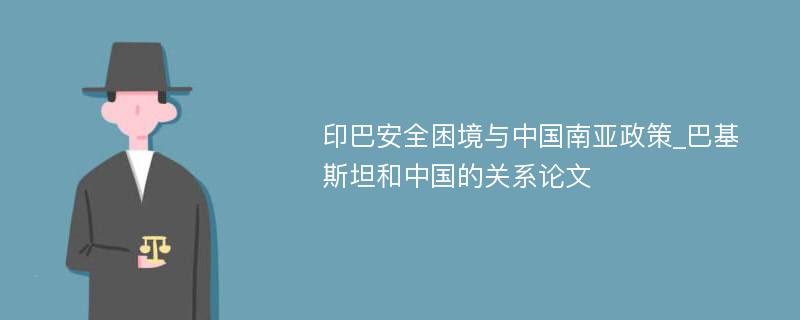
印巴安全两难与中国的南亚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亚论文,中国论文,印巴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两难作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产物,包含着敌意和紧张滋生的逻辑必然性,并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难免升级为对抗或冲突。在南亚,印巴关系提供了安全两难的一个典型范例,突出地表现在立国理念、外交战略、克什米尔问题和核竞赛等问题上。印巴安全两难导致两国外交政策行为模式化,并强烈地表现为主要依据长期的“回忆”来塑造设想中的未来双边关系,并在这一框架内发展两国间短期关系,结果使得印巴双边外交关系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互动:对冲突的记忆是长期的,合作则是短期的。印巴安全两难还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面临一种复杂的形势,呈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即中印安全两难和中巴友好合作。其中,中印安全两难突出地反映在边界争端、核问题和世界强国竞争三个方面。在21世纪,如何使中国的南亚外交政策更好地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中国大战略的需要,是理论界和外交界不得不予以回答的重大课题。当前,建立信任措施、相互核威慑和加深经贸往来有助于缓解安全两难,但最根本的途径还在于加速培育和推动建立包括印巴在内的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和次区域安全体制。
印巴安全两难及其外交政策行为模式
在南亚,印巴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敌对,提供了安全两难的一个典型范例。印巴安全两难情势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所提出的建国理念及其政治实践上的矛盾与冲突。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典型代表的国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梦想以大印度“联邦”的形式全盘继承英帝国留下的“遗产”,认为穆斯林联盟所主张的“伊斯兰国家根本就不是国家”而是“一种宗教上的联系”,在大印度国家内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在经济上是不可思议的”,它意味着“现有意义下的国家不得发展”。(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年,第57页。)相反,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则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这两种文明大体上是建立在相互冲突的思想观念上”(注:G.阿拉纳:《伟大的领袖真纳——一个民族的经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4页。)。据此他们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即印度教徒组成印度民族、印度的穆斯林组成穆斯林民族,并要求把英属印度分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1944年3月23日,真纳在纪念巴基斯坦日的文告中表示:“印度穆斯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巴基斯坦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解放、我们的命运。”1947年8月,英属印度实现了分治。表面上,印巴分治实现了和平建国的目标,但“这是一个带来很大动荡的分治。它影响到我所说的边界这一侧的心理状态,使人们进一步认为印度不甘心巴基斯坦建国。”(注:Janes Defense Weekly,25 Nov.,1998.)50年后巴基斯坦外长的一席谈说明,从一开始巴基斯坦就受到一个很大的敌对邻国的困扰。尼赫鲁也曾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具有不可能实现的神权概念的中世纪国家。它不应该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国人支持真纳的愚见,这件事决不会发生……总有一天合并必然会到来。”(注:引自姜兆鸿、杨平学主编:《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结果,早期有关“统”、“分”之争最终发展定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对立。
分治造成的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注:分治后,在南亚地区400多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印度拥有297.47万平方公里,占南亚地区总面积的70%以上,是南亚其他国家面积之和的2.7倍。在资源分布上,次大陆绝大部分资源集中在印度一国。印度可耕地面积约为1.66亿公倾,占本地区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3%;重要的矿产资源如铁矿、煤、铝土矿等也几乎全部集中在印度。在开发印度洋资源方面,印度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海岸线长达7500公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给印度增加了2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几乎相当于其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二。)也加深了印巴两国之间的安全疑惧和战略对抗。无论是在地理结构上还是在人力、军力、国力方面,南亚都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和占有绝对优势的地区。此外,从中长期看,印度尤其具有不可轻视的发展潜力和成为世界大国的良好前景。鉴于印度庞大的权势基值(居于世界第7位的地理规模、第2位的人口规模和位居世界前列的资源规模),印度领导人视跻身世界强国为理所当然的事(注:早在独立之前,尼赫鲁就这样勾画印度的未来:“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见《印度的发现》,第57页。),并把不结盟作为印度的大战略选择。安全上,印度认为次大陆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实体,它的稳定与安全对印度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而且认为在次大陆内部,对印度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不仅本身对印度进行挑战,而且还引入外部势力对抗印度。这也就是说,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都是对印度安全的挑战。所以,在不结盟的旗号下,“印度强烈反对对任何南亚国家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抱有损害印度利益企图的外部大国的干涉。因此,南亚国家不应寻求区外国家的援助,如果真正需要外部援助,则应向印度求助。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印度。”(注:巴巴尼·古普塔:“印度的理由”,《今日印度》,1983年8月31日。转引自孙士海主编:《南亚的政治、国家关系及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页。)
对巴基斯坦来说,1947年的分治是其“两个民族”理论的重大胜利,但同时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致命的威胁。与印度相比,分治后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更加险恶。地理上,巴基斯坦处于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汇处,且其国土在1971年之前被印度分隔为两部分。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巴基斯坦更易遭受外部的攻击,国内安全与稳定也易受外部世界各种变化的影响而出现问题。印强巴弱的力量结构决定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印度的致命威胁。结果,巴基斯坦对印度一种本能的恐惧和对自身安全的严重忧虑一直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显然,改变地区力量结构性失衡是巴基斯坦政治领袖们梦寐以求的,但问题是仅凭自身的力量巴基斯坦根本无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于是,唯一的可能性便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联盟战略来达到这一目的。无疑,这必将激起印度的强烈反应。早在50年代,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指出:“无论如何,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本质上是基于它对印度的敌意。”(注:海南:“印度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世界知识》,1958年第2期,第24页。)应当指出,巴基斯坦选择联盟战略是对恐惧的本能反应,是地区力量失衡的必然结果。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生存,其本质是防御性的。
随着分治而出现的克什米尔问题充分表证了印巴上述战略上的对立。克什米尔问题不仅涉及两国的民族感情,关乎两国的立国理念,更主要的是它关系到印巴两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在印度看来,没有克什米尔,印度就不会在中亚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地区,它也就切断了巴基斯坦与外部大国的陆上联系,从而排除了外部大国势力涉足南亚安全体系的核心而危及自身安全的可能性;巴基斯坦则认为,如果它允许印度夺取克什米尔,那就意味着巴基斯坦将永远受印度的摆布。用真纳的话说,印度图谋克什米尔表明印度一心要消灭他所建立的国家。立国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无不视克什米尔为其生命线。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印度和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都志在必得。
印巴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还突出地表现为紧张的军事对峙和核军备竞赛。长期以来,印巴两国在安全上一直互视为敌人和威胁。据此,在兵力部署上,印度始终将其陆海空军总兵力的近1/2部署在印巴边境一线和毗邻巴基斯坦的海域,形成对巴基斯坦的绝对军事优势,保持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态势;巴基斯坦也以印度为主要作战对象,针对性地实施全力对付印度的积极防御战略,将陆军70%的兵力集中在东部边境地区与印度对抗,并针对印军加强各项战备活动。
印巴军备竞赛不仅在常规领域进行,还扩展到核领域。作为对印度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及其核政策的直接反应,以及出于对本国军事弱势日益增加的担心,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也表达了对核威慑的需要。1965年布托总理宣称:“如果印度制造核武器,我们即使是吃草和树叶、甚至是挨饿也要有自己的核武器。我们别无选择。”(注:Dawn,Nov.21,1965.)印度1974年核试验成为巴基斯坦加速核武器研究的重大促进因素。布托总理说:“巴基斯坦将永不屈从于印度的核讹诈。巴基斯坦人民也永不会接受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霸权或者是优越地位。”(注:Dawn,May 20.1974.)冷战时期,印度和巴基斯坦都通过模糊核威慑相互对抗。1998年5月印度公开走向核武化后,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巴基斯坦随后也进行核试验。印巴公开走向核武化强化了双方的军事对峙态势,南亚安全形势也遽然紧张。虽然两国在1991年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核设施的协议,两国总理在1999年的《拉合尔宣言》中也同意加强对核武器的控制和建立信任措施,以减少意外使用或未经授权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但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核武器的期望值严重偏差,(注:印度在核试验后称核武器是政治工具,它不具备实战价值,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但在巴基斯坦看来,1998年5月的印巴核试验成为地区形势演变的里程碑,认为从核力量的角度讲,印巴目前获得了某种地缘战略的平衡,并基于印巴两国间在常规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的现状,为保持核报复能力,主张不能放弃“首先使用”原则。)“次大陆目前的形势使得核(武器)实际使用的风险很高”。(注:Survival,winter 1998-1999.)
印巴之间上述严重的安全两难使得两国外交政策行为模式化,强烈地表现为主要依据长期的“回忆”来塑造设想中的未来双边关系,并在这一框架内发展两国间短期关系。(注:Sheen Rajmaira,Indio-Pakistani Relations:Reciprocity in Long-term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1,no.3,September 1997.)作为地区性竞争对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决策者不像超级大国那样关注的范围如此之大。它们很少关心双边外交产生的国际反应,而是主要关注各自外交政策在南亚地区产生的作用。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关心自己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在双边关系中,它们主要寻求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自1947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两国之间三次战争表明相互间紧张竞争和冲突达到了顶点,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彼此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而且官方关系都基于“一方获益、一方受损”的零和思想。在两国关系中,不存在持久的、长时期的合作。两国都基本上把合作行动看成是短期的事情。合作作为一种短期的现象也就不会产生长时期的渐进影响。这表明印巴双边外交关系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互动:对冲突的记忆是长期的,合作则是短期的。
这样,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冲突和合作作为互不关联的外交政策行为模式。这意味着在两国间通过合作来消除冲突的努力不可能获得成功。当然,在一些与克什米尔相比显得并不重要的问题上,例如文化交流、反对毒品走私和非法偷渡等,印巴两国可能开展合作。但在克什米尔这样导致持续冲突的问题上,双边就无法开展有效和可行的合作。就巴基斯坦而言,它更加愿意改变上述“冲突是长期的、合作是短期的”恒态,希望通过快速改变自己的冲突行为来重建一种希望中的新的外交行为模式;对更强大的印度来说,不愿意与巴基斯坦就很快建立一种新的外交行为模式采取主动,它甚至可能不愿与较弱的巴基斯坦减少冲突和进行合作;而巴基斯坦可能愿与印度就减少冲突方面达成协议,但鉴于力量的不对称性,它可能不愿增进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它们激烈竞争的领域,以防止受益的不对称。于是,有助于缓解印巴安全两难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85年12月,虽然包括印巴在内的南亚国家就建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达成一致,但由于南盟规定不得审议双边的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短视的政策实际上使得多边合作机制无法限制南亚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并使之稳定下来,也就不可能建立一种信任措施,缓解安全两难。
中印安全两难与中国南亚政策
在论及印巴关系时,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西藏问题,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印巴核试验……似乎无一不与中国有关。中国作为印巴的邻国,历来重视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但以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1963年中巴签署边界条约为重大标志,中国南亚政策就其内涵来说开始出现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中印严重的安全两难和中巴持久的友好合作,而且中国二元化的南亚政策又不可避免地与印巴安全两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结果虽有始于80年代的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但中国南亚政策依然呈现出二元化特征。
中国的南亚政策中,中印安全两难最为明显,并首先表现在边界问题上。
1947年英国势力退出印度后,印度政府不仅继承了英印政府在中国西藏的侵略特权,而且继承了英印政府的安全战略,把控制中国西藏作为确保其北部边界安全的核心环节。当中国解放西藏时,印度曾一度采取反对和阻挠的态度。但面对西藏和平解放的现实,尼赫鲁政府决定通过在外交上推行对华友好的政策来换取中国政府对印度所主张的(注:内维尔·马克斯维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印)《政治与经济》周刊,1999年4月10日。中文译文见《南亚研究》2001年第1-2期。)以及已非法占领的大片中国领土的承认。对此,一位历史学家深刻地指出:“尼赫鲁在1949年革命后决定与北京发展关系,不是出于他的罗曼蒂克,而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的安全需要他这样做。”(注:Durga Das,India:from Curzon to Nehru and After(Rupa,New Delhi,1981),p360.)尼赫鲁曾指出:“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第一次面对面地隔着一条长长的边界,而且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边界。如果我们是朋友,即使是那样,我们还是有一个存在争论的、危险的边界;如果我们不是朋友,那就更糟了。”(注:Yaacov Y.L.Vertzberger,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TheSino-India Conflict,1959-1962(Westview Press,Colo.),p66.)1959年12月9日,尼赫鲁在议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表示了他对“中国威胁”的强烈担心:“即使我们百分之百地同他们友好,事情仍然是这样: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我们的边境上,这种情况本身改变了整个局势。”(注:《国际问题译丛》1959年第22期,第11页。)安全疑惧加之领土野心促使印度在外交上推行对华友好政策的同时,军事上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结果在1962年挑起了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并遭到失败。
1962年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加剧了中印安全两难。自此,安全问题完全主宰了印度对华政策。到英·甘地出任总理时,她还在宣称,把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说成单纯的争端,那是过于简单化的说法。“无论从当时或随后的发展来看,……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推断,边界争端是一项更为复杂的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旨在破坏印度的稳定,阻碍它迅速而循序前进。”(注:克里尚·巴蒂亚:《英迪拉·甘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甚至30多年后,印度政府的立场还依然如故。1998年3月,在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中,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虽承认最近10年左右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持续存在。这个国家还从物质上帮助我们的另一个邻国成为秘密的核武器国家,从而加速了这种不信任。”
所以,在1962年之后,印度早期强调和平共处的观念被军事准备所取代。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那种印度必须在地缘政治环境中保持对华军事平衡的观点突现出来,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在边界问题上,中国认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1959年5月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印度把边界问题拖下去的真正意图是想把中国的西藏地区变成一个“缓冲国”(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68-276页。)。这显然明示:中国也决不会容许自己的安全受到印度的威胁。
中印安全两难还表现在核问题上。当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印度进一步渲染“中国威胁”,并一改和平核政策,公开宣称印度要确保核武器选择权。出于战略考虑,印度不接受在与中国的核对比中永远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印度朝野一些人士认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印度虽然已经具备同中国在常规武器上的“平衡”,然而面对拥有战略核武器的中国,在常规武器上的平衡充其量只能使印度对其潜在对手具有采取“劝阻”姿态的能力。只有在印度拥有核导弹时,印度才能对中国采取“慑止”姿态,其“最大的好处是在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时,中国的核弹不再能使我们屈从于不利地位”(注:(印)《战略分析》,1990年6月号。)。
世界强国竞争是中印安全两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冷战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注:下述两段论述见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势、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强国的发展演变历程表明,在当代及可预见的未来,世界强国的规模条件已急剧提高。(注: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Four Centuries of European Power Struggle(New York,1962).参见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1987).)换言之,要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流角色,必须在具备先进的技术水平和现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之外,有足够大的“权势基值”,即接近或居于世界前列的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规模。显然,具有这种规模条件的国家,世界上除了美国和中国外,还有俄罗斯、印度,或者还有其他极个别国家。显然,21世纪的世界强国地位可以说是一种最稀有的价值,而在新的世界强国之候选国中,将只有一两个能够取得这种地位。故冷战后国际政治理论界和外交思想界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便是:在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美国之外,可能的新兴强国中哪一个将最先成为世界强国?毋庸讳言,主要归因于中国作为洲际大国的规模条件和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中国被相当广泛地认为是21世纪新的世界强国的头号候选者,至少现在和在可以明确预见的未来时间里是如此。至于印度,就疆域、人口和自然资源而言,其与中国不相上下;就科学技术潜力、经济发展潜力而言,印度也不逊于中国;不仅如此,印度还具有若干远较中国优越的、据以发挥其潜力的重要素质: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大量精通英语的人口以及因之而拥有的向西方学习的天然优势。
世界强国地位是一种最稀有的价值,竞争这一地位的最终结果一般总是非此即彼,落选者将处于比先前更加被动、更受压抑的境地。有鉴于此,作为两个都有世界强国抱负和潜力且又是近邻的亚洲大国,中印之间世界强国的战略竞争将日趋激烈。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印度的反应将会更加激烈。印度防务问题分析家苏布拉马尼姆就曾说:“如果你(印度)拥有能够威慑中国的核武器和导弹,并且能够加强经济实力和扩大同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贸易,这就是同越来越强大的中国抗衡的一个途径。”(注:路透社新德里1997年7月6日电。)实际上,冷战后印度的大战略实施基本上反映了上述观点。当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时,与中国坚决反对的立场完全相反,印度明确表示支持,其制衡中国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
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为推动中印巴关系的良性互动而努力。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与包括印巴在内的所有南亚国家的关系,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基础;其次,在影响印巴关系的核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一贯是不介入印巴之间的争议,不偏袒任何一方,希望它们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一争端;再次,中国政府对发展与印度的关系是真诚的、积极的,希望并强调边界问题不应妨碍双边关系的发展;第四,中国一贯反对“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外交模式。在积极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独立的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欢迎印巴之间任何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举措。但是,中国的努力没能产生积极的效果,根本原因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严重的安全两难和中印安全两难。独立伊始,印度就把次大陆内任何国家的“联盟”战略视为对其安全的挑战;在中印关系方面,印度也一直把安全问题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结果使中印关系不时出现波折,有时甚至是严重的倒退。无疑,印巴间严重的安全两难直接影响了印度对中印巴关系特别是中巴关系的观点和立场。在中印巴关系问题上,印度始终没有摆脱旧的战略思维,把安全问题作为评判三边关系特别是中巴关系的重要尺码,结果使得“中国威胁论”成了印度在看待中印巴关系时的一种“自然反应”,进而也就影响了中印巴关系的良性互动。
无须讳言,正是由于印巴安全两难和中印安全两难的相互影响,中国的南亚政策还有诸多有待解决的紧迫课题:(1)不管愿意与否,也不管真实性多大,中国实际上已经卷入南亚安全体系之中(在印度看来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中国对南亚安全事务几乎没有明确的、可行的建设性倡议,以缓解印巴安全两难,从而促使中印安全两难缓解,增加中国外交回旋的余地;(2)中印关系无疑是中国南亚外交的重要方面。但从大战略角度看,中印关系又不应仅仅从南亚区域来考量。换言之,在中国积极推进多极化的外交战略中,印度作为制衡霸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如何在21世纪把中印关系置于一个适当的基点上,使之既有助于中国大战略的展开,同时又不至于严重偏离中国南亚政策的轨道,将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3)中国和巴基斯坦作为近邻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但由于中印巴关系缺少良性互动,中巴合作关系无疑使印度感到担忧;同样,中国寻求改善、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又将使巴基斯坦不放心。如何突破安全框架,加深经贸领域的合作,以拓展中巴关系的基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冷战结束后,三个主要因素对未来中印关系、印巴关系十分重要。第一,双边拓展信任措施的努力。这包括印巴之间的《拉合尔宣言》,中印之间中印边境联合工作小组和军事、外交、专家谈判小组等对话机制,1993年9月正式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议》和1996年11月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建立信任措施不仅有利于安全与稳定,而且可以培育竞争双方对长期合作的记忆,从而为长期冲突的解决奠定基础;第二,核武器的扩散无疑增加了安全的变数,但作为一种威慑工具,核武器具有明显的防御属性。这样,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攻势政策得不偿失。根据前面的分析,这对缓解安全两难是有利的;第三,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有助于增加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从而缓解安全两难。当然,中国的南亚政策仍将受制于上面论说的安全两难的困扰。正因为如此,加速培育和推动建立包括印巴在内的东亚区域安全体制和次区域安全体制,才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标签: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论文; 印巴战争论文; 中印战争论文; 中国巴基斯坦论文; 印巴冲突论文; 中印冲突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军事论文; 中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