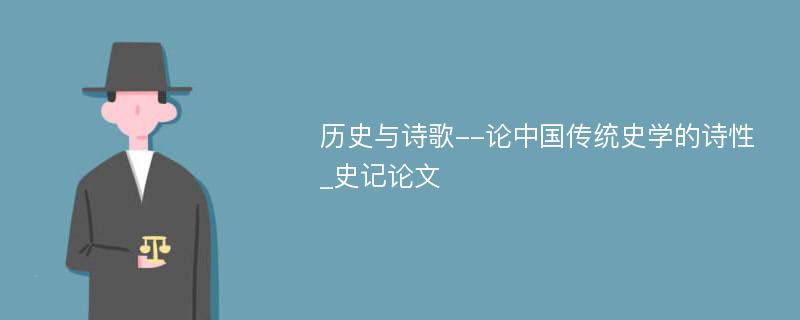
史与诗——论中国传统史学的诗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的诗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文化在诗学及美学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一些特点,在史学批评中也有反映。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一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
“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注:刘知几:《史通·叙事》。),我们先看叙事:传统史学叙事的典范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即《左传》中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注:《左传》成公十四年;另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晋杜预《左传·正义序》,对此作了解释:
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例,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言高则旨远,辞约则义微,此理之常。
钱钟书认为这五例“乃古人作史时心向神往之楷模,殚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从史学实践来说,“春秋笔法”未必能概括传统史学叙事的全部特点,但从史家观念倾向看,此说并不为过。钱钟书还指出“五例之一、二、三、四示载笔之体,而其五示载笔之用”,全都十分合于传统诗学对诗笔的要求,“言史笔几与言诗笔莫辨”(《管锥编·左传正义》)。他还引用杨万里《诚斋诗话》(注:杨万里:《诚斋诗话》:“太史公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左氏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此《诗》与《春秋》记事之妙也。”)中的例子,提出了“史蕴诗心”的命题。
《史通·叙事》一篇被钱钟书看作此五例的发挥:
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能损之又损,而玄之又玄。……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晦之时义,不亦大哉!
刘知几“简”、“晦”两点,亦是论史如论诗。诗之尚简自不待言,至于“晦”,纪昀《史通削繁》谓“即彦和隐秀之旨”,直视其为诗学评论中的重要范畴:《文心雕龙》中的“隐”(注:《管锥编·左传正义》袭此说;另汪荣祖《史传通说》:微而显者,乃“义生文外,秘响旁通”(此据《文心雕龙·隐秀》),其雅之谓也。)。在叙事上对史笔作与诗笔相似的要求,是传统史学诗性的首要体现。
但若仅仅说明史笔与诗笔类似,就仍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史笔必须吸收诗笔的部分特性,只是说史文需要文学语言修饰,此早是史家常谈,本文不论。我们必须更进一步,考究一下言辞表象背后的东西。
其实“简”、“晦”两点,细究之似颇不合于今人治史之常识。史据实而书,事略则省,事繁则详。辞约事举,固然可喜,文详可稽,更谓有功。就史料价值而言,只怕还是宁详毋略,宁繁毋省。如何能一味尚简?而在传统史学中,不仅《史通·叙事》一篇,证诸“史汉比较”话题中的史笔“繁简”之争,尚简派明显处于攻势,如张辅(《晋书·张辅传》)、张守节(《史记集解序注》)等人,大多不讲如何如何须简,而直接得出“简就是好”的结论;而论繁的,却往往处于申辩的地位,竭力证明自己主观并不求繁,之所以繁,实是史文之需。可见尚简是古代不少学人论学的前提假设,一种理论本能。假如在现代史学观念下,这种“繁简”之争本身就很难成立。至于“晦”,于今人更是不可理解。史之记事,自当力求明尽,如何能“晦”?
“简”与“晦”其实都是史笔的一种自我否定,是减法。无疑,就史学自身而言是很难得出这种要求的,这种特性来自诗的感染。只有在诗的语境中,才能得以理解。
作史贵知其意
中国传统诗学与哲学常纠缠于一个命题:言意之辩。对汉语这种模糊语言,古人的基本态度是求“言外之意”,主“得意忘言”。我们或许也可以讲,与传统诗论中老生常谈的“省文取意”说一样,在传统史学中,史笔不求详尽显豁,不突出自己,反而要否定自己,要凸显的正是“言外之意”,体现的态度正是“得意忘言”。
上引杜预文云:“辞约则义微”,《孔子世家》曰:“(《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司马迁也有体会:“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史记索隐》注:“谓其意隐微而言约也”。范晔亦说:“(《后汉书》)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所以,言辞简约与意旨深微是有联系的。范晔还说:“文患事尽于形”,因为作文“当以意为主”(注:见《宋书·范晔传》载《狱中与诸甥侄书》。此类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见之于诗文,见之于声乐,见之于书画,见之于人物品藻,甚至见之于律法(如《晋书·陶侃传》: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本文准之于史,于史文、史事外求史意。)。可见史之用晦(事不尽于形),也是以“史意”论而非以史文论。上文引刘知几论“晦”:“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说的正是“言不尽意”。浦起龙释:“晦者神余象表。……神余者唯以神行,几几无言可说矣。”(《史通通释》)说的则是“得意(神)忘言”了。
作史如此,读史亦当如是,即吴乘权说的那种读法:“读时不求甚解,会心在牝牡骊黄之外”(《纲鉴易知录》序)。程余庆也说:“以意逆志……此真千古说诗之法也,亦即千古说史之法也”。他举《史记》为例:
《史记》一书,有言所及而意亦及者,有言所不及而意已及者;有正言之而意实反者,有反言之而意实正者;又有言在此而意则起于彼,言已尽而意仍缠绵而无穷者。错综迷离之中而神理寓焉,是非求诸言语文字之外,而欲寻章摘句以得之,难矣!(《史记集说序》)
可见,正是对“意”的重视,导致对“言”的忽视,以致要求“言”自觉简化、隐退。约其言而损其体,是为了去其障,而至其虚,得其意。推而广之,传统史学批评中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倾向:不仅对语言,而且对“史意”之外的任何形而下的东西都有一种达观的、通融和有意的忽视。章学诚就曾说:
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史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例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注:《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书》,可参照严羽《沧浪诗话》:“诗者……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章学诚这里讲的,主要指“作史贵知其意”,非“仅求于事文之末”(《文史通义·言公上》)。不知“史意”的,均谈不上“史学”。而得“史意”的,哪怕像郑樵那样只是“稍有志于义”,就纵使“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文史通义·申郑》),都可以从宽发落。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史意”范畴作一个初步的梳理。史意有时也写作“史义”,这时大多指史的惩恶劝善之义,即上述“春秋五例”的第五例。孟子当初讲“事、文、义”,也是指这种褒贬之义;但“史意”一置于“言意之辩”的语境中,便有另一层意思。我们上文所引诸例中的“言外之意”的史意,就不止只是这伦理层面,似已超越善而至于美。徐复观曾解释诗中的“言有尽而意有余”现象:
意有余之“意”,决不是“意义”之意,而是“意味”之意。“意义”之意,是以某种明确的意识为其内容;而“意味”之意,则并不包含某种明确意识,而只是流动着的一片感情的朦胧飘渺的情调。(注:见徐氏:《中国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114页。 其实也有在意义层面索求“言外之意”。历代解诗,向来不乏索隐附会,深文周纳,甚至穿凿罗织,搞点文字狱的。但这可以不加理会。)
徐复观是论诗,其实于史亦然。这里虽然不是像诗的领域里那么明显,但也有些言论会透露消息。像《伊川春秋传·自序》讲:“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前半句的“义”指有确实内容的“意义”,而后半句的“意”则只能是指形上的意味,较明确地分成两个层次。在《文史通义》中的具体言述中,“史意”的两层意思是经常混用,但整体上来说,章学诚较多地以“意味”论史,可谓是古代最有灵性的史家。钱钟书说章学诚论史如袁枚论诗(注:参考《谈艺录·章实斋与随园》。),这是很得神韵的一个评价。宋衡《别求是书院诸生》诗云:“论史无如章氏美,(谈经最是戴君高)”,在我们看来,这个“美”字用得很有意思。《文史通义·书教下》有一段极精彩的话:
《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这段话往往被解读成“记注”指史料汇编,“撰述”则是对史料剪裁加工后的撰著。更有下者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史例划分法,这就完全死于句下,索然无味了。其实不尽然。史例的划分总是明确、谨严的。如刘知几言“史法”,“二体六家”是经典集合,何书归于何类,毫不含糊,是谓“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史通·序例》)。而章学诚讲“史意”,“撰述”、“记注”是很宽泛的划分,是模糊集合,至于“圆神”、“方智”之说,更是神来之笔,未可仅于字句中求解。章学诚曾说《汉书》“于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圆且神者”,又批评后世族史“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史例的划分当非此即彼,而在章看来,《汉书》是亦此亦彼,族史是非此非彼。章还说:
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记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应智,多得官礼之意也。(《文史通义·书教下》)
就体例而言,《史记》和《汉书》同属纪传体,《左传》属编年体,所以《史记》近同《汉书》,而远异《左传》。但以章学诚看来,《史记》得《尚书》之遗意,而中介为《左传》,所以《史记》与《左传》相近,而与《汉书》远。《史记》与《汉书》是“貌同心异”,与《左传》却是“貌异心同”。可见,史分方圆,非形貌之别,乃质性神智之殊,拿现代的术语勉强讲,“圆神方智”不只是历史编纂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哲学领域的。这种现象其实在诗论中很常见,如钱钟书的“诗分唐宋”,“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注:钱钟书:《谈艺录·诗分唐宋》。有关“高明”、“沉潜”之说,《文史通义·答客问中》:“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王国维论词,主“在神不在貌”;章学诚自己论诗时也主张要以情质为准,不可拘于形貌(《文史通义·诗教下》)。总之,以“意味”论而非以“意义”论。
史可以兴
“史意”范畴的引入,清楚地表明了传统史学的诗性不仅是“修饰性”而且是“结构性”(借用柯林武德的话)。史笔与诗笔不只在“言”层面上相似,更是在“意”层面上相契。古人尚有把史笔与书画作比的,也许更能说明这一点。如: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争,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注:刘熙载《艺概·史概》。)
“《唐书》如近世许道宁辈画山水,是真画也。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而心服者,有笔墨之外。”(注:王楙《野客丛书》附录《野老纪闻》。)
史笔与书画作比,史籍于言辞,书画凭借笔墨。两者能比较的地方,自是在言辞之外,“笔墨之外”。反观史笔与诗笔,亦当如是。
这样一种类比,就其思维模式而言,是一种意会直觉,是一种带诗性神秘的“体悟”。史意在第一层面上(意义)可以言说、教导,而在第二层面上(意味)只能感染、体悟。“非识无以断其意”(《文史通义·史德》),章学诚曾把史识解释成悟性(注:《文史通义·答沈枫樨论学》。)。他先“圆神”而后“方智”,即是尚神悟而薄智度,“神以知来,即人之悟性”(注: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七。)。诗道在妙悟,史道亦在妙悟。是以我们或可以用这样一个命题来描述诗对史的结构性阑入:史可以兴。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淮南子·汎论训》)。诗亡而后春秋作。诗之义,春秋窃取之。“诗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论语·阳货》)。诗如此,史亦如此。“经传宜独坐读,史鉴宜与友共读”(张潮《幽梦影》)。故曰:史可以群:《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阙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史记》本身更是太史公受辱后的“谤书”,故曰:史可以怨。下面讲讲“史可以兴”。
“诗可以兴”的含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孔子这句话中的“兴”与“兴于诗,立于礼”(《论语·泰伯》)的“兴”同义,指诗的美刺讽谕功能。但以诗为教化,有“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特点,这启发人们解诗时不必拘于言辞,而可以有更广泛的体悟。道德心理相通于审美心理。于是“诗可以兴”的含义后来进一步发展,逐渐也指诗有“文已尽而意有余”(注:钟嵘《诗品序》。)的审美效果,能兴起、感发人的某种哲理义蕴(不止是伦理意旨),包含意象、意韵、意旨、意境、神韵、境界等等。
这里,“以诗为教化”的诗学功能观,体现了传统文化美善合一的追求。“兴”的涵义的发展,较突出表明了经“善”的体认而至于“美”的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以“美善合一”为特点,向己求善,自诚而自得,自主而自由。仁之境界便是乐之境界,善之境界便是美之境界。而完整人格又由“内圣外王”两方面构成。这些特点在现代学者的诗学与哲学研究中,都有了详尽的梳理。反观史学研究中,在“善”的层面上,传统史学凸显史的伦理教化功能;在“经世”路向上,传统史学强调史为政道资鉴,这些也都已是史界常谈。那么我们可否追问,在“美”的层面上,在“内圣”的路向上,传统史学又有那些特点,这些特点又多大程度上是与传统诗学和哲学相契合呢?
所以我们讲“史可以兴”,虽然首先也指“以史为教化”的史学功能观,史之褒贬有类于诗之美刺;但我们还可指出,史笔的“文见于此,而义归于彼”,“虽发语已殚,而舍意未尽”,同样也能像诗一样,兴起、感发人的某种哲理义蕴,使人们在品评史籍、认识历史时,也像在说诗论诗一样说史论史。在这一层意义上,对“史意”这一范畴,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就相当于诗论中的意境、神韵、境界等等。
“史可以兴”其实是一个可以从《文史通义》中勾划出的观点。章学诚有“易之象通诗之兴”的说法,诗学界早已有人论及。而由此可推出“史可以兴”的结论,史界前贤似未曾留意。从《文史通义》相关各篇中我们可以体察出章学诚的思路大致如下:
《易》立象尽意,系辞尽言。言辞止乎于是,指陈有限;象意该括无穷,遗味悠远。言有尽而意有余。辞与象之间,若诗之兴。而史之事与理,亦如易之象与辞,诗之言与意。事有实据(注:《文史通义·经解中》“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记注有成法(注:《文史通义·书教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是以春秋之体,谨严不可假借,通于礼之官(注:《文史通义·易教下》“礼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谨严而不可假借矣”。),易之辞,见于周官法废(注:《文史通义·书教上》“周官法废而书亡,见春秋之体也”。);理无定形,故撰述无定名,是以春秋之用,变化不可方物,通易之象,诗之兴,见于诗之亡(注:《文史通义·书教上》“王者迹息而诗亡,见春秋之用”。)。故曰:史可以兴。明诗之兴,方可论史(注:《文史通义·史德》“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史记》便是深于诗者(注:《文史通义·史德》“骚与史,皆深与诗者也”。)。
史可以观
诗可以观。郑玄注:“观风俗盛衰”(注:何晏《论语集解》。)。朱熹《四书集注》释“观”为“考见得失”。这与“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资治通鉴进书表》),是允当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史可以观。
但我们这里说“史可以观”,和讲“史可以兴”一样,不是仅局限于形下的政教伦理层面。古人采诗观政,把诗歌、音乐与天下之政化、历史之兴衰拉扯在一起,这和前所例举的把史笔与诗笔、书画拉扯在一起,从思维模式上说是同出于一的。所以上文提到古代史家的比类直觉、诗性神悟,不仅体现在史学理论中,也体现在历史理论中。司马迁把音乐的历史演变与三代秦汉之间邦兴国覆的比类,已为人熟知。其实,《史记》的礼、乐、律、历四书之间(《汉书》把礼乐合为一志、律历合为一志),“礼乐合一”(《礼记·乐记》),“律历融通”(《礼记·月令》)。比附会通、融为一体,体现了古人一体化的时空意识。这种时空观既见之于诗,更见之与史。它要求人们对“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天地之道,要从整体上去体悟,在流观中意会。这种“玄览”(注:史事证补也要“玄想”,如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所说“百世之上,时异事殊。故曰:古之人与事不可传者丛矣。所贵乎心知其意也”,这是就具体史事的想象,与我们这里讲的对整体大历史的“玄观”完全不同。),即我们讲的“观”。
史可以观。非观史之形也,观史之神也。是“观天之神道”(《易经·彖传》)。上文尝论及传统史学对言辞、史例等有一种通达的忽视(“忘”),其实古人不仅以此种观念对待历史文本,亦以此对待历史本体;不仅在史文外求史意,亦主在史事外求史意。方东美曾指出中国古人的宇宙观,是“一个将有限形体点化成无穷空灵妙用的系统”,从而把历史理解成普遍生命创造不息的大化流行(注:方东美:《中国人的宇宙论的精义》,载于《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即是此义。
就此说来,传统史学的“通史家风”,是不能仅于形下层面去理解的。章学诚、郑樵等人对通史的论述,不少是过誉之辞,像“同天下之文”、“极古今之变”(《通志·序》),“通天下之志”(《文史通义·释通》)等夸张的笔调中流露的是一种神秘色彩。周谷城对此有体会,他曾说中国往日所谓通史,有一极玄之含义,与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无关(注: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于《周谷城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通史之一般含义, 或与断代史相反,或与专史相对。而通史这种极玄之含义,所谓“纲纪天人”,是对历史终极意义上的把握。“通”者不蔽不滞,是一种无限观念,由无限来设定有限,其实便意味着对具体史事的“忘”。犹如庖丁解牛,初时所见无非牛者,而后“神遇而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游刃有余,可谓之“通”。
我们还可以证之于诗。汉民族缺乏叙事史诗,但独有咏史诗一类体裁(注:周一良:《周昙咏史诗中的北朝》中称“中国的咏史诗恐怕在西方找不到相对应的体裁”。载于《北朝研究》1989年第一期。),吊古怀旧之篇章甚富。而此类诗章,多半也不是叙事或描述,而代之以象征、暗示、抒情等手法,虚化眼前景象,幻化所咏史事。这很好地说明在我民族文化心理中,历史的诗性意识是超越具体史事的。
进一步说,不仅咏史诗,汉语古诗的整体特征就是对物物关系未定、浑然不分的自然现象保持通融达观的态度,不去分解、串联、剖析,而设法保持人们刚接触物象时的模糊感受,以求直接兴发人的某种哲理性感悟,从而生成所谓的意境、境界等。同样,传统史学也不仅仅在于保存某些历史事实,提供某些历史借鉴;更不大对历史作直线式的焦点透视,没有企图把历史的经验世界纳入某个逻辑框架中,以建构某种规律模式,而是力求引导人们在曲线式的流观中,超越历史的经验层面,去直接体悟某种终极性的精神意境,表达一种对历史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许思园有言:“我先民之于历史,不仅视作前言往行之真实记录,亦不仅资为当前之借鉴,实欲藉历史以通故今之情,传古今为一体”(注: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资鉴只是史有形之用,谈功用是对于客体而言,重心在外,而对史之本体的“观”,是无待乎外的。
史可以观。非以目观,而以心观。目观是向外的,懂一点是一点;而心观是内向的,是一种带诗的神秘的艺术体悟。明人邹元标在给一本从书名到内容都标新立异的史论随笔《千百年眼》作序时说:“夫目之所贵者清虚灵爽,晴虽贵也,着云则翳。古有天眼、道眼、慧眼、法眼,超于形体外,不以一切言语文字求”(注:张燧:《千百年眼》序。)。这里所谓“天眼、道眼、慧眼、法眼”,大概和杜甫《春日江村》诗中:“乾坤万里眼,百年时序心”的“万里眼”一样,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用眼。杜诗后句的“时序心”倒是一个妙词。只有用心,“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才能“观古今之须臾”(陆机《文赋》),才能“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官建置》)。宋人曾道:
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邵雍《观物内篇》)
如古初去今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便到那里;下面方来又不知是几千万年,若此念才发,也便到那里。……虽千万里之远,千百世之上,一念才发,便到那里。(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八)
这便完全消弭了日常意义上的时间。而随时间一并淡出的是件件具体的史事。只有在内心体验中,自我观之,游心于物,古今才能无滞无碍,无不感通。这种内求于己的思路,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张立文曾说西方史学是“由求真而向外开出知识论”,中国史学是“由着意而向内开出心性论”,又说:
中国历史时空存在和历史形而上存在的解释,并非仅在求真,而是求真基础上的着意,即不是追求画的逼真,而是追求画的无限意境。这种意境能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咀嚼,带来无穷遐想和愉悦……给人以心灵的快感和享受,以及情感的陶冶。(注: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这段话受传统美学中“真”与“意”的辨证论影响很大,但移植到史学中,整体上的把握仍是很得个中滋味。
钱穆曾说:“中国史如一首诗”,“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一片琴韵悠扬”。又说“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和也”(注:《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13、25页。)。此论虽不免迹近理想,近乎天真,未必能准之以经验事实。我们也未可据此便认为传统史学的诗性特征与中国历史本身有关(当然也未必无关)。但重要的是此论表明:中国史在经验上未必是诗,但在观念上确有人认为她可以是诗。
本文立论主要在史学理论领域内,我们谈中国传统史学具有诗性精神,只是说古代史家存有这么一种观念,而不是对史家著述实践的总结。史学诗性标准的可行性是有限的。如上文所论的“春秋五例”,钱钟书就说它“虽以之品目《春秋》,而春秋实不足语此”(注:钱钟书:《管锥编·左传正义》。),《春秋》尚且如此,后世史书更不待言。浦起龙也曾说《史通》的“晦”“晦法入微,无文对举也”(《史通通释》)。又如章学诚的“圆禅方智”,圆神的,例不拘常,史家无从循其变化,不会其意,捧心效颦,难得其神;方智的,体有一定,史家不能出其规矩,以文徇例,削足适履,终失其智。以至入章学诚法眼的史书屈指可数,《书》、《春秋》、《史》、《汉》以下,仅《通鉴纪事本末》、《通志》差可一提。即便如此,他仍说《通鉴纪事本末》虽得《尚书》之遗意,“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文史通义·书教下》);说《通志》“立论高远,实不副名,疏陋过甚”(《文史通义·申郑》),“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文史通义·答邵二云书》)。章本人屡次想作史,终未下笔,虽有其他难处,眼高手低也是一个原因。其实即使作成了,也未必能使我们满意,甚至怕不能使他自己满意。诗界中人早已有言:“善论诗者不善作诗”,看来史也是这样。
然而,理论是有其独立价值的。传统诗论的首要价值就未必是指导创作。不能说诗性史学实践意义不大,就可以忽视它。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夸大史的诗性。历史学终究是离诗有一定距离的学科。诗可凿空,而史需质实。诗可不即于象,史必不离于事。史著不说,即使是史评,也不可能真的像诗那样只强调主体性,全然诉诸自我体验。所以本文只是揭示古代一部分史家中曾存有的那么一种观念而已,至于诗的精神于史是否合适,那是在本文论域之外了。
西方史学中有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争,本世纪以来,史学艺术说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在其影响下,近代中国的胡适、刘节、周谷城等都有关于史学艺术性的论述,张荫麟(注:见《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1928年3月第62期), 《历史之美学价值》(大公报1932年7月25日)等文。)、李絜非(注:见《历史学艺术论》一文,《东方杂志》1946年42卷18期。)等有论文,盖蕴刚有论文结集(注:《历史艺术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近年来,这一问题又重新得到史界关注。但本文所论,仅限于中国古代史学,而且没有采用“史学的艺术性”的说法,代之以“诗性”一词。因为我们认为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略举两例:与本文从语言入手论证史学的“诗性”类似,西方史学在语言哲学影响下,也曾从语言入手阐发历史学的艺术性。“语言学的转向”导致历史学作为科学的终结(注: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二期。)。主张历史叙述不可能反映历史真实,初看是类同于中国的“言不尽意”论。但其实不然,在这里西方史学是不断走向语言自身的,语言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特别像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那样,往往把史学理论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海登·怀特就认为历史论战纯粹是语言争论)。这与中国传统的“得意忘言”,语言淡出是南辕北辙、截然两途;又如,西方对科学历史学的另一反叛是史家纷纷放弃追寻所谓的“历史规律”。这好像和中国史学不求建构历史的逻辑框架相似。但其实,西方史学中历史哲学(思辩的历史哲学)向历史学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转化,除了认识对象从历史本身转向历史认识外,认识的两端,“主客观”仍是“紧张对待”(注: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中论科学艺术精神之差别。载《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以下。)的。 就此种外向的、智度的精神而言,与中国传统史学主张的神悟、向内体认、天人合一等依然是说不到一处去。
当然,如果非要在中国传统史学的话语体系中找出与西方史学“科学艺术”之争相对等的东西(这是许多人喜欢做的),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拿出章学诚的“圆神方智”。这本是一个很具开放性的概念,钱穆曾评说“实斋此论虽为史发,实可推之一切学术”(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38页。)。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诠释:“方智”是有序、谨严、明晰、“体有一定”,是智度,是“主客观之紧张对待”(注:唐君毅:《中西文化精神之比较》中论科学艺术精神之差别。载《唐君毅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 页以下。);“圆神”则是无序、模糊、混沌、“例不拘常”,是神悟,是“主客观之和谐融摄”。总之,“方智”是科学性,“圆神”是艺术性,它们一起构成人类思维的两大基本路径。置于这样解读中,中国传统史学的“诗性”精神应该能够得到更深的理解和更好的发扬。
